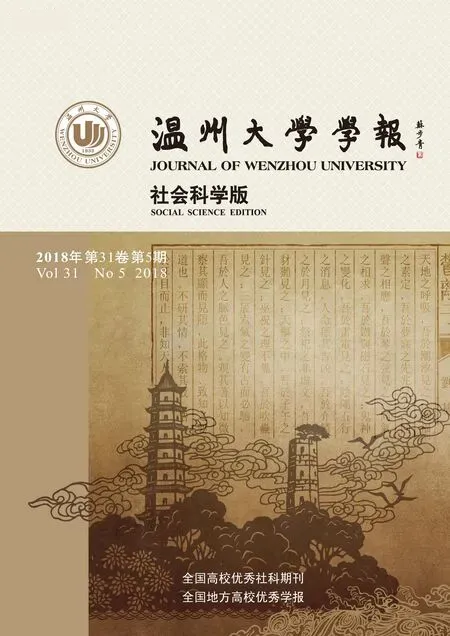从空间向度审视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身体规训机制
赖丹琪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07)
亨利·列斐伏尔在《在场与缺场》中对西方的二元对立哲学思维提出了质疑:“长期以来,反思性思想及哲学都注重二元关系。干与湿,大与小,有限与无限,这是古希腊贤哲的分类。接着出现了确立西方哲学范型的概念:主体——客体,连续性——非连续性,开放——封闭等。最后则有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能指与所指,知识与非知识,中心与边缘……(但)难道永远只是两个项之间的关系吗?始终有三项关系,始终存在他者。”[1]67列斐伏尔从而将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引入哲学思维。虽然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将空间性视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且与现代主义的时间性相区别的特征[2],但令人惊奇的是奥威尔早在1948年写作的小说《一九八四》就表现出对空间向度敏锐的感受。并且,小说中的空间建构不仅含有现实意义的物质空间,也含有抽象层面的理念、心理空间。虽然爱德华·索亚声称“与列斐伏尔不同,福柯自己的空间理论建构从未进入一种相当自觉的状态”[1]190,但他还是承认福柯对空间向度的重视:“每一个福柯式的学者都承认权力——知识的联系,但对福柯本人而言,这种关系植根于权力、知识和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之中,必须始终不要忘记这第三项。”[1]191在《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一文中,福柯提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①按照福柯的观点,规训(Discipline)则是权力运作的一整套技术学。在福柯的权力与规训理论中,规训身体——肉体是权力机制运行的方式。1975年问世的《规训与惩罚》集中体现了福柯对于权力的规训机制如何发展而来和规训如何成为一种肉体政治学的思考。而奥威尔则出于对极权主义社会反乌托邦式的忧虑,构建了一个充满恐怖氛围的“大洋国”社会。在其中,福柯哲学里的身体规训机制得到了极端化反映,并且这种机制始终与空间思维紧密联系。
一、《一九八四》中的“全景敞视”空间
《一九八四》中的空间不是一个完全物质性的空间,而是物质空间与心理空间的交叠,是一种全景敞视空间。它由无所不在的监视“电幕”以及充斥其间的“老大哥”形象,密布社会全方位渗透的“思想警察”,“友爱部”等各类监视机制组成。这个空间的特征与全景敞视建筑在权力运作上的特点有众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在于:监视中心在整个社会散布,而被监视者则无法确知监视中心是否在监视,一种权力和规训的自动化因而实现。
首先,在物质结构层面,在观看/被观看的机制中,《一九八四》中无处不在的“电幕”在监督者的隐秘性、监视的遍在性和全景性方面,具有全景敞视建筑的结构特点。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是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在18世纪末提出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3]244而福柯则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个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以强调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在权力运行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3]226在“大洋国”,“电幕”正是充当了不可见的监视中心的角色,每个密闭的房间则像一个个囚室。“党员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也永远无法确知自己是否的确是单独一人。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在睡觉还是在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受到监视,而且毫不知情。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的话、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受到严密考察。不端行为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不论多么细微的任何乖张古怪行为,任何习惯的变化,任何神经性习惯动作,凡是可以视为内心斗争的征象的,无不会受到察觉。”[4]189监视者观看一切却不会被观看到,“大洋国”正是一个典型的“全景敞视”空间。
其次,《一九八四》中的全景敞视空间的构造具有极权运作的目的。通过“电幕”和“思想警察”的全局渗透监察,整个政治空间呈现出全景敞视监狱的结构特征。在《一九八四》里,有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老大哥’在注视你。”[4]4这种“注视”——监视通过“电幕”完成。因而,小说中多次描写到温斯顿对“电幕”监视的恐惧。“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4]5正如福柯的观察,“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3]226-227它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3]231。因此,全景敞视模式使任何权力结构都强化了。
最后,必须注意到,《一九八四》中的全景敞视空间从物质层面过渡到心理、思想层面,可以称之为理念空间。“新话”中的“双重思想”“犯罪停止”便是规训机制从灵魂内部空间发生作用。如列斐伏尔所述,“……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s)。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①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奥威尔用不无讽刺的笔调描述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对思想空间的侵入过程:“凡是有危险思想出现的时候,自己的头脑里应该出现一片空白。这种过程应该是自动的,本能的。新话里叫犯罪停止。”[4]253思想的空间被挤压、清洗和变形,也成为全景敞视空间的组成部分。思想空间内的权力自动化正是《一九八四》的世界里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也正是奥威尔和福柯在思想上遥遥契合的地方。而这种权力的自动化又与对身体的规训机制密切相关。在这点上,奥威尔也以反乌托邦的具体构想呈现出福柯规训理论的世界图景。以下就进入对身体的规训机制如何在全景敞视空间内运行的探讨。
二、空间、身体与规训
首先,必须对本文中的“身体”概念作出界定。它包括了福柯哲学里作为权力规训对象的“肉体”,但又比之更有广延的涵义。它借鉴了叔本华哲学意义上“身体”的概念,即“……我的身体乃是那唯一的客体,即我不但认识其一面,表象的一面,而且还认识其第二面,叫做意志的那一面的客体。”[5]185“意志活动和身体的活动不是因果性的韧带联结起来的两个客观地认识到的不同的情况,不在因和果的关系中,却是二而一,是同一事物”;“身体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是客观化了的,亦即进入了直观的意志活动。”[5]151因而,本文中身体概念的多层次性与空间概念的多层次性相契合,即在肉体意义上,身体处于一定的物质空间范围内,而作为客观化了的意志,身体又无法与思想割裂而存在,因而它也存在于理念化的空间。福柯剖析权力运作之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着这种‘现实——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但是,我们不要产生误解,不要以为一种现实的人——认识、哲学思考或技术干预的对象——取代了神学家幻觉中的灵魂。人们向我们描述的人,让我们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3]32在一定意义上,福柯由之阐述的规训理论已经考虑到了在物质性的肉体上再加入权力介入的作用,因而“身体”的概念虽然没有直接明晰对应地出现,但是已经渗透在他对规训的技术剖析中。
“‘规训’既不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3]241-242而《一九八四》中的规训机制则是将身体控制在固定的物理空间、活动空间中,又通过权力的自动化使思想空间也遭受“双重思想”“犯罪停止”这些荒谬悖论的压制。它应和了福柯的洞察:“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3]160在“大洋国”,特定时间身体所处的空间都有强制规定:“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癖。”[4]74而每天早起时的体操则是一种监狱式的肉体规训。这种对肉体的操纵并非毫无理由,如福柯所分析,“在成为新的权力机制的目标时,肉体也被呈献给新的知识形式。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3]175
在“大洋国”,身体被安排在全景敞视空间里,被动接受权力的规训。虽然在福柯看来,这种规训是现实社会中权力的机制,但在《一九八四》的世界中,对身体的规训则更具强制性和自动化并存的特征。通过对身体各个时间段内必须被控制于哪种空间的规定,“党”得以维持其极权秩序。小说通过对富有政治狂欢化仪式色彩的“仇恨”的精彩描写,揭示出身体规训的空间性:“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空间的转移——从小办公室到大厅中央,为“仇恨”这一规训仪式提供了空间背景。“仇恨”中,人们需要对身体的生理活动进行控制,包括高声叫喊和控制表情,以表达正确的情绪。而这一身体规训之所以具有强制性和自动化并存的特质,如前已述,是由于空间的全景敞视特性:一方面,“电幕”、潜藏的“思想警察”和告发者,形成一个无形的监视中心,而被监视者则无法看见监视者的存在,这促使权力的自动化;另一方面,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政治狂欢仪式中,“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感情,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4]14特定的空间集聚使得“仇恨”具有仪式特征,因而对于身体规训的形式、技术胜过了规训内容本身。反过来,这种规训机制的效能则因其狂欢仪式特征侵入了被规训者的心理空间。
三、对规训的反抗与屈从
《一九八四》中极权式的身体规训遭到了温斯顿的厌恶与反抗,他的反抗主要是以身体在空间中的反叛来实现的。一方面,“大洋国”极权体制的特点使得身体规训处于权力运作的焦点;另一方面,温斯顿对规训的反抗只停留在物理空间层面,而“党”的身体规训的空间则包括前述的心理、理念空间层次。这解释了最后温斯顿对规训的屈从——奥威尔的反乌托邦预言正是表达出了这种忧虑感:极权的强制规训机制渗透入身体和思想空间内部,人被规训后便开始自我规训。
温斯顿对“党”的身体规训机制产生了抵抗,而这一抵抗正是首先通过身体对权力机制规定的空间范围的僭越得以实现的。“党”的空间是一种密闭封锁的空间:“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没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4]6作为与这种空间的对抗,温斯顿和裘莉亚将约会的地方选在无人的林中,以躲避无处不在的监控形成的类似闭锁空间。后来,他们又住在没有安装电幕的小房子里,同样是从“党”所渗透控制的物理空间中逃离出来。身体在物理意义和抽象意义上超越了权力规定的空间界限,奥威尔诗意表达了此种对于规训的反抗所得到的空间自由:“他转身对着光线,懒洋洋地看着玻璃镇纸。使人感到无限兴趣的不是那块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这么深,可是又像是空气一般透明。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他感到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铜板蚀刻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珊瑚是裘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4]133这个“玻璃”内的空间已经脱离了其物理性质,由于温斯顿片刻的思想自由,获得了一种反抗意味。
但温斯顿的反抗最终没有实现,小说以“他热爱老大哥”这样讽刺的句子结尾,表明了奥威尔对权力身体规训机制的清醒认识:“所谓权力乃是对人的权力,是对身体,尤其是对思想的权力,对物质——你们所说的外部现实——的权力并不重要。”[4]240“大洋国”的身体规训机制不是单纯的肉体规训,而是通过控制身体来囚禁其灵魂,通过对思想空间进行压制,剥夺其自由独立,从而实现整套权力机制的运行。温斯顿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不仅仅是由于他害怕老鼠这个生理性事实。奥威尔描述了他的心理过程:“但是他紧紧抱住一个念头,终于在黑暗中挣扎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唯一的办法,可以救自己。那就是必须在他和老鼠之间插进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来挡开。”[4]261“但是他突然明白,在整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人可以把惩罚转嫁上去——只有一个人的身体他可以把她插在他和老鼠之间。他一遍又一遍地拼命大叫:‘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你们怎样咬她都行。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裘莉亚!别咬我!’”[4]261-262。在此,身体规训机制之于灵魂内部空间的渗透充分显明,即便温斯顿曾反抗过,但外部的身体规训已经内化到内部思想空间。正是通过放弃裘莉亚的“身体”,使之抵挡在自己和自己恐惧的事物之间,温斯顿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屈服于权力机制所设定的空间。他的反抗之所以转变为屈从,正在于他仅仅是通过和裘莉亚肉体上的纵欲来得到一种对权力规定空间暂时性的逃离:“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己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4]114身体在此成了对抗的工具。但是“大洋国”的身体规训机制正如福柯所揭示的,不仅只是一种肉体政治学,而是“……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3]113因而这种身体在空间上的逃离一旦遭遇到思想空间的锁链,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温斯顿从消极的反抗最后走到“他热爱老大哥”这样悖反的结局,即源于权力身体规训机制实质是通过控制思想空间实现其稳固性的,肉体的被规训与征服只是其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