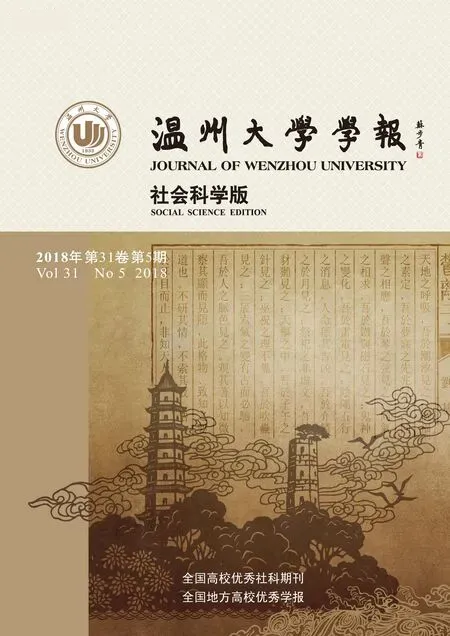刘开渠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艺术批评
沈 燕
(合肥学院艺术设计系,安徽合肥 230601)
一直以来,人们对刘开渠的关注集中在其雕塑艺术创作、雕塑艺术教育和推动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等几个方面。笔者在对刘开渠艺术生涯进行梳理时,发现大家都普遍忽视了他早期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他在艺术批评上的成就。在1922至1927年间,刘开渠撰写了二十余篇艺术批评的文章发表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上,几乎全面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界尤其是绘画界几个重要命题的讨论,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是刘开渠本人艺术个性的呈现,同时也是当时时代风气的反映。
一、国画的前途:严守自然与自由法则
20世纪20年代,美术界最关注的一个命题就是国画的前途问题,东西方艺术与绘画思想的碰撞、交融使得当时的美术界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国画艺术将何去何从?一时间,艺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其中既有主张“国画改良论”的康有为,也有主张“国画革命”的吕澂与陈独秀。还有坚持“中国画是进步的”,要“重估文人画的价值”的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
当时的刘开渠在北京艺专学习绘画。作为一名艺专的学生和五四青年,他也参与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他不满意用西画来改良国画的主张,也不同意“美术革命论”,而是站在了陈师曾“传统派”的阵营支持国画的独立性和传统的复兴。事实上,在那个一切都以西学为标杆破旧立新的时代里,陈师曾的“传统派”并不是主流,甚至是有些“反潮流”[1]。刘开渠作为五四时期的青年能旗帜鲜明地支持国画的传统与复兴,一方面因为他在北京艺专曾受教于陈师曾,受陈师曾影响更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独立冷静的思考,这个思考甚至超越了绘画本身,上升到了美学与艺术学的层面。首先,他将国画衰退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不皈依自然”;二为“固守旧法”。他认为当时的画家们只知道模仿前人,不能潜身于自然,没有了自己的创造,也就自然导致了国画的衰退,要想实现国画的复兴与创新,就需要“皈依自然”“破除旧法”“自由创造”,可是如何才能做到破除旧法,自由创造呢?他提出了一个追问,那就是到底“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艺术?刘开渠参考了美学家邓以蛰的观点,“所谓艺术,是性灵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种绝对的境界。”[2]艺术是来自于自然的“非自然”,是艺术家用自身情感的力量对“自然的印象”进行提炼、加工、改造以形成有着完好组织和独到形式的艺术形象。刘开渠后来又相继发表了《艺术的新运动》《石涛的画论》《徐枋的画》《翟大坤的作风》《傅山及其艺术》等文章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刘开渠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形成了独立的艺术见解。1927年,刘开渠将上述的艺术批评思想进行了整理,并发表了名为《画家的生命与作风》的文章刊登在4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在该文中,刘开渠再次阐述关于艺术家“生命与作风”的命题。“艺术之所以能感动人,是在作家赋予丰富的内容。这种活的有力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作家自己的生命。……作家要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地表现出来,那非有与自己生命一致的作风,是不能把它表现出来的。”[3]意思即为不同的生命力就需要有不同的作风来表现,别人的和古人的作风都没有办法充分表现自己的生命力,临摹与因袭只能走进死胡同。所以要想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内要丰富自己的生命力,在外要注重形成与自己生命力一致的独到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感人的艺术。
二、艺术价值的再界定:“非人生而又人生”
(一)关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两种观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艺术界还有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关于“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大争论。这场争论原本来自于西方。“为人生而艺术”主要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主张艺术应当为人生着想,所以用一定的理想做批评的标准”;“为艺术而艺术”主要以佩特为代表的“主张艺术的目的只在艺术的本身,所以用虚心受入的印象做批评的标准”[4]。20世纪20年代,这两种艺术主张传入中国并引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在文学界也有表现,文学界有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创造社是尊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尊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5]
艺术到底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到底是“象牙之塔”还是“十字街头”?这一争论也引起了艺术界的强烈反响与共鸣。早在 1923年俞寄凡为“艺术的艺术”辩护时就认为“不能说艺术与人生全无关系,……然亦不能因上述之理,而把艺术绝对的隶属于道德(善)之下。要是以为艺术是一种教化人们之具,所以有存在之价值,那是尚没有识得艺术的正鹄。……要晓得艺术确有独立的意义,独立的价值。”[6]“为艺术而艺术”代表着“五四”时期的艺术家们追求个性解放,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倾向。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还是使得更多艺术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主张艺术应该走向“十字街头”,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从而影响民众、教育民众。1927年5月1日至6月1日,林风眠作为北京艺专的校长模仿法国沙龙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艺术大会,这次北京艺术大会以“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为宗旨,并在十字街头张贴标语口号:“打倒模仿的传统的艺术!打倒贵族的少数独享的艺术!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提倡全民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7]
(二)“非人生而又人生”的艺术
作为北京艺专的学生,刘开渠发表了《严沧浪的艺术论》一文来参与当时的这场论争。他既不同意托尔斯泰“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把艺术限制在各种条件之下,不让它独立发展,走它自己应走的路”,对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不同意当时所谓的“艺术的艺术”,他认为这使得国画陷于两种“迷途”,一是“紊乱奇特”,一是“贫弱”,“前一种是故意糊涂,务使其紊乱神秘,使人家不明白,而且自己也不明白。……后一种是贫弱,空无所有,使人一点不能受感动。”[8]这对当时的国画发展也同样是不利的。
那艺术到底该如何?刘开渠参考了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趣”与“理”的论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这个“理”在刘开渠看来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人生、宗教,也是中国传统的“礼”。这段话在他看来就是正确地解释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即“所谓真正的艺术,是非人生而又人生的。”[8]所谓“非人生”是指艺术上的趣味与“理”无关,艺术不是对浮浅人生的照搬,艺术不能就人生而谈人生;所谓“而又人生的”是强调艺术的创造也不能离开“理”,离开人生,那样的艺术是贫弱的东西。但这“非人生而又人生的”的艺术到底如何实现呢?与前一个命题结合,刘开渠认为关键还在艺术家,在于艺术家生命力的熔铸,将那来自人生的事物经过艺术家的处理变成真正的艺术。事实上,刘开渠对严沧浪这段话的解读未必准确,他主要还是托古论今解决当时的问题。
总而言之,刘开渠认为画家与艺术家需要了解他们的时代,但这现实的时代与人生却不能直接成为艺术,需要经过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与生命力的加工,才能产生艺术上的趣味。因此,艺术既不完全是“象牙之塔”也不完全是“十字街头”,“赤裸裸的‘十字街头’上的是人生不是艺术,净玩外面(技巧、题材……)空无内容的‘象牙之塔’里的东西也不是真的艺术。它们要似恋爱的一对男女,有形的,无形的都密密地合起来,彼此浸淫到成了一体,才能产生新的生命——健全、伟大的艺术。”[8]
“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其本质是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中提倡的艺术无功利、艺术的独立性、艺术与生活的分离等内容;而“为人生而艺术”强调艺术的“他律性”,强调外在社会环境对艺术的影响,也强调艺术改变社会民众的思想以达到其社会功能。从当时徐悲鸿与徐志摩关于这个问题的“惑”与“不惑”之争到后来李毅士的加入,可见当时在中国艺术界“为人生而艺术”是占了上风的。从刘开渠后来个人的雕塑艺术创作和批评来看,很明显受到环境风气的影响也是“为人生而艺术”占了上风。他后来明确主张艺术应该为时代服务,为社会服务。比如他在1934 - 1935年间创作的雕塑作品《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就是“为替我们争生存而死的八十八师诸民族英雄而工作,为纪念他们万世不死的伟大精神而工作。”[9]51在《雕塑与抗战》一文中,他强调“为加强抗战建国的宣传,我们希望能利用雕塑,作更有力地激发民众……”[9]56。他后来创作的大量优秀写实主义雕塑作品如《无名英雄纪念碑》、《农工之家》等也都是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
然而当“为人生而艺术”走向极端,特别是当政治完全凌驾于艺术之上,使艺术因为失去了自身的“自律性”而使得内在活力消失殆尽时,他早期所强调的艺术是“人生而又非人生的”观点在“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意义便显现了。
三、艺术批评:敞开艺术的价值
(一)艺术批评家的责任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说“要解释艺术家的作品是不可能的”“批评家与其他人相比,总是更少地被艺术感染。他们大都是文笔流畅的、有学识的、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感受艺术的能力变得有些歪曲,甚至已经衰退。”[10]这番言论引发了当时国内艺术界对艺术批评和艺术批评家的偏见与抨击。这种偏见与抨击也引起了国内一些人的不满。吕澂直接批评托尔斯泰这是“外行的见解”。什么是批评家?吕澂认为“有鉴赏能力的民众是鉴赏者,有翻译能力的鉴赏者是批评家”。批评家对艺术家的作品是一种如实的说明,批评家的责任是站在“作家”和“民众”之间进行解释,让“民众”了解作家和作品,同时对后来的“作家”有启发作用[11]。吕澂不仅肯定了批评家的作用,而且给予了批评家很高的评价。
关于艺术批评家的责任,刘开渠从当时裸体画的艺术批评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刘海粟在上海美专最早采用裸体模特教学,1924年5月,上海美专毕业生在南昌举办画展,遭到了江西督军的禁令。7月,陈晓江在山西办画展,展览中有裸体画,遭到了山西省通令查禁,刘开渠早年的美术老师王子云给他转去山西省警察厅的传知——“饬禁展览裸体画”,其中提到裸体画“败坏风俗,引诱青年”等。刘开渠看到传知后,很快给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刊载在《晨报副刊》上。在信中,刘开渠对裸体画进行了声援,对山西省警察厅的做法予以了批评。刘开渠在这封信中提到了艺术批评家的责任。他认为民众对裸体画不理解和不能认识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批评家没有尽到说明的责任,没有对裸体画做相关的说明与宣传,没有正确引导民众对人体美的认识。“说明人体美的文字,实在少的太可怜了。……所以嗣后我们不必怪一般人鄙视裸体画。我们只能说一般研究艺术的人没有尽他们说明的责任。……我们只要尽力的说明,宣传,不怕一般人不欢迎!到了某个时期,恐怕还要向艺术家去求呢!”[12]因此,艺术批评家不仅要解释、分析艺术品,同时在新兴艺术兴起的时候,还应该做好相关的宣传与批评,给民众以正确的引导。
(二)艺术批评有助于敞开艺术的价值
针对当时流行的“艺术批评无用论”,刘开渠表示明确反对并肯定了艺术批评的用处,认为艺术批评能“指出作家对于自己未曾发现的错处”,但并不是什么艺术批评都有用。刘开渠对当时艺术批评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艺术批评方面的文章不是“漫骂与恭维”就是“单就外形的指责”[13],这都不能真正发挥艺术批评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刘开渠对艺术批评与艺术批评家本身提出了“批评”,他也是当时除吕澂之外为数不多的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较为深入探讨的人之一。刘开渠首先对艺术批评家本身提出了要求,作为艺术批评家一定要有敏锐的鉴赏能力与审美眼光并给予大众以引导。虽然画家是“感觉敏锐,生命力强大的人”,是能够从神秘而隐蔽的自然中找到美并能够表现出来的人,但是画家的作品却不那么浅显易懂,一般人不能很好了解并感受到其中的美,这就需要艺术批评家对艺术作品进行解释、分析,再告诉一般人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原因。艺术批评家的责任就在于成为艺术家、艺术品与民众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既然如此,那艺术批评家也就并非人人都能当。如同休谟将艺术批评的责任放在少数优选者身上,刘开渠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应具有比常人更强的对于伟大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并影响着大众。
什么样的艺术批评家才有敏锐的鉴赏能力与审美眼光并能正确引导大众呢?答案是具有美学与艺术学知识功底的人才可以做批评家。“艺术的批评,不是对于美学及艺术学没有研究的人,可以做得了的。朋友们!不欲做艺术上的批评则已。否则,请先对于美学及艺术学下—番研究的工夫,才能作出有价值的批评呢!”[13]这样就对艺术批评家的艺术与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就像意大利著名现代艺术批评史家文杜里曾认为法国艺术界里艺术史、艺术批评、美学三者之间分立的现象是可笑的,并认为应该设法使三者统一:“像这样把三门学科加以区分的结果,所得到的不过是使得它们变得空洞无物。事实上,即使叙述政治的历史也不可能不按照一定的理论去选择和解析那些需要详加议论的事件,……假使批评家惟一依靠的是他自己的感受,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因为,如果抛弃了一切理论,他就无法确定自己的审美感受是否比一个普通路人的更有价值。”[14]事实上,艺术批评的确需要消泯艺术作品、艺术史、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界限,需要从感性的描述上升到美学与艺术学意义上普遍有效的一般性解释与规范性评价,这样才能体现出艺术批评的价值。
(三)艺术批评有助于构建中国艺术话语体系
作为艺专学生,刘开渠在当时艺术界并不具备很强势的话语权,但他的艺术批评逻辑却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他抛开艺术上的“中西之争”,也避而不谈国画的“改良”“改革”或是“复兴”而去研究艺术的定义,这样就从社会和历史特定的语境里跳了出来,从艺术内部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学术逻辑是智慧的。事实上,正如傅雷所说,当时国画上的“中西方之争”以及“改良”和“改革”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艺术恐慌”[15]。艺术上的“改良”“改革”都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时表现出的文化上的深度不自信。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在同样的历史环境中从研究历史开始最终落实于文化研究一样,他要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入手来建立国民的自信。西方人先进的技术、机械都属于文明范畴,而艺术却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文明本就是两回事,“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16]当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艺术观的基础上把艺术所有的叙事和形式解构掉,认为纯粹的材料与媒介才是艺术的本质并找到波洛克,认为抽象表现主义才是纯粹的艺术时①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 - 1994),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被认为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发言人。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 - 1964),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当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的理论代言人。罗杰·弗莱(1866 - 1934),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美学家,艺术批评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一学术逻辑。事实上从艺术的本质入手更容易让我们去建立艺术自信与自己的批评体系。
四、结 语
在1922至1927年间,刘开渠几乎全面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界,尤其是绘画界几个重要命题的讨论,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是刘开渠本人艺术个性的呈现,同时也是当时时代风气的反映。人们对此忽视的原因一是由于刘开渠留法后转向雕塑艺术,他的关注点和发表的文章自然就转向雕塑艺术与雕塑教育方面,艺术批评的文章就很少了;二是因为刘开渠作为北京艺专的学生,发表艺术批评文章的影响力与当时舆论领袖康有为、吕澂、陈独秀等人相比是有限的。然而笔者认为,对刘开渠这一时期艺术批评方面成就的忽视是不合适的。他的见解对于当下艺术批评体系建设而言,其意义在于:第一,从研究艺术的本质入手更容易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艺术批评体系与艺术自信;第二,艺术是“人生而又非人生的”看法调和了“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两种观点,避免走上任何一个极端;第三,艺术批评家不仅要有敏锐的鉴赏能力与审美眼光,还必须具备美学和艺术学上的知识。艺术批评也需要从感性的描述上升到美学与艺术学意义上普遍有效的一般性解释与规范性评价,才能体现出艺术批评的价值。
1922至1927年,作为“五四”青年的刘开渠有着时代赋予的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他不迷信任何当时的权威,他对陈师曾、王梦白、萧谦中、吴法鼎、林风眠、邓以蛰等艺专老师的艺术思想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并贯穿一生。他的艺术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他自己在雕塑艺术方面的发展而且通过艺术教育活动影响了此后的整个中国雕塑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