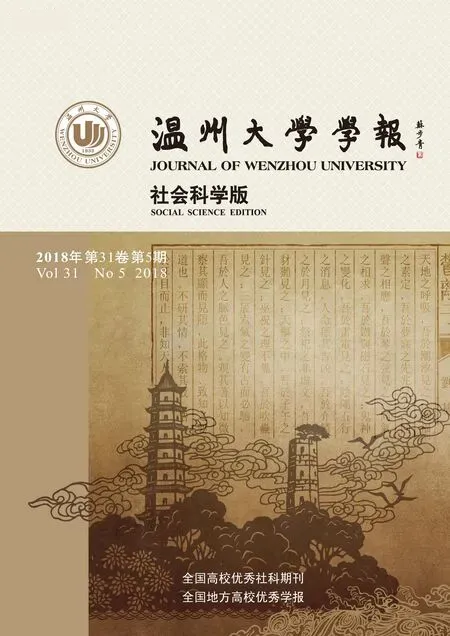走进郁达夫的书评世界
林荣松
(宁德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宁德 352100)
郁达夫一生与书结缘,读书、著书、译书、藏书成为生活常态。他嗜书如命,也写了不少书评,是最有智慧、最具个性的书评家。他的书评不矫情,不伪饰,不迎合流俗,不墨守成规,为文的率真洒脱一览无遗。走进郁达夫别开生面的书评世界,可以更真切地了解这位著名作家,他是那么的有血有肉,那么的睿智不俗。
一
书评,其实就是和书的“对话”。既为“对话”,行文的自由度相对就大一些,最忌面面俱到的宏大写法、人云亦云的枯燥说教和毫无生气的“八股”味道。
郁达夫的书评,每有独到的眼光,传达了独特的生命体验。《<女神>之生日》有感于“文人自古善相轻”的恶习,主张文人不应互相标榜,更不能互相倾轧。借《女神》出版周年之“生日”大家可以开诚布公,谈谈“胸中所蕴积的言语”,“同心协力的想个以后可以巩固我们中国新文学的方略”①引文出自郁达夫的《<女神>之生日》《读<老残游记>》《杂评曼殊的作品》《读<毛拉在中国>》等相关书评,故以下引用时只提引文来源的文献名称,不再以参考文献的形式一一标明具体出处。。同时并不讳言郭沫若好友的身份,极言“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的功绩。《读<老残游记>》从自己的阅读体会切入,第一次读“只觉得它的文字简练,华实相称”,再读“愈觉作者寄托的遥深,牢骚的美化了”。评价《老残游记》“非要设身处地的把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仔细想一想不可”,说它“毫无价值,毫无时代性”是过于苛刻的批评。“以文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却可以称得起《儒林外史》的后继者,不过笔力弱一点,没有笼罩全书的伟大的精神,所以不能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杂评曼殊的作品》眼光开阔,从胡适《最近五十年的中国文学》里“没有苏曼殊的名氏”说起,指出苏曼殊“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经是不朽的了”。他的才气,他的气质,并非指哪一部具体作品,或者说找不出“一篇浑然大成的东西”,而是在全部作品中“流露闪耀”。“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读<毛拉在中国>》针对抗战的严峻形势,以为《毛拉在中国》能给国人以鼓舞,弥补了抗战对外宣传的不足。毛拉是位有“良心”的西方记者,1938年春到中国,以自己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得出了与西方怀疑论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只教能始终团结,能抗战到底,结果一定会得到胜利。”书评不是冷冰冰的东西,书评的对象是投入了作者生命的作品,书评者需要感同身受,才能发现美的所在。
郁达夫的书评,喜欢率性遣笔,读来感觉既亲切又轻松。《序李桂著的<半生杂忆>》开篇云:“李桂先生,和我并不相识,直到现在,也还不曾有过见面的机会;可是,我读了他的这一册的原稿之后,倒觉得和他仿佛是很熟的老朋友了”,完全没有名家对新人那种居高临下的腔调。《读<兰生弟的日记>》以“种种苦楚,紧压住我的心身”,反衬“读了徐祖正君的《兰生弟的日记》,觉得心里非常愉快”,为后面批评该书存在诸多问题作铺垫。“因为徐君是一位贤者,所以我不惜春秋之笔;因为徐君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欲争得一谏友之名。”如此一来,“不客气”的批评就有了“客气”的效果。《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这样描述自己的印象:“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的,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这位俄国大作家的距离。此外,《<古代的人>序》称译者林微音为“我的朋友”,读者为“中国的朋友们”;《<白云轩诗词集>序》称作者为“秋山兄”,配以文言赋体来写并“爰拈七绝二首,藉抒观感”,字里行间都有一种亲和力扑面而来。率性遣笔本为郁达夫所长,在其书评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郁达夫的书评,讲究要言不烦,往往寥寥数语直抵作品要义。《<瓶>附记》400余字,写得风趣而不失犀利:“革命诗歌”不一定要有“手枪炸弹”,或连写“革命的字样”,可以“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一句话“作抒情诗时,正应该望理想中的皮曲利斯而遥拜”。意思是纯粹的抒情诗和诗人的政治活动,二者并不绝对排斥。《<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跋》约200字,分析一语中的:“君的这篇小说,其实是一篇散文诗,是一篇美丽的Essay”,“他所想表现的,就是离人的孤冷的情怀”,而带给你“神秘的美味”的是“那一场静默的Scene”。《<超人的一面>译者附记》不足300字,揭示了“超人”尼采“柔情”的一面。以尼采写给Madame O Luise的七封信,《尼采书简全集》编者引用尼采妹妹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冷酷孤傲的哲学家的一面,原也有像这样的柔情”。另,《<七大问题>序》《<祷告>译后附注》《<春天的播种>译后记》《<我俩的黄昏时候>译后志》多则230多字,少则170多字,无不言简意赅。中国文人传统中序跋与书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具有评论性的序跋其实就是一种书评。事实上以序跋之类来评介图书,在现代作家是一种常见现象。萧乾说,好的书评要用极简练的文字表现出最多的智慧,郁达夫的书评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需要强调的是,郁达夫的书评形式多样、手法丰富,上述几个方面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换句话说,他的书评大都兼有这些特色,不过有所侧重而已。
二
在郁达夫的书评中,《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通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颇具代表性,作者的所长和书评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发挥。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之一。郁达夫此文发表于《人间世》1934年第14期,应当是我国全面评介该书的最早篇章,不仅介绍了小说的内容、流传版本及在西方国家的反响,而且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和不俗的见地,因而弥足珍贵。
郁达夫落笔便将批评家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应是他自己的看法——推了出来:“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批评家们大家都无异议地承认它是一代的杰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甫一问世就争议不断,乃至屡遭查禁。在这样的背景下,郁达夫肯定其为“杰作”,无疑是超前的先进的。从总体上看,“这书的特点,是在写英国贵族社会的空疏、守旧、无为而又假冒高尚,使人不得不对这特权阶级发生厌恶之情,他的写工人阶级,写有生命力的中流妇人,处处满持着同情,处处露出了卓见。”从写法上看,“本来是以极端写实著名的劳伦斯,在这一本书里,更把他的技巧用尽了。”特别是“描写性交的场面,一层深似一层,一次细过一次,非但动作对话,写得无微不至,而且在极粗的地方,恰恰和极细的心里描写,能够连接得起来。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人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名词,他都写了进去,但能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如此还嫌不够,又拿来《金瓶梅》进行比较。“试把中国《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到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却泰来夫人的爱人》里,却觉得工句一行也移动不得。他所写的一场场的性交,都觉得是自然得很。”而且“他对于社会环境与自然背景,也一步都不放肯松。所以读他的小说,每有看色彩鲜艳刻画明晰的雕刻之感”。虽说劳伦斯小说的结构“向来是很松懈的”,“但这一本《却泰来夫人的爱人》却不然,它的结构倒是前后呼应着的,很有层次,也很严整”。有了如此充分的评述,预言劳伦斯为“对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之一,自然顺理成章并在多年后得到验证。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还生动表达了他的欣赏之情:“这一篇有血有肉的小说三百余页……‘一口气读完,略嫌太短了些!’是我当时读后的一种茫然的感想。”这种感性的描述,使书评的理性文字有了情感的力量。
鉴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时还没有中文译本,顾及国人对该书不熟悉,《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介绍背景及故事情节的文字似乎略多了一些,评述上则考虑到尽可能具体全面一些,但并不影响解读的切要和深度。对小说中几位主角的微妙心理纠葛,对“性”这个社会禁忌话题,对现代社会拜金主义造成的人性扭曲,进行了充分的独到的分析。尤其断言劳伦斯是“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更被有的学者称为空前绝后的精辟。即便今天来看,该文基本观点也丝毫不觉落伍,对于读者领会这部世界名著的深刻内涵,接受“性”的艺术描写,仍有积极意义。
有趣的是,在西方历经磨难的劳伦斯及其作品,中国文学界1930年前后即报以宽容和欢迎。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现在 1934年,除了郁达夫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还有孙晋三的《劳伦斯》、章益的《劳伦斯的<却特莱爵夫人的爱人>研究》、邵洵美的《读劳伦斯的小说》、林语堂的《谈劳伦斯》等,尤以郁达夫和林语堂的两篇文章影响广泛。两年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一部完整中译本出版时,译者将郁、林两文置诸书前,显然认同并寄望发挥导读作用。郁达夫算得上劳伦斯的中国知音,他当年结合国情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解读,让人感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方始得出的结论早在他笔下就有过了。郁达夫能准确抓住该书的基本特点和最大亮点,很大程度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审美趣味和创作实践有关,他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现代人的苦闷”,他认为性欲和死有更大的“偏爱价值”,他的小说更以写“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著称。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莱夫人的爱人〉》将书评的指向意义和功能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三
郁达夫对当时的出版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粗纸滥印的一折书的出现”,虽为“适应经济破产后的大众而产生”,但多为封建时代的旧书,十分之一的新书又“浅薄错乱”;“高价大部的古今类书的再兴”,是为“上层阶级”而印,遗憾的是“只剩了一点过去的追怀,而没有了现在与将来”。从图书出版的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国运人事的衰落”[1]。郁达夫对写作的甘苦、发表的不易,有切身体会;对鲁迅所说的谁也不去理会无名作家,一任他自生自灭,深有感触。一方面图书市场缺乏好书,另一方面有些好书又难以面世。基于此,郁达夫不满足于为写书评而写书评,而是结合时代潮汐、文坛动向、新人成长来写书评。
郁达夫和蒋光慈、冯蕉衣的关系颇能说明问题。蒋光慈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1925年从俄国回国致力于革命文学的创作。其时革命文学还没有流行,革命文学的理论准备显得仓促而不足,蒋光慈的文风为一般人所不满,创作始终处于左右不是的尴尬中。郁达夫自谓“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①1933年春,在宋庆龄家举行的一次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上,郁达夫对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说: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1939年初,他在《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一文中又说:“我不过是一个文艺作者”,并重提当年对史沫特莱说的那句话。,对蒋光慈的遭遇和早逝很有感触。在《光慈的晚年》一文中认为,“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在《<鸭绿江上>读后感》中对收入小说集的八篇小说给予中肯评价,热情肯定蒋光慈小说在革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指出作者“有驾驭文字的手腕,有畅所欲言的魄力,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之后,不能起激烈的冲动,狂暴的兴奋”。究其原因在于“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和革命或曰无产阶级还有隔膜,因而削弱了使人“激动”、“兴奋”的力量。蒋光慈身上的问题,实际上是革命文学的通病,革命文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消除这种“隔膜”。避乱星洲的冯蕉衣因贫病交加早逝,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晨星》刊发“纪念诗人冯蕉衣专辑”,写了《悼诗人冯蕉衣》,又为其遗诗的出版写了《序冯蕉衣的遗诗》。序文给予冯蕉衣及其诗作应有评价。“一、冯蕉衣是一位生来的抒情诗人。”“二、冯蕉衣并不是一位革命诗人。”郁达夫批驳了“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过激论,指出冯蕉衣“所缺少的,就是直接推动革命的行动与歌咏这些行动的激情而已”,与写下不朽杰作《奥倍曼》的法国作家塞南古“很有点相像”。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想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他对冯蕉衣从创作到生活的热情帮助,其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对某一“个体”的扶持。
类似的情况不乏其例。郁达夫在《<惜分飞>序》中肯定王余杞的小说“是力的文学”,在革命文学盛行的现在,“虽然没有口号,没有手枪炸弹,没有杀杀杀的喊声,没有工女和工人的恋爱,没有资本家杀工人的描写,然而你一直的贪读下去,你却能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感动。”要说遗憾,就是这种“感动”还“不十分强而有力”。在《读刘大杰<昨日之花>》中指出,作者具有“陈述”想提出的问题的素质,而描写细腻心理非他所长,希望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塑造出几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物。在为白杨《爱情的梦》作序时,称小说“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作者态度的率真”,最感动的地方就是情感价值的结构技巧,不足之处则是“缺少一点文采”。在《介绍<美丽的谎>》中认为,马来亚青年作家温梓川的风格朴素坚实,集中的小说“篇篇都写得很整洁”,而以写小贩的《阿松伯的生辰》和写苦力之死的《解脱》“为最精彩”,写恋爱则非其所长“不够味儿”。文学青年的成长既需要热情鼓励,更需要发现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凡此种种,不难看出郁达夫的良苦用心。
与此同时,郁达夫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文学青年传输为文之道。在应《学校生活》之约而写的《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中告诫说,要成一个作家不能走“避难就易”的道路,更不能“以冀得名利双收”。在为《读书月刊》所作的《学文学的人》一文中要求学文学的青年,首先应重视“本于天性的一种基础”,其次“要有牺牲的精神”,然后才是精通文字。在《希望于投稿诸君者》中希望投稿者“扩大写稿范围”,可以从“书评、人物论、报告、图书(木刻、照相)等方面”努力。在《看稿的结果》中坦言提高写作水平的“对症药”,是“眼到、心到、口到;多读、多写、多想、多改”地读书。本着这种精神,他的书评多能高屋建瓴、有的放矢,成为书籍的“传感器”和人生的“助推器”。
四
我国已进入全民阅读时代,书评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同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书评被边缘化、庸俗化,书评缺乏独立性、公信力,似乎成为一个难以破解的老大难问题。书评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创作——对所评图书的再创作,既评介了图书,也写出了自己。写书评绝非易事,写出好的书评更是难上加难。怎么写书评,怎样的书评才是好的书评,郁达夫的书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书评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传递有用的资讯,构建图书、作者、读者和出版者之间信息交流的渠道;二是给予人精神上的享受,影响乃至改变人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书评是否有价值,既取决于被评之书的优劣,更离不开书评者的社会阅历、人文素养、学术积累和审美眼光,以及对被评之书的思考、感悟、升华和更深的洞见。“书即是人,人亦即是书。”[2]书评需要用心去写,只有真正沉下心来才能写出超越偏见、见解独到的书评。好的书评固然要有思考的乐趣和情感的温度,科学的态度和责任的担当更应坚守。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与书评的发展密切相关,称得上书评家的五四作家不在少数,除了郁达夫,鲁迅、周作人、叶圣陶、茅盾等等都是个性鲜明的书评家。他们的书评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自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生涯。鲁迅的书评提纲挈领、笔力强劲、焕发着“力之美”的光芒,周作人的书评往往随意写来而又思路开阔、知识丰富,叶圣陶擅长真诚平实、短小精悍的广告式书评,茅盾追求书评的广度、深度、社会效果及文学理论色彩,郁达夫的书评则更见真情、性情与才情。
郁达夫的书评看似情胜于理,却并非“滥情”或者“无理”。他坦言自己“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3],有这样的认知,他的纵情宣泄才没有局限于仅仅聊发心声。“道德的本质是天良,天良的运用是良知,纯正的批评便是良知的表现。我们下批评的时候,总要凭着我们的良知,不违背道德的本质,论衡轻重,辨别真伪,才能压服众人,挽回颓俗。”[4]书评有书作为依托,或许不必过多论证,重在情与理互补,重在意趣和发现,这正是郁达夫书评孜孜以求的境界。郁达夫自诩“卖得文章为买书”,生平坎坷却收藏了古今中外图书约五万册,作为藏书家和书评家可谓相得益彰。他当过编辑,积累了丰富的审稿经验。他当过教师,养成了条分缕析的思维习惯。更为重要的是,郁达夫从不放弃为人为文的原则,“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5]为写好书评,他丝毫不敢懈怠,总是在掌握大量资料、认真研读辨析之后,再提笔成文。他的书评既激荡着时代的风云,也跳动着生命的脉搏。读他的书评有如品茗,能让你从喧嚣中沉静下来,在回味之余去体察社会、感悟人生。
郁达夫的文化个性,既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明显影响,又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郁达夫对文体素有研究,有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是勇于创新的文体家,从文学到应用文的各种文体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指出:“文体当然是个人的;即使所写的是社会及他人的事情,只教是通过作者的一番翻译介绍说明或写出之后,作者的个性当然要渗入到作品里去的。”[6]他主张:“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7]表面上看来,郁达夫强调文体是作家个性的物化形态和创作不必死守陈规的观点,不过是文体构成的两项基本因素——内形式与外形式的具体发挥,和刘勰《文心雕龙》所说“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并无多大差别,实则不然。郁达夫的文体观体现了“人的觉醒”的五四精神,和别林斯基“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的思想一脉相通。郁达夫的书评正是这种文体观的自觉实践,尤以评论、随笔、序跋、引言、附记、读后感式书评得心应手,且能不落窠臼、不同凡响。
诚然,郁达夫的书评并非字字珠玑,篇篇锦绣。比如,郁达夫似乎不喜欢“高大上”的书评,可有时又会过多植入外来词语,造成很少接触外语的读者产生阅读障碍。他早期所写的书评,尤其为译作所写的书评,喜欢动辄嵌进英语词汇、句子乃至片段。这种对西方语言符号的简单复制,既是郁达夫现代身份的隐喻,又是缺乏文体自律的表现。好在他没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随着思想、艺术趋向成熟不复如此。又如,郁达夫书评中个别提法或可商榷,像《读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从评劳伦斯小说引发的感慨:“到处都是为了Money的争斗、倾轧”,“人生万事,原不过是一个空虚!唯其是如此,所以大家在拼命的寻欢作乐,满足官能”,就是典型的郁达夫式的愤世嫉俗,可见浓重的生存焦虑与弥漫的虚无气息,而这正是其人其文被诟病颓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瑕不掩瑜,郁达夫作为重要书评家的地位毋庸置疑。他的书评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具体作品的评介,也不仅仅在于引导读者避免误读,还在于蕴含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可以透视社会、直指人心。从上述书评中,一个实话实说、见性见情、爱国忧民的郁达夫跃然纸上。正因为郁达夫是这样的人,他的书评让人心悦诚服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