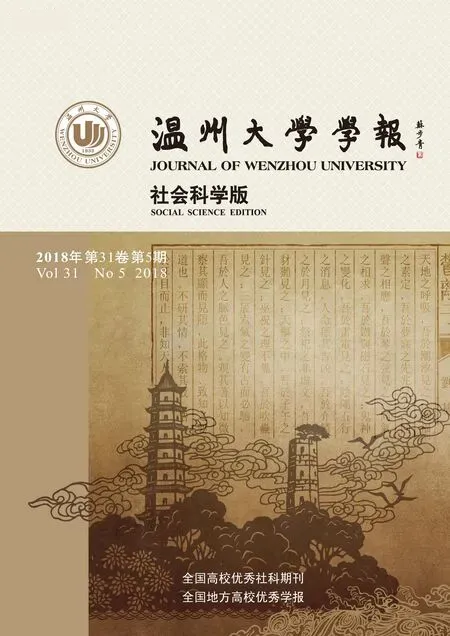《中山诗话》卷数繁简考论
刘 育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内篇五》中将诗话比拟为可“经”、可“史”、可“子”[1]的一类创作。这种在内容上的驳杂性和丰富性特点,使得后人在利用诗话时通常更侧重于就事论事,关注其中包含的信息与思想。相较而言,对于一部诗话外在形制上的问题则少有人问津。事实上,诗话虽然在狭义上不能算作文学作品本身而仅仅是对诗歌这一文学体裁做出的批评性话语,但在它的文本传播过程中,有时确也存在着类如文集一样的卷数繁简或版本差异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拟以一部具体诗话作品——《中山诗话》及其作者刘攽为考察对象,尝试推论是书卷帙在历代目录的著录中繁简不一的深层原因。
一、关于《中山诗话》的卷数疑云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一字戆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与其兄刘敞同登庆历六年(1046)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宋史》卷三一九有传,附于刘敞名下。刘攽在当时以博洽称,尤精史学,曾受司马光之邀参与编撰《资治通鉴》的汉史部分,同时亦有不少个人著述。史称“攽所著书百卷”[2]10388,其中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彭城先生文集》六十卷、《内传国语》十卷(以上四种见《郡斋读书志》)、《芍药谱》一卷(见《直斋书录解题》)、《易传》《易数钩隐图》(以上二种见《遂初堂书目》)等,然而是书多已不传,今所见者,惟《中山诗话》一卷,《彭城集》四十卷,《汉官仪》三卷以及《四库全书存目》著录的《文选类林》十八卷。从史志目录记载的主题多样的著述成果来看,可以推测刘攽的确博兼今古、经史皆通。但遗憾的是,如同历代大量古籍的命运一样,他的著述也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现在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字中去认识揣摩其才学,诗歌评论类著作《中山诗话》就是其中的一个媒介。
《中山诗话》亦称《刘贡父诗话》,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同为今天所能见到最古老的诗话著作。按照四库馆臣的说法,早期的诗话并无定名,仅称“诗话”而已,后来人们为了区别不同文人的作品,才以郡望、字号等冠名[3]2740。于是我们看到,此书见于古籍目录中时就常常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如《中山诗话》(《四库全书》)、《刘贡父诗话》(《通志》)、《贡父诗话》(《皕宋楼藏书志》),或是在单称《诗话》(《宋史·艺文志》)的同时标注作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这些不尽相同的著录名称相应,古书目录对于此书的卷数上也出现了几种不一样的记载。
以上三种情况少则一卷,至多也不过三卷,相互之间差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以上众多藏书目录中,堪称宋代私撰提要目录双璧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其作者晁公武(1101–1174?)、陈振孙(1179–1262)[4]生活的时代,距离刘攽及其《中山诗话》的成书无疑是最为接近的。然而,正是这两部可靠程度理应最高的书目,在著录《中山诗话》时,却出现了上述一多一少的两种极端:晁书录为三卷,而陈书仅作一卷。在相距时代最近的前提下,两人所藏所见却有如此差距,窃以为这一现象是不同寻常的。
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一书中对此解释到,“是书《郡斋读书志》及《通考》作三卷,《宋四库阙书目》作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及《通志》又作一卷。今世通行本,如全集本、《百川》本、《说郛》本、明刻《宋诗话五种》本、《津逮》本、《历代诗话》本及《萤雪轩》本,均为一卷,无作二卷三卷者。惟钱曾《述古堂藏书目》有三卷本,疑是传抄本,未必为刻本也。窃疑是书卷帙,或有繁简,当时传录已有不同之本……”[5]9。随后,他举出了两个他书所引在今本诗话之外的例子,即李心传《旧闻正误》引“宰相须是读书人”及何汶《竹庄诗话》引“李慎言梦观宫女戏毬”两条。这一文本内容上的阙失明确提示我们,《中山诗话》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散失、造成部分内容亡佚的情况是无疑的。再以刘攽本人的《彭城集》为例,见于《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之记载均为六十卷,但今观其书,已不见三分之一,只剩下四十卷。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文本传播形态的异变,使得一部古籍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卷数面世,就成为一个可以接受审视和讨论的问题。就《中山诗话》这个具体案例来说,本文认为除了抄本较之刻本,本身形态更不稳定这样一个可能为诸多古书共同面临的现实以外,主要是政治环境的因素在发生作用,导致了它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里就已发生了卷数上的衍变。
二、《中山诗话》卷数异变现象原因考辨
就政治环境来说,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有宋一代基本趋向于文官政治以后,其间发生了数次以文人集团为派别的党争,元祐党争是其中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一个典型事件。神宗时王安石推行“熙丰变法”,史称“新法”,这次变革意义之深刻,在一些当代学者眼中,甚至被誉为“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并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它也是一次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建国家的尝试”[6]447-448。然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派政党对于这个尝试却持有截然相反的否定态度,政局于是随着双方在朝廷势力的消长不断变化,一方上台执政,另外一方即受打压。到徽宗亲政时,前变法派的成员蔡京手握大权,大力贬斥保守旧党,在将司马光一派定为“元祐奸党”的同时,实行了严酷的精神报复,把元祐党人的著述列为禁书,掌控了思想上的生杀大权。本文讨论对象,其作者刘攽之名尽管不见于《元祐党籍碑》名录,但值得玩味的是,他的这本《中山诗话》却成为了此番党禁的受害者之一。
据徽宗崇宁初年的一份诏书称,“三苏集及苏门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7]。可见,与其他旧党人士的著述一道,刘攽的《中山诗话》也曾一度被禁,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考虑到这种状态需要一直持续到党禁解除,故此原本就卷帙有限的《中山诗话》在南宋时即已有一卷和三卷之别,极有可能是经禁毁后再传于世的版本内容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删改,从而出现了容量与质量上的异变情形。换言之,本文认为晁公武记载的三卷本当更加符合该书的原始形态。
首先,我们在上文所引诏书中看到,与其同期被禁的多是可供抒发己见的私人文集或者能够微言大义的史类著作。如前文提及的那样,《中山诗话》明显具有早期诗话的特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并不完善,与南宋及其后迭出的富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诗话作品不同。作为欧阳修在诗话领域奠基之作《六一诗话》之后出现的紧随者,其基本写作理念和前者“以资闲谈”[8]3的趣味与追求相去无几,理论上来说,它也“没有要在文学作品与其它价值体系(政治、道德、社会等等)之间的关系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上做出正式声明、明确表明自己立场的动力”[6]。那么因党争而遭遇禁毁,操纵这一事件的新党究竟师出何名呢?
其一,最直接的牵涉关系当然在于,刘攽立场鲜明地反对新法,并与新党人士特别是其首脑王安石多有摩擦,《宋史》本传记载:
刘攽理据分明地针对王安石侍讲可坐的提议进行了反驳,一面从古今常礼的祖宗规矩中找定立论基础,一面又似有让步式地表示,如果是皇帝亲允的,那代表了人君之德,也未尝不可以坐。这样一套逻辑严密的论证系统,立即得到了礼官的附议,遂使王安石的意见完全遭到无视。尽管我们没有看到王在此次交锋以及落败后的具体反应,但毫无疑问的是,刘攽在他心里的印象不大可能会是积极正面的。因此,当刘攽其后又一再与新党人士作对,直到义正言辞地给王安石写信抨击其改革措施时,后者终于怒不可遏地将他遣置到了一个治安极差的地区去应对乱局。引发这一饱含怒气和不无刻意报复之嫌举动的,大约正是下面这番激烈的言辞:
暴发性心肌炎起病急骤,发展迅速,若未及时发现与积极治疗,猝死的可能性极大;且治疗条件要求高,费用昂贵,给患者及家属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5-6,11]。护理人员需做好安抚工作,及时向患者家属反应该患者的病情变化,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并以积极的心态投入护理工作。
介父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而特开设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
今郡县之吏,率以青苗钱为殿最,又青苗钱未足,未得催二税,郡县吏惧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犹能小为方略以强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罚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请,安得不纳,而谓其愿而不可止者,吾谁欺?欺天乎?
可以看到,在这封以王安石本人为第一(或者,在写作当下就是唯一)读者的书信里,刘攽毫不客气地对王安石新法中的重点举措青苗法展开了强烈批驳,渐进式的质问语气不断加强,从“不亦可羞哉”到“吾谁欺?欺天乎”,刘攽的行文意图就像是要拆穿一个罪大恶极的骗子,其后他甚至援引出商鞅和张汤两例未得善终的历史人物,在看似告诫的意味里暗含威胁,语义之不善不但针对王安石,实则也包含了一系列站在新法背后呐喊助威的人。以此观之,刘攽因其对新法深恶痛绝、不惜加以诅咒的态度触怒的,当不仅限于王安石一人,故此,虽然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元祐党籍碑上,但《中山诗话》作为其主要著述遭到禁毁却是合乎“情理”的。
其二,刘攽与旧党人物过从甚密,也让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新法的对立面。他曾经应司马光之邀编修《资治通鉴》,在其中负责汉史部分;此外,《宋史》本传虽篇幅不长,却专有一笔写到,“哲宗初,起知襄州。入为秘书少监,以疾求去,加直龙图阁、知蔡州。于是给事中孙觉、胡宗愈,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言:‘攽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宜优赐之告,使留京师。’至蔡数月,召拜中书舍人”[2]10388。《叶祖洽传》中也写到,当叶因言险获罪时,刘攽与苏轼同挺身而出,为其申辩[2]11167。再如鲜于侁与王安石不睦,其传记中记载,“时王安石、吕惠卿当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荐举之权,而所列非贤,耻也。’故凡所荐如刘挚、李常、苏轼、刘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时之士。”[2]10397-10398种种迹象都表明,刘攽确与旧党人士有着亲密友好的关系。
同样,检攽之文集与旧党人物诗文,也可窥见到他们的交游情况。例如现存《彭城集》中不乏写给苏轼兄弟的诗作或者和诗、次韵之作,相应地,二苏也有许多与刘攽交往的记录,像是苏轼文集中留存的和刘攽共事时一起拟定的公文,以及他们私下交往的赠诗,如下面两首《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
在这些诗歌里,苏轼、苏辙兄弟毫不掩饰对于刘攽的欣赏,以及彼此之间相交相知的情谊。由此可见,无论是与新党失和,抑或是与旧党交好,刘攽都明确无疑地站在所谓“元祐党人”的队伍里。在这种情况下,于党禁之中被废书废言,当然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但是,以上论述仅仅证明了《中山诗话》遭禁的事实及其合“理”性所在,至于是书出现的不同面貌,本文认为主要是因为它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人为改动,遂造成了其卷数从三卷到一卷的显著变化。首先,证据之一在于,刘攽本人脾性特别,本传称之为“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2]10388。宋魏泰的《东轩笔录》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11]:
应该说,这则富有戏剧性的对话故事很好地佐证了正史中对于刘攽的评价,并尤其凸显了他性格当中不善于审时度势从而容易得罪他人的一面,这种个性反映在以闲谈为主、任由作者随性发挥的早期诗话创作中,就可能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比如现存一卷本的《中山诗话》中,就有“景佑中羌人叛”和“太宗晚年烧炼丹药”两条,前者透过《题关西驿舍》一诗,将生不逢时的情绪渲染于诗句之中,后者则直言太宗皇帝赵光义晚年迷信丹药的史实,尽管这两个条目乍看上去无伤大雅,特别是在国运稳定的时期其悲时和讽刺的意味并不明显,甚或可以忽略不计,但假如暂且忘记它们并未被删除而是幸运存留至今的事实,其实很难说这会是当权者喜闻乐见的东西。那么以此推之,以刘攽本人的性格,他最初写就的诗话当中想必还有其他更加不宜流传于世的部分。因此本文认为从三卷本到一卷本,极有可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经过了删汰,且其内容不仅限于上述《宋诗话考》征引过的两条佚文。
其次,更有决定性的第二点证据是,古今学人对于《中山诗话》都存在着相当矛盾的评价。即,无论是四库馆臣还是当代学者,都在肯定刘攽个人能力与学识的同时,指摘该书存在多处失误。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就在称许“攽素称博洽”之后,紧接着列举了“《花蕊夫人宫词》”、“李商隐《锦瑟》诗”、“赫连勃勃蒸土”等六条内容有误或语不可解的例子,并认为是书“所载嘲谑之词,弥多冗杂”[3]2740。无独有偶,郭绍虞先生在对《中山诗话》的考证中也称,“惟刘氏虽以博洽见称,而是书所载转多误谬”,并转引了数例诗话有误之说,最后加以个人推断曰,“贡父虽博洽而可议之处转较他书为多,岂此为公不经意之作,不暇察其疵累耶”[5]9。
然而,对于一卷总共包含六十三个条目的小型诗话来说,单是《四库全书总目》的误说举证,就已经相当于整部诗话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如果换作一般文人的手笔,或许情有可原,但对于刘攽而言,出现如此数量可观的讹误,实在不是正常的现象。上文说过,本传中记载哲宗时胡宗愈、苏轼等人在力保刘攽留京任职时就称赞他“博记能文章”。更有意思的是,仍旧是四库馆臣为此诗话所撰的提要,最后的评语竟是“攽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所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南宋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3]2740。盛赞之辞与先前指出占全书十分之一强的失误难免形成抵触。再看收于《四库存目》的《文选类林》一书提要里,清代学者甚至认为“攽兄弟以文章学问与欧阳修、苏轼诸人驰骋上下,未必为此饾饤之学”[3]1801,从而怀疑此书为后人伪托刘攽之名所作。暂且不论《文选类林》之真伪,仅凭这一将刘攽与欧阳修、苏轼等当时顶级学者的学术水准相提并论的判断,以及《宋史》本传、《四库全书总目》对刘攽学识的高度认可,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今本所见《中山诗话》的谬误比例之高是不合常理的。退一步来说,假若以刘攽之才学尚不肯为此堆砌词藻之学的话,那么对于一部人们可确知是出自其手的署名作品,他又怎么会随意慢待以至漏洞频出呢?至此可见,现存的一卷本《中山诗话》与刘攽原作面貌恐怕已经存在相当的距离。
此外,从社会背景来看,尽管在唐宋变革这一宏大的叙述系统之下,宋之新变中尤为受人瞩目的一个要点就是印刷术的普及[6]428,我们因此可以想见宋代以来印刷术的大规模使用和由此产生的书籍文化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变了此前手抄文本易于散失、变易的不稳定状态,但是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们也普遍承认,“印刷书‘最后的胜利’要到十六世纪才发生”[12]。换言之,在手抄文本仍然大行其道的时代,传抄过程中的脱漏、讹误等确也是无可避免的状况。具体到本文讨论的个案《中山诗话》来看,除了前述有意为之的更改,也不能排除它在传播过程中遭遇到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异变。事实上,这种文本可能面临的自然流失情况,我们也可以从同时代的其他著述中了解一二。例如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第十二条中提到,“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8]40;又于二十四条中说,“闽人有谢伯初者,字景山,当天圣、景祐之间,以诗知名……其诗今已不见于世”[8]77-78。可以看到,在印刷文化尚不逮普及至整个社会的角角落落时,文人作品的佚失也并非是偶发事件。
最后,在所有著录《中山诗话》的公私目录中,《群斋读书志》作者晁公武的生活时代距离刘攽最近,因此他在编写目录著录到此书时所使用的很可能就是党禁之前的全本。而到了距离次近的《直斋书录解题》,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百年,综合上述政治因素、讹误疑云以及传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散失,很难说陈振孙看到的会是成书最初的状态。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后来者未必不能看到更早的版本,因此,这一可能性尚待细考。
三、结 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山诗话》一书的原貌应当是三卷而非目前所见的一卷,这是将刘攽及其著作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下,在对刘攽所处的时局、他的学识与文本中谬误之间的矛盾,以及印刷时代尚没有完全到来的现实情况分别进行考察之后,对这本早期诗话著作在历代目录中“或有繁简”的著录现象所作的尝试性推论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