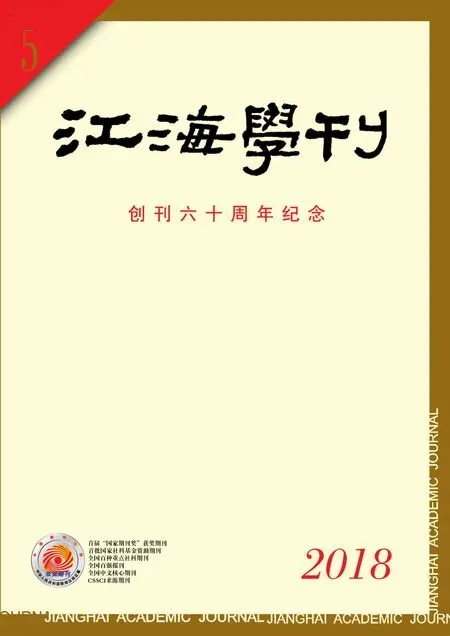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大根基
内容提要 军国主义既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制约日本真正走向和平之路的最大障碍。16世纪日本完成国家统一时,就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又利用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的优势,大力推行军国主义的国策,疯狂地向外扩张。直到1945年战败前,日本军国主义始终与崇高武力的武士道、崇拜天照大神的神道教和弘扬皇道使命的天皇制紧密结合。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大和民族心理,也给亚洲各国人民的尊严与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解构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根基,剖析大和民族的集体心理,揭示军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牢记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明治时期以来,军国主义一直是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日本的立国之本。在这种军国体制下,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整个国民生活,都从属于对外征战的需要。在1874-1945年这70余年间,日本以“开疆拓土”为目标,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和深重灾难。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一己私利,以盟军名义独占日本,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彻底清算,而受到美军庇护的侵华日军竭力以“终战”来否认战败的史实。迄今为止,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始终没有从加害者的立场去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反而在一些历史公案问题上,拂逆天下公理,践踏人类良知,美化侵略历史。为了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牢记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构军国主义的三大文化根基,以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崇尚武力为核心的武士道、以崇拜天照大神为皇祖神的神道教和以弘扬皇道使命为特征的天皇制。
武士道: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基因
日本是一个东亚岛国,长期以来,日本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造就了大和民族的双重国民性,既重视耻感文化、又崇尚武力。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借助于日本人最偏爱的“菊”与“刀”,深刻剖析了这种矛盾的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①“菊”本是日本的皇室家徽,为16花瓣8重表菊纹,借以指代大和民族的重礼好义之风,这可以看作日本国民性中美的一面;“刀是武士之魂”②,则表明日本人对强权与蛮力的崇尚,这可以视为其国民性中丑的一面。作者对日本国民性中并存的审美性和好战性的揭示,不仅彰显了这个岛国民族精神的内在矛盾,也折射出日本人既内敛、自卑,又狂暴、自傲的狭隘民族心理。长期以来,在这种独特国民性的作用下,日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畸形发展,并衍生出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以崇尚武力为核心、以武士道精神为表征的军国主义。
作为一个注重将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国家,日本历史上形成了许多称为“道”的文化,其中武士道起源于封建时代的武家政治,是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并日益发展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日本的社会心理。早在平安(794-1192年)初期,大和律令制国家就颁行垦荒令,促进了日本的土地制度从国有班田制向私有庄园制的转变,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武士阶级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而促进了武士道的产生。
起初,以农为主、兵农结合的武士为封建大名(贵族领主)庄园看家护院;后来,他们完全游离于农业生产之外,演变成为专事保护庄园和相互争斗的私家武装。平安后期,武士建立起与天皇朝廷相平行的统治政权,开创了以武家政治为特征的幕府时代(1192-1868年)。从此,掌握日本国家实权的不再是代表上层封建主利益的皇室和贵族,而是代表中下层封建主利益的军事集团。武家政治前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和德川三个幕府,延续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这是日本封建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特征。在形式上,将军名义上由天皇任命,幕府尊重朝廷,而事实上,以将军为首的幕府操纵着朝廷,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和元首,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但只是有其威而无其权的精神领袖,或政治傀儡。将军和武士之间结成的主从关系,即所谓的“御家人制度”③,是幕府政权的阶级基础。依赖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大名庄园,武士阶级不仅获得了生存空间和活动舞台,还衍生出为日本社会所极力推崇和效仿的武士道。
日本国际政治活动家新渡户稻造指出:“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④他认为,“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过去的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惠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武士已成为全民族的崇高的理想。”⑤从思想根源来看,他坚持武士道形成混合说,认为它源于中国的儒家学说、佛教的禅宗教义和日本的神道教思想:孔子在遵守五伦与处世智慧方面赋予武士道以主导思想,孟子的平民思想和丰富的人情观也充实了武士道的内涵;武士道的平常心,以及沉着、轻生慎死等秉性来自佛教;神道教的忠君、敬祖和孝顺的观念,使武士在傲慢的背后兼具服从的德性。笔者不认同这种看法,而赞成中国学者戴传贤先生⑥的观点,即“日本的尚武思想和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在《日本论》一文中,戴传贤从精神和行为两方面对武士道作出界定:精神方面包括轻生死、重然诺、尚意气;行为方面涵盖击剑、读书、交友⑦。中国台湾学者林景渊教授也指出,武士道中的“德”涵盖忠诚、武勇、名誉、礼仪、廉洁、朴素、勤学等内容,“行”则包括复仇、切腹和隐居等特殊行为⑧。武士道究竟涉及多少“德”与“行”的内容,虽然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心,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日本的武士阶级宣称腰间利刃不见血不算真武士,可见他们对“武勇”的膜拜已到了极端的程度。他们崇尚的日本刀,就是武士道精神之魂,也是“大和魂”⑨的核心。新渡户稻造自幼接受了武士道传统教育,后来又领了基督教洗礼,他作为一个学者,在那本名为《武士道》(Bushido)的小册中,一方面竭力美化和推崇日本的武士道,另一方面则对他理解的欧洲骑士精神颇有微词⑩。由此不难看出,武士道作为“大和魂”在日本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客观地说,武士道同骑士精神一样,同时具有美与丑的两面性,至多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情。
16世纪末叶,日本刚走出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太政大臣丰臣秀吉便提出“欲侵中国,灭朝鲜”的狂妄计划,把武士道精神转变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动。1592年4月,日军进攻朝鲜的釜山,揭开军国主义对外征战的序幕。在中朝人民的联合抗击下,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没能得逞,丰臣秀吉也愤懑而死。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8年),日本延续丰臣氏推行的“四民”(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这是一种类似于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其中武士为“四民之长”,属统治阶级,享有使用姓氏和佩刀的特权。幕末明初,在“王政复古”运动中,下层武士以割腕之勇气,还政于天皇,废除武士阶级的特权,结束了武士专政的幕藩制度。但是,武士道精神已浸入日本国民性之中,它并没有随着明治政权的确立和武士阶级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顽固地延续了下来,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国民生活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武家政治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下层武士不仅是“王政复古”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日本现代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明治维新时期,从政治到军事、再到产业方面,几乎所有的日本领导人都是武士出身,或是武士的后裔,武士道精神成为他们承袭或拥有的共同价值观。在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武士道原先为武士阶级专属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被明治政府改造成为日本国民的民族精神。“武士道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民及个人……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由于明治政府强化国民生活军事化,武士道不但成为日本对内毒化和控制国民思想的精神工具,也成为其对外进行黩武扩张的战争工具。
神道教:日本军国主义的神学支柱
神道教,简称神道,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神学支柱。作为一种民间宗教,“原始神道萌生于原始人对自然现象和祖先崇拜之中,形成于农耕社会祈求五谷丰登及丰收后答谢神灵的祭祀场上。3世纪后原始神道逐渐发展为有固定社、宫、祠的神社神道。”5世纪以后,日本皇室神道逐渐吸收了中国的儒家伦理学说和佛教教义,形成了“佛本神从”的神佛结合型神道。为了协调神道教和佛教的关系,765年第48代天皇称德女皇(764-770年在位)颁令,宣称她既忠于佛教三宝(佛、法、僧),又忠于神道教众神;她还自称是以出家人身份治理国家的,大臣们自然也可以是出家人。“称德女皇的诏令,反映了当时所流行的这样一种观念:神道教的神只不过是佛教神和圣者的化身”。9-11世纪,虽然佛教“在日本不但取得了正式的国教地位,而且还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但神道教作为佛教的附属物,也长期存在。
神道教由日本的原始信仰发展而来。“神道”一词,最早源于《日本书记》(Nihon Shoki)中的说法:“天皇信佛法,尊神道”。严格说来,神道教既无经典、也无教义。或许,8世纪初的两部官修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勉强算得上经典,它们毕竟承载了神道教最为推崇的天照大神(《日本书纪》)或天照大御神(《古事记》)的传说。在神祇观方面,神道教是一种多神信仰,主张万物有灵,崇拜对象极为广泛,涉及自然现象、原始神灵、民族先祖、生殖魔力等,这反映了日本人宗教文化精神的一个侧面。
镰仓时代(1192-1333年),武家政治兴盛,日本统治者极力鼓吹神道思想,神道教渐渐脱离入世思想的拘囿,形成了以神道为主、佛儒为辅的遁世宗教观。德川时期,幕府独尊儒术,强化对民众的思想与信仰控制,随之派生了神儒相融的理论神道(学派神道)。其中,吉川惟足(1615-1694年)创立的吉川神道(亦称理学神道)和山崎闇斋(1619-1682年)创立的垂加神道,都将崇拜最高的天照大神——皇祖神(天皇始祖)的神道教主张,与南宋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强调尊皇忠君的封建伦理观。垂加神道还主张神皇一体、祭政一致,赤裸裸地为明治时期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提供神学依据。德川后期,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催生出了神道复古主义,就是反对以神道教附会儒佛思想,主张依据日本的古典作品来探明所谓“真正的日本精神……创立了以《古事记传》《古道大意》《古史证》等为经典的‘复古神道’(国学)。”作为学派神道之一的神道复古派,力推“尊皇”“攘夷”,反对用佛儒思想来解释神道,为明治时期国家神道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还鼓噪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主导思想的世界秩序,极力推动日本走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为强化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明治天皇强令神佛分离,废除佛教的国教地位,拆除宫中佛殿、移走佛像,清洗神道教中的亲佛僧人,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神道”。日本“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
由于外来文化的长期影响,日本的神道教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皇室神道)、学派神道(理论神道)、国家神道和教派神道等几个发展阶段,其流变演进的历程相当繁杂,并形成了三大谱系:(1)民俗神道。(2)教派神道。又称宗教神道。(3)神社神道。又称祭祀神道。这是三大谱系的主体,得名于遍布各地的祭祀场所和宗教活动中心——神社。它以尊崇天照大神为主要内容,重视修缮神社和祭祀活动,祭祀天地神和祖先神。目前,日本全国八万多个大小神社,其中以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祭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祭祀战争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最为有名。为了强化皇国体制和对国民灌输皇国思想,明治政府把原来的民间宗教神社神道提升到国教的至尊地位,宣称战死疆场的军人都会变成“护国神灵”,将会受到上至天皇、大臣,下到平民百姓的祭拜。后来,日本的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这种急剧膨胀的皇国思想——军国主义的具体实践。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军以盟军名义独占日本,并对日进行民主化改革。为确保“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依据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对任何人均保障其信教自由,任何宗教团体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不得强制任何人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例行活动。国家及国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由于本宪法明文规定日本实行国家与神道分离的国策,神道教只能作为一种普通的民间宗教而存在,靖国神社也就失去了享受国家机构特权的法律依据。然而,又由于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是被迫进行的,这个过程掺杂了美国人的私利,试图让日本听命于他们,因而那些限制神道教和靖国神社的法律规定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战后以来,由于自民党长期执政,日本社会右翼思潮暗动,国民的靖国神社情结从未了断,政客们更是不忘为世人唾弃的军国主义幽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官员一再参拜已经被降为民间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
那么,靖国神社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日本的执政党、右翼政客以及军国主义者后裔为什么热衷于参拜?其实,靖国神社的建立,既与神道教分不开,又与军国主义的侵略史相关联。1869年(明治2年)6月,天皇颁令设立“东京招魂神”(Tōkyō Shōkonsha),目的是祭祀明治前后在内战——戊辰战争(1868年)中阵亡的军人。东京招魂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1879年(明治12年)6月改称靖国神社。至今,靖国神社正殿还悬挂着明治天皇题写“御言”的牌匾:“为国捐躯,永祭壮士魂”。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20日,靖国神社举行春季例和秋季例“大祭”时,通常由天皇或天皇使者前往致祭。这充分表明:第一,借助祭拜神社的形式来招魂,并没有悠久的历史依据,而是明治时期确立的新“传统”。第二,从明治年代起,神道教就作为一种享受特殊地位的官方宗教(国家神道),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直到二战结束以前,日本全国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理,唯独靖国神社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足见其军国主义的意义。第三,靖国神社作为一种享有特殊待遇的国家机构,受到国家的重点支持和保护。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处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桓征四郎、松井石根等14人的牌位,偷偷移入靖国神社合祭。此前,还有一千多名乙级和丙级战犯也被合祭其中。今天,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个亡灵牌位,大多是明治维新以来150年间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官兵,入祀靖国神社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此,靖国神社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更是一个超越宗教范畴、播扬武士道精神和皇国思想的政治活动场所,一个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军国主义寄托所。由此不难看出,参拜作为军国主义象征的靖国神社,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活动,更是一种超越宗教信仰范畴的政治活动。换言之,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企图重温军国主义旧梦,反对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的危险信号。
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动力
日本是一个海岛小国,其文明发生和文字形成的时间较晚,确凿可凭的信史并不长。战国至秦汉之际,成熟的中华文明传入了东亚大陆离岸的东瀛海岛。对日本早期文明的认识,不论是中国人,抑或日本人,都需要借助中国古代典籍。起初,华夏族把四方少数民族统称为“四夷”,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中的东夷,又分九种,有“子欲居九夷”之说。疏曰:“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论语·子罕》)汉代以来,东夷之一的倭人,专指日本人。先秦时代,日本尚未出现文明,中国对“倭”的详细情况阙如,仅仅知其大致的方位。《山海经》如是记述:“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东汉史家班固撰《汉书》,其中留下了关于日本的初步信息:“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最早对日本进行确切记载的历史文献。此后,中文典籍对东瀛史的记录才逐渐明晰。
日本,初为“倭”“倭国”,隋唐时正式称日本。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北九州的邪马台国是日本列岛最早形成的国家政权。南朝史家范晔在《后汉书》中有较为明确的记录:“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里称邪马台国的统治者,“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这意指卑弥呼女王独身,不临朝听政,仅满足于深居幽宫,以鬼道收拢人心,而把国务交由御弟为摄政大臣总揽。卑弥呼本为神秘的巫女,她采取统而不治的执政方法,或许就是日后天皇效法的对象。
日本文明起步固然不早,但令人费解的是日本人颇为自大,他们对《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所记关于天皇起源、日本开国以及君权神授的传说,总是津津乐道,以为信史。在谈及天皇制时,他们能从遥远古代神话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数到现今的第125代天皇明仁,所谓“万世一系”。他们相信,神武天皇是皇祖神(天照大神)的后代,曾亲率诸皇兄从日向经海路东征,“伐荒神而统大和”,在橿原宫(现今位于奈良县橿原市)即位,以治天下。那个遥远的古代应是何时?他们把神武天皇的立国时间定在公元前660年,把他即位的具体时间定为2月11日。这就是今日日本国庆日的由来。然而,这种天皇“万世一系”说缺乏坚实的信史基础,却彰显了大和主体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我们知道,用汉字编成的《古事记》作为日本第一部文学作品,分上中下三卷,内容涉及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等;《日本书纪》采用编年体例撰写,凡30卷,主要记述了从神代至持统天皇时期的历史传说。总之,它们都把神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附会为日本的创造者,并把天皇塑造成神的化身、神的后裔,宣称皇统即为神统,日本即为“神国”。由于天照大神享有最高尊位,人间的一切都要接受神的后代也即天皇的统治。日本人认为,他们作为“天孙民族”,应当统治全世界。这种好事主义者凭传说去演绎古史,既无史实、又无求证,无异于杜撰小说,缺乏起码的史徳修养;他们以含糊不清的神话作依据,来追溯、演绎天皇制的起源,实为以讹传讹,罔顾历史。这种做法,如果不是客观上反映了大和民族好大喜功、固守传统的文化心态,那么至少在主观上透露了那种无端自大、病态虚荣的军国主义野心作祟。事实上,兴起于本州中部的大和国统一日本后,天皇制才逐渐出现、并发展起来。依据唐初官修正史《隋书》,有年代可考的第一个日本天皇,当是飞鸟时代(593-710年)初期的推古天皇(554-628年)。这也是日本史上的第一位女帝。
崇拜强者、学习强者和诚服强者,这是日本人的求生之道,也是大和民族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行为哲学。推古天皇当朝时,以圣德太子为摄政,开始仿效隋唐中国,革新陈腐的大和政治,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求得中华文化真谛和佛学经论,圣德太子委派小野妹子作为首任遣隋使到访中国。607年(隋大业三年),小野妹子呈上大和国国书,其中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次年,小野妹子再呈国书时,第一次使用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文句。这是最早涉及“天皇”称呼的日本文献。以此推断,大和国称其最高统治者为“天皇”,并弃用“倭国”称呼,改作“日本”,应在隋唐之际,不早于飞鸟时代。其间,大和留学生和学问僧频繁来华,拉开了中日官方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序幕,也开启了以中国正史记载为参照的日本信史。大化初年,孝德天皇(645-654年)发布《改新之诏》,开始了一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效果更显著的改新运动。借助于大化革新,日本成功地学习和引进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实现了从部民奴隶制到律令制封建制的社会转型。
天皇制一经产生,即长久传承,至今不辍。这是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最显著特色。从8世纪起,封建庄园制的勃兴日益摧毁大化革新后律令制国家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天皇制旁落。在武家政治横行的幕府时代,朝廷权力被架空,天皇从台前退居幕后,“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仅满足于作大和民族的精神领袖。但是天皇并没有消失,也从未消失,皇室及贵族依旧受到尊重。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把神话混同于历史、将传说当成信史的民族。由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作品早已将天皇神话化、神圣化,就是把天皇的起源、传承与威力的传说,转变成为大和民族宗教信仰的“历史”依据,对天照大神及其后裔“现人神”天皇的崇拜,亦已构成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既然天皇被提升到了至上的神的地位,天皇也就成为“神国”日本的至尊权威,而不是绝对权力的象征。这也就为后来下层武士打着“王政复古”旗号的倒幕运动和德川将军向天皇朝廷奉还“大政”提供了神学依据。
16世纪末叶,日本迫不及待地把目光投向海外,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之路。只是由于德川初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才暂时受到了抑制。不过,这个蕞尔小国从未放弃军国主义扩张梦,就是企图以小搏大,主动出击东亚大陆,甚至吞并全世界。18世纪初叶,军国主义理论家和西化推动者佐藤信渊(1769-1850年)发表《宇内混同秘策》(A Secret Strategy for Expansion)一文,首倡“和魂洋才”精神,鼓励国民在西方列强威胁面前,既要保留日本传统文化,又学习西洋科技,通过积极的经济与军事改革,推动日本加入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所谓的“宇内混同”,就是“世界统一”的意思。那么由谁来统一世界呢?佐藤信渊坚持“皇国史观”,他狂妄地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和“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就是呼吁日本来统治世界。为此,他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还杜撰出一个“大东亚”的政治术语,其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论调,为明治政府的亚洲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幕末明初,日本结束了近七百年来将军和天皇二元并立的政治格局,重新确立起中央集权体的天皇制。它再次借助于变革图强,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摆脱了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命运,迅速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由于受制于国内市场狭小、封建残余深厚、列强扩张威胁等多重因素,明治政府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还积极构建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拼命挤进帝国主义阵营,以图参与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1869年设立兵部省,培养军事人才,扩建兵工厂,目标是推进军事现代化。1871年,先设立陆军参谋局作为兵部省的外局,再撤销参谋局,改设参谋本部,使之直接隶属于天皇的控制下。由明治天皇直接推动的兵部省官制改革,造成了军部机关高于政府的不正常局面,也使维新政权添增了军人专政的鲜明色彩。比较来看,幕府制度下的武家政治,不可与明治时期的军人专政相提并论。表面上,明治军人专政是向武家政治传统看齐,而实际上,军人专政不啻是对传统的超越。因为在幕府制度下,武家的作用主要局限于内战,就是在日本列岛内的打斗虐杀,而明治以降,军人的作用完全是海外的,推进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19世纪中叶,经过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日本已从羸弱状态中崛起,并表现出认同武家政治文化的社会心态和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企图构建一个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目标的所谓“大日本帝国”。
具体来说,日本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承袭了“忠君、节义、武勇”的武士道精神、“大和中心论”的神道教狭隘民族主义。为了维护天皇的神性和大和民族来源的神圣性,日本还以立法形式确立起以神道教为信仰基础的皇国体制。1889年(明治22年),日本公布以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以“君权神授”和“主权在皇”为立宪原则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共7章76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2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4条);“天皇依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第5条);“天皇批准法律,命其公布及执行”(第6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1条);“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第13条)。根据这部钦定宪法,明治天皇拥有被称为“天皇大权”的广泛权力,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与宗教之大权于一身,从而摆脱了武家政治时期天皇有其威而无其权的虚君局面。日本学者井上清指出:“按照天皇制,军队统帅权就是天皇大权。”随着天皇权力的强势回归,天皇就成了权力与威力相统一的专制君主,为军国主义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精神动力。正是在明治时期,日本开始大肆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走上了一条以“开疆拓土”为目的的军国主义不归路。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代统治者都极力神化与美化天皇制,尤其是利用武士道精神、神道教信仰以及教育和立法手段来宣扬天皇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将“神国”观念强制性灌输给青少年,欲使大和民族能一代代地永远保持对历史上一直起着独特作用的天皇制的崇拜,以服务于军国主义扩张的需要。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被迫发表皇室诏书《人间宣言》,承认天皇不再是“现人神”,不再具有神性和至上的权利,而是个凡人,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天皇走下神坛,恢复其凡人面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长久以来国民对天皇心存的敬畏和愚忠。但是,美军为了长期占领和控制日本,没有像废除神道教国家地位那样去摧毁天皇制,而是仅对天皇制进行了适当改造,使之成为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既然如此,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裕仁天皇,就堂而皇之地由日本最大的战争罪犯,转变成为《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体制下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从而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今天,即使在大多日本国民心中,天皇依然还是大和民族和日本国的保护神,当然也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综观日本史,以崇尚武力为核心的武士道、以崇拜天照大神为皇祖神的神道教和以弘扬皇道使命为依归的天皇制,既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大根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追溯历史,剖析日本军国主义,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而是否反省历史,是考验日本是否真诚谢罪、记取历史教训的试金石。日本只有放弃错误史观,彻底清算自己的战争罪行,避免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才能放眼未来,真正融入亚洲和国际社会。
③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⑤[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彥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3、89-90页。
⑥即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人物戴季陶(1891-1949年),著有《日本论》,其中言简意赅、精辟透彻地解剖了日本文化的要旨。
⑦引自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80年,第2-3、10页。
⑧参见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80年,第六章、第七章。
⑨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新渡户稻造为向外国人介绍日本的传统文化,乃用英文写成《武士道》一书,副标题就是“日本魂”(The Soul of Japan)。
⑩这里,作者借用了英国史学家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 1777-1859)的论述。参见[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彥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