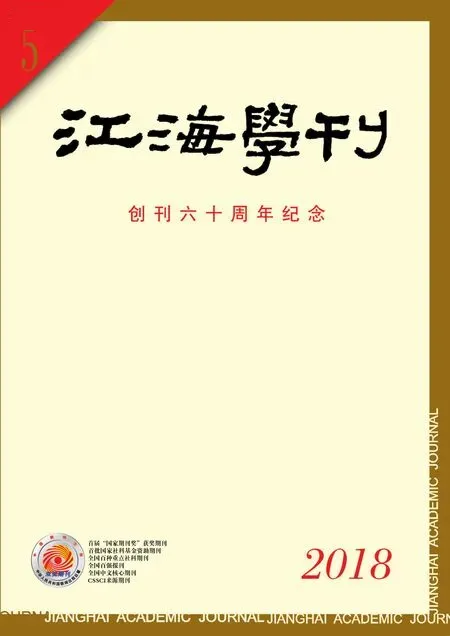从暗面到亮面:反身性的再转向及其效果*
内容提要 “反身性转向”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涌现的一股炙手可热的学术思潮。“反身性”的多元内涵之间隐含着“反思”和“自反”的紧张。第一次“反身性转向”凸显的是现代性的暗面。但在米德等实用主义思想家的学术脉络之中,潜伏着“反思”引导和控制“自反”的维度。2000年前后,英国社会理论家阿切尔推动的“反身性的再转向”,接续和彰显了米德这一传统,让现代性的亮面得以光大。暗面和亮面的分化,折射出当代人类矛盾的生存境况:一方面风险社会并非耸人听闻,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每一个“积极施动者”。“一般化他人”“社会理性”和“团体能动性”的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为反思和自反相结合并让现代性的亮面照进现代性的暗面,提供了可能。
“反身性”的涌现及其凸显的现代性暗面
“反身性”(reflexivity)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西方学界涌现的一个核心概念。霍兰德曾说,“1968年我开始对‘反身性’感兴趣时,社会心理学的文献和辞典上还没有它的踪影,而到1989年我翻开《牛津英语辞典》第二版时,却惊异地发现这个令人费解的概念已成一种公共资财。”(Holland,1999)这个表述再现了“反身性”在西方学界的地位的戏剧性变动。到世纪之交,有学者更为肯定地说,“反身性”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不言而喻的真理”(truism)(Cant & Sharma,1998),整个有关“实在”的研究出现了“反身性转向”(reflexive turn)(Maccarini & Prandini,2010),阿切尔甚至断言:“没有反身性就没有社会。”(Archer, 2007:25)。
从20世纪60年代的“籍籍无名的小兵”(Archer, 2007:62)到20世纪90年代的“不言而喻的真理”的华丽逆袭,带给“反身性”这个概念的不可能是清晰的内涵界定和合乎逻辑的理论建构,而恰恰是相反的情况:用法混乱和内涵莫衷一是(参见Bartlett,1987; Suber,1987; Lynch, 2000),以致阿切尔(Archer, 2007)抱怨在社会理论中,反身性是一个有待破译的“密码”。
阿切尔的批评并不公允。早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就开始在厘清反身性的多元内涵及其关系上大费周章。这些研究的一个普遍切入点是澄清从“反思”(reflection)或“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向“反身性”的转变所蕴含的深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譬如,博雷纳认为,“反思”指涉的是理性主义的反映论(mirror),是主体在特定理念和实践范围内的自我澄清,而非对这些范围边界本身的追问和质疑;反身性则同传统认识论对立,是一种“反常话语”(abnormal discourse),是对常规的理性主义探究行动所特有的自满情绪和对自身某些部分的无视的扰乱甚至破坏(Pollner,1991)。博雷纳的这种辨析代表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观点,强调了“反身性”对于代表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反思”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参见Sandywell, 1996;肖瑛,2005a)。
基于西方学者的论述,笔者曾把“反身性”的多元内涵及其关系简化为一个范畴:反思与自反。其中,“反思对自反的关系,是‘以一种反身性来治疗另一种反身性’;自反对反思的关系,则是以一种反身性来宣告另一种反身性的无效。这样就在‘反身性’内部形塑出‘以一种反身性反对另一种反身性’即反思与自反相互对抗的独特景观。”(肖瑛,2004a:82-83)在第一次“反身性转向”中,主要是以自反来否弃反思,以揭露现代性的暗面为谋。
反身性视角下现代性的暗面,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出现的“曼海姆悖论”,以及该视角被科学知识社会学派(SSK)接受并对所有科学活动进行分析,导致了科学的全盘相对主义化(参见肖瑛2014b),科学由此成了雨果所说的“自啮尾巴的蛇”;一是反身性现代化理论关照下,晚期现代性阶段的人类社会成为“失控的”“风险社会”(参见肖瑛,2005b,2007)。
现代性的亮面:米德对“反身性”的反思性运用
反身性的专利并非是现代性的暗面。其实,在“反身性转向”发生之前和发生之时,其对现代性的亮面之彰显就已经在运作:在社会学认识论上,布迪厄(布迪厄、华康德,1998)以“社会学的社会学”来突破“曼海姆悖论”,重建社会学的客观性;在实践领域,“反身性系统治疗”(reflexive systemic therapy)(Deissier,1998)、“反身性考古学”(Hodder,2000),都是运用反身性来获取积极的职业效果的尝试。最为重要的是,早在20世纪早期,美国实用主义学者如皮尔斯、米德就在以反身性为视角来构建积极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米德在“我想要更加积极的生活”(转引自赵立玮,2017)的使命感召下,其社会行为主义和历史哲学的建构,都是在“反身性”的旗帜下展开的。
(一)反思与历史的自我循环:历史的反身性构成和变动
米德反对自然主义的时间观念,认为单纯时间的自然流逝没有意义,构不成历史。他要表达的观点是:历史是反身性地建构而成的,每一个过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从它自身的立足点对它的过去进行重构”(米德,2003:16)。建构的立足点是“现在”,但目的指向“未来”,“我们准备做的事对我们正在做的事发生影响”(米德,1992:63),亦即“未来”影响着“现在”。具体言之,突生的东西塑造一个与“过去”不同的“现在”;在“现在”的立场上想象一个“未来”;为着“未来”,基于“现在”,形成一个重建“过去”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下,“既定的过去”在唤回者面前呈现新的形态,“如果出现了突生的东西(emergence),那么这种突生的东西……会导致一个新的过去”(米德,2003:17;Mead,1932: 9),“构建过去的材料就在现在中”(米德,2003:51)。质言之,“过去(或者说过去的意义结构)和未来一样是假定性的”(米德,2003:21)。但若仅仅这样来理解历史,就会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沼。事实上,米德还看到了相反的情况:“所有历史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在于它对现在的解释和控制”(米德,2003:48),“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以空时的方式决定了将要出现在未来的事情”(米德,2003:24)。换言之,“过去”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影响“现在”和“未来”。
上述讨论引申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理解“现在”?第二,历史的反身性自我循环是自然主义的还是带有人的主观性?更为准确地说,自然主义和主观建构在具体历史脉络中表现出怎样的关系?
先来看第二个问题。历史的反身性自我循环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自然主义的。个体或群体虽然在时间之中,但不仅对时间而且对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没有意识,因此“历史”并不存在。第二个层次是实践意识层面的。历史中人“习以为常地监控着自己所处情境的社会特性和物理特性”(吉登斯,1998:65),即他们始终是具体历史脉络中的存在者,并参与到塑造现在以及现在、过去、未来的循环之中,但很少自我反思自己的这些努力对于自己和历史的意义,只是把一切交给特定的习俗或韦伯所谓的“命运”。历史中人参与反身性地“重构”历史的活动就这样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地进行着。第三个层次是自我反思性的,个体或群体较为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正在重新理解过去,并知道这种重新理解不可规避,因此想方设法对这个理解过程进行控制,以建构一个同自己对未来的预期相符合的过去。只有到第三个层次,人是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在控制和引导反身性,历史中人的主体性才得以显现,反身性过程本身才变得有意义,“历史”处于人的自觉建构的脉络中,其确定性和开放性相伴相随。
但是,“自我反思”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试图“对所有已经过去的过去都做出说明,并且将这些说明纳入最新提出的陈述之中”(米德,2003:13)。这种“试图”,建基于启蒙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相信理性主义的反思可以洞察已发生的所有反思和反身性现象。但米德认为,“既定过去”是无限的,而人的活动、思想和陈述始终是“有限”的,用“有限”来应对“无限”,其结果依然是“有限”的,因此是无意义的(米德,2003:13-14)。换言之,第一,过去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唤回”的;第二,要通过理性主义的反思让所有已发生的事情都变成可知和可控的“历史”,无疑是痴人说梦。“想要使科学研究中的技术精密到绝对准确的程度的努力已经一败涂地”(米德,2003:58);第三,理性主义的反思,其实就是笛卡尔(2000:23)所谓的清除“沙子和浮土”然后找到“磐石和硬土”的工作,但问题是历史的每一步都建立在有意无意的“假设”基础上,不仅“沙子和浮土”不可能真正清除,即使得以清除,剩下的不会是“磐石和硬土”,而是虚空,即伍尔加的“后设反身性”(meta-reflexivity)式的无穷倒退(参见Latour,1988)。进一步看,理性主义反思的上述困境,暴露了反思性反身性同循环性反身性之间的紧张:第一,对米德而言,循环性反身性就如如来佛的手掌,是无边无尽的。反思作为历史中的行动必然被卷入其中难以挣脱;第二,面对历史中无限的循环性反身性成果,进入“自我反思”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这两点都决定了理性对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控制能力的有限。
但是,米德并不因此而心生失望,相反,他乐观主义地分析历史和社会的构成及演变,认为人的“反思”虽然是有限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建构和未来控制能力,“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对过去进行重新表述,把它表述为未来的限定条件,从而使我们可以控制它的再次出现。”这种乐观主义,来自理性的人们可以从现在出发,基于对未来的目标和想象,如自己所愿的那样来重建作为行动条件的历史:“我们不能使这些过去就像它们当初曾经发生的那样重现,我们只能使它们以它们现在出现的那种方式出现。彻底展现它们的方式只能是重新经历它们(reliving them)。”(米德,2003:27)在这里,反思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引导和利用循环性反身性,从而对历史进程施以控制和引导。
从逻辑上看,米德的这种不同于启蒙理性主义的历史乐观主义还是建立在有限反思和无限反身性的矛盾基础上。如何纾解米德的困境?答案也许只能从反思和反身性的辩证循环所造成的实际历史效果而非矛盾本身中寻找,即历史可能只是对过往的不断重复,而无所谓进步。在这个逻辑里,要么“反思”没有发挥作用,要么“反思”特定历史的参照系始终来自该历史经验自身而非之外。另一可能,就是个体或群体带着旧的历史烙印进入新的历史场景中:“属于一个系统的物体,由于它和系统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它就具有相应的性质,当这个物体过渡到一个新的系统秩序中,它就会将旧的系统中所有成员的某些性质带进它在新的系统中所进行的重新调适过程之中。……而在革命中,旧的系统就会变成新的秩序赖以建立的结构。”(米德,2003:90)这样,“反思”没有给“反身性”带来新的要素,历史要么是在原地踏步,要么开启了一段扩大的循环。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米德的想法。虽然“一些同一性条件从过去一直维持到现在”(米德,2003:86),但是,历史“并不能决定突生性事情的全部现实特征”(米德,2003:29;Mead,1932:16)。也就是说,历史的“突生性”(emergence)和“同一性”(identity)(Mead,1932:32)是同时发生的。不仅如此,同一性既可能同突生性“相互排斥”(米德,2003:134),又可能“使得新的物体得以幸存并维持自身”(米德,2003:81)。
分析“突生性”的来源,有两个角度:第一,“我们对过去的重构是随着它延伸的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这些重构并不认为它们是一劳永逸的终极结果。一旦发现新的证据,总是有可能对它们进行重新阐释,而这种新的阐释可能会更加完善。”(米德,2003:52)这是一种相对客观化的立场,强调新的证据是重构“过去”的凭依,就如很多新的考古发现会改变人们对某段历史的既有认识一样。第二,“在将那些体现在个体身上的各种倾向组织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突生的力量,赋予这些倾向以一种唯有这个个体的处境才具有的结构。当从已经过去的时间流程和这一流程所暗含的(对现在的)限定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各种倾向,对这些倾向的组织化结构发挥作用时,它们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米德,2003:31;Mead,1932:17-18)这个说法凸显了历史的主观性,每一个体都有建构历史的能力,而且,不同历史个体的生平和理性不一样。因此,即使个体之间对无数过去的选择和重建都是一样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些不同过去的组合也具有个体自己独特的方式和结构,因此其所生产出的未来不可能相同。但是,米德并不认为历史就是纯粹个体的历史;事实上,具体个体的独特性需要进入到他所属的共同体的“组织化结构”之中,转换为一种共同的力量来发挥历史性作用。在这些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循环性反身性在多个层次和维度上运转:(1)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2)个体与所属共同体之间;(3)历史中人与具体历史之间。反身性机制的不停歇活动,实际上是在时时刻刻重建过去,改变未来的路向。而其“突生性”的关键机制,是“反思”也被卷入到这些循环之中;而且,“反思”一定会把某段历史之外的因素引入其中来建构未来、现在和过去;因此,只要有“反思”的卷入,“循环性反身性”就一定是在不断地同时延续和更新历史,每一次循环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效果。这也是过去不可唤回的原因之一,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根本。
行文至此,我们顺便回答一下前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突生性”之所以对于历史如此重要,关键在于它为历史中人区分历史,即把历史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历史的“‘真实的绵延’(real duration)是通过独特事件(events)(这些事件是通过它们质的差异而彼此区分开来的)的出现而成为时间的”(米德,2003:38),“我们正是借助这种独特事件来区分流逝过程,将它划成不同的阶段”(米德,2003:67)。“事件”是历史成为历史的直接表现。但是,“没有突生性,就没有可以相互区分的事件。”(米德,2003:84;Mead,1932:49)有了独特事件的不断再生产,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在时间节点上,而且在各自的内容和意义上,都进入不断的循环性再生产机制中:历史中人以新出现的事件给“现在”定位,这个独特的“现在创造了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它自身的时间尺度是随着这个突生事件的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米德,2003:40;Mead,1932:23)①突生事件对于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让世界变得不同,让历史中人不得不重新界定时间,而且还让世界充满偶变性和不确定性(米德,2003:74-75)。正是这个原因,今天的一些社会学家特别强调“事件”的地位,并将“历史社会学”称为“事件社会学”(应星,2016)。
上文分析了反思和反身性的循环关系下的历史效果,但没有很好地回答一个问题,即未来的突生性在反思理性的边界之内吗?米德(2003:54)说,“我们的过去和我们对将要到来的未来的想象一样,都是心理过程。”这句话表达了历史与历史中人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历史中每一个具体个体的心智(mind)和自我(self)结构中。
(二)心智:反思能力的反身性构成
首先,何谓“心智”?心智就是自我意识,“我视之为心智特征的是人类动物的反思的智能”(米德,1992:105),即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的自我反思结构。其次,心智是如何产生的?毫无疑问,心智需要特定的生理基础,但这个基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只有当社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或者说出现在该过程所涉及的任何一个特定个体的经验之中时,心智才在该过程中产生。”因此,心智不是原子主义式的,而是一个引入其他环境和参照系来进行自我反思的社会结构,心智是通过意识到自己参与某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其他参与该过程的个人发生关联,自己在参与过程中的行动和互动改变着该过程。“当整个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进入该过程所包含的任何一个独立个体的经验之中时,当个体对该过程的顺应受到他对它的意识或了解的更改和限制时,心智或智能就逐渐显现出来。”最后,反身性机制是人和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同时也是心智形塑的基本机制,没有反身性就没有自我反思的心智:“正是通过反身性(个体经验返回到他自身),整个社会过程被引入该过程所涉及那些个体的经验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个体能够对他自己采取他人所取的态度,能够有意识地使自己顺应那一过程,并且在任何特定社会动作中用他自己的顺应更改那一过程的结果。因而,反身性(reflexiveness)是心智在社会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米德,1992:119;Mead,1934: 134)
姿态会话是这种反身性机制的具体表达(米德,1992:41-42;Mead,1934:c47-48)。我们可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想象姿态会话培育心智的具体过程。最初,是两个相遇的个体之间尝试展开交流。其中一个个体在向另一个体释放某种姿态以求表达自己渴望传递的某种意义时,他首先是反问自己这个姿态的意义是什么,让自己明白自己所渴望表达的意思;然后,他努力地把自己想象成对方,想象对方对于自己所传递的姿态的态度,对其背后的意义的理解,以及相应的回应。对于表达姿态的人而言,对方的态度和反应一定是他自己所渴望的态度和反应;再往下,接受姿态的一方果真如表达姿态的一方所愿的那样表达了相应的态度,做出了相应的回应,表达姿态的人受到鼓励,进入下一步的姿态表达。可以想象,如果第一次互动没有成功,两个个体会反复地从想象对方的角度来反观和推敲自己怎样才能表达一种能让对方充分理解并做出合适回应的姿态。若互动成功了,则意味着特定姿态和特点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这两个个体之间得以确立,并在随后的互动中得以稳定化,即特定姿态成了特定的表意符号。从具体姿态到表意符号,有一个抽象化的演进。这个演进,为双方之间建立起了一些共同的表意符号和符号理解,从而为进一步的交流创造了初步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初步的交流工具。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以后的不同个人之间的交流就有了“特定的社会动作或社会情境”。随着姿态交往的反复发生,参与姿态交往的人员越来越多,交往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具体姿态的抽象化、普遍化和稳定化的程度也在相应提高,一个个拥有共同意义体系的共同体就慢慢出现。
姿态会话的过程是多重反身性相互交织的过程:通过个体内部的自我会话来确定自己的姿态与所有表达的意义之间是否契合;通过虽然在个体内部发生但实际上是个体自身同想象他人之间的会话,来确定姿态会话能否成功。“合理行动始终涉及一种反身自指(reflexive reference to self),即,向个体指明他的动作或姿态对其他个体所具有的意义。”(米德,1992:109; Mead, 1932: 122);通过个体外部的会话即个体同他人的姿态会话来确定会话是否成功;个体内部的两种会话是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会话作成功保障的。但就姿态会话而言,无论是内部会话还是外部会话,都具有生产性效果,即:(1)生产和再生产各种抽象化和模式化的意义和表意符号,这些意义和表意符号的组织化和结构化构成社会性情境,为后续更为丰富、深入和宽泛的交流规定方向并提供工具;(2)当社会情境涌现后,符号交往的反身性维度也在增加,即增加了个体或群体同社会之间的反身性关系,一方面,“社会过程及其各种影响被个体经验实际接受下来……在一定意义上它在个体身上得到重演”,另一方面,“在这姿态会话中,个体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改变着社会过程自身”(米德,1992:159-160);(3)生产和再生产个体的心智。人和人之间第一次非社会情境的偶然的姿态会话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即非反思的,“我们在他人身上引起我们在自身引起的某种反应,以致我们不知不觉地模仿了这些态度。……我们不断在自身引起我们在他人身上引起的那些反应,尤其是通过有声的姿态,使我们在自身的行动中采取了他人的态度。”(米德,1992:61)但随着表意符号这一抽象化进程的推展,人的心智开始发生,人开始成为“思考的个体”,其行动开始变成“富有意义的行动”(米德,1992:65),并随着姿态会话的进一步推展而发展,达到理性化层次:一是超越身体的限制而理解甚至创造抽象化的意义体系的能力;二是能同时扮演自身角色和他人角色的能力,“当动物进入一个范围更大的系统,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结果是它扮演自身角色的过程能够促使它自己同时扮演其他的角色,而扮演这些其他角色又是它扮演自身角色所必需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动物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即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自身的对象。正是这一发展使借助沟通媒介来维持其生命过程的社会成为可能。在这里,具有心智的生命产生了。”(米德,2003:143);三是由这种能力而来的社会性能力。“心智健全的有机体可以同样拥有社会性(sociality)的其他方面”(米德,2003:135),即在所遭遇的新旧系统之间调适的能力。
心智的产生和发达,意味着姿态表达所内在的反身性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姿态表达的个体不再是任由反身性机制推搡、卷入和挤压而不自知的零件,而是能洞悉自己所预定要进入的姿态表达的反身性机制,并可以通过自我反思来获悉自己在这个机制中占据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还能在卷入其中的同时反过来调控和引导这个机制,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标,如让自己更好地适应情境,或者改造他人和该社会情境:“它使个体有机体能够有目的地控制和组织它的行动,即……有关它涉身其内并对之做出反应的各种社会情境和物理情境的行动。”(米德,1992:81-82)进一步看,由于“反思的行动……指涉未来的存在”(米德,1992:106),个体对自己所卷入的反身性机制的认知和引导,达到的效果不仅是改变现在,而且指向未来,未来也就不简单地停留在自然主义的层面而成为建构的对象。
心智即反思能力从历史的反身性机制中形成并反过来成为重构历史的主体力量。这个结论呼应了米德的历史是一个心理过程的判断,但还是没有回答历史的突生性或曰新颖性和同一性的来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入对“自我”的理解中。
(三)作为“一般化他人”的“自我”:共识何以可能
“自我”和“心智”的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几乎是同步始于并成于社会生活;“自我”本质上是“心智”将社会经验和态度组织化、结构化并内在化的产物,只有通过“自我意识”“在我们自身唤起我们在他人身上唤起的一组态度,特别是当它是一组重要的、构成共同体成员的反应的时候”(米德,1992:144),“自我”才出现。换言之,“自我”不是相对于“社会生活”而独自生长和存在,而是占有和分享特定群体的“集体人格”。米德把这种从个人角度出发获得的“集体人格”称作“一般化他人”(the generalized other):“他把自己置于一般化他人的位置,后者代表了群体所有成员的有组织的反应。正是它指导着受原则控制的行动,而具有这样一组有组织的反应的人便是我们在道德意义上所说的有品格的人。”(米德,1992:144;Mead, 1934:162)
同“心智”在姿态会话中成长一样,“一般化他人”也是在类似的活动即“角色扮演”中形塑的。“角色扮演”有游戏和竞赛两个阶段。这不仅是个人生命史的映照,也是人类和人类社会演化的阶梯。竞赛阶段是“一般化他人”的关键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心智”才具有结构化和整体化的能力,推进个人与具体社会成员和特定社会群体以及群体所属社会环境之间循环往复的试错-调整-成功-抽象化和结构化的反身性交流,并将结构化和整体化成果内在化,形成“自我”。这个反身性机制,同心智的形成机制没有本质差别,故此处不赘。需要强调的是,“一般化他人”要达到的目标是超越个人之间推己及人和推人及己的“切人”层次,而进入社会层次:“仅仅采取人类社会过程中其他个人对他以及彼此之间所特有的态度,仅仅这样把整个社会过程引进他的个体经验,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像采取其他个体对他以及彼此之间所持的态度那样,采取他们对他们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或社会群体的成员而参与的共同社会活动或一系列社会事业的各个不同阶段不同侧面所持的态度;而且他必须一般化这些个体对整个有组织的社会或社会群体本身的态度”(米德,1992:137-138;Mead,1934:154-155)。
“一般化他人”或曰“完整的自我”所表征的是个人与特定社会的完全合一。“只有通过个体采取一般化他人对他们自身所持的态度,才为具有共同的即社会的意义、作为思维的必要前提的那一系统即论域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进一步看,有了这种价值基础,个人才能成为该社会秩序的积极拱卫者和该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对于他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或共同体(及其某些部分)在任何特定时间所面临的问题,在该群体或共同体所从事的各不相同的社会计划或有组织的合作事业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采取或持有该群体或共同体的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并且,作为一个参与这些社会计划或合作事业的个体,他据此支配自己的行动。”(米德,1992:139;Mead, 1934:156)但是,这种合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虽然从个人主义角度看,是“个人”参与“社会”,但从“社会”角度看,毋宁是“社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个人”只是“社会”的影子。正因为同一社会中的个人拥有共同的“一般化他人”即“自我”,所以,该社会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同一性似乎就不再是一个问题。这样,随着沟通媒介的日益抽象化和普遍化,历史上的形同部落般的社会组织之间的边界被夷平,整个人类按照合理性(rationality)原则统一起来,那么,“历史的终结”和“主体之死”也就到来了。②
这一结局显然同米德的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的观点相违背。事实上,米德在强调历史的同一性的同时一直寻求个人主体性与历史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每一个具体的自我都是独特性和结构性的结合:“我们并非只是人有我有:每一个自我都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自我;但为了使我们能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必须有一种共同的结构性”(米德,1992:145)。首先,只要有反身性就有社会和个人的变动。“在这姿态会话中,个体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不断改变着社会过程自身。……他采取他人对他的刺激所持的态度,在采取那一态度时他发现它已改变,因为他的反应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反应,并导致进一步的变化。”(米德,1992:159-60)如前所述,采取他人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模仿,亦非生理上的刺激—反应,而是有意识的自我的过程,是个体在自己的心智内部,根据他人的姿态、语言及其蕴含的意义的想象而作出的或恰切或不恰切的回应,这种回应不同于他人的姿态。一旦作出回应,就会既影响对方也影响自己,并反身性地进入社会过程,影响社会过程的进程和方向。“这种变化可能是合意的,也可能不合意,但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米德,1992:192)
其次,“社会”是复数的。“引起人格分裂现象的,是一个完整、单一的自我分裂成了构成这个自我的许多部分的自我,这些自我分别与这个人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得他的完整单一自我的那个社会过程的不同侧面相对应;这些侧面即他在那一过程中所属的不同社会群体。”(米德,1992:128)换言之,即使由“合理性”所代表的共同体也不可能是单维度、单层次的;正是社会现实的多维度和多层次,让个人获得的“一般化他人”也呈多样性,表现出人格即自我的分裂,越到现代社会,这种情况越严重;另外,现代性的增长同人的“心智”基本上是同步的,自我在多重决策和选择中必然遭遇不完满的尴尬,造成人格的分裂。社会的多样化和自我的多样化被卷入到反身性进程中,结果自然是历史的变动性和突生性的不断涌现。
最后,这种社会的多样化和人格的分裂,在个人的“自我”中最为典型且正常的表现是“主我”(I)和“客我”(Me)的分离和反身性结合。“主我”作为社会经验的沉淀,“实际上是作为‘客我’的一部分在经验中出现的”(米德,1992:157)。③但是,如上所述,在分化社会中,同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作为组成元素的诸多自我”(compontent selves)(Mead, 1934: 144),它们在个体面对不同社会情境时,可能彼此分离,“把正在做某事的那个个体同对他提出该问题的‘客我’区别开”(米德,1992:157),“客我”就是该情境在个体身上的具象化,“但‘主我’始终有别于情境本身的要求”(米德,1992:158)。而且,悖谬的是,反身性是“自我”的构成性特征:“自我”就是“一个反身性构成”(Sandywell,1996:251),“表示那个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的东西”,也就是说,自我可以“作为其自身的对象”,“自我以某种方式进入对自我的经验”(米德,1992:121)。这意味着自我内部的循环中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主我”和“客我”的分化。“‘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组他人态度。”(米德,1992:155)但是,即使有这种功能的区分,也会出现“客我”替代“主我”即主客体合二为一构成一个完整自我的情形,如发生在宗教、爱国精神和集体工作中的(米德,1992:241)涂尔干式的集体欢腾。自我内部的反身性循环,还表现为“主我”和“客我”在时间轴上的相互转化(米德,1992:155)。
“主我”与“客我”的区分以及其间的循环性反身性关系,无论对于“自我”还是对于“自我”所处的“社会”都至关重要。一方面,在现代分化社会,个体占有的多重“自我”就像舒茨所谓的“手头库存知识”一样,面对不同环境时可以祭出不同的“自我”,而且在这些应对中不断地接受新的社会经验,实现自身的不断更新和重组:“他不仅采取他自己的态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采取他的下属的态度”(米德,1992:172);另一方面,“自我”把自己从其他社会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带入具体社会环境的适应中,通过“主我”审视、支持或反对“客我”的方式实现对具体社会环境的改变。“向未来前进,是自我、‘主我’跨出的步子。它是‘客我’所不具有的某种东西。”“‘主我’……包括一种新的成分……产生自由的感觉、主动的感觉。”(米德,1992:157-158)具体言之,假如一个人要改变社会,“是建立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可能得出与周围整个环境相反的观点”。这“更高级的共同体”就是“主我”。但是,“主我”实现自己目标的前提是“他必须用理性的声音对自己说话。他必须理解过去与未来的各种见解。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一种超出该共同体的见解。”也就是说,“主我”的前提是“客我”,唯其如此“主我”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如“改变事物的秩序……把共同体的标准变成更好的标准”,“社会得到进步”(米德,1992:149)。韦伯说的历史的“担纲者”,在米德这里,就是把“主我”和“客我”很好地统一的杰出个人和群体(米德,1992:167、192、193)。
“自我”的价值不止于此,它还是抽象社会与具象个体循环互动的基本条件。同很多人以韦伯的“铁笼”(iron cage)或后来帕森斯的二元论的模式变量为视角观察现代社会不同,米德认为,抽象和非人格化的社会,也是由活生生的具体个人建构的,抽象性和具象性是社会构成和变动的一体二面;而且,历史的人格化使得历史中的个人对历史负有了“自觉的责任心”(米德,1992:158);此外,正因为“自我”的同一性,历史很难断裂,“倚靠个人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米德,1992:274)。这类将抽象关系具象化为自我之间的“认同”现象,即使在被视为完全按照“切事”规则运行的市场社会中也不可规避,因为市场中人必须“越来越具体地采取他人的态度……必须与其他个体结成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不仅要参与这个特定的交换,而且要弄明白他需要什么以及他为什么需要它,支付条件将是什么,所需货物的特定性质,如此等等。”(米德,1992:261)像亚当·斯密一样,米德由此给市场经济社会打上了道德和伦理的烙印。④
上述分析是“主我”同“客我”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理想合作模式,反思力量有效地引导着反身性机制,历史在同一性和突生性的辩证关系中向前演进。但是,换个角度看,“自我”的这两个部分之间也可能发生严重冲突:“客我”作为特定社会情境和共同体的组织化的“一般化他人”,代表该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价值,“号召自我为整体而牺牲”即“自我的自杀”(米德,1992:190),以维护一个“有秩序社会”(米德,1992:196);“主我”则是“绝不可能完全预测”的、“始终有别于情境本身的要求”(米德,1992:158),是自私和反社会的,甚至是冲动的(米德,1992:205);而且,如前所述,不同个人的“自我”也是各有千秋。“自我”的这种内部冲突,会把历史带向何方?米德(1992:269、284)承认,自我的冲突肯定会存在,有时候还很激烈。但是,(1)既然“主我”属于一个人拥有的多个“一般化他人”,那么反社会的行动“在其最宽泛和最严格的非伦理的意义上……是社会的”(米德,1992:267),即“主我”最终摆脱不了“一般化他人”的羁绊;(2)随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反身性建构关系的推进,不仅“社会”而且“自我”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本能的冲动在降低。因此之故,个人会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健全人,必须“做一定量的老一套工作”(米德,1992:189)即首先扮演好“客我”,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与整个社会的生死与共,“社会重建和自我或人格的重建,是一个过程即人类社会演化过程的两个方面”(米德,1992:271; Mead,1934:308),⑤从而“可以高度发展存在于他自己天性中的各种可能性,而且仍能采取他所影响的他人的态度”(米德,1992:284)。当然,无论自我如何发达,其中的“无意识”和非理性成分、主我和客我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现象还是不可能消除,它们不可规避地卷入到自我和社会的反身性循环之中,削弱甚至破坏自我反思对反身性的引导和控制。需要承认的是,这些都是一个“必须为个体本身的表现留下余地”的社会(米德,1992:196)必须付出也能够接受的代价。而且,有了“自我”的这种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历史才一方面不陷入决定论的泥沼,“不存在社会进步必定朝着它前进的固定的不可变更的目的或目标”(米德,1992:258),另一方面在突生性和同一性的交错再生产中前行。
强调“自反”对“反思”之宰制的社会学家都认为悖论和诠释循环维度的反身性就像一个永动的、巨大无朋的“利维坦”,吞噬的是理性,吐出的是相对主义和不确定性。米德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但同时认为:反身性本身包含着生产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能力的机制,拥有特殊神经系统的人在姿态会话这一自然的反身性中不仅在不由自主地生产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在生产人自身的理性能力、自我意识和自我,生产心智对反身性的有意识调节和引导,生产社会的抽象化、普遍化同多样化的统一,生产自我的多样化和同一性的统一,生产历史的同一性和突生性的统一;虽然自我反思能力不可能反过来完全控制反身性,但反身性所生产的历史同一性和理性化“已导致对其环境的非常全面的控制”(米德,1992:220),为反思对反身性的有效引导创造出相对理想的环境。因此,具体的历史进程可能会有各种搅动,但终究走在个人自我价值和社会整体秩序辩证发展的轨道上。总之,米德之所以能够彰显反身性的正面,关键在于相信理性的力量,并因此而没有把反思和反身性做二元论的处理。
“内心对话”:在关怀与行动之间
贝克和吉登斯提出的问题是现代性如何走向了失控和不确定性,米德的问题是社会是如何实现同一性和突生性的合一的,到阿切尔这里,问题则变成了“一个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自我如何恰恰能够避免成为一个完全被社会化的自我。”(Colapietro, 2010:52)问题意识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学者们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认识的变动,也意味着建构这种认识的关键词“反身性”的内涵的转变。贝克、吉登斯建构反身性现代化理论和对风险社会的发现被阿切尔视为社会学的第一次反身性转向(reflexive turn),而她汲取皮尔斯、米德等实用主义思想家和印裔英国学者巴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成果所构建的“内心对话”(internal conversation)理论则是“反身性的再转向”(reflexive re-turn)。⑥
(一)重建“反身性”
如前所述,在贝克和吉登斯的制度主义视角下,“反身性”首先是“自反”的循环或悖论,即使其“反思”也内在于这个循环和悖论,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从而加剧了从知识的“自反”到社会的“自反”的转化过程。阿切尔批评“贝克、吉登斯和拉什的书《反身性现代化》造成大量概念上的混淆,标题中的形容词暗示‘系统反身性’,而文本处理的是危险的和不可控的‘副作用’”。她不能接受“反身性”这样一个好端端的“自我调控”和“自我控制”的概念在贝克和吉登斯的文本中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而且,该理论起于“系统反身性”(systemic reflexivity)却终于“个人反身性”(personal reflexivity),亦是矛盾的(Archer, 2007:30; 2010:3);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反身性”不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的深思熟虑同行动之间强有力的因果关系”,而是无常的风险社会中个体在叙述上的随意建构、解构和重构:“对于贝克夫妇而言,个人生身在本性上是非连续的。它屈从于坍塌、重构和再造。它唯一的连续性不是各种潜在和持久关怀的连续性,而是叙述形式的连续性。这种叙述形式被其叙述者的各种随意且肆无忌惮的‘决定’强加在连续性上。换言之,贝克夫妇眼中的社会存在物最终只是一种观念性自我建构物而非行动的化身。积极的施动者被分散在其风险环境之中并与该环境混杂在一起;至多,这个施动的男性成了一个暂时的男人,这个施动的女性成了一个暂时的女人。这样一来,他们内心深思熟虑的能力虽然可能得到增长,但其本性和效果却是任性和易变的。”人们是抱着玩彩票中奖的心态在做决定,因而是过度随意的(Archer,2007:36-37)。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贝克夫妇的“制度化的个体化”(Beck,U. & E. Beck, 2000)不仅彰显而且逼迫着个人强化和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和自主性,但由于风险社会是一个完全个体化的而非再结构化的情境,个人认同因缺乏终极关怀的支持而处在不停歇的建构和解体的循环中,个人对自主性的理解和对理性能力的运用也完全受制于各种偶遇和突变,此一时彼一时。
对反身性现代化理论的上述两种批判(一是对“反身性”的内涵及其使用的批判,一是对这种使用所想象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的特点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阿切尔会反过来支持保守主义。阿切尔把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作为保守主义的典型,批评它赋予人的反思和行动以过度的连续性(Archer, 2007: 48)。这种批评也可以应用到米德的自我理论。米德的“客我”作为“一般化他人”,“是遵循社会的各种指令而行动的”,因此,其“内心对话”与其说是“同自己对话”,毋宁说是“同社会对话”;同样,米德的“主我”“在我自己的精神活动中也只扮演非常非常小的角色”。职是之故,阿切尔得出结论,米德的“内部对话”“不是让个人的因果力得以实现的中介”,而是一种“使社会结构要么得以再嵌入要么得以更新”的机制。换言之,米德没有凸显“自我”的主体地位,而将其建构成社会结构的傀儡(Colapietro, 2010: 47)。
上述理论批判,连同此前她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Archer,2000),蕴含着两个深切关怀:一是何谓人的主体性?二是晚期现代社会是主体之坟墓吗?关于第一个问题,她批评后现代主义把自我感消融于语言之中;现代人的预设把人想象成先验的理性人和原子人;社会人假设则认为我们所有作为人的性能和能力,都超越于我们的生物学构造,而是社会的礼物。阿切尔认为所有这些努力都忽视了人的多面向的存在事实,忽视了人的实践性。她从巴斯卡的理论中获取力量,世界是由自然、实践和社会三重实在构成的,它们各有自己的性能和能力,不可相互化约即“异文合并”(conflation),共同构成人的生活环境。这三重实在独立于我们怎样看待它们,怎么建构它们,人是被先在地抛入并嵌入其中的,不能在三者中做出任何舍此就彼的选择。人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展开具体的实践。实践让我们获得语言,获得知识,获得区分自我和他物(otherness)、主体和客体,最后抵达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分的认识。这些知识和语言效果,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来源。实践的人们在同环境的积极互动中首先获得稳定的自我感,然后形成个人认同,拥有独一无二的自我。个人认同同反思性总观的成熟能力铆合在一起。虽然人们不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地忽视这三重实在中的任何一种,但我们能够依据我们的主导性“关怀”(concern)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赋予部分以优先权,然后来协调我们的其他关怀同这重实在的关系。这些关怀的独特模式使得每一个人的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都与众不同。个人认同也同情感评价联系在一起,评价关涉幸福,不同的情感类型分别关涉我们在自然秩序中的生理健康、在实践秩序中的行动成果以及在社会秩序中的自我价值,由于一个人的关怀会有畸轻畸重的情况,因此三者之间并非总能和谐与共,而可能相互冲突,当我们的情感在这三者中既有取舍又能达到精确平衡时,稳定且严格的个人认同就达成了。在阿切尔的论述中,“关怀”由此而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关怀什么决定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它给我们一副构成我们个人内心整合的模型,让我们成为别人可以识别的独特个人。对实在进行反思的这种丰富的内在生命是我们最为重要的个人突生性性能、我们独特的身份和在此世的生活方式的生产机制,若没有这种力量,我们就会贫困化为“现代人”或“社会存在物”(Archer,2000:1-13)。
阿切尔用实在论重建了实用主义所想象的“主体”。反身性是人类主体的一种“个人性能”,“它优先于并相对自主于同各种结构的或文化的性能相关联的因果效能,并且它也拥有这种因果效能。”质言之,反身性决定主体性(Archer,2007:15),“主体”只有通过自我反思的反身性——如自知、自我观察、自我监控、自我批评,等等——才能得到确认。当然,阿切尔努力证明“反身性”比通常意义上的“反思”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反身性的突出特征是它具有将某些想法‘向后反转’落到自我指涉的特质,这样,它所采取的形式是主体-客体-主体。”说得更复杂一点:“在一个包含自我能够把它自身当作它自己的对象来思考的过程中,一个主体思考一个与主体自身相关的对象,并把这个对象向后反转映照到主体自身。”(Archer,2007:72)具体地说,(1)相对于寻常“反思”的主客逻辑,“反身性”的逻辑是主客主三维,是一个从主体出发作用于客体又返回主体的循环;但是,(2)这个循环本质上是自我反思性质的,是自我反思的行进路径。从根本上看,它不会导致“反身性转向”阶段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意外后果和失控社会的无度再生产,而是带来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对社会的有效改造;(3)这种“自我反思”,不是自我或纯粹神经系统内部的循环,而是以社会为参照并指向社会的:“‘反身性’是所有正常人的精神能力的有规则操演,这种操演就是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情境来思考他们自身,或从自身来思考他们所处的社会情境。这类深思熟虑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为人们决定自己未来的行动事宜创造了基础,虽然他们的自我描述有对也有错。”(Archer, 2007 :4)(4)进言之,就如皮尔斯(2006:61)说没有意识这种“内心世界的决定和操作就不能影响外部世界的那些实际决定和习惯”,“反身性”不仅仅是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反思性关系,而且是“行动中的反身性”(Archer, 2007 :62),是“我们穿透这个世界的方式”,其“主体性能力对客观结构或文化力在影响社会行动时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调节,故对解释诸社会后果而言不可或缺。”(Archer, 2007: 5)
关于第二个问题,阿切尔批评贝克和吉登斯关于晚期现代性的说法,并非不承认“情境的非连续性”的不断增强和全球化倾向的与日俱增,她强调的是,晚期现代性社会中日益增长的“脱域”即抽象化并非单向行进的,而是同一种转变的机会结构相适应:全球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再结构化的过程,而非变得日益解体。这种社会环境虽然使“对于所有人而言惯例的或例性的行动都变得日益不合时宜”,但不是相反地陷入“制度化个体化”的无序之中,而恰恰是个人反身性在决定我们怎样在世界中生活方面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Archer,2007: 54),“它的范围已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大幅扩张,尤其在现代急剧变迁的社会中”(Archer, 2007: 5)。用阿切尔的同道威利的表述,那就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凸显实际上是把自我的神圣性当作这个社会的最显著特征,个人的能动性变得愈益重要,这种能动性给个人以尊严和社会价值,进而给人以自信、能量和内心价值感(Wiley,2010)。
(二)“内心对话”:反身性的操演
在阿切尔之前,威利就基于实用主义提出并论证了一个基本命题:不仅思想是通过内部言语(inner speech)操演的,行动亦如此,“行动是在内部言语领域同自己交谈的对话性自我的成果”,“内部言语是行动中的控制性或指导性因素”。威利将实用主义的两大旗手皮尔斯和米德分别构建的“主我(I)-你(you)”和“主我-客我”这两种自我的“内部言语”模式组成“主我-你-客我”三重反身性模式,以表达自我的内部言语结构,其中“主我”代表现在的自我,“你”代表未来的自我、非惯习性行为和能动性(agency),“客我”代表过去的自我、确定的习惯系统和结构。在这个对话性自我中,“主我”直接跟“你”交谈而间接地或反身性即自知地朝向“客我”。把“自我”理解为这三重要素的结合及其反身性关系,描绘出一幅人怎样更好地参与时间性的图画,“我们就是三条腿的凳子,同时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⑦我们可以把过去和未来都囊括到现在之中,但是,“我们整合时间的这三个层面的精确方式主要依赖于我们的各种目标,特别是我们筹划的和期待的各种行动。”在这里,威利凸显了实用主义对人的内在性的重视:首先,自我是社会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其次,自我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处在时间流中的关系;最后,这种关系的构成和改变,端赖于具体个体在特定社会中的不断自我审视、筹划和行动,它既是社会行动的源泉又是其结果。威利详细讨论了“内部言语”同“能动性”(agency)的关系。“能动性是一个意识过程和有目的的人类行动”,其过程涉及三个方面:“可能行动在头脑中的建构或设计,从手头各种选项中实际挑选这种或其他可能行动,在行为上执行挑选出的行动。总之,所谓能动性,就是我们在建构,在选择,在发动”。所有这些有关能动性的过程,都倚靠“内部言语”。“行动不是能量的突然爆发,而是一个增强和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对话阶段推进的。它同自我言语并驾齐驱,从中获得意义,它作为叙事按照时间顺序推进,并遵守各项实践语法规则。”自我之所以需要以“内部言语”来释放和推进“能动性”,关键是只有通过“内部言语”,自我才能建立自身内部的团结,并赋予它自己完成这些事情的力量。他参考涂尔干的通过仪式构建社会神圣性的理论,提出个人如何神圣化的问题。个人的神圣性和能力虽然一部分来自社会制度,但也同自我意识,同个人的内心世界休戚与共,也就是说根源于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剧场”中做事并谈论自己。“自我也是一种参与到内心仪式的共同体”,这些仪式“提供了团结,而团结又赋予自我以意义和价值”。一言以蔽之,“很大程度上是内部言语建构了个人的神圣性。”(Wiley,2010)
作为实用主义的继承人,阿切尔同样以“内心对话”(internal conversation)来具体化反身性,将其界定为人们操演反身性深思熟虑(relfexive deliberation)的基本方式:“内心对话”是个人的自然性能,是自我意识的表达,“静静地向我们自己提出各种问题然后回答它们,是思索我们自身,思索我们所处的环境的某些方面,当然最为重要的思索我们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Archer, 2007:63)。
阿切尔从三个角度阐明了“内心对话”的作用:“从内心世界本身看,既然我们作为个人的独特性是由我们的一系列独特关怀构成的,那么,正是通过自我谈话(self-talk),我们才界定清楚我们的终极关怀,并因此而明确我们的个人认同。就外部世界来看,我们首先通过进一步的内心对话来谋求如何实现社会中的这些关怀,内心对话鉴别出哪些角色可以表达这些关怀。然后我们寻找那些存疑的角色。最后,在对那些与我们的社会关怀相符合的角色进行人格化的方式中,社会认同得以产生。换言之,内心会话不是“无意义的”,其最为重要的因果力之一,就是反身性地想象和实施那些我们用以穿透社会世界的一连串行动。”(Archer, 2007:64)在这里,“内心对话”的内在功能就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信息时,个人在心智上对这些信息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个人认同,实现主体的团结(Archer, 2000:10)。但是,与认知心理学把内部对话放置在纯粹个人的自说自话境地相反,阿切尔认可皮尔斯的看法,内部对话不仅仅是外在世界在个体心智中的内在化,而且本身具有极强的改造外在世界的效果,即通过生成典范性的生活方式来改变社会的外向力量(Archer, 2007:70)。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内心对话”如何对并不由个人决定的外部世界产生作用的。就像马克思(2015:9)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也是生活在既定的世界中,而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下形成自己的认同的。而且,人们后续的每一个有目的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也并非完全如其所愿,而会带来一连串的非自愿性和意外性。⑧阿切尔说,这就产生了若干如何处理反身性的个人性能(a PEP)同非个人性的社会因素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两个社会因素分别是社会中涌现的各种结构性能(SEPs)和文化性能(CEPs)(Archer, 2007:64-5)。结构理论采用的是一个二阶模型,以为主体因素直接作用于对象,主体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用劲推,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则用力拉,势力悬殊当然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但阿切尔的观点是:“反身性讨论压根不谈及‘独立影响’或‘直接结果’。它讨论的是中介以及反身性作为一个中介性过程的不可或缺。这里的关键差别是,诸客观因素的‘因果效应’必须依赖于它们的反身性中介作用。客观优势必须被主观上视为有优越性,客观红利必须被主观上认为有价值,客观进步必须被主观上承认是可欲的。没有这些,各客观因素对人类主体的‘直接效应’就不可思议,除非所有人性都被从主体中拿走,人被化约为一台简单的吞吐机器,即最终仅仅是一个‘消极的施动者’(passive agent)。”(Archer, 2007:89)具体而言反身性的中介机制,就是“反身性的‘内心对话’负责调解社会中涌现的结构性能和文化性能,因为正是主体的各目标以及其内心世界对外部可行性的深思熟虑决定着它们怎样直面它们规避不了的结构性和文化性环境。”(Archer, 2007:64-5)阿切尔基于此建立了一个“关怀-筹划-实践”的三阶模型(Archer, 2007:89)。这个模型是个人同实在包括所有社会性秩序的互动关系,其互动依赖于反身性的操演能力,特别是自我控制的操演能力,通过反身性的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控,我们知道在外部世界应该追求和规避什么(Archer, 2007:90)。
阿切尔对内心对话同外部世界关系的上述界定,实际上是从心理学角度对巴斯卡所说的“诸社会形式的动力源要以施动者为中介”(Archer, 2007:10)的论证。这种观点,突破了实证主义者将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对立的做法,强调外部世界虽然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但若不能进入人的反思范畴,就没有意义。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米德的幽灵,看到了阿切尔论述中米德的自我理论和历史哲学。也就是说,阿切尔虽然对米德有所批评,但无论其所引用的巴斯卡的观点还是她自己的理论建构,都没有摆脱米德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只不过在米德突出“一般化他人”的地方,她突出了“积极的行动者”(active actor),并且把米德的姿态会话和角色扮演用“内心对话”来替代并将之用于经验研究。一言以蔽之,阿切尔的“反身性再转向”,实质上是通过挖掘和彰显米德的遗产来批评和反动第一次“反身性转向”。
结论:接榫反身性的转向和再转向之可能
“反身性的再转向”发现并张扬了实用主义尤其是皮尔斯和米德对于反思和反身性关系的卓越思考,并为反思此前的“反身性转向”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笔者曾认为,“曼海姆悖论”可能是社会学难以跳脱的宿命(肖瑛,2004b)。但站在“反身性再转向”的角度,发现该判断有一个基本局限,即用逻辑的批判代替现实的批判。具体言之,它把逻辑的悖论与现实生活和社会科学的现实操演混为一谈,似乎只要有逻辑上的悖论,现实生活和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不复有效,只要相对主义得不到终极规避,社会交往和社会科学就不再可能。其实,社会生活不是一个可以从逻辑上设定的体系化存在,而因社会成员的高度多样化取向而必然不断再生产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但是,矛盾和冲突的生产和再生产同社会共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同一个过程,米德的“一般化他人”和舒茨的“主体间性”,就是社会共识的表征和反身性生产机制。社会共识的不断扩大再生产,虽然不能杜绝误解、矛盾和冲突,但恰恰让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难以走向绝对化,从而为社会交往的持续深化提供了可能性。同样,社会科学并非一劳永逸的活动,其对社会的理解和研究,虽然难以彻底超越研究者自身的各种局限,但无论是曼海姆的“社会运动”,还是布迪厄主张的学术群体的集体自我反思(参见华康德,1998:43),都可以视为“一般化他人”和“主体间性”的反身性机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有了这种自觉,研究者虽然不能最终达到但还是能通过自我反思和沟通来追求对其对象的尽可能准确的理解。由此可以判断,“曼海姆悖论”虽然不仅是社会科学也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构成性难题,但无须因此而犬儒主义地走向消极无为,而应视之为反身性的积极运用的机会和动力。
阿切尔对“反身性现代化”的批判无疑是为了引出其关于行动者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以彰显个人在社会变动中的主体性位置。但是,她没有注意的是:(1)“反身性现代化”理论中反身性的多元内涵及其间的根本紧张,并非概念使用的混乱,而恰恰是为了凸显科学理性的内在悖论,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及其后果,而她自己所关注的,仅仅是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的日常理性。这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反思”,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反身性运作机制。(2)“反身性现代化”理论不是停留在无序和偶然的“制度化个体化”层面,而是蕴含着一种自觉的转向,即从对科学理性的内在悖论的讨论转向通过彰显“社会理性”来限制这种内在悖论的无度自我再生产及其引起的风险社会和“制度化个体化”。“社会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跳脱出了“反身性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推论,而从逻辑之外的社会关系角度来思考风险社会中人的能动性的来源和作用面。(3)阿切尔所说的“团体能动性”(corporate agency)即“我们”(We)同贝克的“社会理性”有走向一致的可能性。阿切尔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其“内心对话”是个人通过理性的自我反思不断确认和再确认个人认同的机制。但是,她没有否定“社会认同”,只是认为“社会认同处于更为宽泛的个人认同的下位”,是通过个人认同来实现的,因为如前所述,“个人认同”是在协调自然、实践和社会三重实在中得以确定的,而“社会认同”只是个人认同在社会实在中的集体表现。“社会认同”让米德和威利意义上的“I”蜕变成“We”,并引出“团体能动性”在推进社会改变中的关键作用(Archer, 2000:11-12)。由此可以作出两个判断:米德所谓的“一般化他人”对于阿切尔而言就是个人认同在社会实在层面的表达,同社会认同并无二致;“团体能动性”同贝克的“社会理性”都是指个人在面对共同的非确定性和非连续性社会情境时,在对自己同他人的结构性关系的反思中,发现和激活“自我”的社会合作能力,个人由此而成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参与到针对共同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始作俑者的共同反抗行动中。这样,反身性的转向和再转向,并非像阿切尔所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两极,而在“社会理性”这个点上有了接榫的可能性。
①米德对“事件”和“历史”之关系的解释,让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回忆往往不是以年、月、日等抽象的计时标准为依据,而是以某件重要事件为基点来确定其他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②米德(1992:235;Mead, 1934:266)说,“在某种意义上,不可能有比以合理性为代表的共同体更大的共同体”。
③米德没有对“主我”做严格界定,因而引发诸多争论(参见Maccarini & Prandini, 2010: 80)。但依据米德的论述,可以判断“主我”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生物本性,是他说的“冲动”的源头,二是不同“自我”在具体情境下的具体结合。
④米德之所以与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所见略同,更为基本的原因在于前者接受了后者的如下观点:个人的自我经济利益、需求和物质关注并非植根于天生的贪婪而独立自存,而是产生于社会化的个体化过程和道德教育,这个个体化过程和道德教育代表一个共同体接受和分享的组织化的文化态度的符码。甚至,“亚当·斯密为米德的社会哲学提供了核心隐喻”(Sandywell,1996:254)。
⑤“当一个有机体在自己的反应中采取了其他有关的有机体的态度时,……‘理性’便出现了。”(米德,1992:291)“如果个体能够采用其他人的态度并用这些态度控制他自己的行动,并通过他自己的行动控制他们的行动,我们便具有了可以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米德,1992:291-292)理性的角色扮演,其实是米德所建构的涂尔干意义上的“道德个人主义”。
⑥阿切尔一方面回到皮尔斯和米德开创的传统中,申称“倾听我们自己,然后向内做出回应而非向内看”的反身性思想是美国实用主义的伟大发现(Archer,2010b:5),另一方面把巴斯卡著作中的批判实在论引入反身性的建构之中,并反过来延展了批判实在论(Gorski, 2013)。
⑦威利(Wiley,2010)认为米德关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非未来。若结合本文对米德的历史观的分析,就会发现威利误解了米德。
⑧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循环性反身性在带歪“内心对话”的路向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