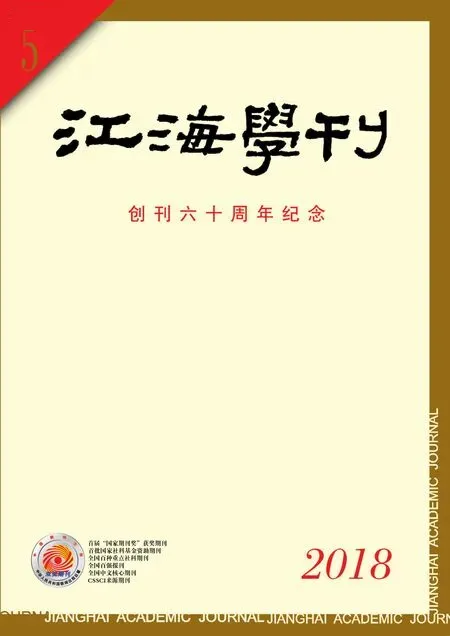“民本主义”之输入与意涵之回归*
内容提要 民本、民本思想、民本主义等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话语中相当流行。其实,在中国古籍中稀见作为名词的“民本”。1916年前后,“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或概念在日本知识界颇为流行,意为Democracy的日语译名之一。1917年,“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日语借词由李大钊等人输入中国,成了Democracy的汉译名词之一。1919年该词的用法受到陈独秀的质疑。1922年梁启超将民本主义拉回到中国语境并做了系统的阐述,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其后的20余年里,民本主义在汉语界有两种用法:一是作为Democracy的汉译名词;二是特指民视民听,民贵君轻的思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本主义与Democracy日渐疏离,逐渐回归儒家政治学说已成定势。
民本、民本思想、民本主义等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话语中相当流行。其实,在中国古籍中稀见作为名词的“民本”①。1916年前后,“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或概念在日本知识界颇为流行。1917年该词由李大钊输入中国,但其意涵是作为Democracy汉译名词之一,与中国传统思想并无关联。1918年,该词的使用引起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关注与讨论。最先将“民本主义”拉回到中国语境的是陈独秀,他用“民本主义”一词来表达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思想。1922年,梁启超对中国语境中的“民本思想”做了系统的学理分析,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吉野作造与日语中“民本主义”之意涵
甲午以后,中国知识界受“东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新名词的使用。“清末国人对日译新名词的批判与抗拒,最后几乎全军覆没,没有留下太多的遗迹。”②“民本主义”作为一个来自日本的名词是诸多日语借词的“后来者”,但其意涵最终回归中国语境。
1919年,陈独秀说:“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③李大钊也提到过:“‘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④陈、李均有留学日本的经历,熟悉日语的相关概念。问题是日本人用“民本主义”作为Democracy译名,能否说成是“影射”?日语中出现的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在意涵上有无差别?
日语中最早出现“民本主义”一词是在1906年⑤,有关心民瘼和福祉之含义,与汉籍中的重民、养民、保民思想相近。民本主义成为一个热词是在大正年间(1912-1926)。受日本知识精英的鼓动,大正年间掀起了一场民主运动。这是“继承明治十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而在全国人民中大规模兴起的第二次民主运动……以城市工业资产阶级为指导阶层,以工人、农民和劳动小市民为基础而展开的民主主义群众运动。”⑥与明治年间的自由民权运动不同,大正民主运动是对明治时代国家中心主义造成的国家强大化和个人矮小化的两极化现状表达的抗争,较之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声势更为浩大。
吉野作造⑦是大正民主运动期间的精神领袖之一,正是他赋予民本主义以体现时代精神的意涵。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多篇相关的政论文:《提倡民本主义》(1915年底)、《论宪政之本义及其完成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径》(1916年1月)、《论民本主义的内容及再论完成宪政至善至美的途径》(1918年1月)。他心目中“至善至美”的宪政应包含三个规定: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会制度。
大正年间,日本民主人士面对明治以来宪政运动的挫折,产生了“绝对悲观说”和“相对悲观说”两种情绪。前者对宪法制度的效用彻底失望;后者认为“只因宪法制度有缺点,运用方法又有不妥当之处,所以没有获得预期的成绩”。吉野本人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完成宪政有终之美,需要国民根据一定之主义、方针进行极大的努力奋斗”。所谓“一定之主义”就是遵照宪法精神,即作为“近代文明必然产物”的“构成立宪政治普遍根据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民本主义”。⑧
吉野使用的“民本主义”是对Democracy的一种新译或新解,与过往的译名“民主主义”相比“显然是另一个概念”。按照吉野的解释,如果说“国家的主权从法理上说在于人民”就是民主主义的话,那么“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从政治上说属于人民”,则就是民本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民主主义包含两个内容:一是“主权之本来的当然持有者必须是一般人民”,这是“绝对的或哲学的民主主义”;二是“在某个特定的国家里,按其国家宪法的解释,主权之所在在于人民”,这是一种“相对的或解释性的民主主义”。但这两种解释均不符合日本现行宪法的规定。日本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四条“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此宪法之条款行之。”因此,“在宪法的解释上毫无容纳民主主义的余地”。在吉野看来,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且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以此为方针的主义,就是民本主义,亦即在国家主权的运用上成为指导标准的政治主义。至于主权在于君主抑或在于人民,则在所不问。”⑨
吉野倡导的民本主义有两大诉求。一是“关于政治的实质目的的民本主义”:“当今国家主义昌盛的时代,为了矫正其片面的弊端,至少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及其利益、幸福之类的问题,更多注意些。”针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跋扈”,有必要采取措施“照料个人中心主义”。二是“关于政治组织形式的民本主义”:“指导并左右国家命运的精神,任何时候都出自少数贤明人的头脑,这是不错的。”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高明的政治措施皆难生效。在现代政治中,“贤明的哲人思想”即“精神的贵族主义”与“民众的力量即政治的民本主义”两者“浑然融合”,“宪政之花才能盛开争妍”。“在今天,通过赋予参政权,将尊重民意的意义贯彻到底,这种民本主义,才是宪政的本义。”⑩
显然,吉野所倡导的民本主义是在承认明治宪法的前提下进行必要而积极的民主改革。在大正民主运动期间,探求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在当时是一大禁忌,为规避“民主”(人民主权)与“君主”的对立,以免冒犯天皇体制,遂将民主主义转换为民本主义,强调的是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建立通畅的民意表达制度。就思想内涵而言,吉野倡导的民本主义,意在扬弃法国文化中过于张扬人民主权说的浪漫化的民主主义,转而接受英国式的温和而务实的民主主义,如此,既消解了民主与日本国体的紧张关系,亦可切实推进日本的民主化进程。
大正民主运动期间,除了吉野倡导的民本主义外,还有美浓部达吉的“民政主义”、小野塚喜平次的“众民主义”、尾崎行雄的“舆论主义”及“公论主义”,“民权主义”也不乏倡导者,但吉野对民本主义的阐发影响最大。
陈独秀与康有为之争:“民本主义”一词的借用
1917-1918年,康有为与陈独秀围绕中国能否行共和体制展开了一场笔战,彼此均使用了日语意义上的“民本主义”一词。
清亡民兴,“夫以专制之害也,一旦拨而去之,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治,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这话虽然出自康有为,但反映了民初政治领袖和开明士绅的普遍心态。然而,随着民国大幕的徐徐展开,呈现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政治失序、社会失范、武人横行、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到了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复辟的时候,国人对共和民主体制的观感颇似日本大正年间的“绝对悲观”和“相对悲观”。筹安会、古德诺、康有为等均为绝对悲观论者,他们断言共和虽美,但今非其时。1917年底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刊发8万余字的《共和平议》(合计三卷),是全面阐述中国不具备行共和体制条件的最具学理性的代表作。
康有为在《共和平议》中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民主共和”,但他在文中转引了日本《每日新闻》的《论中国政局之支离灭裂,蹈俄国波斯突厥之覆辙》一文,将原文中出现的“民本主义”照录过来。
今次之政局破坏(1917年6月张勋复辟,段祺瑞遂组成讨逆军讨伐之——引者注),以民本主义为动机,在反抗旧式之军人政治,固属大有可观,然此民主运动,乃引彼等所欲排斥之旧式军人为助。
所谓民本主义之运动者,亦如英国、法国或美国之对抗德意志,则前途必可庆幸,然国民缺乏英法美诸国人之要素,而欲效其国人,或仿其国政,反酿成其亡国之机会者已多。前例波斯之革命,亦为民本主义活动之结果,然而今竟如何?
接下来,康有为在回应日本媒体上的这篇文章时顺势使用了“民本主义”一词:“吾国人醉于民本(主)义,以为万应丸药,无人知其非者!俄、波、突厥亦然,甚矣,醉药之易于杀人也。日本此文,指陈明切,末语忍俊不禁,吾国人若不醒悟,犹泥民本(主)义,旁人将代治之矣。”这里康有为使用的“民本主义”是作为日语借词。
具有斗士气质的陈独秀是一个执着乐观主义者。针对康有为的《共和平议》,陈独秀撰文反驳。他认为共和之路绝非平坦的大道。“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中外古今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陈独秀斥责康有为“奈何日夜心怀复辟,且著书立说,诅咒共和,明目张胆,排斥民本主义,将以制造无数狄亚士(又译为爹亚士、狄爱士等,1877-1911年任墨西哥总统——引者注)、拿破仑、袁世凯以乱中国哉!”接下来,陈独秀指责康有为反对民主共和的理由是逻辑混乱:
忽称自由权利为天经地义,忽又称为洪水猛兽,不中时之陈言;忽而赞美国为公有,凡政府自人民而起,为人民而设之说;忽又指斥为民本主义争国为公有者乃饮药自杀;忽自称为发明民主共和之先觉;忽又自称不以民主为然——是殆图便骋词,任意取舍,遂不觉言之矛盾也!
显然,有过留日经历的陈独秀,对日语中“民本主义”的用法并不陌生,这里使用的“民本主义”也是日语借词。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并非是使用民本主义的第一人。1917年初,李大钊也提到过“民本主义”。“往年日本议会骚喧正烈时,提倡民本主义之吉野博士,即于某杂志疏举此事,以促议士之觉悟。”同年《申报》在转引日本媒体对“府院之争”的评论时,第一次出现了“民本主义”。日本媒体称“黎总统免段总理”,“或称其英断果决,或颂为民本主义之进步”。此外,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倡导者河上肇写的《民本主义云何?》也在该年译成中文,其政治立场较之吉野更为激进。
民本主义政治有两条件:其一握政权行政治之干部诸人以得国民多数之信任而跻其地位,以失国民多数之信任而去其地位;其二顺从国民多数之希望,即所谓舆论而施行其政治。此两条件既备,尚须时时以易与国民多数耳目接触之形式,将两条件之事实向世人表示焉。
综上,可以推定,作为日语借词的“民本主义”在1917年传入到了中国,但尚未引起中国知识人的关注与质疑。
陈独秀与杜亚泉之争:“民本主义”的新解
1918年岁末至1919年初,《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发生一场招来众人围观的陈杜之争,后人称之为“东西文化论战”,论战涉及对“民本主义”一词的理解与评价。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是一个执着的文化接续主义者。“国家之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复何所用其接续乎?若是则仅可谓之顽固而已。……反之,有开进而无保守,使新旧间之接续,截然中断,则国家之基础,必为之动摇。”他在回应陈独秀的质问时说:
《新青年》记者谓:共和政体之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作何解?谓之叛逆,谓之谋叛共和民国,谓之谋叛国宪之罪名。记者以为,共和政体决非与固有文化不相容者。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
杜氏推崇古典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思想,并认为这一思想遗产“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其“政治原理”与现代共和政体并无紧张关系。
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文化革命论者,坚信古今中西绝不相融。
呜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倘由《东方》记者之说,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则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实不至之国体而论,亦与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
显然,陈、杜在论辩的时候,概念出现了歧义。杜氏认为,民视民听、民贵君轻的思想“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原理”;而陈氏则认为民视民听只是“古时之民本主义”,与当下倡导的西洋之民主主义“绝非一物”,杜氏将其说成是民主主义是错误的,错误的源头在日本。其实,将民视民听、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等思想理解为民主思想并非始于杜亚泉。鸦片战争以后,从魏源到维新派人士,大多循着“西学中源论”的思维,将中国古籍中相关名句名言或典故说成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民主元素,意在表达西方的那些民主制度(选举、议会等)中国古已有之,但维新派思想并未用过“民本”一词,而是用“重民”(王韬)之类的提法。“五四”时期,杜氏将民贵君轻理解为民主主义,已不同于过往的“西学中源论”者的牵强附会,而是一种基于文化会通主义的理性思考。
陈独秀在文中提到的“民本主义”与一年前与康有为论战时的用法不同,这里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日本人使用民本主义来“影射”民主主义(Democracy)是不恰当的,中国人不应错上加错。二是民本主义在汉语中只能用来指民视民听的思想,这一思想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
1919年前后汉语中“民本主义”之意涵
新文化运动处在一个“主义”的“通胀”期,各种五花八门的“主义”都能得到畅达的表达,而Democracy一词的译名更是各取所好。“德谟克拉西”的普遍使用以及陈独秀干脆用“德先生”,表明Democracy在汉语界使用的乱象及知识界对汉译该词的困惑与歧义。陈独秀虽然指出了民本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意涵,但这并没有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相反,作为日语借词的民本主义在1919年前后的中国知识界还有流行之势。
1918年,朝野、南北围绕采用或制定何种宪法展开纷争。12月25日,有留学美国背景的王宠惠与蔡元培、景耀月等人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倡导会”,认为制定宪法为平息南北之争,维护和平的第一要务。他们在该会的宣言书中采用民本主义来翻译Democracy:“国民制宪云者,即以国民总意为渊源,国家总体之福利为目的,而制定民本主义之宪法,不许少数人行其私意之谓也。”此间,相当活跃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其机关刊物上频繁使用“民本主义”来翻译Democracy:
Democracy可译作民本主义,Bolshevism可译作过激派主义。前者主动是由于美国,后者主动是由于俄国。我先照着普通解释这两个主义来解释他。民本主义有广、狭两种的解释。广义就是不独政治要民本主义,社会也要他,教育也要他,工业也要他,几乎世界无一日不要他,无一人不要他;所以他不可不打破官僚与军阀,不可不扫平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不可不废除贵族文学。至于狭义的民本主义,就是专指政治而言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唱的民本主义,就是这种狭义的而非广义的。此次欧战告终,有说是民本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有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专制主义的,总而言之,终不出“政治”两个字的范围。所以现在一般所说的Democracy应当写作Political Democracy这才名实相符。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谭平山也加入了对Democracy这一概念的讨论:
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维(为)何?稍有识者,莫不知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德谟克拉西”者英文为Democracy,法文为Dèmoc-ratie,兹从英文音译也。今人从义译者,日本译作民主政治,或作民本政治,或作民主主义,或作民本主义。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也使用过民本主义。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
针对中国学界对Democracy一词多译的乱象,此间出现了几篇专门讨论该词译名的文章。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政治科的陈启修,1917年底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他认为汉语界对民主译名的混乱现象与日本有关。
此其原因,或因欲拥护日本固有之国体而故意曲解或因受政治上之压迫而隐约其辞,或因其人并不深求而拾片鳞寸爪以自饰,纷纷聚讼,令人无所适从。中国政论界及学界近时万事皆受日本之影响,故关于Democracy之议论,亦与日本同弊。然中国与日本国体制迥殊,关于国宪及政治学上之诸原理,实不必随人足而跟,依样葫芦。若不察国情之相异,而漫纳彼邦人士有为而作之学理,则一说之差,流毒数纪。
陈氏列举了汉语中对Democracy的8种译名(民众主义、民权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唯民主义、民治主义、庶民主义),一一评点其得失。
民本主义,古昔仁君贤相所行政治,莫不以民为本,故“民本主义”四字,使人生民为被动者之感,实则Democracy不如是也。日本学者喜用“民本”二字,致假官僚及武人以口实,谓仁民爱民之主义即是民本主义,亦大喊为Democracy,悲矣。
1923年1月,李大钊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写成《平民主义》列为“百科小丛书”出版,专门讨论“Democracy”一词的译名,他主张用“平民主义”来翻译Democracy一词。他列举了汉语对Democracy一词的多个译名并分别加以讨论。
“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有译为“民治主义”的,有译为“唯民主义”的,亦有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以避“民主”这个名词,免得与他们的国体相抵触。
综上,在1919年前后,汉语中的“民本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大多理解为Democracy的译名。
梁启超与“民本主义”意涵之回归
1922年秋,梁启超应邀到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岁末,该讲稿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为名出版。梁启超在序论中讲到:“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梁氏对“民本主义”一词的分析不仅理性平实,且有独特的学术视野。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檃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译言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申言之,则国为人民公共之国,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此二义者,我先民见之甚明,信之甚笃。惟一切政治当由人民施行,则我先民非惟未尝研究其方法,抑似并未承认此理论。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虽然,所谓政由民出者,不难于其理论也,而难于其方法。
该书第三章“民本的思想”专门讨论先秦时期该思想的由来。“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互相结合,在政治上产生出一新名词焉,曰‘天子’。天子之称,始于《书经》之《西伯戡黎》,次则《洪范》,次则《诗经》《雅》《颂》中亦数见。《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语最能表出各代‘天子’理想之全部。”天子代表了天,但天意又是通过民意来表达,梁启超称其为“间接的天治主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如此,“则人人可以为天子也,此种人类平等的大精神,遂为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天既有动作,必有意志,天之意志何从见,托民意以见。此即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之所由结合也。”
梁启超在第三章的末尾加一附录:“民本思想之见于《书经》《国语》《左传》者”,摘录了大量与民本思想相关的名句、箴言。梁启超书中对民本主义的阐述,完全摆脱了日本语境的影响。他不仅通过学术的溯源,厘清中国民本思想的由来与影响力,且与林肯对民主的界定作了比较分析。
1920-1940年代:民本主义的双重意涵
所谓“民本主义”的双重意涵,是指既有人用其指Democracy,也有人特指儒家的政治学说。
1.作为Democracy译名的民本主义
民主制与君主制难以兼容,这不仅令吉野作造困惑,也是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普遍认知。到了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人开始放弃这种排他性的理解,认为君主体制也可以行民本主义。
现代各国的政治,都是民本主义的政治。民本主义的政治,是使大多数人民有参政权,再依这大多数人民的舆论所定的策略,实行实际的政治。民本主义与国体,并不发生问题,像日本和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也能和法美那样的共和国一般,实行着舆论政治,只在这一点已无异于民众政治了。
1920年代以后,用民本主义作为Democracy汉译名词,还与一本影响甚广的译著有关。1919-1921年,杜威来华讲学,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杜威热”。中文报刊上翻译了不少杜威的演讲稿及其论著,但对杜威讲的Democracy的译名并不统一。1920年申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岫庐编译·公民丛书·新书预告:《民本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美国Prof. John Dewey著,编译中”。“岫庐”是著名出版家王云五的号,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据陶行知年谱载:1920年,陶行知应邹韬奋之请,“校阅其翻译的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有部分改译,并介绍给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是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邹韬奋将杜威的DemocracyandEducation一书的前四章翻译出来,并以《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为题刊于《新中国》杂志1、4、7、8各期。其后,邹韬奋将全书翻译出来,1928年3月全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出版,书名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署名:邹恩润(韬奋)译,陶行知校。由此推测,1920年《申报》上的新书预告疑似邹韬奋的译稿,但尚在“编译中”的书稿当年可能没有出版。
邹韬奋对该书的序言做如下翻译:“本书是要说出民本主义的社会所含的种种观念,并把这种种观念应用于教育事业的问题……这书所述的哲学,是把民本主义的演进,与科学上‘实验方法’的发展,生物学上‘进化的观念’,及‘工业改造’,彼此互相联络贯串起来;并要把他们在教育与方法上所发生的变化,一一指出。”
胡适、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教育界的名流均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与杜威有师生之谊,故而《民本主义与教育》对民国时期教育学的影响可想而知。“民本主义之涵义:盖杜威所谓民本主义,不仅政治之一种组织,且为社会生活之一方式。据彼之意,任何社会,其各分子间,必有若干共同之利益,而其对于他团体,必有若干相互之关系。其共同之利益既多,而相互之关系又甚自由者,则为理想的社会。”
这一时期,不少词典将“民本主义”列为词条收录。如,1929年高希圣等编辑的《社会科学大词典》:“民本主义:即德谟克拉西主义,见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即主张民主政治的主义,又名民本主义。”1933年孙志曾主编的《新主义辞典》:“民主主义(Democracy):民主主义又名民本主义,或译为‘德谟克拉西’。”
2.作为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
与此同时,知识界不少人承接梁启超的用法,用民本主义来探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但对民本主义的价值判断以及民本与民主关系的看法不尽相同。
陈登元在探讨荀子的政治学说时引用了诸多荀子重民爱民的主张,并称其为“民本主义”。“其言之爱民,可谓彰明昭著,其劝人主之以人民为国家之本,亦可谓剀切陈言。昔乎仅以乞怜之态度,为民请命于暴主,而不思积极以扬民权,是则时代限之使然,不可苛责荀卿一人也。”
胡毓寰通过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探讨,认为其与西方民主主义可以汇通。
孟子政治思想,在吾华古政治思想中,可谓最富于民本意味者。彼谓暴君如匹夫,凡民可取革命的行动推翻政府而代替之。彼以为治之道,首宜富裕民生,致治上一切施为,应以致人民之衣食丰足为中心。又谓欲政治完美,当以教育为本;国家之行政司法用人,皆须得全民同意。此等致治思想,能(与)近世西方之民本政治,殊相仿佛。至其民生政策上之井田制,倡为受地平均说;行政组织上之任贤制,谓政治如建筑巨室,主人须信任专家处理之,此能(与)中山先生之思想,亦甚接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强化党化教育,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党化教育之正典,有些学人通过挖掘民本主义的现代价值,来强化三民主义的正当性。
孟子所说的民本,分拆起来,恰也有三,就是保民、养民、教民。保民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养民就是充实民族的生活,教民就是指引民族的生计。这三个关系:养民教民是基础,保民是目的。……孟子的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从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脱胎而来的。所以,孟子主张保民,保障民族的生存,中山先生也倡民族主义;孟子主张养民,充裕民族的生活,中山先生也倡民生主义;孟子主张教民,指引民族的生计,中山先生也倡民权主义。
曾留学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陈伯康试图从学理上厘清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两个概念的区别:
中国的历史上,表现得最显著的理论并有若干事实,是民本主义。而民本主义的经济措施,就是恤民,取之于民有度。历代关于暨(贤)君良相,行恤民之政的,史不拒书,那都是一些开国或中兴的君主。……所谓‘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则载身,水则覆舟’,这几句话充分道出民本主义政治经济意识的奥秘,同时也说明了民本的政治经济意识的立场,仍是站在君主方面,这也是明显事实。不管历代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较(绞)尽脑汁,托称先王之仁政,托之灾异数见,其目的无非在安定社稷,效忠君主。发挥民本主义政治经济意识最完美的人,是汉代一个青年政论家贾谊。
概而言之,作为日语借词的“民本主义”自进入汉语界后,日渐回归中国历史语境,这与多数日译新名词的命运迥异。随着“民主”作为Democracy的中文译名被中文世界普遍接受,民本主义作为Democracy曾经的译名之一,虽然保留在相关的词典中,但多为一种历史记忆。
①《商君书·画策》中有“民本,法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制强敌者,必先制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走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这里的“民本”是“制民之本”(制服民众)的缩略词;“法也”,对民要“绳之以法”,并非指“民为邦本”。
②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6页;另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
③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⑤1906年7月12日,《东京朝日新闻》上有报道:“古贺警保局长对警官们的训话时讲了三个关键词:民本主义,简捷主义,活动主义。”1912年5月27日,《万朝报》记者茅原华山在该报上发表《民本主义的解释》,将民本主义作为与“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人政治”相对立的概念使用。东京帝国大学保守派教授井上哲次郎和上杉慎吉等则将民本主义视为帝王重视臣民福利。
⑥⑧⑨⑩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李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62、168、169、169-170页。
⑦吉野作造(1878-1933)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06-1909年在北洋法政学堂教书。吉野回日后在东京大学法科讲授政治史,1910-1913年游学欧美,返日后继续在东京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