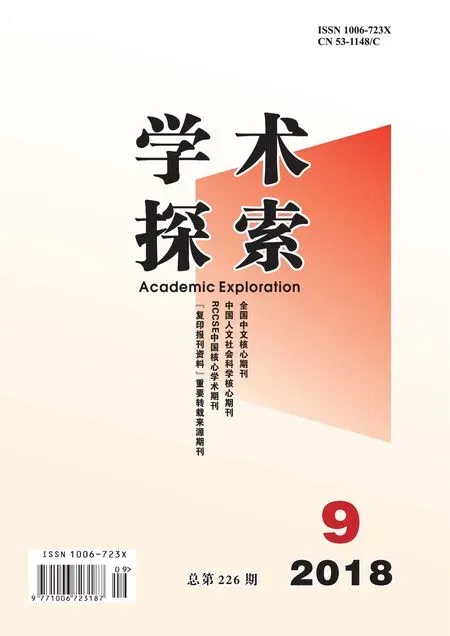乾嘉文人的社会治理构想
——基于文言入冥小说的整体研究
田 宁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清乾嘉年间的文言小说作家众多,卷帙浩繁,入冥小说尤其丰富。这些作品客观反映了乾嘉时期民间宗教信仰风貌和社会伦理道德困境。传统入冥故事的写作大多是为自神其教,清代的文言入冥小说则重在规约现实世界伦理道德,传达小说家对社会的治理构想。
一、社会治理需求促兴文言入冥小说
入冥小说兴盛是明清劝善思潮制度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满足了社会伦理治理的深层需求,也是乾嘉文人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安全选择。
(一)鬼神劝善的制度化发展
以宗教辅助社会伦理治理是传统的统治策略。明清以来的宗教劝善借由“圣谕宣讲”进行*“圣谕宣讲”是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圣谕而举行。宣讲活动要求地方官员、乡绅、读书人在每月的固定时间、地点宣讲圣谕,再列举诸多现实故事来深化以上观念。,乾嘉年间圣谕宣讲活动达到高潮,乾隆多次下诏要求其在社会各层面落实,并将施行情况纳入各级官员的考核中。[1]宣讲故事内容多借入冥展现鬼神地狱果报轮回等赏善罚恶案例,借以弥补理学的社会治理短板。
清代的官方哲学为宋明理学,严苛僵化,毫无建树,强制全社会遵守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但有心无力。人们对理学道德伦理或知而不信,或知而不行,三纲五常、天理人伦成为现实世界利益算计的工具。官员或麻木保守、懒政怠政,或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社会道德伦理败坏,伪善诡诈层出不穷。违背人伦者、趋避推诿者、算计盘剥者、狡诈无赖者多不胜数。到乾隆年间,社会道德秩序危机面临失守窘境。法律只能制裁违法犯罪,无法祛除阴谋诡计。“若无明确的制裁,道德法则似乎会在一种‘基本矛盾’中寿终正寝”。[2]自明代兴起的宗教劝善活动在乾嘉时期达到新的高峰。大量的劝善故事在全社会流通,讲述鬼神全知全能和赏善罚恶的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出信仰的氛围,“几乎没有人敢于正面抨击对鬼神的信仰——可能是畏惧破坏了祖先崇拜这种普遍和必须的现实信仰——被视为一种坚固而悠久的民间信仰”。[3]全知全能的鬼神环伺在人的周围,每一个人都处于鬼神监督体系中。这就将全体社会成员连接成一个宗教信仰共同体*[德]F.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发现,社会以法律、契约、思想为基础,而共同体则是以共同信仰、习俗、文化为基础。“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日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异国他乡。”,如果以共同体理论来衡量乾嘉时期的社会,就会发现在宗教信仰领域内,士大夫阶层与普通百姓并没有呈现出大传统、小传统的区别。[注]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存在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是城市知识阶层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的是农村农民阶层的文化。文言小说家也信鬼神、命定、果报、宿业、幽冥一理等观念,和其他社会成员共享一个文化体系。[4]小说家在创作风格上虽各臻其妙,但“幽冥一理”“果报不爽”则是其普遍表达的内容。由政府组织的全民“圣谕宣讲”活动又把民间零碎的鬼神传闻集中起来,给文人大规模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读者,促兴了文言入冥小说的创作。
(二)乾嘉文人的社会治理愿望
1.小说是乾嘉文人介入社会治理的安全路径
乾嘉时期文网严密,文人动辄得咎,鬼神世界是王法律条鞭长莫及的另一世界,为文人谈论现实问题提供了一块相对安全的区域。入冥是一个框架,“具体关目,实有多种。除佛经中所云误拘至冥复出者外,又有梦入冥间、应邀入冥间、随巫者入冥间、生入在冥间兼任阎罗王等冥职、死入冥间负宣传任务返阳世、死后设法逃回等等。”[5]这些故事是作者记录民间传闻、友朋闲谈并搜集文献所得,是文人交往交流的媒介。其中那些恐怖、阴森、神秘的入冥细节不但启迪小说家的遐想和想象,满足其自娱的文化需求,也引起读者好奇探究,“使小说家在创作时有了广阔的空间,读者接受时亦有非常主动的参与”。[6]
2.小说地位的提升为乾嘉文人施行社会治理提供了便捷
文言小说叙事灵活、寓教于乐,比经典和考据书籍更易发挥劝惩作用。“稗官小说,搜神志怪,谈狐说鬼之书,则无人不乐观之。故文达即于此寓劝惩之方,含箴规之意。托之于小说而书易行,出之于诙谐而其言易入。”[7]小说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其内容虽然“荒诞悖妄虽不足数,其近于正者,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注]参见盛时彦给《阅微草堂笔记》所做的序言。“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注]参见梅鹤山人给《萤窗异草》的跋。尤其在补救人心、挽回社会风气方面,比班班可考的经史圣贤遗训更加深入人心:
“夫编氓生长穷乡僻壤,耳不闻先正遗训,而同此秉彝,同此好恶。……或其农工之暇,二三野老,晚饭杯酒,署则豆棚瓜架,寒则地炉活火,促膝言欢,论今评古,究原竟尾,影响附会、邪正善恶、是非曲直,居然凿凿可据,一时妇孺环听,忽不自知其手舞足蹈。言者有褒有贬,闻者忽喜忽怒。事之有无,姑不具论,而藉此以寓劝惩,谁曰不宜?”——《里乘》自序
在“入冥”荒虚幻诞的框架下,作者可以相对自由展现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并佐以雷击、鬼报、冥罚等骇人听闻的方式施行赏罚,以此引导社会伦理道德方向,实现社会治理观念。入冥小说越受重视,作者传达的理念也就越能顺利作用于人的潜意识,实现小说家对社会治理的迫切愿望。
二、入冥小说的社会治理构想
乾嘉文人引经据典论证鬼神存在的真实性,维护鬼神监督的权威,以鬼神管理幽冥两界的赏罚细则引导规范人的行为意识,实现社会治理理想。
(一) 维护鬼神信仰观念,强化鬼神监督权威
乾嘉小说家认为鬼神世界真实不虚并强化这一点,他们大多数人本身是精通考据的学者,发生在自己或者亲友、熟人身边的入冥事件成为鬼神存在的有力证据。钱泳曾记载:“扬州罗两峰自言净眼能见鬼物,不独夜间,每日惟午时绝迹,余时皆有鬼。或隐跃于街市之中,或杂处于丛人之内,千态万状,不可枚举。”(《履园丛话》)小说家记录大量入冥故事强化鬼神真实存在的观念,并以此批驳无鬼神论者或游移不定的信仰者。入冥故事中,生前不信鬼神的“儒生”“讲学者”死后或承受鬼神的揶揄奚落,或现身说法劝人相信有鬼神地狱。一些鬼魂甚至白昼来访,反驳戏弄不信鬼者,《阅微草堂笔记》里此类小说甚多:
边随园征君言,有入冥者,见一老儒立庑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与寒温毕,拱手对之笑曰:先生平日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诸鬼皆灿然,老儒癿缩而已。
老儒云:“动云见鬼,皆人自胆怯耳。鬼究在何处耶?”语甫脱口,墙隅忽应声曰:“ 鬼即在此,夜当拜谒。”
一些鬼魂来到阳间淋漓痛快抒发无鬼之论,放大了无鬼论者的迂腐荒谬:
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间何得有鬼,不闻阮瞻之论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释氏之妖妄。……适大车数辆远远至,牛铎铮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无鬼之论,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谨以实告,毋讶相戏侮也。俯仰之顷,欻然已灭。
入冥小说专门将不信鬼神的儒生挑出来进行批判,让他们现身说法劝导人们相信鬼神地狱真实不虚,蕴含小说家治理社会的深心。儒生本身是社会教育引导者,当他们将“不语怪力乱神”理解为“世上无鬼神”,卸除对鬼神冥司惩罚的顾忌后,弱化了鬼神道德监督权威。只有相信鬼神赏罚存在,以报应信仰的理念约束自己思维行动,矫正制约恶的发生,人人如此,就能实现社会治理目标。
乾嘉文言小说家通过“实录”和“考证”入冥故事强化鬼神的真实存在。文言小说发扬了稗史的征实传统,严格记录传闻的来源并以史笔出之。《虞初新志》《聊斋志异》还延续传统的志异方式,记人物、地点、时间往往较为笼统,但乾嘉年间的诸多文言小说在记录入冥故事时,时间、地点、人物精准定位,让鬼神故事更加真实。“所有有关鬼的故事以新闻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有一个共同特征是通过引用历史记载,即出自于一些记载奇闻轶事的典籍,试图赋予这些鬼故事以权威性。鬼故事也形成了一种文学体裁,有自身的创作规则,如果‘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套话被一个精确的时间所替代。”[3]新闻式的“实录”增强了鬼神存在的可信度。
乾嘉时期的考据之风坚固了世俗社会鬼神实有的观念,并将鬼神世界人间化。“《阅微草堂笔记》《新齐谐》这类书,成于乾嘉考证征实之风鼎盛的时代,事实上也表明着征实的态度。”[4]小说家以入冥复出者的经历证实鬼神世界是现实世界未散的“余气”,布帛、衣服等所有的用品乃至冥界本身都是未化掉的物之菁英。比如死去的人时常会托梦给生人请求焚纸钱、纸马、土偶婢女,这些东西“体为灰烬,神聚幽冥”,供死去的人在冥界享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二》)。袁枚在《子不语》中记录父亲的侍妾见死去的主人魂魄在屋瓦上召她,她马上也死了。袁枚的仆人死而复苏,向家人伸手索钱,说要在冥界应酬用,他自己病危时觉得有六七人在身边骚扰,“方信三魂六魄之说,亦属有之”。而古籍中的“升屋复魂之说,非无因也。”(《子不语·随园琐记》)那些人间未曾存在的牛头马面,则是“头戴面具,面如活人”的鬼所扮演。乾嘉文言小说家通过入冥者刻画的鬼神,依然保留着人的种种感觉与意识,入冥者穿行生死之界,完整呈现出不为人所觉察的因果报应链条和冥界赏罚规则,给现实世界提供行为指南。
鬼神世界与现实世界越一致,其监督权威就越强。“宗教的主要道德地位并不在于它是伦理价值的前提,而在于对世俗道德标准的强化方面所起的辅助作用。在行使这一功能时,宗教更多地依赖于一种超自然力量,不论这种力量加诸人的是鼓励还是威慑。”[8]如果人们普遍相信冥司鬼神有严密监督和公正奖惩的力量,报应如影随形,鬼神的劝诫无疑会威慑人心,引导人们遵循规范,净化社会道德风气。
(二) 细化鬼神赏罚标准,强调以“德”致“福”
鬼神只治理现实社会人“不能治”或“不及治”之事:“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渎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测也”(《阅微草堂笔记》)。人的周围环伺着看不见的鬼神,业镜心镜周密客观地记录人的意识行动。业镜和心镜是佛的神通的化身,能够无障碍知悉无量众生多生多劫的所有善恶和所想所念,而且神通一通永通,一得永得。业镜永久保留着人一生“行事之善恶”,打破人死无对证的侥幸心理。心镜能洞见人隐秘无迹的内心世界,“一切阴谋,鬼神皆已全知,无更枉抛心力”,人每一念每一语甚至梦寐中的影像都会纤毫毕现地被记录并通过种种镜面工具重现,如业镜、心镜、一团圆光、一颗珠子、一盆清水等。袁枚记自己同年邵又房幼年的老师钟孝廉梦中入冥,神用一盆清水为镜回放了他三生前谋财害命的罪恶,罚他变为蛆虫,他还魂三日后呕血而死。(《子不语·钟孝廉》)乾隆二十年某侍郎入冥事。他因办案时贪图迎合固宠迁官而杀人太多被拘入冥,小沙弥手中珠子将他假公济私的举动清楚记录了下来,数月后他呕血而死。(《子不语·某侍郎异梦》)鬼神以业镜心镜中记录的事实进行赏罚,其判决令人信服。
鬼神“以有心无心断善恶”,细致区分善恶的层次,监管因果报应如律进行。有德者在生前就已经获得诸如长寿、富贵、平安等善报,当他们“进入另一个世界时,不仅安享福乐,而且拥有与其在世间的德行相应的权力。因为我们要尊重世间有权势的长者,所以相应地更有必要敬重耐心的进入神灵世界的有德权威。中国人认为两个世界的距离好像睡与醒一样的近,所以此岸的权力也会带到彼岸”。[9]现实世界的贤臣、贞妇、烈士魂入冥界后,鬼神能据其精气判断其道德层次,使“最上者为神明,最下者亦归善道”。那些将高尚道德伦理内化到天性中,“一生无利己心”者为上善, 能够出于礼仪而自制其私心者次之,秉怀私心行善邀功者为善之下者。比如同为“贤臣”,“畏法度者为下,爱名节者为次,乃心王室,但知国计民生,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阅微草堂笔记》)由道德义务引发的善行价值更高,享受的幸福回报更大,反之则较小。比如“自奉母以外,诸事蠢蠢如一牛”的乡野农民刘某夫妇,享受八十以上的长寿。志行高洁的乡间老媪能够直接从冥王头顶成仙飞升,穷乡蔀屋中的贞节烈妇,死后享受国家供奉的祭祀品。生前地位显赫者如 “藏瑕匿垢,冒滥馨香,虽位设祠中,反不容入”。“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这些入冥故事关注鬼神赏罚细则,和现实世界的符合其身份权力层次的道德标准。普通人无功不受罚,官吏则“无功既是罪”,而且“禄愈重者责愈切”,生时罚其寿禄,死后被鬼神面斥。鬼神区分善恶细致入微,注重过程,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道德判断的公正性,引导人心向善。
鬼神赏罚强化福德之间的正向关系,树立人们向善祛恶的信念,成为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转化的动力。修持德行必获善报,出于恻隐之心的善念善行远胜斋戒施舍、烧香拜佛,前者源于个体的改过意识,后者则源于求福求安私心。“鬼神一直在表象背后起着作用,监督人的行为并调整地位的分派,以便确保事实的合理性。”[10]祸福穷通主动权就在每个人的意识和行动中,鬼神尊重知错能改、在善恶间徘徊后遽然醒悟而向善的“自制其私心”者。要想改变命运,只能向善而行,提升道德水平。
(三)明确鬼神代施赏罚,激发人的道德自律
在乾嘉文言小说中,因果报应主宰一切,“人自定自移,鬼神无权”(《阅微草堂笔记》)鬼神只是代施赏罚。鬼神赏罚善恶公正公平,“君子偏执害事,亦录以为过;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报”(《阅微》) “夙生债负,受者毫厘不能增,与者毫厘不能减也”。 恶人得手后绝无逃脱惩罚的可能,贪酷官宰的幼媳爱女尽被罚入香粉地狱以填赃款(《谐铎·香粉地狱》)。一位在冥府司茶者告诫欲愤而自戕的儿子:“人可欺,神则难欺,人有党,神则无党。人间之屈弥甚,则地下之伸弥畅。今日之纵横如志者,皆十年外业镜台前觳觫对簿者也。”“神理分明,毫厘不爽,乘除进退,恒合数世而计之,勿以偶然不验,遂谓天道无知。”(《阅微草堂笔记》)无论历经多少次轮回,也终将承受报应。
任何前生善恶决定后生祸福,善恶都是人咎由自取。“神灵基本上被认为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不是超乎其外……人因此可以选择一套有利的系统,来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11]阴律有“小善恶相抵,大善恶则不相掩” (《谐铎·森罗殿点鬼》)的原则,求神拜佛布施并不能改变命运,但真诚改错一定能自赎罪愆。医生耽利误伤九条人命后被判九世服砒死,但如果有人用其解毒秘方救活一人,则他会少受一世业报。于是这个医生给每一个入冥者推广药方,希望能将功补过(《阅微草堂笔记》),激发起人改过的主动性。乾嘉入冥小说将鬼神的善恶赏罚细则明确具体展现出来,让鬼神的奖惩细则控制人的欲望。当个人依于这些细则裁量善恶时,人的道德自律就越强。
三、入冥小说为现实社会提供治理方式
“公是公非,幽明一理”,鬼神世界和现实社会共享一个道德伦理体系。现实社会的吏治腐败是导致社会伦理道德失守的最大原因。入冥小说中的鬼神世界执法者人格高尚,执法公正,既能严格遵守因果报应法则,又能从情理出发体贴关怀治下之民,这种独特的社会治理策略,给现实社会提供了治理借鉴。入冥故事里大量的普通人的善恶果报故事,也成为民众辨别善恶的案例、践行道德的参照。
(一) 为社会管理提供思路与模型
鬼神世界和现实社会组织模式类同,其管理者普遍正直清廉。诸神、仙、佛是聪明正直的代表,他们以其品德而非超自然能力受到人的普遍敬仰:“神正直而聪明,仙冲虚而清静”。冥界选官重视道德品格修养,官员普遍清廉。阴司不通贿赂是乾嘉时期文言入冥小说合力塑造的冥司形象。例如“持律精进”的老僧尊佛斥儒,其“党同而伐异,扬己而抑人”的公然谄媚反而遭到佛的惩罚。《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冥界官员基本清廉明智。小说家塑造的城隍、土地神是鬼神世界的基层官员形象。他们官职小、地方苦、素讲操守而不受非分之财,甚至难得温饱:“城隍、土地之职,如人间府县俗吏,风尘奔走甚劳苦,贤者不屑为。”虽然个别阴司皂隶也会去阳间勾魂诈钱作祟,但城隍并不知情(《子不语》中《土地受饿》《判官答问》《蒋厨》)。据降凡的乩神透漏,不但阎王、判官、城隍,就连关帝也是由从人间拣选的品德高尚,平生正直者担任,“今四海九州皆有关神庙,焉得有许多关神分享血食。凡村乡所立关庙,皆奉上帝命,择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关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子不语·关神断狱》)鬼神世界管理者的清廉正直是保障冥界政治清明的根本原因。
鬼神世界治狱断案公正严谨。冥司审判过程与阳间类似,但“夫折狱之明决,至冥司止矣。案牍之详确,至冥司亦止矣。”(《阅微草堂笔记》)冥司承担着最为繁重的轮回事务管理工作,而出错不多,被判者一般“皆帖服无后言”,即使案情微小,有的甚至要追溯到几十年之前,冥司断狱时也会不惮烦、不自信地反复质证,甚至由冥王亲自复查,力争使冥籍无误。人们相信神聪明正直,神理分明并不因为强大的超自然力,而是知而能鉴、误而即觉的道德自觉。
献县老儒韩生,性刚正,动必遵礼,一乡推祭酒。一日得寒疾,恍惚间,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唤。韩念数尽当死,拒亦无益,乃随去。至一官署,神检籍曰:以姓同,误矣。杖其鬼二十,使送还。韩意不平,上请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遣愦愦之鬼,致有误拘。倘不检出,不竟枉死耶?聪明正直之谓何!神笑曰:谓汝倔强,今果然。夫天行不能无岁差,况鬼神乎?误而即觉,是谓聪明;觉而不回护,是谓正直,汝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无玷,姑贷汝。后勿如是躁妄也。霍然而苏。韩章美云。——《阅微草堂笔记》
只有负责任的官吏才会不厌其烦地查阅记录,秉公而断,毫厘不爽。这也是冥界选官的基本条件。冥界对官员的监督管理严格,赏罚分明。即使阎王也必须接受监督制约。《子不语·阎王上殿先吞铁丸》中,当阎罗王 “有所瞻徇”时,“铁丸已涌起于胸中,左冲右撞,肠痛欲裂矣”。冥司对执法者违法行为惩处尤重。城隍酗酒错差鬼役锁杭州沈丰玉魂魄受妄刑,被关帝及时提参治罪(《城隍神酗酒》)。穹隆山庙中的山神因为赌博,输掉了自己的妻子(《谐铎·神赌》),神贪淫好赌必然受到惩罚。
冥界官吏大公无私,能洞察事情缓急,甚至损伤名声扶助弱者,将情与法措置得当。城隍神庇护李二在沸油摸钱时安然无恙,因为他能洞察到李二并非有意赖账,而是生意亏本暂时无力偿还朋友(《子不语·受私桥》)。“关神“故意错判马孝廉窃鸡而食,因为“汝窃鸡,不过失馆;某妻窃鸡,立死刀下矣。我宁受不灵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识政体,故超升三级。”(《子不语·关神断狱》)鬼神世界里的执政者决本乎善心,以扶危助困、救人性命为要,这正是现实社会中官吏缺乏的品格。
冥司官员审判明辨事理,尊重人性,矫正了理学僵化严苛的道德规定。冥司衡量善恶的方法是“问心”,只要问心有愧即为恶,问心无愧则为善,表彰的是发自内心的道德自律。挚爱丈夫不知避嫌的女子受世人鄙视,在冥界却因“中无他肠”得到敬重。啮齿受玷的烈女被司谳者苛责无已,冥官却从尊严和道义“哀其贞烈”,封她为横死诸魂长。不揆事势利害的医生拒绝为未婚女子堕胎,半年后就被冥司以杀人罪拘走(《阅微草堂笔记》)。冥司本乎人情人性,准许受害者亲手施行恶报,其不忤人心的判决蕴含小说家的社会思想批判,也给现实社会的道德伦理指引方向。
(二) 为现实生活提供案例和参照
乾嘉文言小说中入冥者有身居高位的侍郎、县令,儒者,有贩夫走卒奴仆,他们描述的大都是自己亲朋熟人的故事,涵盖了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群,内容大多是日常生活小事,为民众提供辨别善恶的案例和参照。
“杀人偿命”是现实社会法律的核心原则,现实世界中法律禁止受害人私自报仇,更不赞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鬼神世界将让受深冤大仇者以 “同态复仇法”复仇。比如打着理学之名的官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他们捉寻私情,访拿名妓,将男女褫衣裸杖,务在羞辱折磨以人致死。鬼神让其背上隆起烂桃似的臀肉尽脱的双臀,承受着受害者羞辱痛苦死去。(《妓仙》、《烂桃子色》见《子不语》)鬼神报应中令人发指的惨毒,诸如针刺、刀砍、下毒、剜心、割首等等,再现了施恶者当时的暴行,也给现实生活中的民众以警戒。
鬼神处罚的主要对象是世故太深或趋避太巧的“聪明者”。那些瞒天过海、涂饰弥缝的阴谋在鬼神面前无处遁形,“人心愈巧,则鬼神之机亦愈巧”,报应愈重。以权势计谋等机械万端得来的利益,虽历万劫,亦须填补,或以其寿、禄而抵,无禄可抵则变为六畜以偿债主,一世不足抵则分数世,终罹冥谪。算计主人的奴仆在十一世轮回时变成主人“所食之豚”; 精明盘剥的胥吏老来回乡只看到“满身淫疮”的妻子和一贫如洗的家,坐视朋友妻死家亡之人终得直面冥王指责时的伪善者的面具被揭时除尴尬愧疚外,还能震慑人心。刻薄对待夫族亲友的妇人在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詈,无地自容,惟日避此树边,苦雨凄风,酸辛万状,尚不知沉沦几辈,得付转轮”。(《阅微草堂笔记》)作者通过入冥者能将因果链条完整呈现出来。当读者从入冥故事中旁观因果报应时,必然用鬼神世界中赏罚标准约束自身行为意识,提升道德素养。
乾嘉入冥小说中鬼神世界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行为原则多有展现。不孝、诓骗是鬼神处罚的重点。婺源董某就梦中入冥,替生病的雷公震死不孝妇(《子不语·署雷公》),悍妇不孝不慈,为家庭带来家庭祸患。(《谐铎·鬼妇持家》)扬州妓女莺娇诳骗了朱某求欢的十金,后病瘵卒,投生朱家为一黑牛,卖了恰好十金。(《子不语·莺娇》)绍兴的吕兆鬣,前生做马时救主奋不顾身触崖而死,冥王判他投生绍兴吕氏为儿,后来以进士为陕西韩城令,身份显贵(《子不语·吕兆鬣》)。不同入冥故事以 “乘数效应”将小说传达的理念镌刻在读者意识中,不孝遭天打雷劈,欠人钱财来世当牛做马以还、杀生得报等理念深入人心。那些天性的行善者生前已经赢得子嗣功名、富贵寿考,死后更有巨大福报。入冥小说以丰富的案例给人们提供行为道德奖惩参照,发挥现实的道德教育作用。
乾嘉文言入冥小说塑造出一个公正的幽冥世界,表达小说家的社会治理构想,将小说传统的“借鬼神设教”的教育功能发挥到极致,使文言小说获得了更大的文化价值。鬼神世界广泛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层,也许这种观念永远不能消除。它虽不具备正统宣传的强制效果,但柔性管理的渗透性更强。乾嘉入冥小说发掘了这种力量,并将其深植于人的潜意识中,给这个法律和伦理准则尽将崩溃的乾嘉社会带来了一些安慰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