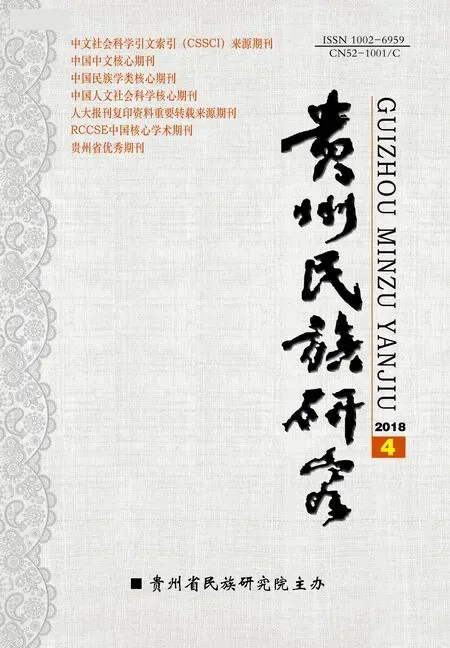“全球城市”的族群权利
姚尚建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城市从政治中心逐渐演变为资本中心。1938年,沃斯从城市作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提出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文化异质性这三大城市核心特征对于城市性(Urbanism) 构建的作用。[1]在世界范围内,城市资本与人口的流动既显示了国家权力的重构,也意味着社会权利的变迁。在国家与族群的互构中,在国家的政治边界中,“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成为了多族群国家认同研究中的‘元问题’。”[2]资本尤其是全球资本的流动进一步复杂化了这种认同,并在人口与资本相对集中的城市中,形成公共治理的多重困境。
一、资本、国家与族群的穿越
从国家的视角,治理体现为整体性与局部性治理的契合;从族群的视角,国家是族群生活外在的政治边界。但是族群与国家的逻辑性差异决定了国家治理与族群治理的不同形态,当国家权力趋于开放时,族群的社会界限对国家的边界的影响越小,反之,当国家权力趋于闭锁时,族群的蔓延就会被政治隔离所横亘,从而形成国家与族群的内在冲突。
首先,国家对于族群迁徙的规范性约束。德国民族学家李峻石(Günther Schlee) 在观测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以畜牧业为主地区的行政秩序和行政区划时发现,由于族群自决纳入宪法,因此行政单元往往沿着族群的界线展开。在这种新边界出来之前,基于畜牧业的迁徙往往借助一些传统机制,但是当新边界出来之后,敌意和迁徙的限制便出现了。[3]政治边界形成族群的内部的政治结构,也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形成族群社会属性向政治属性的转换。如果说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相处尚有传统农业社会的弹性机制,那么在这一转换中,建基于工业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刚性机制正在消弭这种社会弹性。
在一般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国家与族群通过身份互构实现的,这种互构也为国家治理的公正原则所确认:“国家有理由对人们出于种群、信仰、族群以及(最近出现的)性取向的理由而进行歧视的自由加以干预,正如非歧视所规定的一样。”[4](P61)在一般的语境中,非歧视与区别容易区分,但是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族群区别的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歧视,歧视的背后则无法遏制冲突。在民族国家的内在逻辑中,冲突论是一种重要的观点,“冲突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认同,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5]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体系,当国家的框架无法容纳族群的差异性时,族群有可能通过最终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形式来捍卫差异。
其次,国家对于族群生活的规范性约束。即使在国家的体系中,冲突依然存在。学者对于北爱尔兰的敌对群体研究中发现,文化的同质性远不足以保证人们和平共处。[3]因此,试图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来解决权利差异的问题有可能挑起新的社会冲突。在世界范围内,跨民族国家是常态的政治模式,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在于,无论何种族群,在国家的框架中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任何族群不得拥有凌驾于国家政治框架之外的特权。在国家的治理原则中,平等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平等主义反对精英主义(elitist)、贵族主义的(aristocratic)、种族主义的(racist)和其他的观点,这些观点宣称,有些人天生就优越于其他人。”[4](P93)国家通过法律捍卫这种平等原则。
社会善治的前提是良法,在不平等依然存在的国家,法律本身不过是不平等的社会规范的文字体现,“一个体面社会就是一个其社会组织不羞辱人民的社会……组织的羞辱分为法律的(如纽伦堡法案或其他种族隔离法所规定的)和运行方式的(如1991年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 两种。”[6]在国家的刚性边界中,族群必须服从国家的政治规则。在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中,族群的社会行为不停冲击国家的政治体系,迫使国家逐步后退,从而促使国家由权力的共同体逐步演变为权利的结盟。
第三,资本激励下的国家与族群的穿越。“族群性是集体身份认同的一种形式,它与宗教、亲属宗族、部族或者阶级归属等现象属于同一类别。族群性意味着,某一族群的成员意识到自己属于该族群,而且确信别人属于其它族群。”[3]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中,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个重要变量,对于国家来说,在宏观政治上追求国家认同,在微观政策上确认族群身份,往往意味着更少的政治与行政成本。
非洲是现代国家制度发育较晚的地区,民族对于国家的理论证明尚需要制度的支持。族群的历史往往伴随着特定的传统的兴衰,对于拥有悠久游牧传统的族群来说,国家的边界限制了迁徙,并把流动的社会形态固定下来,从而形成国家与族群的政治张力。而在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上,这种族群的张力与国家的张力往往并不一致。李峻石发现,苏丹人之间对于土地的争夺较为激烈,但是苏丹政府却乐意将10万英亩的土地提供给埃及,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这些拥有权力的苏丹人更加认同浅肤色的埃及人。[3]也就是说,国家与族群之间,政治的边界有时候并不吻合,借助于身份想象和文化标识,族群往往可以穿越国家的边界,并在他者那里寻找自我。
国家和族群的边界冲突并不仅仅受到身份的挑战,资本的崛起以其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工业革命确定的国家边界,加快了族群的全球迁徙。阿马蒂亚·森强调,在劳动市场的自由被法律、法规或传统规范所否定的情况下,即使非洲裔美国人在做奴隶时可以得到与自由农业工人得到相同的收入,但是奴隶制本身就意味着基本的剥夺,自由市场的发展是重大的历史进步。[7]市场保障了劳动的自由,全球市场保障了全球劳动的自由,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流动,原先的国家、族群的边界逐渐模糊,人们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进入不同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之中,从而给国家与族群的边界重构形成新的变量。
二、全球城市社会的族群治理
城市是人类历史中一个重大的成果。从农业社会的城市到工商业社会的城市,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到现代工业时期的全球性城市,城市日益集聚大量的人口,并不断挑战现代国家与传统族群的政治与文化边界;而国际移民与国内移民一道,加剧了社会融合的复杂性,并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与族群治理的逻辑演进。
首先,城市的复杂性与“全球城市”的话语转换。从雅典到中世纪的城市,从简单的围墙合围到城墙的拆除,城市在迅速地变化,“城市角色的转换不是及时的,而是通过几个进程,但这种改变就像一股快速的潮流,让我们看到了1850年后的一百年内城市地理的巨大转变,导致了复杂城市的形成,在形态、经济、社会、文化上呈现多种多样的变化。”[8]在交通与资本革命的驱使下,那些与乡村严格区分的城市逐渐模糊了地理和政治边界。一些虽处于特定国家之内,却受到全球规则约束的城市开始出现。
全球城市的概念有个变迁的过程,弗里德曼和沃尔弗(Friedmann&Wolff)首先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此后沙森(Saskia Sasen)则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概念加以修正。总体上来说,“全球城市”(或曰“世界城市”) 是指那些具有国际市场地位的城市。在这样的视角中,那些具有全球化特征的东方中小城市容易被忽略。正如彼得·纽曼和安迪·索恩利在《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中清晰指出:“我们不讨论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很少,她们只在自己民族国家的疆域内扮演有限的经济角色……我们关心的是城市经济功能的量级,以及能够设定城市全球地位的联系。聚焦这些世界城市意味着我们仅仅关注发达世界。”[9](P3)
其次,“全球城市”生活的族群属性。全球资本的流动支持了全球性城市的存在,也瓦解了国家与城市的政治联系。由于资本的介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消弭了城市工商业与人口流动的可控性,从而使城市形态日益多元。虽然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并不过多关注东方的城市,但是他们也承认,“世界城市”假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将城市的重要性按照功能而不是简单的大小来区分,即是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功能,而不是城市的大小决定了城市的地位。[9](P28)在“全球城市”论者看来,伴随着全球资本的推进,作为次国家的城市的独立性日益强化,并日益挑战民族国家的政治等级,甚至挑战国家与城市的利益互动。[9](P50-51)
在公元11世纪,西方城市借助于工商业重新崛起以后,城市就与资本的流动紧密联系。“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是有其内在逻辑的。由于全球化的过程起源于地域经济的扩展,因而全球化现象在地域经济的集结点——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具体讲,经济的全球化在地域上产生了一种复杂的二重性: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高度分离与全球范围内的高度整合。这就产生了对高度分散化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与管理的需要,而城市,特别是在区位上具有独特优势的大城市,无疑是进行这种控制与管理的最佳空间集结点。”[10]
“全球城市”的逻辑强调了城市在资本流动中的节点作用,却容易忽视城市形成以来最基本的判断——社会生活,从早期城邦到简·雅各布斯对于城市理性主义的批判,都说明这一判断确实存在。即使是资本的运作,也需要人力资源的参与,因此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是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这些人口既流向世界城市论者所谓足以控制全球资本的城市,也流向了那些拥有全球市场的城市。在这些资本的流动下,不同的族群不但跨越了国家边界,也跨越了文化边界,从而使全球城市具有不同族群共同生活的属性。
第三,全球族群生活的城市属性。在民族国家的论证中,族群的边界确认往往兼顾文化与地理。事实上,在波普尔看来,国际属性早已存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所有的欧亚文明国家都成了帝国,包括无数有着混合血统的人口。欧洲文明及其所属的所有政治组织,此后一直带有国际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带有互为部落的性质。”[11](P97)波普尔在对民族国家的原则进行批判的时候,一定没有充分想象在全球资本的冲击下,当代“全球城市”的革命性意义,因为在波普尔的论述中,族群多沿着地理边界历史性地、缓慢地变迁,但是在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基本政治原则之后,全球性的族群移民共同开展的城市生活远非“互为部落”所能阐释。
在全球资本的冲击下,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降临时,一些城市中以特定族群为服务对象的——诸如义乌市“土耳其餐厅”等——餐饮服务业开始繁荣,无不揭示了在资本的冲击下,在“全球城市”之中,社会生活依然和特定族群紧密相连,不过是,那些波普尔所谓的“互为部落”已经演化为异地生活,这种异地生活本身既是族群性的、也是城市性的。
三、族群社会的城市治理
“全球化伤害了我们的城市吗?经济的起伏动荡动摇了城市经济的基础吗?随着自由蔓延的资本和日趋扩张的国际竞争对地方重要性的削弱,地方民主能得到保证吗?城市之间日益复杂的关联性和依赖性将对地方民主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12]在这一连串的追问之后,我们仍然要反思的是,当全球化成为一种现实,当城市借助资本与人口的迁徙成为常态之后,资本的撤离与人口的离开,哪一种会对城市形成新的伤害?
首先,确认城市社会中的群体权利。在国家与族群的关系上,波普尔的质疑具有代表性:“民族国家的原则,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领土与一个民族的领土要相一致的政治要求,决不像今天它向许多人呈现的那样是自明的……民族国家的原则不仅是不适用的,而且从来就没有被明确地考虑过。它是一种非理性的、浪漫的和乌托邦的梦想,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和部落集体主义的梦想。”[11](P98)
波普尔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在民族国家理论的背后,是已经形成的国家与族群关系;而在国家与族群的关系背后,存在多数权力与少数权利的博弈。一般认为,公共领域的完整性要求国家漠视少数权利,但是在现代政治学中,作为整体治理主体的国家必须正视差异性群体及其权利的存在,“如果注意到所有可设想的群体权利,我们就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问题结合起来。有些权利或许有这种效果,它们授予群体以与广大社会相关的、重要程度的自主和自治。也就是说,它们允许群体退出广大社会的事务,从而建立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小圈子。”[4](P275-276)
其次,促进城市族群的社会融合权利。多数权力与少数权利的结合是国家政体必须面对的制度性困难,也是一个城市政府所要直面的政策性困境。尊重少数权利会刺激城市乃至国家的瓦解吗?罗伯特·L.西蒙的判断是否定的。他引用了加拿大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锡克教徒(Sikh)不必遵守皇家加拿大骑警的行为规范,却加强和促进了少数群体更强烈的政治包容意识。因为“它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参与广大社会公共制度是受欢迎的,他们不需要放弃自己特定的身份也可以被认可为完全意义的公民。”[4](P276)
当然对于全球城市来说,成为国家公民并不是地方治理的首要选项,但是成为城市居民却是城市治理的事实起点。历史已经表明,只要人口汇聚,只要具有了工商业性质,城市注定就是一个异质性的组织存在。在抽象的公共利益背后,是大大小小的群体乃至个体利益。正如卢梭所判断的那样,“社会的组成可说是普遍性的倾向;只要个人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就组成社会——永久性的或暂时性的——每个社会都具有总意志来调节其成员的行为。大的社会不是由个人直接组成,而是由较小的社会构成;每个包括范围更大的社会规定其组成的较小社会的义务。”[13]
第三,城市族群权利的实现机制。在列斐伏尔(一译勒菲弗) 那里,进入城市意味着权利,这种权利是普遍、正义的,“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就是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甚至从社会中排出。拒绝让一个歧视性的、隔离性的组织将它们从都市的存在中排出,进入都市的权利为这种拒绝提供了合法性。”[14]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城市权利的实现取决于城市个体的城市角色,在戴维·哈维看来,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首先回答的。只有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后,哈维才坚信,“城市权利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人的或群体的权利。另外,改变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力量的运用,所以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15]从萨拜因的城市利益到列斐伏尔、哈维的城市权利,从个体到群体,城市理论完成了权利的转变。
“全球城市”意味着权利概念的扩张,在民族国家边界弥散之后,在全球公民社会仍然停留在理论争鸣阶段时,“全球城市”是否标志着更为广阔的“全球权利”,那么在国家依然刚性存在的历史阶段,人们将如何确认这种权利的边界及其实现机制?我们认为,在城市权利的理论转变中,族群的权利实现并不矛盾,在全球资本裹挟着人口穿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时候,那些操着不同口音、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人口在城市定居,城市政府应该尊重其城市社区“居民”的角色,并通过社区权力开放吸纳不同族群人口的城市融入,即以社区理解城市、以城市认识国家、以居民吸纳公民,从而实现城市权利的整体实现。
结论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eler)强调,“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从城市中诞生的(city born),这是一个极为确定但却从未被深入研究的事实……世界历史与人类历史不同,它的真正标准在于,世界历史就是城市人的历史。民族、政府、政治和宗教,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城市。”[16]全球化冲击了民族与国家的双重边界,冲击着人们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城市体系,资本与权力相互联合,改造着我们熟悉的城市。在城市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制度的捍卫,那些卑微的少数往往无法维系自身的权利,但是“城市权利即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具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15](P5)。当我们认识到权利的集体属性时,那些基于多数与少数、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才可能弱化,那些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的政治主题才可能重新回归我们的城市与生活当中。
:
[1]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4(1):pp.1-24.
[2]郝亚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理论述评与探讨[J].民族研究,2017,(4).
[3](德)李峻石.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M].吴秀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4](美)罗伯特·L.西蒙.社会政治哲学[M].陈喜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卢鹏.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以中越边境哈尼族果角人为中心的讨论[J].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6](以色列)阿维沙伊·马加利特.体面社会[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引言.
[7](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3.
[8](美)詹姆斯·E.万斯.延伸的城市——西方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M].凌霓,潘荣,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340.
[9](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M].刘晔 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0]周振华.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J].社会科学,2006,(10).
[1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美)汉克·V.萨维奇,保罗·康特.国际市场中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叶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19.
[13](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 [M].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57.
[14](美)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5](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6]Oswald Spengeler,Der Unitergangdes Abendland es,转引自(美)罗伯特·E.帕克等.城市[M].杭苏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