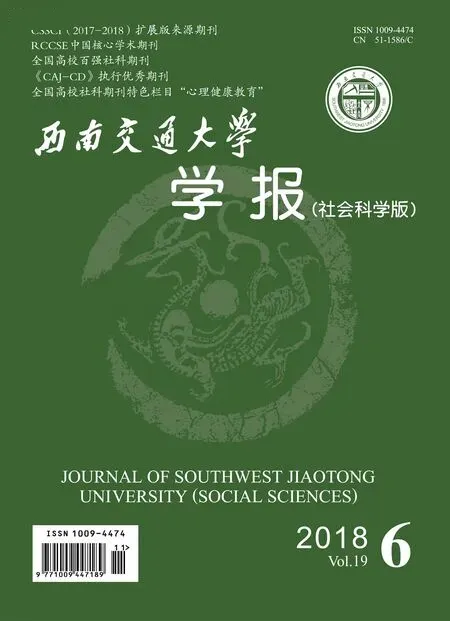论《尤利西斯》汉译主体间性的伦理规范
(1.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2.常州大学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所, 江苏 常州 213164)
国内目前对《尤利西斯》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汉译的语言技巧及表现。有学者着重探讨《尤利西斯》中意识流语言变异现象,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和语域变异等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将这些语言变异现象再现。有的学者则通过比较分析多个译本,以功能翻译和语料库翻译为理论基础探讨译者语言处理的差异,并聚焦于《尤利西斯》汉译的“陌生化”或“前景化”语言或结构和叙述模式再现的研究。(2)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尤利西斯》的汉译。不少学者借助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分析译者如何实现译作与原作的语码转换。(3)译者主体性研究。此类研究侧重于研究萧乾、文洁若译本的创造性叛逆,围绕突破原文藩篱,以目标语读者阅读期待为中心,分析如何实现语义连贯、形远意达、注释之便、翻译选择和翻译思想等“叛逆”现象。(4)对《尤利西斯》两个汉译本的评价。有学者从总体上考察萧乾、文洁若译本和金隄译本的得失,寻找导致巨大差异的原因,重点围绕两译本的译者、译风、注释等进行比较研究。(5)从文化视角研究《尤利西斯》的汉译。此类研究主要以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理论基础,围绕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尤利西斯》进行文化解读。
翻译活动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多元互动的过程,即“间性”互动过程;而翻译伦理学研究则是围绕文本间性、文化间性与主体间性三维层面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进行理论体系的研究。笔者认为只有“译者中心”、“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形成“共生共处”,才能使“原文—译者—译文”三元生态关系得到均衡和谐发展〔1〕,这是间性伦理规范的重要原则。翻译过程是具有典型的间性特质的活动,包括文本间性、文化间性和主体间性等,其中主体间性是间性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显性的行为,因此讨论主体间的翻译伦理具有很好的理论意义,而《尤利西斯》汉译本主体行为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翻译主体间性的相关概念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是“intersubjectivity”,主要指主体之间某种源自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而形成互动与交流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主体间性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体间直接的互动与影响,是人的主体性通过相互承认、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而实现在主体间的延伸。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消解了一元中心主体论,实现了主体多元平衡、共生的多元性。传统的语际阐释一直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要特征是强调一个“中心”,忽视其他“中心”,割裂了作者、文本、阐释者(包括译者、读者等)和赞助人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孙瑜博士认为,主体间性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人际关系和价值观的共性问题〔2〕。哈贝马斯的交际理论把间性理论推到一个高度,认为主体间性是主体间的互动、互融和互相理解的交际关系,能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共识与统一。主体间性的哲学伦理思想就是要倡导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与彼此尊重,要进行和谐、平等、理性的交流与互动。
翻译活动是主体间性发挥的重要表现形式,因为翻译活动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如果翻译没有多元主体的参与,译者也没有存在的意义。因此,翻译得以完成离不开译者的主体性的实现。同样,译者作为主体地位的核心,还要和他周围的各种“他者”要素产生交集、关联和互动,因此翻译主体间性必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属于现代哲学,特别是当代哲学的理论研究范畴,也被称为“交互主体性”、“主体际性”和“共主体性”。根据《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主体间的东西主要与纯粹主体性的东西相对照,它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或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3〕这是一种从认知上对主体间性狭义的阐释和理解。从广义上看,主体间性应是“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4〕。由于人的本质属性是多维、异质性的,因此主体间性也必然具有多维性和异质性,具体表现形态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或为心灵上的,或为物质上的。主体间性的相同性和异质性必然导致主体间会产生亲和力和排他力。翻译活动本质上是间性活动,其中主体间性活动是最为活跃的能动关系。许钧教授认为:“翻译活动,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自在的共体”〔5〕。他借助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阐释学认为作者、译者和读者构成一个开放的共体,翻译结果会受到这一共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最佳的结果就是和谐共生。陈大亮对翻译目的论进行了反思,认为目的论的重点是“放在译前的跨文化人际交往上,重视对发起人、译者、委托人、译文使用者、译文接收者等目的语中的行动参与者和环境条件等翻译外部因素的分析”〔6〕,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这些跨文化人际交往中的各类人是翻译主体,但他们也是翻译活动中主体间性的共体。刘卫东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指出,翻译主体在翻译活动中要以“某种形式承认和遵循某些规范”,因为在翻译活动中主体间性不是以单一直线的方式展开的,而是以复杂的多维方式呈现的,具有群体交互特征〔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翻译的主体间性是指以译者为共体核心的主体和其他主体,包括赞助人、作者、读者、文本主体等之间产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他们之间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通过各自的视域形成某种默契或在异质中寻求某种妥协,构建一种“间性主体”。翻译主体将遵循什么样的主体间性伦理规范?译者是继续作为原作的“奴仆”还是对原作肆意“宰割”?赞助人系统是否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译者施加压力,让译者朝着自己期待的视域发展?读者是否为了自己的审美需求或阅读期待对译作的呈现态势施加影响?这些是翻译主体间性伦理规范应该思考的主要问题。
二、译者与作者的主体间性
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原著的阐释,需要译者和原著作者相互“对话”才能实现。译著其实是原著的一种“复调”,充满着原著作者和译者的双重声音〔8〕。译者对原作者和原著的推崇,就会加大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某种共鸣,译者在翻译时则更会对原著充满敬畏,会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之,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缺乏共鸣,译者就会对译作采取“宰割”的态度,会根据自己对原著的理解肆意翻译,甚至会扭曲原作的意思,这时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性就表现得特别强烈。传统的译学伦理观认为原作者处于主宰地位,译者必须尽可能靠近原作者,在充分揣摩原作者的意图后忠实地再现原作,译者俨然成为原作者和原作的“奴仆”。现代的翻译伦理观则把原作者和译者“隐身”到后台,文本成为翻译的主体,强调翻译语言的“对等”、“等效”或“等值”,译者由“奴仆”变为“幕后者”,即俗称的“译者隐形”。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的翻译伦理观强调译者的主宰地位,认为译者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阐释力,原作者的意图被边缘化,文本成为译者操纵的对象,译者变成了“操纵者”和“改写者”。不难看出,上面的三种译者与原作者主体间性的翻译伦理都是一元的,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主体间性的交流缺乏平等和相互认同。
事实上,许多译者在翻译时很少有机会和原作者进行交流,即便有机会交流,有时候对一些文本的理解也未必能达成一致。当然,若有机会和原作者交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省去不少困惑。例如,1921年12月7日,拉尔博为《尤利西斯》的出版准备了一场报告会,在准备过程中他建议西尔维娅·比奇和艾德里安娜·莫尼埃把《尤利西斯》的部分段落译成法文在报告会上朗读,于是她们请雅克·伯努瓦把《珀涅罗珀》翻译成法文。伯努瓦为了准确翻译《珀涅罗珀》,就恳请乔伊斯把《尤利西斯》的提纲给他,并且和乔伊斯当面探讨了一些翻译难点。如第十八章结尾处的“我愿意”很难译成法语,按法语的习惯,女人在这里说的是je veux bien,语气比je veux弱,所以他在最后添上了一个“oui”。当乔伊斯发现雅克·伯努瓦添了字,很为惊讶,因为原文没有那个字。伯努瓦解释说添加了该词后语气会更好一些,他们为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事实上,更多时候,译者和原作者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因此翻译时就需要译者拥有独立的理解力和阐释力,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译者和原作者的相互认同、承认,虽然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译者对原作者的认同。《尤利西斯》的译者金隄和萧乾、文洁若夫妇都具有类似的对原作者的认同过程。金隄于1945年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期间曾读过《尤利西斯》一次,后来受命翻译《尤利西斯》,再后来被它的语言和艺术性所吸引,最后毕生从事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翻译研究。萧乾早在1939年就对“乔伊斯及其作品比较感兴趣,特别对《尤利西斯》简直是顶礼膜拜”;文洁若年幼在日本时,担任外交官的父亲拿着日文版的《尤利西斯》对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将来就能把这本奇书译出来,在这个奇书的中译本上印上自己的名字”〔9〕。三位译者都对乔伊斯和《尤利西斯》同样地膜拜,并共同选择了乔伊斯和他的“天书”来翻译和介绍。乔伊斯虽然没有机会一睹其作品的中文译本,但是历史和机缘选择了这三位中文译者,相信他一定会对他们成为自己作品的译者而欣喜若狂。译者对原作者的认同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前提之一(行政命令的翻译活动例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翻译活动中原作者和译者双方应该是相互独立、平等的间性主体,他们的交流必须是在相互认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原作者并不具备对原作的唯一解释权,译者在原作的基础上也同样具有他自己的解释权。因此,翻译就是把他者的语境解释融合到本我的语境解释中,译者只有很好地领会原作者的意图,才能实现间性主体的融合和平等交流。
三、译者与赞助人系统的主体间性
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行为,它与外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密不可分,虽然这些因素的影响有时是直接的,但更多是通过赞助人间接地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对译者施加影响。笔者认为赞助人是一个由多维要素组成的,互为影响、互为能动的互动系统。译者翻译活动离不开赞助人系统的支持和帮助。赞助人系统为译者提供必要的生活津贴和工作场所,同时对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杨武能先生曾对自己受益于赞助人感受颇深,他认为《世界文学》的李文俊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绿原先生在非常情况下破格编发他这个小人物的书稿,对他比较顺利地走上文学翻译之路至关重要〔10〕。如果没有出版人的魄力、视野和甘为他人奉献的精神,也不会有一部部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在中国获得新的生命,也不会出现一大批风光无限的译者活跃在中国的译坛。虽然在特定时期,有的译者完全听命于赞助人系统的安排,如选材、翻译方式、出版无法署名等,但是总体来说,赞助人对翻译的具体翻译活动影响是有限的,他们侧重于对选材、目的、出版和服务对象有较为明确的要求,因此译者有充分的翻译自由度。译者在接受赞助人委托时,就要履行服务承诺,但是翻译的结果是多因素的产物,译者只按照赞助人的要求去翻译是不够的。从伦理学的角度考量,如果客户的翻译要求违背了翻译的基本伦理,译者是可以提出异议甚至拒绝服务的。《尤利西斯》这部天书在中国的译介离不开赞助人的努力。金隄先生是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主编袁可嘉的不断劝说下才开始翻译《尤利西斯》的,后来《世界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对他的翻译工作予以积极支持,金隄先生直至去世前一直从事《尤利西斯》文本研究和翻译研究。和金隄先生类似,萧乾先生、文洁若先生翻译《尤利西斯》是在译林出版社主编李景端多次登门拜访劝说后才开始翻译的。译者和以委托方为代表的赞助人系统积极互动,形成了译者和赞助人的间性主体关系。例如《世界文学》主编李文俊专程到天津和金隄先生商议《尤利西斯》选译章节和发表的计划。人民出版社在得知金隄先生选译《尤利西斯》部分章节后,“主动派出副总编秦顺新和金隄先生商谈出版《尤利西斯》全译本事宜,并提出因为该书特别困难,可以多给时间,三至五年交稿”〔11〕。赞助人不是具体的某类人,而是一个群体。笔者认为,赞助人系统“可能是一个个具体的实体,也可能是抽象的单位,可能是可分的,也可能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系统性和关联性。”“可以是具体的实体团体,如宗教集团、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政府、出版机构、大众传媒、团体组织、民间机构、学校;还可以是实体个体,如出版商、丛书的主编、使节、家人、朋友等;也可以是抽象的形态如政治环境、方针政策、诗学观、精神支持、舆论导向等。”〔12〕一部优秀的译作离不开赞助人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交流、互动,理想的译者与赞助人的间性伦理关系是各主体间能够相互能动、相互尊重和相互承认,在沟通和理解中达成共识,最终获得理想的译品,从而实现赞助人与译者的双赢局面。
四、译者与译作读者的主体间性
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最好体验是直接阅读原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拥有阅读原著的外语能力和理解能力,因此翻译在很多时候承担了延续原著在异域生存和再生的任务。译者和读者发生间性主体关系是因为译本这个纽带,译者是原文本的阐释者和创作者,而读者是译作的阐释主体。很少有译作读者会去比对译作与原作,因此他们更希望通过译作感受到和原作读者同样的阅读体验。这需要译者充分地传达原作的意图,实现译作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样读者也需要对译者充分信任和理解。译者通过引导读者阅读译本,促进读者对译本的接受与批评,而读者通过阅读,能对译者做出一定的评价,促进译者继续修订完善译本,这种间性关系是在怀疑与信任中构建的。传统的译学伦理认为译者与译作读者是主客体关系,译者是动作的施动者,而译作读者和原作一样是被动者。虽然译者是主体,但是处于“一仆二主”的境遇,译者处于“仆”的地位,要伺候好原作和译作的读者。“伺候”好原作,就是要求译者能够充分领会并传递原作的意图;伺候好译作读者就是要获得译作读者对作品的满意和认同。解构主义翻译伦理认为译者是原本和译作读者的主导者,可以肆意操纵和改写原作,译作读者是译者的被动接受者。事实上,好的译作也需要读者的反馈和批评,才能不断修正不足,从而译出理想佳作。《尤利西斯》译本一问世就引起了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冯亦代在比较金译和萧、文译第一章后,就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把两个译本仔细地读了第一章首十页,就有36处可以推敲商榷的地方。”〔12〕金隄先生对此也曾撰文进行了解释,译者和读者的互动就这样发生了。刘军平对比了两个译本的目标语的可读性、注释后得出结论:“两家在一些细微末节处都存在一些疏漏,相比之下人民版出现这样的情况较多一些。”〔13〕王振平先生对金隄译作逐字逐句通读一遍后,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王友贵先生也把他过去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反馈给了金隄,这些学者从比较高的层面为金隄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通过和同行读者讨论具体译法和等效原则等,他不断受到启发,促进了他对译作的不断修订完善。”〔12〕金隄先生在去世前完成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尤利西斯》译作的修订工作,但是这部天书的修订是无止境的,太多的谜团也留给后世读者去想象。崔少元教授也指出,金译和萧、文译翻译中出现了一些误解和夸大信息,在比较两种译本的得失之后,他指出了译文中的许多错误,如“wretched bed”,萧、文翻译为“简陋”,忽视了女主人的内心情感变化;“fourworded speeeh”则被翻译成“浪语”,显然都是不贴切的〔14〕。萧乾先生去世后,文洁若先生一直根据学者和读者的反馈意见对译文进行修订完善。在译林版最新修订版的序中,文先生明确指出,“本书全译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一些热心的朋友(尤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冯建明先生)还就某些译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提供了补充的人物表。”文先生把原来繁琐的文字修改得更加简洁,尽量保持意识流特色,同时仍坚持力求易懂的原则。负责出版《乔伊斯全集》的责任编辑孟保青曾对记者说:“文化界普遍认为萧乾、文洁若合译的译本偏重文学性,有些译文未必准确;金隄作为学者追求严谨、还原作品原貌,但同时可能欠缺生动。”〔15〕该评价虽然笼统,但是基本上准确地评价了两个版本的译作。两个译本的译者在有生之年都能和读者很好地互动,倾听读者的建议,并不断对译作进行修正,他们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译者与读者主体间性的互动,即读者对他们充满了信赖,因为他们都用自己的译作为读者提供了意识流巅峰之作的大餐。他们力图对原作者的意图真实的、正确的传递,同时也深信现代读者的理解和阐释能力,能和他们进行良好的互动,尽量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这就是译者与读者之间形成的良好的“契约”关系,即译者有自己明确的翻译策略、诗学和定位,做到翻译的每一个字都是对读者的一种誓言,实现译者与读者之间视野融合一致,真正做到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共识共存、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简言之,对于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天书”,译者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形式,如序言、译后记、研讨会、读者见面会等形式介绍原著,构建读者阅读期待,降低读者对这部语言形式、叙事艺术多变,内容博大精深的巨著的阅读困难,又要避免过度阐释,剥夺读者自己的探索与专研空间,这样才能给读者足够的自由性和主体性,形成原著与读者先见视野的融合,真正让译者和读者之间实现主体平等、相互认同、相互尊重的伦理规范。
五、结语
翻译是复杂的活动,译者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平衡好内外要素之间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着译作的质量。我们在对传统翻译伦理思想和现代翻译伦理思想“去粕存精”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构建更为平衡与和谐的翻译间性伦理规范。主体间性作为间性理论研究的领域之一,是现代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前沿。伽达默尔认为解释活动是主体间的对话和“视界融合”,哈贝马斯也认为孤立的个体是交互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活动本质上就是原作者、译者、赞助人和读者共同参与的活动,因此译作是一种“共生”的结果。这些主体中不存在主次关系,而是平等互助、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的共同主体。翻译共同主体间性关系主要表现为:(1)译者与原著作者的主体间性反映了译者在选材、作者选择等方面和原著作者具有某种心灵契合性;(2)译者与赞助人系统以及译著读者的间性关系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翻译外部生态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通常情况下多是积极的,对文学作品在异域译介起着推动作用和改善译著水平的作用。主体间性理论破除了翻译中的二元对立命题,打破了两极封闭的系统,实现了翻译行为的多元化。因此,翻译活动不再是文本层面的语言转换,还涉及社会因素、译者个人背景、赞助人系统和读者期待等诸多要素。翻译主体间性伦理规范的构建需要主体关系中的各参与主体既要保持相对独立又要相互关联、相互认同和相互制约,要平等对话、彼此理解与尊重,才能实现共识共存,也才能翻译出理想的“译作范本”。理想的“范本”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原文时既充分考虑作者的意图,并尽可能地准确传递原文的内涵,同时又要能兼顾译作读者的阅读期待〔16〕。因此,译者应该是这个主体间性系统中的主动者,他要主动地和其他间性主体协商、沟通,并运用自身具有的双语能力,使原作在译语文化中得到生命延续或者新生,实现把“理想范本”作为世界文学交流的介质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