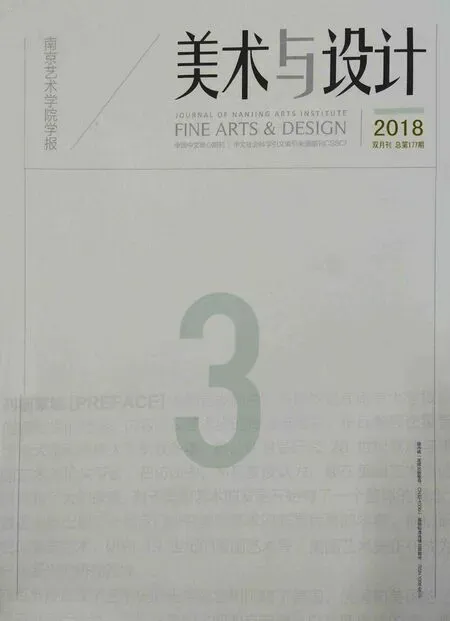“逸”在画论中的含义演变:对“法”的背离与回归
鄢 虹(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逸”作为文人画的最高品格,其地位之确立,是在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一书中。早在南北朝时期,“逸”便已经成为绘画批评的术语,出现在各种画论中,但自从“逸格”被标举为绘画的最高品格之后,“逸”这一概念的内涵便在逐渐发生复杂而微妙的变化。为什么“逸”会成为绘画的最高品格?它的含义在此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考察“逸”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历代画论中发生的演变,某条主要线索或许可以被指认出来:对“法”的背离与回归。下文便将从这一线索入手,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一、“逸”在《益州名画录》问世前后的含义差别
“逸”首次被标举为画作的最高品格,是在北宋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中。此书收录了唐五代活动于四川成都一带的五十八位画家,把他们按水平高低分别收录在逸、神、妙、能四个品格里,其中逸格只收了孙位一人,神格地位稍低,也只收了赵公祐和范琼两人。其余的人,则分别收录在被进一步细分为上中下三品的妙格与能格,以及附于末尾的“有画无名”一栏里。不难看出,“逸格”在这一品第系统里的地位是很高的,这不仅体现在它的排序上,同时也体现在逸、神二格与妙、能二格的人数差,以及它们明显体现出差异的铨次方法上。黄休复推出这个品第系统之后,不断有人对此系统,尤其是对“逸”的地位表示肯定,“逸”在绘画品第系统里的最高地位从此确立,而文人画家们在绘画领域对这一概念的建构与再阐释也随之展开。
早在南北朝时期,“逸”便已经出现在了对画家的品第中。谢赫的《古画品录》里,“逸”一共出现了四次:
第二品,袁蒨:比方陆氏,最为高逸。象人之妙,亚美前贤。但志守师法,更无新意;然和璧微玷,岂贬十城之价也![1]
第三品,姚昙度:画有逸方,巧变锋出,鬼音魁神鬼,皆能绝妙同流,真为雅郑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学所及,虽纤微长短,往往失之,而舆皁之中,莫与为匹。[1]359-360
第三品,毛惠远:画体周赡,无适弗该。出入穷奇,纵横逸笔。力遒韵雅,超迈绝伦。其挥霍必也极妙,至于定质块然,未尽其善。神鬼及马,泥滞于体,颇有拙也。[1]360-361
第三品,张则:意思横逸,动笔新奇,师心独见,鄙于综采,变巧不竭,若环之无端。景多触目,谢题徐落,云:“此二人,后不得预焉。”[1]362
在这四位被用“逸”来评价的画家中,除了袁蒨以外,其他三位都体现出了一种相似的特质,那就是新奇多变,不为法度所拘束。如姚昙度,是“巧变锋出”“纤微长短,往往失之”,画得很有创意,但在细节和比例上面可能不太准确;又如毛惠远,“出入穷奇”;至于张则,则是“动笔新奇”“变巧不竭”。
此后,唐朝的张彦远、五代的荆浩等人,在使用“逸”这一表述来评价画家、画作时,用的也基本都是这个“新奇多变,超脱常规”的意思,如张彦远评价顾恺之有云:“循环超忽,调格逸易。”[2]荆浩说白云尊师“动用逸常,深不可测”,[3]也是说他超出常规。
在这个时期,“逸”在其他文献中的一般含义,也正是这个意思。《说文解字》对“逸”的解释是“逸,失也,从辵兔,兔谩訑善逃也”,[4]指出“逸”的本义是兔子活泼好动,善于逃脱圈套,不肯循规蹈矩。因此,可以认为,在北宋以前,“逸”在画论里的意思,和它在其它文献里的一般含义,基本是相同的。在与“法”的关系中,它明显表现出对“法”的背离。
然而,从北宋开始,“逸”在画论里的含义就逐渐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黄休复晚出一百年左右的韩拙,在其《山水纯全集》中谈到“逸”时,是这么说的:
然作画之病者众矣,惟俗病最大,出于浅陋循卑,昧乎格法之大,动作无规,乱推取逸。强务古淡而枯燥,苟从巧密而缠缚。诈伪老笔,本非自然。[5]
而对黄休复高标逸格一事极为支持的邓椿,在《画继·杂说》里对“逸格”则有如下一段讨论:
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斯人之徒欤![6]
很显然,这两人在谈论“逸”时,都已不再单方面推崇它破“法”的一面,反而开始强调“法”的重要性,如韩拙在批评“乱推取逸”而实有“俗病”的画作时,便说它们是“昧乎格法之大,动作无规”;而邓椿对“逸格”在孙位以后的发展趋势提出批评,则是说后人“益为狂肆”、“无所忌惮”,言下之意,也是说他们没有规矩,不顾及“法”的制约性,因此称不上真正的“逸”。这意味着,“逸”这一品格对“法”的背离已然开始表现出它的流弊,需要得到制约了。
这一趋势发展到明清两朝,就更为明显了。明人董其昌在其《画旨》中有云:
画家以神品为宗极,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曰:“失于自然而后神也。”此诚笃论,恐护短者窜入其中,士大夫当穷工极研,师友造化,能为摩诘,而后为王洽之泼墨;能为营丘,而后为二米之云山,乃足关画师之口,而供赏音之耳目。[7]
这话说得很清楚:“逸”品固然高妙,但因为不重格法,容易鱼目混珠,让护短者窜入其中,因此文人画家们应该“穷工极研”,磨炼画技,先学好王维、李成的法度,再去追求“逸品”的高度。清人方薰在其《山静居画论》里也说道:
逸品画从能、妙、神三品脱屣而出,故意简神清,空诸工力,不知六法者乌能造此?正如真仙古佛,慈容道貌,多自千修百劫得来,方是真实相。[8]
这就说得更明白了:不知“六法”的人,怎么能达到“逸品”的境界?在这一时期的画论中,人们在谈论“逸”时,“法”几乎成了一个必须顾及的前提条件。
然而,此时“逸”在其他文献里的一般含义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康熙字典》对“逸”的三条解释,分别是过失、奔纵、隐遁,基本仍围绕“超脱常规”这一基本中心义展开。由此,文人们在绘画领域对“逸”这一概念的再建构,便非常明显了。为什么他们会采取这样一种建构方向呢?
二、“逸神妙能”绘画品第系统的建立过程
要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需要先对“逸神妙能”这一绘画品第系统的建立过程做一番梳理。逸、神、妙、能这四个品格,并不是黄休复提出来的,在晚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里,此四品便已经以“神、妙、能、逸”的顺序出现,其中神品收了九人,妙品收了二十三人,能品收了六十二人,此三品,皆进一步分出了上中下三个等级。逸品排在能品之后,只收了三人,且不分上中下。
在朱景玄的序里,他对这一品第系统是如此描述的:
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9]
此外,在介绍完归入逸品的三位画家之后,他又附了一句这样的描述:
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之有也,故书之。[10]
由这两段描述,以及逸品在该品第系统里收录的人数和铨次方式(不分上中下)来看,朱景玄对这一品格其实并没有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逸品相对于神、妙、能三品而言,并不像能品相对于妙品,妙品相对于神品一样,其间存在明显的价值等差。朱氏标出此品,更多的是一种“聊备一格”,以待后人的做法。换言之,逸品在这个品第系统里的位次,或许并不能完全说明它的实际价值。
如此看来,朱景玄的这个品第系统,其实与黄休复后来提出的“逸神妙能”之品第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了。
然而,朱景玄的这个品第系统亦有所本,它的前身乃是张怀瓘在《画品》里建立的“神、妙、能”三品之系统,这一点,朱景玄在他的序里说得很清楚。张怀瓘《画品》已佚,然其论画之言语散见于后人画论中,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便有一条这样的记载:
张怀瓘云:“顾公运思精微,……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喻之书则顾、陆比之锺、张,僧繇比之逸少,俱为古今之独绝,岂可以品第拘?谢氏黜顾,未为定鉴。”[11]
这是张怀瓘评价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三人的一段话,这三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画家,从张怀瓘的话来看,他对他们也极为推崇,称他们为“古今之独绝”。以今人的观念来看,此类画家一定处于品第系统的最高层,然而,这却并不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对于他们三位,张怀瓘只有一句话:“岂可以品第拘!”在他看来,水平最高的人,是不宜纳入品第系统的。
这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张怀瓘建立的这个“神、妙、能”之品第系统,本来就是不完备的,在这一体系里,很可能还存在一个隐藏的品格,那就是“岂可以品第拘”的最高品格。换言之,“神品”或许从一开始就并不是最高的品格。
张彦远本人的画论里,有一段更为人所熟知、常被后人引用的论述,也涉及这一现象:
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11]38
据这段话来看,张彦远其实也提出了一个品第系统,而且在这个系统中,隐藏的最高品格已经用“自然”一词标出来了。但是,张彦远并没有在他的著作里把这个品第系统付诸应用,所以这个“自然——神——妙——精——谨细”的说法不常为人所知,实际存在于“神品”之上的最高品格,仍然缺少一个公认的名称。试想,如果张彦远实际使用了这个品第系统,那么“逸”还能不能成为最高品格的名称,乃至黄休复还会不会高标逸格,都是很难说的。
因此,概括说来,黄休复以前的绘画品第系统,其实都存在一个空白部分,而且这片空白还恰好处在品第系统的顶端。虽说中国各类艺术的最高境界一旦向“自然”这一概念靠拢,或多或少地都会带上一种“不可言传”的特质,但人们仍然需要一个表述来对此境界展开讨论。因此,像这种最高境界缺失名称的情况,注定不会持续太久,这是由绘画理论本身内在的发展要求决定的。
那么,当朱景玄不置可否地提出一个新品格之后,他便相当于给缺失名称的最高境界带来了一个获得名称的契机,而黄休复最敏锐的地方,就在于发现了“自然”和“逸”在阐释上的相通性,抓住了这个相当不错的契机。他在首倡逸格时,对逸格给出了这样一段描述: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员,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12]
正因为绘画领域的最高品格迫切地需要一个名称,而黄休复又如此巧妙地抓住了朱景玄提供的这个契机,这个发生在绘画品第系统内部,看似不起眼、实则相当大胆的结构调整才会显得格外重要,并且顺利地获得了后人的赞同或默认。邓椿在他的《画继·杂说》里便写道:
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作《益州名画录》,乃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6]75-76
此外,苏辙在其《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中,也对这一品第系统表示了赞同:“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13]此二人之赞同,在表述上几乎都是不假思索的、直觉式的。
三、“逸”对“法”的反转与“逸”的流俗化
“逸”之所以在北宋一跃成为画作的最高品格,与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亦大有关联。对“逸”的推崇,以黄休复的高标逸格为一标志性事件,然而这一事件的趋势,却最晚在中唐时便已经开始出现并发展了。中唐到宋初,是我国绘画在法度上渐趋完备的时期:唐人重法,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潘天寿先生称其“精到详尽,实为吾国通纪画学最良之书”[14],中唐画法、画学之兴盛,可见一斑。
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将兴起的文人画之大宗——山水画之画法的全备。元人汤垕在其《画鉴》中有云:
如六朝至唐初,画者虽多,笔法位置,深得古意。王维、张璪、毕宏、郑虔之辈出,深造其理。五代荆、关,又别出新意,一洗前习。迨于宋朝,董元、范宽、李成,三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之法始备。[15]
由此可见,对绘画来说,宋初是个法度完备的时期。然而,法度完备,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发展困局。因此,“逸”这个名称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与绘画的最高境界结合,并不仅仅出于它和“自然”在阐释上的相通性,也与它“超脱常规”的本义有很大关联。
对法度过于周全一事保持警惕的思想倾向,其实早在张彦远的书中便已经出现了:
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于自然而后神……。[11]37-38
“了”就是周全完备,在张彦远看来,画画不怕画得不周全,就怕画得太周全,太周全,就会失去自然天真,最多只能达到“神”的境界。张彦远之后,法度浸孳,至于北宋,终于激起黄休复高标逸格,大家纷纷响应。这一标志性事件的背后,如上所述,其实存在一个相对漫长的蓄势过程。
然而,当“逸”这一针对法度的反转性力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文人认同、推崇,并随着文人画的主流化而获得更广的接受面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逸”本身正在转变成新的“法”,甚至在转变成一种流俗。
从唐末以来,用逸笔、有逸思的画家就颇受时人追捧,如宋人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记载道:“赵德齐,温其之子。袭二世之精艺,奇踪逸笔,时辈咸推伏之。”[16]“韦道丰,江夏人,善画寒林。逸思奇僻,不拘小节,当代珍之,请揖不暇。”[16]45又如元人夏文彦在其《图绘宝鉴》中提到:“孙知微,字太古,眉阳彭山人。世本田家,天机颖悟,善画,初非学而能清净寡欲,飘飘然真神仙中人。喜画道释,用笔放逸,不蹈袭前人笔墨畦畛,时辈称服。”[17]
能为逸笔者如此为世所珍,请揖不暇,到了元代,黄公望便已开始在《写山水诀》中告诫后学:“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才多便入画工之流矣。”[18]依黄公望之言,逸笔不能多用,用多了竟会沦为画工,可见当时这种画法有多么流行。
在恽寿平的《南田画跋》中,也有一条记录反映了这种情况:
不落畦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趋,谓之逸格。其创制风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滥明初。[19]
综上可知,本以“不落畦径”“不入时趋”为本质特征,被文人画用来标榜自身的“逸格”,到了明初已经流于泛滥,而这一趋势可谓直指“逸格”之本质特征的反面。面对这一形势,文人画家们已不得不作出回应,寻找新的理论话语来维护文人画的身份与地位。
四、文人画论的应对:对“法”的回归
面对逸格的泛滥,文人画论有一种相对直接的反应,那便是将“逸品”的评定标准严格化,不断把未达标的画家与画作清理出“逸品”的行列,如前文提到过的邓椿,便将石恪、孙太古、贯休、云子等人皆斥为“粗鄙”“无所忌惮”,只承认孙位一人足称逸格。到了明朝,历代以“逸”相轧的画家已不可胜数,而被董其昌承认的逸品,从古至元,只有张志和、卢鸿、米芾、倪瓒四人:
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代唯张志和、卢鸿可无愧色。宋人中米襄阳在蹊径之外,余皆从陶铸而来。元之能者虽多,然禀承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20]
结合“逸格”“逸品”在绘画品第系统中出现及地位上升的过程来看,邓椿、董其昌等人这种“抬高门槛”“清理门户”的论述,其实颇有历史根源:“逸”之概念在与绘画的最高品格结合之前,指的曾是《唐朝名画录》里某个“姑备一格”的品类,既然飞上枝头,获得了最高地位,当然需要自矜自重,接受追捧与建构,将不符合新标准的画家、画作剔除出去——对达标人数的限制,本身也能抬高此类作品的价值,毕竟奇货方称可居。
除了上述反应,文人们还会指斥“伪逸品”的存在,如上文提到的韩拙在其《山水纯全集》中批评某些作品“昧乎格法之大,动作无规,乱推取逸”,以及董其昌指出逸品“恐护短者窜入其中”,故士大夫须“穷工极研,师友造化”等等,就是很好的例子。除此二例之外,方薰在其《山静居画论》中亦称:
诗文有真伪,书画亦有真伪,不可不知。真者必有大作意发之性灵者,伪作多檃栝蹊径,全无内蕴。三品画外,独逸品最易欺人眼目。[8]239
文人画家们批评这些由“乱推”“护短”“欺人眼目”之法吹捧出来的“伪逸品”,除了有心揭示当时乱象之外,实际上也在对支撑这些吹捧的价值判断标准提出质疑:昧乎格法,不看画家在“法”这一维度上的造诣,只看他有没有所谓“逸”的气质,如此缺乏客观标准而相对依赖主观判断的做法,如何使人信服?在这种风气底下,首先,真正能够体现文人画之最高品格的“逸品”与实际上在流俗中打滚的“伪逸品”难以区分,“逸品”的数量也难以控制:由于“逸品”的原始特征就是对“法”的背离与突破,因此,它比那些法度严谨的作品更容易模仿,伪逸品的作者们只需短时间地“檃栝蹊径”,学习一些流行的、以“逸”为名的成法,便能大致获得真逸品之效果,而这些真逸品,其实是画家们通过长时间揣摩法度而后由博返约的创作成果——这可能会造成优汰劣胜的不良影响;其次,原本藐视“画工画”之匠气的文人画,如果没有“法度”的加持,在面对画工们的质疑时,也容易显得没有底气,如董其昌所担心的那样,不足以“关画师之口”。
这种现象,无疑极不利于“逸品”保持它的地位,因此有心人才会接连就此事发声,提倡另一套判定标准,而这套标准的重点考察对象之一,便是画家在法度方面的修为。正是在这一形势的影响下,“逸”的含义才会象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出现对“法”的回归趋势。
五、“双遮”式的表述策略
然而,法度本身也需要警惕。一旦矫枉过正,过分拘泥于法度,文人画便有流于谨细刻画、走上回头路的危险,又将重新落入画匠画的窠臼中。因此,文人画家们在“逸”之流俗与“法”之束缚的双重夹击之下,逐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微妙的表达方式:一种双重否定式的表述,也可以称作“双遮”式表述。
双遮,也叫双遣、双非,本来是佛家的一套思维和修持方法,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法。虽然这套方法在佛家思想里被运用得比较复杂,需要层层叠加、不断推导,但它的基本原理相对简单:“遮”是阻断、阻碍,“双遮”,实际就是对对立的双方同时加以否定。[21]清代的画论在讨论“逸”时,便常常用到这种表述,如唐岱在其《绘事发微》的《游览》篇中写道:“逸品者亦须多游。寓目最多,用笔反少,取其幽僻境界,意象浓粹者,间一寓之于画,心溯手追,熟后自臻化境。不羁不离之中,别有一种风姿。”[22]又如恽寿平在《南田画跋》中引其伯父香山翁恽向之语曰:“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有,所以为逸。”[19]17方薰在其《山静居画论》中也曾列举穆倩、松圆、衣白、朗倩、端伯、半千、大风、年少、尺木等数位他认为可入逸品的画家,并总结他们的特点道:“不为法缚,不为法脱,教外别传,当为逸品。”[23]很明显,上述这些“不羁不离”“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有”“不为法缚,不为法脱”之类的说法,都运用了“双遮”式的评判技巧。
若只考虑“双遮”最基本的含义,不讨论它在佛家思想里的复杂推衍与终极指向,那么在儒道两家的著作里,也存在类似的表达。苏辙在《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中肯定黄休复首推逸格时,对被归入逸格的孙位有这样一句描述:
而孙氏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从心不逾矩之妙。[13]
“从心不逾矩”,用的是《论语》里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4]的讲法,它是孔子七十岁时才能达到的人生最高境界。“不逾矩”,是对规矩的遵守,而“从心所欲”,却是对规矩的否定,如此,“从心不逾矩”,便是一个相当接近“双遮”的表述,而这种“双遮”指向的美学境界,是儒家“中和”“中庸”的境界。苏辙借孔子对人生最高境界的描述来讲绘画的最高品格,可谓用典精当。
道家对“双遮”式表述的运用,则与佛家又多了一个相通之处:它们都指向本体的不可言说性。[21]11在佛教里,“双遮”法是三论宗用来讲真谛的,这一方法其实意在强调真谛的不可言说性。[25]中晚唐以来对士大夫群体影响渐深的禅宗,更是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21]11也认为真谛不可言说,方薰在上文中对逸品的讨论,就直接用了“教外别传”这个说法。至于道家,《道德经》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6]音者,声也;象者,形也,“大音”、“大象”,乃是最高的、本体层面的音和象,老子却否定了它们的“有音”和“有形”,这种语言层面上的悖谬,其实也指向了本体的不可言说,即所谓“道隐无名”。[26]明人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对逸品的讨论,便恰好利用了类似的“双遮”式表述,层层递进地指出了“逸”这一概念难以言说的特性:
逸虽近于奇,而实非有意为奇;虽不离乎韵,而更有迈于韵。其笔墨之正行忽止,其丘壑之如常少异,令观者冷然别有意会,悠然自动欣赏,此固从来作者都想慕之而不可得入手,信难言哉。[27]
恽寿平在《南田画跋》中另有一条对“逸品”的讨论,也跟《道德经》的上述表述方式接近: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笔中之笔,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19]52
天外哪里还有天?水中哪里还有水?笔中哪里还有笔?墨外哪里还有墨?这明显也是一种利用了语言层面上之悖谬的表述策略。上文曾分析过,“逸”之所以成为绘画的最高品格,其原因之一便是它与“自然”有阐释上的相通性。“自然”是道家哲学里指向本体的一个表述,而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境界,又往往会向这一不可言说的本体靠拢。因此,恽寿平对“逸品”的描述,也恰好与“逸”作为文人画最高境界的特征相契合。
总之,自唐朝以来,儒、道、佛三家之思想本就渐趋交织、融合,常常共同构成一般中国文人的精神底色,而由“双遮”式表述凸显出来的“不可言说”之特性,不仅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相适应,事实上也与今人常说的、艺术审美的直觉式思维方法遥通款曲。因此,文人们会用“双遮”式的表述来阐释与建构“逸”这一概念,可以说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六、余论
画论对“逸”的阐释与建构走到清朝,其实又陷入了一个很微妙的境地:一方面,此类理论确实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对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艺术的本体都有一些精微的论述;然而另一方面,这种玄而又玄的表达方式未免显得有些难以捉摸,若凭借这些理论话语作出评断,不仅不一定能服众,也很难说解决了逸品容易“欺人耳目”、有“护短者窜入其中”等问题。因此,评论家们往往还会提出一些与绘画不那么直接相关的辅助考察对象,以此作为他们评定“逸格”的佐证。是不是读书多、有没有书卷气,或者说是不是轩冕才贤、衣冠贵胄,这类看似不宜左右艺术价值判断的知识优势或身份优势,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影响了评论家的最终评断。毕竟,在直接与艺术本身相关的评判标准渐趋微妙的情况下,他们也需要一个庶可服众的、相对实在的证据。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复杂的现象,然恐行文芜杂,此处不再详论,仅举一例于此,乃董其昌与《卧游册题词》中推崇其好友李长蘅之语:
余友孝廉李长蘅,故自清士承先世之业,与两兄太史、黄门之家声,广交好客,宾至如归,其点缀一石一水,直寄兴耳。即唐解元自称爱写青山卖者,长蘅了不屑也,以故无赞毁于胸中,如意自在,甚恬甚旷,与画家临摹伎俩日刻相远耳。又况其公车之业,号为专门,诗骚子史,博通淹贯,一一发之于画,宁不超超逸品耶![7]258
总之,有导向性的、催生潮流的审美价值判断,一定是发生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的,它与各方面的力量相牵扯,受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影响,其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阐释与建构:它从来就不仅仅关乎“美”。然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每个个体来说,艺术审美体验与价值判断又往往是件冷暖自知的事。这两者相互角力、影响、渗透,古往今来,不知激起了多少妙论,亦不知聚讼几何,而故纸堆中之波涌,又或可借以反观今日之现象,供有心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