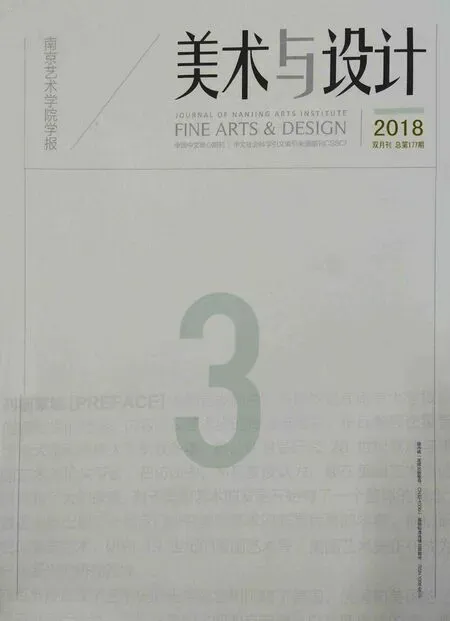图像与时间
刘 琼 李 婷(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评论家们认为,当代艺术主要由观念驱动,而驱动当代艺术的观念本身却是一些比较终极、相对基础的范畴,比如身体、时间、场所等。这种对当代艺术创造的先锋性的判断,与其所采用的范畴的基础性之间形成明显对照。事实上,当代艺术不再像过去时代的艺术更直接地由技巧、技术的改进所支持。虽说观念的改变一直都是艺术发展的深层动因,但过去时代深刻影响一个时代艺术创造的观念更新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艺术创造,不像当代艺术,观念本身成为艺术的工具。而且,过去时代影响艺术创造的观念更新也不像驱动当代艺术的观念那样呈多元形态,而是一个时代区别于此前时代的主导的、有时可能是唯一的思想标识。比如文艺复兴区别于中世纪的人本主义立场与旨趣。不过,与这种观念多元相吻合的应该正是观念的终极和基础属性。换种说法,当代艺术的内驱力源于对传统的怀疑和挑战,那些传统就是终极范畴在过往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和艺术相对稳定持久的标准,然而在当下,这些标准动摇了。
要全面考察驱动当代艺术的各种观念并不容易,本文因此选取单一“时间”观念,从一个传统上相对视觉艺术而言最具张力的角度,结合西方思想史的时间观念,尤其是柏拉图-基督教式的时间观念,①在时间的本质问题上,西方思想区别了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两种立场。实在论者坚持时间是一种客观、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独立于人心对时间的实际感知。实在论者的著名人物包括柏拉图、牛顿、爱恩斯坦等。([美]沙伦·M.凯、保罗·汤姆森:《奥古斯丁》,周伟驰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1页。)由于实在论立场的时间观念更贴近我们经验的时间感觉,因而本文选取实在论立场的时间观念作为讨论视觉艺术时间表达的理论参照。检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视觉艺术对时间的不同表达,分析其不同表达的思想文化动因及其价值意向,尝试勾勒其表达时间的不同模式。在此,“时间”是讨论具体视觉艺术作品的角度,而所有的讨论又有一条纵向的历史脉络。也就是说,既有一个历时时间的参照,又以时间表达本身作为讨论的焦点。这样的讨论应该本身就比较有趣,也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艺术,甚至当代文化。②学界对视觉艺术形式的研究比较多见,但对视觉艺术时间模式还缺少关注,尚未见到专门讨论的论著。
一
众所周知,视觉艺术的出现当然不能说是以表现时间为契机的。而且纵观西方视觉艺术史,现代艺术之前的相当长历史时期中视觉艺术也基本不以表现时间为主要目的,绘画等诉诸观者的视觉和心灵,以表现美,传达情和意,或者其他更高目的。比如,一个经典的例子,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The Virgin in the Meadow)(1505-1506)。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对此的分析指出,这幅画事实上是“古典的”作品,拉斐尔反复尝试,追求的是人物之间的合适的平衡和使整个画面达到极端和谐境地的合适关系。在速写簿中他反复探索如何最好地平衡圣母、圣婴和小圣约翰这三个人物。在定稿中,他确实把这幅画画得合适了,人、物各就其位。而且,拉斐尔不断努力最终获得的姿态与和谐显得自然天成,毫不牵强,几乎未能引起观者的重视。正是这种巧夺天工的表现,使圣母的美和孩子们的可爱极富感染力。也正是这种自然天成的境界,曾是视觉艺术表现美的理想境界。[1]34-35在这幅画作中,几近完美的和谐显得单纯而平静,让观者忘记了时间,一种难以言喻的永恒感流溢在画面情景中,仿佛人、物从创世以来就一直那样。
换种说法,古典的作品大多并不在意时间对视觉传达的影响,可能正是这种忽视和遗忘,给予古典艺术一种深沉宁静的永恒感,一抹超越时间的神圣光晕。
当然最能传达这种静穆的永恒感的艺术是古典艺术中的中世纪艺术。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和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的”作品不同,中世纪艺术因为本来就追求世外之美,其表现的时空本来就与尘世的时空有别,所意向的也本来就是超脱凡俗的永恒和神圣,因而从世俗时间的角度,中世纪艺术的时间表达也是缺席的。观者无视作品的时间,也忘记此在的时间,自然也不以世俗空间的观念衡量作品呈现的场所。这类作品让观者因忘记时间而直抵永恒。而且很大程度上,忘记时间一直都是世俗之人体会永恒的便捷途径,这种途径也能有效地排除世俗空间要素的干扰。
20世纪横跨哲学与神学领域的杰出思想家蒂里希(Paul Tillich)的理论比较好地诠释了这种艺术表现的永恒。在《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中蒂里希有专章分析时间与空间问题。他认为,与空间相关联的神,也就是基督教所谓异教神,比如古希腊诸神,其神性是褊狭的,不具有普世性,此种神性往往表现为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并带有神秘主义等属性,其悲剧性的境遇难以克服。而与时间关联的神——基督教的上帝——能够破除此种狭隘,成为唯一的普世的神。因而与时间相关联的神其神性自呈为永恒。①Paul Tillich , Theology of Culture , London , Oxford an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9 , pp.30-39. 另参阅保罗·蒂里希:《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蒂里希对时间与空间问题的分析是在柏拉图式时间观念的序列之中,是对柏拉图-基督教式时间观念的某种当下反思和阐释。在此,蒂里希强调的是普世的时间对有限空间的超越属性,如果艺术最终能够超越空间的限度的阻隔,它就能具有穿越、贯通时间的永恒精神,自带沉静、祥瑞的神圣光晕。在本节讨论的艺术样式中,作品以忘记时间、专注于永恒一刻的方式排除空间干扰,获得天国或近似天国的不朽属性。换句话说,古典艺术以遗忘时间的方式表现超越时间的维度,让观者浸沐在作品散发的神圣光泽里。
二
不过随着文艺复兴重新开启的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视觉艺术也变得对世俗时间敏感起来。对时间的敏感由重新关注现世而来,人们把目光从基督教的那个完美光辉、永不腐朽的来世转向现世,个体存在的限度变得醒目而突兀,人们不得不关注并思考时间之于个体存在的种种。自此,视觉艺术重新开始并加强了对时间及其表达的探索。从静态形式的艺术以表现时间(Representing Time)的方式,②本文在两个层面使用“表现”一词:第一个层面比较狭隘,特指静态形式的艺术对时间的象征性、暗示性传达;第二个层面是一种宽泛的用法,也是比较一般的用法,泛指所有视觉艺术对时间的表达。也就是以象征的方式呈现的时间,到艺术家们主动地以运动和变化的形式在艺术作品中赋予时间以具体形式(Embodying Time),[2]126视觉艺术对时间的思考和表达有了显著改变。
在古典艺术中,甚至古希腊罗马的某些作品,当艺术家自觉意识到时间并试图刻画时间的影响时,其方式也大多是象征的方式,是表现时间的方式占据主导。这当然因为古典的视觉艺术大都是静态形式的艺术。由于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常常依赖于在空间中的运动,对时间的测量和表现要通过变化来实现,静态形式的艺术因此并不直接与呈现时间相关。事实上,艺术作品若以表现时间的方式呈现时间,画面本身不会包含任何物理意义上的动态元素,因此只能暗示时间的存在及其影响。在古典美学理论中,莱辛的《拉奥孔》提出的视觉艺术呈现“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的主张,使静止空间能够获得相对强烈的运动感和时间在场的印象。[3]83这应该是视觉艺术较早的对表现时间的最自觉的策略。无论视觉艺术是否想表现叙事,这样的策略都是极其可取的表现时间的方式。并且由于画面自呈的动与静的对照和对抗,这类作品往往极具视觉冲击力。比如《拉奥孔》群像。它表现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恐怖场面:两条巨蛇从海里游出把特洛伊城祭司和他的两个无辜的儿子紧紧地缠住,群像用躯干和手臂的肌肉来表现绝望挣扎中的努力与徒劳,祭司脸上扭曲的痛苦表情,两个少年枉然扭动的身体,以及把整个骚乱与动作凝结成一组永恒群像的手法,表现的正是“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1]110-111正在经历的苦难和无助预示即将到来的死亡和悲怆,使这组雕像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效果都格外令人震撼。
然而即使在这类暗示了时间的作品中,时间也并不是艺术的主题,甚至与作品的主题无直接关系,虽然作品选取在动态时刻让运动戛然而止,继而得到一种静止时间的印象。因为在这里,时间与情感、情绪、情意、情念连接在一起,表现某个特定时刻的场景是为了更强烈地触动观者的情绪,某种恐怖和绝望的情绪。而人们也能在这种情感、情绪之流浸润心田的过程中感知时间缓慢而沉重的节奏,预知时间流逝的可怕后果,领悟时间表现中的强烈情感特质。
三
在静态艺术中表现时间最显著的改变或者“进步”发生在工业革命最辉煌的时代,从艺术史的角度,大约在19世纪中叶。那时,法国绘画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孕育了后来被誉为“现代”艺术第一次大运动的印象派运动,这一运动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艺术的基石,同时也预示着时间表达新样式的出现。[4]66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革命的突出成就促成了人们有关时间概念的变化,这一变化当然地引发了绘画新观念和新技巧,其后果之一就是,艺术家们在静态形式的绘画中直接以运动和速度作为时间表达的重要方面,或者时间本身成为作品主题。比如约瑟夫·透纳(Joseph Turner)的《雨、蒸汽、速度,大西部》(1844)。大西部连接泰晤士河谷与德凡郡。19世纪40年代初,这条铁路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左右,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速度。透纳喜欢火车和速度。这幅画除了左侧隐约可辨的河、桥和小船外,最突出的就是迎面驶来的那辆蒸汽机车,由于整幅画的色调单纯而朦胧、构图也比较简洁,显得火车好似从天际直冲而来,赋予整个画面充沛的动感,成为极具时间感的静态绘画。[5]41这是较早将速度作为新时代象征加以表现的例子。在此,时间借助对速度的表达,与“进步”一起成了绘画的主题。很大程度上,19世纪末印象派画家在绘画中研究和表现瞬息万变的光线对颜色以及形态的短暂影响,也是静态艺术表现动感时间的实例。比如莫奈(Claude Monet)的鲁昂大教堂(Rouen Cathedral)正面的系列作品《鲁昂教堂三景》(1892-1894),表现一天中不同时间,光线条件的不断改变对建筑及其风景的影响。①[意大利]翁贝托·艾科编著《美的历史》,彭淮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莫奈这一作品,与古老的叙事性视觉艺术的策略——多幕(multi-episodic)模式——部分相似,但莫奈并不叙事,他表现时间本身。多幕模式在当下视觉艺术中也有采用,比如连环画与漫画书等。时间、光线因变化相关联,由建筑颜色和形态的不同(尤其是颜色较之形态更明显的不同)示意的光线变化,显示了时间的在场和流逝。
前面提到,这种改变由时间概念的变化引起。在那个时代,由于科技和工业进步,尤其是速度的极大提高,人们的时间意识空前觉醒,而且由于对速度的把握,显得也能够把握时间。时间效率极大提高,进而呈现为一种世俗意义上的进步,很多人也的确将速度颂扬为进步。据此,在视觉艺术中直接呈现变化与速度就可视为静态形式的艺术表现时间的一种进步。
同一时期与这种观念更新相呼应的其他表达时间的尝试也取得了不俗成就。比如20世纪初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对表达时间的不同方法的探索。立体主义者们把一个对象从不同角度、不同时间观察到的不同景象,结合并融入到同一静态构图中,这显然是莫奈工作的下一步。这样,绘画就能表现更为复杂、更为强烈,同时也显得陌生的时间感觉。例如被认为是立体主义绘画的最初楷模的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阿维尼翁少女》(1907),据说画的是一个妓院的情景,画中人似乎是由女性身体上的许多小平面组成,它们是不同时间从不同方向观察所得,表示人人都知道应该在那里,但又很难一眼辨认出来的东西。……画家首先把人物的形象打碎,然后客观冷漠地把破碎的小平面重新组装起来,打碎、组装,画面曲折地传达出时间过程,并由此得到一种粗野的、让人吃惊的艺术效果。[6]6-7
如果说印象派和立体主义对时间表达还比较隐晦间接的话,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就直接得多。未来派对速度的膜拜,除了绘画作品的直观表达外,更有诉诸理论的集中而明确的表述,比如马利内提(Filippo Marinetti)在《新宗教:速度的道德》(1916)中宣称:“如果祈祷意指与神沟通,则高速旅行就是祈祷。轮子与车道神圣。我们要跪在车道上,向神圣的速度祷告。我们要在环动罗盘的旋转速度面前下跪:每分钟两万转,人类达到的最大速度。我们一定要从星星偷取它们神奇不可思议的速度的秘密。……我们的圣徒,是那些以平均每秒4万2千米速度穿透我们的大气的无数微粒子。我们的圣徒是速度每秒3×108米的光波与电磁波。在汽车里高速飞驰的兴奋,就是觉得自己与上帝合一的喜悦。车手就是这个宗教的第一批信徒。(接下来马上就是)摧毁房屋和城市,改建为汽车和飞机的集合场。……”在这段引文里,表述者因为对速度的痴迷与虔诚,激动得似乎语无伦次,几乎有些癫狂,自顾自痴人呓语着。[7]396
与此不同,超现实主义者们选择了相反的路径,他们尝试通过放慢时间,或者让时间停止(静止钟表的意象),去表现恒变时间与恒变文化的徒劳无益;或者,采用将各种元素出乎意料地并置的典型策略表征离奇的时间等。比如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名作《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31)。画中的软面钟起源于一句双关语:La montre moll(“伸出您的舌头”),但也有软面钟的意思。这样钟就画得软塌塌的像舌头了。达利说,这些东西都喜欢受虐待,期待着一个可怕的结局。它们慵懒地悬等在沙滩上,深知那刻板行进的时间之鲨必将吞噬掉它们全部。这幅画的时间表达一定是有寓意的。整个画面色调还算明澈,但画面景观却像精神病患者的幻觉,神秘诡谲,画中软面钟的指针又基本失灵停摆。[6]44-45怪异的场景与停摆的指针:恒变的时间也期待着永恒,也几乎等于静止的永恒,或者说恒变的时间终于也相当于时间的缺席。这里呈现的时间主题深邃而费解,极具前瞻性:无论恒变还是恒止,都同样令人疑惑,让人难以确定。在这一点上人们的时间感又似乎相通。
此类以静态形式的艺术表现时间的诸策略不同于此前选取“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对时间的表现。后者对时间的表现尽管也基于动与静的对比,但作品以极具意涵性的画面暗示着时间,并未在画作中直接指涉时间。在相当程度上,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还是为了最大可能地丰富画作的内容,传达更厚重浓烈的情感,强化观者的情绪感受。而印象派、未来派等表现时间的画作,其主题大致就是时间,意图使人们觉悟到与此前时代不一样的时间感受及其文化内涵。在此动-静对立的两面中,“动”的方面已经有了比“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更明确的彰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艺术史的角度,静态形式的艺术表现时间的方法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艺术创作中运用较多,但在当下仍然有以表现时间的方法创作“时间艺术”(time arts)的作品,只是相对动态形式的艺术的创作要少。而且,除了上面讨论的各历史时段主要的表现时间的方式外,也还有其他的对表达时间的方法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前面注释中提到的多幕模式的叙事性视觉艺术策略等。不过介于本文的意图是初探视觉艺术的时间表达,就不展开对更庞杂细微的创作方法的分析与归纳了。
四
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技术进步直接促成时间观念的改变,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变化在视觉艺术领域引起的回应。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并不会停止,它在继续深入,延伸向观念层面更具革命性的转变,这些革命性的转变又反过来作用于技术与艺术,它们彼此影响相互激发,促使视觉艺术表达时间的方式与此前所有表现方式都有了更大不同。具体说来,随科技进步而来的摄影术、连续静止摄影和电影方面的实验和成功,人们对时间的理解更明确、更理性地与空间变化联系起来,这成为20世纪初关于时间的最新观念。这种新观念见之于物理学、心理学、哲学以及文学创作等广泛领域。比如,物理学领域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狭义相对论(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1905)认为:“人不能假定他对‘现在’的主观感受适用于宇宙的任何部分。原因在于,爱因斯坦强调,‘每个参照系……都有自身独特的时间;除非已经知道相关时间的陈述所对应的参照物,否则对每一事件的时间陈述其意义都无法确定。’”①Lincoln Barnett ,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 rev. ed. , New York : Bantam Books , 1957 , p53. 爱恩斯坦的时间观念仍然在柏拉图-基督教式时间观念的序列之中。前面注释已经指出,它们在时间的本质问题上采取了相同的实在论立场。区别在于,在柏拉图(甚至蒂里希)那里时间是绝对的(任何地方都一样),是用天体的运动来衡量的。而在爱恩斯坦那里,时间是相对于感知者的,其衡量是地方性的。([美]沙伦·M.凯、保罗·汤姆森:《奥古斯丁》,周伟驰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1页。)很显然,爱恩斯坦的时间观包含了空间要素,换句话说,与柏拉图-基督教式时间观相比较,爱恩斯坦的时间观更具有世俗属性。而两者的区别,某种程度上就是神圣与世俗的差别。这里,时间是与参照物、场所、空间相关而论的。如此,对时间流逝的最直观感受就是随时间流逝的空间场所变换,用场所的不同明示时间的变化,进而,通过加快空间改变的节奏就可以表现时间变化的速度,以达至控制时间的效果。这样的想法,与移动的影像技术(电影摄影术)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与时间相关的媒介这样的后果,直接相关。由此,以时间的具体化表现时间主题的艺术形式成为时代潮流之一,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流行文化领域。而赋予时间以具体形式的艺术就代替静态形式的艺术成为艺术表达时间主题的主导样式。
据相关研究,赋予时间以具体形式大致有三种样式。第一种是本身包含运动要素的艺术作品,比如动态艺术和行为艺术。第二种是采用能营造出运动错觉的媒介的作品。第三种被不太严格地命名为过程艺术作品。[2]134在所有这些赋具体形式予时间的艺术样式中,第二种采用能营造出运动错觉的媒介的作品,由于也被流行文化所钟爱,还由于这类展示动态图像的媒介其时间结构较之另外两种样式的作品更容易操控,这些因素共同促成移动影像作品的未来趋势较之其他两类更明确。不过在此,我们更多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关注与艺术传统衔接的、作为艺术手段的移动影像媒介,特别关注使用此类媒介,并表达和时间相关的主题的作品。
在录像艺术家们采用移动影像媒介探索视觉艺术中的时间表达的尝试中,他们常常借助移动影像媒介相关的高科技手段重构视觉艺术的时间结构,通过对时间的速度、节奏,时间的长度、方向等进行调整和操控,获得修改时间、破坏时间、甚至消解时间等艺术效果。具体而言,他们首先以此作为创造视觉叙事的手段。比如,以录像视频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们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率先采用策略——闪回、跳跃剪辑(jump cut)、淡入淡出、加速镜头等——为基础,此后,结合多通路投影、高级尖端设备以及编辑软件,开始运用声像同步之类的技术,可以得到放慢运动速度,回放、打破和增加连续镜头等更多操控时间的工具和手段。当然,还有更多其他正在实践和发展中的策略。这一系列的工具和策略达成了动态艺术叙事的多种可能。比如,玛丽·露西尔(Mary Lucier)的荒野(Wilderness)系列。这个作品将三盘内容不同的录像带混合在一起同步放映(画面被彼此交织地投射到七台大型显示屏上),观赏那些同步放映却又对比强烈的图像,观者会有某种时间错乱的不真实感,思绪在不同画面的不同时空之间游移,并由此萌生出对神话时间(荒野意象)与历史时间(现实状况)的重新想象和思考。[2]142-149这样的艺术当然是观念艺术:时间,既是工具又是主题,而且延伸至更远。
不仅如此,艺术家们也用这些媒介及相应技术手段制作非叙事性的关于时间的作品。甚至,以动达至静的效果,以移动影像表现近乎静止的画面,呈现为又一逆转。例如,美国艺术家安德里亚·鲍尔斯(Andrea Bowers)的录像作品《等待》(Waiting)(1999)。录像里一位年轻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双膝跪在冰面上,静静地跪着一动不动,然后突然从冰面上抬起冰凉的手。这段45秒钟的视频被连续循环地播放。观者的实际感受是,一直在等待一个从未开始的故事,而整个画面却几乎毫无变化。这段录像更像一幅画,而非动态的摄像。[2]137艺术家似乎要在一个时间快速飞逝的时代努力恢复已渐被遗忘的“缓慢带来的乐趣”,又或者是想表达如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一样的主题——对西方文化传统既绝望又寄望的难言心境,或者还有其他……。
从观念层面看,这种艺术策略(以及前面论及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策略)及其导致的意义逆转很有深意。首先,以动态达到静态的效果,以这样的艺术直观地说明静与动的连接与转换。而且此间的转换是双向的:静态艺术可以暗示运动和时间,动态艺术也能够获得静态艺术效果。更进一步,从动与静到时间与空间,也能够这样推演:变化的时间能够停滞、静止,静止的空间也可以运动、变化。不仅在艺术作品里,更在日常经验中。由于时-空的这种关联,从逻辑上推知另一种永恒——时空连续中的生成转化之永恒——就是合理的,而且能够将神圣属性赋予这种永恒,像尼采在其哲学中所做的那样。①[德]尼采:《瞧!这个人》,刘崎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尼采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基本概念“永远轮回”(“生存转化”)是人类所曾获得的最高肯定方式,是信仰这个尘世肉体的不朽,是他所建构的神圣。事实上,从更贴近人的立场,生成转化之永恒才是“永恒”更确实的内涵,生存转换之神圣也才是确实属人的神圣。这似乎回到了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万物皆变,无物常驻,如同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揭示的存在的永恒变化这一基点。②转引自北京大学西方哲学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事实上,尼采哲学就深受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影响。而柏拉图-基督教式线性时间,也并不更显优越。
如果说古典艺术的静穆(时间被忽视或者缺席)是某种永恒,那么相对于当下各种赋予时间具体形式的艺术利用无数的空间场景变化所传达的,时间在场的“变化之永恒”而言,只能算是某种虚假的永恒,是我们生命中无可奈何的那一面的理想性表达。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艺术最能代表这种静止的永恒。蒂里希在《文化神学》中讨论时间与空间问题时,除了指出与时间关联的神的普世属性外,还指出线性时间的一维线性方向。他认为,基督教通过预言性的神示赋予线性时间一种确定的方向,从而在人的历史中拂出混乱和无序,使其朝向明确的、包含希望的、进步的方向。[8]35-39但问题在于,我们时代永恒的变化之系统,却并不像基督教的线性时间所预言的那样有一个明晰确定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无论艺术对动-静、时间-空间转换的探索,还是对变化之永恒的揭示,基督教的一维线性时间观都不能证明具有充分的阐释力。而且在人的历史中,也并没有和希望的方向一致的方向,空间的狭隘性同样也没有随历史进程被克服。尽管当下我们已经有了不同的、多样的时间观,③由于科技进步,当下时间观的多样化不可避免。除了古老的时间观比如线性时间外,还有同步时间、甚至一些另类时间观,比如科幻作品中构想出的平行宇宙等。但上述困境依旧还是困境。说到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时空连续体,人的时间感受从未真正与空间分割。
从观念层面重回艺术创作,视觉艺术的时间模式,从静态到宽泛的动态艺术,其恒变求新的路径,应该也不能被确然地理解为线性进步。
五
自1980年代以来,催生动态图像媒介的科技力量带来各种能提供即时信息(手机信息、有线电视新闻节目等)的新兴网络技术,对当下的时空观正在施加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人们可能正在丧失将事件置于任何历史时空中去的能力,或者说,正在丧失参照物、丧失与空间相关联的时间感,丧失文化的记忆、思考的能力。这正是艺术家们所描绘的,在冲突或无序状态中共存的碎片化的时间。因为碎片化时间的断裂形态使得凭借古老的因果范畴去理解世界,进而建构意义变得困难。文化理论家们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比如安德里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就指出:“数据库和图像磁道里储存的记忆越多,我们的文化就越不愿也无法去铭记。”[9]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现在人们离开手机就会十分焦虑,好像没有了手机就没有了生活本身,所有与外界的联系因为并不基于真实的记忆而只能处于搁置状态。在此情形下,运动、速度,曾经被颂扬为历史性“进步”的科技,又以一种悖谬的样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一种更加深刻的逆转——通过引入空间以有效操控时间,对时间的操控又逆转为(与时间关联的)空间要素再次消隐——正在发生。具体说来,操控时间的直接后果是被时间操控;继而是另一方式的丧失时间,曾经极其强烈的时空感受变得相对奢侈,那种充满诗意和力量的时空经验已经渐行渐远,一同远去的还有沉重实在的历史感觉;最后,甚至可能丧失基于记忆的思考和创造能力,尤其在精神领域,时间及其所孕育的财富,在人们的生存中变得难以为继。
事实上,虽然理性与科技的力量带来速度以及物质进步,但精神财富必然基于整体性存在的人的创建,而这样的人总是时空中的有限存在,他的创造基于时间也受制于时间。人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并为创造与物质进步相配称的精神财富付出与空间关联的具体而切实的时间。换言之,对艺术和文化抱有的乐观进步观念至少需要一个停顿,去检视是否已然有一个与物质进步相应的艺术和文化进步。从精神层面看,柏拉图-基督教式的线性时间观并不像所允诺的那样具有普适性。实然的历史,是与空间纠缠的历史。考虑到蒂里希在分析与空间关联的神和神性时言及的限度[8]31-35,这样的人类历史当然很难超越空间所设定的限度,也就难以以物质进步的节奏前行。我们已经看到历史中不断发生的时空纠缠。这些纠缠当然不能以单一的时间观念去统摄。比如,当下由观念引导的艺术创造很多时候表现的是对传统观念的怀疑和颠覆。这与进步的信念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全吻合。说到底,与建构相较,解构总是相对容易的,但却更少进步属性。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角度看,习惯于传统艺术和流行文化的观者,面对由观念变化所引导的艺术创造,因为缺乏观念的自觉,往往很难欣赏和领会作品的含义,甚至比较排斥这类作品,虽然也不能排除这类创作中缺乏真正创新的作品带给观者的困扰。毕竟观念的自觉并非直观所得。而当代艺术的这种尴尬,也旁证了单一时间观念的局限。
需要格外警惕和防范的,正是当下的文化记忆危机,艺术家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在探索新的时间策略时,也尝试重访和纪念过去的视觉艺术实验。这些实验某种程度上对不断颠覆传统形成补充。也就是说,他们创作纪念过去的艺术作品对抗当下的文化失忆。当然,当下与历史相关的艺术创作已经不可能更多采用传统样式和古典手法,即使纪念过去,也更多是以某种当下策略进行创作。例如,公共艺术的趋势之一就是制作反纪念建筑(antimonuments),这类反纪念建筑解构公共纪念碑的传统形式,或者纪念令人意外的事件和回忆。比如,美国雕塑家克里斯·伯顿(Chris Burden)创作的《另类越战纪念碑》(Other Vietnam Memorial)(1991)。与此前由林璎(Maya Lin)设计,落成于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1982)的主旨——纪念越战阵亡将士不同,《另类越战纪念碑》力求凸显另一种充满思想挑战的全新视野,以象征性的方式为死于越战的三百万越南人命名,纪念曾经的敌方的亡魂。[10]这也是为了记住,为了强化历史感,但记住的方式又是借助表现对传统观念的反动。
综上可以看出,视觉艺术对时间的探索从静态艺术以表现时间的方式即象征方式对时间的暗示,到动态形式的艺术赋予时间具体形式(现在也有艺术家尝试将两种方式结合在同一作品中),这样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其呈现时间的具体模式从静态艺术“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到直接表现运动和速度的多样尝试,然后是宽泛的动态艺术多种赋形时间的方式,尤其是采用能营造出运动错觉的媒介的作品。视觉艺术对时间的自觉和呈现看起来确实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不过也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经验时间的线性展开并不能保证视觉艺术以及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事实上,就算视觉艺术可以尝试表现纯粹时间,却根本不能让空间或有形彻底消隐。这不能消隐的空间,对于视觉艺术而言是比时间要素更基本的要素(画面本身),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说法,就是人类难以克服的有限性,是现世欲望,是人的“原罪”在文化中的保留。既是不能消隐,就是存在的基底,是文化的载体,是克服当下文化失忆的契机之一。也由于此,艺术家们常常有意无意地不断回想过去,回望历史,恢复或者重新理解、重建历史,以寻找独特的参照,为时间主导的艺术重新置入与空间场所相粘连的生存意蕴,更好地形塑艺术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