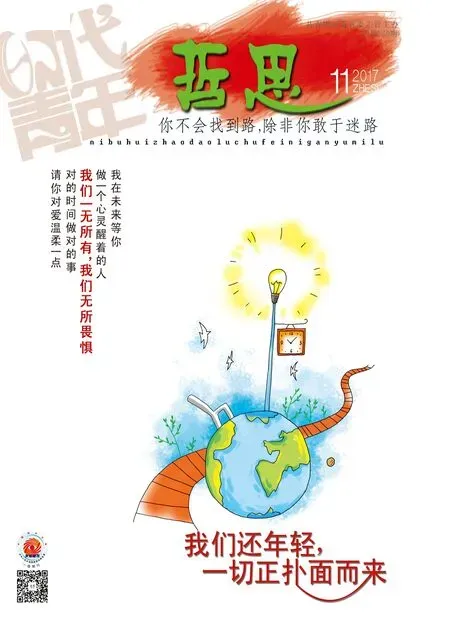最后一份温暖
◎ 肥 肥


奶奶和爷爷很不一样。爷爷总是盘腿跷脚坐在木头长凳上,竹扇一挥,旱烟一抖,全家都要庄严目视。而奶奶,瘦小干瘪,留灰白间杂的短发,穿着潮湿的南方地区常见的塑胶凉鞋。她的身躯是混沌发灰的,在这样的身躯上看不出年轻时在青藏高原上种苹果、挑水、砍柴的力量线索。
她不爱说话,走路无声,家里的物品替她说着话:“滋滋滋”的油锅声、“哆哆哆”的切菜声、“嚓嚓嚓”的扫地声、“叮咚叮咚”的碗筷声……这些是她能创造的最有活力的声音。一双眼睛,是全身上下最灵活的舌头,诉说着她说不出的话。看到她的眼睛的时候,才觉得她是真实的存在。这是我对奶奶单薄的记忆中,关不上的两盏灯。
我跟爸妈住在广东,爷爷奶奶住在广西。小时候爸妈经常上夜班,奶奶过来与我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在大城市里显得更加沉默灰霾,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甚至连我也没记住她当年的模样。她的文化水平很低,面对我,谈不上教育,只能每天给我做饭。广西有一种食物叫粉利,是一种用米做成的类似年糕的东西,可以蒸熟了蘸糖吃,也可以切片切块炒着吃,奶奶来的时候带了很多。她将粉利切成一小条一小条,大火入锅,再放入芹菜和自己腌制的萝卜干,佐以老抽提色,炒出来的粉利是浓郁的焦黄色。她自己的那一碗,通常是全素的,给我的那一碗,通常是满满肉丝的。
年幼的我哪里能知道,奶奶是如何领着微薄的退休金,捉襟见肘地过着生命倒计时的日子,又能变戏法一样让每一顿饭都有鱼肉。她像是厨房阴暗角落里的一块砧板,酝酿着可口菜肴的雏形,几十年哺育着孩子们,每一道伤痕在岁月里模糊成一圈圈没有棱角的轮廓,像树干上的年轮,万古长空,静默无声。
后来奶奶回广西了,我一直在广东生活,每年见面大概也就只有春节那两三天。回去的时候,奶奶会杀一只鸡,蒸一条鱼,炒一盘足料的粉利,拾掇一桌丰盛的饭菜。餐桌不大,人一多就不够坐,默默地端起碗走到客厅独自进食的总是奶奶,在大年初一的团圆夜。
初中时,爷爷病逝,我再一次回到广西那个爷爷奶奶住了半辈子的小县城。爷爷的离世在本来就灰涩的奶奶身上铺了一层更加昏暗的蒙板,她越发像是一道带着一点儿生命体征的影子。
那天从公墓祭拜回来,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走了。县城夜来得早,静得深沉,我坐在一旁有些发怵。奶奶灰色的衣物换成了黑色,她在孩子们间的夹缝中穿行而过,低着头,暗着脸,走进了厨房。厨房里细细碎碎地响起了一些切菜下锅翻炒的声音,她的影子在昏暗的抽拉式黄灯下显得佝偻矮小,可是每一声切菜和翻炒的声响都铿锵有力。少顷,她端着一碗盛满肉丝、萝卜干和芹菜梗的炒粉利出来,一双枯朽斑驳的手把碗放到了我的左手,把筷子塞进了我的右手,说:“一天没怎么吃了。”
那个小小的碗发着焦香的气味,向上飘散的热气蒸腾在我的面颊上。肉丝炒粉利这一道再日常不过的食物,在死亡降临的日子里仍然被奶奶做出了过年的味道,在寒冷里显露出不容置疑的温暖,填充了我身体里一个空荡荡冷冰冰的位置。
第二天临走前,奶奶给我装了一袋子粉利和一块砧板,我接过去,然后一双颤巍巍的手,紧紧地捏住了我。那双黑白明晰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即将离去的我,两行泪落了下来,她随即将泪拭掉:“回去自己学着炒。”
同年,奶奶突发重病,随着爷爷走了。她站在路边目送着我们离开的身影,就是她留在我记忆里最后的模样。这个人终其一生,甘于沉默,但她曾经在全家陷入混乱时,掐灭心底的悲伤,把泪水留给肚子,并端给我一碗最后的粉利。
奶奶走后的十多年间,每年春节我们照样回去,照样吃粉利,照样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一袋。当年与奶奶的粉利一起塞过来的那块砧板,终于在十几年之后正式退休了。这块砧板,尝遍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烟熏火燎,每一刀下去都没有节省一点功夫。它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命运,朴实节制地保持缄默,在每一个看不到头的夜晚,无声无息养育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