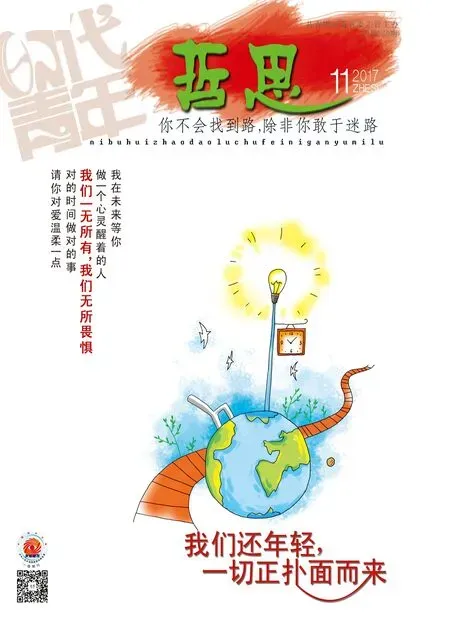所有的告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
◎周文慧

雨下了一整天,滴滴答答,节奏稳如墙上的钟。我在床边收拾着行李,妈推门进来。门开的一刹那,冷风卷动起裤脚,湿气裹携进凉寒,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明天就走了,不去看看你姥姥?”妈说。姥姥家就在街西,与我家相距不过半条街,然而我这次回来,适逢家中变故,并不想见任何人,姥姥这边,也只是叫小妹送些钱去,略表心意。
“不想去。”我抬起头,冲我妈一笑,“姥姥还是那样吗?”
妈说:“现在已经不认识人了,也不会说话了,你不在的时候,我每天晚上过去坐一会儿。”
“她现在还认识你吗?”我问。
“不认识。”
“也不能说话,也不认识你了,那你去了干什么呀?”
“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那里陪陪她呀。”
我有点愣怔,妈站起来,说:“走吧,去看看,再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等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举着灯过去,天已经全黑了。姥姥家是平房,门廊并没有亮灯。小妹叫着“姥爷姥爷”,好一会儿,才听见“吱呀”一声门板响,姥爷开了门。
他们正在吃饭,为了省电,偌大的堂屋只有角落里挂了只灯泡,周遭的光明十分有限。姥姥坐在门后的竹椅上,左手托着一只搪瓷大碗,右手笨拙地拿着筷子,正费力往嘴边送着什么。见我们进来,并不应声,只津津有味地咂摸着嘴,我仔细一看,那筷子一端什么都没有。
小妹走过去,喊:“姥姥,姥姥。”她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便又迅速低下头去。小妹说:“姥姥,姥姥,我大姐来看你啦。”她顺着小妹的指引把目光转向我,脸上慢慢起了笑,一边笑,一边点头,嘴里咿咿呀呀吐着含糊不清的音节,口水溢出嘴角,像个牙牙学语的孩子。
我与姥姥之间,本无深刻的感情。她重男轻女,儿女五个,又是四女一子,她将全部的爱与心意都放在儿子、孙子身上,对于其他女儿、外孙女们,都不甚关心。
幼年我常听妈讲姥姥的故事,讲那些艰难的年月里,四个姐妹劳作不休,却要把那最好的饭菜让给舅舅;讲她早早辍学补贴家用,好不容易做工攒下一点积蓄,却被姥姥悄悄拿去送给舅舅结婚。
时隔多年,妈讲起这些来,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目光平静。而我的记忆里,姥姥从此便形如一个凶悍可恶的女人,重男轻女,暴躁易怒,会站在街口举着把菜刀把邻居骂得鸡飞狗跳,仅仅因为对方拔了她三棵蒜苗。
我实在没想到,回来了,见她,胖胖的身体坐在竹椅里,面目慈祥,笑着看我,“回来啦!”她说。跟我想象的久别重逢实在不同。
姥姥家有很多竹椅,我们回乡定居这些年,记忆中的姥姥,一直是坐在那把竹椅上的。她身材宽阔,坐下去,便如一座山丘,轻易不挪动。逢年过节,我们去看她,开始她还站起来,笑意盈盈,吃饭时胃口也好,满满一大碗饭,不声不响便吃下去大半。吃罢饭,妈带着一众姐妹刷锅洗碗,男人们在院子里簇拥着姥爷喝茶聊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远处,像是在打盹儿,又像是在走神。
要一直走到她面前,摇着她的胳膊,喊“姥姥,姥姥”,她才反应过来,好像突然从梦里惊醒,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人,然后笑了,说:“坐呀,坐。”搬了竹椅放在旁边,她却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问她最近好不好,她说:“好,好。”再多问两句,便不作声了,只是和气地冲着你笑,说:“好,好。”
她不喜欢出门,也没有什么爱好,姥爷喜欢出去打牌,她长日一个人留在家里,洗洗涮涮,完了,就坐在门廊旁的竹椅上,呆呆地看着前方,一坐便是一整天。
漫长的时光里,她一个人活在自己的宇宙中,我们却都不以为意。我们都以为她的安静是源于孤独,而孤独是她这个年纪的人生活的常态。儿女大了,像鸟儿一样一只只飞出去,衔草含泥,筑起了自己的巢穴。而她守在旧日的门廊里,一坐便是春秋四季。
很多年后我常常会想起,那样一个个昼夜轮转的日子,姥姥一个人就那么沉默地坐在时间的转盘中。她孤独吗?她寂寞吗?她的脑海里会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闪回着往事的镜头吗?她的血液里还有热度吗?她的内心还有感情吗?她还能感受到我们对她的爱吗?还是说其实她早已经放弃了这些,只是单纯地在时间的静寂中享受着日复一日的空白和安宁?我不知道。
年少的我一直对她充满好奇。她儿孙众多,我们曾是被边缘化的一支,多年来只有血缘上的联系,甚少情感上的交流。
“姥姥”两个字对我们来说,更像是对长辈的一种尊重,而非发自内心的称呼。我甚至怀疑,出了大门,她未必认得我的身影。
谁也想不到,小妹出生的时候,她突然来我家。
不知道她从哪儿得来的消息,一个人颤颤巍巍地迈着小脚,走了几里的路,挎着个竹筐来了。筐子里放着一小卷花布和半筐红皮鸡蛋,循着镇上的习俗。我们都很惊讶,尤其是妈。
妈叫她:“妈,你来啦。”“我来看看小毛妮儿。”她说。那时她的病还不严重,人也只是不爱说话,她坐在床边,看着小妹的脸,温柔一笑,那个瞬间,像个真正的姥姥一样。
妈妈生完小妹,得了一种怪病,求医问药,怎么都不好。病不大,却很折磨人。家里聚会的时候说起,大家讨论了各种偏方,最终无果。我们说的时候,她就在旁边,一如既往安安静静地坐着,并无言语。
然而当天夜里,姥爷焦急地来到我家,说是姥姥不见了。我们四下寻找,那是夏天,星河低垂,蛙声明亮,找到她的时候,她正一个人跪在村外的荒野上烧纸,口中还念念有词。带她回去,她神情严肃地看着妈妈,说:“我已经问过了,你明天就能好。”
从那以后,姥姥再没出过家门。越来越长的沉默,越来越长的睡眠,越来越笨拙缓慢的举动。有时候她站起来,想要做点什么,然而站起来的那一瞬间,就忘记了,只好摇摇头,再重新坐回去。刚洗了一半的碗就丢在水池子边,她呜呜地哭,要找舅舅。
我们去看她,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看见她一个人坐在竹椅上,嘴里念叨不休,声音很大,脸上因为愤怒涨得通红。我们听了好一会儿,才听清楚她在骂人。而她对面,一个人都没有。
“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怕我们听不懂,又补充了一句,“就是老年痴呆。”
这病,是时间在通往终结的路上早已布好的迷宫,姥姥进去得早,我们发现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了迷宫里的世界,无论我们在外面怎么大声呐喊,她都不出来了。
我忽然想起,十几年前我们全家从遥远的北方回到老家,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见她,我叫她“姥姥”,她回以热情的笑容:“回来啦?”
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文慧呀。”她说:“知道,知道,文慧,我知道,不就是东边大脚的女儿吗?”大家便笑,全以为她外孙女众多,我又多年不见,自然便忘记了。
谁也想不到当时的姥姥,记忆的齿轮已经开始被时间悄悄侵蚀,像久未远航的船,在日复一日潮湿的海风里,慢慢生出了铁锈。后来,她连妈妈也不认识了。冬天里,两个人在厨房烤火,妈妈把她的衣服理好,而她抬起头,眼睛里却是不安与恐惧。
我听见她对妈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来我家?”妈妈说:“我是你女儿,我是你女儿敏敏啊。”
她说:“敏敏是谁?我不认识。”妈妈说:“敏敏是你女儿啊。”
姥姥说:“敏敏是我女儿,那你是谁?”
她们两个人绕来绕去,妈妈一遍一遍回答她,“我是你女儿啊,我是你女儿敏敏啊。”那时候我不懂,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每天吃完饭都要去姥姥家,陪她坐坐,说说话。
直到姥姥不能说话了,嘴里发出的只是含混不清的音节,人也在八十多岁的年纪,重新变成了婴儿。妈妈依然坚持每天吃过晚饭走过去,陪她坐一会儿。
不能说话了,就坐一会儿,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就是坐在那里陪陪她。原来,在渐荒的岁月里,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
“姥姥,我走啦。”我说。
她抬起头来,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滚出大滴的眼泪,嘴里激动地说着什么,然而发出的声音依旧是呜呜咽咽,毫无意义的音节,我突然觉得很难过,姥姥就要以这样难以被人理解的方式走过人生最后的路了。
而妈妈在旁边,温柔地说:“你看,姥姥在和你说再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