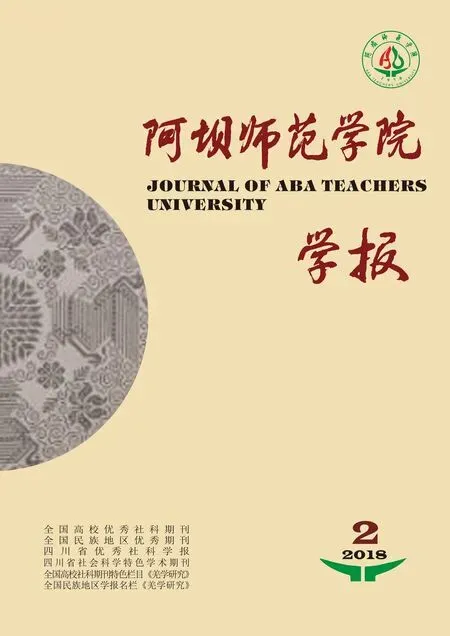羌村社区和文化的灾后重建适应研究
——以岷江上游盘沟村山洪泥石流灾害为例
王海燕
汶川大地震对居住在地震带上的羌族造成严重破坏,不但其生活的地质地貌、自然生态环境发生改变,许多羌族村寨也在地震中损毁或受到严重损坏,而且羌族人口也大幅减少,其古老文化在地震中受到严重威胁。各方专家都对地震之后羌文化的保护、拯救、重建与恢复结果表示担忧。同时,羌族社会在灾后重建中渗透进入大规模的外界事物,包括救灾人员、援助方、NGO、救灾物资、社会意识等等,更加剧了羌族能否继续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忧疑。面对如此剧烈的外部自然灾害与人为干预,羌族文化系统通过一系列解构、重构、适应、更新的过程,自然形成了一个震后羌族社会文化、自然与经济系统耦合体。待这个抗外界干扰的自适应体系基本趋于稳定之时,地震引发的一系列泥石流、洪水、山体垮塌等次生灾害也在震后五年后集中爆发。
美国人类学家托瑞(William I. Torry)认为灾难始终与共同体相联系,不外乎共同体的连续与变迁[1]43-52。灾害虽然对社会结构造成破坏,但其结构会再次平衡,这种平衡关系的恢复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明显,即原住民社会和文化在反复无常的环境条件下可以获得长期稳定性[2]28。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岷江上游盘沟羌村发生于2013年的“7.11”山洪泥石流灾后重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材料来呈现破碎化的村落社区经过灾后重建,被安插于城镇居民社区,面临与原生自然、人文生境的分离,探讨原来的传统村落共同体社区逐渐在日常生活和生计各方面发生的文化再适应过程,由此使得原来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重新凝聚,在城镇居民社区中得以延续,最终达到社区恢复与平衡状态。
一、田野点盘沟村简介
盘沟村位于汶川县城南七公里处,是岷江东岸一条自然沟域。历史上,沟内河坝和两边高半山都分布着羌族自然村寨,而沟口处则零星散落汉族家户。随着民族地区工业化、现代化推进,盘沟村高半山居住的羌族人口不断向河谷平坝迁移,这种迁移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完成。在2013年7月,由于地震、降雨等因素造成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将盘沟坐落于河坝区的自然村落全部冲毁。政府的灾后重建政策将村民从他们赖以为计的生境中剥离出来,在县城各原地震灾后安置区提供“插花式”的安置方式①[3]78-82。这对一个村落共同体来说,不仅会完全割裂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割裂他们的文化与当地环境的关系,在事实上也可能变成“城镇消化”,对于原来的共同体来说风险是极大的。
传统村落的盘沟乡村社区在大灾大难的催化下被城镇化,并入到城镇居民社区中。位于盘沟沟口的居民社区“阳光家园”第四期②成为了“7.11”盘沟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后房屋重建集中安置点,是国家力量与村落传统力量共同作用的场域,一方面充满了由家庭、社区等组织起来的传统性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改变而悄然发生的文化与生计等方面的变迁,变动的乡村社会恰好呈现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
从过渡安置开始,受灾户大多在阳光家园第四期租住房屋,开启城镇居民生活模式。虽然盘沟村民和社区居民历来有交往,比如当地村民往日贩卖自家菜蔬,主要顾客就是这些社区居民,他们中有的成为关系很好的朋友,相互之间很熟悉。但村民与城镇社区居民之间最初相处时仍旧矛盾重重,有很多方面需要磨合和适应,小区里谁家丢个东西,村民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小区垃圾到处乱扔卫生情况差,村民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生活习惯上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是要说有多大的矛盾也没有。相互之间慢慢熟了之后,我跟小岭岗的普格言、窝竹头的亚斯都是很好的朋友,可以随便开玩笑。像他们来社区租房子,找我介绍的时候,我也给他们说要搞好关系,注意卫生之类的。总的来说,没有啥大问题,大家相处久了,就了解了”③。阳光家园第四期小区内做小吃生意的T老板的话,也算是代表了一部分社区居民对这些受灾户们的总体看法。
这些原来住在自然村落中的农民住进居民小区之后,楼下的居民常常上楼敲门,地板声音弄得太响,说话吵闹声音太大等等,影响了别人的日常生活。可能被城镇居民“教育”的多了,笔者在小区村民家里的时候,经常听见大人告诉正在玩耍的两个小孩,不要太吵闹、电视声音不要开的太大、不要拖拉板凳,要不然楼下某某又要敲门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确实住不惯楼房。农村人,相互窜门都成习惯了。以前住在沟内河坝,上百户人家的房屋密密麻麻挨在一起,从来没有不知道某家人房子在哪里的事情。忽然之间,自己曾经的左邻右舍都住进小区楼房了之后,发现要记住那么多人的门牌号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是找东家反而敲了西家的门。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之后,干脆就把村人乡亲的楼房门牌号都写在本子上,继续窜门,时间久了也就自然而然记住了。
山洪泥石流之前住在寨子上的时候,村人每日晚饭过后便到公共活动地点跳锅庄④,藏羌锅庄、黑水锅庄、草地锅庄,以女人们为主,偶尔有男性参与进来。若是妇女节、羌历年或者春节,大家更要穿上多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搞得更正式。灾后村民们比较消沉,她们的民族服饰也在洪水中被冲走,有很长时间大家没有再跳锅庄的激情。后来,在阳光家园第四期居民社区居住的原盘沟村窝竹头、小岭岗、竹子岭沿山三个羌寨的妇女重新组建了锅庄队,在小区公共广场跳舞,有固定成员12人,年龄从30岁到50多岁不等。这个锅庄队平日空闲时候排练舞蹈,逢县、镇举办的文艺演出,她们偶尔还参加表演。跳锅庄舞蹈也成为各村寨的村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重新聚合的一种方式。
三、生计方式的变迁
盘沟受灾最严重的窝竹头、小岭岗、竹子岭三个村民小组,每户人家在高半山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土地。2000年国家实行退耕换林政策的时候,村民们在地里栽种的良种大樱桃⑤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已经开始挂果,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截止2017年,盘沟村有大樱桃400余亩,核桃150余亩,红翠李300余亩。秋冬季节正是对大樱桃树进行维护的时节。做好樱桃冻害、病虫害的防治措施,比如松土、清园⑥、喷药、剪枝、施秋基肥、涂白⑦、浇水和烟熏。村内受灾村民在第四社区安定下来后,很快恢复农民身份,每天早上天刚亮就进沟上山,在山上田边地头挖地,整理蓄水的池子。由于失去了河坝的田地,往日高半山部分被荒芜的土地又被重新开垦,大规模种植樱桃树。商贩从山东运来一车车樱桃树苗在汶川县城贩卖,品种大小不同,价格差别很大,小的一二十元一棵,大的四五十元一棵。开年春雨始降,每家都是全家出动,种树垒地,一切都围绕如何打理好樱桃树而忙碌。
农业生产工具,锄头、镰刀、背篓,耕地机器,还有给果树浇水的水桶、胶水管等最初是放置于安置小区的楼房里的。受灾户们刚住进小区的时候,偶尔占用一下楼房过道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有的城镇居民比较理解农民的不容易,有的不好说话,相互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后来村民们想了个办法,他们在自己山上的地边搭建小房子,可以放置各种农业用具,还可以搭个简易床铺。大家也不用再为社区房屋空间不够而发愁。
羌人在历史上即有“入蜀为佣”⑧[4]41的惯例,每到冬季农闲期南下入蜀地赚取副业,充当背夫,搬运茶叶、大米及其他杂货,往来于羌地与蜀地之间,这种生计方式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盘沟而言,当地村民很少成规模到外地打工。地震之前,盘沟人仅有少数年轻人在成都等地打工,2008年地震后,当地人才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当时广东对口援建汶川,为了解决当地年轻人就业,招募了大批劳动力到广东、浙江一带务工。然而,不适应外面湿热气候,没到一个月,很多人连工资都没有拿到就返回老家了。即使今天,对年轻人来说,外出打工至多是去外面的世界“见见世面”而已。“7.11”山洪泥石流灾后房屋重建完成以后,恰逢当地大樱桃收获,每日要运到汶川县城卖。等樱桃季节过后,年轻人又去成都平原找短工,一般找服务行业的工种。这种农忙时候在家,闲时外出“长见识”的生活方式在盘沟村年轻人中比较常见。无论如何,对于盘沟村民来说,人生起伏,他们适应当前的生活还需要长久的时间,但至少每个人都在努力,没有丢失自己。
四、习俗年节的改变
羌族习俗是每年农历十月初一过羌历新年时就要开始宰杀年猪,家家户户在门前搭上简易土灶,土灶上一锅开水热气腾腾。经过杀猪到烫猪毛、刮毛、肢解、剔骨、腌制、火塘上架、烟熏而形成腊肉。冬季杀两头猪是未来一年全家肉食的主要来源。自从住进社区楼房之后,没有条件再养猪了。村民们现在解决养猪问题的方法便是向周围高山寨子的农民“订购”毛猪,一斤十几块。有的年初就开始预定。到了冬季,在卖家宰好猪、腌制,等烟熏好了再搬回自家楼房内挂着。买一头猪二三千元,够全家吃一整年,这种方式应该会成为搬进楼房的村民们长期适应的方式。
马年春节是村民们失去家园之后在城镇居民小区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可能还未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大家都怀念以往住在寨子上时,过春节,随便走进哪户人家里都是热热闹闹的,围着火塘,亲戚朋友一大群,和住在小区,偶尔看见几个人在楼下晒太阳,平日都窝在家里连个人影也看不见的对比有很大心理落差。住进小区的第一个春节就在低气压的氛围中度过了。不过最近几年的春节,村民们大概也走出了家园被毁的悲伤气氛,慢慢开始适应社区的生活。春节间团年、聚餐、走亲访友又陆续开展起来。鉴于农村家族人数多,居民楼房在宴客办事等方面都不方便,有的家庭在春节团年活动时也像城里人一样,在酒楼订餐。这些变化也是盘沟人住进城镇社区后,其文化变迁的一个微小缩影。
五、人生仪式的变动
羌族人的人生礼仪在时间纵轴上贯穿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横向空间中则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而正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是一个群体的价值”[5]6。仪式只在特殊的场景才展现,意味着仪式的重要性远超日常。如果考虑到羌族传统上并无文字,那么仪式则以充满形式感的场景存在的同时又传达足够信息,既再现事物又勾连情感,既体现文化心理又塑造价值认同,关系着一个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祖先观念、历史以及族群记忆。
小孩出生,要开酒席庆祝;婚礼,要宴请亲朋好友庆祝;寿宴,亲戚好友来家里恭贺;葬礼,村邻友人前来吊唁。盘沟的村子还未被冲毁之前,村民们每家都是宽房大屋,进行这些仪式的时候,家里院子十桌八桌都能安排下。如今住进小区之后,人生仪式的开展在诸多方面受到限制。要在几十平米到百平米的楼房内安排酒席就是最大的问题。文化进程可能对任何方向的变化都是开放的,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外在生活条件的物质改变是否会改变文化生活方式。对羌族人来讲,仪式不可缺少。
妇女生孩子的时候,来吃满月酒的客人,其规模一般来说没有婚丧嫁娶这样的规模大,因此村民们一般会在盘沟村上的小馆子里包酒席招待客人,和传统一样,请来客们吃醪糟,每人发一个染红的鸡蛋。小馆子也是“7.11”之后才开张,老板正是其中一家受灾户,自家人兼做厨师、服务员等,节约了不少成本。一桌几百块规格的饭菜,这家餐馆一次可以安下十来张桌子。
收“竹米”⑨能将就,举办结婚和办葬礼则没有办法对付,来人客去,居民小区楼房不具备这些功能,于是村民们开始把这些仪式活动搬到小区公共空间举办。村人家里曾经置办好的棺材被洪水冲走,重新买的棺材根本抬不上楼,于是大家在小区的小广场上搭建临时帐篷,设立灵堂,一切全部按照传统的羌族丧葬仪式进行。人去世后,马上派人请阴阳先生或者端公来家里推算具体下葬时间。目前盘沟村请过的阴阳先生或端公有盘沟村内的SXH,邻村黄土坎的YDX,郭竹铺的TTB。死者的亲人装殓棺材时,要放一小片碎银在死者嘴里作为下阴间的过路钱。,邻人好友来吊唁逝者,自带香烛、纸钱,并“坐大夜”⑩,进行闭亮、戴孝、哭丧等,所有过程全部在临时帐篷中进行。不过头七的时候忌宅,全家人仍旧是锁上自家房子,去亲戚朋友家躲煞。招待来客的酒席是坝坝宴。做坝坝宴酒席的多是以几人组合成团队,且提供食材,主家只需确定一桌酒席的价格,他们便能作出相应规格的菜肴。
盘沟小岭岗的村民WMX,也是“7.11”山洪泥石流受灾户,灾后在阳光家园第四期完成房屋重建。他的儿子WJG的婚礼,是村民中第一个在小区公共广场举办的。小区广场搭建起百十平方米的临时帐篷,内设桌椅十几桌,吃流水席。帐篷内还专门隔出一间堂屋,进堂屋正对着的一头还摆放着刻了祖宗牌位的神板。婚礼头天晚上“花夜”,临时帐篷内的“堂屋”并排放几张方桌,上面摆着亲戚朋友送的干果酒水等。新郎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为他的最后一个单身日狂欢。婚礼第二日新郎新娘的结婚典礼、拜堂也是在临时帐篷内的堂屋进行。
往日羌寨举办婚礼,自家宰杀一头猪就够所有肉食花费。席面上一般有12个菜,其中8个炒菜,4个蒸菜,蒸菜有三鲜、坨坨肉、咸烧白、粉蒸排骨。而自从住上楼房,不得不请坝坝宴之后,席面的菜肴一般都二十多个菜,除了猪肉,鸡、鸭、鱼、海鲜都有。婚礼第一天共摆酒席26桌,一桌500元,有20个菜。第二天正席摆酒24桌,一桌600元,有22个菜。羌族婚礼要请吹吹的习俗仍然延续。WMX去理县蒲溪寨请的唢呐,婚礼进行两天,每天的工钱为240元。现在的婚礼,又加了一项花费,请摄像师傅成了惯例。一场婚礼拍摄下来,制作六张光盘,需要1200元。W家的摄像师是在茂县请的,据说熟人优惠,只收1000元。以往在村寨上的时候,一场婚礼办酒席只需要花费六七千元,而WMX为他的儿子WJG举办的这场婚礼,虽然只是小范围宴请了村邻及近亲,并没有请更大范围的家门亲戚,但仍旧共支付了大概四万元的账单。
W家的整个婚礼中,有两个支客师,分别是盘沟老街的LXY和W家所在村小组的组长XMY。家园没有被冲毁之前,各村寨村民在办理这些大房小事的时候,请支客师都会请本寨子的人。而今,盘沟五个村寨只有组别之分,大家都住在沟口社区及周边地区,空间上已经没有界限。一场灾难将原来固定的社会结构打破,又重新将人们聚合在一起。
结语
一场山洪泥石流灾难在物理结构上打破了盘沟村民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最后一层区隔。那些最开始居住于高半山村寨的原住民,经过长时期的迁移运动,于2008年地震后全部集中于沟内河坝。一夜之间,被一场洪水从沟内“冲到”沟外,从平房“冲上”楼房。这场洪水灾难与2008年“5.12”汶川地震相比,引起的外部力量的介入,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变革影响更大、更彻底。村民们进入居民小区之后,面临着对城镇生活环境的适应以及失去了以村寨为归属单位的场景后,回归日常生活,与城镇居民为邻,重新确认“我是谁”的认同。我们看到,即使在非常不利于共同体保持完整的现实境况下,当地村落的人或者由于族性,亦或是一种共同体情结,却在无形发挥作用。
乡村的灾后重建,不仅仅是灾民的房屋重建,更是村民们日常生活、土地情感与共同体传统文化的重建。Torry的社会平衡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在遭到破坏之后重新恢复平衡关系,获得稳定性的过程。然而,社会结构中的平衡体却很有可能与之前的那个社会结构有巨大差别,甚至是重新构造。通过盘沟这个村落共同体渡过灾难的过程,我们看到,共同体的恢复是一个继承传统,改进创新,兼容并蓄的适应性体系。在人是物非的社区环境下,村落生态环境没有了,但这个社区的人仍旧维持着农业生产。亲缘、血缘关系在社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仍旧存在并被强化和维持,共同体的主体性,并没有因此荡然消失。生活在社区的村民依靠羌族传统文化、祖先血缘关系以及乡土社会的原生情感,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上建立起一个文化非地,让共同体重新凝聚,在民族村寨城镇化过程中开辟出一方文化非地。
注释:
① 在本文中,作者详细描述了盘沟村的变迁历程,尤其呈现了在灾后重建规划下进行的“城镇化”过程。
② “阳光家园”是2008年“5.12“地震后,由广东援建的灾后城镇居民安置区,一共有12个点(也叫四第),其中一期、二期、三期都位于汶川县城中心地区,只有第四期位于县城郊区盘沟村沟口处。
③2014年6月4日,访谈盘沟第四社区居民TSS。
④ 锅庄,是一种较为广泛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羌寨人都喜爱跳锅庄。锅庄分喜庆、婚丧、礼寿等数种,跳的动作不复杂,容易掌握,动作来源于日常生活劳动。在生产劳动之余,节日喜庆之时或在婚丧嫁娶之时,跳锅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习俗。锅庄一般是歌舞相融,特别是有酒或围在咂酒坛边,十来个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手拉手边唱边跳,节奏欢快、气氛热烈。可以从日落跳到夜幕降临,从黄昏跳到深夜。汶川县的文化宣传部门曾在各村组织群众跳藏羌锅庄。1990年前后,威州跳锅庄形成热潮,盘沟各个学校、厂矿每到下午五六点,就开始放音乐,广播组织跳锅庄,1994年,还举办过藏羌锅庄比赛,有一万多人参加。乡村寨子中,锅庄也以健身锻炼的形式盛行。
⑤ 樱桃,又称车厘子等。本身属于落叶乔木,树体高大,适宜在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温度适应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生长。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传教士和侨民将樱桃带入中国。山东一带是中国樱桃种植最早的地区。经济栽培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面积推广始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云、贵、川、新疆等多省的高海拔地区广泛试种及发展。汶川樱桃大规模种植始于退耕换林政策之后,在此之前只是零星栽种。最近十年以来,当地种植过的大樱桃品种有红灯、那翁。
⑥ 清园,即在二三月份前将田地内的杂草、落叶等开沟埋入地下,消灭越冬的病虫菌源。
⑦ 涂白,在冬季用涂白剂涂抹樱桃树干和大枝,具有保温防冻效果。而涂白剂的成分主要有生石灰、食盐、硫磺粉、动植物油和水,按照一定的比例拌匀,捞走石灰渣即可使用。
⑧ 明朝文人孙复宏作《羌傭行》,描述羌人季节性到四川平原汉族地区务工的情形。
⑨ 竹米,羌语,吃满月酒的意思。
⑩ 坐大夜,宴请前来吊唁的人参加。
参考文献:
[1] Torry,William I. Anthropology and Disaster Research[J].Disasters,1979,(1).
[2] 李永祥.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3] 王海燕.从“共同体”到“集合体”:岷江上游盘沟羌村“城镇化”进程的省思[J].青海民族研究,2018,(1).
[4] 《汶志纪略》(卷四)[M].嘉庆乙丑夏五月新鐫,蘂石山房藏版.
[5] [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