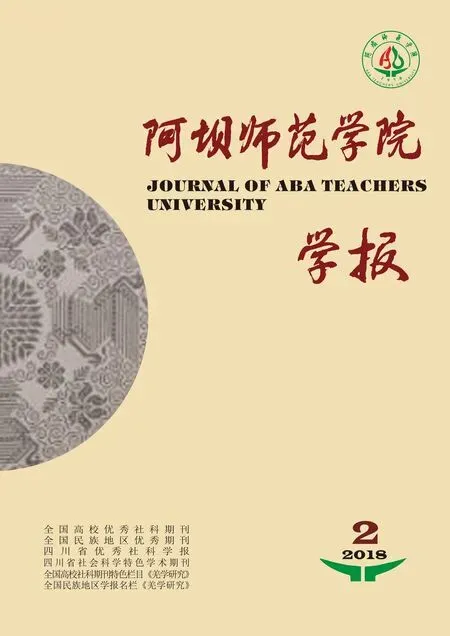节庆旅游与民族传统节日变迁
——以羌历年为例
李治兵,杨 杰,肖怡然
民族传统节日,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一些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日子[1]316。它产生于生产和生活实践,在每年特定的时间发起,以祭祀、纪念、庆祝或游乐等为主题,以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民俗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普遍参与为特征,是先民时间意识自觉的产物。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历年是羌族重要的节日之一,从节日的形成、传承的历程来看,与羌族的历史、习俗、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羌族聚居地区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羌历年的举办目的及运作方式、举办者和参与者群体、举办规模及形式等方面都在不断变迁。我们如何看待旅游节庆背景下羌历年的变迁,对促进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和羌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羌历年概况
羌历年又称羌年,羌语称“日麦吉”或“尔玛吉”,相传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按照羌历日、月、星辰计算,逢十进一,万物起一,即为岁首,有深刻的辞旧迎新之意,是羌族的“新年”。羌历年期间,羌族人民停止劳作,身着盛装,在释比的主持下,举行系列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开坛咂酒,人们喝咂酒、吃团圆饭、跳萨朗,亲朋好友之间相互道贺、迎请。在羌族的历史记述中,不乏关于羌历年的相关记述。羌族释比经典中的《安家神》记载:“十月之时敬神时,刀头再加猪油饼,神要先吃再凡人。三十初一是过年,先没敬神不敢吃,神要先吃再凡人,神要先喝再凡人。”羌族释比经典《说节会》中记载:“十月初一尔玛历,祭祀天神谢神恩,宰杀鸡羊喝咂酒,载歌载舞庆佳节”[2]2224。汶川雁门乡释比经典《木吉卓》记载:“九月三十吉祥日,羌人普谢天神恩。屈指吉期将临近,家家户户忙不迭。”羌族史诗《凿》也有相关记载:“十月初一是羌年,村村寨寨还大愿。村村庙宇刷白泥,换上新装好过年”[3]。从羌族的历史记述可以看出,羌历年是羌族人民庆祝丰收、祈求平安的重要节日,反应了羌族人民早期的农耕文化活动和将丰收与平安归功于神灵、先祖的朴素情怀[4]。羌族人民借助羌历年等传统节日,通过在时空、仪式上的统一,追溯历史起源、强化宗教信仰、巩固依附关系,促使社会的稳定和推动文化的传承。
二、节庆旅游开发与羌历年的变迁
(一)举办目的及运作方式的变迁
祈求神祉、慰藉心灵、满足村落娱乐需求是举办传统民族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一种满足自我需求的“内部活动”。旅游节庆背景下的民族节日是以旅游、商贸为目的,利用节庆的轰动效应而精心策划出来的一种主题鲜明、专事展演的“外向行为”。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羌历年从村寨走向舞台,羌族人民开展羌历年活动的目的开始变迁,传统的宗教信仰、崇拜英雄、祈求平安、庆祝丰收等因素被弱化,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是其主要目的。例如,2017年北川羌历年就以“共融互动、增收致富”为主题,集中展示羌族特色产品,开展商品展示展销会、北川特色产业产品推广会、签约仪式和商务考察等活动,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用。在运作方式上,传统民族节日主要是依照习俗在民间层面自发开展,旅游节庆则是按照市场运作模式举办,一般采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模式,部分旅游节庆活动已经采用资本运作、公司经营的形式。例如,2017年,阿坝州羌历年活动就以政府主办、部门联动、各区域参与的方式开展,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区域性节庆活动。
(二)举办者、参与者群体的变迁
民间性和全民性是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特征,活动主体是部族、村落的群众,自发组织,自愿参加。而旅游节庆则是由当地政府机关组织开展,把原为民间自发性的节日活动变成政府行为,并掌握活动的程序、内容和规模。旅游节庆背景下羌历年的组织开展发生了较大变化,以释比和民间组织者(会首)为中心的传统组织形式被不断弱化,以政府为主导,基层干部为执行者的模式逐渐取代释比和民间组织者的组织地位。政府出于扩大影响、招商引资和传承文化等多重考虑,成立工作机构,有组织地策划羌历年活动,例如提前公布活动日期,拟定活动主题、活动内容等,基层干部则按照上级要求落实各项活动,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者释比和民间组织者则更多地转为“表演者”。同时,部分羌族旅游景点的经营企业出于经营效果的考虑,也组织开展相关活动。从参与者来看,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一是羌族妇女的参与程度不断升高。由于宗教习俗等原因,传统的羌历年活动,尤其是祭祀活动多为羌族男性参与,妇女参与程度相对较低。随着羌历年活动中宗教习俗因素的弱化和表演性活动的增加,羌族妇女的参与程度逐渐提高。二是其他民族群众的参与程度迅速升高。近年来,羌历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观看羌族祭祀仪式、传统歌舞表演、品尝特色美食,羌历年逐渐超越民族范畴,成为整个区域的开放性旅游节庆。
(三)举办规模及内容的变迁
农业社会中,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一般以村寨为单位举行,规模较小。旅游节庆则是由政府或相关部门组织和协调,促使处于分散状态的各个乡镇、村寨的成员结为某一节日的庞大群体,呈现出由原来的每村每寨举行逐渐转向集中地点举行,由基础设施较落后区域向较完备区域举行的特点,举办规模扩大,举办地点出现位移。原羌历年的日期并不固定,一般在秋收前夕。自1988年起,茂县、汶川、理县、北川4县开始轮流主办羌历年庆祝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更是将羌历年定为法定假日,日期为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一般为3天。目前,羌历年庆祝活动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开展节事旅游的重要载体,由政府统一组织,羌族群众、游客、商务团体等共同参与,规模迅速扩大。活动内容方面,传统的羌历年主要反映羌族人民早期的农耕文化活动和祭祀祖先、神灵等方面的情况,内容约定俗成,由释比带领羌族人民进行。在当今的羌历年活动中,由于参与对象的多元化,诸如部分禁忌、制度、仪轨或规约因参与对象的文化背景以及场地条件等因素限制而不易真实反映的活动被缩减或改编,取而代之的如羌女选美、羌歌大赛、锅庄晚会、坝坝宴等项目则逐渐成为羌历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受政府、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及公益机构等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在羌历年活动中被植入“感恩、旅游、重建、科研”等元素,传统的“敬神”、“请神”、“还愿”、“献祭”、“赐福”、“庆祝出生”等内容则相对缩减。
三、节庆旅游对羌族地区的影响
(一)促使羌族地区传统经济活动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等条件的改善,羌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羌族人民的现代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不断增强,羌族地区已经由传统的农业文明模式向以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型。自发展旅游产业以后,羌族地区又逐渐以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向与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和多种经营转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多元化。羌族群众利用独特的民族文化、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手工艺品、歌舞艺术、民宿、特色餐饮、观光农业等旅游商品,逐步由传统农业经济模式向现代旅游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产方式、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促使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节庆旅游开发过程中,羌族人民的经济活动与旅游结为一体,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逐渐融合为一体。同时,随着节庆旅游客流的增加,游客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又客观上刺激了羌族群众改变自身的愿望,促使其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二)促使羌族群众思想文化观念发生改变
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必须以本民族文化自觉为基础。节庆旅游开发推动了接待地社会经济发展,增加了居民收入,由此引发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唤起文化自觉[1]317。随着羌族传统节日被纳入节庆旅游开发范畴,传统节日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客观上也使羌族群众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促使他们以恢复传统节日、习俗、语言、服饰、歌舞、工艺品等形式来保护本民族文化。不可忽视的是,旅游的介入也促使羌族群众对剧烈的文化变迁面临着理智与情感的两难选择。一面是旅游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一面是传统文化面临流失的风险。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行政关系三种社会关系的纵横交错,构成羌村的全部社会联系网[5]71”。随着旅游的介入,羌族人民社会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更多地转向从市场中寻求社会支持,传统上依赖血缘、地缘、行政形成的社会关系不断弱化,原来通过祭祀还愿、祈福消灾、娱乐欢度等形式来不断强化宗教信仰、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在节庆旅游中不断消减,释比、民间组织者等羌族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社会作用与地位发生了改变,青年一代又更趋向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客观上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风险。
(三)推动羌族地区城镇化进程
节庆旅游的开发需要整合旅游资源、整合旅游产品以提升吸引力,而这又必须以一定品质和规模的城镇作为载体。近年来,羌族地区紧紧抓住灾后重建、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等重大工程,大力发展节庆旅游、乡村旅游,有效地推动了区域的城镇化进程。一是推动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节庆旅游的开发有效地促进了羌族地区交通、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设施不断完备,为羌族群众提供了更加完备的基本社会服务,提高了羌族群众的生存生活质量,缩小了城乡差距,大大改善了羌族地区的环境氛围。二是提高了羌族群众参与节庆旅游发展的程度,羌族地区的新兴小城镇凭借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依托节庆旅游主办城市开辟分会场,把村寨建设成为旅游者体验、观光、康养的目的地,广大羌族群众有机会通过节庆活动展演,旅游接待,特色商品销售等参与旅游发展。随着土地三权分置等政策的落实,又进一步增加了羌族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的渠道和资本,促进增收致富。三是带动了周边产业发展,节庆旅游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在满足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基本需求时,可以有效带动羌族地区生态农业、特色产品加工业、文化产业等的发展,促进产业融合。
(四)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节庆旅游的开发是一柄双刃剑,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城乡的自然和人文生态造成一定破坏。自然生态方面,羌族地区大部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在节庆旅游开发过程中,部分地区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在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和打造旅游景观过程中论证不严谨,规划不合理和重复建设等现象客观存在。部分地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无视生态环境容量,超规模接待,导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同时,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加剧了对羌族地区生态自然系统的破坏。人文生态方面,节庆旅游的开发使原本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民族传统文化被推上“舞台”,在外来信息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含义被重新定义和解释,某些文化符号被曲解和浅表化,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失去了本民族文化固有的内涵。近年来,在举行羌历年活动过程中,那些受游客文化背景、场地等因素难以展示的环节被省略或改编,例如婚庆中的喜事锅庄、葬礼中表演的羊皮鼓舞也开始在羌历年活动中展示,选美、歌舞比赛等现代元素被植入羌历年活动中。
四、节庆旅游背景下的羌族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
(一)坚持发展性保护原则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决定的,都依赖于一定的生境,生境一旦发生变化,其衍生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将发生变化[6]。改革开放以来,羌族经济发展迅速,传统的小农经济转变为现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代表小农经济的羌族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生境的变化使传统羌历年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其蕴含的传统文化不断流失。节庆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羌历年是基于新的经济社会环境改良而成的羌族节日活动,尽管其举办目的、参与群体、活动内容等发生了变迁,但它为羌族传统节日的延续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羌族人民在通过展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获取一定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使本民族文化向外部空间拓展,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用性,促进文化自觉,进而自发地保护和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
(二)坚持羌族人民的主体地位
民族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而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少数民族本身。近年来,在羌历年等节庆活动举办过程中,政府、重要文化机构、公益团体、研究机构等外在因素对羌族文化进行了“有选择性”的传承和再造,作为羌族文化的创造与传承者的羌族人民则更多的是被动接受。在今后的节庆旅游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羌族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社区精英、民间组织者、本民族知识分子的带头,探索建立普通羌族群众能够广泛参与决策的议事机制,将羌历年等传统节庆活动的策划、组织等事项交还给羌族人民,政府、社会团体应回归本位,做好协助工作。
(三)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传统节庆旅游的开发也给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外来文化的强烈碰撞下,少数民族群众亦会出现难以调适的情况。近年来,羌历年等节庆旅游的开发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植被破坏、垃圾污染、传统文化流失等,而这些破坏往往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造成的,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在今后羌族节庆旅游发展中,政府可从政策、法规等层面加强引导,例如加强羌族文化遗产保护,确立法定假日,加强学校教育,鼓励科研机构加强研究、引进企业进行适度开发等,引导羌族人民、社会各界规范开展节前旅游活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传承保护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煦,李左人.民族·旅游·文化变迁——在社会学的视野中[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
[2] 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羌族释比经典(下部)[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
[3] 焦虎三.古老的羌历年:“日美吉”[N].中国民族报,2011-05-10.
[4] 郑瑞涛.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嬗变[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5] 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郗春嫒.布朗族传统文化的迷失与重构[J].民族论坛,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