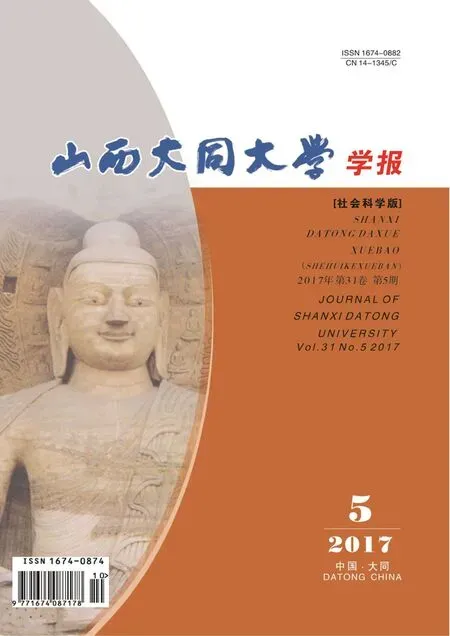黄茂林《坛经》英译的历史语境与传播
胡志国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黄茂林《坛经》英译的历史语境与传播
胡志国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在历史上黄茂林首次把禅宗最重要的典籍《坛经》以英语译出。这既有其自身对佛教的虔诚及勤奋努力的原因,也与当时上海地区浓厚的佛教氛围有很大关系,还与狄平子的敦促赞助有极大关系。该译本的影响主要在于面向英语大众的宗教传播,此传播通过不同出版社的多次重印,尤其是戈达德和韩福瑞分别进行的修订与再版而实现。黄茂林《坛经》英译尽管不完美,但时代因素及修订后再版的传播形式依然让译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证实了赞助人狄平子的现实主义翻译观念的合理性。
黄茂林;《坛经》英译;传播;狄平子
20世纪30年代以前,将中国佛典译为英语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要么是西方人,要么是日本人,几乎完全没有中国人的身影。虽然杨文会曾于19世纪末与李提摩太翻译《大乘起信论》流布西方,但他只给李提摩太解释原著的含义,并不亲自动笔,因而作用有限。从翻译时间和影响力角度综合考虑,黄茂林堪称中国佛典英译第一人。黄茂林于1933年在海外去世后,上海佛教界就曾高度评价:“黄茂林居士为国中能以佛教宏宣于世界之唯一功臣”,“近年来欧洲人士倾向大乘,对于吾国佛教有良好之认识者,皆居士传扬摄引之力”[1]。
释东初和高秉业(Ko Ping-yip)曾对黄茂林作有小传[2,3,4],能让人大体了解黄茂林其人。但二人的传记都很简短,黄茂林又因早逝而未及完全施展才华,加之佛经英译是处于边缘的翻译活动,所以他们的文献少有人知,以致人们对黄茂林多有误解。例如,美国华裔研究者依法将黄茂林定性为“生意人”[5];邓殿臣说“没有听说他(黄茂林)译过什么经”,语气很是不以为然①。
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叙述一下黄茂林生平。黄茂林原籍广东,1897年出生于香港,1919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先在香港警署工作,后调至南太平洋英属地萨摩亚群岛任职,1926年辞职②,到上海担任翻译工作,两年后再次辞职,住狄平子家专心译经。在香港时业余研习小乘佛法,到上海后改习大乘,成为太虚大师的皈依弟子。黄茂林的佛经翻译,最著名的是1930年译出的《坛经》。此后,他翻译了《成唯识论》《阿弥陀经》《佛说十善业道经》等典籍,还曾将丰子恺的《护生画集》译为英语出版③。黄茂林蓄志留学锡兰(斯里兰卡),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经典,以增进对佛学的理解和翻译,最终得到上海佛教净业社的资助,于1931年2月成行④,进入锡兰著名佛学院明珍学堂,师从纳啰达大师,然两年后积劳成疾⑤,英年早逝于异国,年仅36岁⑥。电报传到国内,同仁莫不痛惜。
黄茂林翻译的《坛经》是这部禅宗经典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在后世影响很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史料发掘,将黄茂林英译《坛经》置于历史语境之中,探讨译本的产生过程,并对其传播进行分析。
一、黄茂林英译《坛经》的主体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变化须有根据与条件,根据之谓内因,条件之谓外因。佛教认为,一事一物之生,皆由因缘际会而成,因即自身的因素,缘即旁助的因素。这两种说法颇有相通之处,都说明事物的发生均有内、外两大类原因。黄茂林成为《坛经》英译第一人,自然也是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黄茂林见贤思齐的向学精神让他具备了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坚实的佛学修养。他曾自叙学习英语之刻苦,“弟自衣食于英文后,书非英文不观(佛经除外),口非英语不语,非敢忘本,盖性本鲁钝,又鲜有暇晷以致力于本国文字也”[6]。他在锡兰留学时,对“识数种文字,英文、藏文亦识”的尼泊尔僧人“每天五时便起,立即读经,晚上十时,书声仍不辍”敬佩不已[7]。在佛典研读方面,他曾向太虚法师汇报读书近况,“弟子目下读巴利文本《法句经》、梵文本《心经》,颇有兴趣”[8]。
对佛教的虔诚是黄茂林从事佛典翻译与外传的动力。黄茂林自己信仰佛教,并努力向西方世界传播佛教。除翻译佛典外,自1925年起,他又翻译了一些报道西方佛教徒和佛教组织的文章,如《西人之皈依三宝》《英国比丘马显德博》《德国佛教居士林》等文章,显然他很在意佛教在西方是否被接受。为在语言上扫除西方读者接受佛教的障碍,黄茂林于1931年创办并主编中国第一种英语佛教杂志Chinese Buddhist(《中国佛教杂志》)。1933年黄茂林去世后,杂志随即停刊,可见他在此刊物中的核心作用。
黄茂林一生勤勉精进,惜时如金。在锡兰学习的时候,最初因为“早晚课皆用巴利文,非背诵不可”,三四月后才能兼顾“汉文翻译及编辑杂志”而心生愧疚[7],后来则学习、翻译、编辑齐头并进,最终在几个方面同时取得进步。文献梳理表明,黄茂林的主要成果都是1929-1933年短短数年间取得的,这自然是珍惜时间的结果。
好学、勤奋、虔诚等良好品质汇聚于黄茂林一身,使他成为《坛经》的第一个英译者。
二、环境和赞助人对黄茂林《坛经》英译的促成
除个人因素外,黄茂林取得的成就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浓厚的佛学氛围关系密切。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战火损毁和晚清政府的压制,上海地区的佛教在20世纪初重新勃兴起来。佛教团体增加,上海佛教公会、上海佛教居士林、佛教净业社、中国佛教会先后成立。太虚倡导人间佛教,震惊全国。圆瑛、太虚、持松多次到东南亚、日本、欧洲、北美等国演讲,日本、锡兰、美国等国家也有僧人、居士来上海交流。人们注疏经典,编撰辞典,阐述教义,传播信仰。《佛学丛刊》《海潮音》《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心灯》《威音》等刊物先后创办。黄茂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无疑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与太虚等著名佛教人士过从甚密,还加入了上海佛教净业社。他的《坛经》英译本和英文版《中国佛教杂志》由有正书局出版,《十善业道经》和《护生画集》英译本由佛学书局出版,《护生画集》还受了中国保护动物会的资助,这些出版社及佛教组织都设在上海。
直接促成黄茂林翻译《坛经》的是赞助人狄平子。狄平子于1912年创办有正书局,大量出版经书佛像,在上海佛教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狄平子很早就想将《坛经》译为西方语言,但30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29年春天,狄平子见到黄茂林,遂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翻译此经。当黄茂林以能力不足而推辞的时候,狄平子从三个方面力极力劝说:1.眼下的翻译是很好的练习,译者可以训练自己,为将来的佛典翻译作准备。2.虽然有些人翻译能力更强,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亲自翻译,这些人可以帮助译者修改译本,给译本润色。3.翻译是允许存在一定错误的。尽管译本有错误,对某些人来说,仍是有用的,这些人不能读原著,但因为此前已经掌握了原著的内容,他们只需一两个段落,甚至一两个词,就可以唤醒记忆,回想起已经忘记的宝贵知识。[9](P2)
可以看出,狄平子的翻译观念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他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翻译观念,不认为翻译必须和原文等值、读者只能被动接受译本提供的内容。他认识到,读者在阅读译本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认为他们可以借用已经具备的知识弥补译本的不足。他还认识到了翻译领导者的作用,认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不仅仅只有译者本人,还应该有发起者或管理者,译者和领导者在翻译中的作用不一样,但都是有价值的。出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不能要求翻译一开始就完美无缺,在理想翻译和时代需要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而只要译者严谨努力,翻译的质量可以随着实践的增长而提高。如果从现代翻译理论来阐释,狄平子的三个理由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接受美学翻译理论和翻译市场组织观等当代翻译基本观念不谋而合,体现了深刻的洞察力。狄平子的现实主义翻译观念和黄茂林严谨的翻译态度与积极进取的学习精神相结合,造就了第一个高质量的《坛经》英译本。
综观黄茂林翻译《坛经》的过程,可以说是译者主体和意识形态、赞助人相互作用的结果。赞助人代表了集体的意识形态,译者生活在集体中,并与赞助人发生直接联系,译者为这个集体服务,同时为这个集体所成就。
三、黄茂林英译《坛经》的传播
1960年,佐佐木夫人(Ruth Fuller Sasaki)在编制禅宗典籍英译书目时说,“在《坛经》的首创性翻译中,黄茂林对佛教的虔敬之心表露无遗,但就文本翻译而言,他留下了许多工作尚待完成”;《坛经》需要有一个“学术性的、透彻的英译本”。[10]十多年后,有两位学者在评论《坛经》翻译史时接过这个观点,认为黄茂林的翻译过于自由,常使用“评论性的、而非等值的语句”,或使用一些生僻的词语;直到杨波斯基(Yampolsky)的译本出版之后,人们才拥有了一个“充分利用了现代学术成果的、审慎而基本准确的敦煌本译本”[11]。这两个文献都以学术性为标准,认为黄茂林的译本不佳。然而,正如狄平子所言,“翻译是允许存在一定错误的”,一个不太好的译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读者使用,完全可能发生良好的作用。事实上,从传播过程和历史影响看,黄茂林译本是非常成功的。
(一)黄茂林《坛经》英译的总体传播 根据林光明对《坛经》所有英译本的统计结果来看[12](P5-6),黄茂林译本得到的修订和再版次数是所有译本中最多的。现将黄茂林译本的修订和再版情况摘录如下:

表1 黄茂林译《坛经》的修订和再版信息[12](P5-6)
表1为研究黄茂林《坛经》译本的传播提供了全面信息。但经笔者查证,这个表格有少许缺陷。戈达德《佛教圣经》的1938版本是第二版,这是一个增订本。此书其实最早出版于1932年,收录了“Self-realization of Noble Wisdom”(《楞 伽 经》),“The Diamond Sutra”(《金刚经》),“Sutra of Transcendental Wisdom(Maha-prajna-paramita-hridaya)”(《心经》),“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坛经》)等四部经典。Luzac and Company出版社的1944年版修订者是韩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此书1953年出版了再次修订本。Shambahala出版社The Diamond Sutra&The Sutra of Hui Neng一书所收的《坛经》与韩福瑞1953年出版的修订本没有区别,此书首次出版时间为1969年。
1957年Buddhist Book Bistnbutor版、1992年香港佛教流通处版、1994年上海佛学书局版,笔者无缘得见,但各种《坛经》英译研究文献均无记述,因此很可能是黄茂林版或其他人的修订版的重印。此外,可以肯定的是,1996年顾瑞荣版是黄茂林译本的韩福瑞修订本的重印。
黄茂林译本为何会得到反复修订和再版,可以从当年韩福瑞的版本选择中找到答案。“伦敦佛教会曾购买(黄茂林译本)一百多册运到伦敦,1939年,尚未售出的书转到英格兰,很快便销售一空。”面对更多读者的需求,“出版者有三个可选方案:重印以前译本,缺陷一仍其旧;另起炉灶,译文、评注完全重来;打磨现有译本,不改变基本模样”[13](P5)。韩福瑞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说明黄茂林译本虽有不足,但总体是不错的。
韩福瑞的陈述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黄茂林译本契合了当时西方读者了解禅宗的急迫需要。相比于韩福瑞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对这一点可以认识得更清楚。在19世纪,西方总体上将中国和日本佛教视为南亚佛教的退化和变种,不具有特别价值。尽管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试图改变人们的误解,但因介绍不够系统而未能达到目的。1900年,铃木大拙英译《大乘起信论》出版,为西方世界重新了解大乘佛教提供了最基本的经典依据。继1907年《大乘佛教概论》之后,铃木大拙于1927年出版了《禅佛教论集》,将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系统地介绍到了西方,西方世界由此发现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独立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佛教学者及佛教徒迫切需要禅宗典籍的译本,从原典阅读中理解这一宗派。因此,黄茂林《坛经》译本的出版恰逢其时。据佐佐木夫人统计,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除黄茂林译《坛经》和铃木大拙各种著述中的翻译外,其他禅宗典籍的英译屈指可数,仅有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的《永嘉证道歌》(1941),约翰·波菲尔德(John Blofeld)的《黄檗传心法要》(1947)和《顿悟入道要门论》(1947)[10]。这些作品不仅翻译时间晚,而且原典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坛经》。所以,黄茂林译本长期受到欢迎,并被选作底本进行修订,实在情理之中。
(二)黄茂林《坛经》英译的戈达德修订本 在林光明列出的七种修订本或重印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的修订本和克里斯玛·韩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修订本,这两个版本的传播情况尤其值得关注。
戈达德版本在1938年以后,至少还有1952年E.P.Dutton出版社、1956年 G.G.Harrpa出版社、1970年 Beacon Press(休斯頓·史密士[Huston Smith]作序)、1994年Beacon Press(新增罗伯特·艾特肯[Robert Aitken]序言)出版的版本。德怀特·戈达德(1861-1939)本是杰出的工程师,但在29岁时进入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往中国传教。传教期间,他“认为基督教传播在纯宗教方面是失败的”[14],于是在1923年开始学习佛教,1928年接触到日本禅宗,大受震动[15],认为“在生命意义问题上,和当下的基督教相比,中国及日本宗教可以提供更多的东西”[14],不久便到日本跟从铃木大拙潜心学习,同时开始编纂《佛教圣经》,改编、收录著名大乘经典的英译本,其中包括《坛经》。戈达德制定的改编方案是:“省略所有与经书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重新组织,令原文更加有序;连接、压缩同类教义;阐释隐晦的词语和教义”[16](P9)。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黄茂林译本中 60次“i.e”(即)所引导的注释内容,在戈达德译本中多采用不加注的方式进行处理,仅保留了其中6个放在括号中;黄茂林译本中的中古英语词汇如whither、thither被改成了现代英语词汇;原文“疑问品第三”在译文中被省去了;原文不少内容的顺序也被调换,有些章节被重新组合,如第五章中的内容分别对应原本付嘱品第十和忏悔品第六中的部分内容[17]。戈达德还增加了多处注释,如第七章“顿渐品”中,戈达德为了说明顿悟和渐悟的区别及该区别在禅宗史上的重要意义,专门写了一条长达200多个单词的注释。
笔者认为,戈达德这样修订,一是因为他写过大量的关于基督教、佛教的论文及著作,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很自信,认为自己的改编不影响准确性;二是因为他的汉语不好,他的修改大多是通过与中国比丘Wai-tao合作来实现的,有限的汉语让他无法根据原文亦步亦趋地严格修订。
从总体传播情况看,戈达德的修订本获得了好评。《普林斯顿佛教词典》“Goddard,Dwight”条说,“《佛教圣经》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拥有大量读者”[18]。该词典“Kerouac, Jack”条还说,“克鲁亚克曾仔细研究过《佛教圣经》,还曾背诵过其中的章节”[18]。但从学术角度看,戈达德的译本不大成功。正如佐佐木夫人评论道:“这个译本(戈达德的修订版)病在作者汉语知识有限,依靠个人直觉而非学术。它不能用于严谨的禅宗研究。”[10]
(三)黄茂林《坛经》英译的韩福瑞修订本 韩福瑞版本在1944年首次修订后,至少还有1947年、1953年、1966年、1973年的重印或再次修订本。韩福瑞(1901-1983)虽笃信佛教,但以律师为业,他的修订带有法律上的考虑,显得小心翼翼,与戈达德大刀阔斧的修订形成了鲜明对照。首先,他尊重初译者的版权,在黄茂林已经去世、他无法获得修改许可的情况下,决定“小心地避免任何改写,甚至避免以易于理解为目的的浅显化解释”。其次,考虑到大量读者已经背诵了黄茂林译本,他“把改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13](P5)。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韩福瑞修订本的某些句子较黄茂林译本稍短,更易于理解,偶尔省略或改变了黄茂林译本中过多的“i.e”解释结构,但完全保留了黄茂林译本与汉语原本十品一一对应的篇章结构,在选词上和黄茂林译本也基本一致,在总体上的确修改得很节制。
虽然韩福瑞修订本也受到了佛教徒的欢迎,但同样遭到了佐佐木夫人从学术角度的批评。佐佐木夫人在罗列所有截至1960年代初的译本后说,《坛经》依然期盼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性译本,可见韩福瑞译本也非她眼中的理想译本。此外,她批评道,韩福瑞把书名中黄茂林本来译得很好的“Gem of the Law”改为“Chariot of the Law”,明显弄巧成拙了,而另一方面,黄茂林译本中该改的错误却没有改,“编者(韩福瑞)只要看看《大正藏》中《坛经》的标题,就会知道,黄茂林把汉语的‘宝’字翻译成梵语的‘ratha’,要么是工人印刷错了,要么是黄茂林本人把‘ratna’拼写错了”[10]。翻开韩福瑞的1953年版的修订本,发现他已经把标题中的短语改进为“Treasure of the Law”,而梵语词ratha也已经省去了,显然是接受了佐佐木夫人的批评。
综观黄茂林译《坛经》的传播史,可以看出,黄茂林译本和戈达德、韩福瑞的两个修订本都属于非学术翻译,影响主要在于宗教传播方面,而不在佛学研究方面。有正书局的最初译本印数不多,因而影响有限,但后世无数次的修订与再版延续了这个译本的生命,其中戈达德和韩福瑞的修订版作用尤为显著。虽然后世的修订多少改变了底本,但黄茂林作为底本的译者,其贡献不可否认。
结语
黄茂林以短暂、好学、勤奋的一生,将多部中国佛教典籍译为英语,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译作中,《坛经》尤为成功。严谨的翻译、宗教传播的定位让这部译作获得了西方佛教徒的青睐,屡次得到改编、再版,为西方世界了解六祖慧能和禅宗提供了基本经典。这个译本虽然有种种不足,但完全实现了赞助人狄平子西传佛法的目标,证明了其现实主义翻译观念的合理性。由狄平子倡导、黄茂林主笔的《坛经》英译正式拉开了中国人英译汉语佛教典籍的帷幕,汉语佛教典籍英译史自此才算真正有了中国人的积极参与。
注释:
①“南传佛教的经典文献——南传佛教讲座”,http://bbs.foyuan.net/thread-114159-1-1.html.
②关于黄茂林早年的信息均来自高秉业文的简要介绍。此处说黄茂林1926年辞职,可能与到佛化教育社任翻译有关。该社出版的由太虚大师主编的《心灯》旬刊第16期(1926年9月18日出版)刊有一则《致黄茂林先生函》,“敦请先生为佛化教育社英文翻译,敢恳俯就,俾佛法得以广被于异域,岂但同仁之厚幸哉?”这个邀请大概是黄茂林转赴上海开始职业翻译生涯,并与上海佛教界发生密切联系的开始。这个推论与释东初说的“后来沪任翻译工作”一致[2](P1001)。高文说“初二年,在邮政局工作”,笔者不知翻译工作和邮政局工作之间的关系,不过可以肯定,黄茂林的职业与依法给他定性的“生意人”相去甚远。
③黄茂林英译的这四本佛书出版信息:《成唯识论》(第一卷)(Vijnaptimatrata Siddhi Sastra)发表于Chinese Buddhist(《中国佛教杂志》)1932年第2期 (佛学书局有单行本);《阿弥陀经》(Buddhabhashitamitayus Sutra),佛学书局,1933年;《佛说十善业道经》(Buddhabhasita Dasabhadra Karmamarga Sutra),佛学书局,1933年;《护生画集》(Ashimsa in black and white),佛学书局,1933年。这四本译作在《佛学书局图书目录》1935年1月出版的总第8期第34页都有销售广告。高秉业说黄茂林还译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笔者未能以资料证实这个说法。但本文所引的黄茂林讣告及资助其身后孤寡之倡议书,包括《中国留印佛徒黄茂林病故》《广东黄茂林居士在锡兰病殁》《为近故黄茂林同志身后萧条征资恤助其家族通告》,均未提到这些译作。Shambhala出版社1969年曾出版The Diamond Sutra&The Sutra of Huineng,署名译者普莱斯(A.F.Price)和黄茂林,意思是普莱斯翻译《金刚经》,黄茂林翻译《坛经》,不是二人合译这两部经。
④黄茂林出国时间,参见黄氏本人信函[7,8]。这个时间,释东初误为1933年[2](P1001),邓殿臣误为1933年(见网页“南传佛教的经典文献——南传佛教讲座”,http://bbs.foyuan.net/thread-114159-1-1.html),高秉业误为1934年[3,4],依法误为1934年[5]。
⑤黄茂林积劳成疾,为上海佛教界人士所共知。黄茂林去世后,《威音》刊发讣告说,“黄君因求学劳心过度,于去年染患肺病,入院医治,经数月,乃稍杀。后因补读旧课,致旧病复发,沪上同仁,曾屡发电慰问。讵日咋忽得该地与黄君同学某氏拍来急电云,黄居士已于十月二十八日身故。本埠同仁得电,惊愕非常”[19]。
⑥关于黄茂林的逝世原因,有三种说法。(1)病亡:“中国留印佛徒黄茂林病故”[19];“以用功过度,致罹肺疾,寿终锡兰”[2](P1001)。(2)溺亡:“讵于本月一日得吉隆坡西友来电,惊悉黄君惨于上月廿八日溺海身死”[1]。(3)因病住院疗养期间溺亡:“(黄居士)患病住院作康复治疗,不幸发生意外,溺死于泳池中”[4]。
[1]王一亭等.维持黄茂林居士遗族募捐启[J].海潮音,1933(12):122.
[2]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M].台北:中国佛教文化馆,1974.
[3]Ko,Ping-yip.The History of“The Sutra of Hui Neng”in English Versions Translations[A].The Dharmalakshana Buddhist Institute Buddhist Journal(Vol.IV)[C].1996.1-19.
[4]高秉业.英译《六祖坛经》版本的历史研究[A].六祖慧能思想研究——“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学术研究杂志社,1997.54-65.
[5]依 法.西方学术界对惠能及《六祖坛经》的研究综述[A].《六祖坛经》研究集成[C].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104-122.
[6]黄茂林.黄茂林君致云台函[J].聂氏家言选刊,1926(03):134-138.
[7]黄茂林.锡兰留学记[J].海潮音,1932(02):63-65.
[8]黄茂林.黄茂林上太虚大师书[J].海潮音,1932(01):115.
[9]Wong,Mou-Lam.Sutra Spoken by the Sixth Patriarch (Wei Lang)on the High Seat of‘the Gem of Law’ (Dharmaratha)[M].Shanghai:Yu Ching Press,1930.
[10]Sasaki,Ruth Fuller.A Bibliograhy of Translaltions of Zen(Ch'an)Works[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60(10):149-166.
[11]Beilefeldt,Carl&Lewis Lancaster.T'an Ching(Platform Scripture)[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75(02):197-212.
[12]林光明,蔡坤昌,林怡馨.杨校敦博本《六祖坛经》及其英译[M].台北:嘉兴出版社,2004.
[13]Humphreys,Christmas.The Sutra of Wei Lang[M].W.C.:Luzac&Company LTD,1953.
[14]Starry,David.Dwight Goddard-The Yankee Buddhist[J].Zen Notes,1980(07):2-5.
[15]Aitken,Robert.The Christian-Buddhist Life and Works of Dwight Goddard[J].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1996:3-10.
[16]Goddard,Dwight.A Buddhist Bible[M].New York:Casimo Inc,2007.
[17]宋伟华.《坛经》黄茂林英译本与Dwight Goddard英译本比较[J].中国科技翻译,2013(01):19-22.
[18]Buswell,Robert&Donald Lopez.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M].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19]威音新闻.中国留印佛徒黄茂林病故[J].威音,1933(54):7-8.
〔责任编辑 裴兴荣〕
Historical Context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Platform Sutraby Wong Mou-Lam
HU Zhi-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Sichuan,621010)
Thanks to his qualities and the social Buddhist atmosphere,Wong Mou-Lam unprecedentedly translatedThe Platform Sutrainto English.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is translation lies in the religious spread among the English public,which was realized by repeated republications,especially by those of Goddard and Humphreys in revised editions.Although it is not perfect,Wong's translation was rendered influential by the particular times and reception means,verifying the realistic view on translation held by his patron Dih Ping Tsze.
Wong Mou-Lam;translation ofThe Platform Sutra;spreading;Dih Ping Tsze
I046;B946.5
A
1674-0882(2017)05-0080-06
2017-03-20
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英语世界的中国佛典翻译与研究”(SC15WY023);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六祖坛经》英译研究”(SCWY15-02)
胡志国(1975-),男,四川蓬溪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