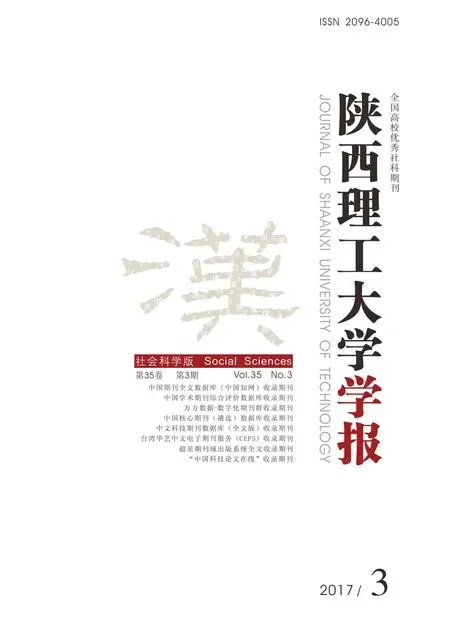锡伯族历史文化的全景式书写
——评拙木豪格长篇小说《大清锡伯营》(第一部)
陈思广, 孙婷婷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14)
锡伯族历史文化的全景式书写
——评拙木豪格长篇小说《大清锡伯营》(第一部)
陈思广, 孙婷婷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14)
锡伯族作家拙木豪格的长篇小说《大清锡伯营》(第一部),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变迁,以民族传说“乌拉本”的书写展现锡伯族的民族精神记忆和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传达作者对传承和发展民族精神的期盼,以英雄群像的刻画凸显了锡伯族文化中的英雄崇拜,通过特定的人物设置彰显了锡伯族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是锡伯族历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全面展现锡伯族西迁历史和锡伯族文化的长篇小说。
大清锡伯营; 锡伯族; 历史文化; 全景式书写
锡伯族作家拙木豪格(安德海)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锡伯营》(第一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锡伯营》。,是锡伯族历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全面展现锡伯族西迁历史和锡伯族文化并具有史诗气度的长篇小说。
1764年,清政府从东北锡伯族官兵中挑选千余人,协同家眷一起迁往新疆伊犁地区驻防屯田,拉开了锡伯族人民西迁的序幕,西迁垦荒戍边可谓锡伯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正所谓“民族文学以及它独具的艺术风格,是这个民族的历代作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民族的文学风格,首先在反映民族的生活题材内容上体现出来”。[1]267作为我国多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锡伯族文学,其重要的一个特色便是对于西迁历史题材的持久关注和呈现。如在诗歌领域,锡伯族民间长诗《西迁之歌》、《喀什噶尔之歌》、《拉希罕图》等都有动情的描绘,尤其是锡伯族诗人管兴才的长篇叙事诗《西迁之歌》,以恢弘的气度吟咏了锡伯族人一路历尽艰辛西迁垦荒的历史,影响深远。而在小说创作领域,佟加·庆夫的短篇小说《锡伯井》、《大山撤路》、《马背上的琴声》,傅查新昌的“锡伯族西迁系列小说”15篇,包括《大迁徙》、《跟着夕阳去》、《荒原上的欲望》、《呼图壁》等短篇作品,皆选取西迁垦荒戍边历史中的一些场景、人物、故事来展开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叙写,如《马背上的琴声》描绘西迁队伍中一位攀登险峰,勇射黄羊,又以琴声给队伍带来欢声笑语的普通青年锡伯族士兵;《大迁徙》再现了两百多年前西迁队伍泪别家乡时的动人情景;《跟着夕阳去》描写了在征选中落选的安吉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执着地追赶哥哥所在的西迁队伍而去的故事。这些作品“艺术地再现了西迁路上锡伯族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塑造了忠诚、勇敢、乐观、锲而不舍的锡伯族人民形象”。[2]256而第一次以长篇小说创作反映锡伯族西迁历史的作品是郭基南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流芳》*第一部《情漫关山》,第二部《虹展乌孙》。。小说截取西迁垦荒历程中几个重要的横断面,以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礼教的视角,反映了锡伯族人民西迁垦荒的艰辛历程和锡伯族男女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被认为是“忠于史实,透视了锡伯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开掘了民族灵魂,认识了民族自身”[3]103,填补了锡伯族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显然,《锡伯营》的创作也是承继这一民族特色和书写传统而来,但拙木豪格也带着拓新的写作意愿。在拙木豪格看来,虽然锡伯族西迁垦荒的历史被许多小说家反复书写,但“大部分努力仅限于事件本身和由此引申出的标题式的西迁精神,更多耐人寻味的人文景象却被忽视”,而实际上,西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4]2因此,从文化的视角透视锡伯族西迁垦荒的历史并烛照锡伯族这一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态,就成为拙木豪格重写西迁史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学夙愿。《锡伯营》就是这一文学夙愿的具体实现。
一、 传说书写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锡伯族作为一个长期游牧,几经迁徙的民族,很早就从祖先观念中孕育了属于自身的民族精神元素。[5]372西迁这一历史事件则为锡伯族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在《锡伯营》中,作家主要设置了明暗两条叙事线索,明线为锡伯部族在清乾隆年间奉命西迁伊犁戍边并开挖察布查尔大渠的历程,暗线则为对锡伯部族传奇“乌拉本”故事的书写,*“乌拉本”是对锡伯族一些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锡伯部族原始记忆的诗性想象和技术链接的产物。双线交织,展开了对锡伯族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书写。
“乌拉本”是关于锡伯族祖先的故事,作者将这一神话传说设为暗线,意欲回答“我从哪里来?”的历史追问。海尔堪玛法与喜利妈妈在充满激情的氛围中相爱,产下天马和神鹿的子孙锡伯人;喜利妈妈逃过答石亥惊天动地的追杀,挽救锡伯族的九姓先民并率领他们迁徙繁衍;大玛法托雷与火云夫人相爱并艰难产下锡伯族祖先雨赫和雷夫;伊散珠妈妈奔走呼伦四岸、治病驱魔而成为锡伯族萨满始祖。当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互为表里。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最初记录”“任何民族的神话,总与这个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相贯通”。[6]393《锡伯营》也意在凭借“乌拉本”故事的书写,展示锡伯族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如九姓先民被答石亥大王杀戮、拖雷被屠帕大王追杀、雨赫万里寻母中经历十八场劫难,就是锡伯民族苦难历史的象征,也是锡伯族人民在苦难中锻造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而海尔堪玛法作为神马的化身、雨赫饮狼母之乳、伊散珠妈妈与狐女的交往则是锡伯民族与自然相依,崇拜自然的勇敢与力量的表现。作者以锡伯族的神话传说为底色,通过对锡伯族始祖传说的诗意加工和细致描写,既充分展现了锡伯文化中的神性色彩,也在书写锡伯族共同的精神记忆中展现了锡伯族人对于民族精神记忆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不过,在书写“乌拉本”传说的过程中,表现锡伯族人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是作品的核心内容,它与西迁历史的“当下”叙述形成了参照和互动,赋予了西迁戍边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乌拉本”故事中,“行走”与“苦难”是最重要的主题。从喜利妈妈带领九姓先民躲过答石亥大王的屠杀,不辞辛苦千里流亡,到托雷大玛法带着爱子雨赫逃离屠帕大王的追杀,到二玛法雨赫奔走十载历经千辛万苦寻母的故事,锡伯族的祖先们在不断的“行走”和“苦难”中表现出了坚忍不拔、不惧艰辛的高贵品格。而西迁军民经历的泪别家乡、骨肉离散的苦难历程;经历的盗贼的围追、瘟疫的侵袭、沙漠戈壁的考验、高山大河的险阻、人心浮动的危机,也正是关于“行走”与“苦难”的继续。“乌拉本”中关于“行走”与“苦难”的祖先故事,被作者不断地穿插进小说明线西迁历史的“当下”叙述当中,形成了一种参照和互动,是展现锡伯族人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的二重奏,而祖先故事所展现的精神内核既成为支撑锡伯民族西迁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成为西迁精神的生动象征。正如摩伦喇嘛深情吟诵雨赫奔走十载万里寻母的故事时所感叹的那样,当下的西迁走过的路“正是咱们的大玛法们曾经生活过厮杀过逃亡过也热爱过的山山水水”[4]268。“乌拉本”与西迁历史的叙述是远古与当下、传说与现实的相互映射,它使西迁不仅仅是一次有着爱国主义意味的行动,更有重走祖先之路、追述民族历史、承继和发扬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的浓厚意味。
传说“乌拉本”的书写,也让人深感于作者对锡伯民族精神认同、传承与发展的深切期盼。在小说中,作者将“乌拉本”描绘成民族传承的史诗,成为连接锡伯爱曼各部落的精神纽带,并且多次强调其口口相传的传承方式。而“乌拉本”以一种诗化的口头传奇形式存在,正如小说中写道“这些靠众口相传的故事,一旦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它就成了一个死的东西,一定会慢慢被人遗忘”[4]70。只有不停地默念、记诵和传递,强调心的认同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而这一传承方式的另一深意正如小说中摩伦喇嘛所说:“祖上立下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规矩,正是为了让乌拉本在传承过程中能够像一棵树一样长出更多更繁茂的枝杈来”[4]268,口口相传的方式因吟唱者所处环境和自身特点不同使“乌拉本”的传承呈现出差异,在传承中使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得到丰富和发展。“乌拉本”本是作者在民族神话传说基础上加以总结和加工的产物,其所谓的传承方式自然不是真实的情形,但作者对这种传承方式的反复强调,正透露出作者对于民族精神文化消融的担心,表现出他对于民族精神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深切期盼。
“乌拉本”故事中的喜利妈妈传奇、海尔堪玛法传奇、托雷故事等锡伯族民间神话传说,在锡伯族已有的一些诗歌和小说作品中也被反复书写和提到,如管兴才的《西迁之歌》、佟加·庆夫的《在那遥远的国土上》、郭基南的《流芳》等作品里都有精彩的描写。但对锡伯族的民间神话传说进行系统地整理,并加以诗性的想象,将其织入到锡伯族西迁垦荒历史的整体叙述脉络和民族精神内核的展现之中,这在锡伯族文学中还是第一次。叶舒宪先生曾说:“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群体的梦”[7]2。小说对民族神话传说“乌拉本”的书写,正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和激情想象的锡伯族神话世界,展现了锡伯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记忆,展现了锡伯民族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借“乌拉本”表达着对于锡伯民族精神的一种态度,那便是对于民族精神认同、传承和发展的呼唤。
二、 英雄书写与英雄崇拜
英雄书写与英雄崇拜,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格萨尔王》到《江格尔》、《玛纳斯》,无不以史诗形式叙写本民族的英雄传奇,而英雄崇拜亦是锡伯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英雄或许并不像“英雄崇拜”史观的代表卡莱尔所宣称的“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8]1-2那样对于历史有绝对性的作用,但对于锡伯族这样一个经历了漫长部族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来说,部族英雄对于民族的发展,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和传承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所谓时势造英雄,锡伯族西迁垦荒正是为各路英雄的登场提供的历史机遇,也为作者塑造各色英雄群像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而小说的另一个吸引人之处,便是塑造了为数众多、生动活泼的英雄群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锡伯族的英雄崇拜文化。
就人物塑造方面而言,如果说我们在郭基南的《流芳》当中,更多地看到人物之间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看到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崇高与卑下、勇敢与怯弱的话,那么《锡伯营》则着力于挖掘和展示锡伯族人的英雄气质,凸显人物的英雄色彩。在《锡伯营》近六十年的叙事时间跨度中,小说塑造了以图伯特为中心,包括双箭、萨凌阿、哈拜、恰拜、舒尔泰、安泰、扎林阿、安巴、安达、阿卡、乃奔泰、敖音图、武英泰、布占泰等三代共十余位性格各异的英雄群像,值得称道。这其中,既有充满传奇色彩的第一代老辈英雄群体,又有文韬武略的第二代壮年英雄群体,更有英勇的第三代青年英雄群体,尤其是哈拜、图伯特、安泰三位英雄刻画得相当成功,也赋予小说英雄史诗的气质。
在小说中,双箭、哈拜、恰拜、萨凌阿等代表第一代的老辈英雄形象,充满着传奇色彩,若以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奇”,而神秘老练的独行侠哈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哈拜这位从小失去父母兄弟的将门之后,带有一种东方的神秘精神,年轻时便能摔死黑熊,在西迁时随萨凌阿出入匪穴解救人质,在南疆平乱时千万军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单刀匹马追击残匪等英雄事迹,已经使他声名大噪,在部落民众的口口相传中逐渐成为一个英雄传奇。哈拜行踪神秘,但却每每在关键时刻出现:萨凌阿灵车被阻,他毅然出现以自己的威望和气势打破了双方僵持的局面;面对杀人逃逸的布占泰,他只身一人从容追捕,敢以老迈之躯勇斗壮年之身;独自冒险进山与盗马贼阿曼佐夫周旋,设下巧计活捉匪徒,打破了舒尔泰等人栽赃的企图;八旗公议大会上他又在关键时刻出现监场,给予图伯特有力的支持。哈拜行踪神秘、行事老练,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神秘、从容、机智和自信,充满了传奇色彩。此外,憨直义气的双箭、骄傲而悲情的猎手恰拜、沉稳睿智的萨凌阿等都是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世传奇、老当益壮、重视荣誉,虽不免也有英雄迟暮之感,但这都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代传奇英雄。他们的人生境遇也逐渐沉淀为锡伯族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为后世所传扬。
图伯特是小说中第二代壮年英雄群体的代表,小说突出其“谋”的一面,充分展现其文韬武略。图伯特是锡伯族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在锡伯族英雄谱系的排列中,第三任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在锡伯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最高,也是小说最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当锡伯族驻守伊犁,面对水源缺乏不能满足激增人口的生计问题时,他力排众议,提倡开挖察布查尔大渠。在八旗公议大会上,面对以副总管舒尔泰为首的反对派势力的咄咄紧逼,图伯特沉稳机智,先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当舒尔泰抛出卡伦军情以反对挖渠之时,他抓住时机喝断舒尔泰,力斥他泄露军机动摇民心,涨了对手的气势。接着他从容稳健陈述开挖大渠的意见,从锡伯族的戍边使命出发,仔细分析了锡伯营生计问题的对戍边日益凸显的影响,又详述对大渠方案的设想,最后描绘了大渠开挖成功后的美好蓝图,层层深入,令人信服,最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挖渠建议遭到伊犁将军的反对时,他又以血书明志,动员民众立下“渠不成,请夷九族”的誓言,可谓壮怀激烈。如果说领导开挖大渠的过程充分展现了图伯特的“文韬”,那么浑巴什河一役则充分展现了图伯特的“武略”,是其军事指挥才能的一次精彩汇演。第一轮战斗他抓住敌人毫无准备的心理,鼓舞士气进行闪电突击。第二轮战斗充分估量了敌方反攻的兵力和心理特点,实行分队突击,又派安泰率精锐的生力军从侧翼突击打乱敌方部署。第三轮战斗则以箭阵的远程射杀和预备队的近程围歼相结合,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图伯特在这场战役中显示出他对于地理地形、战场形势、战士心理等多方面准确的判断能力,显示了领导者的卓越才华,小说对于这场战斗的分析描写也是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图伯特以沉稳、睿智、有魄力的领导者气质,成为小说中最为光辉的英雄形象。此外,锡伯营副总管舒尔泰虽不免有骄傲和自私的一面,但同样果敢、坚毅,也是一个谋略过人的英雄形象。而小说对这两位壮年英雄的文韬武略和矛盾交锋的描写,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安泰则是小说中第三代英雄群体中的佼佼者,体现了青年英雄的“勇”,散发着青年人的勇敢与朝气。这个饮过狼奶长大的孩子天生便带一股狼性,年少时为保护弟弟勇斗四五个成年男子,在教场中他是令对手望而生畏的狠角儿,并逐渐历练为意气风发的青年英雄。在浑巴什河一役中,图伯特展现了主将的“谋”,安泰则充分展示了先锋的“勇”,他率百余生力军,手持云血宝刀一马当先奋勇杀敌,以威势有力地震慑冲击了敌军的心理防线。而追击敌首江噶勒的最后时刻,选择与对手进行一场精彩的个人决斗,则显示了他非凡的自信和勇气,也使他最终成为锡伯营新一代的巴图鲁(勇士)。此外,安达、安巴、阿卡等锡伯营西迁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有着不同于祖辈的人生轨迹,也难免带有年少的轻狂和莽撞,但却继承了先辈的勇敢和坚毅。
英雄不尽是完美无缺的超人,许多英雄也有着凡人的一面,甚至在性格上也有一些瑕疵。《锡伯营》在塑造舒尔泰、乃奔泰、扎林阿、布占泰等英雄人物时,就刻画了他们性格中的一些不足,使他们更符合凡人英雄的本色。舒尔泰一出场便展现了他的勇敢和朝气,在校场比武中力克强敌脱颖而出。对于开挖大渠,舒尔泰虽然有出于个人名利的自私和骄傲,但也有对于锡伯营命运的真切关心,在八旗公议大会上他以锡伯营主要职责、开挖大渠的耗费、萨凌阿失败的前车之鉴等理由与图伯特针锋相对,其言辞条理清晰、雄辩滔滔,显示了他过人的谋略。随着大渠的开挖,他逐渐从个人意气与名利争斗中走出来,有条不紊地规划管理了大渠的后续开凿,而在卡伦被围,自己的女儿雪萝被敌方抓走之后,他也强忍悲痛,极力阻止官兵冒险行动,显示出开阔的心胸和沉稳的气质。舒尔泰这一形象有自私、骄傲和固执的一面,但小说也着力突出其有勇有谋、顾全大局的英雄本色,其性格心理的变化也使这一英雄形象更具真实感,内涵更加丰富立体。在小说中两次如程咬金般半路杀出的乃奔泰,其暴烈如火的性情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个“一板斧都砍不翻”的汉子,在大哥与两个侄儿战死沙场之时,因不满丧礼的简单而大闹灵堂,但在长嫂面前又一片真情尽露。当得知哈拜、恰拜两个侄儿带走了哥嫂的骨灰,他立马冲出来咆哮责骂并与哈拜进行了一场打斗,后又在侄儿的劝说下放弃己见,放声泪别亲人。小说中乃奔泰虽然只出现过两次,但这个暴烈又率性的英雄形象生动鲜活,令人印象深刻。布占泰在小说中虽然是一个仅出现过一幕的小人物,为妹出气杀人逃亡的他,在与哈拜的交手中虽然惜败,但也显示了他的神勇,而其从容赴死的豪气也尽显英雄气质。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显示了作者对锡伯族英雄崇拜观念的独特理解,英雄有不同类型,英雄的存在不在于人物本身的完美性,而在于英雄精神的展现。这一类英雄形象,也因为它们性格的多面性和丰富性,显得更具复杂性和真实感,提升了小说人物塑造的品质。
小说注重表现英雄的群体性特点,又兼顾特殊性的展示,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的英雄形象,同时对有缺陷的人物也注重英雄色彩的突出,为锡伯族的英雄崇拜文化写下了最好的注解,也为小说注入了一股雄健的气息,使小说具有了英雄史诗的气质。
三、 特定的人物设置与开放的文化心态
锡伯族在历史上经历多次迁徙,与汉族、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都有文化交往,是文化接受性比较强的民族之一,[5]250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使锡伯族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锡伯营》就尤其注重通过特定的人物设置和书写展现锡伯族开放的文化心态。
小说上卷以锡伯勇士双箭与蒙古族郡主乌云蒙和的爱情故事,展现了锡伯族与蒙古族之间的纯真情谊和文化交往。双箭以战胜黑熊英雄救美的勇敢,憨直义气的品格赢得了高贵的蒙古族郡主的芳心,郡主乌云蒙和不惧民族文化差异、不惧门第贵贱、不惧西迁险阻甚至不惧婚姻伦理,毅然千里追寻双箭。乌云蒙和起初为双箭的锡伯族家人所反感,但最终用自己的勇敢和亲和感动了大家,在双箭丧妻之后与双箭蒂结连理。虽然这是一个带有理想浪漫色彩的公主骑士故事,但也真切地展现了锡伯族与蒙古族之间的纯真情谊和文化交往,展现了锡伯族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
如果说双箭与乌云蒙和的设置意在通过不同民族间男女感情的纯真表现锡伯族开放的文化心态的话,那么巴音萨满和摩伦喇嘛的关系设置,则真切体现了锡伯族包容开放的宗教文化态度。巴音萨满是锡伯营神力无边的萨满,出入鬼神、驱魔治病,代表萨满教的神秘和激情。摩伦喇嘛则是一位虔心礼佛的青年喇嘛,性格沉静慈祥,代表着佛教的纯净和虔诚。这两个本不相关的人物在小说中因亲情的羁绊而联系在一起,摩伦正是巴音苦苦寻找多年的弟弟,巴音萨满师父的儿子。两人认亲时宁静而温馨,在为郑立春和扎林阿的葬礼做法时,摩伦诵经念佛、巴音激情跳神,一动一静的场面令人感动。小说中两人相互尊重又不过分亲近,保持着一种平衡而和谐的关系,这正体现了锡伯族文化中两教和谐并存的关系,表现了其包容开放的宗教文化。萨满教的激情活力、佛教的高深沉静也体现了锡伯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特点。而摩伦喇嘛前往藏地学经、住持靖远寺传播佛法也再现了清代佛教进一步融入锡伯族文化的历程。
此外,小说中第三代人海林与古莱亚蒂、任杰生的交往,则显示了锡伯部族在定居伊犁之后文化发展的新路向。与继承了祖辈勇敢坚毅品质的安泰、安巴、阿卡等第三代青年不同,海林不再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建功立业之上,而是醉心于对艺术的追求。从海林用购置聘礼的钱买了一把心爱的曼陀林开始,他便踏上了不同于先辈的人生轨迹。海林与维吾尔族少女古莱亚蒂因为对于音乐和舞蹈的热爱而走到一起,他们交流各自民族的音乐艺术,艺术上的相互理解使他们心灵相通。海林与汉族艺人任杰生也因对艺术的热爱而相见恨晚,两人用锡伯语改编汉族的眉户调和秧歌,将秦腔中的折子戏翻译成锡伯语,排演出具有锡伯特色的眉户调秧歌剧,两人的交往如高山流水一般。海林与古莱亚蒂、任杰生的交往再现了清代锡伯族与维吾尔族、汉族等民族艺术文化交往的生动景象,海林的身上体现着锡伯族人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也展示了西迁之后锡伯族文化在艺术方面的新发展。
在锡伯族文学关于西迁和屯垦戍边的历史叙述中,展现锡伯族与各民族的交往和友谊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如佘吐肯的长诗《察布查尔畅想曲》就描绘了蒙古族人助西迁队伍休养生息的动人场景;在佟加·庆夫的《在那遥远的国土上》里,索伦营(达斡尔族或鄂温克族)侍卫阿明巴图与锡伯族侍卫米安里的生死相托;蒙古族老人对米安里的热情救助都令人倍感悲壮与温情。在郭基南的《流芳》中,西迁途中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等各族人民向锡伯族人民送物资、援病患、助生产,让人倍感民族之间的深厚友谊;而《锡伯营》则采用文化的视角,在表现民族间、宗教间的协助和友谊之时,更注重展现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和发展,以特定人物关系的设置和书写,充分展现锡伯族与其他民族的深情厚谊和文化交往,展现锡伯族在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新迹象,进而落实到挖掘和展现锡伯族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和其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上来,思考和书写也显得更加开放而有深度。
拙木豪格曾在小说序言中谈到:“西迁之于锡伯族,首先是一次文化断裂,也就是种族传承的大部分文化积淀都被遗留在了东北老家,这就意味着摆在西迁锡伯族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文化重建。所以我认为,锡伯族西迁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重建的历史,期间涌现的诸多代表性人物和发生的代表性事件既是锡伯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延续,又是激情澎湃的文化探险与创造。”[4]2《锡伯营》正是通过引入民族传说“乌拉本”参与小说叙事,通过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特定人物关系的设置和书写,来展现锡伯族文化的根性认同、英雄崇拜以及开放的文化心态,由此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现在进行了全景式的生动描绘,堪称锡伯族历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全面展现锡伯族西迁历史和锡伯族文化并具有史诗气度的长篇小说。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在我国多民族文学格局之中,锡伯族人数较少,在文学创作方面虽然起步较早,历史悠远并且独具民族特色,但在总体实绩和文学影响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历史上锡伯族文学主要以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见长[9]2,以民间诗歌、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为主,而现当代以来的锡伯族文学,继承自身民族文学传统,文学创作也以诗歌(尤其是长篇叙事诗)、散文和中短篇小说见长,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则显得较为薄弱,仅有郭基南、傅查新昌、觉罗康林、拙木豪格等少数几位作家在这一领域耕耘探索,目前仅出版十余部长篇小说。这部以文化角度全面审视和书写锡伯族西迁垦荒历史的《锡伯营》的问世,不仅在展示、传播和传承锡伯族民族精神文化上有重要的意义,也是锡伯族长篇小说创作史乃至锡伯族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对于提升锡伯族文学在我国多民族文学格局中的影响也是有益的推动。
当然,在肯定《锡伯营》对西迁历史和锡伯族文化展现,认识《锡伯营》的创作对于锡伯族文学的重要意义之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作者初次涉足长篇小说创作,对如何驾驭长篇小说还有待进一步磨练。例如在结构上,小说稍显枝蔓和详略失当,各线索之间缺乏较为紧密的联系,未能形成有机的叙述网络。作为一个诗人,飞扬豪迈的文笔给小说带来了更多的诗情画意,但转入到具体的人物场景描写时,却不免有些生涩乏力,特别是作者对于关键事件和重要场景的描绘,显得有些简单。在人物塑造上,如何提高人物的立体感,刻画出更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依然是作者在之后的创作中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不过,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更多地赞叹拙木豪格带给我们的惊喜,作者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丰富的锡伯族历史文化以及深入的文化思考,都使这一部全面展现锡伯族西迁垦荒历史和锡伯族文化的长篇历史小说具有了拓新的意义。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贺元秀.锡伯族文学简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3]郭从远.锡伯族历史的画卷——读长篇系列小说《流芳》[J].新疆作家,1998(1).
[4]拙木豪格.大清锡伯营[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贺灵.中国锡伯族[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6]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7]叶舒宪,冯昌仪.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托马斯·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M].张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9]中国作家协会.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锡伯族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陈 曦]
2017-02-20
2017-05-10
陈思广(1964-),男,新疆库尔勒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小说;孙婷婷(1992-),女,四川达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2YJA751003)
I106.9
A
2096-4005(2017)03-00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