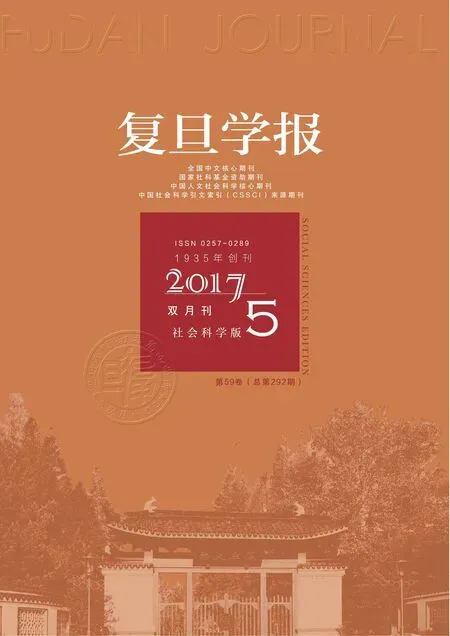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智性?
——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一
杨泽波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中国哲学研究
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智性?
——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一
杨泽波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儒家生生伦理学”的建构问题。要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必须解决其逻辑起点问题。在充分借鉴笛卡尔、胡塞尔、唯识宗的智慧后,我将这个起点确定为内觉。所谓内觉简单说就是在伦理学范围内人的一种自我觉知能力。通过内觉我可以觉知到自己正在思考“我应该如何成就道德?”这个问题。根据儒家传统,这种思考的功能即为智性。有了这个发现,暂时不需要其他条件就可以证明我有智性的功能了。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内觉先于智性,只有内觉才能成为这门学说可靠的逻辑起点,而不能反过来以智性自身来替代这个重要角色。这样我们便解决了这门学说的逻辑起点问题,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儒家生生伦理学 内觉 智性
在相继结束了孟子研究和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后,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儒家传统伦理学说的转型问题,并将这种初具雏形的学说叫做“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这种新型学说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在充分借鉴笛卡尔、胡塞尔、唯识宗的智慧后,我将这个起点确定为内觉。这个话题涉及面很广,本文先从智性说起。*除此之外,儒家生生伦理学的逻辑起点还有如何面对欲性和仁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我另有专文《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欲性?——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二》、《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仁性——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三》(均将近期刊发)详加讨论,敬请关注。
智性在学界一般统称为理性。虽然宋明理学非常重视“理”的问题,但理性一词却无疑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特别是康德之后,理性明确有两种所指,一是理论理性,二是道德理性。理论理性用于认识论,道德理性用于伦理学。认识论不是儒学关注的重点,儒学从孔子创立之日起,所关注的重点即在道德。在这方面,儒学有一个用语很有特点,可供参考,这就是“智”。“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智在孔子那里特指学习的思想,准确说是指通过学习而成就道德的一种性向。为凸显儒家思想的这个特点,以与西方哲学相区别,本文在讨论儒家相关思想的时候,使用智性的说法,而不泛称理性。*我选用智性这一说法还有一层考虑。在西方哲学中,感性与理性两分是一个常见的模式,但在儒家思想中这种模式并不适用。我一贯坚持主张,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日起,就没有沿着这种感性、理性两分的路线走,而始终坚持欲性、仁性、智性三分的格局。如果再用理性这一说法,不容易将儒家这一思想特点凸显出来。参见拙著:《孟子性善论研究》(再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一、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三种不同内涵
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伦理学问题,中心话题理当是“我应该如何成就道德?”。面对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中一般的回答是:我有理性,运用这种能力可以发现和制定道德法则并按照这些法则去做,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学者往往都是这样做的,屡见不鲜。
儒家生生伦理学不接受这种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在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便把它作为前提暗中确定了下来,有独断之嫌。它至少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如何知道自己是有理性的?或许人们会说,我有理性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我承认我有理性是一个事实,也承认这个事实的可信性,但我更加关心的是,我是怎样得到这个事实的?或许人们还会说,我有理性这个结论是通过逻辑推论得到的。比如,人有理性,我是人,所以我有理性;或者,能够思考“我应当如何成就道德?”问题的人是有理性的,我能思考这一问题,所以我有理性,等等。我并不排除逻辑推论的力量,也不否认这种推论的真实性,但坚持认为,在逻辑推论之前必须将其前提弄清楚。如此说来,确定我有理性这个问题包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远非如一般想象的那样简单。
这方面笛卡尔的思想对我有很大启发。笛卡尔是历史上第一个正视这一问题的哲学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成为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经过漫长的中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哲学家们纷纷回归古希腊,希望能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重新建构形而上学,以至于整个17世纪都可以称为“形而上学的时代”。要完成这一伟大工作,自然离不了科学的方法。当时的哲学家们对哲学方法都抱有很大的兴趣,笛卡尔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笛卡尔认为,日常生活中经常夹杂着一些模糊的语词和观念,在科学领域探求真理,不能使用这些模糊不清的东西。真正的科学知识、真理性知识必须具有确实性,而这种确实性特指一种明晰性。为此,笛卡尔运用怀疑的方法将那些不确实可靠,不清楚明白的东西统统排除在外,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以此作为其哲学思考的阿基米德之点。这一命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黑格尔对此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盛赞笛卡尔“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了这个基础上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四,北京:商务钱书馆,1981年,第63页。
尽管“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十分重要,但这个命题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乃至严厉批评。在一些人看来,“我思故我在”是一个直言三段论,即:
所有思维着的东西都存在,
我思维,
所以,我存在。
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在这个直言三段论中,大前提有瑕疵,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所有思维着的东西都存在。即使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大前提也仍然只具有经验总体化的意义,且不说要确定这个大前提首先还必须厘清什么是思维、什么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另有一些学者不将“我思故我在”理解为直言三段论,而视为假言三段论,即:
如果我思维,那么我存在。
我现在思维。
所以,我存在。
这种理解同样难以达到圆满。按照假言三段论的要求,前提中至少应有一个全称判断,但这里的前提全部是单称的。从假言三段论的要求来看,这个推理有同语反复的成分。即使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这里仍然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比如,如何从内容上论证这个被隐含的大前提?什么是我思维?什么是我存在?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如果将“我思故我在”视为一种推论,则很难符合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认为,作为最确实知识的第一原理必须满足两个要求:第一,必须是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真理;第二,必须是没有前提的,不依赖于其他知识,其他知识则完全依赖它,以至于可以离开其他知识来单独理解这个原理。既然“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那么它必然没有前提,无论将其理解为直言三段论或假言三段论,都与这一原理不符。
于是,更多学者提出“我思故我在”不是一种推论,而是一种直觉的结果,并在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中找到了根据。在那里笛卡尔这样写道:
当有人说:我思维,所以我存在时,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看出它来的。从以下的事实看,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他是从一种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他就要事先认识这个大前提:凡是思维的东西都存在。然而,相反,这是由于他自己感觉到如果他不存在就不能思维这件事告诉他的。*笛卡尔著,徐陶译:《第一哲学沉思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译文参考汪堂家译法做了改动。
按照笛卡尔的思路,获得必然的知识有两条途径,一是直觉,一是演绎。演绎依赖直觉,直觉则不依赖演绎。一切先天的真理和自明的公理作为推论的前提都由直觉发现。因此,“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原理的基础是直觉。只有被直觉把握到的东西才是最简单最确实的,同时也是最清楚最明白的。它不需要别的东西给它提供证明,自身即是证明。*汪堂家:《“我思故我在”新探》,《学术月刊》1989年第6期。其后作者将此文移入《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一书之中并作了相应的修改。参见汪堂家、孙向晨、丁耘:《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59页。
笛卡尔这一著名命题出现上述不同理解,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思”有不同的含义。据学者研究,“我思”这个重要概念“在笛卡尔那里原则上可以划分出三种‘思维’类型:1.对思维的‘直接的认识’或‘直接的意识到’;2.思维本身;3.关于思维的反思的认识。”*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5、54页。换言之,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的“我思”包含着三种不同的义项:第一,我在思考;第二,我感知到我在思考;第三,对前两种情况进行再思考即反思。第一个义项是这种思维本身,第二个义项是我意识到我在思维,第三个义项是对这种思维本身,以及我意识到我在思维这两种情况进行反思。遗憾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理解忽视了第二种义项。倪梁康的分析点出了问题的要害:“从以上两处可以看出,笛卡尔本人并不认为,对‘我思’的知道只能借助于反思这个途径。相反,除对‘思维’的‘反思认识’以外,他还提出另一种直接认识,并将对‘我思’的知道建立在这种对‘思维’的直接意识到的基础上。这种‘直接的意识到’先行于反思的认识,它可以说是‘思维’在进行时对自身及其过程的直接意识到。这里的潜在涵义就在于,‘思维’并不需要依靠以后补加的反思才能确认自身的存在;反思的无穷递推在这里并不是唯一的结局。据此我们可以将笛卡尔的答辩概括为:对‘我思’的确定并非通过一种‘反思的认识’,而是通过一种‘直接的认识’。”*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5、54页。
于是,情况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我思”包含三种不同含义,所以对“我思故我在”应该从三个方面做具体的分析。其一,我正在思考,所以我存在;其二,我感知到我正在思考,所以我存在;其三,我对我正在思考、我感知到我正在思考这两种情况加以进一步的反思,所以我存在。如果我们只以第一种情况来理解笛卡尔这一重要命题,势必掩盖这一命题的后两种含义。同样,如果我们只以第三种情况理解笛卡尔这一命题,又容易忽视这一命题的第二种含义,从而造成这样一个理论难题:我需要在确定一个对象存在之前就对其进行反思。因此,重视这一命题的第二种含义尤为重要。按照笛卡尔自己的说明,“我感知到我在思考”是通过直觉进行的,这种直觉是一种自明的东西,不需要其他证明便可以证明“我存在”。这一思想意义十分深远,它告诉我们,一方面我在思考,另一方面我可以通过直觉感知到我在思考,而这种我感知到我在思考并不需要事前通过推理加以证明。通过这种直觉,即可确认“我在思考”,进而确认“我存在”,并将此作为整个哲学的起点。
二、 胡塞尔现相学内意识概念的意义
从直觉的角度探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哲学意义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只是到现相学*在中国文化的语汇中,象与相是两个不同的字。与西方“Phaenomena”相对应的当为“现相”,而非“现象”。与之相应,现在通常所说的“现象学”,准确说当为“现相学”。详见拙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三卷·存有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兴起后才充分被人们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非胡塞尔莫属。
现相学的创立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事件。抛开那些极其复杂的术语,意向性始终是现相学的中心概念,无论这里所说的现相学是指胡塞尔早期的描述心理学,还是指他后来的先验现相学。布伦塔诺首先将“意向的内存在”引入近代心理学之中。这一概念在布伦塔诺那里主要用来规定与物理现相有本质区别的心理现相。心理现相的标志就在于其与一个内容的关系,即一种在自身中意向地含有一个对象的现相。胡塞尔的思想虽然后来与布伦塔诺有了分歧,但意向性作为现相学的核心概念,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在胡塞尔看来,意向总是指向一个对象的,即“意识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个被指向的对象即为“意识的相关项”,因此,意向性“便是指意向活动与意识相关项之间的相互关系”。*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52、253页。“意向性既不存在于内部主体之中,也不存在于外部客体之中,而是整个具体的主客体关系本身。”*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52、253页。被意向指向的对象,就是通常所说的现相。整个世界都是意向指向的结果,而这个世界也就是现相的世界。
在胡塞尔现相学的复杂系统中,我特别关注其内意识的思想。内意识在胡塞尔那里有多种称谓,如内感知、原意识、自身意识,等等。为了不使概念过于繁复,特别是为了与儒家哲学术语相对应,我统一用“内意识”这个说法。*倪梁康更喜欢“原意识”这一说法,见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第390页。按照胡塞尔的理解,在每一个意向行为进行的同时,行为者对此是有所感知的,即他可以感知到他正在进行这个意向行为。换言之,在胡塞尔看来,行为者有一种能力,可以在意向行为的同时,感知到这种意向行为正在进行。这种对意识行为本身的感知始终伴随着意识活动进行,是每一个意向体验的内部因素,意向体验通过这个因素而能够意识到自身。比如,我的意向在指向一棵树的同时,我也感知到我正在进行这种指向。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我感觉到我在看”,“我感觉到我在听”,这些说法已经蕴含着内意识的道理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在认识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不仅意识到认识的对象,而且也意识到认识的行为。例如:当我看一朵花的时候,我不仅意识到一朵花,而且意识到对花的看。当我听音乐的时候,不仅意识到音乐声,而且还意识到听。这里看和听的行为虽然没有被指向,但它们都被体验到(Erleben)或被体认到了(Gewahren)。它们为什么能被体验到或体认到呢?按照胡塞尔,我们的意识活动在对准对象的同时有一种返观自照(Reflexive)的行为,借助于它,我们意识到意向行为本身。”*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关于胡塞尔的“内意识”概念学界研究较多,倪梁康对其特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第394~398页。,其中我特别关心的是前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内意识的主体是意识自己。内意识这个概念中的“内”字首先指明了这个概念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内意识的主体是意识自己,不是意识之外的任何东西。内意识的主体指向自己,说明意识自己有一种能力不需要借助其他力量,即可以意识到自己。如果是意识之外的任何东西,那自然就不能称为内意识了。明确意识自己有能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价值很高的判断,可以引导我们对意识自身的特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有助于达成对于人自身的认识。
第二,内意识是当下进行的。从时间上看,这种对意识自身的意识可以被描述为原初的。这里的“原初”是最初的意思,也就是说,内意识是在意识进行的那个瞬间产生的,不是后来补上去的。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表达,即叫做当下进行。胡塞尔在分析内意识特点的时候,多讲“原初的”或“原的”,意在与“后反思”相对照。这就是说,一方面是原意识,一方面是作为“回顾”或“后觉”的反思。我们不否认“回顾”或“后觉”的作用,但在此之前必须肯定意识活动进行的当下,意识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活动正在进行。
第三,内意识必然有其内容。内意识必须有其指向,有其内容,不是空的,否则这种内意识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指向就是正在意识中的意识本身,如我意识到我在看,意识到我在听,等等。内意识最重要的功能就体现在这里。有了这种内容,有了这种指向,行为者才能对自己的意识有所感知。我们重视内意识的一个重要用心即在于,希望借助这种能力把握自己的意识,进而加强对自我的认识。
第四,内意识尚不构成对自身的认识。内意识只是在意识过程中对意识的“直接感知到”,这种感知还停留在原初的水平上,尚不构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说,虽然原意识构成了事后反思的前提,但并不是这种反思本身。“被意识到”还不意味着“被知道”。在现相学系统中,“内意识”只是一种“内觉察”,只是一种直接的“感知”,而不是课题性的“认知”。这就是说,内意识还只是“自身意识”,而不是“自身认识”。“自身意识”和“自身认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自身意识”)只是意识到自身,还谈不上对自身的完整认识,而后者(“自身认识”)才是对自身的一个完整的认识。
由此可见,“内意识”是对于意识活动本身的一种知晓方式。内意识一定与意识活动同时进行,任何意识活动都伴随着内意识。这一思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意向活动同时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意指行为,即意识对于外部对象的赋意活动;另一方面,人能够同时感知到这种意指行为正在进行。虽然事后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此加以证明,但这种证明之前,人已经在那个瞬间感知到了自己的意识活动。这个道理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隐含的意义正相吻合。胡塞尔特别重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正是想利用这个道理来发掘笛卡尔思想的意义。在胡塞尔看来,历史上关于“我思故我在”多从推理论证的角度去理解,并不得法,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在于,一方面我思,另一方面通过内意识感知到我在思。虽然“感知到我在思”需要后来借助反思进一步加以证明,但“感知到我在思”的那个瞬间并不是反思,而是一种直觉。正是这种直觉可以使自己确定“我思”,并进而确定“我在”。质言之,我可以直接发现自己具有思想的能力,尽管在发现这种能力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这种思想是如何发生的,它的运行机理是什么,但我确实感知到我在思想。胡塞尔将笛卡尔这一思想引进现相学,把这种直觉称为“内意识”,对其加以阐发,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内意识”的问题才引起了人们的足够关注。
三、 唯识宗自证分思想的启示
随着现相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虽然“内意识”是20世纪现相学的核心概念,但类似的思想佛教很早就涉及了。
原始佛教产生于对苦的思考。从特定意义上说,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以脱苦为目的的。原始佛教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一切皆苦”后来演变为“涅槃寂静”),明显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依因缘和合而生,没有恒常的本质,没有所谓的自性。人生亦如此。众生皆苦源自人对外物有着强烈的执着,由于执着的对象本身没有自性,随时会因为因缘的变动而消失和分解,使自身陷于不断的痛苦之中。如果能够从这种无明中觉醒,认识到苦的本质,就诞生了觉性,用觉性打破苦的循环,从而从苦海中解脱出来。
围绕这一基本原理,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派别,既有大乘,又有小乘,其中大乘佛教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大乘佛教亦有不同流派,早期最为重要的是空宗。这一派由佛教论师龙树、提婆所创,认为世间一切法皆是因缘聚合而生,空无自性,万物只是唯名假立,故有空宗之名。这一派走向衰微之后,公元4至5世纪,印度佛教论师无著、世新兄弟创立了大乘瑜伽行派,提出“万法唯识”,“识有境无”的观念。龙树主张,“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诸法因缘而生空无自性,但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假名幻有。从缘起方面认识万物的本体为空,从性空方面认识万物假名为有,此即中道缘起观,亦即中观。在龙树看来,利用世俗的名言概念不可能获得诸法实相,必须采用否定的遮诠方法才能达到目的。为此他发挥了佛陀二谛说,主张既要认识诸法的自性本空,又要认识诸法的假名之有,通过世俗谛以通达胜义谛,从而建立了二谛的辩证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相关学说逐渐产生了两个重要概念:见分和相分。见分又叫能取分。见,即见照,能缘之义。从哲学意义上讲,可视为认识、照知相分的那个行为者。相分又叫所取分。相,即相状,所缘之义,为认识之对象,亦即被主体之心所认识之客体形相。在见分和相分的划分中,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见分而构成相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正在见分之中,亦即我们是否知道见分这一过程呢?古代印度哲学在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可以划分为三派:*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7~129页。耿宁(Iso Kern)是瑞士著名现相学家,在海外有较大影响,带出了不少中国学生,张庆熊、倪梁康皆出自其门下。经这些学生的努力,将唯识宗与现相学联系在一起,以唯识宗的自证分解说王阳明的良知,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发展方向。
一是说一切有部派。他们认为,意识意识到它的对象,认识认识到它的对象,但它并不自知,正如一把刀只能切割别的东西,而不能切割自己,一个手指能指向别的东西,而不能指向自己。一个认识活动能被认识到,可是它不能被它自己在当时所认识,只能被一个以后的、另外一个认识活动所认识。
二是数论派。他们认为,认识活动本身并不能意识到自己,这一点与前一种看法相似,但可以通过一种更高级的、超物质性的官能、一种非物质的精神、灵魂或者自我被意识。这种精神性的自我是不变的、永恒的,它作为观察者或见证人,把它的光明照射到物质性的、非永恒性的认识活动上,使它被意识到。尽管这种精神性的自我和物质性的认识活动有根本区别,但它有一种倾向,可以使自己跟这些认识活动相结合,使自己跟它们一致,把它们看作是它自己的活动。
三是经量部和瑜伽派。他们认为,一种认识活动不是通过跟随它的下一个认识活动、也不是通过一种叫做自我或灵魂的超越的官能去认知,而是在自身中被它自己所认知的。仍以前面所述为例,刀和手指可以指向外部的对象,也可以指向自身。这就好比灯,既可以照亮周围的事物,也可以照亮自己。认识活动也是这样,既可以认识其对象,又可以认识其自己。陈那对这个观点做了周密的分析,区分了意识的三种成分,从而使这一理论成为唯识宗的思想基础。
在唯识宗系统中,所有的心法(即八识)、所有的心所有法(比如贪、恨等)不但有一个见分和一个相分,而且有一个自证分。比方说,按照唯识宗,“听见”这种识即包括三个不同的内容:一是听这种心理活动,这是见分;二是所听见的对象,这是相分;三是对这种活动的自知,这是自证分。当我听见一个声音的时候,我不但听见了这个声音,而且此“听见”在这个意识活动中必须被知道,即我知道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这种自知就叫做“自证分”。其义理简要结构如下*这只是一个简表,详表请见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第129页。:
见分 相分
缘
意,意念(意向) 物,事,意之所在
自证分
这一义理结构蕴含着重要意义。因为按照唯识宗的理论,“每一种心理作用,每一种意识活动,比如看、听、回忆、判断、希望等等,不但具有它的看见的、回忆到的对象,而且它也感知到或者意识到它自己。换言之,按照他们的看法,这种自知即知觉,不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不是一种特殊的反思,而是每一个心理活动都具有的成分,是所有意识作用的共同特征,即每个意识作用都同时知道自己。”*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第127页。
唯识宗关于自证分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创见,向我们指明了,意识不仅可以意指一个对象,创立一个对象,而且可以感知到自己在意指。也就是说,意识意指一个对象,而在同一时间也可以意识到这一活动正在进行。这一思想刚好能够与胡塞尔现相学基本义理对应起来。唐初,经过玄奘和窥基以及其门下弟子慈恩一宗的努力,唯识宗有了很好的发展,规模庞大,成为显学,但随后直到明末的八百年间,几乎被教界和学界遗忘。明末有过一段复兴,但清初很快又归于凋零。直到清末民初,唯识学才大体摆脱了沉寂和被遗忘的状态。因为这一思想的内在价值与现相学的义理有相通之处,在海外很受重视,唯识学遂成为一个不小的学术热点。
四、 通过内觉确认智性
前面我们分别分析了笛卡尔、胡塞尔和唯识宗的相关思想。这些思想重点并非完全相同:笛卡尔是为了找到其哲学的阿基米德起点,胡塞尔是为了建构第一哲学,唯识宗则是为了说明中观思想。我把这些内容组合在一起,是因为这些不同理论向我们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人对自己的意识活动有一种直接把握的能力,不管这种能力叫“直觉”(笛卡尔)、“内意识”(胡塞尔),还是“自证分”(唯识宗)。
笛卡尔、胡塞尔、唯识宗上述思想主要集中在认识领域。而我注意到,人在道德领域同样具有这种特殊能力。在道德领域中人的这种特殊能力,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可以称为“内觉”。“内”与“外”相对,特指眼光向内收,而不是向外看。“觉”字含义较广。《说文》:“寤也。”《广韵》:“晓也。”《公羊传·昭三十一年》:“叔术觉焉。”《注》:“觉,悟也。”《庄子·齐物论》:“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大梦也。”又有明义。《左传·文四年》:“以觉报宴。”《注》:“以明报功宴乐。”佛又称为“觉王”。如《旧唐书·高祖诏》:“自觉王迁谢,像法流行。”《魏书·释老志》:“浮屠正号曰佛陀,华言译之则谓净觉。”皆因于此。由此可知,“觉”字一般指醒悟,如觉悟,觉醒,又指人或动物的器官受刺激后对事物的感受辨别,如感觉,知觉。因此,内觉是一种向内的觉悟、觉醒,特指对自己意识活动的一种直接把握的能力。
因此,我关注内觉这个概念,与笛卡尔、胡塞尔、唯识宗有明显区别。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我感知到我在思,所以我在。“我感知到我在思”是一种直觉,这种直觉不需要其他前提条件,所以可以作为其整个理论的阿基米德之点。胡塞尔也是如此,虽然其早年的思想还处于描述心理学的水平,到后来才借鉴康德回到先验哲学的立场,但他希望以此为整个哲学寻到一个可靠基础的愿望是始终一致的。唯识宗则是强调人在见分的同时有一种能力,可以感知到自己正在进行这个过程,以便较好地说明中观思想。无论是笛卡尔、胡塞尔,还是唯识宗,其关注的重点都是认识问题,而我将这一思想引入,关注的主题是伦理道德问题,是为儒家生生伦理学寻找到一个可靠的入手处。虽然光有这个入手处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围绕它做很多工作,但这个入手处本身必须是自明的,不能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它不再需要其他条件,自身就是整个学理的前提。
由此可知,笛卡尔、胡塞尔、唯识宗都证明了自我有一种内觉的能力,在思想的同时,可以感知到自己正在思想,那么依据这一原理我们完全可以证明:一旦我思考如何成就道德的问题,我凭借内觉可以“觉知”(此时改说“觉知”,不再像之前那样说“感知”,主要为了与内觉概念相对应)到我正在思考,就说明我有这种思考的能力,这种思考的能力即是一般所说的理性,也就是我所说的智性。换句话说,当我思考如何成就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觉知到我正在进行这种思考,这本身就足以证明我是有智性的。虽然仅有这一步还远不够,还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对此进一步加以证明*这进一步的工作我称为“内识”。“内识”与“内觉”不同,“内觉”只负责觉知到我在思,“内识”则是对“内觉”的过程和对象进行再认识,以完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关于“内识”概念的具体界定和分析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当另文详述。,但那是事后的事。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我们不需要其他前提,仅凭内觉就可以初步证明我们是有智性的。
当然,有人可能对此提出质疑。他们会说,你以内觉确认智性,希望以此作为儒家生生伦理学的入手处,而你对内觉的证明却是借助笛卡尔、胡塞尔以及佛教唯识宗进行的,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入手处还不是真正的起点。对于这个质疑,我想做这样的答复:为了证明人有内觉的能力,我确实借助了笛卡尔、胡塞尔和唯识宗的智慧,但这只是一种事后的理论说明。而我觉知到我有内觉的能力,觉知到我正在思考“我应该如何成就道德?”的问题,以此确认我有智性的能力,并不需要这个过程。这就是说,通过自身具有的内觉能力,我即可以将自己有智性这个事实确定下来了,借助一些学派的思想对内觉加以说明,只是为了在理论上加强论说的力量,把问题说得更明白,更便于理解而已。
总之,通过回顾笛卡尔、胡塞尔和唯识宗的相关思想,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在伦理学范围内人同样有一种自我觉知即所谓内觉的能力。通过内觉我们可以觉知到我在思考“我应该如何成就道德?”这个问题。根据儒家传统这种能力即为智性。有了这个发现,暂时不需要其他条件就可以证明我有智性的能力了。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内觉先于智性,只有内觉才能成为这门学说可靠的逻辑起点,不能反过来,以智性自身来替代这个重要的角色。
HowtoAffirmOurIntellect:TheThinkingofLogicalStartingPointofSheng-shengEthicsofConfucianism
YANG Ze-bo
(College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ng-sheng” ethics of Confucianism.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must be located for the work. Having been enlightened by Descartes, Husserl and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decided to set it as inner perception, which could be simply interpreted as a kind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realm of ethics. Through inner perception, we can percept that we are thinking on the problem of “how to become a moral person.” In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this function of thinking is regarded as intellect. Therefore, it proves that we have this function unconditionally. In the system of “sheng-sheng” ethics, inner perception is prior to intellect, and thu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s supposed to be inner perception.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pens the path to the overal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sheng-sheng ethics of Confucianism; inner perception; intellect
[责任编辑晓诚]
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