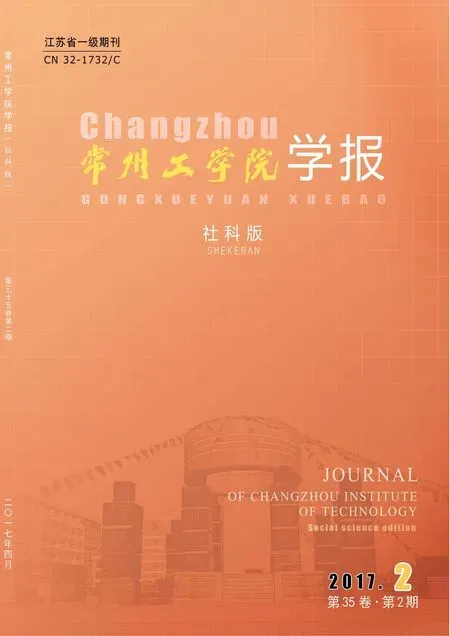从成语视角看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叙事设置
钱亚玲,陆克寒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从成语视角看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叙事设置
钱亚玲,陆克寒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文章从汉语成语“倾城倾国”的语源和语用角度,结合文本的细读,探析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叙事设置。张爱玲通过演绎一个现代“倾城”的“传奇”,表达了她对诸多历史“倾城倾国”事件的质疑,对古老的“红颜祸水”思维定势的颠覆,也正是通过这一艺术化的解构过程,张爱玲表达了她的现代女性观。
成语;倾城倾国;叙事设置
谈到语言在社会生活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现代小说名家张爱玲曾有过文学性的表述:“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织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①她特别提及成语与现代中国人的亲密关系:“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接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②“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小说创作见长的张爱玲显然也是运用现代语言的大师,对汉语的拿捏纯熟,老到。不难发现,在张爱玲诸多现代“传奇”叙事中,作为汉语语汇精华的成语被频繁地运用,俯拾即是而又精彩纷呈,鲜活又恰到好处。
作为文化的载体,成语素有中华文化“活化石”之称,生动形象地折射了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在运用民族语言从事小说创作时,得力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积淀、西方文化的吸纳滋养和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对照,张爱玲对汉语语言尤其是成语的理解、引用和演绎,也鲜明地折射出张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发表于1943年9月的中篇小说《倾城之恋》堪称其中的经典实例。这个文本较之张爱玲其他小说,至少有三点非同寻常。第一,它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但当时受到著名翻译家兼文艺批评家傅雷先生较为严苛的批评。第二,张爱玲几近同时(亦即1944年)又将它改编为四幕八场话剧,并于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演,映现了张氏本人对这部小说的厚爱。第三,故事以大团圆的喜剧形式收场,这在以“苍凉”为底色的张氏小说叙事中实不多见。不过在我们看来,这篇小说还有一处意外,在于结尾: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不知张爱玲是担心读者疏漏,还是低估了读者的理解力,作了一番本该略去的絮叨,多少有损文本的余韵。我们认为,正是作者的“画蛇添足”,导致这个结尾未被充分地释读,成了“显在”的“盲区”,通过这些貌似“多余的话”,张爱玲分明在强调自创的“倾城”与历史上“倾城倾国”史实的关联与对照。回归文本可以发现,张爱玲意欲通过演绎一个现代“倾城”的“传奇”,表达她对历史上“倾城倾国”事件的质疑,对古老的“红颜祸水”思维定势的颠覆,也正是通过这一艺术化的解构过程,张爱玲表达了她的现代女性观。
一、成语“倾城倾国”语源与释义
《倾城之恋》篇名出自成语“倾城倾国”。《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意谓有才的男子可称霸王,有才的女子使国覆亡,妇人有才便如枭如鸱,花言巧语善于说谎。祸乱不是天降,而是出自妇人一方,也不是他人的教诲,只因贴近女子红妆。整首诗歌讽刺周幽王宠幸褒姒,荒政灭国,这是“倾城”一语的最早出处。
汉代班固《汉书·孝武李夫人传》记载,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因为爱悦佳人之深而使得城与国倾覆,后人自此便用“倾城倾国”一词形容女子容貌的绝美。又据班固记载,汉武帝听罢李延年之语感叹:“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告诉他,李延年的妹妹正是这样的一个绝代佳人,于是,“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这位受宠的美人便是后来被尊为孝武皇后的李夫人。
汉代袁康所作《越绝书·外传计倪》亦云:“祸晋之骊姬、亡周之褒姒,尽妖妍于图画,极凶悖于人理。倾城倾国,思昭示于后王,丽质冶容,宜求监于前史。”古人显然极其重视历史教训的归结,最后达成共识:泱泱邦国的倾覆,多与女子尤其是妖妍的女子相关,她们貌美,但通常心狠手毒,不恪守人伦,故面对绝色的女子,无论君臣都要以史为鉴,免蹈历史的覆辙。然而,历史偏偏总以相似的面目轮回,继骊姬、褒姒之后,有西施之于吴王夫差,貂蝉之于董卓,杨玉环之于唐玄宗李隆基……,男人们断送了江山伟业,古人进一步归纳,得出更为明确的论断:红颜乃祸水也。检视中国的社会历史不难发现,从骊姬到杨贵妃,这些绝美的女子,几近个个身败名裂,背上了耻辱的骂名。
从“倾城倾国”的语源以及后人使用的情形,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三点。第一,中国人不论男女,自古便对女子的外在美有着感同身受的体认。第二,在古人的理念中,何种女子谓之美?首先要经得住视觉的检验,要有闭花羞月、沉鱼落雁之貌,然而仅外在好看还不够,假如内里有才华有技能,譬如能歌善舞,精通音律,或能说会道,才是风华绝代。第三,绝美的女子多巧言令色,每每使帝王耽溺其间,轻则肾虚体亏无力朝政,重则乱政而误国,最终导致国家覆灭。由于女子美貌潜伏着危险,具有杀伤力,出于恐惧心理和警戒的意图,古人便用“倾城倾国”指代女人的绝色,直陈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今人看来,古人貌似合乎逻辑的推断,其实是经不起论证的,他们借以推断的事例仅为历史长河中的个别和偶然,美颜与政权大厦的颠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更何况在一个女性历来被“消声”的男权专制社群。将家国的倾覆毁灭归于“红颜”之罪,不仅有失公正,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社会中心地带男人担当意识的缺席和主体意识的萎缩。
二、白流苏:寡妇再嫁
张爱玲《倾城之恋》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同步行进,城邦与家国正处于倾覆之中,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中国,从北到南由东向西,一路沦陷,爱情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惶惶的动荡背景下。动荡慌张的乱世背景的设置,初步显露了张爱玲意欲背离传统“倾国倾城”故事模式。
故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亦非风华绝代,从传统世俗的角度看,白流苏不过是个寡妇,张爱玲要讲述一个寡妇再嫁的故事。小说伊始的“报丧”情节,显示了女主人公生存现状的不容乐观——“离婚”而后“返家”,她的家是一个跟不上时代弥溢着腐味暮气的旧式家庭。毋庸置疑,在男权中心的家长制家庭,“失婚”对女子又意味着事实上的“失家”。白流苏离婚的主因是丈夫“当初有许多对不起”她的地方,“两个姨奶奶”的存在,让白流苏守着“活寡”。现在,前夫死了,本应和她无关,但是,兄嫂所坚守的“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一致认为流苏“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离异后的流苏成了真寡妇。俗世的经验表明,一个待字闺中相貌平常的女子要嫁人几乎没有难度,一个漂亮寡妇再嫁也没有太多困难,是寡妇又长相一般且生于乱世想要再嫁,难度就非同小可。小说标题给了读者无比美好的阅读期待和跨越时空的艺术想象,而事件的核心人物的身份却如此平凡、低微,乃至“另类”。张爱玲显然有备而来,铆足劲要讲述一个现代版的“倾城倾国”传奇。
“离婚”,折断了白流苏通往未来人生的理想翅膀,而现实又不予她立足之地,浮在半空的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然而,白流苏的“心虚”,不仅缘于现实中无定位,生活上缺乏物质长久的支撑,更在于“离婚”女子的心理禁忌。小说借四奶奶之口,传达了现世社会对失婚女子和寡妇们的成见:“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离婚”成了“不吉不祥”“不洁”的代码,白流苏听后“气得浑身乱颤”,表明在心理上她难以逾越这一传统的恶俗陋见。离婚,寡妇,不复年轻,“又没念过两句书”,白流苏的人生将从这里重新开启,张爱玲的故事打这儿开场,这场倾城的恋爱该何去何从?小说一开始,观者就得屏气凝神,张爱玲不愧是讲故事的高手。谈到写小说,张爱玲曾直陈:“是个故事,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就是磨难,就是麻烦。”④距离历史上“倾城倾国”的标杆越遥远,预示即将到来的磨难越深重,白流苏得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一路披荆斩棘方能杀出一条生路。
事件的进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白流苏最后收获了婚姻,成了华侨商人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子。顽固的遗老遗少与现代洋派,半老的寡妇和年轻的商人,熟悉的故土与陌生的香港,这些参差的对照,着实迷离了人们的眼睛。然而在小说中,事件的进展又如此地合情合理。梳理白流苏经历的各种磨难,她的圆满归结于作家张爱玲设置的两个关键点:其一,和范柳原初识时的共舞,其二,香港周旋之际心智的发挥。这两个关节点的设置,既折射出张爱玲对历史上诸多“倾城倾国”故事某些质素的扬弃,又传达出作家主体的现代女性意识。
范白之恋发于白流苏陪妹妹与范柳原相亲,为了敷衍面子,白流苏和范柳原跳了几次舞而为范柳原所注目,妹妹的亲事由是告吹,被众人目为败柳残花的白流苏进入公众视野,在此,技艺打败了年龄,外形屈服于质里,这与历史上的倾城绝色形成了某种遥远的回应。骊姬、褒姒、西施、李夫人、赵飞燕、杨玉环,无不能歌善舞,乃至身怀绝技。以现代眼光观之,这些绝色的美女,原来都有一技之长,而不只是瓷质“花瓶”。面容姣好的女子天下有的是,为何独独她们成了帝王将相身旁的宠儿?古人崇尚母仪天下,显然强调的还是举止的风范。如是看来,单凭“红颜”便定为“花瓶”“祸水”,未免武断,实在是委屈了历代的美女子,也低估了历代帝王的治国用人之道。历史证明,女子欲立足社会,尤其欲立足于男权中心社会,核心要素是内里,靠才艺。历史的发展同时证明,女性的才能于人类物种的繁衍和社会文明的演进意义非凡。故张爱玲于20世纪40年代毫无掩饰地说:“女人取悦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⑤与其说这是女性的自白自赏,毋宁说是张爱玲对男权中心社会的揶揄和警醒。
即便如此,“女人无才便是德”的女性观代代相承,女性的才能,自古被历史歪曲,搁置,蔑视。白流苏仅因能舞,抢了妹妹的风头,搅黄了一场媒妁之约,在兄嫂看来便是“失德”。事实上,白流苏的舞技显然还不足以赢得范柳原的倾心,对于一个留过洋的新派人物,见识过的“舞女”实在太多,譬如,小说中的配角——印度女人萨黑荑妮便是一个舞林高手。白流苏征服范柳原的杀手锏是智慧,女性的智慧——在社会边缘和屈辱生活中累积的生存经验、人生见识和观世心态。女性的智慧向来被男权中心社群所无视,即便沐浴着现代科学文明之光,女性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仍遭低视,傅雷批评《倾城之恋》的缺陷在于“两个主角的缺陷”,认为他们都是“浑身小智小慧的人”,尤其是白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⑥。傅雷显然疏漏了一个常识,人类的智识包括书本知识最终源自生活经验和人生的历练,白流苏固然不是腹有诗书的女子,但离婚、返回母家、遭兄嫂撵赶等各种人生逆难,于白流苏等无数传统中国女性都是磨砺,更是心智的沉积,只是在一个歧视女性历史悠久的社会,女性的智慧连同女性的身体,被无情地遮蔽,更被残忍地剥离。
换言之,在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前,徐娘半老的白流苏比待字闺中的妹妹们更沉稳、老到,也更有胆识与勇气。张爱玲为白流苏设置的赴港之旅,较为逼真地呈示了一个被逼到生存绝境的女子双手辟开生死路的决绝与勇猛,在所谓“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⑦中,张爱玲透过细腻的人物心理活动,呈现了传统中国女性在历史积压之下练就的生存智慧,它们无疑是“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⑧,自然免不了有些扭曲与畸形。
三、范柳原:浪子回归
原本,一个女子的容颜和国家的倾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用“倾城倾国”的狼藉和危重来赞誉一个女子的美色,实在有些荒唐,但古人又云“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两者发生关联和缠绕,一是借助女子的巧言,二是靠男人的倾听和吸纳,说者和听者都不可或缺。纵览中国社会历史,从骊姬、褒姒,到赵飞燕、杨玉环,个个擅长在帝王耳旁“吹枕边风”,从商纣到唐李隆基,个个又都是“听话”的君王,于是悲剧便发生了。中国古人用“倾城倾国”的废墟之象,警示后人红颜所招致的骇人图景,流露出强烈的谴责之意,看似惊叹女性的绝美,暗含对女性的讽刺和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才是掌握历史走向的核心质素,而将国家政体的倾覆和毁灭归咎于女子,实质上抹煞了无能的覆国之帝本该承担的历史罪责,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绝对的男权中心地位及其对女性的凌辱与歧视。无数的史实证明,女性在长期的历史积压中,不仅塑造了自身,强健了心智,还凭借生命的本体特质和才智影响,改造乃至净化了男人及其世界,成为拯救父权社会的无形之力。历史上固然存在家国社稷因“红颜”而倾覆之诸多偶然,但又存在凡夫俗子因“红颜”而建功立业之现象。“浪子”在“红颜”的影响下脱胎换骨,皈依人生之途,是张爱玲诸多篇什演绎的又一主题,《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这一人物形象,正体现了作家张爱玲这一现代女性意识。
在张爱玲文坛知己苏青看来,范柳原只是“一个华侨的少爷,嫖赌吃喝样样都来……”⑨,苏青的评价有失全面,吃喝嫖赌、玩世不恭只是其表象,确切地说,范柳原本质上是一个自暴自弃的浪子。范柳原没有归宿,但与白流苏的“失婚”导致“失家”不同,他的心结与隐痛是“无家”和“无国”所致的无根浮游状态。首先,他是个“无家”的“弃儿”。范柳原是父亲与一位华侨交际花的庶出,依照中国人传统,他仍是范氏家庭的一分子,在法律上仍有继承权,但由于族人的报复思想与敌视的态度,范柳原自小在英国长大,及至而立之年,依然得不到族人的认同,所以,范柳原丧失了作为男性所拥有的对于“家”的绝对占有权。其次,范柳原又是一个“无国”者。在中国人视界中,范柳原寄居英伦多年,是位地地道道的“洋派”人物,“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其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思维方式都很难被中国旧式家庭所认同,而另一方面,无法更改的外形气质、性格嗜好,又使范柳原难以被外族所接纳。如同无根的浮萍,范柳原四处流浪,“无家”“无国”的双重失落,显然给予他很深的内心创伤,放浪形骸的生活便是发泄情感的一种表征,当然,土生土长的中国妇人白流苏根本无从体认他“家国认同”的焦灼和思想意识的危机。在小说设置的多个范白两人对话场景中,范柳原文雅而高深的言语在白流苏听来莫名其妙,与其说这样的情境彰显了白流苏“骨子里的贫血”,毋宁说这是张爱玲为其男性主角精心设置的独语舞台,藉此展览一个漂泊浪子内心的迷茫、困惑与期盼。
家国认同的缺失,既造就了范柳原“浪子”的身份,又使他与人交往时难有诚意和责任意识。与白流苏交往之初,范柳原潜意识中,便欲将白流苏变成他众多情人中的一分子,那么,是什么促使范柳原由最初狎玩到后来庄重心理的逆转?吸引范柳原的是白流苏“那一低头的温柔”,白流苏这个充满个性特质的小动作,暗合了他想象的中国女性独有的风韵与魅力,换言之,范柳原眼中的白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她点燃了范柳原家国认同的欲望之火,强化了其民族认同感,范柳原要借助这个真正中国女人实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认同。
白流苏并不是图画上妖妍的画像,亦非美丽的幻影,她是实在而平凡的。前文已述及,白流苏离过婚,守着寡,被目为枯枝败柳与不祥的灾星,比照异国摇曳生姿、性感年轻的萨黑荑妮,也没有惊艳的外表,但中国女人白流苏有的是本分和内敛,优雅和谨慎,她恪守着传统的忠贞,执着于安稳的家庭生活理想。她外在柔弱而内心隐忍、坚毅,充满智慧。她又很勇敢和无畏,为了婚姻和家庭可以孤注一掷甚至生死不顾……白流苏身上呈现的中国传统女性的特质给变动不居、内心孤傲的范柳原未曾有过的踏实、温暖与亲切,使他对人伦关系和现实生活有了新的体认。正是白流苏,使飘浮的范柳原回归自己的家园,也是白流苏,使范柳原回归了平凡而健康的日常生活,开启了未来人生的行程。
故事圆满收场,但“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这是传统女性普遍存在的自视盲点,这无疑也是女性经年被遮蔽置于边缘、被“妖魔”化的历史之必然。然而,张爱玲是清醒的,她用文字还原出日常的真实和女性存在的真实:有多少白流苏似的女子将范柳原样的男人从昼夜颠倒的无序带进有序的日常,把放浪形骸的男人从自我放逐中拯救出来。什么比拯救一个男人的灵魂更有意义?又有什么比促使一个男人向上向善地生活更有价值?拯救,无疑是女神之举,不能无视女性的拯救之力和存在之美。庆幸的是,古今中外的不少文学经典,都曾观照女性的拯救之行,张爱玲当属其一。检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只有强壮、安静、踏实、充满母性的地母才是最美女神,因为是她拯救了大地,象征了重生和希望。
四、结语
与其说是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不如说是白流苏向死而生的决绝、勇猛和智慧感动了港城,以自身的陷落铭记一场跨越时空的恋情,纪念一位平凡女性的神奇与一个浪子的回归。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运用特定的人物、情节设置等叙事手段,对传统世俗的“红颜祸水”女性观进行了一次合情合理的颠覆,艺术地揭示历史上“倾城倾国”乃“红颜”之过的荒谬不实,很显然,张爱玲最想表达的还是:女性的价值和美取决于女性的才智,有才智的女性不仅能解放自己,还能拯救这个世界中堕落的男人和男人的世界。
注释:
①②③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2页,第22页,第22页。
④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⑤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⑥⑦⑧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13页,第411页,第411页。
⑨苏青:《读〈倾城之恋〉》,《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64页。
责任编辑:赵 青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02.014
2016-09-11
钱亚玲(1968— ),女,副教授。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SJD516)
H136.31;I206.6
A
1673-0887(2017)02-005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