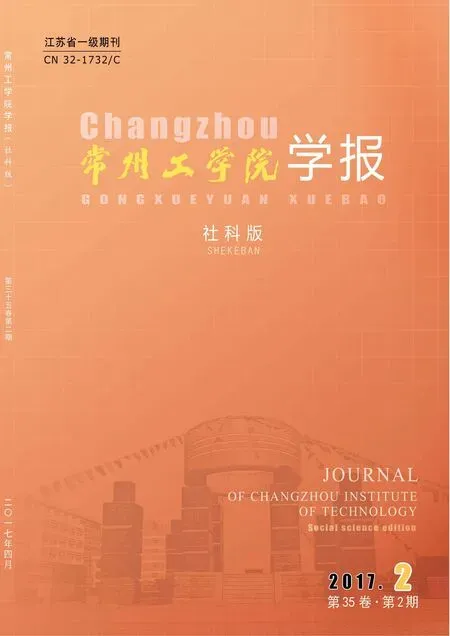城乡冲突下的退与进
——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青年形象的精神轨迹
吴玲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4)
城乡冲突下的退与进
——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青年形象的精神轨迹
吴玲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辽宁沈阳110034)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一个社会急遽变动的时期,也是文学创作日新月异的时期。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政治和经济的拨乱反正给文化的自由与繁荣带来了新的生机。在这个时期,一大批迥异于此前作品人物的青年形象开始出现在作家的笔下,他们以自己的悲欢歌哭为我们再现了那个大转折时代的青年的成长轨迹与心理症候。以路遥的《人生》为起点,作家们通过这些青年形象对当时城乡之间的矛盾倾注了热切的关注,同时,也通过青年人物对城乡不同的人生选择表达了自己对于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态度,相应地,也折射出乡村在城市现代文明挤压下日渐溃败的时代主潮。
城乡矛盾;知青“返乡”;农村青年进城
有研究者称“城乡划分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显著特点”①,城市与乡村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生成着迥异的价值和美学观念。从最初的农村包围城市,到以城市为中心,直至“以工促农,以农助工”的发展政策,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民进城务工,到农村开展招商引资、开办乡镇企业等,城乡的交流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二者的冲突与融合也“成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有效的视角”②。这种冲突与融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多个侧面,如路遥所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③对于这些矛盾与冲突、交流与融合,当代作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也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描述与展示,并且在文本中塑造出了一大批在城与乡的冲突与融合中挣扎奔突的青年形象。如在1982年发表的《人生》中,路遥就以高加林这一“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想象给了全社会振聋发聩的一击,而高加林为城市梦想的奋斗及这一梦想最终的破灭,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的精神轨迹恰可成为我们研究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青年形象精神内涵的切入口。以此为原点,并参照20世纪80年代具体的创作实绩,本文将当时涉及“城乡问题”的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大致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乡村返回城市后由于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人生意义,又重新返回乡村的青年。从作家作品来看,这一类多是“文革”后的“返乡知青”。第二类是面对城市对于乡村所具有的诱惑力而固守着传统观念的青年,他们或许认识到了现代城市文明对乡村传统观念所具有的冲击力,但他们仍选择留在农村,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第三类青年清醒地认识到城市文明的优越和乡村传统的落后,他们渴望摆脱落后而愚昧的乡村,热烈地追求着现代、先进的城市文明,渴望着能以进城作为改变个人命运的起点。
一、“返乡知青”的乌托邦幻想
“文革”结束后,知青们最终得以返回“故乡”——城市。然而,在这“故乡”,他们却再次遭遇人生的幻灭与迷惘,城市的污浊,人性的溃散等等,理想再次被延宕。在返回城市之后,返城知青们在阔别十年之久的城市遭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失落,重新归来的他们惊愕地发现,城市早已不是身处乡村的他们想象中的迦南美地,城市里乃至有着至亲血缘的家庭里也不再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在城市中,他们处处遭遇挫折,时时生活在苦闷之中,他们似乎变成了被流放于城市之外的“多余人”,他们无路可走。凡此种种,都促使他们对“上山下乡”时的乡村原野乃至山区生活产生了无尽的怀想与回味,他们开始怀念农村社会里温馨质朴的传统乡情、纯真和谐的传统伦理道德,他们不得不逃离城市里让他们不满意的一切而重返乡村。在这种怀想、回味与重返中,包含了这批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青年们对自己逝去的青春与理想的怀恋与追寻。如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孔捷生《南方的岸》中的易杰与慕珍等。
王安忆在《本次列车终点》中刻画了一个男知青陈信,返城之后,陈信面临的是工作的不顺意,是家人冷嘲多过热情的窘境,他不能继续留在城市,只能怀着“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④的幻想乘着“本次列车”再次流浪。无独有偶,在《南方的岸》中,易杰、慕珍和阿威返城后工作问题并未及时落实,为了生存,他们共同经营了一间“知青粥粉铺”,生意尚可,他们本可以此谋生。但在易杰看来,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各种利益纠纷中仍坚持着浪漫的理想。而这种坚持也很快被打破了,麦老师以及“知青工友”的变化,是他始料不及也不能接受的,而慕珍更是在父母姐妹的咒骂声中成为冷漠家庭的“多余人”。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方的岸”,那里有着他们青春的爱和记忆,理想和激情。但是,无论是对于陈信,还是易杰、慕珍来说,此番返乡注定无效。那即将踏上的乡村是只能想象而不能再次经验的幻想中的乌托邦。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于再次返乡的知青们来说,时过境迁,他们的返乡只能是一次想象中的跋涉,他们再也不可能走在十年前的那条路上,也不可能再遇见十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当年易杰和慕珍们挥洒汗水甚至牺牲生命种植的那片胶林如今已经成片成片地枯死了,而王安忆甚至都没有给陈信的“本次列车”设置可行的终点站。
对此,作家韩少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创作于1985年的小说《归去来》⑤,主人公黄治先在一次访友的途中鬼使神差地进入一个破落的村庄,虽未曾相遇却似曾相识,而且他也被村里人误认为是知青“马眼镜”,被询问各种相关的人与事,他疲于应付。此时,历史在他眼前呈现出多重面目,而这历史所带来的熟识感又让他唯恐失去自我、陷入迷障。面对这不能合理阐释的遭遇,他选择了不告而别,逃回城市。黄治先的仓皇出逃似乎打出了一手反牌,当作家们纷纷将回城之后百般受挫的知识青年以各种方式“遣返”乡村时,韩少功却道出了乡村对他们的拒斥。也就是说,黄治先逃离乡村并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在乡村社会独有的社会伦理和生存哲学面前他无力融入,最终被无情驱逐。
二、“乡村留守者”的现代失落
李杭育在《最后一个渔佬儿》里塑造了一个固执地坚守着传统文化伦理和生活方式的“葛川江上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柴福奎,“他每夜都数那一溜街灯,却从没数准过究竟是多少。他对这些街灯很感兴趣。……如今西岸这富丽堂皇的气派,委实叫人着迷”⑥。虽然他心里热爱着现代化城市里的一切,但他仍然守在住了一辈子的葛川江,守在那污染越来越严重,甚至连一个钓钩都买不到的地方——对于柴福奎这个渔佬儿来说,“死在江里,就跟睡在那荡妇的怀里一般,他没啥可抱屈的了”⑦。然而,并不仅是这个老人固执地不愿走进城市而宁愿死在落后而守旧的渔船上,在一些小说中,如陈忠实的《枣林曲》、魏雅华的《丢失的梦》和贾平凹的《他和她的木耳》等,青年主人公不但在进城的路上一步一回头,最终甚至反身重新回归了农村。不同于陈信和易杰等人,在另一些作家如陈忠实和魏雅华等的笔下,塑造出了一批经过重重挣扎之后最终留在乡村生活的青年形象。在这些小说中,青年主人公对城市现代文明有着了解与接触,享受过城市文明所代表的高于乡村传统文明的物质与精神食粮。但是,他们依然愿意留在乡村而拒绝城市,或者是在城市梦想受到挫折时无可奈何地退回到乡村生活中去,最终在现实的剥蚀中泯灭了曾经对于现代城市的梦想。
1980年《延河》杂志发表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枣林曲》,小说中的女知识青年玉蝉放弃了在城市落户与工作的机会而返回农村投入改天换地的工作并收获了爱情。虽然姐姐和姐夫对玉蝉的前途有着明确的规划并帮助斡旋,给她争得了调回城市和进入工厂工作的机会,但是玉蝉却跟随着内心的愿望放弃了这一切而再次回到枣林沟。她和枣林沟的好青年社娃的恋情,她对枣林沟一望无际的青山的热爱等等,无一不是枣林沟对玉蝉的牵引,而她对以姐姐和姐夫的家庭所代表的城市的厌恶则进一步加深加重了这种牵引的力道。就这样,玉蝉撕碎了姐夫辛苦为她求来的进城机会——合同工登记表,毅然地回到了靠山吃山的乡村生活中去了。
但是,小说总是以其无意识的力量向我们展示着文本所具有的潜在内蕴,而比较有意思的是,从《枣林曲》我们不难读出“十七年”文学的固有味道——“姐姐的家——是一个世界,一层世事;她和玉山叔以及社娃所在的青山坡的枣林沟,是另一个世界,另一层世事;两层世事,两个世界,玉蝉只能凭直觉看出这个存在和差异……反正想到枣林沟那个世界,她心里好生快活!想到姐姐的家事,姐夫出来进去神秘的样子,她好生烦腻!”⑧当社娃为了集体的事业生病住院时,玉蝉觉得自己在姐夫的斡旋下出来在工厂做合同工自己挣钱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情。于是她大义凛然地对姐姐呐喊道:“人活着图啥呢?只有钱吗?人得为集体办好事,大家才尊重你……”⑨这些无不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感,而事实上我们的感觉从来不会说谎,在柳青的《创业史》中,当徐改霞报名参加工业化建设时其内心感受与玉蝉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笔者在此可以做出大胆的结论——如果玉蝉的选择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话,那么在“拨乱反正”已进行过数年的时代里,这未必不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也就是说,玉蝉所选择的这种历史道路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


三、“个人奋斗者”的艰难追求



因此,如果对这三种青年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并存的现象做出归纳的话,我们就会看出变动的年代对青年人物的多方面要求与影响。主流文化需要青年人具有凌云壮志,但是城市空间确实有限,这就产生了有才华的青年人数日渐增多而可供他们展现才华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城市工作岗位紧缺之间的矛盾。玉蝉留在农村大干一场的选择或许给我们青年提供了一条可行的人生道路,但是其意指内涵的陈旧却使得这种选择变得面目可疑,而凌云进城的失败与皈依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新思考中国社会制度与城乡差别的不同的路径,高加林和沈萍的人生追求却由于现实的逼仄而处处受阻……这一切都不得不引人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青年们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实现自我的个人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又如何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这将是一个值得长久探讨的文学与社会选题。
注释:
①②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第34页。
③⑩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5期,第17页,第16页。
④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小说编年(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⑤韩少功:《归去来》,《上海文学》,1985年第6期,第32-39页。
⑥⑦李杭育:《最后一个鱼佬儿》,《当代》,1983年第2期,第179页,第184页。
⑧⑨陈忠实:《枣林曲》,《延河》,1980年第7期。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2.008
2016-10-21
吴玲(1990— ),女,硕士研究生。
I207.42
A
1673-0887(2017)02-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