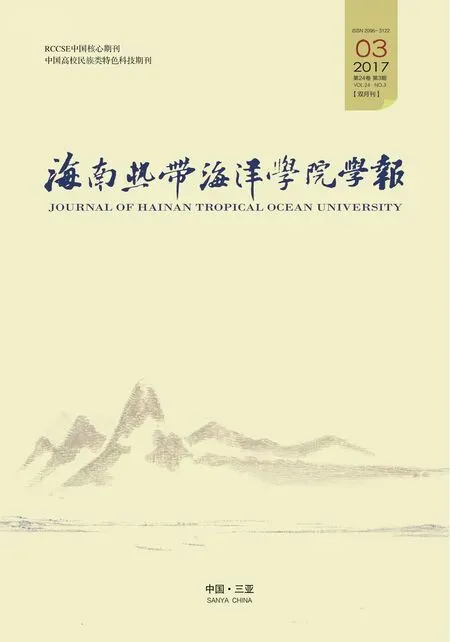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与墨家类比推理之比较
沈 琴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阳 550000)
亚里士多德与墨家类比推理之比较
沈 琴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阳 550000)
亚里士多德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作了系统阐述,也涉及到对类比推理的论述,但没有形成系统。中国古代墨家著作《墨经》中建立了以“譬”“侔”“援”“推”为形式的类比推理。墨家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推理具备各自存在的合理性,既相似又相异,两者都是在类比主体、类比源和类比项三要素的组成下,以“类”关系为基础,根据概念的外延关系构成的或然性推理。逻辑学诞生初期的中西方大文化背景下,墨家类比推理是为实用,而亚里士多德类比推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求知,因其或然性无法获得准确的知识,在西方早期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类比推理在中西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类比推理;亚里士多德;墨经
亚里士多德(以下简称为“亚氏”)被称为“西方逻辑之父”。西方形式逻辑都是在亚氏的逻辑思想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这在学界没有任何争议。但关于中国有没有逻辑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对此问题暂且不作细致讨论,本文采取的立场是鞠实儿教授主张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同时并存着多种不同的逻辑类型”[1],他指出:“显然不同的逻辑类型可以有他们各自的合理性。”[1]由此可见,他认为存在着不同的逻辑类型,并且逻辑是相对于文化的,这些逻辑类型在各自的文化下是合理的存在,因而中国逻辑的存在是合理的。本文在分析中国逻辑文本时,将采用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由此对墨家类比推理与亚氏类比推理做分析比较。
一、 亚氏类比推理和墨家类比推理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一)亚氏类比推理存在的合理性
在比较两个不同文化传统下的类比推理之前,我们要清楚何为类比推理?类比推理也称“类比法”,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某些属性上都相同,进而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的推理”[2]。
亚里士多德虽没有系统的论述过类比推理的推理规则和推理类型等,但从《工具论》来看亚氏确实对类比推理的形式和性质有过一些阐述,并且在推理过程中有运用到类比推理。亚氏在《工具论》中未明确提出“类比”之概念,但他在《工具论·前分析篇》中提到“例证”,定义为“当大项通过一个相似于第三个词项的词项被证明属于中项时,我们就获得一个例证,必须既知道中项属于第三个词项,又知道第一个词项属于与第三个词项相似的词项”[3]233。他在证明的过程中,引入了第三个词项,并且这第三个词项与大项、中项都有一种关系即相似,这种推理形式即是借助事物的相似性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类似的结论。亚氏还举了一个关于战争是罪恶的事例来作阐述,由此,学界普遍认可“例证”即是一种类比推理。
“但有的学者认为亚氏关于‘例证’的论述不是类比推理,而是归纳和演绎的相继结合”[4]157,张晓光认为“以思维进程的方向不同就是判别推理的类型各异的依据”[4]157,那么从思维进程的方向这个角度来讲,亚氏的“例证”既不属于纯粹的从一般到特殊,也非纯粹的从特殊到一般,而是特殊到特殊的推理过程。亚氏还从大项、中项、小项的关系上分析了类比、归纳、演绎三者的不同。“归纳是从对全部个别情况的考虑表明大项属于中项,并不把结论与小项联系。相反,例证与它相联系,也并不使用所有个别情况来作证明”[3]234,即是说类比与归纳的区别在于,归纳是由所有的个体结合去推知结论,而类比不必要求全部个体结合去推出结论,类比与演绎的差别就不言而喻了。从思维形式来看,类比推理在传统逻辑中可以作为与归纳、演绎并列的三类推理之一。但现代逻辑从真值角度看,应只有归纳和演绎两类,归纳推理是或然性的,演绎推理是必然性的,类比推理应是归纳推理中的一种。
(二)墨家类比推理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墨家的类比推理,是受到学界认可的。20世纪初学界开始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真正自觉地研究。在明清学者对先秦诸子之学的考据与校释基础上,梁启超首次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给《墨经》作注解。他认为墨经用“名学的演绎与归纳而立义;其名学之布式,则与印度因明有绝对相似处,同时有西洋逻辑之三段式”[5]。他肯定了《墨经》在逻辑学上的学术价值,尽管他最初的目的是以西学比附中国旧学,达到学术救国。但从梁启超以后,学界对《墨经》越来越重视,其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界定义中国古代逻辑推理的形式是“推类”,那么类比推理是否就等同于推类呢?
本文认为,推类与类比不能等而视之。“推类”首见于《墨子·经下》:“推类之难,说在之大小。”[6]173即是说,推类是件困难的事情,缘于类的范围大小不同,推类,是依据事物间的类同关系而进行的。汪奠基教授认为:“古代辩者所谓‘推类’,并不就是普通逻辑上的类比推论。但是,它的内容或形式,既有‘推类’的特殊意义,亦有作为‘推理’的逻辑基础的一般意义。”[7]由此可见,如果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来表达,那么可以说类比推理是“推类”的一部分,被包含于“推类”,明显两者的外延是不同的。古代名辩学家的推理是以类同关系为基础的,基本上遵守“同类相推,异类不比”的原则。刘培育先生指出:“异类不比,不限于某一具体的推理形式,实际上是关于推论的一条总原则。……《墨经·小取》中提出的各种推论式,基本上都是同类相推。”[8]他还认为:“中国古代逻辑讨论‘类推’或‘推类’者很多。‘类推’或‘推类’是一种内容相当宽泛的推理论证形式,并不就等于类比推理。”[8]也即是说,推类本身包含了形式多样的推理,包括一些运用到演绎或者归纳的推理论证,而全部的推理论证形式基本上都是以“类同关系”而推的,类同原则作为推类依据,不仅仅适合类比推理,而是普遍适用于包含演绎与归纳在内的论证形式。这也显示了中西方逻辑推理形式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联系。由此,类比不等同于推类。
那么在《墨经》出现的推理形式是属于哪一种呢?在《墨经》中出现了八种独特的推理形式:“辟”“侔”“援”“推”“止”“假”“或”“效”。我们根据《墨经》对这八种推理形式的定义和说明逐一分析其性质。沈有鼎先生认为:“‘譬’‘援’‘推’在本质上都是类比推理,而‘效’‘止’等则包含着对演绎和归纳推理的运用。”[9]“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也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6]213辟(同譬)即是用与所论对象相类的事物设譬并进行推类,用一种已知事物譬喻未知事物而使人知之,“墨家的‘譬’在很多情形下类似类比推理”[10]。例如,“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6]222,首先小孩两手着地学马行走是自致劳累的一件事是显然的事情,那么大国攻打小国时,两个国家的农民不能耕地,妇人不能纺织,这着实与童子之为马是同样的道理。援式推理的特点即是引述对方的论点与己方论点进行比较,以双方论点属于同类来驳斥对方对己方论点的否定。《耕柱》: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耶,鬼而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于此,其一人者见子从事,不见子则不从事;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不见子亦从事,子谁贵于此二人?”巫马子曰:“我贵其见我亦从事,不见我亦从事者。”子墨子曰:“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也。”[6]220
巫马子认为墨子在无所利益下行义是一种疯病,而自己也选择见到或不见到都为其做事的人,这样的人在巫马子看来是有疯病的人,既否定疯病又肯定疯病,这是自相矛盾的。同理可得“侔”是命题间的类比,《小取》:“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6]214这是两个相似的“辞”作相同连缀的并列推理,由引例可见,前提和结论中的主项与谓项有包含的关系,这保证了推理的正确性。“推”是理由或论式的类比,以对方所否定的观点和其所肯定的观点是同类而诘难对方,正如无鬼神而必学祭礼类比于无客而学客礼,以否定的后者相类于其所认可的前者的存在,推导出无鬼而学祭礼的不成立。现在我们看另外四种推理形式:“假者,今不然也”[6]213,单从字面上来看仅定义了命题的性质,是假设的暂未施行,这无关类比因素。“或也者,不尽也”[6]213,即非全部,其后有“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6]214,这里的“或”可理解为“有些”,这与特称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6]213,这是论述命题是否正确的标准问题。“止。举彼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6]179,即是说认为某类事物具有某种性质,只要这类事物中的某一并不具有这种性质,就可驳斥其原结论,这种推理从表面上与类相关,可它是在一类事物中进行讨论的,没有类与类的相关性。故而,《墨经》中主要是“譬”“侔”“援”“推”这四种推理方式是属于类比推理。因此,与亚氏类比推理做比较的主体并非《墨经》中的全部推理形式,而是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前四种。
二、 亚氏类比推理与墨家类比推理的相似性
(一)类比推理的基础一致
在类比推理的过程中,人们之所以可以根据某事物与另一事物的在客观上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推出其他属性的相同或相似,是源于“类”。何为“类”?中国古人对“类”的认识是与事物间的同异比较有密切关系,着眼其相似或相异之处,相似则“类”,相异则“不类”。《墨经》中将“类”作为逻辑范畴解释为“同”,在亚氏推理中,肖尔兹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可以说是一种谓词的或概念的逻辑,也可以说是类的逻辑。”[11]归根结底,类比推理的基础在于事物间属性的“相似”。莱布尼茨曾指出:“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进行类比,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极其不同的事物,找出他们的相似点。”[12]这即是说万物之间存在着的统一性使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的“相似”,事物间的区别都是相对的。这就为我们从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的方法。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为类比推理提供了客观基础。我们来看亚氏在《工具论》中所举的“例证”:“假设A表示‘坏’,B表示‘对领邦发动战争’,C表示‘雅典反对忒拜’,D表示‘忒拜反对福奥克斯’。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证明反对忒拜的战争是坏的,我们必须认定对领邦发动战争是坏的,其证据可从相同的例证中得出,例如,忒拜反对福奥克斯的战争是坏的。因为反对邻邦的战争是坏的,所以很显然,雅典反对忒拜的战争是坏的。”[3]234在这个例证中,若引入三段论加以解释如下,大前提是A属于B,小前提是B属于D,由此得出A属于D,因为C和D属于同类,所以A属于D。在这个论证过程中,C和D因相似而同类是客观的,由于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只需要三个词项,那么遇到多词项的时候就难免出现谬误,而利用事物客观属性上的相似采用类比推理是可行的。《墨子》记录诸多事例基于“相似”,正如《兼爱上》论述圣人治乱与医生治病都要寻求其乱之根源,引用相似之事例可提升辩说之效,在此不作细致阐述。
(二)类比推理的构成要素相同
两种文化背景下的类比推理都具有基本的三要素——类比主体、类比源和类比项。在进行推理之前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类比主体即是认识主体,通俗地讲是人,对类比推理过程中各要素的结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充当类比主体,诸如婴儿,智力有限的人,对世界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也没有积累足够的客观材料,就很难进行有意义的类比推理,因类比主体的存在,即个人思想意识的参与,也就直接影响了类比推理的性质是或然性的。类比源和类比项可认为是认识客体,两者是独立存在的。类比源是在类比推理过程中充当参照物的事物或现象,类比项是在推理过程中存在歧义的食物或现象,是整个推理过程中尚待解决的成分。我们看《墨子·耕柱》:
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也?”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捧水而灌之,一人操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捧水者之意,二非夫操火者意。”子墨子曰:“吾意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6]219
墨子在此援用巫马子所认可的捧水灭火的主张与自己兼爱的主张是一致的,从而证明自己的正确使得巫马子接受自己的主张。在这个事例中,墨子之兼爱天下的主张是类比项,而巫马子认为捧水救火乃正确的作为类比源,类比项和类比源在类比主体的结合下于某些属性上是相似或相同的。但在现实中是独立存在着的多类事物或现象,其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类比源于类比项是异中有同,而在类比推理的运用中是异中求同。在亚氏类比推理中亦如此,都需要这三个基本要素才能进行论证,只是在亚氏推理形式中,它们被称大项、中项、小项,因其三段论式严谨完整,这三词项中把两类事物中的相同点定义为中项标示出来,但与上述三要素是相同的,亚氏举例:如果要证明雅典对忒拜的战争是坏的,可以用忒拜反对福奥克斯是坏的来作为例证,其中有个说明即对邻邦发动战争是坏的,这是两件不同事件的共同点,“忒拜反对福奥克斯”作为类比源,而“雅典对忒拜的战争”则是推理中的类比项。总体来讲,中西方的类比推理在此内在机制上是一致的。
(三)类比推理的性质——或然性
类比推理以两事物属性间的相似为基础,这种相似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而事物间的差异性有时候是其本质属性,有时是非本质属性,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就限制了推理的可靠性。亚氏是演绎推理的创始人,其首创的三段论对西方逻辑学的发展影响是空前的,在演绎推理中,前提的真直接推出结论的真。而在其论述的类比推理中,前提的真不一定推出结论的真,亚氏在《工具论》中说:“当两者都属于同一个词项,其中一个被知道时,则一个例证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与整体,或整体与部分的联系,而是一个部分与另一个部分的联系。”[3]234由此可知,在类比推理过程中,并非考察两个词项全部外延间的关系,而只是考察其在部分上的相似,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考察其非本质属性是相似的,而未被考察的本质属性是不同的,由此进行推理得到的结论不是必然性的,亚氏在逻辑学的论证过程中追求的是知识,必然性的真,类比推理没有保真性的推理规则,以此方式只能使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知识。
关于墨家类比推理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必然性”的,也有学者认为是“或然性”的,刘培育先生指出中国人“头脑里默认了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大前提,比如‘天地万物为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类不悖,虽久同理’等。古代的推类实际上主要是在大前提相同的情况下的推理,无论是类比推理,比喻推理,还是演绎推理”[13]。此中所提大前提,有学者认为是“类同理同”,可以表述为:“一类事物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同样的一个理,亦即如果K和L是同类的,则K与L必定有一个共同的理N。”[14]31“类同理同”被认为是一条公理贯穿在类比推理过程中,由此类比推理可以视为是演绎性的,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其性质是必然性的。也有学者认为其性质是或然性的,《淮南子·说山训》中有“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则同,所以入水者则异”[15],即是说神经错乱的人向东走,而追赶的人也向东走,但他们向东走的原因和目的是不一样的,不能以两者皆为向东走以同类推出相同的结论,入水者如上。此例即是说,事物的相似属性和推出属性不一定具有必然联系,属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就导致了结论的或然性。作为公理性的原则“类同理同”可以说是让类比推理可以进行的可能性,但是不能保证推理结论的确切性。类比推理的可靠性不是由“类同理同”所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共有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的关联程度、类比主体要找出类比项与类比源之间更多的相同属性,且尽可能地接近于其本质属性,这样就可以提高类比推理结论的确定性。
(四)概念的逻辑
肖尔兹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可以说是一种谓词的或概念的逻辑,也可以说是类的逻辑。”且“末木刚博教授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推理是根据概念的外延关系构成的,是概念的逻辑。”[16]虽然亚氏对类比推理的研究未形成系统,但不可置疑,类比推理是亚氏逻辑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且亚氏对类比推理的定义——“当大项通过一个相似于第三个词项的词项被证明属于中项时,我们就获得一个例证,必须既知道中项属于第三个词项,又知道第一个词项属于与第三个词项相似的词项”[3]234——我们可明确看到在这个推理运行过程中词项与词项有着属于的关系,即是不同的词项在外延上有部分的相似或相同,类比推理得以成立的基础即在于概念与概念之间有相似的关系。因而将亚氏类比推理视为一种概念逻辑是可行的。
《小取》所谓“以名举实,以词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6]213明确说明了“名”“辞”“说”三者的关系。“说”是一种论证过程,相当于推理或论证,任何具体的类比推理形式都是一种“说”。“名”是构成“辞”与“说”的基础环节,先秦各家几乎都有对“名”进行解说。从狭义来看,“名”即今日之概念,墨家逻辑是一种谈说论辩的逻辑,其目的在于取当求胜,若要辩论得当,首先得保证对“名”的正确使用。《墨经》中对“伐”与“诛”的区分就说明了概念在墨家逻辑中的重要性。墨家类比推理也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也是一种概念的逻辑。
三、 宏观视角下亚氏类比推理与墨家类比推理的区别
(一)文化背景不同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不少哲学家思想中萌芽了逻辑学思想。苏格拉底著名的“精神助产术”在与他人的谈话过程中通过归纳方法为伦理概念找出最初的定义。亚里士多德之师柏拉图在提出或者改造其中心思想理念论的过程中,已经广泛地使用到逻辑学中的一系列思维方法,诸如定义、划分等。我们可以看出在亚氏之前许多思想家探讨的都是求真求善之法,但他们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而亚氏系统的解决了一些逻辑问题,并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在他的时代里诞生逻辑学,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必然。亚氏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积累了广泛的资料,这足以支撑他进行类比推理的论证。但同时求真求善的传统也使得类比推理得不到更多的重视。
中国的类比思维在《周易》中就有记载了,其特征为“取象比类”[14]54,并确定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4]76之类原则。中国古代人们的具象思维发达,这一民族传统持续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继承发扬。因而,墨家对类比推理作出系统的分析阐述,总结出其推理运行的规范也是有其文化积淀,而非一蹴而就的。文化传承中的具象思维让墨家的逻辑思想融入各种事例,是一种用古汉语表达的应用逻辑。
(二)价值取向不同
总的来说,亚氏类比推理和其演绎逻辑一样是为求知;而墨家类比推理是为实用。西方逻辑受启发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对自然的认识。他们生来追求的逻辑就是确定的真,如冯友兰先生套用孔子之语——“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孔子有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7]。雅典虽一度成为古希腊的文化中心,但大多学者乐于游历四方,交流探讨知识。而且古希腊是城邦制国家,人们在思想上的自由确保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柏拉图曾提出“哲学家王”的思想,在此背景下,人们都追求善,追求真正的确定的知识以摆脱无知成为有德行的人。亚氏类比推理即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衍生出的,但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因而并没有如演绎推理般受到重视,也无法形成系统的发展。
古语有言“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可看出人们在世的追求是什么,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思想严谨且深入人心,而且先秦诸国战争不断,各家所主张思想的前提都是为国家统治服务,他们所主张的思想的存在需要统治阶级的认可和依赖。即是说,一思想要有实用性才能被采纳,因而先秦各思想学派很少追求类似西方纯粹的逻辑,纯粹的知识,皆是在寻求齐家之法,治国之道。即使是逻辑学集大成的墨家,旨在“取当求胜”,即是辨别是非,区分正误。在统治者选择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以维持统治秩序后,也难逃销声匿迹之命运,直至近代才重见天日。
(三)发展历程不同
西方逻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占据着重要的理论地位,但类比推理自亚氏开始,就没有形成拥有公理和推理规则的系统,尽管如此,类比推理的思想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仍然在逻辑发展进程中受到一些重视。培根《新工具论》中提到“类比的事例”[18],表达某些事物的相似和连属,这种推理方式不能发现法式,但是是有助于显示宇宙各部分的结构,引导人们发现更深刻的原理。此外,康德也曾说:“每当理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19]类比推理是一个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可以以我们熟悉的事物去解释陌生的事物,使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在西方逻辑史上,虽然没有对类比形成系统理论,但科学家们大多自觉的在使用这个方法,如魏格纳在类比基础上提出“大陆漂移说”,伽利略利用类比的方法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
在中国史上,逻辑学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就墨家逻辑而言,其学说在孟胜殉城之后就四分五裂了,此后《墨经》中所载的逻辑思想只被少数思想家作注解和引用,而类比推理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消沉,无更多创新性的理论发展。直到明清时期才慢慢复出。
结 语
综上所述,亚氏类比推理与墨家类比推理兼具共性与特性。客观而言,两者在类比推理中的决定性因素或性质上是相似的,东西方因不同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会构成不同的推理表现形式,但类比主体、类比源和类比项三个因素都不可或缺,一个类比推理的成立源于“类”关系的成立,只有具有类同性质的事物或现象才能进行相推,且类比推理的推导过程是根据词项的外延关系进行的,这种根据“类”和外延进行的推理形式是不稳定的,因为词项的类关系和外延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同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从广义角度来看两者从萌芽期到发展期存在较大差异,在现今的家族逻辑背景下,中西方早期类比推理得以融会贯通,学术界对类比推理开始重视和研究。类比推理本身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或者可以说类比推理的过程就是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下是非常重要的思维方法。类比推理的特殊性让它成为有别于其他逻辑思维方式的独立体系,它在任何学科中都有重要意义。在今日之不同文化大背景下的逻辑,应该自觉地重视类比推理,类比,演绎,归纳三者应该在逻辑学中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尽管类比推理从始至终都没有形成如演绎、归纳般的推理系统,而正因为它的创新性,灵活性更强,更加适合今日之变化多端的世界,它作为逻辑学的一个部分,值得学界作出更多深入的研究。
[1] 鞠实儿.论逻辑学发展的方向[J].中山大学学报,2003(增刊):3-8.
[2] 逻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逻辑学词典[K].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595.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工具论[M].余纪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张晓光.推类与中国古代逻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5] 周云之.中国逻辑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416.
[6] [战国]墨翟.墨子[M].[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7] 汪奠基.“略谈中国古代‘推类’与‘连珠式’”[G]//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09-114.
[8] 刘培育.类比推理的本质和类型[G]//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研究会.形式逻辑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56-261.
[9]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29.
[10] 温公颐,崔清田.中国逻辑史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35.
[11] 武明洋.基于“三段论”和“小取”的亚里士多德和墨家逻辑比较[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4.
[12] [德]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集[M].祖庆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6.
[13] 刘培育.中国古代哲学精华[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355.
[14] 刘明明.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5] [汉]刘安.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953.
[16] 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6.
[1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4.
[18]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论[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73.
[19] [德]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47.
(编校:王旭东)
A Comparison of Aristotle and Mohism Based on Analogical Reasoning
SHEN Qi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Aristotle elaborated on deductive reasoning and inductive reasoning, and also discussed analogical reasoning, but he did not form a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gic, Mohists, in Mo Jing, established 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forms of “analogy” “mou” “aid” and “push”. Both reasonings have their own rationalities for existence.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rences between them. Both are based on the “class” relationship under the composition of analogy subject, analog source and analogy item, and form the probability of reasoning accord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In the contex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early days of logic, the Mohist analogy stressed on practicability, but the ultimate aim of Aristotle’s analogy is to seek knowledge, and due to its inability to obtain accurate knowledge from probability, it didn’t get enough attention, and so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China and the West formed very different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alogical reasoning; Aristotle;MoJing
格式:沈琴.亚里士多德与墨家类比推理之比较[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7(3):42-48.
2017-03-08
沈琴(1993-),女,重庆人,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逻辑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逻辑、中国逻辑史。
B81-09
A
2096-3122(2017)03-0042-07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3.08
——对《物理学》8.6(259b1- 20)的一种解读
——“自由落体”教学中的物理学史辨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一课的教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