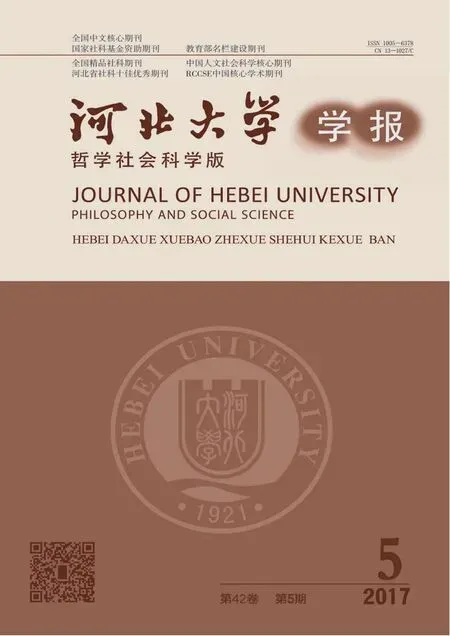人天合一:汉代天人观解析
杨清虎
(安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人天合一:汉代天人观解析
杨清虎
(安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其思维形态可以理解为多个阶段的动态过程,汉代恰好处在一个动态升华的关键时期。汉代开始,神本思想渐褪,对人的关注致使“天人合一”思想偏向于反映人的能动作用,尤其是儒家从“人”到“仁”思想的超越,直接成为“天人合一”理论走向深入的驱动力。“天人合一”中的“天”虽有中国哲学的本体地位,却又是为政治服务的“人为之天”,是神学思潮影响下“天人合一”转型的产物。从对人关注的层面上,“天人合一”应为“人天合一”,如此才易于理解汉代儒学的没落与兴盛、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服务统治者与服务民众等争议话题的矛盾与统一之症结。
天人合一;人天合一;董仲舒;汉代儒学;神学政治
“天人合一”思想孕育于氏族社会,发轫于春秋战国,成型于汉魏,成熟于宋明,嬗变于近代,复兴于当代。“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基本的中国哲学命题,汉代是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尤其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此为思想原点而构建出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更显说服力。也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基本上贯穿整个汉代社会,支撑了汉代儒学思维构架,是儒家思想转型的重要理论。“天人合一”绝非静态的思想演化,以“合”为中心的动态化演变,是解构“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思路。
一、“人天合一”循环论初现:汉代天人观在理论发展中的承启地位
“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有别于“天人相分”“天人相交”“天人一体”等天人关系命题,其精髓在于天人合一具有动态性。这个动态的思想演进过程,至少有四种运动趋势:第一,天与人同时同步无限地向“一”接近,继而形成一个无限趋向于终极的“一”的状态。司马迁所追逐的“天人之际”,即是这种天与人统一体;第二,人作为活动的个体,天作为静态对象,继而人慢慢地向天靠拢,形成人在“天”中,实现天即“一”的理想状态。董仲舒所谓之“人副天数”,天为人祖,人是天的副本,人从天出就是这种动态形式;第三,人投射一个静态的价值终结点,天作为一个动态裂变的信仰和道德实体而不断凝结,最终天主动演化为人预设的超验对象,以达到天向“人”的重叠。道家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就是让道与人合一;第四,人先实现向天靠拢,达到天与人的同步,最后天与人又回归人的需求,形成“人——天——人”过程的循环,最终无限往复而形成“合一”。张载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就是依托这种人天循环理论,实现人价值的无限追求。
“天人合一”的动态化路径,基本上代表了不同阶段对天人关系的综合认识,存在一种递进且交织的理论认识深化。人与天之间永无止境地互相追逐而形成人天循环,达到无限对一的追求,是“天人合一”思想演化的最高形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不在四种“合”的路径之中,却是循环论形成的重要阶段。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以“感应”解释天人之间的关联。“感应”论其实并非董仲舒的发明,《周易》《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萌生,比如《周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吕氏春秋》曰“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1]《淮南子》曰“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2]664董仲舒明确提出的天人能“感应”的看法,上接儒道墨等诸子百家,熔炼阴阳五行以后,又下启张载的天人合一循环论。
在思想史上,之所以起到了上下承接的作用。这是因为,在董仲舒之前儒家的哲学思想还停留在天人关系问题的探讨上,更多地是对天命、对人性的认知,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更多地强调天人如何相处,如何关联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两者的“合一”。《尚书·泰誓上》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说的是人与天如何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听命于天,还是与天对抗。子曰“天何言哉”(《论语·阳货》),透露的是对天的无奈或者回避心态。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是把关注点回归人性,关注人性,其实就是知天而成仁,人是天的一部分而已。荀子所谓“天行有常”(《荀子·天论》),强调的是天的运行与人无关,谈论的是人对天道应该如何自处。先秦以来的天人学说,大多停留在天与人认识的关系,或天与人孰重孰轻的争论上。到了董仲舒,依然是讨论天人关系,但打破了单向的凝固状态,特别是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以神学思维来化解天人关系的难题,无意中把天人关系盘活并提升到一个更哲理化的阶段。其表现有:第一,天有了人的某些特质,比如形体、性格、地位、尊卑等;第二,人有了对天属性的继承,比如至上性、神圣性、规律性等;第三,人与天可以达成某种默契,比如人能感应天的喜怒哀乐,天能向人传达凶吉善恶等;第四,人与天有了某些一致性,比如人处于天地之间,人与天形成某种对应特质等。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论,对先秦天人关系有一定的继承,但更多的是发展。甚至董仲舒直接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只不过这种“合”是感应的协调,而非天与人的合二为一思想,但毕竟这种思想为天人关系演化成“天人合一”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从人到仁:汉代天人观形成的理论驱动
从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本主义占据主导的社会。在长达数万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们笃信鬼神,认为鬼神是主宰人类社会的根本力量。然而,绝地天通改变了这种情况,民神得以分离,中国社会因此而逐渐脱离神本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颛顼宗教改革、尧舜政教改革、周公的宗法改革。经过这些改革以后,人的职能与神的职能发生了分离,各司其职,民不再肆意祭拜鬼神,神也不能再轻易干预民间事务,理性主义开始占据社会主导。然而,真正实现理性主义从原始宗教思想中解放出来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春秋战国时期进行的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史称“百家争鸣”。经过了这场思想大解放,理性主义才真正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所以《荀子·天论》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的就是天的自然属性,天与人类社会的兴衰没有关系。故又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最后的结论是:“唯圣人为不求知天。”[3]荀子把天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抛去了天的神秘性,是春秋战国后期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汉代,理性主义占据主导的一个最大表现是汉代人本思潮的兴起与确立。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之谓道。”[4]韩婴又曰:“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5]《淮南子》曰:“烦气为虫,精气为人。”[2]218汉初学者虽对人从性、道、命、气多层次阐释,但基本认为人都是自然所化,是受外界影响,具有可塑性,是可以被道德伦理所教化的。《淮南子》曰:“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2]352《淮南子》以道家之立场,反对纵欲,强调对人的约束。董仲舒吸收百家思想,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6]288。按照董仲舒的逻辑,事要顺于天,也就要求人要顺于天,方能“天人合一”。在“人”与“天”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具有能动性,而天则是参考物,是不变的,说来说去还是想强调可变的人,而不是所谓的天,所以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莫贵于人”。因为人为“中人”,所以尚可教化,故“不教之民,莫能当善”[6]304。
董仲舒虽然倡导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甚至直言“天尊于人”,但也并不是忽视人。《春秋繁露》曰:“王者,人之始也”;“仁之法在爱人”;“不独在天,亦在于人”;等等,时刻不忘人的作用,有着抬高人主动性的目的。“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6]161,源于人的“仁”,其重要性已经超越天,统一于“天人”,成为“一”的代指。谭嗣同著《仁学》,但其本意就是在倡导人权和人本主义,主要手段就借助“仁”来推动变法,“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他认为,仁是自然界与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或最高的哲学范畴,倡导仁学可以揭露“数千万之祸象”,扫荡现实中一切桎梏[7]。仁是对人性的尊重,仁就是人本思潮的产物,依然是由人而生发之情感。故《春秋繁露》曰“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强调的就是儒家“仁”的核心地位。杨国荣把儒家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关怀,称为“善的历程”[8]64,这种“善”就是一种至善的内省和化“天之天”为“人之天”[8]274,所谓的“人之天”其实质还是源于儒家核心思想“仁”的解读,是“仁”驱动而形成的天与人的循环。可以说,“天人合一”看似天与人的关系,实质还是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强调人向天的靠拢,是“仁”主导和作用的结果,故可以把人提前至天之前,称之“人天合一”。
三、神学化转型:汉代天人观的思维逻辑与精神实质
“天”是什么,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哲学思想里,“天”就类似中国哲学史上的道家之“道”、佛教之“佛”、理学之“理”、心学之“心”,是新儒家之“心性”。用现代哲学的观点来看,天就是汉代儒家哲学宇宙论之本体。天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它是比“天、地、人”之天更高的抽象与具体糅合的广义之“天”。在这个统摄万物的天之下,有具体的天,以及地、人。具体的天怎么理解呢?首先天应该是天的本来面目,《春秋繁露》曰:“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6]269这里的“先祖之所出”,应是自然之天。当然,如果把天仅仅解释为自然而然的天,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董仲舒所谓的天还是“神”,《郊义》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6]403。《春秋繁露》又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讥之。……今秦与周俱得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异于周。”[6]398原本自然存在的天,已经被神化为鬼神之首,是“百神之大君”,可见这里的天就是信仰体系中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统领所有神祇的首领,是最高的神灵。所以金春峰总结说:“自然之天从属于道德之天,道德之天又从属于神灵之天。”[9]《春秋繁露》曰:“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6]410这里的“天”已不再是自然之天了,开始演变成一种人伦关系,是天地的关系,也是君臣、父子的关系。在这里天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伦理之天。当然,在这种统摄万物的天之下,还有人格之天。《春秋繁露》曰:“天子者,则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独何为不欲其子之有子礼也。”[6]399董仲舒挟天以令天子,表面上把天之子的名誉让渡给了天子,实质上是使其“以身度天”,为儒所用。
董仲舒为了宣扬自己的天之本体,打了很多通俗的比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把天比作“祖”,一曰:“天者,群物之祖也。”[10]2515二曰:“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6]410三曰:“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6]318这个比喻虽然通俗易懂,但也极易造成误解,容易把天与人相提并论,天与人之间构成了一种血缘关系。天也就因此有了人性,有了道德。《春秋繁露》曰:“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6]329又说到“天”:“多福者,非谓人也,事功也,谓天之所福也。”[6]398孔子思想的仁,在董仲舒这里,人是“天之所福”,成了天的本性。又曰:“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6]330人与天的性格都是一样,有喜怒哀乐。
可以说,董仲舒所谓之天,是复合的天观念,囊括了自然之天、伦理之天、神灵之天。这个天,既是宇宙论之本体,又是信仰之至上神,是理性与信仰多重观念的“聚合”。在董仲舒聚合之天的哲学思想里,实际上糅合进了历史、阴阳、刑法、道德、民间信仰等理论与思想,既融百家思想为一炉,又为己所用,利用自己儒生身份,把这一套理论演化为“新儒学”。使用如此复杂的思路去整合诸子思想,又以儒学统摄诸说,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达到“独尊儒术”。当然,这个儒术,是董仲舒的儒家学术,更是儒家的权术。某种程度上,董仲舒是把儒学推衍至权术而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从此后数千年的儒家地位来看,在儒学的政教化之路上,董仲舒对儒学政教的贡献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
董仲舒挟天能够取得成功,固然与其理论的缜密无隙有关,但必然之中亦有偶然,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极大关系。董仲舒的这种成功,不是依靠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更不是依靠个人的威望和影响力,而是使用民间信仰的神学手段推行开来。董仲舒为了让人信服他的天人理论,不断吸收阴阳五行等神秘主义学说和理论。首先,他试图依靠对正史的解读,来为自己的理论建立依据,故曰“臣谨案《春秋》之文”云云,试图以天授命,“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10]2502,等等。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最高代表,春秋之语早烂熟于心,已达到了“《春秋》注我”的境界,让《春秋》为自己的天的哲学提供依据自然易如反掌。然后,又利用阴阳之辩证,证明自己“天之道”的合理性。他接着说:“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10]2502。最后,还不忘挟天威慑天子,他说:“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10]2515正史载汉武帝极其迷信,年轻时辽东高庙着火,“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10]1331,董仲舒、公孙弘出现之前,诏书曰“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10]160。晚年更不必说,因巫蛊之术被处死的人不计其数。时势造英雄,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历史环境下,董仲舒的宏才大略,加上与无懈可击的天人理论,再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社会和汉武帝笃信鬼神的心态,自然能够挟天而令天子,把儒家推上了一个至高的地位。
按道理说,儒学自孔子以来,是理性战胜信仰的伟大胜利。但是到了汉代这样一个儒学独尊、儒家至上的社会里,儒学反而又主动去吸收非理性的宗教性思想,形成了儒学发展历史上的一种严重“偏离”。究其原因,固然与董仲舒为了宣扬儒学不择手段有关,但从当时的社会而言,民间信仰还存在巨大的能量,汉代信鬼崇巫之社会风气不减,尤其是以武帝为首的政治集团相当笃信鬼神,让儒家不得不对其重视。故《春秋繁露》引《诗》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怀多福”,借以宣扬“天之所福”[6]398。天是“百神之大君”,按照周代礼仪要祭祀先祭天,才能祭祀其他。韩星就在关于董仲舒的“天论”中认为董仲舒的神灵之天,其思想渊源来自对上古以来的宗教之天的继承[11]。这种神灵的继承源于对王权合法性解释的迫切需要,且与适应整个社会的神本思潮有关,当然也与董仲舒一时之间难以找到更好的宗教理论来支持自己的神学思想不无关系。
所以说,董仲舒所构建的“天”,一直未脱离神本思想的束缚,处处都有神本主义的色彩。纵观整个汉代历史,可以发现,儒学虽然独尊,理性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人本主义已经被统治者所接受并推行,但神本思想并未被完全从汉代社会中清理出去。尤其是广大的民间社会,其信仰依然保留着非常浓烈的神本色彩。《史记》载南越地区巫鬼盛行,汉政府不得不顺从当地敬鬼习俗,“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12]。汉代各个阶层,上至皇亲贵胄,下到黎民百姓,都是信奉巫鬼的,因此《汉书》中记载了大量死后成“神”的信仰,如西汉的石庆、胡建、段会宗、文翁、朱邑、召信臣,东汉的邓训、岑彭、祭彤等[13]。胡适评论汉代儒学时说:“这种宗教和思想背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普遍广泛流行的各种信仰和由于移民、军事上的征服,最后由于秦、汉王朝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神秘莫测的迷信。”[14]汉代的种种神秘主义不是儒学与生俱来的,而是受到汉代社会浸染对人本思潮异化的产物,是神本思潮依然在民间大行其道的结果。
无论怎么去诠释天,但不变的是,天是为人服务的,是依附于人观念的产物。只有在人不占有它时,它才存在,而人一旦占有它,它就消失了[15]。在董仲舒的哲学理论里,天实际上仅充当了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依靠人的占有而存在。董仲舒释天目的就是“挟天以令天子”,天只不过就是一个用来牵制王权的法宝。董仲舒在威慑天子的同时,还试图让天子屈服于自己营造的天的权威之下,听命于天:“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10]2502“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6]458从这个层面来说,董仲舒所谓的天虽然广阔无垠,是漫无边际的全能之天,但也逃不出一个天,那就是服务于儒家权力的“天”。说到底,化“天之天”为“人之天”之后,所谓的“天”,还是人的天,还是为人的天。正是因此,所谓的“天人合一”,是借助了神学思想的为政治服务的“人天合一”。
四、天人合一:汉代天人观引发的儒学命运之反思
汉代社会崇尚理性主义,注重人价值的挖掘,儒家的天人观本应倡导“人天合一”,但实际却宣扬“天人合一”。形式上的“天人合一”,不是要让天去迎合人的需求,那既不是儒家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事实上的“人天合一”,这种天人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该是人,是对人性、人道、人学的关注。现实情况是,汉代儒学因为献媚权术,让儒学开始演化为儒术,颠倒了人与天的关系,也让儒学偏离了对人性的追逐。正是这种倒置的天人观,致使众多学者对汉代儒学的发展之路充满质疑。
其一,汉代儒学发展现状上,儒学的堕落与兴盛并不矛盾。汉代儒学是冯友兰所谓经学时代的开始,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继续,是一个文化昌盛、儒学大展宏图的时代,还是一个牟宗三认为的“哲学堕落”[16]、劳思光所谓的“儒学之衰乱”[17]的时代。言其汉代儒学之昌盛,无非是因为,政治上,汉代罢黜百家而儒学独尊,儒学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接纳,成为社会思想主流;道德规范上,孔孟之道成为社会的基本道德和伦理,“三纲五常”奠定了今后几千年社会基本规范;经学上,公羊春秋独占鳌头,儒学研究一派欣欣向荣;军事外交上,儒家大一统思想让汉代帝国得以巩固,王朝盛极一时。言其汉代儒学之衰落,是因为汉儒抛弃了孔孟儒学的基本理念,献媚王权,肢解原儒,吸纳神秘主义,染指意识形态,以至于到了近代推翻专制王权的同时,儒学也备受牵连,遭千夫所指。
实然,汉代儒学的没落与兴盛是形与神的关系,形似兴盛,但神已衰败。儒学最大的败笔就在于与政治联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儒学政治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固然有助于儒学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儒家思想的推广,也有助于儒学学术的活跃。但儒学政教化,屈尊于王权之下,既要迎合帝王心理和国家发展需要,又要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不甘受制于王权。与其说中国古代历史是王权与相权之争,不如说是王权与儒家权力的争夺。汉代儒家炮制的“新儒学”,其理论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儒生一直试图为历代帝王套上这顶带有神权光环的“天人合一”紧箍,但是适得其反,往往都招来杀身之祸。汉武帝时长陵高园殿起火,董仲舒本想借此宣扬他的天人感应理论,以灾异之说震慑天子,结果适得其反,差点儿命都没保住。
汉代儒学一味强调政治功用,反而忽视了先秦原儒强调的内心修养,儒家之学完全流于形式,在成为统治工具的时候形成了种种“名教”规范。“天人合一”无限放大天的神学特质,直至“神人合一”。神学思想毕竟不是儒学的主干,只能算是支流,甚至可以称为“异化”。“神人合一”背离了孔孟儒学的“以德治心”,神秘主义泛滥,尤其是东汉以后儒学吸收谶纬学说,更是让汉代儒学不堪重负,直至汉末儒学名存实亡,儒生近乎绝迹。故而,儒学兴盛与衰落仅为汉代新儒一体之两面,并不相悖,本质是儒学更化演变的宿命。
其二,汉代儒家发展的趋势上,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共存。卡西尔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8]人有其社会性,先秦哲学就是对人性追求的哲学。“仁”是孔子对美好的人性的一种最好诠释,虽然带有先验性,但毕竟从道德层面树立了儒学的独有魅力。孟子对此给予发扬,提倡“仁爱”为政,试图让施政者接纳这种德治的儒家思想。不管怎么说,孔孟的政治理想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是把“人”扩大到国家理论的一个过程,这样人的本性才能显现出来。对君子的孜孜追求,代表了先秦儒家的理想。荀子处于战国末期,是百家争鸣带来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最高峰,荀子《天论》倡导“明天人之分”,把天人相分,人神分离,代表了这种理性主义的趋势。
按照先秦儒学的发展脉络,儒学应该继续引领人性思潮,讲求天人相分。然而,汉代儒家的天人哲学却脱离了人本思想,偏离了儒学走理性主义的方向,反而试图回归神本时代。汉代新儒学,看似一个弱化人、强调神的时代。天人关系,在汉代更多地演化为神人关系。事实上,汉代儒学发展是多元的,在汉代社会有一个下移的过程,儒学理念推广到下层民众,依然是注重人伦教化的儒学。
民间信仰延续了先秦原始的宗教观念,是社会民众的主要信仰内容,儒学是理性主义的萌生,代表了进步、科学。从民间信仰与儒学承载的社会思想潮流来看,天人之间的分裂、分离是汉代社会的主流和积极趋势,人只有独立于天,发挥人的主动性,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从儒家追求的理想而言,则是强调天与人的合二为一,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并使儒学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近代儒学,在西学的影响之下,“天人合一”一味禁锢人性,夸大宗教性,致使知识理性思想遭受蒙蔽,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当前儒学,又极力剥离宗教性,让“天人合一”没了灵气,就只剩下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
由此,也不得不让人反思,天人合一是文化的主流,还是天人相分是文化的主流,亦或是始终存在着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结合,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和最高道德标准,但文化的发展一直都停留在天人相分的发展历程之中?
其三,儒学服务的对象上,统治者与民间大众的统一。汉代儒学的发展是一个在变革中发展的时代。“儒术独尊”让儒学思想的触角伸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儒学走入民间,成为大众儒学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儒学宗教化的过程可以看到,儒学紧紧依靠了政治来推广宗教性的神学思想。这种做法无疑是失败的,教权与政权难以调和。宗教的建立,基本上都是依靠下层民众的支持成为普遍信仰,最后才形成权力中枢。但儒学没有选择走这样的道路,仅仅依附于王权,只是借助神学外壳实现自己向权力政治的延伸。汉代儒学虽然倡导人的重要性,但更多是治人、用人之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人学。这与民间信仰在手法上一致,但目的却有差异。儒学的终极关怀,是“人”为基本对象和前提的世俗信仰,是以现实关怀为起点的,儒家哲学两极是统一的。汉代儒学政治化与世俗化,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统治者与民众的共同需求,“天人合一”成为儒学政教化与宗教化融合的产物。
说到底,“天人合一”与“人天合一”并无分歧,这种复杂的天人观代表了汉代儒家对社会需求的一种调和与融会,更多地强调的是对人的需求的捕捉。当代新儒家走向世界时,才意识到儒学应该服务于大众,才认识到走心性之路的正确性。只有挖掘人的价值,注重对人的关注,才是儒学的最高理想,是儒学存在的目的与归宿。从现代价值来说,人类社会从神本主义中走出来,在人本之路上不断探索。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本的挖掘,西方自由主义泛滥,社会物质的高度发达,把社会的重心转向物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者是依靠神本主义的神权来约束西方社会,以此构建中世纪人屈尊于神的秩序。近代以来,宗教世俗化却又难以从道德上束缚自由主义的浪潮,看似解放人性,强调人权,实则倡导物本,让人屈从于物的权威之下。
总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采众家之长,吸收民间信仰以及历史上的自然、道德、神灵之天为一炉,用诸子百家思想武装了一个聚合的“天”,并向宋代儒家的“一贯天”发展。这种天人观念,运用天人感应之论、阴阳五行之说,吸纳神学理论,利用民众心中尚未褪去的神本主义思潮,以动态化思维把天与人联系起来,进而试图打造无缝天衣似的“天人合一”学说。这个理论看上去是人与天的合二为一,但实际上,“天”是依赖于儒学理论体系的天,是受“儒”诠释支配的天。可以说,这个“天”本质上是对人认识的产物,天人关系中人的地位高于天,天是人的附属品,是天趋向于人的“人天合一”,而非“天人合一”。
[1]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285.
[2]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307.
[4] 刘盼遂.论衡集解[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65.
[5]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5.
[6] 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290.
[8] 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修订第三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55.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1] 韩星.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从宗教与哲学视角看董仲舒天人关系思想[C]//金泽,赵广明.宗教与哲学: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14:45.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478.
[13]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2.
[14] 胡适.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C]//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8.
[15] 谢林.哲学与宗教[C]//赵鹏译,金泽,赵广明.宗教与哲学:第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9.
[16] 龚鹏程.汉代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
[17]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2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
[18]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3.
【责任编辑吴姣】
UnityofManandNature:TheAnalysisofThoughtsofHeavenandManintheHanDynasty
YANG Qing-hu
(Department of Marxism,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Guizhou 561000;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ncludes a moving process of multiple stages, and Han Dynasty is one stage. The thought of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reflects human initiative, especially the transcendence of Confucianism goes deep from “human” to “benevolence”, with the thought of God gradually losing. Although “Heaven” is the philosophy of the ontology, it is a political service form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ological thought. The expression of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s wrong, but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s right from the level of concern for the people; only in this way, the decline and prosperity of Confucianism, relations between Heaven and Man divided, serving rulers or people, can these questions be easy to understand.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Dong Zhongshu;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theology and politics
B234
A
1005-6378(2017)05-0043-07
10.3969/j.issn.1005-6378.2017.05.008
2016-03-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东汉礼经学学术编年”(17CZX023);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汉礼经学研究:以郑玄‘三礼注’为主”(GD16YZX01)
杨清虎(1981—),男,陕西西乡人,中山大学在读博士,安顺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