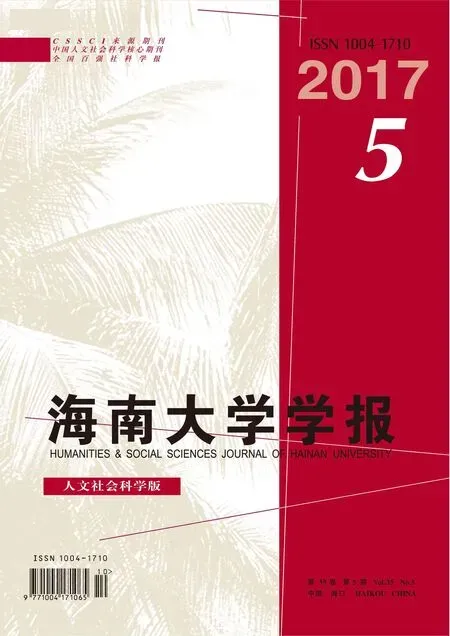天民 民命 民主——论《尚书》民本思想的逻辑建构
林国敬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
天民民命民主——论《尚书》民本思想的逻辑建构
林国敬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
《尚书》民本思想是后世民本思想的源头,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自洽的内在逻辑关系。一,以天民思想为其理论前提,论证民意本于天意,回答君王何要以民为本的终极理论问题;二,通过“民命”(民意)秉承“天命”展开民本思想言说,以此论证王位的合法性,从思想高度促使君王敬德、保民;三,将“天子”诠释为“民主”,以民的视角解释君王的涵义,凸显“民”的主导性地位,完成民本思想建构。《尚书》民本思想的这些内容有力推动了前诸子文化由“神本”向“人本”方向的转变,对之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书》民本思想;逻辑建构;天民;民命;民主;
学人对《尚书》民本思想的研究已非常丰富,但多从天民、君民、“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视角阐发其内容*如梁启超从天民关系把《尚书》的民本思想称为天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结合,并称这种表述在书中已经十分圆满。(梁启超:《先前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页。)台湾学者金耀基从天、民、王三者关系认为天意非显于君王,但显于最广大民众的好恶之中,论证民意即是天意,认为真正临驾于君王之上不是“天”,而是具体的“民”,“自理论言之,天为最高的主权者,事实上则民方是真正的主权所在。”“君王只不过是一个执行民意的权利机关而已。”(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北京: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0-34页。)李存山先生从天民关系角度解读君王的合法性问题,认为《尚书》中“民”是相对于“天”而言,而天意服从民意,是君主政治天下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帝王必须要遵从民意,并之为“天民之一致”思想。(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民主》,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53页。)陈来先生从“敬德”、“保民”视角认为《尚书》“敬德”、“保民”思想使天命具有了确定的道德内涵,表现出政治民本主义,称之为“天民合一”,并从思想发展史的视角认为是天命观的“民意论”转向。(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3-218页。)王友富从明德慎罚、安民利民、敬德保民等内容来阐发《尚书》民本思想内容。(王友富:《尚书民本思想解析》,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以上这些学者对《尚书》民本对论述,皆未涉及其思想背后的逻辑关系,使《尚书》自成体系性的民本思想被肢解成各个部分,削弱其思想的深刻性。,对内蕴其中的逻辑关系阐述较少,甚至被忽视,这使《尚书》民本思想内容被肢解成各个部分,削弱了其思想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本文通过梳理不同篇章中的民本思想核心,揭示其内蕴的逻辑关系,将《尚书》民本思想呈现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天民同构:《尚书》民本思想的理论前提
“民”是《尚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统计今文《尚书》,其中“民”出现187次(不包括“百姓”“众”“人”等),“天”为184次(不包括“上帝”),“德”为116次*由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存在较大争议,行文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10年版)收录的今文内容为依据,对有争议的句子或篇章随行文予以注释和说明。。这说明“民”在《尚书》中受到极大的关注,其程度甚至超过“德”和“天”,这与民是天之民思想密切相关。《尚书》民本思想的“民”与之后民本思想的“民”的一个重大区别便是,《尚书》将“民”纳入天的视阈予以建构,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天民同构理论,即天意与民意之间的相类相通性。这一理论从超验的维度回答了君王何要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成为《尚书》民本思想展开的理论前提。
首先,民与王皆为天之子。《尚书》关于天、民关系的语境非常多,如“惟天监下民”(《商书·高宗肜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周书·大诰》)、“天亦哀于四方民”(《周书·召诰》)。天如此关注下民,因为民是天之子,是天所生,所谓“惟天降命肇我民”(《周书·酒诰》)王先谦解释:“惟天之降命赋性,肇生我民。”*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5页。《诗经》也有同样的表达,如“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大雅·荡》)“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大雅·烝民》)在周人观念中,民皆是天之子,都是上天降命赋性而生,在此意义上,王也是“民”。如“非天夭民,民中绝命。”(《商书·高宗肜日》)这里的“民”就是指王。梁玉绳《瞥记》解释:“祖己曰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为高宗。盖对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诰》曰:‘惟民自速辜。’民为商纣。”*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12页。这里周人把以往的王都称之为“民”。周人称自己的先王也为“民”,如“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商书·高宗肜日》)孙星衍注:“民者,对天之称,谓先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5页。这便从天的视阈解构了笼罩于王头上的神秘性,使民与王处于平等的地位。王的神秘性被解构后,王的不同之处体现为其为元子。《周书 召诰》言:“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孔疏引郑玄注:“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为之首尔。”*孔安国:《尚书正义》,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79-580页。在周人语境下,帝王虽然同是“天生烝民”中的一民,但其特殊性在于他是天之大子,即“元子”。但“元子”却非天生,而是后天选定的,其选定的标准就是谁有才德安民、保民。时王如果不能安民、保民,天就会重新选定“元子”。可见,在周人的语境下王权在谁家并不是天命注定不变的,而是会因民意转移的,因此君王要“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周书·洛诰》)、“用康保民”(《周书·康诰》)“疾敬德”(《周书·召诰》)这便从超验纬度架构起了君王保民、爱民的依据。
其次,天为民择主。周人在接过商家政权后,深入反思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一方面是为了说服商人,周家为什么能够代替商家治理天下,一方面是出于政权的忧患意识。周人认为商朝政权之所以覆灭,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殷人的天命观蕴藏了王朝覆灭的文化陷阱。因为殷人的天命观是专断的,天命不会因为外在原因而转移,永远是属于商人,因此在某种情况下会走向极端,使主政者不再重视民意,走向民众的敌人。《商书·汤逝》引夏桀的话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大传》曰:“伊尹入告于桀曰: ‘大命之亡有日矣。’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18页。孔颖达疏引郑玄注“桀见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尝丧乎?日若丧亡,我与汝亦皆丧亡。引不亡之征,以胁恐下民也。”*孔安国:《尚书正义》,第287页。夏桀认为天命在于身,不会因为民而变,所以他无畏于民,把自己比作太阳,是永远不会覆灭的。桀以此来说明自己王位的永恒性,恐吓下民。商人大概在接过夏人政权后,没有做出深刻的反思,其天命观和夏人的天命观如出一辙。周文王灭黎后,商大臣祖伊非常恐惧,告诉纣王说:“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商书·微子》)祖伊告诉纣王民众无不期盼国家早点灭亡,祈祷大命者的到来,但纣王认为“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记·周本纪》引此为“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墨子·天志中》言“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毋僇其务。’”(《商书·微子》)孙星衍注:“言有命在天,民无能为也。”*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52页。蔡沈:“民虽欲亡我,我之生独不有命在天乎?”*蔡沈:《书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王先谦注:“言纣恃天命不去,不僇力其事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第252页。纣王认为自己之所以是王那是有命在天,是天的赋予,民众怎么能够去之呢?所以他自恃天命在身,无所忌惮,既不敬上帝,也不敬祖先神灵,更不敬民*《周书·牧誓》言:“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商书·微子》言:“今殷民乃攘窃神衹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从这些现象反映了纣王可谓是无所畏,天地神衹、黎民百姓没有是他所敬畏的。《墨子·非命中》言:“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墨子·天志中》也有相同的话:“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毋僇其务。’天亦纵弃纣而不葆。”可见纣王恃专断天命,不敬天、不敬祖先神灵、不敬民是一直在流传的,而后被写进不同的文本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专断天命观所内蕴的文化危机被纣王以极端的方式践行了出来。
周人认为民众之所以需要君王,并不是为了君王本身,而是天为了要安定下民,才需要设定王来作为天的元子,辅助天安定民众。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帝,宠绥四方。”(《周书·泰誓上》)*《泰誓》虽为《古文尚书》,但先秦《孟子·梁惠王下》引曰:“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可见,此句为古《泰誓》所有,作为周人的思想体现是可靠的。这里明确提出设立君是为了能够协助上帝,安定四方百姓。孔颖达解释:“众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也。”“天爱下民,为立君立师者,当能佑助天意,宠安天下,不夺民之财力,不妄非理刑杀,是助天宠爱民也。”*孔安国:《尚书正义》,第405页。民不能自己治理自己,天需选立元子作为民主,治理天下,因此君王的责任就是协助天安定百姓。又如“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周书·洪范》)孔颖达引王肃注:“言天深定下民,与之五常之性,王者当助天和合其居。”*孔安国:《尚书正义》,第447页。王者之所以为王,乃能协和于天,助天安民,否则便失去其合法性。于此意义上,周人称长官为“天牧”,如“尔惟作天牧”(《周书 吕刑》)屈万里注:“天牧,为天治理民众者。”*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在周人看来,臣亦非君之臣而是天之牧,皆因天而立。这也叫“天工人其代之。”(《虞夏书·皋陶谟》)蔡沈:“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无非天事。”*蔡沈:《书集传》,第30页。君臣所做之政务皆为天之功事,是代天理政,所以不得不以民为务。周人通过反思政权的合法性依据,构建起来天、民、王三者之间的关系,王成为天命的代理人,但这种代理不是永远给定的,而是会因民而更替,不能助天安民,天便重新选定代理人。周人将政权的忧患意识凝练到天命观中,改变了以往专断的天命观,将天与民联系起来解释王权的合法性。
再次,天意通于民意。商人的天命观可以说是天民相隔绝的,只有王和巫能与天意相通,这或许与“绝地天通”有关*在原始宗教的第二个阶段,人人可以参与祭祀,家家作巫,人可以任意与天相同,后来民神杂糅扰乱了原先秩序,触怒上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因此,到最后普通人与天之间不能相通,乃由巫师专门来承当这一任务。参看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34页。。在“绝地天通”后,普通民众与天之间没有了沟通的权利,整个权利便落入帝王之中,“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首。”*陈家梦:《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第535页。因此,帝王成了天命的唯一代表人。商人的天命观可以说是这种天民相绝观的典型,民与天之间无涉,天命也与民无涉,只与帝王相关。周人对这一落后的天命观进行了解构,将天的意志与民的意志结合起来,赋予民意以神圣性。书言:“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虞书·皋陶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泰誓中》)*《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鲁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万章上》引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此当为真古文《泰誓》所有,这些天意在于民意的先进思想为周人思想,是武王伐纣时所说的誓词,起先或许为口头流传而后被整理入儒家典籍中。因此,李民认为“凡篇中有‘民’字者亦非商代作品”(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1年,第122页。)李民认为关于“民”的思想皆非商代所有,而是周人所创,其所指当为“民”的天、民同构思想。刘起釪认为:“我们已查得春秋至战国时文献中引武王伐纣的《泰誓》篇中的文句共二十二次,早者为《国语》、《左传》所引,晚者为《孟子》、《管子》及《礼记》所引,其中《国语》、《左传》皆几次引到武王在《泰誓》中所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语,又有相同意义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语。这是正对商代唯知重鬼尊神、绝对相信天命而发,提出了远为进步的天意是根据民意的意思,因而是可信的。”并认为“这是武王、周公所倡导的思想,儒家就更重视这一思想,因而写入了所整理编定的搜集原有流传的资料写成的《皋陶谟》偏中,这是很自然的事。”(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09页。)孔传:“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归者天命之。天视听人君之行,用民为聪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讨之,是天明可畏之效。”*孔安国:《尚书正义》,第153页。蔡沈注:“天之聪明非有视听也,因民之视听也,因民之视听以为聪。天之明畏非有好恶也,因民之好恶以为明畏。”*蔡沈:《书集传》,第31页。“天”以“民”的耳目为耳目,以民的欲求为欲求,民所反对的,天必然会讨伐之,从而体现“天”意志的有效性。“天”是如此地爱“民”,从“民”之所愿,作为继承“天命”的君王,如果不从民之所愿,则天必然会遗弃他。民的意愿成为“天”之意志的体现,天与民在此是一致的,同构的。李存山先生称之为“天民一致”思想,他说“中国上古时期以‘天’为最高的信仰对象,而‘天’的意志又服从于民的意志,这就是儒家的‘天民一致’思想。”*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民主》,《博览群书》,2006年第12期第53页。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天民关系是单向的,而非双向的,即天可以通民意,知民生之疾苦、民之所求,但民不能直接沟通天意,这一点上商、周天命观又是一致的,都将与天沟通的权利限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但相比于商,周人的天民同构思想从终极意义上确立了“民”比王的优先性,“因为皇天授命君主的目的是代行天意来爱护保护人民”*陈来:《殷商的祭祀宗教与西周的天命信仰》,《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第21页。,这一点无疑是先进的,是周人的创见,它为君王爱民、敬民、保民立了一个形上基础,从超验的维度促使王者敬畏民意,敬畏王位,消解了蕴涵于殷商专断天命观中的文化陷阱。
二、“恭承民命”:《尚书》民本思想的逻辑展开
上述《尚书》民本思想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即“民”是天之民,王乃代天治民,天意行于民意。特别是最后一点,是周人天命观的一个显著特征,为西周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天意行于民意之中,君王秉承天意需要通过爱民、保民途径,而非单纯的祭祀上天和祖先神灵,这是商、周天命观的本质区别。商人认为天命是专断于王家的,与民无涉,因此只要通过祭祀祖先神灵和上帝便可获得天意,“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后礼”(《礼记·表记》)可以说是这一天命观的现实体现。因此,殷人的思想开显不出鲜明的民本思想。周人认为天命虽然源于天,但秉承天命不是直接从天这里继承,而要通过“民命”间接地获得天之大命,而后才能被赋予天命,助天安民。这便将天意的表达和天命的秉承途径转移到“民”上来,谁要获得天意,秉承天命治理天下,就需要从“民”处而得,从而从世界观的高度导出西周的民本思想。“恭承民命”可谓是对这一思想的简练概括。
“恭承民命”出自《商书·盘庚下》,其言:“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商书·盘庚下》写作年代虽各家说法不一,有盘庚时代说(马融、郑玄首倡)、小辛时代说(司马迁所创)、殷商时代说(王国维力主之)、殷周之际说(杨筠如主之)、西周初年说(以张西堂《尚书引论》为代表),有春秋时代改定说(顾颉刚持此说),李民、王健认为《盘庚》为周初统治者追忆当年盘庚迁都之事,以帮助周初大规模迁徙殷民措施的推行。(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8页。)此外,屈万里认为此篇“疑为殷末人(甚至宋人)述古之作。”原因是“盘庚之名乃后人所命,非盘庚在世之称,可知本篇非当时所作。小辛时亦不当有盘庚之号,故知亦非作于小辛时也。”(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68页。)笔者认为《盘庚》内容必有商代文献之依据,但我们现代看到的样子必定是经过了周思想的润色和过滤。虽然不能说周之前就不重视民,但将民提升到天的视角加以审视,将天命与民意进行相沟通,则无疑是周人的思想。因为商人的专断天命观开显不出“远为进步的天意是根据民意的意思”。(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09页。)文中所表达的“恭承民命”思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无疑是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是周人先进天、民思想的植入。学者对这里“民命”的解释主要有三义。(1)以孔安国、蔡沈为代表,孔安国:“我当与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长居於此新邑。”*孔安国:《尚书正义》,第361页。蔡沈:“乃上天将复我成汤之德,而治及我国家。我与一二笃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长居于此新邑也。”*蔡沈:《书集传》,第105页。这里孔安国以“奉承民命”解释“恭承民命”,蔡沈以“敬承民命”来解释“恭承民命”,“民命”是民之令,民之所求。(2)以孙星衍、王先谦为代表,孙星衍:“言今天将兴复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我汲汲恭敬以抍民于溺,以顺天命,用久长其地于此新邑”*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第240页。王先谦:“恪恭奉承民命,以顺天心”*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第464页。这里孙星衍、王先谦以“抍民于溺,以顺天命”,“奉承民命,以顺天心”解释“恭承民命”,将“民命”与“天命”相沟通,救民于疾苦,奉承民意即是顺天之命。因此,李民、王健直接认为“民命,即天命。”*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3)以吴汝纶、刘起釪、屈万里为代表,吴汝纶:“言我宜笃敬,奉救民命也。”*吴汝纶:《尚书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0页。刘起釪:“我很急于敬奉上帝之命叫我恢复先祖的业绩来拯救民命。”*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925页屈万里:“恭敬地保护民众的生命”*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第84页。这里吴汝纶、刘起釪和屈万里等人将“民命”解释为民之生命,并不与“天命”相联系。
从语境上来看,《盘庚》中的这句话是说,上帝将复兴高祖之德于我家,我与各位笃敬之臣当敬从民命,永久居住在新邑里。这里上帝复兴其高祖之德,与敬从民命有着联系。“民命”在此语境中既可以为民之生命,也可解释为民之令,但在语义上解释为民之所求,民之所令为长,因为民之所令、民之所求在《尚书》中代表“天命”之所显,是“天命”所诉求的内容在民心中的体现,因而“民命”与“天命”之间才有了沟通,“天命”才主于民心,即张子所言“帝天之命,主于民心。”(《张子全书》卷二《正蒙·天道篇》)但在“民命”所求的具体的内容上,则又内蕴使民以生,救民于疾苦的含义。这一含义在此句中虽未明确说明,但《尚书》中其他关于“天”“民”关系的语境提供了其所内蕴的含义。如“惟天监下民”(《商书·高宗肜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周书·大诰》)、“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周书·康诰》)、“惟天降命肇我民”(《周书·酒诰》)、“天亦哀于四方民”(《周书·召诰》)、“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周书·洛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泰誓上》)等。从中可以看出“天”保佑下民,监视下民、惠利下民、哀怜四方之民、从民所欲,其目的便是使民以生,即“使民有以遂其生”*郭仁成:《尚书今古文全璧》,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28页。,而民之所欲也无非是得以生。因此,“恭承民命”既是敬从民之所令与所求,同时也内在地关涉民之生命,内含使民以生,拯民于困的意义。孙星衍“抍民于溺,以顺天命”,王先谦“奉承民命,以顺天心”便关涉此二义。
因此,从“民命”内涵来讲“天命”便是要君王遵从民心、民意,关切民之疾苦,以助天惠民、爱民,从而使民以利,使民以生,此既是天对王的要求,也是民对王的要求。基于这样一种天民相因的内在逻辑,“民命”内蕴了“天”的意志,违背“民命”即是背弃了“天命”,如商纣王无视民之生命、民之诉求,则是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其最终的结果是“天降丧于殷”。(《周书·酒诰》)任何君王不顾民之命,不顾民之诉求,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即“天命殛之。”(《商书·汤誓》)《尚书》文本所折射的“天命”惩罚,无不体现以“民命”为依据的思想意识。
可以说,“民命”的介入使“天命”的秉承转化于“民”之中,“天命”隐于“民命”,成为“天命”意志的体现,顺民之求,使民以生,即是敬承“天命”。“民”在此意义上具有了神圣性,对“民”不仅要有“敬”,更要有“畏”,如《酒诰》言:“畏天显小民。”“天显”即是“天命”,“民”与“天命”是王所“畏”的共同对象。“天”“民”在此相互关联,传递“天”“民”相因相合之道,正如蔡沈所指“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见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蔡沈:《书集传》,第19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民众的意愿具有体现上天意志的强大道德基础和终极神学基础,所以在理论上民意比起皇天授命的君主更居有优先性。”*陈来:《殷商的祭祀宗教与西周的天命信仰》,《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第21页。其他具体的民本措施和思想,如“抚民以宽”(《周书·大诰)、“惠康小民”(《周书·文侯之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书·无逸》)、“明德慎罚”(《周书·康诰)等皆是在此理论下展开。
三、“天子”诠释为“民主”:《尚书》民本思想的继续与完成
天命的体现和表达最终下落于“民命”之中,使“民命”具有了道德神学依据,王者因“民命”承天命,助天治民,从而获得合法性。至此,可以说《尚书》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民本理论,但并未就此止步。
《周书》进一步提出了“民主”概念,将天子诠释为“民主”,使“民命”成为“天命”意志的体现变得更加彻底,具有了可操作性。书言:“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简代夏作民主。”(《周书·多方》)蔡沈注:“言天惟是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为民之主,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使为民主,而伐夏殄灭之也。”并引吕祖谦之注解:“曰求、曰降,岂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无统,涣散漫流,势不得不归其所聚。而汤之一德,乃所谓‘显休命’之实,一众离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之于汤,汤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岂人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蔡沈:《书集传》,第211页。桀不能助天安民,所以天因此而重新寻民之主,而众多诸侯中唯汤能够聚天下之民,所以天降大命于汤,代替夏朝成为新民主。吕祖谦认为这里的“求”和“降”并非天真的有“求”和“降”的行为私授于汤,而是民众不得不趋向于汤,归于汤,而汤不得不受之。吕氏的解释凸显民的主导地位,将民的集体行为上升为天的意志所体现,传递了民之所求、民心所向即是天之所为的思想意识,将“民主”概念内蕴的思想予以清晰的阐发出来。周代商也是如此:“天惟降时丧,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士,罔堪顾之。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商到了纣王不能善民,只顾自己享乐,天降威,选择能够代替殷命的民主,最后选择了周王。孔传对此解释道:“天惟求汝众方之贤者,大动纣以威,开其能顾天可以代者。”“惟汝众方之中无堪顾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众。”*孔安国:《尚书正义》,第673页。纣王虐待民众,天视下寻找能够代替的人选,众方国人士中唯有周王能善承民意,敬德、保民,因此民不断趋向于周,选择周,天便因此选定周家代替殷商,助天安治天下。因此,周公在面对殷遗民论证自身获得王位合法性时,不讲天求天子,而讲天求民求,体现的是民的自主选择性,凸显了“民”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反过来讲,纣之失天下,也是民的选择,是民要弃纣,因而天最终放弃了纣。纣时“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周书·召诰》)孔颖达疏:“谓纣之时贤智者隐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时无良臣。多行无礼暴虐,于时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携持其妇子,以哀号呼天,告冤枉无辜,往其逃亡,出见执杀。”*孔安国:《尚书正义》,第581页。纣之暴政导致贤良不居位,民众携妻背儿逃亡,是民之弃纣,因此“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周书·召诰》)因纣甚是暴虐,商朝那么多祖先神灵在天也不能保住殷之大命。周人对桀纣失天下的这一解释,有意凸显民在这一过程中的选择性和主导性,其选择之结果,即便是天和祖先神灵也不能更改之。
周人提出“民主”概念,从民的视角重新诠释了君王的涵义,深化了民意为天意之体现的命题。“天子”与“民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不甚相同。“天子”从“天”立意,是天之子,体现其合法性的是“天”,有极大的神秘性和专制性,他人不能撼动天子的地位,唯有“天”才有这个权利。“民主”,依“民”立“主”,君王从“民”中而来,“民”是王的合法性依据,至上神天在此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终极依据。换言之,君王是通过“民”的选择而成为治理天下的人,继而才成为天之元子,因此,即便是普通之民,只要有大德,民归之,同样可成为民主,成为帝王,成为天子。这一思想解构王权的专断性及笼罩于王位之上的宗教神秘性,代之以理性的言说方式,从而使天命显于民命的思想践行具有可操作性。
基于此,周公指出“天命不易,天难谌”“天不可信”(《周书·君奭》)进一步消解了天的宗教性。“天”之所以不可全信,是因为“天命”显于“民命”,没有“民”则“天命”隐而不显,通过民意、民情、民心,“天命”才得以彰显。从而在思想的高度上转向对“民”的敬畏,对民事的专注,这是周人对以往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中国先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天子”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隔断,绝大数情况下王者皆以“天子”自居,在后来民本思想发展中更是如此,“民主”思想仿佛被悬置了起来。假设在后来的民本思想进程中,能将源自《尚书》的“民主”思想贯彻到底并加以发展,让君王的确立实实在在落实到民意的选择上,民主政治在古代便有可能得以产生。然后历史没有假设,《尚书》的“民主”思想如昙花一现,不可不说是一种遗憾。
四、结 语
《尚书》民本思想以天民思想作为其理论前提,以“民命”承接“天命”,将“天子”诠释为“民主”,在看似散漫的论述中,建构起内在的逻辑结构,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人本”方向的转变,深刻影响来之后文化的发展。如“民和而后神降之福 ”(《国语·鲁语上》)、“夫民,神之主也。是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鬼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天生民而树之君”(《左传·文公十三年》》)无不是《尚书》民本思想的传递与延续。经此洗礼,先哲们逐渐放弃对宗教之天的宏大叙事,由重民转而专注于对人和人事本身之善的探索,将宗教之天转化为道德之天或理性之天。《尚书》民本思想于此意义非凡。
HeavenPeople,theWillofthePeopleandthePeopleLord:ALogicalConstructionofPeople-OrientedThoughtinShangShu
LIN Guo-j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ShangShuis the source of later people-oriented thought, showing a strong religious feature and self-consistent internal logic. First, it, with heaven people as its theoretical premise, demonstrates that the will of heaven is in the will of people, which is an ultimate answer to the theoretical question why the king should act on the will of people. Second, that “the will of people adheres to the will of heaven” is used to talk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prov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throne while urging the king to respect virtues and protect the people ideologically. Third, “the son of heaven” is defined as “the people lord”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highligh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eople while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ll these contents about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ShangShugreat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s of previous philosophers from “divinity” to “humanism”,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cultural development.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ShangShu; logical construction; heaven people; the will of people; the people lord
B 22
A
1004-1710(2017)05-0085-07
2016-12-31
林国敬(1984-),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哲学。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