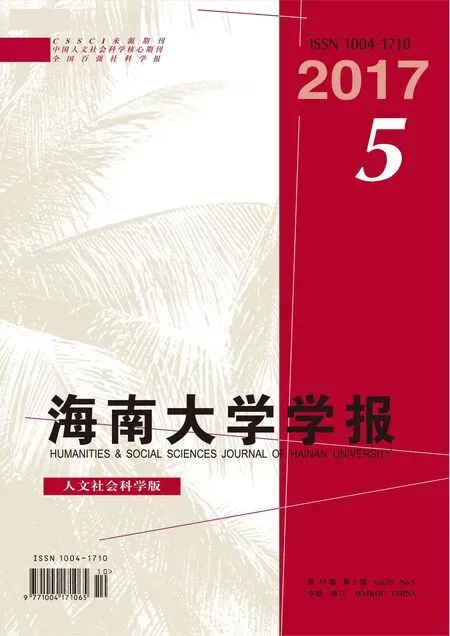从对象世界到生活世界——谈马克思的“生活决定意识”
杨晓晶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2.杭州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0024)
从对象世界到生活世界——谈马克思的“生活决定意识”
杨晓晶1,2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2.杭州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0024)
马克思的“生活决定意识”可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的纲领性概括,相较于传统意识哲学,这乃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大多学者也在此意义上,认为其完成了一次哲学上的理论转向(一般被称为“实践转向”或“生存论转向”),并在此转向中同时开启了一场哲学革命。但是,在西方学界,诸如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却认为,马克思“生活决定意识”所谓的“实践转向”不过是黑格尔绝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这种颠倒只是反过来确证其所反对东西的本质。可见,熟知非真知,“生活决定意识”并非一句看来自明的话,它必须在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对话中重新被审视,才能达到本质的澄明。
意识内在性; 对象性活动;对象世界;生活世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此段话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纲领性概括,亦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生活决定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同时,这一奠基性的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们最重要的启发之一。简要地说,“生活决定意识”要求我们摒弃意识自身存在的优先性,并试图在“生活”中揭示意识的源初发生。正如马克思对意识一词所做的拆字法所表明的,“意识(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Bewusst -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152页。这即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意识哲学”,相反,他改变了问题的提法,试图从“实际生活过程”本身的发展来揭穿意识自身所建立起的种种幻相(正如“意识形态”一词所表明的)。如果我们还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那显而易见的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有一个明显的理论转向,亦即一般被学界称为“实践转向”或者“生存论转向”的那种东西。正如有专家所言:“我们在比较中感觉到'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优越于其他类型的指称,更贴近马克思文本思想的实际。”*吴苑华:《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探讨》2005年第6期,第55页。
鉴于此,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此转向中“揭露超验世界的虚无化本质,最终撼动形而上学思想大厦的基础”*唐忠宝等:《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 论马克思的感性经验世界》,《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第9页。。不过,这一点在当代许多哲学家那里是不被承认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不过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颠倒;即便这形成了与黑格尔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也仍然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生产关系仍然遵从辩证法的劳动过程,其本质依旧在于思想*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4页。。这即是说,即便马克思不从意识、理性、逻辑出发,而从人们的生活、社会存在、物质生产关系出发,这也仍然局限在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之内,因为“生活”本质上仍是意识所建构和把握的对象。
海德格尔这段评论的原则无疑十分明确,可以说他在根基处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革命性,同时,也进一步引发我们对于理性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思考。如果说知识论路向的传统形而上学完成了“意识”对于“生活”无所不在的统治与支配,那么,是否反过来将在其统治下的“生活”置于“意识”之先,就意味着超出了形而上学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某种与意识相对立的东西出发,执著于对意识的“反动”,那也不过是形而上学的颠倒。同样的,即便我们从两者互相作用的方面考察认为,“马克思主张既要有经验的视域,又要有超验的思维”*唐忠宝等:《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 论马克思的感性经验世界》,第7页。,但两者仍以同一个形而上学的根据为前提,这一根据即是对于世界的二重性划分本身(意识—存在、理性—感性、经验—超验)。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海德格尔另一句惊人的话:“从这个观点和角度来看,我可以说,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至。”*F·费迪耶辑录:《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版纪要》,丁耘编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9页。
站在海氏的观点上看,“生活决定意识”乃是一句虚妄且矛盾的话。如果“生活”不过是被意识包裹的知识性存在,那么,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仍旧是被范畴规定了的对象世界,亦即具有某种形而上学本性的意识之内的东西。与其说这是“生活”,不如说这是意识自身外化的结果。说它是“意识决定意识”恐怕更为贴切。如果此言属实,那我们又从何谈论马克思那里存在一个“生活世界”的视域呢?
不论海德格尔所言是否确切,但其所问事关重大,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根本性质,甚至是哲学本身的存在意义。由此可见,马克思或许过分乐观了,“生活决定意识”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一件事,在如今看来仍需我们深思一番。由此,本文所要思索的内容可以被归纳为如下问题:
传统的意识哲学在其完成之处达到了怎样的结论,即它究竟如何理解“生活”?
马克思是否突破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并由此开辟了一条通往“生活世界”的道路?如果是,那又具有怎样的内容?
一、主体性哲学的基本建制
传统形而上学之存在论的根本性质在于主体性,这一原则由笛卡尔的“我思”发端,在黑格尔处达到了真正完成。当笛卡尔以“我思”确立了整个近代形而上学定居的基地之后,存在问题就必须由意识自身来规定。换言之,决定意识的肯定不是“生活”,“意识乃是自我决定,其存在不能用意识之外的,非意识的东西来说明”*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这便是“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原则。不过,诚然笛卡尔发现了“我思”作为决定性的一般主体的地位,但依据黑格尔哲学,其作为主体的主体性的结构与运动仍未获得展开,这个主体必须被提升为绝对的自我认识,所谓“绝对”,即是说,主体作为决定一切客体性的认识,这一运动结构必须被自我认识到。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也唯有如此,主体才能以正确的方式,亦即康德意义上的,变成先验的和完全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存在乃是绝对地自我思考过的思想,存在与思想是同一的。”*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5页。
黑格尔的这一想法意味着,对象之所以成立,是由意识设定出来的,即“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在化建立了事物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8页。。简要地说,这一“外在化”即是“意识表象某物,并把这个被表象者同自身联系同时聚集起来,通过这一聚集,这一被表象者获得了贯通”*海德格尔:《路标》,第505页。。这一贯通过程,即是主体作为主体自发生产出它的主体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黑格尔所谓的“辩证法”。它乃是主体自发的必然行为,其经历的生产过程依据主体性的结构具有三个层次。
首先,作为意识的主体直接联系于它的客体,但这一“直接联系”乃是不确定的、无规定性的东西,黑格尔将其称之为“存在”,亦即最普遍但也最抽象的东西(客体之正题)。其次,客体一经反思作用,便是向意识的转化,它乃作为主体的客体,即是受到意识规定并具有了规定性的客体;同时这一转化也是主体作为与客体相联系的主体被表象出来的自为过程(主体之反题)。最后,这一客体到主体的运动过程,是以反思为中介的,这一中介作用本身必须作为主体的最内在运动加以把握(主体-客体之合题)。整个这一正、反、合的进程便是主体性之自我展开的统一性,它乃是主体性从对立面的统一来把握对立面(也即思辨的),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对“统一”的把握,首先且始终重要的在于对“对立面”本身的把握(反题乃是起支配作用的)。由此,辩证法的全部意义在于,其揭示了精神本身之生产过程作为对立面的矛盾统一。诚然,黑格尔称“辩证法”是“方法”,但这绝不是在说,它是一种思维工具或者探讨哲学的特殊方式;而是说,辩证法是主体性最内在的运动,是绝对者作为现实性之自我安排与组织的生产过程。它是“存在之灵魂”,是现实性的最基本特征。换言之,辩证法作为一种流动着的“方法”,决定一切发生事件,亦即历史。
因此,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形而上学之完成者,其对“生活”的理解之要点可以被归结如下。
1.“生活”不过是意识按其本性所建构起来的对象世界,它乃是意识自身外化的结果。换言之,现实的对象世界必须被收归到意识内部,唯此才获得其本质性。
2.“生活”的全部基础在于理性,它作为意识自我设立的对立面,是必须加以克服和扬弃的对象。
所以,海德格尔将近代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基本建制称为“意识内在性”,是极为精当的。他通过对意识主体性的细致分析,论证了自笛卡尔以来,“我思”之基本建制从未得到质询,并且就其本质来说,根本就无法贯穿对象领域,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而试图从这一封闭的区域中出来,同样亦是自相矛盾的*F·费迪耶辑录:《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版纪要》,第55页。。
通过海氏“意识内在性”的这一总结,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作为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的黑格尔哲学其实从未触及“生活世界”。这话听起来有点好笑甚至狂妄,好像哲学家从来不知道还有生活这回事。但此“生活”非通俗意义上的生命活动,而是在说一个被传统形而上学遮蔽掉的领域。即便黑格尔哲学一再强调“现实”,强调哲学乃是与抽象最为对立的东西,也并不妨碍其在存在论的根本性质上错失了“生活”,因为黑格尔哲学所知道的,只有精神的纯粹范畴规定所建构的“对象世界”,而决非“生活世界”。诚然,黑格尔哲学要求精神进入具体现实之中,但其目的在于确认精神在其对象化的异在中实现自己,并向其本身解放自己,现实之本质性的一度仍在于观念。换言之,意识之所以能够进入并理解生活,乃是因为生活的本质从来就是意识。这就好比,经济学家只知道“经济关系”而不知道“生产关系”,思辨哲学作为他们隐秘的老师,所做的乃是将事物抽象化,并以范畴的形式使其成为意识的对象。但这不过是思维自身的异在性,也就是说,这种对象不可能是“现实生活”。
综上,所有的关键在于:存在不能是意识的对象。而只要我们从意识出发,其实也就不可能赢获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经验,这种经验的获得需要一个与意识不同的领域,一个被海德格尔称为“此在”(Dasein)的领域。所谓“此在”(Dasein),与意识(Bewusstsein)正相比对,意指着将“存在”(sein)从意识(Bewusstsein)的内在性中解放出来,并强调真实的“存在”乃是在意识之外的“存在”*F·费迪耶辑录:《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版纪要》,第55页。。
值得玩味的是,在此海德格尔同样用了马克思对“意识”(Bewusstsein)一词所做的拆字游戏,试图将“sein”(存在)从“Bewusstsein”(意识)的包裹中拯救出来。这样一个巧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马克思是否真的如同海德格尔所说,即便使用同样的拆字法解构了“意识”,也仍然处于“意识内在性”之中呢?
二、意识内在性与对象之虚无性
马克思哲学是否仍在根本上陷于“意识内在性”之中,乃是判决其是否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关键,同时也是其是否发现了被“对象世界”遮蔽的“生活世界”的关键。诚然,我们可以在字面上找到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许多相似之处(正如他们使用了相同的拆字法),但这并不能在本质上构成对海德格尔评价的反驳。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一说“生活”, 亦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范畴论意义下的知识性存在,譬如将“作为物质生产的生活”单纯地理解为“人的经济生活”。在此,这种字面上的比较其实是无效的。与其说这是一种理智上的错误,倒不如说,这是近代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强势遮蔽的结果。正如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也一再被人理解为另一种形而上学一样,这种误解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更可能是不断地实现自身,并成为马克思哲学阐释的一种“常态”。
因此,恐怕我们还是得回到马克思哲学的秘密与诞生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一窥究竟。当然,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奇怪,我们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如此卓著,难道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其次,如果存在“秘密”,那为何这部早期的《手稿》竟然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与诞生地?难道不应该是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吗?
就第一个疑问而言,我们认为,只要一种思想是真正“活着”的,那就意味着它总是处在不断地“被发现”过程中,因而总是有秘密可言的。所谓的“发现”,无非是这种秘密的被揭示。所以我们时常看到,当代思想家能够从伟大的先哲中不断地再次有所“发现”,譬如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之于海德格尔的“在场”,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之于马克思的“历史本质性”。而《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并非我们主观的穿凿附会,乃是与马克思思想中最重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就学界一致公认最重要的“实践”概念来说,第二国际理论家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提供了一个南辕北辙的理解方案。普列汉诺夫径直将这一“实践”规定为“经济活动”,同时还认为马克思完全误解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其实是懂得“实践”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汝信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6-777页。;相对地,卢卡奇则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将“实践”理解为“解除世界的必然性的‘行动’”,用他后来的自我评论来说,这乃是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并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直观”*吴晓明:《哲学之思与社会现实》,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这种对“实践”的对立阐释所透露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它根本上牵涉到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根基。人们认为,迄今为止,这一关乎根本的问题仍未达成某种共识。
这就来到了第二个疑问。如果仅从马克思思想史来说,由于《手稿》所处的独特历史地位,它应当非常有助于回答这一存在论基础。事情也确实如此。如果说马克思1845年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超越费尔巴哈的标志,那么,这种超越必定以某种方式作为潜能存在于《手稿》中了,否则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几乎就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他是如何从一个不成熟的状态,忽然变得成熟的?难道这真如阿尔都塞所说,是某种“奇迹似的、破天荒”的东西?事情若是这样,那么倒不如说是在回避问题了。《手稿》的意义正是在此体现出来。其中的表达确实是新旧参差与不稳定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不稳定”就径直将其理解为“不成熟”。事实上,它包含着马克思与形而上学搏斗的种种努力,并对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生过程及其变革意义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正是在这部手稿的最后一章中,马克思曾经写道,“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意识所以知道对象同它之间的差别的非存在,对象对它来说是非存在,是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可以说,这段话恰如其分地代表了马克思对意识哲学的存在论上的总批判,毫无疑问击中了“意识内在性”的要害。这一批判的要点在于:
1.对象是意识自我外化的产物。这即是说,对象在黑格尔那里“仅仅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差别环节”*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19页。,它作为意识在自己的纯粹活动中被创造出来的对立面,是意识的异在形式,也就是“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
2.对象本身的“非存在”性质。诚然,自我意识声称自己创立了对象,但“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创立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3页。。这即是说,对象实际是一种思想物,它是“事物性”,但绝非“事物本身”。对象作为“对象之假象”,根本上是一种唯灵论的存在物,亦即非存在。
综上,按照黑格尔哲学的原则,对象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必须被收归到意识内部的,一个在实践上有待改造,并加以证实其虚无性的非存在。所以虽然我们称黑格尔哲学为思辨唯心主义,但不能以为意识哲学家们好像愚蠢到只会进行抽象的思辨,一点也不“实践”。只不过他们理解的“实践”,乃是“实践证实”,本质性的一度在于“观念的自我实现”。所以确切地说来,它同样也是“实践唯心主义”。这种“实践唯心主义”亦即被海德格尔称为劳动在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同样的意思马克思也曾说过。他指证道:“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0页。。这里所指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并非只是简单地制造精神产品,而是以意识的知识本性之外化的劳动。所以如果我们将“生活”理解为与意识相持立并有待意识认识并规定的“对象世界”,它就成为意识为了回复自身所需的“材料”,一种有待克服的障碍,从而成为相对于意识来说的“有缺陷的存在物”。这即意味着生活本身不能自足,其本质在其自身之外,是一种为其自身所缺少的东西。
不难看清楚的是,马克思在此揭露的正是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虚无主义,其虚无性就在于,将人类的现实世界理解为出自意识本性的“对象世界”。据此,我们不能同意将马克思视作黑格尔哲学的单纯颠倒而判其为“虚无主义的极至”的说法。恰恰相反的是,马克思可能是最早在存在论根本性质上突破近代形而上学困境的思想家之一。
三、对象性活动与生活世界
基于对黑格尔哲学“对象性本身是虚无性”的阐明,马克思哲学的起点首先就在于试图挽救并重建对象性关系,这一挽救最重要的表述就是“对象性(gegenst?ndliche)活动”。当然,这个说法带有浓重的近代形而上学意味,很容易被我们错认为笛卡儿主义传统中的东西,对此保有警惕是十分正常且必要的。不过同时,我们理解一个术语不能仅仅从其字面的意思,还得深入到该提法本身的语境中去。如果马克思确实要求“对象”不能封闭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对象性活动”一词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指。它首先意味着必须走出意识自身、与意识的知识本性的脱离,而这正与知识论路向形而上学相对。马克思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8页。换言之,“对象性关系”不是一种认识的、逻辑的关系,它乃是认识前的,感性的。譬如太阳的存在根本不能脱离它的对象——植物,“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植物也同样如此,“太阳乃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5页。。这一原则实质是来自费尔巴哈“对象性直观”的启发, 它所表达的是存在无需任何先行的设定,就其内涵来说,它本己地就包含对象,其对象之存在也即其自身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5页。这即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存在”就是对象性关系本身,这种对象性关系是一种原初关联,舍此无从谈起任何存在物的存在。
但如若只是谈论对象性关系,并不谈论人这一特殊的存在物,那么,这实际上是在问人的本质力量同其他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区别。直接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事实上和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没有区别,关键还必须阐明人这样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何以还会有一个世界(区别于环境)?在此,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一个认识论的任务。显而易见的是,在进行任何对世界的认识活动之前世界已然被给予我们,也就是说,人拥有一个世界信念的根源在于,人实际上已经和整个自然界发生了全面的对象性关系。这完全是逻辑前、理性前的。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在马克思那里,人同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从何处发生?(其实这一问法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仿佛人和自然界都已现成存在,而这恰恰是需要追问的,在此限于找不到更好的表述,姑且这样发问。)
这一对象性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着很清晰的阐述:“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3页。这段话沿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类存在物”,并且看起来似乎太平淡无奇了:谁不知道人和动物的差别在于有意识呢?不过说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是不是说“人的生命活动”必须以意识的先在为前提呢?
理解人与动物的差别之关键,就在于如何领会这一“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必须予以明确的是,当我们在谈论人的活动的时候,确实也就承认了意识的存在。但首先,“意识”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即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实在部分,否则那就变成了动物式的自然心理;其次,承认“有意识”并不等同于承认意识的优先地位。按照如上这段话,“意识”即“他本身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可见意识起源于他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活动,这就已经否定了意识作为内在性而生的自发性;同时,“类存在物”这一提法,并不是说“类”已经先行包含在“意识”中,而是说人的“类存在”须臾不能脱离“他自己的活动”,并且这“活动”不是意识先在的设定,而是出于人之对象性本质。 正如马克思在“对象性活动”的提法中明确表达的,对象性活动之设定并非主体,而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即是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意识的优先性,而将本质性的构成建立在“对象性活动”。因此,话不能倒过来说,仿佛人首先得有意识,而后才能有对象性活动。更为真切的实情是,人恰恰是在对象性活动中才产生了意识。所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其实表达的是“对象性活动”的两个方面:就其自觉性的一面而言,它就是意识;而就其现实性的一面而言,它就是劳动。劳动使人同其他存在物的每一种对象性关系都成为有意识的,这就是说,劳动将人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变成了属人的本质力量。“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4页。这意味着,人通过劳动不仅生产自己的生活,同时还把整个自然界作为属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再生产出来,此一再生产的产物,即是“生活世界”。
基于此,我们若要谈论马克思的“生活世界”,就必须从其属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出发。若用某种比拟的说法,这一“生活世界”就是“感性的自然界”,即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7页。,这一“感性的自然界”是不能被理解为理性的知识构造出来的“客观对象”。不仅如此,它甚至更是所有建构在理性法则上的知性科学的真正基础。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可以脱离人的自在自然与脱离自然的抽象个人。人与自然的呈现必须在“生活世界”之生成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恰恰不是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建构,而是来自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历史运动。
综上,如若我们想要概括马克思“生活世界”的基本涵义,想必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点:
1.“生活世界”是理性前、逻辑前的“感性的自然界”,它必须与意识相分离,即它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与自然界的原初关联。
2.“生活世界”作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乃是对象性活动对人来说的生成史,即人的本真的历史性。
由此,我们再看马克思的这段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3页。所谓的“思辨”,指的正是以意识自身之先验展开而设定对象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所谓的“现实生活”“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指的正是摆脱范畴规定的、理性前的“生活世界”的历史运动,这即是“生活决定意识”的根本意蕴。
FromObject-WorldtoLife-World:AnInterpretationofKarlMarx’sViewThatConsciousnessIsDeterminedbyLife
YANG Xiao-j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at “consciousness is determined by life” by Marx can be regarded as the guiding summary for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is completely a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 in contrast with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In this respect, most of the scholars hold that it completes a theoretical turn in philosophy, generally as “practical turn” or existential turn, while starting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n this turn. However, Martin Heidegger a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field regard the “practical turn” stated by Marx in the statement that “consciousness is determined by life” as simply the reversal of Hegel’s absolute metaphysics, which just in turn confirms the essence of what Marx has argued against. As indicated, what is known well is not the same as what is known truly. And that “consciousness is determined by life” is not self-evident, which must be further reviewed in a critical conversation with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so as to clarify its essence.
interiority of consciousness; subjective activity; object-world; life-world
B 016
A
1004-1710(2017)05-0073-06
2017-07-03
杨晓晶(1987-),男,江苏高邮人,杭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部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严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