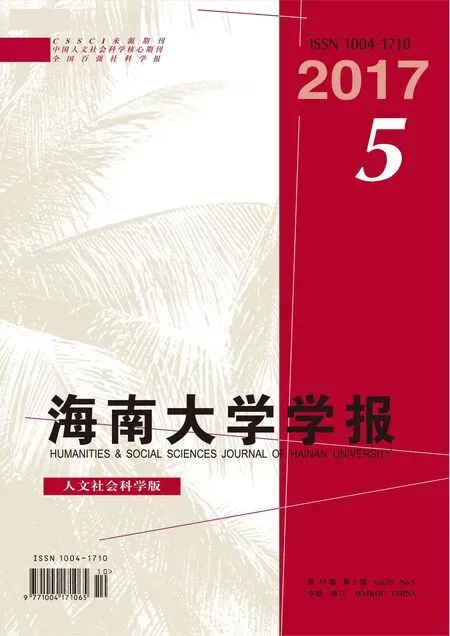柏拉图笔下的“自然状态”问题
张文涛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柏拉图笔下的“自然状态”问题
张文涛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尽管表面上并没有出现“自然状态”这一字眼,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等人在建构合宜的政治制度时,已经在实质上面临着类似现代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学说及相应理论立场的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的同时,苏格拉底等人也发展出了不同的“自然状态”理解及相应的自然人性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不同于民主制构想的君主制或混合制构想。
柏拉图;苏格拉底;自然状态;《王制》
尽管现代哲人如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学说颇为复杂,但就其最关键的要素而言,其一在于对人性或人的自然的理解,其二在于对与此人性理解相应的缺乏共同权威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生存关系或状态的看法。显然,更为紧要的是第一点,它乃是第二点的理论基础。现代“自然状态”学说仍然根植于一种“自然论”或“人性论”,这种新的现代人性论与古代人性论在最紧要处针锋相对*基于对个体人性(小写的人)的理解来建构国家政制(大写的人),这既是柏拉图在《王制》(《理想国》)中的基本思路,也同样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基本思路,这一点从《利维坦》的前言已经可以清楚看出。霍布斯:《利维坦》(引言),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
在《利维坦》的前言,霍布斯便开宗明义地说明,为了论述“利维坦”这个“人造人”,必须首先要弄清楚作为个体的自然人,其基本任务仍然与古典哲人苏格拉底肩负的哲学使命“认识你自己”并无二致。不仅如此,霍布斯还特别强调,对人性的认识不能仅仅依据人的外在“行动”,从外在行动来判断一个人是靠不住的;必须“探究人心”,也就是说,探究人的内在意愿、害怕、希望、思考、推理等。用柏拉图的话说,即探究人的灵魂的本性。在这一点上,霍布斯的思路仍然与古典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保持一致:从《王制》(《理想国》)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发展出来的真正有效探究人性、人的德性的思路,正是从关注人的可见的外在行动,转入考察不可见的人的内在灵魂。不过,在另一更要害的地方,霍布斯拉开了与古典哲人的距离:“由于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与别人的相似”,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对自己内心的反省,从而“在类似的情况下了解和知道别人的思想感情”*霍布斯:《利维坦》,第2页。。这一认识原则实际上隐含着霍布斯关于人性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自然人性是普遍平等的*在笔者看来,霍布斯在《利维坦》前言中所展示的思路,很像是在模仿柏拉图《王制》中大写的人与小写的人相类比的方案。在《王制》中,苏格拉底的这一类比方案显得颇成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部分失败的;霍布斯重拾这一方案,显然是要在古典哲人失败的地方重寻成功的可能。。
不少论者都指出,作为现代政治哲学之理论基石的“自然状态”概念,并非霍布斯的发明,从思想史上看,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久远的古希腊政治哲学传统*Thomas Cole,“Democritus and the Sources of Greek Anthropology”,Ohio: Press of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1967,pp. 148-152. 刘小枫:《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柏拉图〈普罗塔戈拉〉中的神话解析》,《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第5-12页。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90-106页。。本文试图佐证这一看法,尝试指出,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尽管表面上并没有出现“自然状态”这一字眼,但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等人在建构合宜的政治制度时,已经在实质上面临着类似现代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学说及相应理论立场的挑战;在应对这一挑战的同时,苏格拉底等人也发展出了不同的“自然状态”理解及相应的自然人性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不同于民主制构想的君主制或混合制构想*因此本文将“自然状态”概念打上引号,意在表明柏拉图对话中关于“自然状态”学说虽无概念之名、但有思想之实的这一状况。。考虑到篇幅及论题的复杂性,本文仅仅尝试处理《王制》的相关文本及其思想内涵。
一、《王制》中苏格拉底面对的“自然状态”问题
在《王制》中,类似霍布斯式的理论立场,首先来自卷一中苏格拉底与之鏖战的智术师特拉绪马科斯。特拉绪马科斯关于正义的界定简洁明了,“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王制》338c)*柏拉图:《王制》,史毅仁译,未刊稿,下引此书皆随文夹注。。通过仔细而透彻的分析,可看出特拉绪马科斯这一正义界定背后的诸多看法,特别是他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
特拉绪马科斯所谓的强者其实是指各种政制下的统治者,由此,其正义观全面而准确地理解起来便是:强者(统治者)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正义的。对弱者(被统治者)来说,正义意味着遵守强者(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从而做的是对强者有利、对自己无利的事情,并由此“完成”或实现了强者的利益。如果要做对自己有利、而非对强者有利的事,弱者只能违反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从而成为“不义”的人(参338e-339a,339c10)。
仔细思考特拉绪马科斯的正义解释,可以发现至少这样几个关键要点:(1)正义即城邦的法律,它体现了统治者或强者的利益,源于强者的意志。(2)对弱者来说,正义即守法(不义即违法)。要完整理解“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还必须得补上“不义是自己[弱者]的利益和好处”这一对立面(344c,参367c)。(3)弱者的利益与强者的利益相互冲突(而且,弱者之间的利益也相互冲突)。(4)但另一方面,弱者的利益与强者的利益(以及弱者之间的利益)在含义上又是一致的,指财富、物质等属己的“私人利益”*关于“私人利益”这一用语参《王制》卷二360c。。 只有这种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以追求这种利益为目的或达到“幸福”。由于这种利益才是真正的、最好的利益,特氏的正义-利益观还暗含着的一点看法是,属人的最好生活应该是最大化、无止境地追求这种利益。无疑,特拉绪马科斯看重的这种私人利益,也正是霍布斯等现代政治哲人强调的自我保存及发展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人的基本利益。
在特拉绪马科斯对正义-利益的理解中,蕴藏着他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或假设:所有人,无论他是强者(统治者)还是弱者(被统治者),其自然本性都是崇尚物质利益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在利益问题上的普遍冲突,恰恰基于他们对何为利益(由此何为“好”及“好”的生活)问题上的普遍一致。“特拉绪马科斯想当然地认为,人的特性都是‘贪婪’(pleonexia)的”*Jacob Howland,“The Republic: The Odyssey of Philosophy”,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1993,p. 71.。对特氏来说,人性没有其他可能;人性的全部可能都在于追求他所理解的利益,满足他所理解的欲望。质言之,特拉绪马科斯持有的是一种普遍平等的人性论。
特拉绪马科斯通过法律来解释正义的这种正义观可称之为“法律正义观”。由于他进一步将统治者(或统治者的命令、意志)理解为法律的来源,这种等同正义与法律的观念,也就意味着一种关于法律或正义的约定论或习俗论。按照这种习俗论,正义在法律之外没有其他或更高的来源,而法律则除了城邦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之外没有其他或更高的来源。城邦之外无法律,法律之外无正义。关于正义、道德的这种习俗论,施特劳斯曾称之为“庸常的习俗主义”,并就以《王制》中的特拉绪马科斯为典型代表*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5页。施特劳斯:《柏拉图》,见施特劳斯,克罗波西编:《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在特拉绪马科斯本人所表达的正义看法里,只有“习俗正义观”,而没有比如“自然正义观”*Leo Strauss,“City and Ma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 75. Seth Benardete,“Socrate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 26.。
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表述看起来比较粗糙,其实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后来霍布斯等人通过“自然状态”概念发展出来的系统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元素,特别是对利益或人性欲望的理解和普遍平等的人性假设。甚至可以说,现代自然状态的“战争状态”含义,也已内含其中:相比于此前玻勒马科斯区分敌友、助友损敌的正义观,一个持特拉绪马科斯正义观从而必然无止境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是没有“朋友”的,人与人之间由此只能互为“敌人”。
当然,与现代哲人的理论表述相比,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表述尚缺乏一个根本环节,这就是“自然”概念。在特拉绪马科斯看来,一个人(哪怕违反法律或“行不义”地)追求或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其实是“好”的或“正当”的(参344c、348d、351b),但由于理论建构上的缺陷,一个如此行动的弱者(被统治者、大多数人)只能成为一个违法者、不义者、一个不道德的人。只有一种情形例外:当一个人成为 “僭主”的时候,最大化地追逐利益与遵守法律便统一起来了。“非道德主义”由此成为特拉绪马科斯理论表述的必然结果。如果引入“自然”概念,情况将会在根本上得到改观。推进这一重大理论建构的,在《王制》中是聪明的哲学青年格劳孔,而柏拉图另一篇对话《高尔吉亚》中的卡里克勒斯则可谓是这一理论建构的最终完成者。
实际上,在特拉绪马科斯的看法中,自然概念呼之欲出,他其实只需补充一句,即每个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自然的、自然正当的,这样便可以达到真正与苏格拉底相抗衡的理论水平(因为苏格拉底后来关于正义的理论建构正是基于自然概念)。特氏自己没有补上,但《王制》卷二伊始,格劳孔便帮他补上了。格劳孔们不满于卷一中苏格拉底对特拉绪马科斯的反驳,认为首先应该将特氏的理论立场推演清楚,然后再让苏格拉底来彻底清算。
格劳孔对特拉绪马科斯理论的发展,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自然”概念(358e),二是提出“契约”概念(359a):
他们说,行不义自然就好,遭受不义自然就坏,但遭受不义的坏远远超过行不义的好;因此,当他们彼此行不义又遭受不义,尝过这两种滋味儿以后,似乎不如——对那些没有能力逃避一者而选择另一者的人而言——在他们自己之间定下一个既不准行不义又不会遭受不义的契约。这样一来,他们开始定下他们自己的诸多法律和契约,将法律要求的事情称为合法和正义的事情。因此,这就是正义的生成和存在(《王制》358e-359a)。
“行不义”在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表述中是“好”的,但格劳孔现在为它补上了关键的“自然”一语,于是,习俗性或约定性的“好”就成了“自然就好”。“自然就好”非常像现代政治哲人说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正当”)。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就好”是相互冲突的,人人不加约束地依循“自然就好”的原则行事,必然引发“行不义”与“受不义”的双重结果(“彼此行不义又遭受不义”),即“好”“坏”并存的双重结果。但没有人想要“坏”的结果,于是,人与人(用特拉绪马科斯的表述方式就是弱者与弱者)联合起来,定下一个折中的“契约”,尽量让大家都避免坏结果而实现好结果。这一契约尤其体现为现实政治生活中实际制定的法律,并成为现实生活中规约人之行动的“正义”观念的来源和保障。
注意,格劳孔这里表述的“契约”原则意味着对“自然就好”的限制或折中,它与霍布斯说的“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完全一致,这一原则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订立契约者的“好处”*对比霍布斯所言:“当一个人转让他的权利或放弃他的权利时,那总是由于考虑到对方将某种权利回让给他,要不然就是因为他希望由此得到某种别的好处。因为这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任何人的自愿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霍布斯:《利维坦》,第100页)。,虽然现在这一“好处”受到了无奈的限制。因此,格劳孔将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立场主要朝民主制方向进行推演,从而避免了特氏那里赤裸裸的对僭主制的张扬。不过,这一“避免”只是暂时的,因为接下来,格劳孔马上往前走向了特氏的僭主制立场:如果一个人在“能力”上特别出众,有特别的行不义的能力,那么,他才不会与别人订立什么契约,或者说不会理会现实契约(法律)的限制,而会去放手大干,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自然”的“好”*格劳孔说:“如果最好的是行不义而不受惩罚,最坏是遭受不义而直接没有能力报复,那么正义就处在中间。人们关心正义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它由于没有行不义的能力而受崇敬。……正义的自然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自然而然地从这些东西当中产生出来”(359a-b)。。另一种情况是(格劳孔通过讲述居吉斯指环的故事表明),如果有某种特殊的能力或机会,让他行不义而不被发现,这个人也会像前述那样行事。因此,格劳孔说,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正义者还是不义者,他们在人性或自然欲望上都是一样的:“所有天性(自然)都认为这是好的,但法律强行阻止它,使它崇奉平等。”(359c)这句话的前半部分点出了特拉绪马科斯的看法所蕴藏的关于人性自然平等的基本假设,后半部分则暗中指出崇奉平等的民主制其实潜藏着僭主制式的个人生活价值理想。
如果把特拉绪马科斯与格劳孔的理论表述结合起来,可以说,这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常类似于“自然状态”的看法,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原初的、在没有公共权威约束下的相互冲突、相互敌对的战争状态。尽管特氏和格劳孔都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但从他们对自然人性的理解不难推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就“自然权利”概念而论,格劳孔说的“自然就好”已经基本与之一致;而在《高尔吉亚》中的卡利克勒斯那里,“自然法”这一概念得到了西方思想史上的首次熔铸,其欲表达的思想内容在实质上与特拉绪马科斯和这里的格劳孔所欲表达的并无不同:
就因为这些,这就被人凭法律讲成既不义又可耻,即力求比多数人拥有更多,他们称之为行不义。但至少我相信,自然本身昭示,这恰恰是正义的,即更优者比更差者、更能干者比更无能者拥有更多。但显然,在多数地方情况恰恰如此,无论在其他生物中,还是在属人的所有城邦和族类中,正义已经这样得到规定,即强者统治弱者并拥有更多。因为,薛西斯率兵反对希腊,或者他父亲反对西徐亚人,还能使用何种正义呢? 或者,某人还有其他无数这类事例可讲?不过,我相信,这些人都根据正义的自然做这些事情,对,凭主神宙斯起誓,至少根据自然法,尽管也许并非根据我们制定的那种法律。*柏拉图《高尔吉亚》483c-e(李致远译文)。
不过,需要特别分析的一点是,在格劳孔的理论表述中,“自然就好”与“正义”仍然是冲突的。一个人追求“自然”的好处,却仍然可能处于“不义”的境地。从自然的“好”无法推出自然的“正义”。这一矛盾或困难的根源,在于格劳孔对法律的理解仍被限制于习俗性、契约性或实定性理解中,这一点是特拉绪马科斯法律理解的根本特征,格劳孔的法律理解维持了这一根本特征。要解决这一矛盾或困难,必须突破对法律的习俗性、契约性或实定性理解,走向对法律的“自然性”理解,从而提出与实定法不同或比它更高的“自然法”。在柏拉图笔下,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正是《高尔吉亚》中异常强悍的智术师卡利克勒斯完成的。苏格拉底可以在《王制》中驯服特拉绪马科斯,但却未能、也不可能驯服《高尔吉亚》中的卡利克勒斯。通过对自然概念的全面运用,卡利克勒斯在理论上完成了自然的好、自然的正义、自然的法的统一。在卡利克勒斯这里,与在特拉绪马科斯-格劳孔那里一样,正义仍然是强者的利益;与他们不同的是,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追求利益而违背实定法律的人会背上不义、不道德的罪名,但依据更高的原则看,他的做法就是合法的(合乎自然法)、正义的(合乎自然正义)、道德的。这样,在特拉绪马科斯那里的“不道德”诉求就完全得到了洗地漂白。
回到《王制》中的特拉绪马科斯。作为一个问题来看,特拉绪马科斯的正义立场及其背后蕴含的人性理解,其根本意义在于提出了政治问题最基本的困难:如何避免政治共同体的内在裂痕。如果共同体中人人都只追求自己的私利,那么,无论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还是被统治者相互之间,其利益必然都是相互冲突的,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如何可能存在便成为一道根本难题。格劳孔通过对特拉绪马科斯立场的推演发展出了民主制的“契约”原则,显然,前述公共利益或道德基础的难题由此也自然被传递到民主制的基础理论之中。现代政治哲人所发展的民主制理论仍然无法避免这一最根本的政治-道德困境。
二、苏格拉底对“自然状态”问题的重新思考
面对特拉绪马科斯-格劳孔的挑战,苏格拉底在《王制》接下来的全部篇幅中展开了严肃应对。因此严格来说,苏格拉底对特拉绪马科斯的反驳,并不仅仅展现为卷一中非常具有修辞性的回击,毋宁说更体现为卷二后半部分直至卷十结尾的全部努力。由于格劳孔(也包括之后的阿德曼托斯*在格劳孔对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推演之后,阿德曼托斯还继续做了重要补充,一个关键之处仍然在于对人之自然(天性)的理解。不过,阿德曼托斯对天性的理解并不与格劳孔完全一致。限于篇幅,这里暂略讨论。)特别提出了自然(“天性”)的概念,苏格拉底后来建构正义的方法,从根本上看,正是由此依据于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理解,更准确而言对人的灵魂之自然的理解。
不过,表面上看,苏格拉底的方法首先在于遵循大写正义(城邦)与小写正义(灵魂)的类比。在运用这一类比方法的初期,可以说,他也提出了另外一种非常类似于“自然状态”学说的论述。他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辞”中的城邦(或政制)的起源问题:
我相信,出现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足,需要很多东西。你相信城邦的建立还有别的起源(或译“始基”)吗?(369b)
苏格拉底这里对城邦起源的设想,无疑不是历史性而是理论性的,其思考原则正是“依据自然”(370c)。他提出了一种原初的社会分工论来建构原初的城邦,人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食物、房子、衣服、鞋子等)是这一分工的自然依据。他还对为何采纳这一依据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是因为人之天性(自然)的不同,二是因为效率问题。可见,苏格拉底的分工论已经隐藏着对人性的差异性理解,虽然现在这一差异性理解距离将来他对人性或灵魂的等级性理解还非常遥远。
凭借人的自然需求建构起来的原初城邦,是一个健康、质朴的城邦。这个城邦存在着基于自然分工的群居性社会秩序,存在着城邦的“管理者”(371c),但是它还没有权威性的统治者,城邦中还缺乏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因此严格说来,这还不是一个“政治”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苏格拉底描述的这个“猪的城邦”类似于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如果可以这样看待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在苏格拉底所描述的这种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那种人与人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性、战争性关系。这种自然状态与隐藏在特拉绪马科斯理论中的自然状态或后来霍布斯所设想的自然状态相比显得全然不同。为什么不同?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在于,苏格拉底所假设的这种自然状态,从人性基础上看,乃基于必要的“需求”,而非基于后来发展出发烧的现实城邦的非必要性需求(373d)或“欲望”。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神”并没有缺席于人的群居生活之中(372b),但无论是在隐含于特拉绪马科斯立场之中的自然状态还是霍布斯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中,“神”均是明显缺席的*限于篇幅和论题,“神”的问题在这里无法展开,暂且作一简单交代:苏格拉底与特拉绪马科斯的区分似乎在于统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是哲人还是非哲人,但这样理解二者的区别远不充分和彻底。即便法律来源于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但特拉绪马科斯认为,统治者的个人命令或意志便是法律的唯一、最终来源,而满足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则是法律的唯一目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并不这样认为。一方面,在立法的目的或为谁的利益上,苏格拉底认为应当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或者说城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而绝非统治者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立法者立法的时候还有外在于、高于自己意志的依据——神。特拉绪马科斯这里统治者立法的私利论和“神”(宗教)的缺失,是其关于法律的非常狭隘的城邦来源论最根本的两个特征。关于后者可以注意的是,克法洛斯的离开某种意义上确实意味着“神”(宗教)的退场,但这一退场并没有导致苏格拉底那里“神”的问题的消失,反而苏格拉底后面要建立新的“神学”(379a),而城邦中立法者必须要考虑的最重要法律便是关于神的相关法律(427b)。柏拉图对这一问题的真正展开,当然是在《法义》。关于卷一中“神”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法洛斯的正义理解中,“神”是在场的(331b)。但这一理解被其子玻勒马科斯“继承”下去之后,旋即被遗忘,这一遗忘成了“剧情”层面特拉绪马科斯正义观念出场的基本背景(正如Seth Benardete所说,“克法洛斯的离开,让讨论从圣神者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也就释放出了特拉绪马科斯[这头怪兽]”。Seth Benardete,“Socrates’ Second Sailing: On Plato’s Republic”,p.20)。当然,一般而言,这也就是特拉绪马科斯所在之列、智术师出现的背景。在卷二开头格劳孔、特别是阿德曼托斯对特氏看法的补充或发展中,“神”是关键问题之一,两兄弟对“神”的问题的强调,恰恰凸显了特氏立场出现的背景和根源。真正重新拾起“神”的问题的,正是提出要建立新神学的苏格拉底。没有这一新神学的视域,特拉绪马科斯的正义立场无法得到最根本的抵制。。
在发烧的城邦中,“战争”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这个奢侈的城邦中,正义与不义也就“自然地”生长起来(372e)。当然,这个发烧的现实城邦,已经走出了健康城邦那种非战争性的自然状态,进入到了有统治者和军队(二者统称为城邦的护卫者)及被统治者的文明状态或政治状态之中。在接下去对正义城邦的建构过程中,特别是对个体正义的解释中,苏格拉底慢慢给出了关于人性或人之自然(灵魂)的非平等性理解,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他才得以全面反驳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立场。简单地说,苏格拉底区分了构成灵魂的三个基本成分,即理性、血气和欲望,进而看到在具体的个体身上三种灵魂成分组成比例的差别,由此形成了对人性的差等性理解。这一理解认为,灵魂中理性部分比较发达的始终是极少数人,但这极少数人恰恰是最有资格做统治者的人选。可是,由于不同灵魂部分的爱欲根本不同(理性爱欲智慧、血气爱欲荣誉、欲望爱欲钱财和食色),人性中自然性的内在分裂便预示着政治共同体中的内在分裂(内讧)这一自然性的危机。
但是,我们在苏格拉底一开始对处于“自然状态”的健康城邦的描述中,并没有看到这一人性的自然分裂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一方面,苏格拉底隐藏人性自然冲突的原初状态,是为了拉开与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距离,从而故意在其设想的自然状态中描绘出一番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景象;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苏格拉底所理解的人性中内在的自然冲突(它也必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冲突),与特拉绪马科斯立场所暗示的人与人之间外在的自然冲突,并非一回事。前者基于人性的自然差等论,后者基于人性的自然平等论。由于必要需求向非必要需求的发展,隐藏在原初自然状态中的人性的质朴差异,才最终发展为人性的全面的差异(差等)。
在健康城邦那种原初的自然状态的群居生活中,既没有统治者,也没有哲学。在发烧的现实城邦中,统治者有了,哲学也有了,而哲人与统治者的自然性冲突也就成为从现实城邦走向“美好城邦”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或者说悖论)的体现就是苏格拉底在卷一中反驳特拉绪马科斯时便已暗中指出的(参345e以下),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去攫取特拉绪马科斯所说的那种私人利益或者去当一个统治者,因此人性并非如特氏所理解的都一个样,而且,恰恰最有能力或资格做统治者的哲人自身却最不愿意去统治。由此,智慧与权力、爱智慧者与爱权力者如何可能结合,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呈现出来的解决政治问题最根本的困难*这里值得对“血气”做一点关注。从特拉绪马科斯的立场看,受欲望的驱动,人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都想当统治者,政治问题的解决当然极为困难(最好方式也就是格劳孔所推演的基于契约论的民主制构想)。从苏格拉底的立场看,受理性的驱动,懂得如何治理城邦的热爱智慧的哲人又不愿意去统治(暂且不说相反的一面),政治困难仍然无从解决(除非有一种逼迫性的力量出现或某种机缘出现)。自愿的统治者却导致败坏的政治状况,可以导致优良政治状况的人又不愿去统治。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自愿的统治者仍然可能导致良好的政治状况?从根本上说,这一可能性的人性基础何在?恰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血气”对于解决政治困难的积极性所在。一个受血气驱动的人,其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不为满足身体性欲望(最极端情形便是不顾对生命的自我保存),也不为对智慧的追求,而是对遭受到的不义的愤怒和自然(自愿)性的勇敢反抗。苏格拉底看到,人性中这种抵抗不义的自然性或自愿性冲动,可能成为解决政治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除此之外还得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血气必须接受理性的“呼唤”或者说制约,二是血气如何可能从对自己所受不义的愤怒扩展至对同胞或整个城邦所受不义的愤怒(参440c-d)。另外,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什么在苏格拉底这里,人性的自然差等状况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战争状态。一方面,基于血气的人性的自然冲动超出了基于欲望的“自我保存”冲动(勇敢而不顾失去生命),另一方面,基于智慧追求的更高的生命冲动更是远远超出了“自我保存”的冲动(智慧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对生命-死亡问题的理解)。从柏拉图-苏格拉底的人性理解出发,即便像霍布斯那样去假设一种公共权威缺乏下的自然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人性的多样性(人性原初的非同质性)使得人与人的全面战争并不必然可能,或者说并不是唯一的可能,虽然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这一状态肯定是需要人力去进行扭合的非政治状态。。为解决这一困难,也就是说在全然不同于特拉绪马科斯的人性理解的基础上建构正义而美好的政治秩序,是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努力之一。我们知道,他为此提出的最终建议,是哲人当王的君主制或贤人政制构想。
IssueofStateofNatureinPlato
ZHANG Wen-tao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lthough “state of nature” does not appear as the exact words in Plato’s dialogues, it can still be noticed clearly that Socrates and other protagonists, while founding the decent political system, have already confronted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doctrine of “state of nature” similar to the modern philosophers like Thomas Hobbes and its relevant theoretical standpoints. Wrestling with these challenges, Socrates and others have also develop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state of nature” and corresponding hypothesis of the natural human nature, which are used as the bases to construct their conceit of monarchy or mixed government different from that of democracy.
Plato; Socrates; state of nature;Republic
B 502.231
A
1004-1710(2017)05-0014-06
2017-09-0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06112015CDJXY470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QDXWL-2014-Z014)
张文涛(1975 - ),男,四川简阳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西方古典学等研究。
[责任编辑:严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