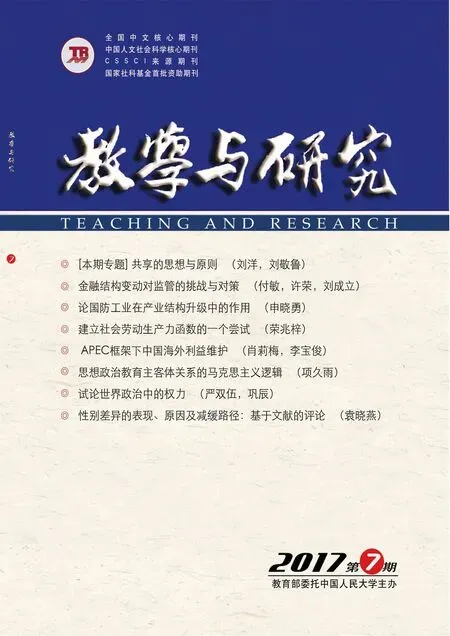延伸与超越: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思考
延伸与超越: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思考
吴文珑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从学理意义上阐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含义、特征与相互关系;初次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动力问题;论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路径。这种认识脉络基本上遵循着从“是什么”、“为什么”到“怎么做”的逻辑架构。从宏观思想演变的视角来看,其认识既有思想继承和完善的一面,又有思想创新和超越的一面。批判地吸收其思想资源,无疑是有意义的。
延安时期是学界公认的文化思想极富创造力和个性的时期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视野中,它也是一个需要从不同角度反复研究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如诸多既有研究成果所表明的,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是中共思想理论界之政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从建党至今,这一特征一以贯之,没有发生性质上的显著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共思想理论界的这一政治理想部分变成了现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思考是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相始终的,这种学理意义上的探讨在建党初期短暂出现后,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又真正重新开始*参见赵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十大理论创新》,《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庞松:《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坐标》,《党的文献》2007年第1期;王鹏程:《恽代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探微》,《理论学刊》2005年第3期;王彦民:《五四运动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论视野》1999年第3期。这些研究成果总体呈现两种特征:一是集中于对建党初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之社会主义观的考察,中间时期成为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二是注重对思想精英和经典理论的意义强调与内涵溯源,一般的知识和思想世界未能得到开发。应该说,就延安时期而言,这一问题没有成为集中讨论的热点,主要是因为中共在抗战初举的是“三民主义”旗帜,后来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问题,改成“新民主主义”,而未凸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共思想理论界没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研究、阐释和讨论。。但在笔者看来,思想的“断裂”或“空白”所掩盖的恰恰是一种有意义的延续,在思想似乎停滞的时代,思想的历史却仍在前行。因此,在社会主义由理想转变为现实内容之前,中共思想理论界同样存在着一个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延伸着建党以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认知,成为连接建党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脉络的重要枢纽。基于这种判断,本文将对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认识与思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影响和意义等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延安时期的开启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繁荣的来临
随着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的基本结束及其落户陕北,中共开始步入延安时代。在民族战争迫临的危急关头,中共领导人及党内理论工作者愈发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于巩固党组织和解决其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在此形势下,他们积极成立研究团体、开展学习竞赛、奖励自由研究、做好宣传教育。所有这些,都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得到凸显,由此形成了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
中共中央落户陕北后,根据党自身实际情况和现实任务的发展变化,以巩固党的领导、加强干部教育和提升理论兴趣为目标的诉求在党内逐渐形成,受此影响,一大批学术机构和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尤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并决定“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前后,[1](P533)中共中央愈发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于培养新干部和建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组织的重要意义,努力通过开展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和“巩固党”等措施,弥补由于剧烈的革命战争形势所导致的党员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缺失。期间,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与延安新哲学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等学术研究团体为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整风开始后,随着思想战线上“三风”的进一步被整顿和肃清,中共创制的学习制度开始步入更加规范的轨道。
思想理论界则致力于清除侵略者与汉奸提出的侵略理论和封建思想,通过发起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广大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纷纷将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开启了学术运动的新局面。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优待知识分子、奖励科学研究政策的感召下,党内理论工作者清楚地认识到同官方保持理论互动的重要性。自1937年开始,艾思奇、何干之、陈伯达、张闻天、胡乔木等陆续同毛泽东互通信件,商讨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同时,党内理论工作者还意识到,要清除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封建残余,抵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就必须做好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宣传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的指导下,各理论研究机构先后翻译出版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和《列宁选集》16卷本等在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它们为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知识资源。
上述重视理论研究、追求学术自由的时代氛围,构成中共回溯历史、思索民族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在此期间,全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纪念马克思诞辰日为主旨的“五五”学习节活动,在延安和重庆等地的中共领导人和吴亮平、许涤新等党内知识分子纷纷在《解放》、《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回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功绩,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深入解读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掀起了自建党以来的一次学习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潮。同时,这些文章作为对国民党政论家叶青“假三民主义”错误言论的回应,它们在阐释和解读新民主主义的有关理论、梳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批判叶青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曲解和污蔑、树立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信仰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
总之,延安时期,中共根据自身的理论状况和面临的现实斗争形势,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得到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在一系列有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共思想理论界广泛地学习、讨论和阐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关理论问题,从而有力地促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史上一个“黄金时期”的来临。
二、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的阐释
自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早期的共产党人在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首先思考和回答的常常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类前提性问题。如李达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初期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什么,我以为这应该首先在这里说明。”[2](P61)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和思考仍然延续了这一基本脉络,他们在理解、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也首先以两者的概念、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切入点。
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而言,由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社会主张,而且也是现实的社会运动,因此,中共思想理论界对两者的概念分别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解释。张闻天等认为,社会主义是“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一种学说”,[3](P46)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最后的和不变的东西,它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向着更高形式的社会前进”,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完结”。[4]对于共产主义,艾思奇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5]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学说、思想与科学”,又是“将来社会的理想”。[6](P233)中共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其最终目标自然是“解放全人类,建立光明美满无人剥削人无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7]可以看到,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博大广袤,当时的理论工作者尚未能从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角度对两者的概念进行整体的高度概括,其认识仍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朦胧感。
如果说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概念的界定仍显抽象,那么,其对特征的认识则要相对细化和具体。此期,他们主要从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状况等八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关于分配方式,胡绳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容许资本主义制度之存在,不能容许依靠利润而生活的资本家,而要使一切生产品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分配”。[8]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所能实现的原则,乃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9](P664)吴亮平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能够‘各取所需’”,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10]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是要看你做多少工来计算的,……所以,物品不是以需要的原则来分配,而按照消费的劳动量来决定”;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物品的分配则是“以社会成员之需要作标准的,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作为原则的”。[11]关于生产力状况,董必武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生产力还未充分发达;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量浪费及社会发展的动摇既不存在,于是靠着生产力无限制无障碍迅速的提高,便可秩然有序的支配一切自然财富,而形成和谐的经济荣盛状况”。[12]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样高度,使每人可以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东西”;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伟大的生产力能供给无穷尽的财富,人们的工作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和最大的快乐泉源,而人类的一切聪明才智犹如鲜花怒放,充分发展”。[4]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吴亮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手段归社会所有”。[10]胡绳也认为,在社会主义概念中“必然包含着废除私有财产的属性,一切生产手段——包括土地、工厂等等,都为全体生产劳动者共有”。因此,“假如还不能做到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消灭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实现生产手段的社会公有制,那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8]总之,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完全属于公有”。[11]关于阶级关系,董必武、吴亮平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即“旧的阶级区别,还有残余存在,还没有完全消灭”[10]、“智力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城市和农村间矛盾之残余,阶级区别的残余等等,仍然未完全消灭”;[11]反之,共产主义时代“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没有剥削制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后等”,[6](P122)届时“劳动便不替资产阶级仇敌创造利益,劳动将由维持生活的工具,一变而为人生的第一种需要;一般人类经济的不平等、被奴役的阶级的艰苦贫穷等都绝迹了”。[12]总体上看,在当时的理论工作者眼中,正是阶级关系等八方面特征的多重组合,共同塑造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架构,这些特征在该架构中最受中共的青睐,相关理论言说也最为丰富。
此外,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当时的理论工作者也作出了学理意义上的说明。吴亮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如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或甚至如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那样的两种不同的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程度不同的阶段或层级。”[10]因此,这两个阶段“并没有社会形态的原则上的不同地方(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从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就将不须要有革命的突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将采取进化的逐步过渡的性质”。[10]当然,这两个阶段之间也存有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基本的是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别”,以及“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与共产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差别”。[10]
以上就是中共思想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内涵所作的一般论述。从论述的三方面情况看,部分表述虽还不够系统和准确,但也不乏闪光之处。可以说,它们反映了此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基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知,勾勒和展现了其理想中的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和图景。当然,这些理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知,也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他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曾作出过不符实际的判断,“这个新式的国家正在胜利的大踏步前进,并已跨过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正在过渡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去”。[13]可见,同以往的社会主义先驱者一样,他们也未能摆脱时代的限制。
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基本矛盾与发展动力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界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两个争论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参加讨论者包括苏联哲学家尤琴、乌拉索夫、高罗霍夫、柯列斯尼柯瓦。争论发生后,《中国文化》随即登载了其详细内容,延安各学校及学术研究团体进而受到影响,经济学家王思华详细阐述了他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
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上,哲学家尤琴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他指出,在苏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完全的适合,生产力没有遇到任何的障碍,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在一切阶级冲突的社会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是矛盾的,而它们间的适合只是相对的适合。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成为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之障碍”。[14]尤琴完全赞同斯大林关于苏联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完全相适合的判断,认为斯大林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乌拉索夫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个统一体,而任何统一体“都不是形而上学的同一;它们本身包含着差别,因之,也就包含着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也是存在着矛盾的”。[15]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乃是历史发展底普遍法则,而在一切社会经济结构中都是起演作用的。其表现底方式,在社会底各种发展阶段上各各不同,但是矛盾本身并不因自己形式底改变而消灭”。[15]因此,乌拉索夫持有与尤琴完全相反的观点。高罗霍夫和柯列斯尼柯瓦对乌拉索夫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矛盾的,并对尤琴的观点进行辩护,“生产关系是跟生产力状态完全相适应的,因为生产过程底社会性又被生产手段底社会公有制所巩固”[16]、“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适应,铲除了产生两者之间的对抗性底一切的社会的原因”。[17]
在该问题上,经济学家王思华基本赞同乌拉索夫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没有对立的斗争,没有内在矛盾,一切的发展都不可能。所以一切发展着的现象,其中必会有矛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既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当然也就存在着矛盾。他进一步指出,任何统一体的本身,既然包含着差别,也就蕴含着矛盾,这是辩证法上的一个普遍法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显然是有差别的,……在社会主义之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回答的问题,也是不相同的,……因此,也就包含着矛盾。因为,‘差别就是矛盾’”。[18]在这里,尽管王思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但他同时反复强调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对抗性矛盾”仅存在于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冲突,没有对抗性的矛盾。生产关系决不会阻碍生产力的自由发展”。[18]
王思华还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问题。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之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生产底可能性与社会需要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在社会主义之下,社会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开展的,但那时“劳动大众底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大大地提高了”。同时,为了扩大社会主义的再生产起见,“生产的消费也不断地增加着”,所有这些社会的需要在客观上不自觉地必然刺激着社会生产的自觉提高与不断发展,而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与提高,更会刺激着新的社会需要的不断增加,同时社会需要本身又创造新的社会需要,因此,社会需要总是在社会生产的前面,总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王思华强调,这一矛盾“只有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与发展中,只有依靠劳动大众的集体努力生产,才能得到解决”。[18]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争论各方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判断。尤琴由于不承认社会主义之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而尽管其宣称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但这个动力,在尤琴看来,就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是两者之间的完全适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完全的适合,是生产力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14]乌拉索夫将“生产方法”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解释道:“生产方法本身为处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跟适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底统一体……在社会主义之下,生产方法将是社会发展底动力,社会主义生产方法本身将决定全部上层筑物体系。”[15]可以看出,这里的“生产方法”亦即生产方式的同义语。但与尤琴不同,乌拉索夫强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唯物论底本质,就是如此。这一本质表示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为社会底动力”。[15]高罗霍夫既然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当然也就不同意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跟生产力状态完全相适应的,因此研究者在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时,“决不可应用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他对抗社会类似底方法,而忘记随着资本主义底消灭,在社会关系上,劳动组织上所发生的根本的变革”。[16]对此,柯列斯尼柯瓦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与上述矛盾问题的争论相一致,王思华对乌拉索夫的观点颇为赞同,并对尤琴、高罗霍夫的观点进行了驳斥,重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仍是其生产方式”。[18]他说,“高罗霍夫认为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间底矛盾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底动力,是‘诡辩的’,是‘不肯具体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底动力问题’的结果,……但是我们能否如高罗霍夫一样,由此便排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呢?不能够的”。[18]他强调,由于高罗霍夫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是没有“对抗的社会矛盾”的社会,因此,他便主张“关于一切发展底内在基础——矛盾,新旧斗争问题”,不复能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之上,这表明“他把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同一化了,他认为一切矛盾都是带对抗性的,没有对抗性的矛盾,便不能有任何矛盾,这种观点,是非辩证法的,是错误的”。[18]同时,他也反对尤琴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适合看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围绕该问题的理解和判断,直接关系到争论各方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因为“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哲学根基,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回答而连带出的对感觉和经验的理性关注是社会主义产生的认识论前提”。[19](P6)可以看出,在这场争论中,王思华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提出了今人看来仍相当可贵的思想。如从历时性角度看,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及其矛盾的评判,与十年后中共八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及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有关论述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前后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而展开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借鉴*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广泛地研究和讨论了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与上述讨论联系最为密切的是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后,围绕“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讨论,以及改革开放前后有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的讨论。这两次讨论分别涉及社会主义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但其持续时间之久,发表文章之多,交锋之激烈,却是延安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详见《关于我国国内当前主要矛盾的讨论》,《人民日报》1956年12月9日;张磊:《我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和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光明日报》1957年1月9日;方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科学论断不容篡改》,《哲学研究》1978年第1-2合期;陈延政:《关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2期;等等。。毋庸讳言,王思华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仍存在局限,如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解仅立足于“差别即是矛盾”的感性认知层面上,而未上升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互动层面,而后者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才得到了系统呈现。
四、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哲学沉思
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除了在学理意义上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含义、特征和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外,还着重论述了其对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这种认识脉络基本上遵循着从“是什么”、“为什么”到“怎么做”的逻辑架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认识、思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系统性与全面性。
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并没有给予直接回答。因此,共产主义者或只能从经典作家思想的精神实质与方法论中寻找理论依据,或则要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0](P466)延安时期,中共思想理论界显然只能更多地依靠前者。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地吸收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通过重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才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道路。因此,中共思想理论界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探索,首先就体现在他们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上。如龙潜等就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有其历史意义的贡献,但是他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是一个坚决彻底的革命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换言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了解社会的规律,站在与政治斗争毫无关系的一边,自己却‘高于阶级的冲突之上’,去进行改良主义”。[21]因此,这种不是用斗争而是用和平联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主张,虽然有许多独创的见解,但却“不能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22]
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应当如何实现呢?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反思为中共思想理论界探寻答案提供了借鉴,他们从发展生产力、依靠无产阶级以及开展政治斗争三方面进行了论证。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张闻天、艾思奇等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空想的计划,不是凭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而是在旧社会崩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实世界。无产阶级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文化和物质的条件”,[23]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出来”。[24](P163)换言之,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以现代化生产力最高度的发展为先行条件”,[25]“必须广大的运用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拥有“具备新的生产技能与新的劳动强度,能够很好掌握并运用这种新的技术的人”。[10]在有关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及政治斗争的开展方面,陈伯达等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否定无产阶级历史作用及其革命性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建立的,它是走的政治斗争的革命道路,而不是经过和平方法便可达到的”,而且,“只有无产阶级能成为真正组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正领导者(如在苏联)。这个阶级是人类最后的阶级,也是最革命的阶级”。[26]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除了依靠于那和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外,除了无产阶级联合一定的革命同盟军、经过政治斗争而获得成为社会的主人之外,是决不可能的,……离开了这阶级及其政治斗争,就不能有现实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6]所有这些,都是“从历史分析得出的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全世界历史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总路线的基本原理”。[27]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未来社会实现路径的探讨,尽管都体现了中共思想理论界固有的社会发展理念,但我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目前所追求的现实目标。胡绳、许涤新等人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言说反映出,他们并不主张目前就实行社会主义。如胡绳就认为,在中国现状下,人们还不可能第一步就走上废除私有财产,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后,才能够渐渐产生走向社会主义去的可能”,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就不是当前迫切的任务,而是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相当时期以后的问题”。[8]许涤新也指出,当革命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当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我们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28]
总之,对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构成了此期中共思想理论界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个层面。中共理论工作者对生产力的重视、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强调不仅在理论上无可厚非,而且至今仍具有其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思辨的深度,他们并未能全面而系统地领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实现路径的精神实质,更多还是将思想的光芒投射到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仅仅希冀从“批判——重构”的角度去探寻未来社会的实现路径,这自然又是片面和局限的,难免会重陷黑格尔和列宁都提醒过的“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生”,用“轶闻奇事”解释历史现象的“常见的笑话”中*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221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列宁哲学笔记》,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如在上述理论言说中,他们单方面强调“政治斗争”和“革命”,忽视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显然不够准确。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在坚持暴力革命思想的同时认为,在英、美等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29](P179)、工人阶级“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30](P524)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的实现路径应以具体的历史情境为根据,而不总是一成不变、依然如故的。
结 语
从建党初期至新中国成立的近三十年中,中共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应当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陆续地亮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知。如果说中共思想理论界早期政治思想的产生更多还是与不同政治思潮开展争锋和较量的结果,那么,此期则主要是抽象思辨和学理意义上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初步的且不成熟的。可以说,延安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期。一方面,中共思想理论界批判性地继承了建党初期即已萌芽的部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对其加以纠正、完善或进行系统化、学院化阐释;另一方面,他们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些以往尚未涉猎的思想侧面,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无论哪方面的尝试,都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特有的印痕。
就思想的继承和完善而言,上述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和特征,以及其实现路径的论述就可为证。施存统等早在1921年8月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出的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也就是经过了社会革命期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已没有了阶级的区别和生产机关底私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已消灭,……至于分配消费品,还仅能采用‘各取所值’一条原则”;[31]而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国、无家、无阶级、无政府的社会”。[32]他们相信,“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看革命为第一义。……劳动者的知识增加了,经济的条件满足了,才能以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社会”[33]、“‘自由劳动,自由消费’的社会,要以生产力十分发展为前提”。[34]类似这样的观点和理念,在中共早期理论工作者的著述中曾多次出现。因此,从宏观思想演变的视角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较之于建党初期,中共思想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的探索,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大开拓和创新。
至于上述思想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诚如列宁所言:“在俄国,各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根深蒂固,自然是由于俄国落后的缘故。”[35](P654)社会经济状况与思想政治主张就是如此地紧密相连,中国的情形亦复如是。因此,如果说思想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和根本价值是在于“创造”,在于通过客观的描述这一手段去挖掘和把握当事人无意识的要素,那么,作为历史事实的文化学探讨,今人的任务在于,重新反思前人走过的曲折道路,检查在我们的血液、思维和行为中是否依然保留着某些残迹。
[1] 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李达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张闻天文集[M].第3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4.
[4] 费煦.什么是社会主义(续)[J].解放,1940,(120).
[5]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N].新中华报,1939-04-28.
[6] 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 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N].新中华报,1939-06-30.
[8] 沈友谷.论所谓“毕其功于一役”[J].群众,1945,(16).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0] 黎平.关于苏联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J].解放,1939,(63-64).
[11]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别是什么?[N].新华日报,1939-02-02.
[12]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J].解放,1937,(6).
[13] 纪念巴黎公社六十九周年[N].新中华报,1940-03-15.
[14] 尤琴.继续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哲学问题[J].中国文化,1940,(3).
[15] 乌拉索夫.论社会主义社会底动力矛盾问题[J].中国文化,1940,(6).
[16] 高罗霍夫.论社会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底完全适应于生产力[J].中国文化,1940,(1).
[17] 柯列斯尼柯瓦.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底动力[J].中国文化,1940,(2).
[18] 王思华.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J].中国文化,1940,(6).
[19] 张奎良.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与实践指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列宁全集[M].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1] 龙潜.什么叫空想社会主义?[J].群众,1940,(5).
[22] 王匡.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续完)[N].解放日报,1942-01-21.
[23] 艾思奇.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J].解放,1939,(88).
[24] 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5] 定思.“新奇”的“理解”[J].群众,1943,(19).
[26] 陈伯达.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J].解放,1939,(87-88).
[27]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J].解放,1939,(89).
[28] 许涤新.中国经济底道路(下)[J].群众,1945,(24).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J].新青年,1921,(4).
[32] Y.K..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J].少年,1923,(7).
[33] 新凯.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答张东荪与徐六几[J].新青年,1922,(6).
[34] 光亮.马克斯主义底特色[J].觉悟,1921,(9).
[35] 列宁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李文苓]
ExtensionandTranscendence:UnderstandingandThinkingofSocialismandCommunismintheCPCIdeologicalandTheoreticalCirclesduringtheYananPeriod
Wu Wenlong
(Department of CPC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CPC Central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
socialism; communism; the Yanan period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f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of CPC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Putting forward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society and the motive force of their development for the first time; Proving the scientific path of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This thread of understanding basically conforms to the logical framework from “what is”, “why”, and “how to d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macro thinking, it has not only the ideological inheritance and perfection,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It is undoubtedly meaningful for us to critically absorb this ideological resource.
吴文珑,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