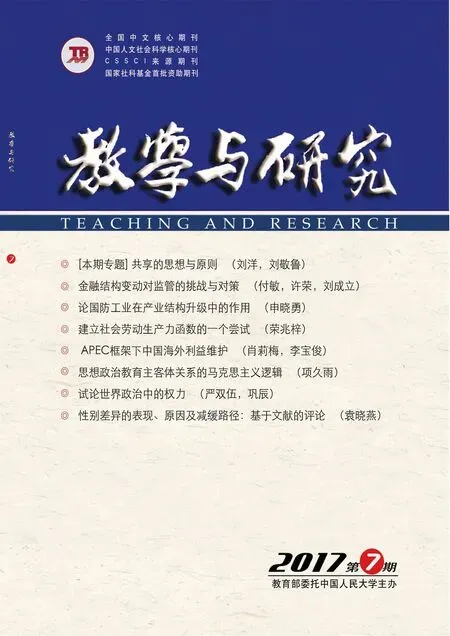超越“群享”与“私享”: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超越“群享”与“私享”: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洋
马克思;共享;当代价值
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是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大致出现了“群享”与“私享”两种方式。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发展成果的“私享”方式,宣扬社会发展成果由“私人”“公平公正”地享有。但马克思察觉到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虚伪性与意识形态性,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的事实指认、资产阶级分配理论的谬误分析与私有制的根源剖析,对其进行了全面批判。批判“私享”的目的并不是要回到“群享”,马克思提出了建立在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共享发展方式,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社会个人所有制和联合劳动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来共同享有社会总产品。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就在于将其理论观点转化为改革所有制、分配制度与发展生产力的实践策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围绕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应运而生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故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应构成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彰显出发展的价值旨归。关于社会共享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已提出,要求“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P689)那么,在当今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理念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创新,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共享思想,这一问题域构成了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时代课题。
一、“群享”与“私享”:马克思面对的历史与现实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519)而为了维持个人的存在“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P531)这些东西不论是最为基本的生存资料,还是较高的“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P710)人们要想从社会中获得它们,就必然涉及到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问题。可见,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贯穿整个人类发展史。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方面来谈社会成员的享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以何种方式和原则让人们享有发展成果主要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关联。因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P436)社会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结合的结果,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同,历史上出现了“群享”与“私享”两种不同的发展成果享有方式。这里所谓的“群享”指的是一种群体本位的享有方式,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但因公有制形式简单、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整个群落的生存和发展,个人利益必须要服从群体利益,故群体享有优先于个人享有。例如,氏族、部落以及古典时期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区域都遵循这种享有方式。
“私享”则是与“群享”相对的一种个体本位的享有方式,它建立在生产力与私有制较为发达的基础之上,此时私人利益被突出到群体利益之上。因此社会在发展成果的享有上遵循私人享有优先的原则,如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实行这种享有方式的典型。对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来说,“群享”是历史上出现的享有方式,而“私享”是现实中面对的享有方式,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这两种方式对马克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要理解马克思的共享思想,还得先从“群享”和“私享”说起。
“群享”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它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简单公有制形式相联系。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这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发展成果“群享”的方式主要出现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以及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之中。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中,由于人们多靠狩猎、捕鱼和耕作为生,所以生产成果多靠土地产生,但土地财产却并非个人所有的财产。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土地财产是属于共同体的,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3](P124)也就是说,在亚细亚社会,“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3](P132)正是由于土地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公社,使得由土地带来的生产成果也必然实行“群享”的方式。在亚细亚的公共所有制条件下,个人可以获得的只有能够“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的成果,而剩余产品“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3](P124)从以上可以看出,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土地财产及公社的生产成果实行的是共同体享有的形式,也即“群享”的方式,此时共同体的利益是要高于个人的,这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维护群体的延续所必然采取的方式。
古典古代时期与亚细亚时期的人们虽然都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3](P126)但在所有制方面二者已有不同之处:亚细亚属于完全公有制形式,古典古代时期的所有制实行的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并列的形式。之所以在共同体中会出现私有制因素,因为在古典古代时期,人们“远离自己的原来住地而占领异乡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3](P127)个人能力提升了,单个人的财产需要依靠共同劳动来利用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由此个人才有可能变为私有者。但这种私有制却未能改变发展成果“群享”的方式,这主要是由个人占有成果的目的及这种私有制的性质决定的。从个人占有成果的目的来说,它“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3](P128)从私有制的性质来说,此时还未能表现出完全的独立性,仍受到共同体的限制。也就是说,虽然古典古代时期的所有制存在着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两种形式,但“后者决定于前者,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定是私有者”。[3](P135)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财产是魁里特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3](P129)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典古代时期虽然已有私人所有的形式出现,但在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上,它仍同亚细亚一样,私人所享有的只是维持生命必要的自给自足,而整个社会仍以“群享”方式为主,因为私人的“剩余时间正是属于公社”。[3](P128)
“群享”方式向“私享”方式的真正转变是从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开始的,这种所有制逐步摆脱公社共同体的束缚,开始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公社“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3](P131-132)此时,“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3](P132)而公社作为一种共同体只是连接个人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所有制中,也有着公社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的并存,但由于私有制的发展,使得“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3](P135)因而公社财产变为了“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3](P133)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个人所有制已经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此时的社会发展成果主要是由个人或家庭私人享有。于是,私有制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社会发展成果的“私享”方式出现了,而这仅仅是发展成果“私享”的开端,将这种方式发展到极致的是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1](P583)这种私有制既是分工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促进了社会的总体发展,尤其是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有着以往所有制所不可比拟的优势。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庞大的商品堆积,使得可供享有的总的社会发展成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既然社会发展成果总量不断增大,那么如何享用社会发展成果便成为了突出问题。虽然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享有方式必定是“私享”,但究竟哪些“私人”被列入享有范围,以及如何确立“私人”对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比例,都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并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亚当·斯密对社会成果分配的研究,也即社会成员如何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是从其价值创造理论开始的。斯密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成果的主要来源,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4](P1)这是否意味着发展成果应该由劳动者平均享有呢?斯密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价值来源于劳动时间的命题只能适用于原始蒙昧社会,而当土地私有与资本积累产生之后,价值的决定就应该从劳动时间转换到工资、利润与地租这三种要素上。斯密认为正是由于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使得生产劳动要使用这些要素就必须支付报酬。因此劳动成果不能只由劳动者享有,而必须在劳动者、资本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分配,也就是说社会发展成果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这三种类型的“私人”所享有。同样,斯密还分析了发展成果在三种类型的“私人”间享有的比例。通过对国民收入形成的深入考察,斯密认为,工人享有的工资量应该由其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决定,这就是工人劳动的“自然价格”;资本家所享的利润量与其所投资本量成正比;地主所享有的地租量则是租地人扣除生产费用和利润后的最高额。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们拥有大量的成果可供享用,同时古典经济学家对享有原则的制定又保证了每一个“私人”都可享有到社会发展成果,社会在这种“私享”方式下仿佛进入了“人人享有”的理想状态。
二、在批判“群享”、“私享”中诉求共享
发展成果的“群享”与“私享”方式,分别是马克思所面对的历史与现实。“群享”对马克思来说已是历史,他对这种成果享有方式的批判并未有太多篇幅,只是从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的批判中折射出“群享”方式解体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支撑“群享”的公社制生产关系有其局限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3](P134)可以看出,这种所有制所对应的生产力是低下的,它仅仅是对使用价值和个人的简单再生产。也正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为了维护氏族、部落的发展,才采取“群享”的成果享有方式。而这种方式“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3](P148)也就是说,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成果的“群享”方式便会自然解体,它被“私享”替代有其历史必然性。
“私享”是马克思面对的现实,故马克思对享有方式的分析与批判多集中于“私享”。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其必然实行发展成果的“私享”方式,也就是通过如斯密式的合理分配使每一类“私人”都可享有发展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人人皆享”的理想社会状态。但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私享”方式并不具有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看似普遍主义的承诺背后隐藏的却是特殊者的权力关系,贯彻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马克思指出,证明资本主义“私享”方式虚伪性的最恰切的证据就是工人阶级无家可归的命运。他敏锐地看到了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所不愿承认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P156)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虚伪性、剥削性,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进行详细考察,从现实领域、理论领域与制度领域对资本主义“私享”方式作了彻底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私享”仅仅是资本家的享有。
第一,在现实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工人阶级因异化劳动所导致的“非人”生存状态的揭示,批判了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虚伪本性。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享”只是单单属于资本家的“私享”,是资本的享有,而普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只能是被剥削。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对发展成果的享有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5](P68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虽然是产品的生产者,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作用下,工人生产的产品却被不生产者(资本家)无偿地享有了。而工人所享有的只能是被剥削和奴役,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仅失去了劳动的成果,而且受自己劳动结果的支配、统治和奴役。“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1](P157)劳动产品的异化无疑源于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人的内在本质是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了。劳动活动成为了动物式的生产,它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的生活需要,而纯粹只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仅仅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此时,劳动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生产,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受人制约、被人监管,甚至在皮鞭下从事劳动,他们“享有”的只会是肉体上的折磨与精神上的摧残。从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享有生产成果的只能是占据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只有他们才属于“私享”的范围,而广大劳动群众所享有的只是被剥削和奴役。
第二,在理论上,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对价值创造、价值分配进行科学分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私享”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异化劳动的事实使马克思察觉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虚伪性,并开始对古典经济学的享有理论产生质疑。古典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理应分配为工资、利润与地租三大部分,这是由生产过程的三个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所自然决定的。从这一逻辑出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私人”不论是劳动者、资本家还是地主,都可按照自己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来“公平公正”地享有社会成果。这种表面的“公平公正”使得资本家和大地主完全掌控和享有着社会的绝大部分成果,而工人只能取得维持自身劳动力延续和家庭生存的悲惨遭遇被“合理化”了。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发展成果的享有理论是荒谬的,它只对国民收入中的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了量的分析,却忽视了质的分析。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生产要素、收入等具体范畴中抽象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的一般范畴,即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及剩余价值(M)。马克思发现了在生产投入中存在着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它在生产过程中只发生价值转移,不会发生价值量的变化;而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它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而且生产出剩余价值。这样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这部分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量的变化,即发生了价值增殖。但是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由劳动力带来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由劳动者所享有,劳动者得到的只会是资本购买劳动力的价格,也即生产过程中的可变资本,这仅仅只能够维系劳动力的延续和劳动者家庭的生存。劳动力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情地享有了,而这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中被“合理”掩盖了。因为他们没有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而是将剩余价值看作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这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迷雾。
第三,在制度上,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私享”方式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要克服发展成果的“私享”,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5](P873)前一种私有制是属劳动者的私人所有,其生产成果是由劳动者及其家庭个体享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个人劳动与个人享有的一致性。但这种私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是一无所有的,除了劳动力外不具备其他任何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注定了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自己的基本生活资料。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6](P45)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中,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实质。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让劳动者也可公平公正地享有社会发展成果,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劳资对立、剥削才能得到彻底消灭,资本家绝对享有社会生产成果的局面才能被打破,最终“私享”因其社会制度根基的瓦解而废除。
马克思在现实、理论与制度三个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的“私享”方式展开了全面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虚伪性与意识形态性。但对资本主义“私享”方式的批判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他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7](P7)在这个“新世界”中,马克思既要打破资本家的“私享”地位,又拒绝回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享”方式。因为“群享”是忽视个人利益的,马克思主张要“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P689)马克思所提出的发展成果享有方式便是共享,要求让社会发展成果由所有人共同享有,这就实现了个人享有与社会他人享有的一致性,体现了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协调,从而完成了对“群享”方式和“私享”方式的全面超越。这种共享方式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这便是马克思揭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其中,生产资料采取社会个人所有制,由全体人民共同劳动创造社会生产力,并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由此使得共享发展成为可能。
第一,社会个人所有制构成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制度保证。马克思指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私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那要实现全体成员的共享发展必须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一种代表全体人民的所有制形式。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存在三种基本形态,它们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反—合”三阶段是相符合的。第一种形式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纯粹的公有制与简单的私有制形式,像氏族所有制和小农、小资产阶级私有制。第二种形式是对前一种的否定超越,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否定的否定”,也就是马克思指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在他看来,“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P874)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显然不再是某种单个人或“私人”的所有制,而是一种社会个人所有制,它体现的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1](P582)这种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方面它提倡“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即个人所有,同时它又强调这种“个人”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即共同所有。故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包含了“个人所有”与“社会共同占有”的张力,强调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享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发展。
第二,联合劳动生产的社会总产品构成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总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生产发展的成果是社会享有的物质基础,只有社会总产品能够满足人们一切合理需要时,共享发展才能成为可能。马克思将共享发展的社会基础定位于共产主义社会,这其中实行的是社会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而生产资料的这种所有制只是决定了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形式,要真正实现共享还必须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2](P460)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它吸收了大量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积极文明成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物质财富。但同样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1](P688)可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实现了极大丰富,这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之所以能够使生产力高度发展,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社会成员的共同生产,即联合劳动生产。这种联合劳动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只是作为结果而存在,而社会个人所有制下的联合劳动生产则是真正的“共同生产”,生产的社会性既作为前提又作为结果而内在于生产过程。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被扬弃了,从根基上保证了生产的社会联合与社会性调节,使得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都被调动起来,提供了源源不断可供社会成员享有的物质财富。
第三,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构成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社会个人所有制为共享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共享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最后还需在分配方式上加以合理规划。如何分配才能使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呢?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还未达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程度,人们依然需要依靠劳动谋生,此时对社会产品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2](P434)这便是劳动者根据自己的劳动量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以一种公平原则保证全体劳动者共同享有社会生活资料。而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时,当迫使人服从的分工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时,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此时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P436)的分配方式。在这个阶段,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人们在占有和消费上的不同,人们从事劳动完全源于内在需要。这时候社会产品的分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真正需要,这样所有社会成员真正平等地共享发展成果,使得每个人的潜能和才能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保证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在中国发展实践中把握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当代价值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马克思思想理论的重要价值旨归,其共享思想可以集中表述为: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社会个人所有制和联合劳动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来共同享有社会总产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8](P12)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实现以上目标,必然离不开对马克思共享思想当代价值的把握。这种把握就是要实现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当代“激活”,要以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解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中的实践问题。但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已有一百多年,虽不能说沧海桑田,也已是日新月异。另外,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是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而当今中国的发展实践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从这两个方面看,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当代中国问题存在着时空的不一致性,故我们以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来指导当代中国实践,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的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和运用,这样才能把握与发挥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一,在共享的制度设计上,应当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构建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理论观点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中所有制改革的实践策略。在马克思看来,不管对消费资料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分配,从根本上都是由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所决定的,故要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首先要让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实行社会个人所有制。但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健全,此时构建社会个人所有制并不具有现实性。在这时要实现共享发展,我们只有按照马克思所建立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原则来进行适当的所有制改革:一方面坚持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目标方向,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尽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体说来:
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实现共享的根本保证。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了生产成果最终由谁享有,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资本家对生产成果的“私享”,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而要想打破“私享”走向共享,让生产成果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就必须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对这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坚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条件下,全体人民共同掌握和支配着生产资料,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生产过程的计划与管理当中,同样也可以从全部生产成果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这样,就从根源上切断了少数人对生产成果的霸占和垄断,保证了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和享用。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生产成果共享的必要的制度前提。
二是要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要积极推动劳动者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并努力促使国有制成为公有制的特殊形式。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朝着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目标发展,必须创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保障共享发展的更好实现。当前,劳动者股份制是一种既符合马克思社会个人所有制要求,又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所有制形式。所谓劳动者股份制是一种以股份制为联合方式的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它以股权形式赋予了劳动者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收益权,并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与传统的公有制形式不同,劳动者股份制不是以全社会范围内的共同所有权为基础,而是以一定范围内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联合为基础。这样,劳动者就不再是被动的结合,而是自主、自愿、自由的联合。这种自愿的联合,一方面促进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所有劳动者都可享有生产成果。另外,随着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制将不再是公有制的普遍存在形式,但它仍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存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当中。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施行宏观调控提供物质基础,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避免贫富差距的拉大,从而将共享发展落到实处。
三是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活市场经济活力。坚持公有制的主体性地位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生产成果的全民共享,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因此在所有制的改革过程中,我们还要吸收和利用一切积极的所有制形式,构建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从而为共享创造更多的发展成果。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包含公有制经济成分又包含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实现了二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并存,并使之相互融合、互为补充。这样一方面使得经济发展可以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平稳有序地运行,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激发广大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竞争意识,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各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也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其他各生产要素也按贡献参与到分配过程当中。于是劳动者的收入来源实现了多样化,既有劳动收入,又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使得共享发展的财富基础得到巩固。
第二,在共享的物质基础上,应当将马克思联合劳动生产创造社会总产品的理论观点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中发展生产力与人民共创的实践策略。一个社会享有的只能是发展的成果,马克思的共享思想以社会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社会成员共享的是大家联合劳动创造的社会总产品。马克思设想的实现共享的社会基础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时生产力已高度发达,产品也极大丰富,但目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达不到这一水平,故首先我们还必须极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共享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同时,马克思还强调共享的社会总产品是由联合劳动创造出来的,这就表明在当下中国我们要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必须以人民共创为前提。具体说来:
一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享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从总体上看,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实现共享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在经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刻意制造共享社会无异于空想社会主义。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在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知识等一切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这样,才能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才能创造出大量可供全体人民共同享用的社会总产品。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才“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9](P299)另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可以保证人们有机会、有能力去享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内容,从而使共享可以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能够推动共享发展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跃升。
二是要坚持人民共创,让共创成为共享的前提。马克思指出要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共享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联合劳动生产,这就表明发展成果共享要以人民共创为前提。以共创作为共享的前提,一方面保证了享有原则的公平正义性;另一方面共创还应着眼于激发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潜能,促进能力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一直十分强调人民共创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原则,这里的“人人参与”和“人人尽力”就是对共创的具体表达。可见,共享发展不是某一特殊群体的事业,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需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强调共同走向创新驱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同样,人民共创不仅可以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还可以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才华和潜能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展现,从而实现了能力共享,这也成为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在共享的实现机制上,应当将马克思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理论观点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中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策略。生产成果共享必然要依靠一定的分配形式和分配机制,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而当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使得我们必须发挥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一切要素来发展生产力。此时在共享的实现机制上就不能单纯地套用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而是要既有按需分配的理想目标,又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现实策略。要将这种理想目标与现实策略融合,切实保障广大劳动群众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
一是形成市场化机制和效率导向的初次分配格局,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从初次分配来看,为激发市场活力,保证成果共享,就必须发挥市场与效率的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完善市场对要素贡献的评价与分配机制。坚持从市场原则出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允许个人以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市场要素获得相应的合法收益,而对那些以行政权力、不当竞争、行业垄断等非市场性要素获得的不法收益则要彻底取缔。此外,还要合理控制不同市场要素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既不能差距过大也不能过小。差距过大将造成两极分化,差距过小又会降低市场活力,这些都会制约共享的实现。其次,要提高劳动报酬比例,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尊严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成果的分配往往存在着重资本轻劳动的现象,这就使得以劳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收入群体收入普遍较低,从而难以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造成劳动人民“获得感”不强。对此,在收入分配制度中应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共享发展成果。
二是形成政府调节和公平正义的再分配格局,以利益补偿促进共享。由于市场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因此,共享的实现还需充分发挥政府的再分配作用,要利用国家预算、转移支付、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手段进行调节,进一步保证社会享有的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虽然得到显著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呈现逐步拉大之势。如果任由这一状况继续下去,不仅共享发展无法实现,甚至还会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而要想缩小利益鸿沟、平衡利益诉求、实现利益共享就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在以效率为原则的初次分配基础上继续实行再次分配。在再分配过程中,国家必须积极推动税务体制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部分高收入群体加以必要限制,同时建立健全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通过转移支付对那些在初次分配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给予相应的补偿,从而缓解因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造成的不良影响。此外,还要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加强民生事业建设,在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续原则的指导下,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生态保护等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市场原则的弊端,使公平正义得到彰显,确保共享发展落到实处。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M].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孔伟]
Beyond“GroupEnjoyment”and“PrivateEnjoyment”:Marx’sCommunionThoughtandItsContemporaryValue
Liu Y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Marx; sharing; contemporary value
The way of enjoying the frui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a new and eternal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re are generally two ways of “group enjoyment” and “private enjoyment”. The capitalist society in which Marx lived implemented the “private enjoyment” of the development fruits. The frui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ere privately enjoyed through “fair and justice”. But Marx perceived the hypocrisy and Ideological attribute of the “private enjoyment” of capitalism, and made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f the facts of alienated lab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zing “private enjoyment” is not to return to the “group enjoyment”, instead, Marx proposed the Communion of development fruits based on the communist society, which demands that all members of society share the socia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individual ownership of the socie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joint labor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nd th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needs. In the practice of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Marx’s communion thought lies in transforming his theoretical views into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for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及其当代实践意义研究”(项目号:2012BKS001)的阶段性成果。
共享的思想与原则
刘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433)。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当今语境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理念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创新,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共享思想,这一问题域构成了时代的重要课题。刘洋认为,发展成果的享有方式问题,贯穿整个人类发展史。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方面来谈社会成员的享有问题的,即以何种方式和原则让人们享有发展成果主要与社会的生产方式相关联。英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杰拉尔德·阿伦·科恩把“共享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刘敬鲁教授认为,共享原则与我国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