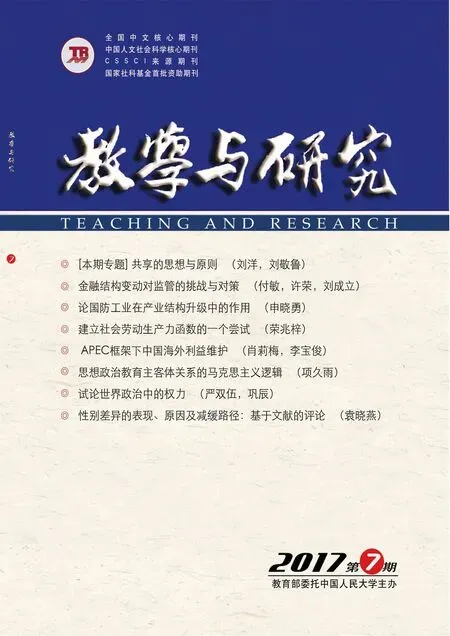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逻辑*
项久雨
马克思主义视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诉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关键、最基础的理论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并不仅仅是指教育者,而是具有多种主体形式的主体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指向也不仅仅是指受教育者,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不同,客体所呈现的形式也会存在差别。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具有动态性,在一定条件下,主体与客体可以相互转化。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呈现出多种形式,因此,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是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最关键、最基础的理论问题,深刻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科学内涵,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其重要价值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共识,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即究竟孰为主体、孰为客体以及二者的关系等,尚未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理论为出发点,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进行探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含义与表现
目前,学界关于主客体及其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主体是什么”的探讨上,例如,“单一主体说”、“双主体说”、“主体互动说”、“主体间性说”等等。之所以出现各种不同的观点,除了该问题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外,最基本的原因是主客体问题是来源哲学认识论的问题,要将哲学中的问题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学术分歧。所以,要讨论这一问题,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
主体并不是先在的,在主体和客体分化之前,主体和客体是混沌一体的,随着人类劳动和分工的产生,人逐渐从自身出发认识外界事物,人把自身当作主体同外界事物分开。因此,从主体产生的历史来看,主体是人,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里的人就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1](P91)但是,后现代主义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认为“人类无一例外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2](P139)后现代主义者显然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人类现有的体系、制度也都是人作为主体创造出来的。“主体是人”这一观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主体是人,并不就等于“人就是主体”,例如,在异化条件下,主体失落,异化为客体。所以,主体的属性与人的价值属性是密不可分的。进一步说,主体首先应该是具有自然属性的,表现在人对自然的依赖,甚至是对自身身体的依赖,人是“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P324)其次,主体还具有社会属性,“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3](P302)主体的社会属性除了人的社会性存在之外,还表现为人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体现,而精神需要的满足衍生出人的社会精神交往等方面的需求。主体的第三种属性是精神属性,即主体是有意识、能思维的存在物,其中既包括了理性的逻辑与思维,也包括了非理性的情感等,“主体的精神属性也是主体全部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重要依据。”[1](P960)
既然主体是人,那么根据人的存在形式的差异,主体也具有多种类型,包括个人主体、集团主体、社会或国家主体三种。其中个人主体就是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单个人,个人主体是最基本的单位,是其他两种主体形式的基础和前提。集团主体则是指按照一定的规范、准则、目的等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或行动方式的群体,例如,政党、阶级等。如果将集团主体的范围扩大,以整个国家或者社会为一定的利益共同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则是社会或者国家主体。具体来讲,其一,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交流和交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国家利益的差异,往往会存在意识形态的传播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以国家为利益主体,向其他国家的公民传播本国的价值观,这种以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传播活动的主体就是国家主体。不同的国家主体具有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主体所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政党服务,就必须坚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坚决抵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其二,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P179)统治阶级往往借助于各种组织的力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例如,教育部门、教师组织等,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主体的一部分。其三,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目的是要使受教育者接受相关的知识、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就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而论,“学生在教学中的活动可以确定为主动的和有目的的活动体系,他们在这种活动过程中,通过教学资料来认识客观现实的对象和现象,并利用所获得的知识来求得新知识。”[5](P181)所以,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认识新知识的过程,最终实现受教育者认识上的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均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主体。简言之,国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主体,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主体,而受教育者则是自我教育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通过改造主观世界而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实践活动,人作为主体是以类的形式存在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有第四个主体,即类主体,而且把“类主体”作为最理想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错误观点,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幻觉。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主观世界的改造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人类发展过程伴随的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必须融入先进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体现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任何以借口“全人类的利益”,而否认“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类主体”都是虚无的主体,也是站不住脚的主体。
主体虽然存在多种形式,但是其最为本质的依然是人,所以,主体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主体性,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主体,都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特征。当然,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存在也决定了主体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也是有差异的。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必然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人。一直以来,学界围绕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谁是主体的问题争论不休,争论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理解不同。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6](P692)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就会存在什么样的主体。所以,主体的形式其实是由它所参与的实践活动的形式决定的。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不同阶段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会有差异,而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也是不相同的。
因此,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把教育者界定为主体,也不能简单地把受教育者界定为客体,更不能静态地把教育者或受教育者一成不变地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或客体,而应该依据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实际功能发挥来判定其主体地位和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这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谁组织、发起、承担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谁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只有真正履行了组织、发起、承担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职能者,才可以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一句话,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相对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发起者、承担者和实施者。
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有阶级性,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诉求。把握好这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属性,对于我们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含义与表现
学界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时,有人把主体间性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认为现代条件下,客体都成了主体,思想政治教育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实,这个观点是值得推敲的。试想,没有客体,哪来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客体,其主体就失去了对象依托,就沦为了无客体的主体,其主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就像主体离不开客体一样,客体也离不开主体。
客体是与主体一起产生的,是实践活动中“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客体既可能是物质的东西,也可能是精神的东西”。[1](P117)既然客体是物质的东西,那么自然也包括了人,其中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身。客观事物是否能够成为实践活动的客体,以及成为什么样的客体,如何成为客体,既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以及实践活动的性质,同时也取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首先,客体必然是具有客观性的。这是区别于主观性而言的,客观存在是客体之所以成为客体的前提和基础,客观存在的事物包含的范围很广,太阳、河流、生产关系、政党等都是客观存在,但是,对于那些主观臆想出来的虚假事物则不能够成为客体,例如,上帝、天堂等。其次,客体还应该具有对象性。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丰富多样的,但并不是所有客观存在的事物都可能成为客体。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P306)客体概念仅仅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所以只有成为主体活动对象的客观事物才能够成为客体。对象性是客体之所以成为客体的关键性因素。再次,客体也具有被动性。客体在被纳入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时就已经体现了其被动性的特征,客体无法自由选择主体,但是主体却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相应的认识和实践客体。客体在被纳入主体的活动之后,也是根据主体的原则进行改变,主体将自身的思想、观点或者行为应用于客体,实现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最后,客体还具有规律性。客体的规律性是指客体在参与认识或实践活动时,具有自己相应的准则和规律,正如列宁所说,不应该把客体简单地了解为存在,而应该了解为“完备的、‘具体的、自身完整的、独立的东西’”。[7](P154)客体的规律性一方面制约着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决定着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客体的规律一旦被主体掌握,也就可以帮助主体更加准确地认识客体,改造客体。
根据客体属性的规定,客体也具有不同的类型。按照客体的表现形式的差异,可以将客体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精神客体三种类型。自然客体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客体形式,小到微观领域的分子、原子,大到宏观世界的宇宙,只要是人类认识已经触及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人类认识的客体。而且,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自然客体的外延会不断扩大。如果说自然客体是自然界存在形式的客体,那么社会客体则处处充满了人类活动的痕迹。社会客体主要包括了人、物质系统和精神系统三个方面。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客体是从主体自身出发而言的,在人相互认识的时候,如果将自身作为主体,对方就成为认识的客体;而社会客体中的物质系统包括了所有人化自然的产物,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精神系统则是指社会的精神生产产品、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切制度的总和。精神客体主要是指客体的思维、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东西。精神客体之所以可能被纳入客体系统,主要是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同时也要改造客体的主观精神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改造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客观世界改造的重要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可以指向一定的精神存在物,即客体的精神世界,但是这种精神存在物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特殊之处。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客体,首先是因为精神也是客观存在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等是以人的生理为基础而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精神现象。心理学所揭示的就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现象,而文化学则是揭示的关于人的外在客观精神世界的现象,例如,各种文化现象、人文风俗等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精神现象一旦与人发生了对象性的联系,就成为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对象,于是就产生了精神客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3](P305)一般说来,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客体的精神世界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
任何主客体关系的建立是要以满足主体的利益为最终归宿的,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自然也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需求和利益。按照这一逻辑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就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意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改造精神世界的实践活动,将教育对象作为客体,其目的是要实现人的精神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国家主流价值观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促进人的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就必须把受教育者视为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主体的客体,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当然,任何理论都是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徘徊和斗争,在对实然的批判和反思中才能够不断向应然世界靠近。过去,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受教育者理解为一成不变的客体,是以教育者主体为出发点来理解的,这种理解方式不仅扼杀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理解不仅要考虑主客体关系的属性,同时还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特殊性。在这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视为活动的主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作用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和受动者,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相对应,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主体和与之相对应的客体。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关键在于把握客体的基本属性,以及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有着不同于一般物质客体的根本特征。一般物质客体在接受主体的作用时,往往是被动的,当然,有时也会在主体作用时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只是客体受到主体作用时的一种条件反射,而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能动反应。然而,作为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他们就不会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活动,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最大化。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不仅具有主观能动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能获得主体性。从一般意义上讲,客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所具有的,有了客体性才能成其为客体。主体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具有的,因为只有有了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但在当受教育者对他人进行教育或进行自我教育的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也能获得主体性,并逐渐上升为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客为主,由客体转变为主体,但这时他已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而已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了,具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具有的属性、地位和作用”,[8](P88)实现了客体主体化。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属性是思想性、政治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作为教育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属性,我们才能真正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一般教育活动区别开来,从而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育人活动,它有着鲜明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总是要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要求,为一定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所制约,服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从而为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服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并不是单一存在物,如果主体的具体指向不同,其对象也存在差异。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科,已经具有自己相对完善的理论结构。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结构为基础,结合前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中,大致存在以下四种关系。
第一种是认识关系。主客体的产生标志着哲学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所以,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是所有主客体关系中最为基础的一种。在主客体认识关系中,主体是能动的方面,客体是认识的对象性存在,“如果我们把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一定的活动和功能的动态结构的话,那么,主体和客体就是构成这个结构的两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极,都不可能构成认识的结构,不可能产生认识的活动和功能。无主体的认识和无客体的认识,都是不可设想的。”[9](P61)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但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层次的不同,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具体指向也不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认识主体,而他们认识的客体既包括了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人,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同时也包括了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政策等等,可以说一切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任何事物都能够被纳入到认识客体的领域,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才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进行。在过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时,认识关系往往被当作实践关系,从而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它具有认识活动的特殊性。
认识关系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认识活动是一切活动的起点,但不是终点,认识活动的目的是为下一阶段的实践活动做准备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如果事先没有对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政策等有一个认知环节,就必然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盲目性。列宁在阐述其“灌输论”思想时,也是因为对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做了初步的认识,并得出了“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0](P317)同时,列宁还对当时工人阶级所处的思想环境进行了考察,认为当时的情况“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10](P326)列宁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才为他在工人阶级中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活动提供了认识论的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关系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一开始就形成了,并且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认识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会发生认识上的变化,而认识变化又会促进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者方法,从而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种关系是实践关系。马克思将实践的概念引入哲学,使传统哲学从思辨走向了生活,哲学不再是哲学家的哲学,而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工具。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桥梁,是主体和客体从二元对立转为相互统一的中介,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转化的工具,实践关系是主客体关系的本质。马克思在谈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时写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4](P138)虽然,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一切人类从事的活动都定义为实践活动,但为了与其他活动相区别,这里所说的实践关系特指在主体改造客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主体与客体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实践活动,主客体之间通过实践活动相互渗透和转化,主体按照本身的目的和需要并依据客体的属性对客体进行改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与认识关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认识关系中的主体并不改变客体的形态,而实践关系中,主体的目的就是要按照自身的尺度改变客体,使客体符合主体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关系具有学科的特殊性,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活动、评价活动等相区别。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实践关系体现在对受教育者主观世界的改造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通过改变受教育者的政治认知、道德素养、价值观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实践活动并不是教育者单独可以完成的,必须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协作,一起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够对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这种实践活动实际上是属于精神实践活动,通过这种精神实践活动,实现了教育者主体的客体化和受教育者客体的主体化,以及受教育者精神客体的主体化。而当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成为一项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时,整个人类社会将成为自己共同的主体,通过自觉的教育活动改造自身的主观精神世界,这时,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成为同一的过程,也就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关系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学过程之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也都充满了主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只不过主体和客体的具体指向不再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这时,主体往往是教育决策部门,而客体则是客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内容、方法等。实践关系中的主客体的具体指向与实践活动的形式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就会有相应的实践主客体。
第三种关系是价值关系。价值反映的是人和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范畴。在价值论中,外物通常被称为价值客体,人则是价值主体,价值就是主体和客体发生关系时,客体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任何一种价值关系都应该具备三种规定性:其一是属人性,价值的产生和大小一定取决于主体的尺度和标准的,凡是符合主体的尺度和标准的客体才会对主体产生价值。相同的客体对不同的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价值,价值就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11](P79)其二是客体性,价值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主观臆想的,它必然是源于外部世界的。“价值是客体的固有属性(与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因而完全存在于客体固有属性之中。”[12](P37)其三是主客体之间必然要形成联系,价值关系是主体和客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就是客体的属性与主体尺度之间形成的有用性关系。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是价值关系形成的两个基本要素。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现实意义上讲,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相对于主体的生存与发展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是一种带有主体目的色彩的事实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价值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个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关系。从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的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来看,起码具有三种价值关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具有价值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又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手段具有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特点,从而满足不同价值主体的需要。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社会群体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价值关系,社会群体包括了一定的政治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等等,思想政治教育以满足和符合这些群体的需要而形成了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精神价值等等。再次,人类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也存在价值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从而推动客观世界发展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要发展,也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之间也会形成价值关系。教育者和受教育作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环境等要素形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客体的属性满足了主体的需要,从而促进主体的发展。而对教育者来说,“教”既是一种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属性,同样受教育者具有“学”的需要和属性,所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也互为价值主客体。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是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
第四种关系是审美关系。人的审美活动不仅是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人的精神生产和生活的特殊形式。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对象通过信息的相互交流和更新而实现人的认识上的飞跃和精神上的升华。“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4](P55)所以,审美关系中的客体必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外界事物,而审美的主体则是活动中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关系一旦构建并发生规律性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原来的教育者、受教育者都成为审美关系中的主体,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又互为主客体,以情感和理性的统一去认识和把握审美客体——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活动本身。”[13](P70-71)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审美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审美主体的特殊本质力量与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客体的特殊本质力量相对应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对象性关系。过去思想政治教育被认为枯燥无味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关系的忽略,尤其是对受教育者作为审美主体地位的忽略,使受教育者无法感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美、过程美、形式美,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单方面的灌输活动。提倡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关系的确立实际上是要将受教育置于审美主体的地位,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感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过程中的美,使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审美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审美心境,“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的自主性一定会在感性领域展现出来,感觉的力量在它自己的界限之内一定会被打破,自然的人已经净化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现在只要按照自由的法则就能从自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这样,从审美状态到逻辑状态和道德状态(从美到真理和义务)的步骤,比从自然状态到审美状态(从纯粹的盲目生命到形式)的步骤,不知要容易多少。”[14](P72)因此,只有当教育主客体的审美关系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塑造真、善、美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规定。因此,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双方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看作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坚持认识和实践的统一,现阶段,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辩证统一。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中,认识关系与实践关系辩证统一。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认识活动是适应实践的需要,为解决和完成实践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通过教育活动方式把主体和客体直接地、现实地联结起来,使主体能从客体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完成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如此一来,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有用性和效益性就凸显出来了,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也就应运而生了。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价值关系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才逐渐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属人的世界,并与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审美关系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对象性关系”,审美关系有着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只有当思想政治教育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和合乎社会发展的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性和合乎社会发展的态度对待思想政治教育,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审美关系才得以确证。因此,审美关系是基于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基础上才能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一种特殊关系。
进一步说,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在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不仅表现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即认识关系,而且形成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即实践关系。在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作为主体活动的力量来源和内在尺度,对于主体活动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即需要与满足需要或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得以确立,而且,这种价值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对人的思想品德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肯定,即审美关系的确立。
一言以蔽之,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四对关系,它们是一种相互对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事实关系,共同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存在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是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的统一。这种统一既体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意义,又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
[1] 齐振海,袁贵仁.哲学中的主体和客体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苏]M.A.帕尔纽克主编.作为哲学问题的主体和客体[M].刘继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列宁全集[M].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9] 夏甄陶.认识论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 列宁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项久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 周芳.思想政治教育审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李文苓]
OnMarxistLogic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ubjectandObjec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Xiang Jiuyu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Marxist view;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bject; obj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enjoys distinct ideology nature, reflecting the proletarian class as well as its class interests.According to Marxist subject & object theory and the speci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subject & object relationship, the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oes not only refer to educators, but results in a variety of subject systems. The object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educated, but,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form of the object is also different.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dynamic.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y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ach other. As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e on various forms,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kin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e and cognition, value and aesthetics form the subject & object rel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y are the factual relationship of mutual correspondenc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development, commonly pointing to the present existenc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refore,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key for us to deeply discus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cientifically.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研究”(项目号:13AKS011)的阶段性成果。
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喀什大学“自治区天山学者”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