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
----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姜 哲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
----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姜 哲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经学;现代化;小学;第二朴真;诠释学;后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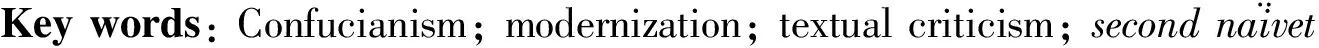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经学的现代化至少可以追溯至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经学以“朴学”而闻名,尤精于小学、考证,即所谓“实事求是”、所谓“无征不信”。“乾嘉学派”主张“由小学入经学”,将经学之本立于小学,其确实渗透出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而且似乎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现代化的路径。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小学”毕竟不是“经学”,“考据”也无法取代“解经”。“乾嘉学派”所标举的“实证方法”,既是其本质性的特征,也是其无法超越的“限度”。因此,在反思“朴学”的治经理路之时,我们还需要为经学之现代化开出新的路向。
一 前现代的现代性因素:经学之小学化
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P370)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中更是以一种“独断”(dogmatism)的口吻道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的断语。[2](P1)由此可见,清代经学“小学化”的诠释路向,其以“实证”和“归纳”为核心,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乾嘉学风的形成在学术界尚存争议——这种“前现代的现代性(modernity)因素”究竟是中国传统经学及学术的自然演进,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所传播的天文、地舆等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及其技术理性的影响?这一争论虽有逐渐升级的趋势,但迄今为止尚没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而且,无论其争论的结果如何,其实都不会对我们反思“乾嘉学派”的“小学化”经学研究路向构成本质性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成大国’了。”[3](P204)实际上,“小学”在清儒手中非但已成“大国”,且更有殖民“经学”以降为“附庸”之势。日本学者池田秀三在《训诂的虚与实》一文中比较了高邮王氏父子在治学方面的差异,他认为王念孙的学问“其根底里尚存有对经之大道的信仰”,而其子王引之则“舍弃大道,以小学本身为终极目标”。[4](P18)具体而言,王引之几乎将“语助”或“发声”的规定发展到了“极致”的程度,其不再是为了注经之用,而是“小学的自我目的化”,[4](P19)即所谓“为学问而学问”。[5](P36)因此,五经文本或《十三经》文本也随之由“圣经”的地位降格为与史、子、集同科,并沦为王引之文字学理论的“注脚”。
至此,我们似乎应该回溯“小学”与“经学”在经学史中的关系,以期了解二者等级序列(hierarchy)关系“倒转”的某种缘由。“小学”之名古已有之,其为“刘向、班固之序六艺为九种”之一,[6](P38)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载,此“九种”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和“小学”。由是可知,“小学”最初确实附属于“六艺之学”,也即“经学”。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被视为小学之重要文献的《尔雅》,在《艺文志》中并未被列入“小学”,而是被归于《孝经》类。这一归类是否妥当,我们暂且不论,总之“小学”在《艺文志》中所收录的多为“字书”,其范围较为狭窄。后来,“小学”随着经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仅将《尔雅》一类的注经之书囊括其中,也逐渐形成了文字、训诂、音韵等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从《艺文志》中的“小学”不录《尔雅》又可看出,“小学”与“经学”实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为其日后“蔚成大国”甚至脱离“经学”之轨范早已埋下了伏笔,即二者等级序列关系“倒转”之可能性已经被预先决定了。
池田秀三在前文中亦解释了,为什么郑玄多以“实义”来解释王引之所谓的“语助”或“发声”,这主要是由郑玄的经学家立场所决定的。作为经学家的郑玄,其“对于圣人之言的信仰,支配了他的训诂”,他无法忍受传达“恒久之至道”的经文中充斥着大量的“无义”助字。[4](P15)因此,池田秀三指出“注释之学的典型乃郑玄,而郑玄与王引之的对立,即注释之学与语典之学的对立”。[4](P19)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立似乎又恰好回应了《艺文志》中作为“释经之书”的《尔雅》与“收录字书”的“小学”之所以分列的原因。平心而论,“小学”对“经学”确有助益,但其并不应完全附属于“经学”,其超出“经学”之轨范乃势所必然。
然而,“小学”不但超出“经学”而又欲反制“经学”的倾向,则需要进行更为深刻的省察。如前所述,王念孙所提出的“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之命题,其大抵不错,但是“小学明”何以一跃而能够达到“经学明”的境界呢?难道“经学”直接可以等同于“小学”或“训诂声音”吗?试问《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一句在“训诂声音”上究竟有何不明,为何《公羊传》与《穀梁传》的诠解却大相径庭?前者以大一统、长幼尊卑之分而美隐公还位于桓公之意,后者却因“成父之恶”以责隐公之废大义而“行小惠”之举。像这样的“小学明而经学难明”的例子,在经学诠释中可谓俯拾皆是。其实,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在《修辞学与诠释学》(RhetorikundHermeneutik)一文中即已表明:“对于每位读者而言,某个古典文本是无法得到理解的,如果人们唯客观性的科学理论概念之马首是瞻,并将这种文本预先形成的特性作为理解的独断(dogmatische)限定。”[7](S278-279)
同样,讲求“考索之功”的小学家们,其表面上“朴素而科学”的“实证理性”,恰恰暴露了其内心中“非理性”的“傲慢”与“独断”。难怪梁启超对惠栋一派的治学方法给出了这样的讥评:“凡古必真,凡汉皆好。”[5](P24)这种“崇古的前见”使看似“科学理性”的训诂考证显现出其牢不可破的“诠释前提”。这也就是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所说的理解的“先行结构”(Vor-Struktur),*“先行结构”这一概念可详参[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in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d.2,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ss.199-200.)。即“解释从来就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事物作无前提的把握”。[8](S200)因此,若质而言之,清代经学的“汉、宋之争”亦都是“六经注我”的诠经模式:后者以“我之义”格“六经”,难免“断章取义”,遂使“六经”沦作“我之注脚”;而前者明为“我注六经”,却暗自以“字义”替换“经义”,实则“断字取义”,而更显其“支离”与“独断”。
就“独断”之程度而言,前引戴震“由词以通其道”之论似远不如王念孙。然而,后者亦是承袭前者将“道义”或“经义”降为“词义”,进而再降为“字义”的“释经理路”。实际上,这一“释经理路”渗透着对“意义”以及“真理”之“不在场”的深刻“不安”。中国传统经学在释经方面,大都以追寻“圣人之意”为旨归。然而,圣人已殁,“圣人之意”如何可得?王昶《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中记载了“戴震难师”的一段文字:
授《大学章句》至大注“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而。”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大奇之。[9](P217)这段引文大都被用来表明戴震日后“好深湛之思”的缘由,[9](P217)然而这种“深湛”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焦虑”,即由“圣人已远”这种“时间间距”所产生的对“圣人之意”的“疏隔”。因此,“圣人已远”所留下的“意义空白”必须由经文之“古字古义”来“补替”(supplément),*“补替”的解构内涵可详参[法]雅克·德里达著:《论文字学》(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ditions de Minuit, 1967, p.208.)。从而虚幻地营造出“圣人之意”的恒久“在场”。
所以,“经学之小学化”虽已初具知识之现代化的雏形,但同时也是作为“大学”之“经学”走向式微的写照。同样,在当下的中国学界,“国学”迅速“升温”,而“古文字学”这种杂合了现代考古学及相关科技手段的“小学”研究,随着大量简帛的出土与回购已有渐成“显学”之势。然而,历史本不该有如此的相似。如若当下的国学研究仅能以承“乾嘉学派”之余绪的“古文字学”为主脉,那么亦很难说是国学之幸还是不幸。虽然“古文字学”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即使在最大的限度上,它也只能构成对当代学者在诠释古典方面所体现出的意义建构能力之虚空的“象征性补替”。
二 “后批判”的“朴真”:经学之信仰化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经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然而,从内部瓦解“经学”及其信仰基础的则应首推后来的“古史辨运动”。促成该运动兴起的重要人物有钱玄同与顾颉刚,他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晚清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崔适的影响。但是,晚清今文经学“辨伪”古文经书是为了从根源上摧毁古文经学,其格局仍未跳脱传统经学之轨范。其实,“辨伪”也同样是乾嘉“考据之学”的重要方法,是“训诂名物”不可或缺的功夫。而梁启超所谓的“清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5](P51)也正是看到了“乾嘉学派”的“实证理性”与其“崇古的前见”相龃龉的方面。晚清今文经学似乎就是以乾嘉学者之矛而攻其盾,然其仍仅为经学内部之较量。而“古史辨派”则欲完全跳脱“经学”,执“疑古”、“辨伪”之利器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一并打落。
在《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顾颉刚表明其只是在方法论上承袭今文经学:“但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10](P631)而在《古史辨》第五册的《自序》中,顾颉刚更是以颇具“学阀气”的口吻言道:“我们的推倒古文家,并不是要帮今文家占上风,我们一样要用这种方法来收拾今文家。”[10](自序P3)其实,“古史辨派”并无多少深刻复杂的思想,其只不过是将经学文本视为史料而逐一考辨其真伪,而其“辨伪”时的“先入之见”亦极为明显。在更深的层面上,“古史辨派”亦是远承“乾嘉学派”之衣钵,其以“史学”替换“经学”的方法与后者以“小学”替换“经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其最大的问题也正在于此,基督教的《圣经》中也包含着历史的“踪迹”(trace),然而即便是神学家们也不会将其一一坐实。因为“经学”毕竟不同于“史学”,何况“古史辨派”的史学观又极其狭隘,在他们而言“历史”似乎仅仅等同于“史实”。
因此,“古史辨派”的主张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命题绝不相同。按余英时的说法,章学诚主要以“文史校雠”之法探明文史之义例,进而由文史以明“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其是以“文史校雠”来对抗“乾嘉学派”以文字训诂明“道”的诠释理路。[11](P160)可见,“古史辨派”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远不及章学诚的丰富深广。此外,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亦在“经学”的视域之下对“经、史关系”进行了辨明。其在《经学通论》一书中指出:“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个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12](P22)当然,皮锡瑞的“诠释前提”是“孔子作《春秋》以借事明义”。而“古史辨派”则一定会从“史实”的角度否定“孔子作《春秋》”一事。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全面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是搬倒“经学”的关键——“孔子删述六经”可以说是整个经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命题”。难怪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开辟时代》中,以一种极其“独断”的语气将“六经”的“神圣制作权”归于“孔子”:“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13](P2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钱玄同在《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一文中则一定要将二者分离:“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底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14](P52)然而,将“经书”作为记载具体史实的“史书”,即便剔除了所谓的“伪史”又如何能将“历史”讲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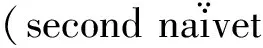
即便我们不能依照原初的信仰栖居于神圣的伟大象征之中,我们这些现代人也能在批判之中并通过批判求得第二朴真。简言之,通过解释我们可以再次聆听;在诠释之中,我们同样能够将象征所提供的意义与解码的可得而闻的初衷结合在一起。[15](P326)
其实,若以利科观之,“古史辨派”所谓“六经”中的“伪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象征”或“隐喻”(前引皮锡瑞区分经、史的论述已暗含了这一视角),“六经”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言说“真理”的。总之,利科的“第二朴真”为我们重获“六经”的“启示”打开了新的可能——“六经”之“真理性”本不必系之于“孔子”的删述,就如同“四福音书”的“真理性”不必系之于“耶稣”的真实存在一样。二者的“真理性”甚至也不必系之于某种狭隘的“真实性”,例如《古文尚书》无论辨伪到何种程度,其对宋代历史的实际影响都不应该有丝毫减损,这就是其毋庸置疑也不可撼动的“真理性”。
然而,随着大批出土文献的发掘与释读,某些学者遂提出了“重写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主张。出土文献的释读确实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世文献,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出土文献的“真实性”而冲动地“虚拟”其“真理性”。以那些没有实际参与中国古代思想史进程的出土文献,如何“重写”已经实际发生的历史?这样的思想史也只能是一部“借尸还魂”的“虚幻历史”,其虚幻性绝不亚于以“文字训诂”替换“微言大义”。
让我们再回到“第二朴真”的命题上来,利科在上述引文中特别强调这种“朴真”是“在批判之中并通过批判”而获得的。正是通过“批判”的“去魅”(Entzauberung)或“去神话”(Entmythologisierung)作用,无论是西方的《圣经》还是中国的“六经”,才能够以一种更为“本真”的方式向我们发出“召唤”。就“经学”而言,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经终结,不再是“俛拾青紫”的手段,今文经学家们的“妖妄”也无从附丽。由此,“经学”之“信仰的维度”也许才得以真正地开启,而其中又必然包含着“理解的维度”。因而,利科又提出了“为了信仰而理解,为了理解而信仰”(Ilfautcomprendrepourcroire,maisilfautcroirepourcomprendre)的诠释学命题。[15](P326)在这种“信仰”与“理解”的诠释循环之中,“六经”的“微言大义”及其“真理性”才可能不断地向我们显现。
三 “后经学”的超越性:经学之诠释学化
也许是由于“经学”已经成为“僵尸”,所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予同提出“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13](序言P6)而且这种“经学史”应当是一种“超经学的研究”。[16](P633)但周予同所谓的“超经学”也只不过是超越今、古文的“师说家法”或“汉、宋之争”,以一种历史的、客观的态度来研究经学及其相关的问题。无论是其“综合的记述的工作”,还是其“分析的解释的工作”,都显出某种“超越性”的不足——其既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经学已有的问题视域,也没有超越“古史辨派”以“史”治“经”的狭隘范式。[16](P634-635)相比之下,现代西方诠释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诠释学”(ontologicalhermeneutics)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却为中国传统经学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向,使其可能从根本上再度超越“超经学”(extra-Confucianism),从而转变为一种“后经学”(meta-Confucianism)研究。
在《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的启示》一文中,赵敦华已经谈到了“经学诠释学化”的问题:
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对中国学术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如果说经学与古典学相媲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小学”和“义理”的分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张力,也可视为现代解释学问题。[17]因此,如果说“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解释学不过是对古典学为基础的西学传统作出哲学解释”;[17]那么,我们也理应对“经学”这一中学传统作出哲学尤其是“现代诠释学”的解释。所以,我们也不妨将其称之为“经学诠释学”(hermeneuticsofConfucianism)。
“经学诠释学”绝不是“一头怪兽”,因为它并非如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Kubin)所言,是出于文化不自信而产生的“攀比心态”——西方有“诠释学”,中国也有而且更早。[18](P311-312)这种“攀比”与“比附”的研究,与“经学诠释学”毫无关系。如前所述,“经学诠释学”是一种“后经学”研究,这也就是说它“超越”了传统经学原有的问题视域。具体而言,其研究的基础和重心主要不是放在对历代经文注疏的梳理和总结以进行“同类项的合并”工作,也不是分析某一注疏正确与否或比较几种注疏的优劣,甚至更不是利用出土文献或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对某一经文提出新的理解与解释。这种仅在量上进行积累和递增的研究,我们将其归之于传统的经学研究就已经足够了。因此,作为“后经学”研究的“经学诠释学”,其首先和始终要追问的并不是经文注释的“什么”(what)而是“如何”(how),即一种经学诠释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prerequisite)。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的“第二版序言”(Vorwortzur2.Auflage)中,对其“哲学诠释学”的一贯主张做出了重要的申明:“但是,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意愿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7](S438)这其实已经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其所谓的“哲学的主张”是一种“后设性研究”。而伽达默尔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申明,就是因为他使用“诠释学”这一具有悠久传统的术语引起了某些误解。在该篇序言中,他首先表明了《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写作目的:
理解的“技艺学”(Kunstlehre),如其在以前的诠释学中那样,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阐明一个技艺规则(Kunstregeln)的体系,以便能够描述甚或引导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程序。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探寻人文科学工作的理论基础,进而使获得的知识付诸实践。[7](S438)同样,“经学诠释学”也绝不是要为理解经学和具体的经文以及经文的注疏等提供一套方法论的“技艺规则”,而是要深入到方法论的背后去探寻其基础。这也就是说,“经学诠释学”要对前人的经学研究做“前理论”或“前科学”的考查,而这正是经学自身的“基本概念”(Grundbegriff)和方法论体系所无法达到的。
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看,任何学科都是建立在一些由其自身所设定的“基本概念”之上。就此而言,“孔子”即便是在“传统经学”中也应该被视为这样的“基本概念”,而且其作为“基本概念”的意义远远高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孔子”。此外,对“孔子”和“六经”这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与规定,又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经学历史发展的不同形态。周予同曾将中国传统经学分为三大派别,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和“宋学”。[13](序言P1)而这三派的不同则表现为: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13](序言P3)
其实,这种“以……为……”的表述方式,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所说的“作为结构”(Als-Struktur),其可被视为“先行结构”的具体化,是任何理解与解释得以产生的“先决条件”。诚如海德格尔所言:
在理解中被展开之物,也就是被理解的东西,总是已经如此被通达,即在其中它的“作为什么”(alswas)总是可以被明确地提出。这个“作为”(Als)形成了某个被理解之物的明确性结构;“作为”建构着(konstituiert)解释。[8](S198)“某物只有被作为某物”,它才是可以理解和通达的。按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所有解释都活动在此前提出的先行结构之中。每一对理解有所助益的解释必须已经对所要解释之物有所理解。”[8](S202)
既然如此,那么在理解的过程中似乎就出现了一种“循环”(Zirkel)——“理解”既是“解释”的前提又是“解释”的结果。然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决定性的不是从这一循环中脱身,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种循环。理解的循环不是由一个任意的认知方式活动于其间的圆圈,而是对此在自身的生存论上的(existenzialen)先行结构的表达。”[8](S203)进而,海德格尔又向我们表明:“理解中的‘循环’属于意义的结构,这一现象根植于此在的生存论构成,根植于解释着的理解。作为在世界中存在而关注其自身的存在的存在者,具有存在论上的(ontologische)循环结构。”[8](S204)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于解释者自身在存在论上的循环结构所导致的“诠释循环”(diehermeneutischeZirkel),称为“存在论的诠释循环”。那么,为我们所熟知的“部分”与“整体”的循环,则仅可被视作“方法论的诠释循环”,因为其只是前者的“派生形式”而已。
因此,“经学诠释学”必须对每一种经学诠释的“先行结构”及其“循环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且对其在具体的经学诠释命题以及经文注疏中的潜在作用给予澄明。
四 结 语
就现代知识论而言,传统的“小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科学认识的范畴,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与价值,而且其中的科学因素也包含着现代性的怀疑与批判。“古史辨派”即是继承了这种怀疑主义与批判性,从而将经学“扫荡”和“收拾”了一翻,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经学的存在基础。然而,对于“经学”而言,这种“扫荡”和“收拾”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为我们更加成熟地面对儒家经典创造了某种机会。这些经典固然可能是“层累地造成的”,[14](P60)其原初形制也不大可能被完全恢复。而且,经典的开放性还使其不停地被使用甚至滥用、不断地被理解也被误解。然而,这些儒家经典在核心上却仍然保持着同一性。其有时虽不免被扭曲,但在信仰、理解和解释的反复作用下,其仍然在不断地被丰富。[19](Pxvii-xviii)总之,身处“后批判”(post-criticism)时代的我们,在反思经学诠释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这些经典文本中的伟大“象征”和“隐喻”及其为我们建构的“意义世界”。
[1] [清]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A].[清]戴震.戴震全书(第六册)[C].合肥:黄山书社,1995:370-372.
[2] [清]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A].[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藏版,1981:1-2.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七册)[C].上海:中华书局,1936.
[4] [日]池田秀三.训诂的虚与实[A].石立善译.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五辑)[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4.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九册)[C].上海:中华书局,1936.
[6] [清]龚自珍.六经正名[A].[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6-38.
[7]Gadamer,Hans-Georg.Hermeneutik II: Wahrheit und Methode,Ergänzungen, Register[M]. In: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Bd.2,Tübingen:J.C.B.Mohr(PaulSiebeck), 1993.
[8]Heidegger,Martin.Sein und Zeit[M]. In: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Bd.2,FrankfurtamMain:VittorioKlostermann, 1977.
[9] [清]王昶.春融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三八)·集部·别集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0] 顾颉刚.古史辨(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 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
[12]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54.
[13]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 顾颉刚.古史辨(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Ricoeur,Paul. Finitude et culpabilité II: La Symbolique du mal[M]. Paris:Éditions Montaigne, 1960.
[16] 周予同.怎样研究经学[A].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627-635.
[17] 赵敦华.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的启示[N].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9, 6(30):11.
[18] Kubin, Wolfgang. “Chinese ‘Hermeneutics’—A Chimera? Preliminary Remarks on Differences of Understanding”[A]. In: Ching-I Tu, ed.,InterpretationandIntellectualChange:ChineseHermeneuticsinHistoricalPerspective[C].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311-320.
[19] Leys, Simon. trans.,TheAnalectsofConfucius[M].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Canonical Interpretation and Belief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JIANG Zhe
(Liberal Colleg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2015-10-20
姜 哲(1978—),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西方诠释学比较研究、中西经典互译.
B222
A
1008—1763(2016)01—004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