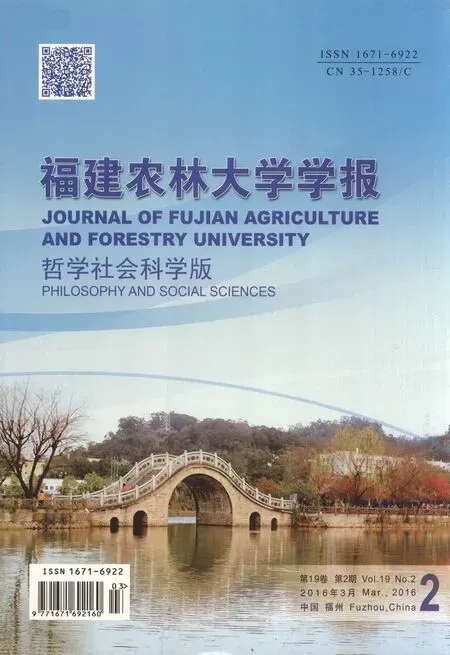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中的媒介支持系统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张 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中的媒介支持系统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张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在人际传播网络、大众传媒及新媒介、组织传播渠道等不同形态媒介的介入和助推下,完成了非农职业角色的获得;并通过新媒介使用、组织沟通、城乡人际交往等传播实践,在职业生活中的信息、技能和情感层面实现自我赋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职业自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中媒介助推的影响与自我赋权的努力之间不断互动重构,本质上是一个媒介支持系统推动他们不断职业化的过程,进而影响到其自身城市适应进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媒介支持
[DOI]10.13322/j.cnki.fjsk.2016.02.005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统计,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如就就业层面而言,他们的外出就业动机、就业关系网络、就业所属领域都与父辈们有着显著差异[2]。近年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虽然现有研究丰富和深化了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并使得后续研究站在更高起点上,但其存在的“问题视角”偏向仍不容忽视。这体现在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视为一个社会问题,描述这一群体在就业上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制度、社会、文化、人力等方面的原因,然后从政府、企业、社会、个体等层面提出建议,更多的是一种应然式的对策探讨[3]。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视角从就业能力、就业质量的实然层面出发,建立相应的测量指标体系,揭示出就业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但由于就业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动态循环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的丰富体验和适应实践容易被忽略掉。其实,对于新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外部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忽视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作为理性主体创造自己生活世界和进行意义建构的能力”[4]。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探索、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就业实践,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与此同时,有别于乡村社会,城市社会大众传媒发达、新媒介普及率高,且组织传播渠道完善、人际交往频繁,媒介已经渗透到城市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当中,媒介也扮演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其参与、促进、影响甚至是改变着他们的就业体验。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媒介推动他们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就业适应过程,以及他们如何借助媒介实现一定程度的职业自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媒介,它不仅仅是指我们通常最直观可见的大众传媒及新媒介,也包括了人际媒介、组织媒介这2种形态。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思路,所使用的资料来自于2014年4月至8月在长三角地区(江苏南京、浙江温州、上海等地)对27名受访者进行的深度访谈。受访者出生年份都在1980年及以后,来自于湖北、安徽、江西、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也有来自江苏的本地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他们普遍拥有智能手机,上网频率较高,也有不少人接触电视较多;人际交往圈子主要限于同事、老乡及小部分城里人。此外,他们在企业内大多处于基层岗位,也有个别活跃在中层管理岗位,组织内的为人处世能力因人而异。
一、进城务工:传播环境的变换及所面临的就业挑战
在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里,只有依照亲疏远近形成的“社会圈子”,而没有依据效率和分工原则组建起来的现代组织。人们依附于土地之上世代务农,自产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信息交换的范围和频率都很有限,且多局限在以血缘、地缘联结为主的人际传播网络内。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的渗透也比较有限,传媒资源的配置失衡、传播内容的视角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在农业生产活动上所发挥的效应,虽近年来手机等新媒介在农村迅速普及,但并不足以改变当前涉农传播薄弱的局面。
与此相反,城市是一个被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城市务工从一开始就需要依托于一个有着明确目标的职业组织,个体的相当部分社会活动也只有在组织的框架下才能得以开展。组织是个体生活中无法绕开的客观存在,它为城市里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平台和契机,由此衍生出来的业缘关系,如组织内部的领导、同事和下属,以及组织外部的顾客和相关合作伙伴,逐渐在个体的人际传播网络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此外,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使得相当多职业不仅流动性强,而且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和互联网新媒介,为个体接受充分的资讯信息提供了可能。
从乡村到城市,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传播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媒介的类型从一元变为多元,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程度更深,媒介所发挥的功能也更加多样化。这种转变给他们的职业生活带来了种种挑战,在城市就业过程中他们在受到媒介驱动的同时,又会对媒介的这种介入作出回应,由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媒介体验。
二、众力汇聚:媒介助推下的职业获得与角色适应
就业连接着个体与社会,个体通过就业才能成为家庭的完全劳动力、企业组织的人力资源以及社会中的一员,因此就业从来都不只是私人的事务,它被纳入到社会的结构性层面当中,成为社会政策、制度和法规的指涉领域。在城市发达的传播系统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受到了不同形态媒介的推动,无论是围绕家庭、居住地和工作场所形成的人际传播网络,还是以用人企业、职业中介、劳动人才市场为主的组织传播渠道,亦或是以报纸、电视为主的大众传媒以及互联网新媒介,它们出于伦理、人情、利益或道义上的考虑,从信息传播、资源传递和情感沟通等层面推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角色获得。
(一)职业机会搜寻:多方供给的信息传播
人的社会性属性决定了人无法脱离于一定的人际传播网络而存在,因此“亲友介绍”成为两代农民工初次求职的主要途径。然而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完善,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市场化的求职方式也在这一群体当中逐渐兴起[5]。这既包括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及互联网新媒介,也包括了用人企业、职业中介、劳动人才市场等组织媒介。
1984年出生的志伟是湖北黄冈人,2006年中专毕业后外出务工,曾辗转于北京、江苏和广东等地,从事过网管、销售员、保安等工作,目前待业在家。虽然进城初期主要经亲戚、老乡和同学介绍工作,但他觉得“身边的人都是和自己混得一样的,找他们也介绍不到什么好工作”,近几年来志伟主要通过职业中介、劳动人才市场和互联网等渠道谋职,并对这些不同的渠道形成了一些固定认知,如“介绍所就是你给他钱,他带你到你想去的公司面试”,“民工市场,一次可以看很多家,现场问清楚”,“网上合适的很少,有些就是骗人的,10个工作信息里面有三四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在我们的访谈中,像志伟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在职业机会的搜寻过程中,他们初期依赖于人际传播网络中流通的知识、经验与信息,但随着城市生活经历的丰富,也会转而求助于一些市场化渠道。此外,也有一些公益性渠道如社区服务中心、非政府组织,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各种就业信息线索。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机会获得途径越来越多元化。人际传播网络依旧占据着主导位置,大众传媒及新媒介的地位日益凸显,组织传播渠道也获得了肯定,在这种多方供给的信息传播格局下,他们的就业选择机会更多,并将以此为起点开始自己的城市打工生涯。
(二)职业技能习得:组织主导的资源传递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其初次务工年龄普遍较小,以吸纳年轻人就业为主的服务业,要比制造业和建筑业更有吸引力。相对来说,服务业需要与人沟通交流,工作流程更为复杂,对于职业技能的要求也更高,因此企业组织参与和引导的范围也要广得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往往会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帮助入职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善职业技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组织。
小高是安徽阜阳人,2013年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半年,次年春节过后便离开家乡前往温州务工。在姐姐的带领和介绍下,她应聘成为一家酒店的服务员。工作6个月来,小高感触颇多,她觉得城市务工和乡村务农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公司管着”。虽然开始还不太适应被一个外在组织约束着,但企业组织并非只是消极地束缚个人自由,它同时也是个体成长的平台。正是在酒店一系列工作制度的引导下,小高逐渐学会了依靠自己的劳动在城市立足和生存,“我们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餐前、餐后做各种准备,礼貌礼仪、餐桌、卫生、食品什么的,刚开始去肯定都不熟悉,这些主管领班都会给我们讲,墙报上也有介绍,看着学,不会就问老员工,我们部长还会给我们开会,讲很多道理,他会谈到自己工作时的经历、感受,餐饮本身也没多复杂,大家上手都很快”。除此之外,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们要幸运得多,他们在入职前能够有机会去接受系统化的职业培训。这是一种市场化的资源传递过程,个体支付培训费用,学校进行技能传授,然后组织推荐工作或个体自谋生路;有时个体与组织之间也并不发生直接货币交换,而是以一定年限的无偿或低偿劳动代替学费,从“打下手”开始,个体以学徒的身份逐步掌握工作所必需的关键职业技能。
作为一项具体的工具性资源,职业技能是个体在组织内得以立足和发展的根基。新生代农民工在正式入职前后,各种组织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技能培训,培训的广度和深度根据每个组织的行业属性、经营规模和发展目标的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些由组织主导的资源传递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习得各种技能,并在职场初步立足。
(三)职业群体接纳:人际互惠的情感沟通
职业技能的习得往往只是融入职场环境的第一步,而职业群体的接纳对个体而言更为重要。就职场交往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职场环境要比老一代复杂得多,既要与同龄人相处,又要与比自己年长很多的同事、领导打交道。与长辈们的交往,既有可能面临“因为年龄比较小,大家都还是比较让着我,如果嘴巴甜一点的话,有什么情况人家都还是愿意教我的”的状况,也可能遭遇“他们仗着自己年龄大,指使我们干这干那的”的情形。
相对于与长辈们的交往来说,同龄人之间没有代沟,比较能够“玩到一块去”,同辈群体之间工作和生活上的交流与互助,对个体融入职场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28岁的海婷是江苏南京人,在省内的镇江、苏州、南京等地务工,12年来一直从事服装制造工作。刚参加工作不久,她就遇到一件尴尬事,“刚上班那会儿,我总是以为像在学校,做40分钟就中间休息一会儿,当时没人跟我讲这些,闹了个大笑话”,而与职场“老手”们的相处也给她平添了几分烦恼,“别看是操作机子,有些同事不但不愿意传授工作经验,而且还会排挤新人”。直到与同龄人之间建立起稳定的交往,情况才慢慢有所改善,海婷表示“后来时间长了就有朋友了,主要是些和我一样没什么心眼的小姑娘,工作中互相帮帮忙,下班后在宿舍相处得还不错,混熟了在厂里就好说了”。随着时间的推进、交往频率的增加,交往内容也由浅到深,同事之间也慢慢熟悉起来,“熟”本质上是一种被群体接纳后所产生的适应感,进而个体才能了解职场环境中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
尽管同事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情感互动水平不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长期工作过程中还是可以形成一些“共事之情”的,同在异乡漂泊的处境和同为打工者的命运,使得他们具备了情感交换的基础。中国人又素有追求人际秩序和谐的传统,组织内“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客观上也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因此职业群体根据熟人交往中的“人情法则”,可能会做出一些利他性行为,帮助个体熟悉职场环境,这本质上是一个带有人际互惠性质的情感交换过程。
三、自力更生:自我赋权中的媒介利用与职业自觉
西方赋权理论认为,赋权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所以它与人类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6]。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受到了不同形态媒介从外部施加影响,但他们并非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们也可以借助于新媒介使用、组织沟通以及城乡人际交往等传播实践,积极规划职业生涯、扮演职业角色以及确认自身职业价值,并发展出一定程度的职业自觉,这体现出他们在信息、技能和情感等层面自我赋权的努力。
(一)信息赋权:新媒介使用与职业生涯规划
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新媒介成长起来的一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介便于携带的“移动”特性契合了他们“流动”的生存现状。借助于新媒介使用,他们获取学习资料、招聘机会、工资行情、创业渠道等相关职业信息,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完善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新媒介的社交属性还可为他们提供职业生涯所需的社会关系网络。
前文提到的志伟,他在日常生活中有着较高的触网频率,会经常在网络上聊天交友、看视频、看新闻等,但在这些娱乐化应用之外,他也主动在网络上搜索过不少职业方面的信息,并借助供职于某家网店的契机,学习到不少网店运营经验。除此之外,基于QQ聊天之上的虚拟社交,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线上社会资本,他表示“我在网上聊QQ挺多的,遇到很多开网店的朋友,好多都赚到钱了,自己也学到很多,如哪里进货啊什么的”,虽然最终没有将其转化为线下社会资本,因为“他们不会给自己讲太深入的东西”,但是志伟对于新媒介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主动利用意识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介的接触与使用,远远不只是获取职业信息、搭建职业人脉这么简单,它不仅可以用来帮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甚至它本身就可以作为职业生涯平台。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互联网成为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上的“造梦厂”。在访谈中,不少人表示过曾有开网店的想法,这绝非只是志伟身上的个别现象,对无数个志伟们来说,新媒介已经超出了娱乐工具的内涵,在对信息充分挖掘、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他们的技术素养也得以升级,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信息赋权。
(二)技能赋权:组织沟通与职业角色扮演
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表现出更低的稳定性,这既可以说是职业韧性不够,也可看作是通过换工作来寻求更好职业角色扮演空间的一种努力。作为企业的劳动力,为完成自身及其家庭的再生产,个体要在企业组织内部谋取相应的物质或精神方面的资源,就得依赖于他的职业角色扮演水平。当个体表现出“称职”乃至超出了组织期待的水平,他在组织内谋取各种资源时将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而这需要在对组织角色规范领悟的基础上,对不同关系实行有区别的传播策略,因为“组织是各种关系的总和”[7],就内部来说,它不仅包括垂直方向的上司下属关系,也包括水平方向上的同事关系,个体在组织内部的沟通能力影响着他的职业角色扮演水平。
1988年出生的杨子是湖北黄冈人,高中二年级时学业还没完成便辍学来到温州务工,最开始在一家制鞋厂做模具,历经10年打工生涯的磨砺,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家鞋业公司的开发部主管。与同龄人相比,他在工作上相对安分,在他看来“打工都差不多,跳了不一定有原来的好,与其重新开始,还不如在公司里面好好混”,至于混法就是要在“干好工作的前提下,处理好各种关系”。心得颇多的他表示“没有利益冲突的话,关系都挺好处的,到一定阶段产生一些冲突时,就会有拉帮结派。一般就见人说人话,能配合就配合,不能配合就推”。针对组织内部各种关系的沟通,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小厂做事、大厂做人,既要跟上面处好,又不能得罪下面”,这样“工资自然会涨,关键是老板信任,但最重要的还是你有利用价值”。杨子既会“做事”又会“做人”,因此他的就业稳定性较强,但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既有组织里沟通能力得不到发挥,便会通过“跳槽”来寻找能充分展现自己的平台。
职业角色扮演可以理解为围绕组织角色的设置、定位和要求,获取定位于相应位置资源的组织沟通过程,沟通水平的高低左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组织内所能获得的资源种类和数量。而无论是职业待遇的增加还是职务级别的提升,都可以视为一种工具性层面带有实用性质的技能赋权。
(三)情感赋权:城乡人际交往与职业价值肯定
价值是评判客体对主体需要满足的尺度,职业对于个人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职业的价值既可体现于生产过程,又可蕴含于分配领域;既有显性的、表层的,又有内隐的、深层的[8]。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注重职业分配领域的、表层的价值,如工作待遇、薪酬福利,而且注重职业生产领域的深层价值,对于他们而言两者同样重要。另外,工作本身是否有趣、能否发挥个体的创造力、能否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也成为他们选择或转换职业的重要依据。
1990年出生的阿方是湖北荆州人,17岁起便在杭州某服装厂做服装包装,常年站在车间里包衣服,每天的工作简单而重复。时间一久阿方颇感无聊,“像坐牢一样”,流水线工作给他的身心带来巨大不适,2年后他辞职去了嘉兴某化妆品店从事销售工作。提到这2份工作的对比,阿方认为,“与做服装包装不一样的是卖化妆品每天都会有变化,每天来店里的人都不一样,要求也都是不同的,要主动和她们交流,了解她们的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荐适合她们的化妆品,有不少顾客成为了回头客,她们和我聊起,夸我的眼光还不错,看到自己的建议被别人认可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在同各种城乡顾客的人际交往中,阿方建立起了“做销售更有挑战性”这样的一种职业认知,虽然工作场所当中的交往有较大局限性,不过来自于外界的认可和肯定,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职业认同感,从而确认了化妆品销售工作在他心中的价值。从2009年至今阿方一直在该店工作,对公司也产生了某种职业上的承诺感和归属感。
因业缘而展开的各种城乡人际交往当中,新生代农民工会形成一系列关于职业生活的效能信息,这些积极的人际传播实践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程度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在对职业价值的审视和初步确认中,他们实现对自身的情感赋权。
四、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使得分工得以不断进步[9],这导致城市社会的务工体验与乡村社会的务农体验迥异,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过程中也有所差异。一个显著差异就是乡村社会的务农,媒介参与少,介入程度也很低;在城市社会,各种不同形态的媒介广泛参与其中,介入到职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于伦理、人情、利益或道义上的考虑,各种媒介从信息传播、资源传递、情感沟通等层面推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角色获得;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借助于新媒介使用、组织沟通、城乡人际交往等传播实践来激活自身权能,并在信息素养、资源汲取和情感认同等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赋权。无论是各种媒介助推的持续影响,还是自我对媒介的循环利用,不可忽视的是媒介在他们城市就业中扮演着的重要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支持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适应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为主的人际传播网络,以企业、政府、社区为主的组织传播渠道,连同大众传媒以及新媒介,构成了他们城市就业的媒介支持系统,对他们的职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按照系统论创始人冯·贝塔朗菲的说法,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10]。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媒介支持系统中,既包含着不同形态的各种媒介,作为支持方而存在;也包括了在就业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困难的个体,作为受持方而存在。在这个系统内部,不同形态的各种媒介尽管在功能上有同有异,但作为系统的构成部分,它们还是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基本的信息支持、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这些功能的正常发挥也是系统自身得以存在的前提。而面对媒介支持系统,新生代农民工也并非坐等受援的消极客体,他们作为有着主体能动性的行动者,能够借助这些不同形态的媒介,开展一系列人际的、组织的、大众的以及新媒介传播实践,发展出信息赋权、技能赋权和情感赋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中媒介支持系统的运转是媒介与行动者互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他者与自我、组织与个体、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碰撞,既有媒介支持系统对行动者的支持,又有行动者自身对于媒介支持系统的利用。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系统之所以成为系统,不仅因为系统具有许多要素,还因为各要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关系,各要素只能机械地集合为一“堆”,不能形成整体性的行为和功能[11]。就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媒介支持系统来说,它的内部也存在着两类关系,一类是各支持方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支持方与受持方之间的关系。
就各支持方之间的关系来说,虽然不同形态的各种媒介,各有分工和专长,如对城市就业而言,人际传播网络主要提供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如借钱借物、出力帮工和情感陪伴;组织传播渠道主要提供工具支持,如技能培训、资源分配和物质奖励;大众传媒与新媒介主要提供信息支持,如招聘机会、工资行情和行业知识,但各种媒介在系统内的功能发挥上并不是彼此分离而是可以互补的。按照不同形态媒介在个体职业生活中嵌入度的深浅,可将媒介支持系统划分为三层,人际传播网络因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嵌入,居于核心层;组织传播渠道是各种职业活动展开的基本空间,居于中间层;大众传媒及新媒介营造的是一种信息环境,居于最外层。这些不同层级之间是具有“可替代性”的,比如说大众传媒及新媒介主要提供信息支持,人际传播网络提供情感支持,但当人际传播网络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缺位状态时,这时大众传媒及新媒介上的娱乐、社交等应用,也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对个体情感产生慰藉,尽管这种经过中介了的情感支持具有一定脆弱性。
就支持方与受持方之间的关系来说,媒介与行动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1)就人际传播网络来说,行动者对它既有维系又有拓展。虽然既有的人际传播网络在城市就业初期,对于行动者的生存安顿提供了大量帮助,但为了谋取职业发展,行动者必须在此基础上拓展交际圈。(2)就组织传播渠道来说,行动者对它既有依附又有利用。进城以后,一方面行动者必须依附于某一特定组织才能在城市立足,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与组织进行资源交换;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在组织的既有框架内谋取发展,形成一个摄取资源常规化和稳定化的角色扮演模式,且并不排除会采取突破既有组织框架的行动,如职业流动。(3)就大众传媒及新媒介来说,行动者对其既有接受又有汲取。如大众传媒及新媒介通过对城市就业情况的报道构成了社会的“拟态环境”,它们支撑着行动者的信息感知和信息决策;而智能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对行动者来说绝非仅仅只是沟通工具,同时也是社会资源,他们会主动在媒介信息的渗透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成分。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中媒介支持系统的运转远非行为主义模式下的“支持—受持”这么简单,唯有通过媒介的“他助”,行动者才能达到更好的自助,进而才能促进自身的职业化。就乡城转移而言,它本身也是一个职业化的过程,职业活动与身份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维度,从这里出发,可以看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分化和专业化[12]。职业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前提,而个人现代性的获得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理想状态,因此职业化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必经之路。而媒介支持系统的完善与否、层次丰富性、功能发挥以及个体利用程度,会形成不同层次的职业化水平,与此相应的职业薪酬、职务级别和职业地位都表现出明显的分化,进而对他们的城市适应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4-05-12)[2015-10-3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2]许传新.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10(3):1-12.
[3]张波.流动与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及其传播实践[J].北京青年研究,2015(2):48-55.
[4]郑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11(3):71-77.
[5]许传新.农民工的进城方式与职业流动——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10(3):1-12.
[6]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J].开放时代,2011(1):124-145.
[7]埃里克·M·艾森伯格,小H·L·古多尔.组织传播:平衡创造性和约束[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60.
[8]顾雪英.职业价值结构初探[J].心理学探新,2001(1):58-63.
[9]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19.
[10]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51.
[11]吴元梁.社会系统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6.
[12]张康之,张乾友.论社会职业化中的职责[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5-11.
(责任编辑: 林小芳)
Media support system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employment—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s an example
ZHANG Bo
(College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China)
Abstract:From rural to urba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ndergo a shift of the non-agricultural vocational attainment, with the interven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mass media, new media, and 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However, they also develop a series of communication practice such as new media us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etc. Through empowering themselv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motion in career, they show a certain degree of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between media promotion′s effects and self-empowerment′s efforts in the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urban employment,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media support system to promote their continuous professionalization, thereby affec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ng into urban society.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adaptation; media support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22(2016)02-0019-06
[作者简介]张波(198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与社会变迁、人际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XW024)。
[收稿日期]201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