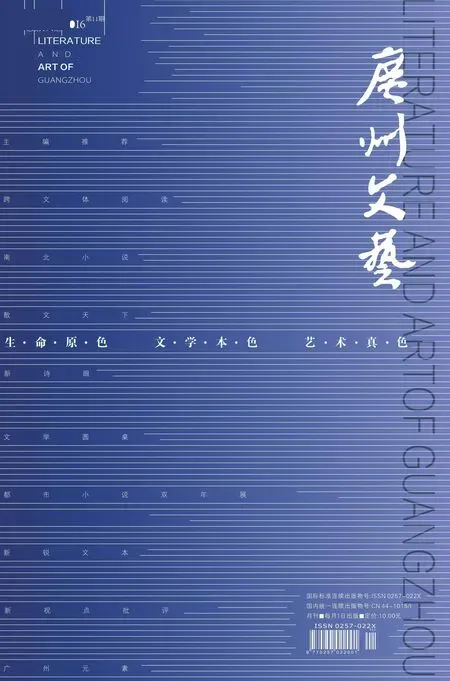马头男之死
陈乐
马头男之死
陈乐
从涂满斑驳蓝漆的白色房车上走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男人满脸阴郁,就像遭受狂风暴雨的渔夫。林白抽了一根烟递给男人。男人熟稔地吞云吐雾起来。林白问男人从哪里来?男人答非所问,说:“我是警察。”男人说完,第二个人从车上下来,是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女人瞥了男人一眼,把男人嘴里的烟拔出来,像个烟鬼,猛吸了一口。
一根烟让林白交到了两个朋友。男人和女人邀请林白上了房车。女人充当司机,巨大的房车在一瞬间像被猛踢的皮球飞奔起来。林白好奇地问男人和女人是什么关系?大约三十五岁的男人闷声闷气地说:“我们是离婚的夫妻。”男人的话让林白感到很可笑。但男人并没说谎,他和女司机在五个月之前的确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林白不便再往下问,把目光投向身体纹丝不动的女司机。
房车在一个废弃足球场上停止。林白下车自顾自踢起了足球。林白踢累了,男人掏出手机给林白看他站在被几百个观众围成椭圆的颁奖台捧着奖杯喜笑颜开言谢的视频。男人容光满面,话语铿锵有力,言辞犀利。观众们开始噼里啪啦拍掌时,林白问男人他做了什么崇高的事,得了这个奖杯?男人默不作声瞧了一眼躺在草坪上唱歌的前妻,右手中指指着视频中定格的观众,字句斟酌地解释:“这几百个人被困在一座岛上,我开着一条船,帮这群人脱了险。”
男人的话让林白心头一震。他的未婚妻五个月前曾简讯他,胆战心惊叙述了她被困一座蝎子形岛最终被警察开船解救的恐怖经历。未婚妻还发了照片,不过照片是警察的背影。林白找到那
张照片给男人看。男人接过照片,像得了糖果的馋孩子,舔了舔嘴唇,目不转睛地望着,表情很严肃。几百个人凄厉哭嚎、悲声抿气说感恩戴德话语的画面在眼前浮现。
“我的未婚妻也在这几百个幸存儿里面,”林白温吞地说,“你就是那个警察吧?”
男人关掉视频,向林白僵硬地点了点头。林白没想到这样一片荒凉的沙漠会有一个足球场,更没想到会遇到未婚妻的守护神。
“那几百个人脱险后,一直给我送花,大概送了一个星期。我拿着他们送我的花,和他们走上搭救他们的大船像孩子一样跳舞。”男人回味着,眼神痴迷,仿佛那几百个人回来了,就站在他面前,手捧着鲜花。
“五个月前,我未婚妻把这件事讲得滚瓜烂熟。在这件事上,她似乎永远感觉不到疲倦。”林白说,用左手食指捣了捣浮想联翩的男人,“她说你开船的背影就像《终结者》中抱着长枪扫射恶人的施瓦辛格。”
男人嬉皮笑脸地向站起来去擦车的前妻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然后开始像专业足球运动员一样踢林白手里的足球。
在冗长低沉旋律悠扬的日文歌中,三人出发了。日文歌结束的时候,珍妮径直把车开进了一间废弃的教堂。教堂里有很多低着头喃喃自语祈祷的女人。珍妮下了车,便从车里取出插电的音响和话筒,插上电;接着珍妮打断了女人们的祈祷,站在教堂前端高高的台阶上,像个万人膜拜的歌星,有模有样唱起刚才在房车里播放的日文歌 《海鸥》。珍妮的日文歌打动了女人们。女人们从教堂角落找来荧光棒像铁杆粉丝对着唱歌的珍妮呐喊助威。
珍妮演唱完日文歌,从教堂外走进来一个戴着马头面具的高个子男人。马头男走上 “舞台”,接过珍妮手里的麦克风,用那种高亢嘹亮的音色唱披头士的 《Hey Jude》。
马头男凭借 《Hey Jude》博得女人们的雷鸣掌声,在某种程度上也征服了外表冷艳的珍妮。在珍妮的盛情邀请下,马头男加入了房车阵营。马头男头上的马头对珍妮诱惑力很大,珍妮很想摘下它,对马头男一探究竟。但是,珍妮暂时还没足够的勇气或者理由让马头男摘下面具。珍妮开始幻想马头男是一个像披头士一样帅、一样才华横溢、一样能歌善舞的美男子。幻想让珍妮不自然地窃笑起来,就像她在六合彩投注站买了一张价值一百万的彩票。马头男的出现让珍妮忽视了旅程中陪伴她很久的前夫——昆丁,以及在沙漠中上车的林白。
昆丁并没有吃马头男的醋,相反,潜意识中,他内心也升腾起对他一探究竟的冲动。
就在所有人对马头男好奇专注的时候,马头男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把马头对着吸烟的珍妮,用男中音柔润的腔调亲切地说:“能陪我一起跑步吗?”珍妮几乎立刻满足了马头男的请求。于是,昆丁接替了珍妮。车开始奔驰起来,像吃饱饭的麋鹿,但速度不快。
珍妮戴上蛤蟆镜,涂了点口红,在车内狭小的换衣间换上鲜少穿的旧运动衣。于是,在硕大的房车面前出现了这样一幕——两个分别戴着马头面具和蛤蟆镜的
年轻人挥手扬臂、仪态大方、步伐矫健地奔跑在柏油马路上。珍妮和马头男就像职业运动员那样身姿绰约地奔跑。坐在副驾的林白不断给奔跑者拍照,不断把画面上传到微博上,然后不断有粉丝夸赞马头男和珍妮的潮和酷。
珍妮自从和昆丁离婚,虽然表面上一副喜笑颜开无拘无束的模样,但其实从她签下离婚协议书那一刻起就没有真正开心过,她的内心一直处于紧张的矛盾中。珍妮觉得昆丁跟她离婚后像婚前一样和她平和自在地相处全部是造假,就像她在虚张声势一样。但是,和马头男步伐轻快地奔跑,却让她找到了某种平衡,博得了一点自信以及消失已久的心安,她感觉到呼吸变得顺畅,心跳变得温和,笑脸变得轻盈。她跑的每一步,都让她感觉离那个惶恐不安的自己远一脚。但是,这一切,昆丁都看不到。昆丁只是配合地开着车,吸着烟。
珍妮和马头男返回房车的时候,马头男开始讲述自己。马头男说,他是守塔人,他长年守着一座塔,那座塔在宽阔无边的海边。这份工作只有微薄的工资,但他从没有嫌弃过。他总是戴着马头面具,手握自制的佩剑,穿着铠甲,像个刚正不阿的战士,静静地站在灯塔中央,平静地眺望大海。同时,他从未感到过疲倦,相反,守护灯塔让他感到了身先士卒的成就感。眺望大海,让他感觉到内心的平静、心灵的安宁。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头男认识房车里这对离婚的夫妇。马头男开了口:“昆丁、珍妮,我曾在洛杉矶天鹅镇那座野生动物富饶的山上见过你们。”马头男打了个响指,像铺垫探案小说,“那天,你们穿得像新婚夫妇,昆丁西装革履,珍妮白婚纱裙摆衔地。你们平静地向山上走,碧波无澜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哀伤。你们轮换抱着一动不动的孩子。你们的孩子死了。2003年11月9日那天,你们的孩子被载满青苹果的长卡车猛烈撞击后像保龄球飞出七米远,这成了洛杉矶的头条新闻。”马头男说完,清了清嗓子。
马头男的话让珍妮和昆丁不禁陷入失去骨肉的悲悯中。但是,珍妮希望马头男继续说下去,因为自从她的儿子在美国死后,和昆丁勉强度日直至离婚的七年,她都不曾正式在任何场合提起儿子;她神经质地希望马头男把她带回她和丈夫埋葬儿子的那一晚,她想回到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再见儿子一面。珍妮握着方向盘,头也不回地对马头男说: “继续说吧。”昆丁则面无血色,就像濒临死亡的鳗鱼。
“你们把儿子平静地放在石头上,像新婚的夫妇平静地跳交际舞。你们默不作声跳了很久很久,直到鸡鸣,接着你们喝了交杯酒。埋葬儿子的时候,你们才哭。两个大人像小孩子一样稀里哗啦地哭,就像世界末日濒临地球。我看见你们亲吻头被撞走形的儿子稚嫩的脸颊,困惑不安地嘀嘀喃喃。你们哭着挖了一个很大但不深的坑,把儿子放了进去,极不情愿地埋了他。然后,就像世界末日提前到来,你们扭曲着脸,鬼哭狼嚎起来。那时候,你们失态得就像过街老鼠。”马头男说。
昆丁没想到马头男会出现在他儿子的葬礼上。那座山是他精挑细选的,平常那座山除了飞禽走兽鲜少有人光临。他和珍妮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他想给儿子一个特殊的葬礼。
昆丁和珍妮离婚前每一年都会驱车去儿子的墓沉心静气地跳上一段交际舞,心照不宣地喝上一杯交杯酒。就像每一年的那一天不是儿子的祭日,而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一家三口的盛典日。
“你怎么会在那里?”昆丁下意识问马头男。
“我那天去取景。除了看守灯塔,我最大的爱好是摄影。”马头男说。
马头男那天并不是去取景,这一点只有他心里明白。2003年11月9日那天的车祸也并非偶然。那天,马头男讲究地穿上燕尾服、尖头皮鞋,对着擦拭一新的镜子拘谨地练习微笑,去理发店烫了飘逸的卷发。当一切准备妥当后,他像参加假面舞会一样平静地套上马头面具。站在擦拭一新的圆镜前,他像贫苦孩子过年觅得鱼肉一般兴奋利索地旋转身体。杀死保尼 (珍妮的爱子)的念头并不是马头男蓄谋已久的想法,那更像是心血来潮。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给珍妮打匿名电话 (他喜欢上珍妮是在珍妮从中国去韩国做交换生那一年,之后便失之交臂),珍妮通常为了打发无聊,会逢场作戏和电话那头的匿名男人轻车熟路地聊几句,但那天,她和昆丁吵了架,发了火,摔了桌子,所以她直接挂了匿名男人的电话,并说了句——Fuck。电话这头的马头男崩溃地吃起苹果,马头男的嘴像挖掘机一样不断吞噬苹果,吃完最后一苹果,他做了那个可怕的决定。
既然吃了苹果,马头男就和苹果玩到底。马头男在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外偷窃了一辆司机正在小便的卡车,然后亲手装满红彤彤的苹果。当时,保尼正在路边堆积木。马头男摇晃着牢牢套在脑袋上的马头,放起咆哮的英文重金属音乐,平静地撞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的保尼。
事情就这么简单。
昆丁当然不知道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就是这个头上戴着古怪马头的年轻男人,更不知道妻子因为取乐曾和这个年轻男人暧昧地插科打诨。和珍妮以及林白的想法一样,马头男只是一个标榜个性彰显自我的玩酷青年。杀死保尼的凶手,到目前为止还是杳无音信;保尼玩积木的那条马路没有探头也没有目击者,更没有凶手的指纹。面对残酷的现实,昆丁只能得过且过。
马头男随身背着的那个小巧玲珑的旧式皮包里装着昆丁和珍妮每一年去祭祀保尼时跳交际舞和喝交杯酒的照片。这些照片统统是黑白的。马头男私下病态地亲吻这些照片,抚摸它们,然后狠狠撕碎它们,然后再去数码店重新还原它们。那些照片就像马头男必须吸食的可卡因。他去照相馆放大了几张,和真人一样的高度。他和放大后的照片轮换跳交际舞,轮换喝交杯酒。这两件事,对于马头男来说,就像精神病人的镇静剂。当马头男和虚无的照片跳完舞喝完酒,杀死小保尼的自责和愧疚,会像退潮的海水,消退一点。马头男当然想过自杀,用那把在美国买的小巧玲珑的左轮手枪插喉结束自己。但是,由于害怕枪杀的痛楚,他每一次都轻而易举地放弃,就像杀了人只是他在小学做错的一道数学题。每当这时,他总是紧张不安地戴上他的马头面具,然后像个嬉皮士一样唱奇怪的歌,跳奇怪的舞。
房车停下来,在一家咖啡店。苦涩的黑咖啡提醒珍妮必须道出事实。在这趟看似无休止的旅程刚开始,她便怀孕了,那是
她和昆丁离婚后仅有的一次性爱。那一次她没有做保护措施。小保尼死后,深陷悲痛的夫妻俩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是,两人都难以启齿,就像那是一件见不得光的丑事。咖啡店生意萧条,只有房车的四个人喝咖啡。珍妮喝完咖啡,走到平常表演者登台献唱的小舞台,像个演说家清了清嗓子,然后宣布了怀孕的消息。珍妮话音刚落,昆丁便像喝醉酒的酒鬼把满嘴的咖啡喷了出来,他没想到珍妮会怀孕,在他的感官世界里,保尼死后,珍妮永远也不会选择怀孕。珍妮怀孕的消息像晴天霹雳,马头男打翻了餐桌上的咖啡,像个迷路的羔羊坐立不安起来,他感觉喉头发黏,喘不过气,就像有人掐住了他的脖子。马头男曾不止一次幻想过和珍妮双宿双飞同床共枕的美妙画面,自从他杀死了保尼。珍妮的怀孕摔碎了马头男的幻想,不留余地地。这一刻,马头男甚至想杀死珍妮。但同时杀死珍妮这个想法却让他心惊胆战,心痛不已。
但是珍妮并没有公布会不会生这个悬念,就连珍妮自己也不清楚她到底会不会生下这个孩子。保尼死后的一年,她曾整日整夜地睡不着觉,不间断地梦游,大把大把吃安眠药以及无休止地自杀。每一次自杀,她都深深割下手腕,血像湍急的河水漫过掌心。但是,自杀带来的似乎不是生理上的疼痛,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当血水流失、呼吸举步维艰、气力慢慢消散时,她感应到的不是死亡带来的恐惧,而是一种畅快淋漓的放松;就好像跑了一场马拉松的蹩脚运动员终于跨越停止线躺在草地上呼呼喘气一样。面对怀孕,珍妮是不知所措的,就像昆丁和她都不愿提及的心结一样。刚得知这消息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她戴上炫酷的蛤蟆镜,浓妆艳抹一番,像个参加格莱美颁奖音乐节的明星,默不作声吃了几十颗安眠药。但她没有死成,搭救她的不是别人,正是此刻坐在旋转椅上心急火燎的马头男。那是马头男第一次鼓起勇气敲响珍妮的房门。叩门没得到任何回应,于是,马头男便像窃贼一样大胆闯了进去。结果,映入眼帘的却是昏迷不醒的珍妮。于是,他拨打了120。如果马头男知道珍妮那时候已经怀孕,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模样,如果了解,他也许会选择袖手旁观,直到珍妮呼吸停止。珍妮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天搭救她的是何方神圣。医生在医院宣布珍妮死而复生的消息后,马头男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他心里开了一朵花。
珍妮开始渴望拥有一副像马头男一样的面具。怀有身孕折磨着她。潜意识中她认为怀孕是对逝去的保尼的不忠。保尼几乎每晚都会光顾她的梦境。她总是拼命追赶微笑着跟她捉迷藏的保尼。保尼总是旗开得胜,她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保尼在她眼皮底下像鬼影一样销声匿迹后,她就会坐在石头上哭。她像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声泪俱下地哭。她总是在悲催的啜泣中苏醒,怀孕几乎折磨得她喘不过气,她既想诞下新生命探索新生活,但又害怕愧对死去的小保尼。珍妮渴望戴上一副面具,把自己的惊恐万状和失魂落魄藏在面具背后,把令人焦头烂额的抉择抛之脑后,躲在面具铸造的虚拟世界里尽情深呼吸,尽情大哭大笑,尽情张牙舞爪,尽情左摇右摆,尽情释放自己,尽情扼杀一切负面精神枷锁,把所有的悲伤和痛苦抛向大海。珍妮很羡
慕马头男有这样一副马头面具。
马头男开始在夜晚离开房车,白天回归。离开房车的夜晚,马头男做的不是别的事,而是给珍妮打匿名电话。马头男看着昆丁夫妇埋葬小保尼的那晚之后,他就停止给珍妮打匿名电话了。停止匿名电话这事,对于马头男来说,就像鳗鱼停止在水里游泳。对于马头男来说,这是极其残忍的一件事,也是从间断匿名电话那一晚,他开始了自残。马头男从水果店买来锋利无比的水果刀,不温不火地在胳膊上缓缓割下一条条形态分明的血线。马头男感觉不到丝毫的痛楚,他更多感受到的是释放的快慰。他每割下一刀,死去的保尼就会向他冉冉微笑一下。当血水渗透出来,马头男内心的负疚就会松懈一点。
重新打匿名电话,让马头男十分紧张。马头男颤颤巍巍握起公共电话的话柄,像个杀人凶手一样浑身发抖,手心不间断冒着热汗,沾湿话柄。珍妮接通电话后,马头男像个初入洞房的处女扭扭捏捏说着话。珍妮一听到马头男的声音,便心知肚明了。这是以前和她打情骂俏插科打诨的匿名电话。匿名人和马头男的音色惊人地相似,但却没引起珍妮丝毫的猜测和联想,她认为那只不过是两个音色相似的男人罢了。寒暄几句后,珍妮开始诉说想要一件面具的冲动。这让马头男十分震惊,他四肢乱颤,头皮发麻,像侦探一样反问为何。珍妮回答:因为她需要逃避一些东西。珍妮的话让马头男忆起第一次戴马头面具的情形。那是他第一次猥亵女生,那是他的同班同学,被检举后他站上了主席台,当着成千上万同学的面羞耻地讲述猥亵经过,然后狠狠扇自己耳光;当天晚上放学,他便捂着红肿的脸走进了玩具店,默不作声买了一副马头面具。戴上面具后,他的罪恶感瞬间支离破碎了,他早晨在主席台遭受的耻辱像乌云一样神奇地消散了。从那以后,马头男,便离不开马头面具了,面具就像替他赴汤蹈火的亲兄弟。
马头男答应给珍妮制作一副面具,但那需要时间,紧接着,马头男给珍妮唱起陈奕迅的 《富士山下》。马头男唱得娓娓动听。电话那头的珍妮,感动涕零,就像那是感化她的佛语。
事情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林白在微博上发的马头男和珍妮昂首阔步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未婚妻朔月的注意。朔月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从小习惯待在卡车里玩耍,日久生情,朔月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而2003年11月9日那天,朔月送完货,途经荒郊野岭,下来小便的她目睹一个戴着马头面具的男人把她心爱的卡车开走。当然,戴面具的人很多,朔月只是猜测跑步的马头男可能是偷车贼。朔月把这一猜测告诉了林白。
由于昆丁是未婚妻的救命恩人,所以,林白有义务把所了解的情况告知昆丁。林白把朔月的猜想以及遭窃的经历原原本本复述给了昆丁,遭窃的时间是他儿子遭遇车祸的同一天。单凭这一点,昆丁是无法判定房车里白天和他一起谈笑风生的马头男便是杀死他爱子的凶手的。这只能算一个巧合,一个可怕的推测。
没过不久,朔月拿出一个被她遗忘的证据。那是一张马头男上卡车的侧身照片,照片里的人和现在房车里的马头男留着一样的披肩长发,身高相仿。朔月还回忆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在马头男上卡车的
那一瞬,她在十米远的荒草地上隐约听见他吞吞吐吐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开始红苹果之旅吧。没错,撞死保尼的卡车由于车速过快颠下来一个红彤彤的苹果,那是昆丁含着悲痛整理被撞得走形的儿子遗体时在路边的松树林发现的。那个红苹果,昆丁放在特地去环保公司定制的真空瓶里,苹果到现在还色泽鲜艳,夺人眼球。每一年去给儿子祭祀时,昆丁都会带着那个真空瓶,怀着痛苦不堪的心情,给瓶子里的红苹果拍照留念。出于警察的职业敏感和朔月提供的证据及证词,昆丁脑海漂浮起一个大胆的猜想——杀死儿子的凶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猜测让昆丁十分兴奋,他就像浑身打满了鸡血,他消沉七年的心在此刻就像脱胎换骨的病人,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渺茫的希望就像寒夜里稀薄的烛光,温暖着他。
猜想愈多,愈深刻,昆丁心中的怒火就愈炽热。他恨不得一枪崩了和他谈论时尚评论世界大战的马头男。逝去儿子的悲痛几乎摧毁了昆丁,但他从未表现出来过,他从未像珍妮一样哭哭啼啼,指桑骂槐,哭天怨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诅咒事不相关的人。马头男此时成了这个警察脑海里的怪胎,而不是刚上房车时把握时尚脉搏的文艺青年,他甚至觉得马头男更像一个恐怖电影里奇形怪状的邪魔。
但猜想终归猜想,证据不足才是昆丁棘手的问题。如果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他是没法制裁马头男的,更别说鱼死网破地一枪崩了他。
马头男对昆丁掌握的对他不利的证据和证词一概不知。他现在只是一门心思地做一件事,替珍妮制造一副面具。即便以前杀了人,他也不以为然,他狂热地希望尽可能快地造出一副面具,就像珍妮迫切需要的那样。为此,马头男像一个即将高考的高三学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坐在他狭小干净的工作室前,聚精会神地制造面具。他的马头面具都是他亲手制作的,每一次面具损毁他都会亲手毁了它,然后迫不及待造一副新的出来。他的世界已经离不开马头面具,如果失去它,他可能活不过十天。他需要它的袒护、包容、亲昵和理解,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珍妮,马头面具是他最好的朋友。
马头男为珍妮绘制了一副五彩缤纷的蝴蝶面具,是那种图案复杂、色彩繁复、让人不禁艳羡的蝴蝶,他要画一只世界上最独特最柔美的蝴蝶,让人感到扑朔迷离但又啧啧称奇的蝴蝶。
在马头男煞费苦心的彻夜鏖战下,珍妮的蝴蝶面具很快 “落成”。马头男褪去自己戴了很久的马头面具,刮了胡子,洗了脸,擦了润肤水,站在镜子前,就像刚满十八不谙世事的小伙子。马头男在镜子前像扎马步的武士静止不动站了很久,他窥视着镜子里英俊的脸,既熟悉又陌生,他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看见面具下的自己,他都快认不出自己了,就像那是其他什么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他的脑袋不停渗出冷汗,他摘下马头面具的次数,屈指可数,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马头男迫不及待想尝试一下蝴蝶面具的滋味。马头男戴蝴蝶面具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戴上面具对他来说就像替入洞房的新娘揭开红罩头一样,不知从何下手。马头男呼吸紧张,脸红心跳,喉头发黏,四肢乱颤,就像那轻飘飘的面具真的是新娘头上的红布,他甚至感觉到
一点害羞和窃喜。最终,他颤颤巍巍戴上了那件蝴蝶面具,戴上面具后,他就像真正结婚的新郎,情不自禁地喜笑颜开,脸红心跳,此时,蝴蝶面具成了他朝思暮想的珍妮,他控制不住地窃笑起来,那笑声盖过了还在旋转的磨光机发出的嗤嗤声。马头男接着从储物间取出他放大后的珍妮和昆丁跳交际舞的照片,像个孩子一样拥抱着它,欢呼雀跃地跳起来,此时工作室里每一件物什都像他结婚的贵宾一样,目不斜视笑容温和地注视着翩翩起舞的他,他感觉快乐极了,放松极了,世界美好极了,这一晚,就像他的大喜之日。
在匿名电话里,马头男把完成面具的消息告知了珍妮。珍妮欣喜若狂,她真切地希望那样一副面具可以掠去烙印在她心灵深处纠缠不清的伤痛和无助。为了回馈匿名男人,珍妮唱起了歌。那是莫文蔚的《他不爱我》,珍妮高亢明亮的嗓音就像真正的歌手。这是珍妮第一次为匿名人唱歌。珍妮唱得情深意切,就像真正失恋的女人那样,悲切、伤感。而电话那头的马头男不知不觉间已泪眼婆娑。他不由自主回忆起和珍妮初识的场景,珍妮那一次是在圣诞晚会上唱歌,唱的是陈奕迅的 《十年》,珍妮栩栩如生的演绎博得了掌声雷动;那一刻,马头男把随身携带的马头面具摔得粉碎,珍妮的 《十年》击中了马头男冷若冰霜的心坎,把埋藏在他面具下的卑微和羞耻一扫精光,就此,珍妮成为了他的心上人。珍妮当然不知道电话那头正是对她痴心不改的马头男,房车上的马头男。她唱歌只是单纯地感谢他为她制作了面具,即便那有点心血来潮。珍妮唱完 《他不爱我》后,马头男哭成了泪人,但他强忍哽咽,假装若无其事地赞扬珍妮,他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腔调,断断续续地说:“你就像真的莫文蔚。”珍妮自己也哭成了泪人,唱这首歌的时候,昆丁、小保尼以及她一家三口幸福温馨的场景不断在她眼前上演,而现在,小保尼死了 (死得很惨),她和昆丁离了婚,还该死地怀上了孩子。一切都很糟糕,就像乌云蔽日,不见天光,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简短的沉默,珍妮邀约了匿名人。
马头男穿上了那件自己亲手缝制的红西服,去理发店烫了飘逸蓬松的卷发。他没有戴马头面具,以便珍妮认不出他就是房车里的马头男。珍妮也病态地穿上了结婚才会穿的白婚纱,涂了鲜艳浓烈的口红。这两个人就像互相牵挂对方情意缠绵的恋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那样严肃认真。
他们约定的地方,是神圣的教堂。
而两个人对彼此盛装上阵是浑然不知的。两人都以为对方会穿平常穿惯的衣服亮相。
马头男没有戴马头面具,却戴上了蝴蝶面具。他就像一个参加假面舞会的人。当珍妮穿着洁白的婚纱亮相时,马头男像喝醉酒一样不由自主向后趔趄了几步。马头男只提了一个要求,让珍妮陪他跳一曲交际舞。珍妮不假思索地满足了他。于是,这一对男女就像结婚的夫妇手牵手,随着舒伯特优美舒缓的 《圆舞曲》步伐轻快地跳起交际舞。这是马头男梦寐以求的场景,由于过度兴奋,牵着珍妮的两只手不由自主哆嗦起来。和珍妮跳舞,就像站在几万人的华丽舞台上跳舞,每一步都让马头男神清气爽。跳完交际舞,他们心照不宣地喝起交杯酒,最后还象征性地吻了对方。
马头男摘了蝴蝶面具,珍妮便瞠目结舌了。原来匿名人是她的同班同学——英仔。他每天早晨都会在她课桌上放一杯优乐美奶茶,经常对她嘘寒问暖。但她拒绝了他的表白。
珍妮没有过多纠结马头男是旧相识,然后两人去了酒吧。在珍妮喝得面红耳赤时,马头男把蝴蝶面具递给了她。珍妮像马头男生命中第一次戴马头面具那样紧张不安。那面具此时不再像她幻想的能除去她心头阴霾的圣物,更像是迷惑她误入歧途、引导她步入万丈深渊、沾着邪气的怪物,就像 《指环王》中闪闪发光的金指环。就像,戴上蝴蝶面具,珍妮会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珍妮吓出了冷汗,口干舌燥,头晕目眩,甚至有一点毛骨悚然。她不敢拿起酒桌上的面具,制作精良、色彩绚烂、图案柔美的面具,此时就像一条吃人的蛇。她甚至不敢直视它。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
在珍妮烂醉如泥的情况下,她借着酒胆哆哆嗦嗦戴上了蝴蝶面具。戴上面具后,珍妮设想的恐怖幻觉并没有出现,没有出现吃人的蛇,没有出现万丈深渊,没有出现邪恶的召唤;而眼前出现的是一只翩翩起舞美轮美奂的蝴蝶,她感受到的是和马头男第一次戴上面具一样的气定神闲,困扰她的焦虑、悲伤、内疚等所有的负面情绪,瞬间支离破碎。此刻,她就像置身世外桃源的公主,天真烂漫信步游走在万花争奇斗艳的花园中。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放松,她在面具背后,微微笑了。
而与此同时,昆丁掌握了更多马头男杀死他爱子的证据。洛杉矶一个废弃的探头经过专业人士修理起死回生,提供了一段五秒种的视频。视频中,褪去马头面具的马头男正惊恐不安地吃着苹果,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不停地用白纱布擦拭它们,在他的身后,停着一辆左前轮沾满鲜血的扁嘴形大卡车。而那辆卡车如果停在那里,必须经过小保尼玩耍的那条马路,也就是说,他必须撞死小保尼,才会左前轮满是血。而这段视频的时间正是2003年11月9日。
昆丁在准备亲手结果杀害儿子的凶手前,和珍妮再次去了洛杉矶儿子的墓地。和以往一样,献完花,他和珍妮娴熟地跳起了交际舞。交际舞就像可卡因一样,让昆丁觉得神魂颠倒,飘然欲仙。喝完交杯酒后,昆丁站在墓前对儿子说:“小保尼,我已经找到杀害你的凶手,爸爸马上替你报仇雪恨,你可以安息了。”说完,昆丁像伊斯兰教信徒那样祷告——用手在胸前比划,然后说了句 “阿门”。和以往一样,马头男还是跟踪了这夫妇俩,并用斯得克士相机偷拍了他们。马头男虽然知道昆丁已经心知肚明谁是杀人凶手,但他却并不害怕,反而感到一丝从未有过的平静。
马头男死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他邀请珍妮给他跳了一曲 《神话》里金喜善跳的那支舞,便当着昆丁的面,饮弹自尽了。
责任编辑 梁智强
陈乐
1992年生,明朝古都花鼓之乡凤阳县人。自幼热爱文学,高中开始写作,曾在 《作品》《上海文学》《家园文学》发表过小说和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