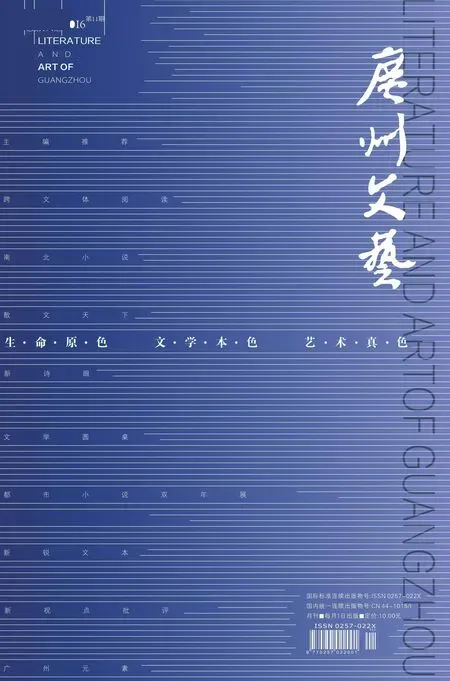一只蜗牛爬过花城广场
鲁敏
一只蜗牛爬过花城广场
鲁敏
看,这里一只大蜗牛!一位女士突然发出惊叫。
飘忽在手机或臀部或楼宇间的目光,跳突了一下,纷纷聚拢向其手指所指方向。广州闹市中心、花城广场的某处台阶上,一大圈休闲鞋、高跟鞋、露趾鞋如万箭所向,果然见到了一只硕大的蜗牛。众人有的弯腰下背,有的蹲如农夫,有的拿起手机来拍,有的兴奋又惧怕,有的迷惑到近于谴责,但见——肥厚的肉吸盘,银质闪亮的涎汁,黑青色的外壳上布有细密花纹,旋转收起的尾部甚至还粘连着一片鲜嫩的绿叶。整一只蜗牛足有三分之一巴掌大,仿佛天外来客,却岿然安详,有如入定,有如思想,有如幻化,仿佛它正置身于茵蕴的密林深处或晨露挂落的野径尽头。
花城广场大约是当下中国很具有 “大都会色彩”的去处。四周有各样声名震震、独踞尊贵行业的高大建筑群。五十度的深浅灰色。流光四溢冰冷如火的金属色。透亮但不透明的玻璃色。细长条或方格子,流线型与圆蛋型。各种肤色的路人。跑步的卷发妇人,臂上镌字的滑板少年。对着自拍杆咧嘴的背包客。黑西装挂着出入牌的瘦高女子。橙色工程装与绿色快递哥。人们像彩色的河流一样在这广场上不停地冲刷。他们的名牌包里有着精确到分秒的日程表,手上一刻不歇地滑动收发着微信表情包,带着生机、欲望、劳碌与野心。这么高级的一处所在,竟会有这么一只蜗牛在这里慢吞吞地爬过呢。
众人叹了几声,碎言散语讨论几句,陆续起身散去。各自继续各自的行程与计划,鞋跟复又敲打路面,暂停键复又翻作加快键。只听凭那只老僧般的蜗牛,留在广场上的某处台阶上。没有人管它,它自何处而来,又欲往何处而去——毕竟,人们连他们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我也走了,轻捷地跳跃地。作为匆匆
过客,已有诸种的周密势利之计,要走亲会友,要吃饭喝酒,要座谈要开会要讲演……但这一路上,不管所观所见是如何繁华流转、声光灼灼的景象,嘴里所讲的是何等应酬或恳切之辞,脑子里终究还是记挂着那只慢吞吞的硕大蜗牛,似有一种强迫症般的,想要替它突兀的出现与丰盈的存在寻求到一条逻辑线:哪怕是微弱的摇晃的。
当思维跟不上时,感官便会仗义地跳出来帮忙、胡乱帮忙。
譬如视觉。我把目光投向街面,广州城的色彩,是极不均匀的,绿色霸占了绝对地位,掠夺的、压倒性的强势。树边有古木有新枝,红棉花,老榕树,皆铺陈繁琐,勾肩搭背,连成一大片一大片的色彩专属区,仿佛出自一个极为固执的偏色风景画家。尤其站在高楼往下俯看,不仅纵横街巷绿意逼人,连众多本该灰白当道的楼顶之上,也被精心布局成绿色的屋顶花园,真个把钢筋水泥变为草木森林了。不由人心念不为之一动,似乎那只蜗牛的出现本也是一个应有的误会了。
又譬如触觉。此时已属夏末,白露节气,但广州并无秋日的高爽气象,其湿答答与黏乎乎的低气压候症,与南京五月间的黄梅天别无二致。北方人可能受不了,可作为长江上下游地域、每年都会黄梅天正面遭逢、抱个满怀的南京人来说,倒也算是一次错时空的第二次握手。行进中的左右人物,屋内外的物件,包括各种飞虫、甲类、爬行小动物,都在水汽的浸泡中泛出几份蒸腾的光泽,不知四时之变,乃至蠢然欲动了,更何况本就喜欢四海为家、浪荡江湖的蜗牛乎?
再譬如味觉。粤菜名扬四海,一日三席,皆是异色不重样,或水产或山货,或野鳝或家鸭,或吊味高汤,或闲味小炒,三碟五盏,美味无可比拟,这须得另作一篇大文章。食味之上,更有一种旧时光、古日月之味,从花城的各个角落里隐隐约约地冲淡而来——发于南海神庙之水波不兴,发于雨打风吹总不改的陈家祠砖雕,发于英雄少年念念有回响的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发于风云变幻名将宿相起于兮的黄埔军校……也难料,那只蜗牛,或本非今朝今世之物,实为跋山涉水、穿古越今而来的那一只蜗牛之祖,它的硕大无朋里,有百年舌尖与千重记忆,有腥风血雨的残断篇章,有狂澜巨涛中的蚀骨印痕,它从岁月的深处爬来,爬到这2016年或2046年或8046年的花城广场中央,它是代际的信物,它是明鉴的独眼,它是曲折十八弯的历史回声……
如此一想,这只蜗牛,其出现当是自有些道理,并更以一种偶然的投射,进入到我们这些路人与游客的视线,从而达成它的使命与寓意:一次不可命名、但巨细有味的相遇。
责任编辑 张 鸿
鲁敏
鲁迅文学奖得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 《六人晚餐》《九种忧伤》《伴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