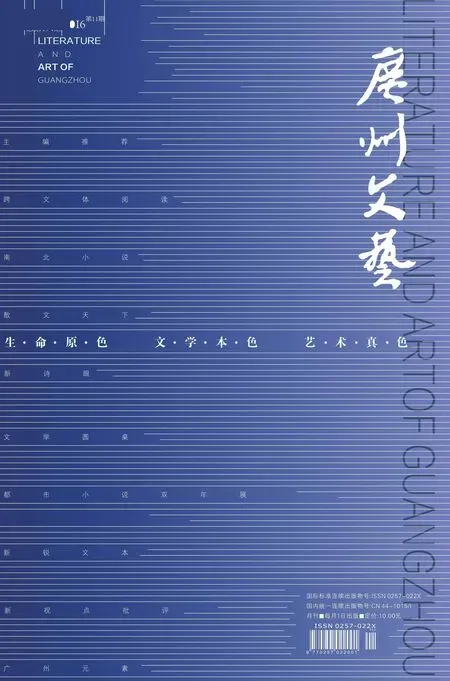忏悔者
刘荣书
忏悔者
刘荣书
需要忏悔的人心里往往装满了恶业。自己不能得以解救,因此便要在上帝、佛、师长、大众面前寻求告白,以求得到宽慰——但问题是,上帝的足迹并未光临此地,其间也不见一座辉煌的庙宇;即便有庙宇的话,也消费不起那日渐冗赘的香火钱;师长和大众更是无可指望,他们只会对你的 “恶业”报以同情或指责的态度……因此生活在这个平原上的人们,心里有了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或是在命运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时,往往会求助于“大仙”。
大仙在我们这里,应是上帝和 “神”的替代品。又或可说,是替人排忧解难的心理医生。
今天,来找大仙求助的这位病人,身份看上去委实有些特殊。
大仙垂目看他,见此人身材矮胖,年纪虽是不大,却已谢了顶。一段颈子好似被夯进脖腔里。肿眼泡,说话声音沙哑。穿一件不知从哪儿得来的工装上衣,衣襟宽大,沾了斑点油腻。袖子挽起一道。一双肥手看上去倒并不粗糙,和那张脸一样,脂肤发亮。衣襟下摆缺一颗纽扣,坐在那儿,闪出一块肚皮来。
仙家,你能看出我是做什么的吗?病人问道。
大仙心里略有不快。平日里那些寻医问道之人,大多是愁容满面的妇人,而少有这样的壮男。即便有一两个男人的话,也大多相貌不凡,不是老板便是官员。他们虽心有隐讳,却大多能敞
开心扉,从不会在身份问题上与她作无谓的纠缠。他这样问,显然是对大仙的 “功力”有所怀疑,故意要考验她似的。大仙微微一笑,成竹在胸地答道:磨刀霍霍向猪羊,刀刀见血断魂肠——你么,是个屠户。
男人身子一抖,惊骇之下,很是敬畏地看了大仙一眼。这才委下身子,如实将自己的病情道了出来。
我是一个杀猪的,大仙……可就在近日,这桩营生我却做不得了。那天我杀一头猪,刚给猪放了血,却没了一丁点力气,连一把杀猪刀也拎不起了。接下来褪毛剖膛,都是我老婆替我干的。我在案板上剔那猪肉,每解一刀,身上便会出一身冷汗。等卖完全部的猪肉,我身子抖得就像筛糠……我疑心得了什么病,去了医院。医生给我拍了各种片子,却检查不出问题,又给我开了一包子药,还假惺惺嘱咐我说,你是累了,要多休息。我依了医生的嘱咐,啥也不干,等死躺在炕上……但病又是不能装的,要装给谁看呢!我吃也吃得,喝也喝得。房梁上又不会掉下馅饼来……就在昨天,我又杀了一头猪,但刀子刚捅进猪的脖腔,身上软得又没了一点力气,倒把那头猪给杀活了……
屠户的讲述,把大仙给逗笑了。她这一笑,便卸下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伪装。抬眼瞅去,发现她只不过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普通村妇,圆脸、细眼,由于不像别的村妇那样下田劳作,周正脸上倒多了一些富态与端庄。
在大仙的哂笑声中,屠户显得很是无奈。他放下自己的病情不提,却又问起多日来令他倍感焦虑的一个问题来。
大仙,我们做屠户的,每日里杀猪宰羊,算不算杀生啊?
大仙收了笑,看他一眼,神色端正说道:算呗!杀猪自然是杀生……
那有什么说辞不?屠户问。
至于说辞嘛……你们杀猪宰羊的人双手血腥味都重,造的孽也重。古语说,做屠夫者,注定今生无妻无子,孤独终老来赎罪……
听完大仙的言语,这屠户脸上倒不见了先前的惊慌与无助,神态反倒自若起来。他双手杵在膝上,朝前挺着身子,摆出要和大仙理论一番的架势。
我做屠户,该是命里的安排。我也想和那些大人物一样,做老板,做官员,可又没那样的本事。我家祖坟上也没长出那样一根蒿草……我十三岁操刀卖肉,全是为了帮衬父母,补贴家用。后来娶媳妇,生了两个闺女,大的结了婚,小的正在读大学,全是靠我杀猪供养她们。卖肉我不差别人斤两,杀猪时虽有一股狠劲,却从来不干欺街霸市的勾当……你说,我怎么就该罪孽深重呢?
在屠户的责问下,大仙自知言重,又觉得戏弄得他够了,犯不上同他在佛法的教义上争论不休。况且自己烧香拜佛,替人消灾除祸,还是以 “和气生财”为重。她便娇嗔一笑:你别急么,容我把话说完……她看他一眼,说,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有自己的营生要做。有人做官,便有人要来当平头百姓;有人享福,也便该有人一辈子受苦……这都是上天安排好的。看你头顶三旋,脚踩七星,你这样的人阳气重,杀猪宰羊,是上天赏你一口饭吃。古时法场上的刽子手,也不见得非要下十八
层地狱,到阎王那里报到时,阎王也会酌情处理……
大仙说完,自顾从炕上下来,先去净了手,又拈起摆在桌案上的一把香烛,用火柴燃了。为了加快香烛焚烧的速度,她仰手在空气中挥了几下,将香烛插在 “观音像”前。那案几上摆有两尊瓷像,一尊是观音菩萨,一尊是财神爷。每尊佛龛前都供奉一只香碗,由于年深日久,香灰从碗里漫出来,于案几上堆成一座小山。据说,这大仙家的香灰,隔不几日,便要用推车往外清理一次,堆在村外某一处洁净的地方,被栽花的人、种菜的人如获至宝收走。又据说,拌了香灰的土质中长出的花草,会分外鲜艳;而那蔬菜,又生得格外水灵……再看香灰旁,散乱着一堆纸币,有红色,也有绿色,还有杂七杂八的颜色。那是香客看完病后,供奉给菩萨的香火钱。从道义上讲,大仙是不该收费的,但诸神却需供养。只是私下里,大仙每天都会从那一堆纸币里,挑拣出几张红色或绿色的钱币塞入腰包。倘若数天老是碰到吝啬的香客,她还会拿出几张红色纸币,掺放进去,以作诱饵,或混淆视听。
屠户对大仙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头顶三旋”这句话他倒能听懂一些,意思是说头上长了三个 “旋”,这样的人也该算作异人。但他抬手摸摸头顶,却实在想不出自己头发浓密时,是否真的生过三个“旋”。至于脚踩七星,他实在闹不明白什么意思……只呆呆地看着大仙的背影发愣。
此刻大仙已在佛龛前做过一番祷告,显然神灵立马附了她的身体。先前略有红晕的一张脸,瞬间变得黄纸般难看起来。神情也随之萎靡,嘴里不停打嗝。她垂着眼皮,转身从香案旁的柜子上,抄起三根竹筷,又在一个盛水的容器里将筷子浸了水,手端一只瓷碗,晃悠悠爬上炕来,将碗放在屠户面前。碗里盛有半碗清水。
大仙对着虚空,用男声发话:说吧,看是哪一路孤魂野鬼,缠了你的身体!
屠户愣住了。一是大仙发出的男声,听上去委实有些怪异,而她此前说话却是柔细的女声。二是因眼前的阵势,他虽未有经历,却曾有过耳闻。据说像他现在的遭遇,不是患了什么病,而是野鬼缠身。驱鬼的土办法,用一面镜子和一枚镍币。由病患者说出一个个死者的名字,若镍币在镜面上戳住,便证明这死者的鬼魂附在他的体内。
屠户略有迟疑,却在大仙声色俱厉的喝问下,险些吓破了胆,只能斟酌着报出一个个死者的名字来。
大仙手中握有三根筷子,待屠户说出一个名字,便将手松开。那三根孤立无援的筷子,看上去绝无在碗里垂直竖立的可能。它们纷乱无序,朝不同方向倒伏。只听筷子磕碰瓷碗,发出 “叮当”乱响。垂头的大仙鬓发披散,神情专注。快讲,快讲!到底是哪一路孤魂野鬼,从阴间逃出来,扰乱了人世。
随着大仙嘶哑的叫喊声,屠户也慢慢变得神情专注。起初他是有些恍惚的,甚至对大仙的举动持有某种怀疑态度。他口中每喊出一个死者的名字,便见那死者的面庞从眼前飘过。屋子里青烟缭绕。那些死者栩栩如生,或是对他展颜一笑,或是对他做出各种古怪表情。或悲伤,或愁苦,或恼怒,却原来都是在生活中与他有过交集的画面……随着竹筷的塌落,伴有大仙
持续不断的打嗝声,屠户甚而感到一种荒唐。在念诵完熟识的大部分死者的名字之后,屠户无计可施,开始有些绝望,忽然放低声音,迟迟疑疑道出另外一些人的名字来。他小声地、不确定地念叨着那些名字,好像斟酌着他们是否还活在这世上一样。
但奇怪的是,当他道出第五个名字之后,那三根筷子忽然在碗里定住了,显得如此突兀。在屠户眼里,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三根筷子的下端浸没在水中,根部有一个呈三角形的支撑,但无所依傍的筷子顶部,却不可思议地紧贴在一起,像是被胶水黏住,直挺挺戳在碗里,并且有着长时间的停顿。
屋子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凝滞了。大仙停止打嗝,目光看定屠户,大叫一声:是他,就是他!他叫什么名字?再说一遍!
屠户没有反应,只是愣愣地盯住那三根筷子。
直到大仙又喊了一声,屠户才启开唇舌,念白般说道:迟贵,迟贵——
屠户话音刚落,那三根筷子便毫无征兆地倒了下去。磕碰瓷碗的声响,在屠户听来,无异于巨物的坍塌。
大仙伸着懒腰,打了一个哈欠,仿佛从神灵附体的状态中醒来,脸上恢复了如初的神色。她扭身拿起一张黄纸,又找出一支碳素笔,准备在黄纸上写下那鬼魂的名字。她准备再施法术,将他祛除,不想等她找到纸笔时,又将鬼魂的名字给忘掉,便垂头问了一句:
他叫什么?
说话的声音又转为柔细的女声。
听不到屠户的回应。
大仙又问。她抬眼看屠户,却见这被鬼魂缠身的人,眼里忽地就落下泪来。
屠户之所以哭泣,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缘由。只因在他出门看病之初,他的家人便已对他的病症作过种种猜测,说这个附了他身体的家伙,就是眼下被大仙抓住的“鬼”。
但无论如何,屠户都是不肯相信的。而现在,在大仙的作法下,却由不得他不信。
迟贵……
他再次喃喃道出那个名字来。
大仙睃着眼睛,用粗粝的笔在一张黄纸上慢慢描画,神态看上去显得极有耐心。她眼神昏花,又识字不多,她所写下的“迟贵”二字,或许会被别人误读成另外一个名字。
屠户收了悲伤,忐忑地看着大仙,忽然迟疑着说道:大仙,真的是这个 “鬼”缠了我的身吗?那可是我的亲兄弟呀!
握笔的大仙停止了描画,皱眉看着屠户。她笔下的名字刚刚写完,屠户的话顿时让她生出一些疑虑——在她无数次的施法中,从未有哪一个 “鬼”会来纠缠自己的血亲。要知道,“鬼”也是知亲疏的。那些时常溜到人间来捣乱的 “鬼”,只会纠缠那些 “邪骨头邪肉”的外人。他们寂寞,或是生前便有着促狭或顽劣的性情。
大仙放下手中纸笔,判官一般审视着屠户,用低沉的嗓音,不无埋怨地说道:你可想想,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兄弟的事,让他到了阴间也不肯放过你!
屠户缩了一下短粗脖颈,露出一副骇然神色。显然大仙的话将他的心事戳中。
他心里虽有委屈,却还是长叹一声:仙家,我虽对他做过一件事,可那却是为他好啊。
大仙不语。
我那兄弟,长得和我很像,我们相差五岁,看上去却像孪生……就在前年,我母亲临死前,我们两兄弟吵过一架。
为啥吵架?大仙问。
因为赡养我的母亲。屠户说。我的老母瘫痪之前,一直跟着他住,帮他带孩子,帮他做家务。等到母亲病了,他提出轮养。轮养就轮养,我这做老大的,理当让着他。母亲先在我那儿住了半年,轮到他养时,他却耍赖,不肯把老母接走……不接就不接,我这做哥哥的也体恤他,他有一个病老婆,什么也做不得,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娃娃。养老母是我的本分,但你总该出些费用吧?我去找他理论。三说两说,我们便吵了起来。他比我年轻,力气又比我大,先是骑在我身上打,后又扇了我几记耳光,只打得我鼻腔喷血。回到家,我老婆见了,一个劲儿骂我窝囊,撺掇我去跟他拼命。我拎了把刀子,真的就想去跟他拼命……屠户讲到这儿,大仙 “啧”了一声,以为接下来会有什么不测的事发生。屠户看她一眼,垂下眼帘,一径讲了下去。
别看我杀猪时胆大,平日里却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我拎着刀,哪里敢去找他拼命啊,说不定刀子被他夺去,只有挨捅的份儿。我拿着刀子,去磨刀石上蹭,其实是不想听我老婆唠叨。我磨刀霍霍,心里渐渐安稳下来。我想,与其和他胡搅蛮缠,倒不如多杀几头猪,多卖几斤肉,多挣些家用,攒出供奉我老母的钱来,老婆见我窝囊至此,便自己去找他理论,幸好被回家的侄子劝了回来。我侄子读高中,知晓事理,当场给我老婆跪下,说大娘,我爹是个浑人,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供奉我奶奶的钱,就先记在账上,等我读书出来,加倍奉还。我那侄子真是懂事啊!又跑来将我好好安慰一番。我虽是受了些委屈,却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从心里喜欢我那侄子……我这人,脑筋古板,私心也重。我老婆是个废物,只给我生了两个闺女,闺女嫁了人,那就是泼出去的水。我想等我百年之后,还要侄子来给送终呢!
屠户一番话,不想却让大仙心里起了反感。因为她也是生了两个女儿的人,以前不被婆家人待见。大仙撇撇嘴,讥诮地说,这么说来,你还算是一个仁义之人了……
屠户听出大仙话里的贬义,不由叹了口气,说:对我兄弟,我应该算是仁至义尽了……自从被他打,我虽有嫉恨,却拿他没办法。他去矿上打工,半年不回家一次,我见不到他,心里倒也清净。
大仙说,如果只打过那一场架,有愧的该是你兄弟,便不该来这世上缠你。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或是死得不明不白,才来找你诉自己的冤屈?
他死得也该心安,死在外地的一家煤矿上。屠户说,死虽是死了,却得了一笔巨额赔偿。那些钱,是我们这些劳苦人,几辈子也赚不来的。
大仙心怀叵测地看着他,忽然就浮想联翩起来。想到会不会在那笔抚恤金上,屠户做了什么手脚。此时看屠户的表情,说起那笔抚恤金,一脸向往的神色。好像用一条贱命,能换回那笔巨款,也是他本人十分情愿的事。
在接下来的对谈中,屠户对那笔巨款绝口不提,却说起他去处理死者善后事宜时,
发生的一些事。
……那一次 “矿难”死了三十多人,有几个找见了尸首,大多数却没找见。庆幸的是,我那兄弟的尸首,是最后一个被找见的。更为庆幸的是,老天给他留了一个囫囵全尸。
当时我们住在一家废弃砖厂的宿舍里,也不知我兄弟他们做活的煤矿,离这砖厂多远,藏在周围哪一座山里。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些死者的家属,来自天南地北,说话口音各异,哭声却是同样的腔调……那数十具尸体断断续续运送过来,起初我们并不知道……等商量完赔偿数额,那些找不见尸体的家属不干了。有几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哭闹着要去矿上找自己的丈夫;还有几个白了头发的老妇,要去那里给儿子烧几刀纸,杀一只招魂鸡……这就把矿上的人给惹恼,说谁要敢动,商量好的抚恤金,不但一分不给,还要把他的腿打断。那几天可真是乱啊!虽是同样遭了大难,我却感到几分庆幸。毕竟,我兄弟的尸体,就停在砖厂的一间小屋子里。我们还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我带上侄子去看过他一次。他们将我兄弟放在一块门板上,用一床棉被裹着。我掀开被子,见他浑身上下全是黑色,仿佛一块煤炭。若不是看他的个头、他的秃顶,我哪里认得出他。我吩咐侄子打来冷水,用一块毛巾,上上下下给他擦拭。直到盆里的水换过三次,才洗出他的眼睛、鼻子、嘴巴。他的嘴巴张着,两颗门牙白得发亮。侄子在一旁不住声地哭。我劝他:孩子,别哭啦,我们算是幸运的。你爹总算落下个全尸。那些找不见尸体的人家可怎么过啊!等抚恤金给了我们,我们就带上你爹回家,好好把他葬了吧。
那笔钱很顺利地就给了你们?大仙皱眉问。
给了,屠户说,矿主还算仁义,那些没找到尸体的家属,又另外给了一笔钱,算是封口费。藏在砖厂的尸体越来越少,都是家住附近的矿工。趁夜深人静,亲属把尸体拉回家,偷偷安葬了。最后剩下来的,就我兄弟和一位河南籍的矿工。起初我想得还算周全。我和那河南老客通过气,不行就雇辆运尸车,即便花再多的钱,也要把兄弟的尸首运回去。实在不行,就找一个当地的殡仪馆,把尸体火化,带骨灰回家也成啊。
但等一切料理停当,准备动身时,却发生了一件事——不知谁把矿难的事给捅出去了。据说省里下来了调查组。矿难是瞒不住的,只能在死亡人数上瞒报。除了几个当地的死者之外,外省的死者便都成了不存在的名额。矿上人说,尸体一律不准出省,怕走漏了风声。我们又商量去就近的殡仪馆火化,矿上的人说,火化需要登记,一登记就会露馅。不行就补给你们一笔钱,你们拿钱走人,就当尸体不曾找见。
那河南人听了此话,不吱声了。我蹲在那里,怎么也想不明白。我问矿上的人:不让带走,我兄弟的尸体你们怎么处理呀?
矿上的人看着我,莫名一笑,说,当然埋了呗,还能怎样!
我从他的笑里,能猜出我兄弟的尸体会受到怎样的待遇。肯定会像一条野狗,被随便埋在这深山的某一处角落,或被丢进废弃的矿井,永生永世,难能见到日光。
那样的话,我兄弟算是死无葬身之地。
矿上的人随即拿出一沓钱来。河南人接过,拿在手里,一边数,一边可怜兮兮说,能不能再多给点。
矿上的人不理他,拿起另一沓钱,朝我手里递送。
我不接。那矿上的人看着我,问:给钱不要,你又想咋样!
我看着他说,我不想咋样。无论如何,我也要把我兄弟的尸体带回家。
你再说一遍!大概是听我口气强硬,站在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向前迈出一步,手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敢整事,老子让你出不了这蟠龙镇。
我垂下头,不敢言声。
河南人也劝我,拿过那钱,硬塞在我手里。我仍是不接,只是闷头在那里蹲着。年轻人骂了几句,一个箭步跨过来,伸手薅住我衣领,拖死狗一样把我朝屋外拖。衣领勒着我的脖颈,险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挣扎,也不反抗,只任他把我拖出屋外,腰里又被踹了两脚。有几个当地人默默站在一旁,表情冷漠地看着我。
第二天,河南人便从那家砖厂离开了。
那一晚我整夜未睡。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带兄弟的尸骨回家。
我虽不必为一个死人考虑,但我要为活着的人考虑周全。每年的清明除夕,我侄儿要给他父亲烧一刀纸,找不到一个坟头怎么办啊?没有那个坟头,我侄儿就没了一个祭祀先人的地方,他就成了一个无根的人。以后他的儿子孙子,就都成了没有根基的人。
也是啊!大仙不无忧虑地插话说道,你看那些横死异乡的人,尸骨带不回来,家里为他堆了一座衣冠冢,他的后人晚辈,一辈子的运气也是不济。
就是啊!屠户感激地看着大仙,眼里泛出泪花。我正是这么想的,况且天亮时我看到了我父亲……我父亲死了多年,很多时候,我连做梦都不会梦到他。但那晚,他就活生生站到我面前来了。也不说话,直盯着我,盯得我心里发毛。我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好,惹他老人家生气。我说,爹,离上坟烧纸还有些日子,你若实在没有钱花,就等回去,葬了我兄弟,顺便给你多烧几刀纸。我父亲还是不高兴的样子。他张着嘴,唇舌蠕动个不停,显然在叮嘱我什么。我却听不到他说的话。直到外面露了晓白,他的身子变得越来越淡,仍旧唇舌鼓荡,说着什么,可我就是听不到。
大仙插嘴说,你那是做了一个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屠户说,不是做梦。那一夜我一直睁着眼睛。——那是我父亲的鬼魂,赶了几千里的路,特意来叮嘱我的。我见他裤脚上沾满了灰土。如果是做梦的话,他说话的声音我怎会听不到?
大仙一笑,不与屠户争执,只是问:最后你兄弟的尸体带回来了吗?
屠户不答,仍顾自往下讲:那天早晨,矿上的人过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说晚上必须从这里离开。晚上十点半的火车,火车票都买好了。他们把车票交到我手里,又不阴不阳地嘱咐我说,好自为之,尽快离开这里,别给自己惹麻烦。
听了这话,大仙心里陡然变得紧张。
我跟人打听,离那家砖厂十里地开外,有一个集镇。那天上午,我走路过去,想在
那集镇上买一把刀子……
在屠户的讲述中,大仙的神情变得更为紧张。起初她断定屠户是想跟矿上的人拼命,决意要带兄弟的尸体回家。但看他懦弱的样子,却实在想不出接下来他该如何应对。
我先去了一家超市。那超市里的货物倒是齐全,却唯独买不到一把刀子。我又去了一家五金店,五金店里有菜刀售卖,我把菜刀从货架上拿下来,用指肚搪搪刀刃,觉得虽麻麻地触手,却离我想象的锋利还差得很远……我在那集镇上乱转,忽然就想起我放在家里的那几把杀猪刀来。我所用的那几把杀猪刀,一把 “擒刀”,是专为刺穿猪喉来用;一把砍刀,专为剁碎猪骨来用;一把剔刀,小巧得像一枚匕首,专为剔骨解肉来用。我侍奉它们多年,深知它们的脾性,它们是谗血又谗肉的;如果久不用血肉来喂它们,它们便会生锈。刚刚下过雪,集镇上出售的货物,显得花团锦簇,和老家集镇上的景象无异。我在一处肉案前停下。卖肉的人是个瘦子,屠宰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案上的猪肉被他割得七零八落,筋筋骨骨连在一起。见我在肉案前张望,他开口问我:割肉?新鲜的猪肉啊。
我指了指他手中的刀子。他正将一把剔刀竖在手中,在油腻的肉案上划来划去。
我说,我想买你这把刀子。
他没听懂我说的话,侧耳又问了一句。
我瓮声瓮气地重复了一遍:我想买你这把刀子。
他怔怔看着我,以为我在同他开玩笑,好半天才说,你这人真怪,不买肉,倒想买我的刀子。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红色钞票,在他眼前晃晃。他看了一眼,生气地说,不卖!
我又掏出一张红色钞票,和另外那张钞票叠放在一起。
他扫了一眼,从鼻孔里 “哼”了一声。
等我掏出第三张钞票,他的目光在那钞票上停了一会,遂把手中的刀子竖在眼前,认真端量着。或许想不出这么一把普通的刀子,哪里就值三张钞票的价钱。我见他动了心,也不催他,只脸上露出一副诚恳的表情。他问:你真的想买?我点头。他笑起来,说,我家里还有好几把刀子,卖你一把倒也无妨……
他左手先是捏过那三张钞票,右手的刀子便直戳戳递送过来。我不好去接那利刃,只等他把刀子放在案板上,才伸手握住了刀柄。
刀柄上沾满油腻,刃口还有红白肉星。我一握刀柄,手便抖了一下。
直到我握着刀子走出很远,才听到屠户从背后传来的喊声:你个怪人!买下我这把刀子,不会是去杀人吧?即便你杀了人,也和我无关啊。
大仙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屠户,仿佛见那持刀行走在异乡的人,眼里肯定布满了杀气。因为此刻,在屠户的眼里,忽地就密布了杀气。
我把刀子别在怀里。刀子硬硬地硌着我的腰,一下便让我有了许多底气。从集镇上出来,我沿着一条路往回走。那里的路弯弯曲曲,全是鸡肠一样的山路,周围的荒山覆了雪,真的就像书中所写:荒山秃岭一个模样。我走来走去,竟迷了路。我怒气冲冲,生自己的闷气。路上不见一个村庄,也碰不到一个行人,跟人问路都
是万难。好在走到下午,终于找回了那家砖厂。
回到宿舍,见侄儿坐在床上,脸上的表情很是无助,看了只叫人心疼。他真是一个懂事的娃儿啊,早早就把行李拾掇好了。见我回来,侄儿长舒一口气说,大大(大伯),咱们早点离开这里吧。见我不答,他又说,大大,我想家了。功课我落下了一个星期,我想早点回学校!我仍是不答,用脸盆打来水,从怀里掏出那把刀子,将刀子慢慢浸进水盆。
刀子滑入水盆,像一条游鱼悄无声息,只水面冒出几串气泡。渐渐地,那盆里的水由清变浊,是刀子上的油腻与血腥稀释,在水中挥发开来。我拿手去捞那把刀子。刀子紧贴盆底,手先是触到刀刃,那刀刃足够锋利,一下便咬了我的手指。只见一缕殷红从盆底滋生,像草一样生长。我顾不得疼痛,一把将它抓在手中。
我用枕巾仔细将那把刀擦拭了一遍。但刀子上的油腻仍不能祛除。我便找来香皂,将它通体揉搓。泛着泡沫的刀子打滑,几次从手中脱落,跌入水中。
我那侄儿在一旁颤声说,大大,我想回家!
我不理他,仍仔仔细细清洗着那把刀子。刀刃上涂过香皂之后,又经清水的洗涤,很快露出青白的锋芒来。刀柄的缝隙间仍有油垢,我便用指甲一点点将它们剔除。当我将刀子端在眼前打量时,发现——那真是一把干净的刀子啊。
经由方才这一番讲述,屠户脸上的神色渐渐安稳下来,仿佛对那把刀子的清洗,已消解了淤积在他心中的愤怒与焦虑。这不由让一旁凝神倾听的大仙长舒了一口气。他不会想用这把刀子去杀人吧?大仙这样想。应该不会,没有一个杀人者会在实施自己的行动之前,这样耐心地去清洗一把刀子。
我将那把刀子拿在眼前端量,侄儿喘着气大声问我:大大,你想干什么?
我看他一眼,对他说,你不要管。你只管在屋里待着就是。
我自然没有胆量去杀人……仿佛为了消除大仙的疑虑,屠户看一眼大仙,恹恹说道。他的情绪忽又变得消沉下来。他垂着浮肿的眼皮,接着往下讲。
我拿着那把刀子,走出门来。砖厂的院子里不见一个人影。一只乌鸦落在墙外的树上,“嘎嘎”冲我叫个不停。一走进停放我兄弟尸体的冰屋子,我的身体不由打起了寒颤。屋子里真冷啊!想我那兄弟,赤身裸体躺在门板上,也不知会有多冷。我掀开被子,先是这样问他:兄弟,你想不想回家?他不语。我又说,不想回家,你就再也回不了家了。他仍是不语。我说,如果想回家的话,就别怪哥狠心,以后也不要找我的麻烦……屋子里很静。这时我又听到墙外那只乌鸦在叫,叫得一声比一声欢快,被我认定那是我兄弟的回答。
你想怎样带你兄弟回家?
大仙似乎猜到了什么,问那屠户。她脸上的表情竟有些惊悚,显然那种想象把她吓到了。
屠户不答,沉吟了一番,冷着脸说:我还有啥办法……我想我那样做,我的兄弟是情愿的。
就这样,大仙随着屠户的讲述,看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当夜她便做了噩
梦,梦到自己成了那持刀剔解死尸的人——刀子划开皮肤之后,仍有暗黑血渍不断渗透出来。场面虽有些阴冷,却并不恐怖。刀下的尸身成了一具祭祀用的物品,或像肉案上供人朵颐的猪肉牛肉,渐渐在一把刀子的剔解下,变得肥白瘦红,花团锦簇起来。直到从梦中醒来,想想那做梦的过程,仍旧令大仙感到一阵阵后怕。
他怎么会那么心狠?亲手肢解了兄弟的尸身!当屠户在叙说中跳过剔解的过程,大仙看着他,心中不禁有了这样的疑问。而屠户接下来自言自语般的讲述,也算作是对大仙疑问的一种解答。
我真是下不了那狠手。但时间紧迫,天色越来越晚。我一边肢解,一边想我那兄弟的坏处,想他同我吵架,我们虽是一母所生,他却张口骂我的亲娘。难道我亲娘就不是他的亲娘?他犯起浑来,真是畜生不如!我想他把我打翻在地,骑在我身上抽我的耳光,全然不顾兄弟的情分。我越想越气,就当是在对付一个仇人。我麻溜地剔净了他身上的皮肉,将一根根骨头收集起来。我只取他身上重要的骨头,像那些指骨和趾骨,我实在没有能力和心情认真地搜集。我想,带他身上这些重要的骨头回家,完全能摆出他一个完整的人形。他比我要瘦,骨头与皮肉加在一起,也就一百四五十斤。单估量那些骨头的重量,也就二三十斤。我把那些骨头码齐,用塑料纸包好,以免血渍渗透到外面,再用床单裹扎几层,塞进旅行包里,坐火车,乘汽车,想来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等我做完这一切,揩净手上的血渍,准备抽根烟歇息时,不经意朝窗口望了一眼,却见那窗玻璃上,镶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那窗玻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边角裂了一个豁口,那双眼睛就暴露在豁口处,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大仙失声叫了起来。
我原以为那会是一双审视的眼睛。是神的?阎王的?我搞不清。看上去却那么清澈,镶嵌着大滴的泪水和惊恐。待到后来,我才慢慢看清,那是我侄子的一双眼睛。想来他把我做下的事,全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忽地就失了全身的力气,瘫坐在地上。
屠户讲到这里,额上照旧渗出一层汗来,脸色变得刷白,想来身体正经受着极度的不适。不由让大仙动了恻隐之心,问他:你没事吧?
屠户摇头,说,没事,就是心慌得厉害。
要不要喝口水?
大仙倒了一杯热水给他。屠户抖手接过,吸溜吸溜喝着。
大概是热水的作用,又或是大仙的关照感动了屠户,他的眼睛瞬间变得湿润起来,仰头问大仙:仙家,你说,我做下的这件事,不会是造孽吧?
大仙想了想,瞬间对屠户充满了同情。
不是,大仙柔声说,怎么能说是造孽呢?她这样自语着,语气加重:你带兄弟的尸骨回家,不是造孽,是成全!
屠户随即呜呜咽咽哭了起来,边哭边说,那怎么每次我杀猪,身上都像被抽走了力气。我清楚那是兄弟在我身上作怪。我老婆也这样说。但我不信,我就是想来你这里问问……我心里虽是无愧,却怕以后再做不了这杀猪的营生,我将靠什么活下去呢?
大仙叹口气,知道那是屠户的心理在作怪,过一段时间定会不治自愈,却仍旧按平日里替人看香诊病的规矩,将那张写有死者名字的黄纸,用火柴点燃,口中念念有词。待黄纸在她指间焚烧殆尽,放入盛清水的碗中,用竹筷搅拌一番,端给屠户,说,你喝下这烧了纸符的水吧。
屠户接了,像一个行走在沙漠中的人,将水一饮而尽。
你回去以后,再折一根桃枝,最好是西北方向的树枝,选三枚狗牙、两根鸡翅骨,用红线拴了,用桃枝挑着,找一个十字路口,埋好。别被人撞见……保你以后再不犯病,继续做你杀猪的营生。大仙看着屠户,这样信誓旦旦说道。
屠户默默听着,一一记在心里。
现在他的身体舒服多了,人也变得格外安详。或许他本就是一个心态安详的人。临走时,他将一张绿色纸币供奉在佛龛前,扭头冲大仙羞涩一笑。
大仙送他出门。分别之际,屠户忽又想起另外一件事,神色再度变得慌乱起来。他说,大仙,要不明天,我带我侄儿来你这儿看看吧。自和我从矿上回来之后,两个多月了,这孩子一句话也不说,书都读不成了。
大仙愣了一下,倒还算是一个明智之人。她幽幽对屠户说道:
小孩子的病,我哪能乱看呢。别把孩子给耽误了。你还是带他去城里,找心理医生看看吧。
责任编辑 梁智强
刘荣书
满族。河北省滦南县人。作品见于 《江南》《山花》《作家》《人民文学》《天涯》《花城》等杂志。有作品被选刊选载并入选各种选本。著有长篇小说 《一夜长于百年》,中短篇小说集 《追赶养蜂人》《冰宫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