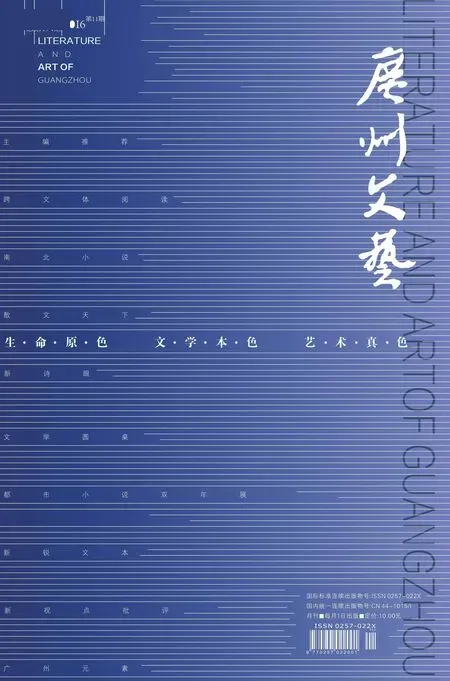你想和谁说话
陈会玲
你想和谁说话
陈会玲
一
我有过很多的梦想,很多很多。这些梦想就像山里那些数不清的小溪流,冬天干了,但春天一到,又潺潺流动。
但何枫告诉我,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不是梦想,不过是想法,就像地上的小碎石,不起眼,还踢脚,一点儿也不好。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啦。但我相信他的判断,我从来没有那么相信一个人,虽然他比我小很多,但我相信他,包括他的调侃,他的恶作剧。
我遇见他,还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漂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在这个城市里漂着。虽然我有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但这对于一个耽于幻想的女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年少时,我渴望逃离故乡,并成功地逃离了,但在城里待久了,我又想念着家乡的一切。
何枫是家乡邻县人,大学三年级那年,他在广州的一家小区当游泳教练。在广州,只要一到夏天,泳池里就浮满了模仿青蛙游泳的孩子,自然,也就少不了何枫这样的体育专业的教练。
那天我闲来没事,到泳池走走,穿着的拖鞋沾水打滑,一下掉到池里去了,狠狠吃了几口水。是何枫把我捞起来的,等我回过神来,遇到他那双似笑非笑的狭长的眼睛,他说,大姐,这么老了还不懂水性啊,不如报个游泳班好好学学吧?他身边的小学员听了都嘎嘎地笑。我很是尴尬,讪讪地说,不用了,谢谢你,以后有孩子了,送给你教吧。
为了感谢他,我要了他的微信号,他还主动告诉我他的QQ号。
第二天,我到网上团购了几张电影票送给他,算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吧。我说,对不起啊,教练,我的命就值这几张票。
这次,反倒是他不好意思了,说,姐,你客气了。
好像再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也不再到小区的泳池去走动了。虽然有时下班的时候,也想着去看看他,远远看一下他教学生游泳的样子,但很快又给别的想法盖住了。
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并不像电视剧或者电影里所演的那样,总会有相遇,并且频频相遇的两个人。就算是住得很近的两个人,只要稍稍用心,巧妙设计,也完全能做到一辈子不见。
等我再到泳池旁边的那条小路上走动时,已经是九月了,何枫他们全都回校了,泳池里有几个他的学员,已经能够畅快地游动了,他们一下一下地做着收翻蹬夹的动作,在游啊游。
这事想来也是有趣,也就一个暑假的时间,广州的泳池就多了这么多扑腾的小青蛙。何枫他们也真够不容易的。
二
也许是一个人生活久了,我越来越懒散。每天下班回到家,简单弄点吃的,就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躺着看书、看电影,更多的时候是在看手机。
有时我会熄了灯,躺在窗前的沙发上,呆呆地看着窗外。因为秋天到了的缘故吧,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虽不至于见风落泪,但沉默和伤感却是让我频频失眠。本来就长得不起眼,还每天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状态也是够差的。
这晚我在沙发上屏息等着身边一只嗡嗡作响的蚊子靠近我,蓄谋一下把它拍死的时候,手机的微信响了。
是何枫。
“姐姐,你的电影票我用了,电影不错,《碟中谍》,阿汤哥老了,但身手没老,我还是很喜欢他。”
“嗯,我也喜欢。”
“姐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看电影?”
“不知道啊!我随便送的,因为我喜欢看电影。”
“哦,那姐姐你平日都去哪里看电影呀?”
“很少去电影院呢,一般在电脑上看。”
……
过了一会儿,他问: “姐姐是客家人吗?那天听口音像呢。”
“是啊,瓮县的。”
“我在你隔壁,史县的。”
“是吗?怎么不早说呀?”
“我给你QQ,空间里有很多我家乡的照片,你一直都没进去看吗?”
“哦,不好意思啊,没呢……”
说不好意思的时候,我真的是怀着歉意的,所以赶紧补充了一句,我一会儿就上去看。
他给我发了个笑脸,接着发了一个挥手说再见的图像。
那个蚊子依然嗡嗡地在我身边飞着,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理它了。
我登录了他的QQ空间,点开相册一栏,里面有不少的文件夹,有同学聚会、
大学生活、游玩,等等。我思忖了一下,点开了同学聚会,于是我看到了大部分在卡拉OK唱歌的照片,合照居多,有些还是初中的同学聚会,他一脸的稚气,穿着运动服,留着小平头,而他的同学,多为洗剪吹的爆炸头,一副非主流小镇青年的模样。一对比,何枫还是属于正常的男孩儿。不过,照片里的何枫脸白白的,皮肤好像比女人还好,如果不是那双狭长的眼睛,真让人怀疑泳池那个黝黑的男孩是另外一个人。
接着我点开了一个命名为 “家乡”的文件夹,里面的照片都是风景,没有一个人,连个背影都没有,看来他是个泾渭分明的人,不古板的话,至少也讲原则和底线吧。
我一帧帧地浏览着这些照片,有正在开放的白莲,还有大片大片的紫云英,尤其是那云蒸雾绕的大山,大山下整齐的田垅,种植着花生、毛豆、水稻,而更远处的农作物,就看不太清楚了,但在那不清楚里面,也散发着扑面而来的熟悉和亲切。
这些照片唤起了我的回忆。
我也有过这样的故乡,也在这样的山地里游荡过,在一棵树下眺望过远方,在草丛中睡过慵懒的午觉,在田垅里偷过邻居家的花生,在一塘的荷花面前踌躇过,想着怎么把最漂亮的那朵摘下。
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无所事事的二流子,就像村里那个遭尽白眼的二皮,他的清闲是我最羡慕的。我常常跟在大人后面,一身泥一身水地去干活,二皮则在树荫下吃西瓜,那西瓜,也是从别人家的地里摘的,肯定是最大最甜的那个,在这方面,二皮比谁都聪明。我一边吞着口水看着二皮,一边往前走着,一不小心就踩在了一个土坑上,脚给崴了。妈妈回头就拍了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脑袋上,刚给太阳曝晒过的脑袋一阵昏眩,妈妈恼怒地骂着:“就知道你懒,就知道你想学二皮,这下可好,不用干活了吧?”二皮在树荫下哈哈大笑,我的脸火辣辣地烧……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到窗外有木棍绊倒的声音,那是我故意放在窗外的,怕的就是晚上有坏人。我一阵紧张,但丝毫不害怕,预感中,不是坏人。我摸黑出门,绕到屋后,看见了一个大大的西瓜,那晃悠着远去的身影,在夜色中依然清晰地让我知道,是二皮!
这么大的一个西瓜,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赃物,真是难为了我。我用手捅了捅它,纹丝不动,我用脚踢它,它滚动了一下,又停下了。怎么办呢?我蹲在这份大礼旁边,愁眉苦脸的。我实在没办法吃了它,动静太大了,虽然二皮是希望我吃掉它,但我其实只需要一小块啊。
既然我没办法吃它,那么,我只能扔了它,但能扔到哪里呢?
扔回瓜田?会不会给人抓住说我是小偷呢?
藏到柴棚?那妈妈很快就会发现。不发现也会烂掉,那整个柴棚就会臭气熏天。
扔到粪坑?第二天挑粪的人会破口大骂,会惊动整个村子。
……
最后,我想到了村外的小河。这条小河是珠江的支流,它一直流啊流,听说它最后去到的地方,叫广州。妈妈一直让我努力读书,长大了就去广州读大学。我从来没离开
过村子,功课也不见得很好,所以那个叫广州的地方,对一个孩子来说,太遥远,不知道我长大了是不是真的能去,但是,我可以把这个西瓜送到广州去。如果也有那么一个孩子,看见了这个西瓜,捞起来吃了,那就太好了。二皮挑的西瓜,永远是最好的,经过河水的浸泡,那肯定是又凉又甜。
这个想法让我莫名兴奋。我决意把它抱到河里去。但西瓜太大,我抱了一小段路就气喘吁吁,白天扭伤的脚也钻心地痛。我只能弯腰滚动着西瓜,向河边走去。
月光下的河流静谧,缓缓流动。我看着西瓜在河水中沉浮着向南漂去,心里涌起了一股柔情,突然觉得这夜色,这河岸的草地,草地背后的竹林,这些在白天的寻常事物,在这一刻,充满了温情,让我欢喜和沉静。
我在河边站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好像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何枫的照片,让我重新看到了这个隐秘世界的场景。那么何枫,你的童年是哪一个呢?是另一个我,还是二皮?
三
白天忙碌,无法和何枫聊天。到了晚上,何枫总会出现。他说大三了,课程少,兼职也没做了,又没女朋友,所以总是待在寝室,喝茶,听歌,上网。现在,他多了一件事,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给我发微信,开场总是:“姐,在干啥呢?”
我能干什么呢?除了等这一条短信,除了想听听他讲讲他的家乡,除了浏览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照片。除了这些,我只能在等待,陷在沙发上,或者躺着,时不时翻个身。
虽然实情是这样,但我依然老老实实地回答:没干什么,刚吃完饭、刚回到家、刚冲完凉……
这些理由,我反复运用,几乎不作变通。
他的回答也总是:嗯、嗯嗯。
这样的开场可以忽略,因为这已经是我们聊天的必备程序,就像我每天上班,出了电梯,立刻左转,在打卡机上打卡报到。
何枫已经答应我,给我讲述他的故事。
第一晚,他给我回忆了他的童年。
“记得七八岁时,家里给的零用钱不多,于是我和我哥上山砍竹子卖。爸妈整天忙着在田里干活,没空到镇里的圩市买肉。我和哥哥就跑到河里或者水渠里抓鱼,每次都能抓挺多的。但回到家里都被爸妈一顿臭骂,因为衣服搞得实在太脏了。鱼和衣服,爸妈更心疼衣服,衣服必须花钱买,鱼就未必。”
“我额头有一个月牙形的伤疤,姐姐你看到没有?”
“没有呢,我只见过你一次,没好意思仔细看。”
“那也是,我一直觉得这道疤很明显,以为所有人看见我的第一眼,就是这道疤。我九岁那年和小伙伴们骑自行车从桥上摔下水沟,桥大概有两米高,水沟里有一些锋利的石头,把我的额头割破了,血流不止。我哥立刻跑过来扶起我,摘了水沟旁边的布荆叶,搓碎敷在我的伤口上,慢慢就止住了血。那天爸妈干活回来得很晚,一看到我的样子,吓坏了,饭也没来得及
做,立刻带我去了镇上的医院。医生说伤口太大了,必须做手术,但额头离大脑太近,不让打麻醉。整个手术大概是半个钟吧,因为没有麻醉,那种疼痛难以忍受,穿皮刺肉,我嗷嗷大叫,手术前他们用绳子绑住我的手脚,但都给我挣断了大半,医院的床单也给我抓破了……
“手术后回到家里休养,因为家里没什么钱,所以也没闲钱买营养品。爸妈每天都要去地里干活,于是我哥又带着我去抓鱼,这次我们要抓的是野生鱼,大人说,这种鱼最有营养。哥哥在下面抓,我就在边上看着,看到哪里有,就告诉我哥。我哥连续抓了一个多月的鱼给我吃。”
何枫的语气是轻松的,这隔着手机,我也能感觉到。但我在这边,心如针芒般刺痛。
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只好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是因为我像真情节目里的知心大妈,还是因为我死缠烂打?
我们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我经历的,你应该都懂。他说。
我说是的,我们都是从山里出来的。
他笑了笑,我的经历还挺丰富的,以后慢慢告诉你。
我嗯了一声。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会反应灵敏,适时给予安慰。但事实上,我竟然失语了。
我进入了何枫的QQ空间,翻阅着他家乡的风景照,仔细地辨认着每一张。我看见了杂草丛生的沟渠,流水清澈,鹅卵石铺在溪底。这是何枫和哥哥抓鱼的地方吧?
我还看到了一个院落,那种典型的农家四合院。照片显示的是一个天井,院子有些破旧,两边的房间墙壁灰暗,天井里有水龙头、瓦缸、红塑料桶、砧板、洗洁精、洗衣粉,横梁上吊着一个竹篮,里面塞着的也许是不翻看就连主人都说不清的物件。何枫在照片说明里写着:我和大伯家。
当年的何枫,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进进出出的吧?年幼的他,额头上贴着青草药,坐在门槛上,忐忑不安地等着爸爸妈妈回来。他和哥哥抓的鱼,就养在水龙头下的红色塑料桶里……
一个故事终于找到了寄身的场景,我一下就流下了眼泪。
深夜了,我丝毫没有睡意,我选用了一张何枫家乡的图片,发在微信上,我写道:故事听多看多了,以为自己已经麻木了。我想,能打动我的故事,也许来自于相同的乡村背景,有着痛感而又浑然不知的童年,因为贫穷而一再放大的温暖……故事的讲述,来自一个漫不经心的青年。晚安,那些在深夜讲故事的人。
很快就涌出了很多留言。
三分钟后,我看到何枫在图片下面留言:晚安。
在一堆的留言中,这句晚安,让我默默地关上了手机。
四
我陷入了对何枫的想象中,说不清是他的故事打动了我,还是我在强烈思乡的缘故。他拍的家乡的照片,背景总是巍巍高山,常年有雾,我想伸手将雾霭拨开,这样,一个少年就会显现,他的面目逐渐清晰,是何枫年少时的模样:嘴唇紧抿,
眼神带点冷漠,但细看,眼神里还有一丝的羞涩。
这样的何枫适合恋爱。
何枫给我讲述他的初恋,是在两个月后,而其他的时间我们都在闲聊,我说我一些所谓的梦想和大学的事,他有时会觉得我很二,所以常常调侃我。何枫的童年故事是让我难受的,在失眠的时候想起,总会湿了眼圈。而平日和何枫东拉西扯的聊天,冲淡了我的这种情绪,让我得以从故事中抽身。
而何枫说给我继续讲故事的时候,我正情绪不佳,独自在楼下空地上兜圈。他说话的兴致却很高,我稍有迟疑,他就敏感地问,姐姐,你不想听我的故事了吗?我当然是否认,哦,不不不,是怕你太累。他雀跃起来,怎么会呢!我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好!我给逗笑了,急急跑回家,将手机连上了Wi-Fi。
何枫的初恋从孤独说起。
“姐姐,你知道被孤立的滋味吗?”
“我大概是知道的,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尝试过。当时我成绩比班长好,她就发动班里的女同学不要和我说话。该怎么说呢,当时心里是苦闷的,因为这事不好和老师、家长说,所以心里是很不好受的。”
“嗯,姐姐,我和你一样。我在小学被孤立过两次,一次是在二年级的下学期,在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全班的同学都不和我玩了,个个都在排斥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以前是朋友的,不再是朋友,是邻居的,见到我也绕路走。这种感觉很奇怪,你找不到原因,也没有人会告诉你,你莫名其妙被孤立,你好像生活在一个魔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没有成年人极力维系的表面的和谐,有的是儿童世界的真实,但这真实太残酷……在二年级之前,我读的是村小学,三年级开始,到镇里的中心小学上学,也许是环境改变的缘故,我们又开始玩在一起了。但到了六年级,整个年级的同学都不和我玩了,这是我第二次感到孤独与无助。但这时候的我已经不再默默忍受了,我频频和学校的同学起冲突,吵架,甚至打架。有一次,他们七个人围着我,我一点也不害怕,一个没朋友的人,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把他们中的三个打倒在地,另外四个站着的也没啥力气了。我自己也受伤了,整个后背痛得发麻,感觉都不是自己的了。全校的学生都在走廊里看着我们,还有老师和学校的领导,但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我们。似乎老师们也是见惯不怪了,之后学校草草地给我们每人记了个大过,连家长都没通知,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我用拳头换来了和平,从那以后,同学再也不敢和我起冲突了。
“我打架,小雪从来没有劝过我,她似乎很习惯这样的我。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她,她很可爱,也很漂亮,坐在我的后面。我们上课传纸条,下课到操场说话,我们很默契,只要一方看一下另一方,完全能感受到,看一眼,也能知道对方想什么。在其他同学都孤立我的时候,她依然和我说话。在我打架的时候,我看见她在人群中看着我,那眼神,没有担忧,似乎是相信我一定能把他们打倒。她相信我,也知道我的孤独。
“在六年级毕业时,也就是去拿成绩单那天,小雪也来了,她给了我一个礼物,是一个水晶球,里面是一对新郎新娘在深情相望。这是她在镇里的精品店里买的。
那时候,我们乡下的精品店都卖这些东西,明信片啊,塑料花啊,星星瓶啊,都是这些玩意儿。她告诉我要好好的,我当时以为她是要我在暑假好好的,没想到的是,她要离开了,她爸妈离婚了,她妈妈改嫁到另一个地方,她跟着妈妈去新家生活。我们在初中互通了一封信后,就没有再联系,听说她有了男朋友,等我读大学时,她就结婚了,如今的孩子已经两岁了……
“初中的时候,我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县里的运动会,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那是我第一次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接受表扬。那一次,我开始知道,唯有荣誉能让我获得尊重,所以我认真读书,考上了县一中。在高一军训期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她走路一摇一摆的,我偷偷叫她企鹅。我追了她两个月,她终于答应了,但一个月不到,她就提出分手,也许是我太心急吧,而她则慢热。这让我很受打击,消沉了一段时间,我决定报考体育专业。这样,我天天练体育,在跑、跳,挥汗如雨中,我的痛苦也在慢慢消失,直到我考上大学,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何枫说完这些时,他说很累了,完全忘记了之前说的自己有个年轻的身体。他说,我需要平静一下,因为每每想起这些,就像整个人重新给撕裂了一次。
我知道何枫的故事结束了。
我曾以为他要讲很久,因为他说过,他希望我能认真感受,像他一样用心,像我自己经历的一样,慢慢消化。
但我有时过于沉默,不能很好地回应,有时又显得漫不经心,就像一个在河岸走动的人,时不时打个水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让何枫失望了,他消失了,再也没有在我的微信出现过。
五
何枫的消失让我无所适从,那一段时间,我好像失去了整个故乡。
我决定给何枫看看我写的东西,那是三年前涂鸦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 《伶俐和丈夫的日常生活》。当年我很想当一个小说家,就像卡夫卡那样的,中国的很多作家都在模仿世界文学大师,我知道有一位作家,年轻的时候就靠模仿卡夫卡出名,所以我也写了这篇貌似荒诞的小说,也许何枫会喜欢,会联系我,谁知道呢!他还说他最敬佩的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菲尔呢。不能小看一个体育生,不是吗?
一下班,伶俐收拾好桌面,提起包就跑,刚出单位的门,一股热浪迎面扑来,夹杂着汽油味和不远处公共厕所的怪味,伶俐几乎呕吐。下班高峰期的广州大道犹如一个巨大的展览场,展出的是各式各样的车型,每辆车又如握着拳头作起跑状的小飞人刘翔,气势汹汹。但是大塞车却如裁判员手中迟迟不响的发令枪,让你紧张又消耗你的耐性,车流如慢镜头回放一样前行。如果车子最能体现这个社会的阶级,那么这一刻,阶级消弭,因为不管你是神气的宝马、奔驰,还是骄傲的法拉利、劳斯莱斯,只要一开到这个展览场,也只能好脾气地挨着夏利慢慢挪动,马路的秩序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伶俐挤上333路公交车,车里的空调不够大,伶俐一头大汗。她别扭地站在一个中年男人的旁边,他拉着吊环,身子随着
车子的颠簸左右摇摆。伶俐身高刚及他的腋下,人群使她的脸扭向他的腋窝,这样,她闻到这独特腋窝发出的阵阵毒气,袅袅而来,似榴莲又似猪骚味。伶俐一阵呕吐,一股黄绿水如喷泉涌出,她听到人群一阵骚动,密不透风的人堆竟然迅速空出一个弧圆,那男人的叫骂鼓噪着伶俐的耳膜。这一路,伶俐像个犯错的孩子,站在人群特意为她留出的这块禁区,守着一摊呕吐物,面红耳赤挨回了家。让伶俐低头羞愧的,不是呕吐本身,而是呕吐物中能清晰地看到她中午进食的食物,这比脱了衣服在人前还让她尴尬。
掏出钥匙,伶俐对着锈迹斑斑的铁门迟疑了一下,心里一阵激动,就像是小别胜新婚的小妇人,她脸色绯红地推开门。灯没开,她按下熟悉的开关,接着,她看到丈夫古铜色的脸庞,今天他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身材笔挺,让伶俐心慌意乱。她娇羞地责怪他:天黑了,怎么不开灯?在家,还是换上睡衣舒服!伶俐给他换上了一套水蓝色的睡衣,这样,她看见丈夫的眼睛里流动着大海一样深沉的蔚蓝。伶俐也给自己换上一套米黄色的睡衣,伶俐一边换衣服,一边对丈夫唠叨着今天在公车上的事。说到吐了那男人一身的秽物时,伶俐眼前迅速映出男人气成酱紫色的猪肝脸,像突然给人点了笑穴,伶俐兀自咯咯笑了起来。她笑得语不成句,但越笑越想说,越说越想笑。到最后,伶俐缩成一团笑倒在沙发上,年老体衰的沙发弹簧受到伶俐的挤压,也 “吱吱”地跟着笑个不停。
伶俐准备的晚餐很简单,一个蒸排骨、一个炒青菜,还有一个西红柿蛋花汤。大笑让伶俐的心情变得出奇的好,她吃得很慢,细细地咀嚼着,似乎不是在进食,而是在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但她又怕丈夫闷,于是批准他先去看他爱看的财经频道。伶俐独自一人坐在餐桌前,面对自己烹饪出来的晚餐,像面对一个哲学难题,有点枯燥,但又引人入胜。灯光下,伶俐的脸庞干净、温和,她收拾油腻腻餐具的手白皙优美,似乎永不厌倦。不远处的客厅,丈夫全神贯注地看着股市报道,电视里的股票分析师在滔滔不绝。股市又跌了!伶俐的心里顿了一顿,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跟风。
11点不到,伶俐就推着丈夫去洗澡,和丈夫一起洗澡是伶俐多年来的习惯。在伶俐和丈夫在乡下共同成长的岁月,有着无数这样的经历,在山塘里,在小溪上,丈夫结实的手臂撞击流水呈现的力量,让伶俐着迷。现在的丈夫还是那么结实,喷头喷出的水抚过他线条硬朗的胸肌,发出泠泠的声响,犹如天籁。温度适中的水从上而下,淋湿了伶俐的一头长发,她把湿漉漉的脸靠在丈夫的胸前,热泪夺眶而出,是夏季水量充沛的瀑布。
这一晚,伶俐在丈夫的臂弯里,做了很多梦。一会儿是一尾白狐轻轻一跃,转身成了逝世多年的老祖母。她全身雪白,像从遥远的北国披雪而来,她曲起拇指和中指,轻轻地在伶俐的脑门上敲了一下,嗔怪道:傻孩子,干吗要苦着自己?一会儿是汪洋大海,伶俐提着一个藤匣,站在甲板上,到一个心里清楚但怎么也说不出名字的地方。船就要离岸,伶俐等的人还没有来,她焦急地想着是独自前往,还是下船,犹豫间,船呜呜开动,伶俐脑子一片空白,突然想不起要等的人是谁。依稀
中,岸上人群大乱,似乎有人落水……伶俐醒过来,汗水把床单湿成一个人形,丈夫睡得安静,好像从来就不会有梦干扰。床头灯没关,窗也没关,风吹动窗帘,带来初秋的静谧和凉意。伶俐关窗熄灯,转身上了床。
第二天是周末,一早,伶俐拧了毛巾正给丈夫洗脸,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伶俐开门,是几名警察,他们礼貌地说,小姐,我们可以进来一下吗?伶俐哦了一声,把门拉开。他们进来后直奔伶俐的卧室,把窗推开,伶俐跻身往下一看,一群警察围在下面,一个男人仰卧着,头歪在一边,想必断气已久。一个稍胖的警察说,初步怀疑是个小偷,失足掉下去了,请问你昨晚听到什么动静没有?伶俐摇了摇头。一名警察低头踱出客厅,猛然给撞了个趔趄,抬头看时,才发现是一个足有一米八高的铜人,皮肤黝黑,双目炯炯有神,不怒自威;双唇紧抿,唇角微扬,似笑非笑;铜人脚踏镶有坚固滑轮的铁板,轻轻推动即可行走;最要命的是,他穿了一套水蓝色睡衣,和真人无异。伶俐呐呐地说,是我丈夫……
警察离开时,低声地嘀咕,昨晚小偷死前表情惊恐,是不是看到什么受惊才掉下楼?邻居的声音从半开的门后传来:这女人的丈夫去世三年了,车祸!除了上班,很少见她出来……伶俐是听不到这些的,她的耳朵,总能天然地屏蔽。她沉默地把门关上,这样,伶俐的世界就只是小小的一套房子了。她继续帮丈夫洗脸,给耽搁了一下,早餐时间都过了,还是直接准备午餐吧!伶俐的周末忙碌又甜蜜。她还寻思着,冬天要到了,得给丈夫织一条围巾,让他围着又温暖又英俊。
我把这篇文章发到何枫的邮箱,我想他会看见的,他会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吗?他会知道里面的伶俐就是我吗?而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孤独的人。
何枫一直没有给我回信,我每天都有意识地看邮箱,看微信,我想看到他的出现,看到他说,姐姐,在干吗呢?
有时坐车路过何枫的学校,我总不由自主地辨认着路边那些学生模样的人,他们每一个都像何枫,但都不是何枫。
几个月来,他音讯全无,我确信他不会再出现了。
他像那年夏夜,我努力滚到河里的西瓜,在流水中一沉一浮,就远去了。
我就像树干上的一个洞,何枫对着树洞说完了他的秘密,转身就走了。
六
今年初夏,我接到了何枫的电话。他声音浑厚,我一时恍惚,没办法将声音与他联系在一起。
他说,姐姐,在干吗呢?我们见面吧,我毕业了。
我下班后去了他的学校,他在校门口等我。在灯光下,我看见他似乎长高了,额头上的月牙形疤痕,让他有着一种神秘的魅力。他对我笑了笑,我一时没话,也只好笑了笑。
我们在校园里散步。
他说过几天就回家了,他一直喜欢家乡,喜欢家乡的安静。老爸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他希望回去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县城住腻了,就回到农村住住。他说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考了车牌,以后工作赚钱了买辆车,往返县城和老家就容易多了。
我说好的好的,真是太好了。
何枫没说这段时间为何不联系我,我也没问,对我来说,这好像也不是问题了。有些人出现,有些人消失,有些人出现又消失,有些人消失又出现,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
何枫说,姐姐,你有空就到史县来吧,我会好好带你去玩的,我知道你喜欢我的家乡。
我说,好的,等你要结婚了,我就去吧,参加你的婚礼,这样会比较好。
他有些愕然,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在送我去车站的路上,他似乎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说,姐姐,姐夫去世了,你就打算这样独身下去吗?——他究竟还是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
我迟疑了一下,说,他并没有去世,他只是离开了我。他和她回到了老家生活,听说很幸福。因为这个,我几年都没回过家乡。当年我希望他是去世而不是抛弃我,所以我写了那篇文章,但现在,我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把隐藏多年的秘密告诉了何枫。
我没有抬头看何枫的表情。当我们听别人故事的时候,我们想的其实是自己的心事。我对何枫的故事如此着迷、投入,大概是因为他的故事里也潜藏了我的心事,在他的讲述里,有我熟悉的旧的那部分,也有我没有经历的新的部分。这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深陷其中,而我用尽全力,不愿脱离。
我坐在车上,看着何枫朝我挥手。
他还是那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少年,那个有故事的少年。他没有变,只要我一直相信,那么他就不会变。
这样,他的离开也就不会让我悲伤。即使在这个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或者找到了,而他们也会像何枫一样,在某天离开,即使这样,我也不再悲伤。
下车的时候,看见路边卖唱的一个艺人,他几乎每晚都在这里唱歌,旁边的台阶上坐满了农民工。我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好好听他完整地唱完一首歌,今晚我想听一听。我站着听了一会儿,觉得累,就挤在台阶上坐下了。
他唱了 《春天里》,唱了 《蓝莲花》,还唱了很多我熟悉的歌。晚风吹来,裹挟着浓浓的汗臭味,而我浑然不觉,只安静地听着,我一直不知道原来他唱得这么好。
在人群散去的时候,我依然坐在台阶上,他也没有停止歌唱。
一个路过的中年人走出去很远了,突然又折返回来,他把一张纸币放在了破旧的琴盒里。他身材高大,表情严肃。在他弯腰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低头掉落的泪水。
这是一个落寞的男人。落寞的男人都有故事。落寞的人都有故事。
我也把一张百元的纸币放在了琴盒里。
责任编辑 杨 希
陈会玲
广东韶关人。有诗、散文、随笔、评论见于各报刊。作品入选多种选本。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