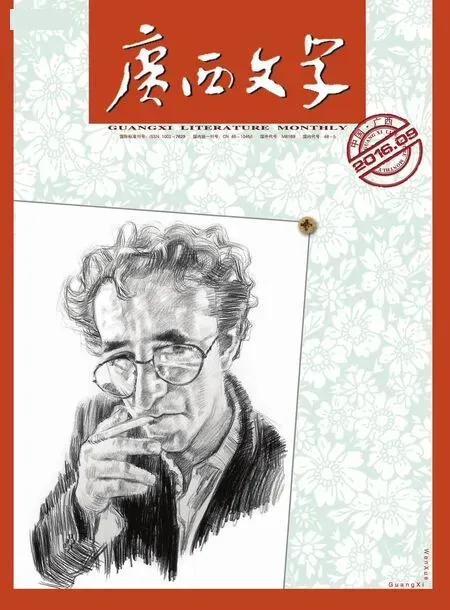正午的阳光
丁 艳/著
三舅爷坐在小凳子上,跷着二郎腿,尽量让那两只锃亮的大皮鞋在正午的阳光里晃来晃去。可是不管他怎么晃,那双鞋都比不上他那个通红的酒糟鼻子更显眼。
“这大热天的,你穿那么厚,不热啊?”卖烤苞米的妇女头也不抬地问道。在她眼里,三舅爷肯定比不上她那香喷喷的烤苞米更招人稀罕。
“不热,热啥呀,我这样穿都习惯了。不这样穿,我们公司的老板不让!”三舅爷说着,下意识地扯了扯系在脖子上的那根皱巴巴的红领带,又顺便偷偷抹了一下顺着额头的“沟渠”淌下来的汗水。那里的几道“沟渠”并不深,只不过是轻微的水土流失,毕竟三舅爷才四十几岁,比他手中的烤苞米老一点而已。
“我请你下馆子吧?”三舅爷歪着脑袋眼巴巴地看着烤苞米的女人,试探着问。这女人虽然也比烤苞米老那么一点点,不过脸蛋还算细嫩,在三舅爷眼里,她绝对比这些烤苞米更招人稀罕。
“我不去,我不饿。我要是饿的话,吃苞米就行了。”
“嗯,你们乡下这苞米是挺好吃,挺香!”三舅爷使劲吧唧吧唧嘴,用袖口抹了抹嘴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你要是陪我去吃饭,我就常来买你的苞米。”三舅爷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女人的脸,仿佛那有一块粘人的吸铁石。女人这回抬起头瞟了三舅爷一眼:“你上那儿去,那儿——洗脚房。”她用下巴往街对面挑了一下。“洗脚房?”三舅爷茫然地重复了一遍。不过当他顺着女人的目光望过去,看见对面一个挂着烫金牌匾的门面前,站着的穿戴十分性感的女人,他瞬间就明白了。他把手伸进兜里,摸了摸兜里那卷汗湿的钞票,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这时候,从那牌匾下面的门里出来了一个男人,那男人与其说是魁梧,不如说是肥胖,那肚子,仿佛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不过,他脖子上挂着的那条金链子,和他的身材倒是十分匹配。三舅爷看着那条金链子,心里凉了半截。
“敢上那儿去找乐子的,可都是有钱人!”烤苞米的女人说这话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三舅爷一眼。这一眼,让三舅爷觉得好像有一只蝎子在他的脸上蜇了一下。他缩了缩脖子。可他的手马上又碰到了那卷钱,这让他一下子又来了精神。他掏出钱,一张一张地打开。这个动作,他足足持续了五分钟。最后,他从最里面取出一张十元的,递给烤苞米的女人:“拿去吧,我没有零钱了,你也不用给我找零了,剩下的给你当小费!”“小费”,三舅爷在心里嘀咕了一遍,这么时髦的词儿自己都能说得这么溜,他不禁有点扬扬得意。在这儿坐了这么半天,他不过就吃了两棒苞米而已。烤苞米的女人接过钱,这回,她冲他笑了一下。这一笑,更增添了三舅爷的优越感。他站起来,在正午的阳光里踱了几步,让那锃亮的大皮鞋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不过,他终于没有到街对面去,而是踱进了烤苞米摊位后面的一家小吃部。
小吃部的门正好对着街对面的洗脚房。三舅爷点了一碟花生米、一碟熘肝尖,就捏着酒盅有滋有味地喝了起来。对面那个女人还在洗脚房的门口站着,每过去一个男人,她都会送上媚生生的笑声。三舅爷始终觉得那笑声一粒粒都落在他的碟子里了,嚼起来绝对比花生米更脆。而且,他发现,门外烤苞米的女人不时地回头往屋里看他,这更让他心花怒放。于是,他就着那个女人的笑声和这个女人的眼神儿,把自己的脸喝得跟那熘肝尖一个颜色。不过,那酒糟鼻子也不逊色,还是一样显眼。
把碟子里的最后一粒花生米送进嘴里,把杯子里的最后一滴酒倒进嘴里,他打了个饱嗝,冲着服务员招了招手:“服务员,埋单。”喊完“埋单”这两个字,他在心里对自己又佩服了一遍。于是,他又掏出了那卷钞票,一张一张地打开,这个动作又足足持续了五分钟。
他出了小吃部的时候,街对面的女人早就钻进屋里去了,这让三舅爷多少有点失望。经过烤苞米的摊位,他望了望卖苞米的那个女人,她的脸被太阳晒得,这会儿倒真有点像她的苞米了,不过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他又买了两棒苞米,而且付完钱还没忘重复了一句:“你们乡下的苞米真好吃。”
说完这句话,他就又把那双大皮鞋放进了1995年夏日的一个正午的阳光里。那是他第一次去县城里存钱,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存折。他也第一次觉得自己终于有资格不再像个乡下人,可以像模像样地当回城里人了。不过,直到2014年他去了县城的儿子家定居,真正成了“城里人”,他始终没听到,当初,当他那双锃亮的大皮鞋把水泥地面上的阳光踩得吱吱响的时候,他身后那个烤苞米的女人嘀咕的那句话:“老山炮!”
嫁接青春
早上七点,一男一女两个半大孩子迷迷瞪瞪地从网吧出来。还没来得及痛痛快快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凛冽的寒气就封住了他们的口鼻。被风卷起的雪粒儿也直往大脖领子里钻,两人几乎同时打了一个激灵。木木地对望一下,这才清醒过来。
在网吧里过夜叫包宿,一晚五块钱。
男孩儿上半夜打“坦克大战”,下半夜靠在椅子上睡觉;女孩儿上半夜看《大长今》,下半夜趴在桌子上睡觉。此刻,女孩儿裹紧了单薄的小棉服,仿佛也单薄成了一片长腿剪纸,抱着肩膀低头向南走去,男孩儿往北走了几步后又折回头追上了她。他们不认识,碰巧在网吧座位相邻,又被清场时一起轰了出来。
“我叫刘大可,你这是要去哪儿?”
“回学校啊,我在八中。”
“我请你吃一碗面条吧,热乎热乎再走。”
一晚上他都在目不斜视地打游戏和睡觉,看样子不像坏人,而且,这张面孔以前也似乎在这个网吧里遇上过几回。相比于饿,女孩儿这会儿更冷,“热乎”俩字着实吸引了她,她跟他走进了路对面的小面馆。吃面,刘大可吃得很卖力气,稀里哗啦地,她也就不再害羞,大大方方地吃面,吃完之后她说:“我叫杜采莲。”
“你读高几?特别想去上学吗?我是九中的,读高二,我不想回学校。”
“我也读高二。”杜采莲没回答他的第二问。
“走,我带你玩去。”
杜采莲第一次进台球厅,不是街边上一间破屋、一张笨案那种,而是真正的台球、真正的厅,三十几个蓝色的案子稳稳地坐在蓝色调的大厅里,加上一些安静地炫着的射灯,说不上哪里来的华贵大气。一走进去,杜采莲立刻觉得自己寒酸得要死,在门口使劲儿地磕净鞋上的雪,才敢迈进门槛。她就坐在一边,看刘大可一个人围绕着案子打来打去。她看不懂,但很着迷这种状态。
刘大可给她叫了蛋糕,叫了咖啡,也叫了四色冰淇淋。眼前,高高瘦瘦的刘大可是一幅画,冷冷的,酷酷的。入画出画,杜采莲边看边吃。
“你是不是父母也离了婚?”打了几杆后,刘大可坐下来。
“你怎么知道?”杜采莲大吃一惊。
“单亲家庭的孩子都有种不一样的气质,我一打眼就看得出来。比如眼睛从来不敢盯着人看,比如遇到陌生人不肯先说话,比如对声响很敏感。昨天你从网吧出来,抱紧自己的肩膀的那个动作,立刻让我有了判断。”
杜采莲点点头,接过话茬:“我上一年级时父母就离了,我爸在天津打工,我妈嫁到山东,谁也不管我了,这些年我跟奶奶过。”看着刘大可询问的目光,她补充了一句,“我住校,奶奶不知道我包宿。”
“同是天涯沦落人哪。”刘大可低声叹了口气,“上初一时我父母离的,我爸是个软蛋,根本就养不了我。我妈找了个老大款,跟他们过倒是既不缺钱花,也不缺自由,可就是不快乐。”
“他们不能保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有什么资格生孩子?你说,你说!”杜采莲从来就没这么大声说过话,白净的小脸涨得通红。
“都是罪人!”
两人碰了碰杯,啤酒一饮而尽,呛得直咳嗽。
下午,他们去了录像厅。“我要看《狮子王》!”杜采莲脱口而出。她被剧情牵动着,看得很投入。演到老狮王坠崖时,刘大可的手握了过来,她没有拒绝,只是又打了个激灵,这回像触了电。刘大可吻了杜采莲一下,嘴尖轻轻触了她的脸蛋,她感觉像一只瓢虫落在腮帮上,下意识地拂了一下。
看着看着,银幕上闪现出一组不一样的镜头:父母一左一右陪采莲看《狮子王》……从电影院走出来,星斗满天……妈妈问她从电影里看到了什么,她想了想说:“不论啥时候都要充满希望。”爸爸抱起她亲了一下:“丫头真聪明,要说到做到呀。”……那是十年前,她七岁生日。
采莲哭了,没等电影演完就走了出来。
“谢谢你今天的招待,我得回学校了。”她一边用脚踢着马路牙子,一边小声说道,“我想明白了。摊上啥样的父母咱无法选择,可咱到底该咋活咱自己能作主。不能就这样沉沦下去,不能在别人的白眼里活一辈子。刘大可,一起努力好不好?”说完,她勇敢地抬起头,直视着那个男生的眼睛。看到刘大可点了头,她继续说道:“那好,不再上网,不再联系,一起加油,决战高考!”
他们是退着离开的,一个用力地挥着拳头,一个把两根手指高高举向天空。
高考后,杜采莲特意到九中看榜,刘大可考进了一本。杜采莲知道,刘大可也会到八中看榜的,自己的成绩值得骄傲。
十二年之后,在机场大厅里,一个戴墨镜、穿狼爪徒步装、背双肩包的高个子打杜采莲身边经过,她杵在那里,她确信那个人就是刘大可。
杜采莲回过神来后,随口说了句“看样子他还好”。她的新婚丈夫回过头来抚摸了一下她的长发,柔声问了句:“亲爱的,你也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