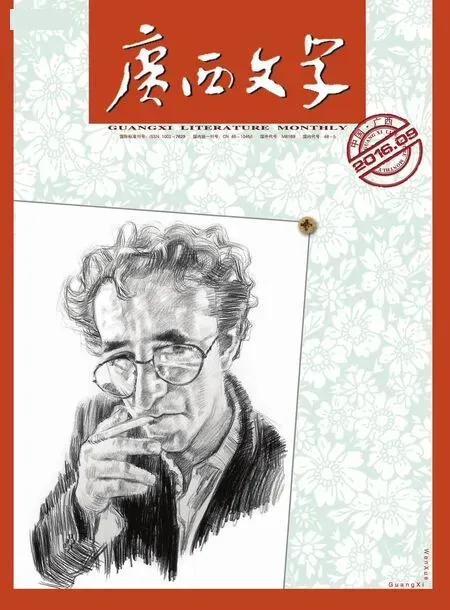散文新观察之罗南篇
刘 军/著
曹魏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倡“文以气为主”之说。时隔不久,南朝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气韵生动”的美学命题。“气韵生动”之说经过后世艺术家的不断阐发,形成了古典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原点,同时也演变成古典绘画、书法、音乐的一个美学标准。一个颇堪玩味的事实为,“气韵生动”之说尽管乘风破浪,却难以在古典文学(诗学)领域蔚然成风。细细思量之,却不足为奇,一方面,作为辞章大国,古典时代文的概念多对应文化意义上的文章范畴,其中包含了许多非审美意义上的杂文体;另一方面,即使落定于诗文范畴,“气韵生动”之说对于史传体、论说体散文,对于重理趣的诗歌,似乎很难施展开手脚。比较而言,才性、气质的理论话语能够恰切地统摄诗文范畴内的各种体式。
本期《散文新观察》栏目,迎来了广西作者罗南的《药这种东西》。作为长达万言的叙事散文,在接受层面,这篇文章带给我们最强烈的一个审美效果,即气韵生动。按说,叙事散文开掘的方向为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思想之力,以及细节、场景的驳杂性等因素上,与强调生命律动、情思流畅的“气韵生动”之说形成了天然的排斥效应。那么,罗南到底依靠什么让天堑变成坦途?在我看来,“气韵生动”审美效果的发生来自以下三个要素。首先是叙事节奏的推进,作者的讲述从容不迫,内外有序。四伯父作为一个乡寨的草医,自身的精神投射力量足够强大,对他者是职业精神的专注、细致以及不计利害得失的施与,对四伯母则是情深义重,不离不弃,甚至临终前对待药物的奇特态度,皆彰显出其异于常人的一面。作为乡土灵魂式的人物,他的一生注定跌宕不平。作者在处理这个主题上,并非简单地将对象异人化,恰恰相反,四伯父在故事架构中一方面是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之间,另一方面又超越于“我们”之上。这两个方面在叙事推进上又构成了一个双行线,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如同琴弦上不同音符的会合,最终抵达一种独特的韵律。其次是情思的提纯处理得尤其漂亮。散文中的亲情或者家族叙事,决定其基本品格的不是情感的浓度与真挚程度,而在于情感的提纯程度。若距离太近,主体的情感很容易被情感的热度所炽烤,以至于执情强物。罗南的这篇散文,采取了童年视角与他者视角交相使用的方式,进而获取了审美距离的完成。在情感的净化与提纯方面,《药这种东西》让我想起乔叶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在情感的处理上,皆跳出了亲情叙事通常的窠臼,以生命来观照生命,激发生命本来的颜色,即王国维先生所言的“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基本原则。四伯父只是一个情感投射的基点,其背后则有一个纵深的空间,即乡土世界中绵延至今的人伦秩序和文化关怀。最后是语言的丰茂。诸多诗性的词语,具备爆发力的句子,如瀑布般嵌入文本之中,构成了错落有致的语言景观。
对照《散文新观察》第四期推出的李颖的《虚幻的鱼骨》,同样作为家族叙事之一种,罗南的《药这种东西》为读者提供了如泉水喷涌般的表达形式。两者所选择的不同路径,也在暗示我们,在找寻“熟悉的陌生人”的旅途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以及这可能性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