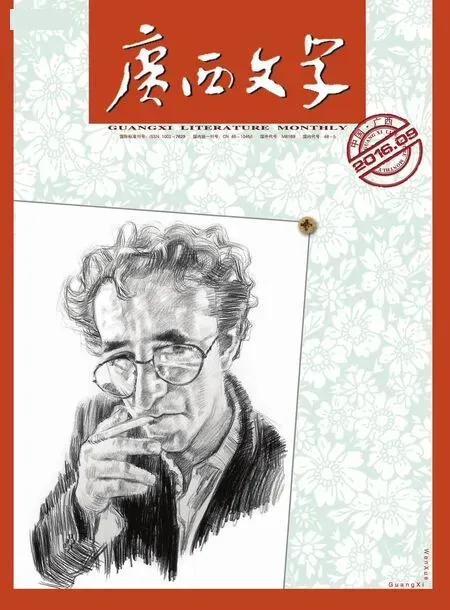切 口(组诗)
赵 琼/著
母亲左腿的腿弯处
长了一个肿瘤
医生说是良性的,切个口
就能将瘤体取出
九十三岁的老人了
在医院里陪着母亲的这几天
我时不时地,总在关注每一个
从我身边经过的大夫
总想着,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
能在我的腹部切口
能将我的担心
也一一取出……
检 讨
面对
稗子身边,那一株
昂首的谷穗
父亲将头
低得,不能再低……
篝 火
飞蛾,一只接着一只
进入火焰的身体。无视
正在往火里添柴
那个人
欢鸣的灰烬,肉香四溢
一次,一次
撞痛
观火人的前胸,以及后背……
洗浴中心
除了肥皂,除了水,除了搓泥儿
传统的,绝不需要另行更衣
拔罐,刮痧,捏骨,松筋
都被摆在一览无余的大厅里
有别或无别的浴衣,罩着
形色各异的男人和女人
这一些,都不是洗浴中心
这个名词的根本含义。在这里
同为名词的包间、包间上的门
以及门上的锁,全都被一个动词
锈蚀至暧昧
在这里,还有,我的一个亲人
她戴着一顶帽子在工作
帽子上,有一枚,同样被锈蚀了的
帽徽……
甲
在体内,被排挤,还以为是出人头地
仍一门心思地去扩大,自己的
疆域
一柄剪刀,就攥在
放它出世的十指之间,时刻准备着
将无尽的贪欲
一一剔去
秋天里的一种生活
挂果太多的那根树枝,“咔嚓”一声
断了
母亲,正在灶间,烧火
柴烟,与母亲的白发,缠在了一起
落在地上的树枝和那一些还未熟透的果
引来了一位拾柴火的老人
和一群
前来觅食的飞鸟……
在新疆拾棉花的二姐
在离家数千里的新疆拾棉花的二姐
昨晚,在雇主的家里打来了电话。
她说:新疆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雪。
雪太大了,也太白了,她明明知道
她还没有来得及拾完的棉花就在雪里
她在雪地里扒了两天了,就是找不到棉花……
听完了二姐的话,母亲冲着电话就骂二姐:傻!
骂完了二姐的母亲,一头便扎在了灶间
让风箱的“吧嗒”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
一团又一团的柴烟,从锅灶直往外窜
雪的雪白,像棉絮一样,顷刻之间
就把母亲,裹成了一团……
秋天里的一只蝴蝶
忽然,就被自己一个
举杯喝水的动作
吓了一跳
杯子,在眼前一沉
像是,与另一个
举着杯子的人
在碰杯
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一阵秋风,从窗口
吹进来,又吹出去
一只蝴蝶
绕着我与杯子
不停地翻飞
此刻,就想着
我这一生,就应该像这蝴蝶一样
只做两件事:
生于斯
归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