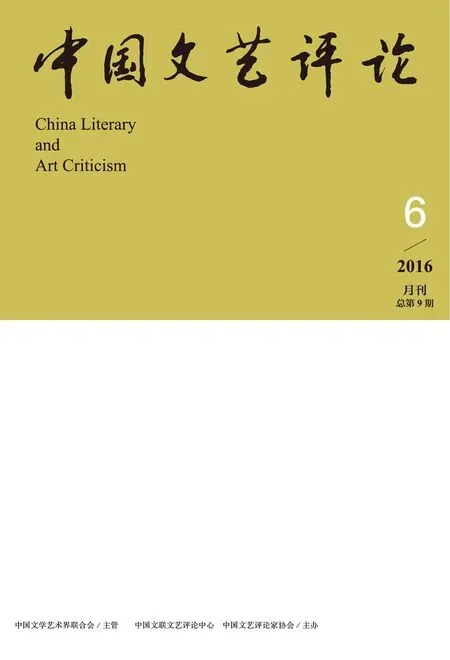走上舞台的鲁迅
—评《大先生》的剧作与导演
林荫宇
走上舞台的鲁迅
—评《大先生》的剧作与导演
林荫宇
约两个月前,描写鲁迅的舞台剧《大先生》在北京上演,引起知识界、文学界、戏剧界的众多关注,人们争相观赏,以至一票难求,遂成圈内盛事。至今,其余音、余兴仍缭绕未尽。
座谈会上,编剧李静女士表达了对出品方、制作人、协作单位及诸多朋友的感谢,诚挚之情溢于言表,称大家为站脚助力的“贵人”。
其实,真正的“贵人”是鲁迅。所有的创作者、参与者,乃至观众都是带着对鲁迅的尊敬、热爱,抱着或探究或质疑的态度来关注《大先生》的。
一、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
我于2014年夏第一次读到李静的剧本《鲁迅》(《大先生》原名)。
阅读伊始,即为开场不久的朱安和鲁迅的一段戏所震撼、所感动:
(以下有引号者均为剧本台词或剧本提示。)
作为原配妻子朱安在丈夫即将远行时,前来送别,并想索要一件东西——合理合情;
鲁迅答应时顺口叫了声“安!”
朱安为结婚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丈夫竟唤她名字而“茫然”……似为解释自己的犯疑,又似抑压自以为不该有的心的涟漪,怯怯地说了一句“女人有了名字,就会不安分……”
鲁迅顿时“不耐烦”起来,斥她“又来了!”
朱安终于“下决心”,向他要一次“笑脸”,并就此倒出心里的苦汁:“……我这辈子过得好冷啊……连路边的讨饭婆我都羡慕,因为她能得着你的笑脸、你的安慰,你放在她手里的钱,还是温热的……可是,当你直起身子看见我时,笑容就冻在脸上,眼睛也结了冰……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可怜每一个受苦的人,却从不可怜可怜我呢?我也是人呀……”“毁了我,成全了你。”
鲁迅“愣住了”,嗫嚅道“你也是人?”“毁了你,成全了我?”他企图辩白,却浸于自怜:“我怕走近你,我怕你忍耐顺从的鬼魂钻进我的身体。”“我也不能退还你,就像退还一件不中意的货品。”
朱安似被电击刺痛一般,“受伤地”无法相信自己是“鬼魂”,终醒豁“冷笑”自己在丈夫眼中只是“货品……”而已。
——不足两页的剧本片段里,鲁迅从敷衍容让→不耐烦→愣住→辩白→自怜;而朱安从随顺→不自信→下决心做一回自己→鼓起勇气,质问反诘→自己的境遇憬然于心。
剧本中写道:朱安“伸手摸向鲁迅的脸,作撕下一层状”——这就是朱安向丈夫索要的东西,一张鲁迅笑着的脸皮——多么奇特的构思!撕下一张脸皮作一生的纪念物!
阅读到此,我想象朱安伸出的那只手臂,迟疑、怆然,本应夫妻肌肤相亲却始终陌同路人的脸……撕揭脸皮时,能想象到朱安的孤、寂、酸、苦、恨,而它们的背景是数十年日日夜夜渴望、冀盼的被爱。
这不是现实生活里的朱安,在不少记述鲁迅文章里的朱安,是个沉默寡言、安于宿命的妇人。这个醒悟的朱安,是李静心里希望的朱安,是李静认知里应该的女性。李静要用这个朱安,对反封建礼教的旗手鲁迅进行谴责,从另一个视角作出李静对鲁迅的评判。
我不是鲁学研究者,我和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一样,只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文学青年的导师、中国文化的旗手、反封建礼教的斗士,崇敬他,尊重他。虽然对他文章的遣词造句行文风格有些许不习惯,对他让妻子孤守一辈子空房,让许广平为他生儿育子、侍奉左右、当伴侣无名分一辈子而心存疑窦,却不敢提出质疑而默语。李静的《鲁迅》展示了一个多么不一样的鲁迅!一个多么不一样的朱安!我为之被震撼,被感动。
继续阅读剧本,到后面,这类简练而丰富的行动性很强的戏剧性场面几乎没有了。我颇讶异,但是,我依然会被引发思索。
在剧本结束前的倒数第三段里,“天堂”的喧哗声中,众鬼扭摆,最初出场的阿Q、王胡、小D、闰土也现身地府,音乐起,鬼众对鲁迅像举行膜拜仪式。
黑衣青年问鲁迅:“过瘾吗?鲁迅先生?”
鲁迅回答:“不……这不是我想要的……”
黑衣青年追问他:“瞧!您怜悯的小人物都当家做主了,您痛恨的大人物都被专政了,读书人都在忙着脱胎换骨了,您呼唤的一切都在天堂里实现了,您已经成了他们的旗帜,他们的导师,他们的教主,这下您满意了吧?”
鲁迅决绝地吼道“不!”他环顾这个所谓的“天堂”,其实等同于“噩梦”,他捡起从包裹里滚出的几个西红柿,称它们为“大脑”,它们“光滑、红色,没有褶皱。空空如也的大脑”。“在这个天堂里,大脑必须都是这样的”。他愤然地把这些西红柿扔出去:“拿去吧模范的大脑、安全的大脑、空空如也的大脑!……都给你们!我只想回到我的坟墓里,盯住所有的罪孽。”
——李静是想告诉读者,无论何时何地,即使鲁迅百年之后,倘若他还活着,他是拒绝充当教主、旗帜、舵手的!
李静,资深记者,著有小说、随笔等,《鲁迅》是她的戏剧处女作,历时四年,读遍鲁迅及相关鲁迅的书籍文章,十易其稿而写成。正因为是首次涉足戏剧创作,她曾困顿但又不会拘囿于因袭循旧的“剧作法”的羁绊,她在《自白》中写道:“……一个令我绝望的难题: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而一部戏如果不表示主人公复杂深刻的内在世界,只表现他表层的性格/人格,有啥意思呢?”她想写的是鲁迅的思想、精神、灵魂,想写鲁迅的沉思、自省,写他心底里的祈望与隐情……那是玄想联翩、四蹄翻飞的行空天马,但这些又必须附着在鲁迅身上,于是,她想到了“梦”,想到了“意识流”。(见《写作的灵魂想象力》《一个戏剧菜鸟的“鲁迅”编造史》)于是,她写了一部没有故事、没有贯串情节、不重在刻画人物性格的思想剧、灵魂纠葛的剧。她把总的规定情境设置为鲁迅先生的弥留之际,总的行动是弥留之际的回眸一瞥,对一生历程的回眸一瞥,对自己念兹在兹的事与人的回忆与眷念。李静说:“我感受到了意识流的气息”。
那年,我是作为老舍文学奖戏剧部分终审评委之一阅读的《鲁迅》,它的结构、叙事形式在七个入围剧本中迥异卓特、独树一帜。我的一票投给了《鲁迅》。
但是,怎样把《鲁迅》的文字形象转换成舞台形象?哪位导演能挑起这副重担?我十分期待。
二、找到恰当的舞台总体样式是导演创作的首要成功
2016年3月底,《鲁迅》改名为《大先生》,在北京首演。导演是年轻的王翀。
王翀是年轻的“老”导演,说他“老”,是他老在排戏。十多年来,他锲而不舍地致力于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作品的翻译与导演,并借鉴用于本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作品的创作与拓展。他艺术视野开阔,善于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他是国内最早一批运用大屏幕加入戏剧场景,现场摄影同步录放之舞台手段的导演之一,从《中央公园西路》到《雷雨2.0》再到《群鬼2.0》,其间还有好几个《×××2.0》,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而且有了自己的发展与创新。
这次《大先生》的舞台呈现,王翀再一次显露了他的聪明才智。他把“傀儡的表演”定为全剧的舞台总体样式,全剧只有鲁迅由演员扮演,其余所有角色的扮演均由演员当场操作傀儡并配音说台词。这是他从台湾偶剧界借鉴而来的。
这一舞台呈现总体样式与剧作内容是相一致的。
剧作内容,按照出版者在《大先生》书的外封皮扉页上写的是“从鲁迅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李静曾说“梦剧结构……”我则将其概括成一句,即鲁迅弥留之际的回眸一瞥。
弥留之际,意识是模糊的,涌现出来的那些人那点事都是散瓦碎片;而回眸一瞥,反观自己的一生,他孜孜念念、萦绕盘桓于心的那点事那些人是纠结了一辈子琢磨了一辈子的,在鲁迅的潜意识里,那是清醒的。
在模糊和清醒之间,在零零散散和(作者想表达的)鲁迅整体灵魂之间,必须要有一个“整合”的舞台语汇。王翀找到了,就是整台的傀儡表演烘衬、凸显人——鲁迅的扮演。
那些奇奇怪怪、形状各异的傀儡,做着摇头摆尾、龇牙咧嘴的动作,似虚似幻;扮演鲁迅的演员赵立新那低沉的或激昂的心声的坦露,实实在在地引着观众沿着鲁迅的心路去思索。
那些傀儡是请赴台湾学艺的当代艺术家黄姒制作的,个个瑰奇灵怪。
那个胖子傀儡鼓着凸眼泡、龇着大暴牙,长歪了的身子由操控男演员与半个傀儡身子组合而成,其造型粗陋诡怪。由女演员操控的瘦子傀儡有一双特大的眼睛,一对大耳朵附着在小脑袋上,脑袋下面是一长根粗粗的塑料软管,其造型显得精明狡诈多变。——两个可笑可气可鄙的形象,但不会引起观众的恐惧感或憎恨感。
朱安傀儡则是由褐色面具的头部和两幅硕大的半透明褐色羽纱构成,出场时操控演员将傀儡面具放得很低,褐色羽纱围着她——立即感受到朱安的恭谨依顺。
而许广平傀儡的构成,有女演员操控的秀丽的白色面具、修长的手臂,巨幅、超长、铺满整个舞台台面的蔚蓝色裙摆,加上灯光如洒下缕缕阳光的婆娑摇曳的树影,鲁迅与之两情相悦,犹如在蔚蓝色的水面上,相随相伴、左挪右移、舒展的台位,是全剧唯一的抒情场面,让观众窥视到鲁迅先生内在的铮骨柔肠。
傀儡的舞台处理煞是好看,从演出开始,观众就目不暇接,乐不可支,适应了演出市场的需要。
傀儡的运用,对操控傀儡之演员的肢体表演、台词的说念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有了更大的展现空间。
三、舞台导、表演手段宜简宜精忌繁杂
《大先生》是王翀首个大剧场作品,他又年轻阳刚,感觉他使出浑身解数,恨不得能排得好上加好。但毕竟年轻,缺乏十足的经验,难免有的过头,有的考虑欠缺,想得不周全。
(一)全台唯独鲁迅由演员扮演。一开演,舞台灯光一亮,观众全都知道演员赵立新不再是赵立新,他饰演的是鲁迅,他说着鲁迅的话,充溢着鲁迅的思绪与感情,传递着鲁迅的精神。然而,这个鲁迅不是人们熟悉的穿着长袍、剃着板刷发型的鲁迅,而是穿着白衬衫、牛仔裤、系带短靴,完全一个现代男子的装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服装设计,而是一个有深刻内涵的舞台处理。
这里,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演员赵立新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鲁迅,又是当代人。这个当代人不仅仅指赵立新本人,而是指一整代人。赵立新同时是现代人与历史名人的载体,是现代人与历史名人的合体,两者要合二为一,成一个整体;有时又要明确地告诉观众这是两个“人”。在赵立新身上,现代人与历史名人鲁迅,要融合,要碰撞,要对峙,或许还有对抗或妥协。饰演这样的角色,演员的表演会有极大的张力,对演员来说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与挑战性。
我们有幸在北京舞台上见过这样的人物处理:1987年10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红茵蓝马》,演员张秋歌饰演的列宁,就是当代人与历史名人列宁的同一载体。今年,2016年3月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由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演出的《俄狄浦斯》,演员康斯坦丁·基里亚克饰演的俄狄浦斯,就是当代人与历史传奇人物俄狄浦斯的同一载体。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两台演出都是外国导演,前者是苏联导演马·扎哈罗夫;后者是罗马尼亚导演西尔维乌·普卡莱特。
王翀成了中国导演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惜他没能了解“蟹钳”的力量,因此,以现代装束扮演鲁迅的舞台处理,只是徒有其表,缺失了深层的内涵。
(二)李静在剧本中写了“椅子”,前前后后都有“椅子”;开场有“椅子”,最后结束有“椅子”。明显地,“椅子”是个象征。
剧本伊始,鲁迅极力想挣脱“椅子”,他说仿佛椅子长进了自己的肉里。剧本接近1/2处,再次提到要挣脱“椅子”,鲁迅说:“即便没有对的路,也要走,不能老是坐在椅子里。”“就算你长在我肉里,我也要挣脱你……烧掉你……”鲁迅再次陷入跟椅子作战的状态。至此,可以理解“椅子”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学习的、传播的、滋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仿佛已经与他的肌体合为一体。而在他追求平等、自由、个人权利的道路上,中国传统文化又成为束缚他思想、精神、灵魂的藩篱,他要挣脱它。
而到了剧本2/3处,再次说到“椅子”时,变成执政官对青年人的指责了:“你们举着大旗,向我的椅子发起进攻,你们以为掀翻了我的椅子,自由就会到来。错了!椅子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有坐在椅子上的人和跪在椅子下的人。”这时,“椅子”十分明确地成了专制权力的象征。
剧终前,鲁迅对青年们说:“你可以掀翻罪恶的椅子,但不可以寻找新的借口再爬上去!”剧本提示里写道鲁迅吃力地跟椅子挣扎,终于掀翻椅子,他又点起火来,天幕现出一把燃烧的椅子,慢慢成灰。鲁迅站立不动。收光。——在这个场景中,既有鲁迅的“挣脱你……烧掉你……”又有“掀翻罪恶的椅子”。那么,“椅子”象征什么?李静把专制权力的象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叠加起来,交错起来,模糊起来,不甚确定起来。
我并不认为李静这么写就好,起码,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或是专制权力,都不可能烧尽,“慢慢成灰”,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没有明确指向是比较合适的,带有了一定的思辨性。
而王翀的导演处理,旨意比较明显。一把硕大无比的红色太师椅框架占据了整个舞台,舞台后区,一个魁梧身躯的塑像稳坐在太师椅上,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然而,旧式的中山装、略显臃肿的体态,又略带反讽意味。
演出过程中,男子的头部悄悄地转了过来,那不是一张脸,而是空空如也的头颅里置放着一把红色太师椅。剧终时,鲁迅像攀岩一样,爬到最高处,奋力地拉出空脑壳里的那把红色太师椅,把它扔了下来。
王翀的舞台处理,指向过于明确,甚至有点犯傻。艺术创作讲究含蓄,从哲学概念上讲究模糊、不确定,这样就有了多种可能性的解释,并提供给观众产生思辨的快感。
(三)李静在剧本创作时有一个设想:四个女性角色——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和许广平及弟媳羽太信子——都由一个女演员扮演。这是希图用一种扮演的方法表达鲁迅对整体女性的观点、感受、思想与情感。
王翀在二度创作时没有实现李静的设想。他首先删去了羽太信子,使戏的枝杈变得干净了些,这是好的。母亲、朱安、许广平处理成三个傀儡。后两者已前述,母亲则是一个硕大的白色头颅,在高高的舞台顶部的吊杆上,俯视着鲁迅,对下端的鲁迅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那是伦理道德的压力,封建礼教的压力。
朱安、许广平、母亲的三个傀儡都很悦目、生动,导演和演员都赋予了傀儡各自人物的情态,就各个片段而言,也都表达了鲁迅与每个“她”的关系,以及他的思索与自责。
然而,鲁迅与这三个女性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相互渗透、互为推力的。鲁迅说:“像所有的孝子那样,为了减轻对母亲的歉疚,假装对她安排的妻子满意?像所有的圣徒那样,把对弱者的怜悯,乔装成对一个女人的爱?”“我恨地狱,可我竟手造了一个最可怕的地狱却不知道。”“你娶的不是新娘,是母亲的眼泪。为了母亲,眼泪是不能背叛的。新娘啊,你这四千年鬼魂的可怜祭品,你竟透不出一丝儿人的活气和光亮。你叫我怎么爱你呀?”他不得不自称“两面人”。30年代是可以娶妾的,但鲁迅绝对不会娶许广平,让许广平屈居于妾的地位。但鲁迅又不愿与朱安离婚,不愿损害朱安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的地位。
这种攀扯纠缠的关系,简言之,为了对母亲的孝,他残酷地冷对朱安;为了尊礼守教不敢离弃原配妻子,却让许广平名不正言不顺地当了一辈子“小三儿”;可又为了对许广平的爱,半辈子敷衍虚应母亲——如若用一个演员扮演,把母亲、妻子、许广平浑融在一起,那么鲁迅的自省、自责、自悔,是对她?还是对另一个她?会看到鲁迅心灵上非常纠结,说不清,道不明,会看到他对中国的女性,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伦理道德的那种极复杂、极矛盾、无解的困顿。
用同一个傀儡表现三个女性,可能会较困难。用三个傀儡分别表现三个女性,从舞台外部手段来说,会比较好看,但失却了鲁迅心理内在层面纠葛的表现。
(四)王翀导演对舞台外部手段比较熟悉、比较热衷,《大先生》的演出从瘦子、胖子由大幕中缝钻出来开始,舞台上就一直很热闹:高高矮矮的黑衣人,奇形怪状的傀儡,讲到闰土时还有两个另样的小偶;成排成幅成列成行的无数骷髅面具冲上台来,围困、冲破、推倒赶至台下;大鸟笼子,关人、放人;瘦子傀儡拖着的那根粗尾巴(塑料软管)一会儿黑色、一会儿蓝色、一会儿又变成红色,她那两个大眼睛里还有群众示威集会的活动视频;摄影师举着摄像机来回走动,舞台后部的屏幕上不断有同步摄影的内容滚动放映……几乎每分钟都有外部的可视的新鲜的内容展示给观众,真个是: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舞台外部手段看得见、摸得着,容易讨好讨喜,但问题是往往会忽略了、影响了戏剧内容的表达与内在精神的揭示。
剧中,有一段戏是督学、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国学家、哲学家、诗人等众学者开研讨会,他们搔首弄姿、巧舌如簧,一片噪声,其中心内容还是清楚的,即老百姓们必须分等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是秩序、传统!谁想闹平等、自由,就是扰乱社会安定!民主,也得推迟发展,等它个30年也不迟。
王翀的处理很聪明很有趣,他没有浪费人力,没有让众多演员或操控众多傀儡分饰这些角色,而是让饰演鲁迅的演员赵立新用各种地方方言区别各个学者,一个人就开完了众多角色的研讨会!赵立新很了不起,他充分展示了他的语言功底和演技,值得赞叹。
但是,效果怎么样呢?我观看了两场演出,周围观众的反应是一样的,热烈、兴奋,纷纷在辨识:这是四川话!这是东北话,太像赵本山啦!上海话!上海话的韵味差点儿!河南话河南话!陕西话!哪儿啊,是陕北话!山东话,俺家乡话儿哎……观众全然没注意研讨会的内容。
当然,可以把学者们的研讨视作鼓唇弄舌,只要造个气氛就行。但是,从剧本里可以看到正是这些鼓噪者的发言,愚弄、蒙昧了(舞台)场上的王胡、小D、女演员、青年们,连黑衣青年也沦为了“蚂蚁窝里的奴隶工头儿”,鲁迅为此而悲伤、绝望……所以,才会有剧终前他面对观众的那大段独白:别被他们的漂亮话迷惑!盯住罪孽!不要原谅,也不要宽容!宁可把身体痛苦地燃尽,也不可以牺牲自由!
换言之,不清楚学者们的言论,就不知道群众的被愚蒙,就无法理解鲁迅的悲伤,就无法明白鲁迅的呐喊。
王翀注重了外部语言和表演的华丽多彩,赢得了观众的快乐与嬉笑,而牺牲了(让观众感悟到)鲁迅心底里的那份痛……
王翀有些导演构思属于飞来之笔,出人意料、非常有趣。
例如一个盲母傀儡是由两个演员来操控的,傀儡的布衣身子套着两个演员,两个人四只手,甲的右手和乙的左手组成盲母的双手;她们各自的另一只手从傀儡的眼睛里伸出来,手指还不停地微微哆嗦……四只手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尚且算是个职业观众,猜测大多数普通观众会和我一样,对四只手有着极大的兴趣:她们是怎么安排手臂的?这哆嗦的手指是眨动的睫毛?还是流淌的泪水?
说实话,我没有去听盲母说了些什么,只是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理解盲母是来看望被枪杀了的儿子。事后,我重新阅读了剧本,方知并非这么简单。盲母是来看被枪杀的儿子,她恍惚、茫然、迟疑,她说她是听他们说:老婆子!你的儿子被枪杀了。也许,他们是对别的老婆子说的呢,世上的老婆子千千万,世上的儿子也千千万,那就不一定是我的儿子被打死了。她揣着渺茫的希望缓缓离开……读到此,好心酸!
我并不是希望导演处理得让观众和盲母产生情感共鸣,而是应当产生思索,一如鲁迅喊出的“我诅咒所有屠杀者。诅咒所有让母亲失去了儿子的屠杀者。诅咒所有让母亲希望死去的是别人的儿子的屠杀者。”——这不是我观看演出当场得到的,而是观后补课憬悟的。
有趣好玩的舞台外部手段,好看的舞台外部呈现,是需要导演具有海阔天空的艺术想象力和超强的舞台创造力的。但是,导演不能因此而沉溺于一种自我欣赏,当这些外部手段干扰了实质内容的传达,导演就要警惕了。
早已过世的何之安教授曾概括过导演构思的进阶过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简,从简到精。艺术创作讲究“简约”“留白”。
这些年来,有幸在国内看到国际大师的导演作品。彼得·布鲁克的《情人的衣服》舞台处理那么简洁,却让观众深深感受到男子极权主义下的残酷与恐怖;他的《惊奇的山谷》更简练,但让我们体悟到环境的压迫感危机感,个人的特殊才能为社会所不容,竟成为个人生存的威胁。两部戏都传达了当代人的恐惧以及精神与灵魂的死亡。
最近,又看到了波兰导演陆帕的《伐木》和《英雄广场》,舞台上几乎没有大幅度的动作,《英雄广场》里的那两个姐妹倚栏而立,整整一场只有局部的细节的外部动作,却让观众看到她们灵魂的颤抖,远胜过满台跑动。貌似很平静的戏,同样传达了深刻的思想,纳粹主义的复活、犹太人的处境,当代知识界、文艺界的人的生存与人的尊严。
王翀导演还很年轻,正处于上升的发展阶段,更需要及时总结,再接再厉。《大先生》还要继续演出,在导演处理上,尤其是外部舞台手段的使用上,希望能多做减法。
林荫宇:戏剧教育家,国家一级导演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