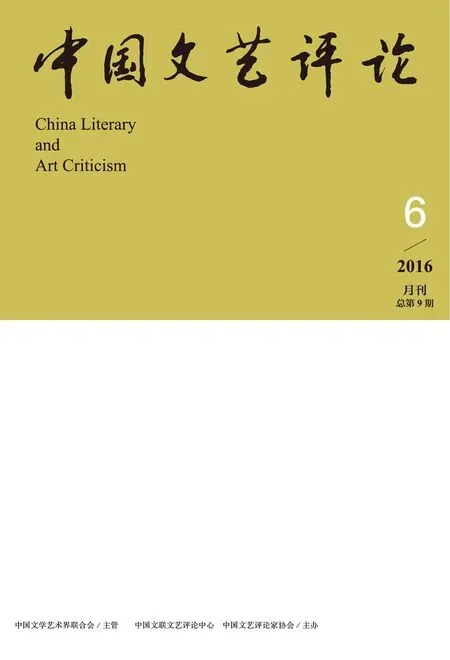情怀与情结:沪剧《邓世昌》的当代镜像
刘祯
情怀与情结:沪剧《邓世昌》的当代镜像
刘祯
近代中国与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中国的国门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洞开的,这也注定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和不幸,使得近代中国被涂上忧郁暗淡的色彩,罩上了因西方列强侵略而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1894年的甲午海战,对中国的发展和努力更是迎头一击,清王朝彻底走向衰败,近代中国满是乌云密布,伤痕累累,浑身的痛。这种痛,没有因为时间,也没有因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甚至也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荡除净尽,但这种伤痛,却也成为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抗争、发奋、自强、进取和振兴的动力源、历史因。时至今日,人类已步入21世纪,中国亦由过去的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走向现代化,但也没有哪个时期有今天这样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和责任让我们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和警醒。
也正因为这样,“邓世昌”这三个字,对于中国人有着非常不同的意义,他代表着一种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意志,影视戏剧作品的演绎已经使邓世昌这一人物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今天,面对同样的历史,同样的历史人物——邓世昌,重读与再诠释,其价值和意义也是全新的。上海沪剧院为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重点打造的大型沪剧《邓世昌》,不同于以往这一题材的作品,有显著的历史视角和时代高度,这在该剧的戏剧结构中有明确的彰显和布局,特别体现在“序幕”和“尾声”中,殒身海底120年两个甲子祭日的邓世昌,所怀想的依然是自己年轻时的一腔报国热血和满寄希望的马尾船政学堂。对于广大观众来讲,海底的沉睡沉静,不能掩盖他们内心的激荡和思考,他们所怀想的岂止是散落的军舰残骸,岂止是殒身两个甲子的邓世昌和他战友的英魂,更是一个民族如何崛起和走向强大的重托与梦想。甲午海战对于中方无疑是败仗,是悲剧,但只有正视这一历史和悲剧,才可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才是负责和勇于担当的应有态度,才能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并超越历史的困局,这应是该题材在当下被再次搬上戏曲舞台并被广大观众接受和认可的原因所在。正如剧中邓世昌沉入海底前,他所惦念的妻子何如真腹中的浩乾,寄托了邓世昌也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期望,这一寓意是显见的也是深刻的。
艺术创作的成熟与成功,特别是在表现重大题材和重要历史人物方面,不在于把历史与历史关系二元对立、脸谱化,也不在于把英雄拔高,只见精神思想而泯灭血肉之躯。还原历史,还原人物真实的面貌和本质,其艺术的憾人力量才会更大。沪剧《邓世昌》聚焦甲午海战,笔触涵括甲戍年夏天到甲午年秋20年间,从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写起,重点则是表现1891年山东威海北洋舰队任职到甲午海战前三四年间的故事,剧中的邓世昌学业优异,求上进,学得一身本领,自强不息,他与他的战友都有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大敌当前,他们毫无私心,努力以自己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御敌抗侮,无奈朝廷腐败,军饷军备不能到位,正常训练不能进行,军饷都发不出,以至于军心涣散,军官们斗志锐减,逛妓院,端烟枪。尽管颓败之势非邓世昌辈所能改变,但他与刘步蟾顶着巨大压力,甚至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去为舰队争取军备拨款。剧中的邓世昌,是军人的楷模,也是现实生活中生动的人,他与刘步蟾等的战友真情、与何如真的夫妻柔情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三年前,刘步蟾因为越级上报受罚,三年后邓世昌为了北洋舰队,为了尽责,策马扬鞭赴津城。“官道路口”一场,邓世昌策马疾驰,刘步蟾扬鞭紧追,非常精彩,极富戏剧性。本来一前一后,一驰一追,邓世昌心急如焚,刘步蟾担心他重蹈自己覆辙,竭力阻拦,“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结果虽然“扬鞭风尘汗衫重”,却最后双双赶赴贤良寺,“不救水师不返转”,兄弟之情、战友之情在共同的目标面前实现了最终的统一。
“战争”题材注定是一场男人戏,何如真这一唯一女性的出场,不是为茅善玉而“定做”的,而是剧情的需要,是塑造新的舞台艺术形象邓世昌的需要。这一人物的在场,不仅形成了戏剧生、旦传统结构模式,更主要的,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使得邓世昌这一英雄的“侠胆柔情”更为饱满、圆润,也使得戏剧的张力扩容。邓世昌作为历史英雄未变,但今天沪剧的诠释,已经不同于以往有的影视戏剧作品一味塑造高大、纯粹的人物形象的表达,在竭力刻画邓世昌英雄形象的同时,也还原其作为普通人的际遇和镜像,不仅展现他报国情怀下的执著、坚定,也描画战友之情、夫妻之情,这正是这位血气方刚的英雄人性最柔软、最鲜活、最动人之处。无疑,茅善玉的饰演,更为有力地衬托了朱俭的角色感和担当意识。何如真对于邓世昌意味着“家”,这个“小家”,有他的妻子、孩子,还联系着父辈,有他的情,有他的爱,有他的留恋和不舍。全剧九场,其中三场涉及何如真,以及邓世昌的“小家”,他与何如真恩爱20年,何如真给了邓世昌各方面有力的支持,也由此,他对“大家”——“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担当就更显得义不容辞,在邓世昌的世界里,这种“小家”“大家”的相互依偎关系是十分明晰的。所以,危难之时,他对国家报效和尽忠是义无反顾的。第七场邓世昌送别妻子一场,彼此清楚这不是一般的分离,而是生离死别,他们真挚感情所透露出的是绵绵不尽的家国情怀,催人泪下。
沪剧《邓世昌》所要表现的不是海战本身,海战只是结果。该剧所侧重表现的是北洋舰队军人的爱国情怀和对造成海战失败自身原因的一种历史反思。与以往这一题材不同之处还在于,以邓世昌、刘步蟾为代表的北洋舰队广大官兵是被充分肯定的,虽有方伯谦的投降之举,但包括对李鸿章、丁汝昌这样的上层人物都予以正面认可。这种转变是基于剧作家思想和创作观念的超越,也是历史研究一种新观点的诠释。确实,李鸿章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以往史学界多认为李鸿章是“主和派”,甲午海战的失败李鸿章难辞其咎。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有学者对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军事、政治、外交上的表现作出了新的评价,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指示”无可厚非,其“保船制敌”的军事方针符合当时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是可取的。至于战争前的外交活动与军事准备,李鸿章的作为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1]何平立:《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李鸿章由原来艺术作品中被否定的主和派,到沪剧中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在对日态度上拥有一种国家立场的老谋深算的大臣,这一变化应该说是巨大的,包括与舰队中下层官兵的关系亦需重新加以认识解读。李鸿章在剧中多处于幕后,是作为正面人物被塑造的,他深谋远虑,重视海军建设,有政治家的气魄,虽出场不多,甫一出场即确立其政治立场和人物定位,他与邓世昌之缘在一句“广东靓仔”中确立,此后,可以说李鸿章的身影和影响在北洋舰队无处不在。第五场北京贤良寺一场的舞台设置和布景很有寓意:龙旗下,一大屏风,一张太师椅。屏风和太师椅都不在舞台中央,而是左侧斜置,远离台口,深居不显,一片静寂中,李鸿章闭目养神,既显其威势,又低调不彰显,这正是对李鸿章的形象刻画,宛如一幅剪影,十分突出。邓世昌与李鸿章有地位的巨大差距,但就爱国卫国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是该剧的一个重要表达和诉求。所以他们的矛盾最终能够化解,邓世昌等能够开启军舰,迎击日军。李鸿章“裱糊匠”之嘲,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历史的实情。丁汝昌作为历史人物颇有争议,此剧中对丁提督的刻画,有其复杂性一面,但基本面把握是准确和可信的。
沪剧是在上海浦东民歌东乡调基础上,借鉴滩簧,后来采用文明戏的演出形式,发展成为小型舞台剧。1927年以后,开始演出文明戏和时事剧。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方正式命名沪剧。沪剧曲调优美,擅长表现市井生活和现代生活,代表性剧目有《十不许》《小分理》《女看灯》《陆雅臣》《啼笑因缘》《阮玲玉自杀》《空谷兰》《雷雨》《秋海棠》《少奶奶的扇子》《蝴蝶夫人》《罗汉钱》《星星之火》等,以沪剧剧种来表现甲午战争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军事主题,在题材风格、行当表演和音乐唱腔等方面,均不啻为一个挑战,显然主创队伍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在保持沪剧剧种风格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特别是两军对峙,大东沟海战一场决战,沪剧音乐的表现有限,作曲家将麒派风格的高拨子融入唱腔,铿锵激昂,与将士们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豪情融为一体,很好地展示出北洋将士那种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表演上对沪剧也多有行当突破,可以说这出戏开拓了沪剧的题材领域,对沪剧这个剧种的发展和创新也具有探索和启示的意义。
该剧对这一重要历史题材有新的理解和突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对沪剧这个都市剧种有新的开拓,经过主创人员多次和反复的加工修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北京、上海演出也取得了极好反响。而就如何提炼成精品、如何打磨来看,还有许多方面可做。剧中人物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对李鸿章的认识和评价,这是一个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剧中这种对李鸿章的塑造,与之前作品中的认识完全不同,它吸收了史学研究的较多成果,也改变了过去对李鸿章这样重要历史人物单一的看法,从一个新的视角努力做到全面、多角度地认识历史人物,目的是通过李鸿章这一人物探究甲午海战失败背后更深刻的制度原因,这是该剧的创新之处。但对李鸿章这样一个以前有定论、曾经被视为卖国贼的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应该更为审慎和客观,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便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并非一无是处,究竟不能和邓世昌等同而观,应进行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和刻画。对邓世昌等人来说,所处时代为国门洞开,西学潮涌而来,特别对掌握现代技术的水师,更是如饥似渴。他们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哺育,也有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处于中西交汇点上,但该剧表现的毕竟是120年前的历史,属于近代史范畴,人们情感表达雅致内敛更有蕴藉之美,人物语言的创造不能过于白话、西化使其缺乏应有的时代感,因此原作中去掉为庆祝邓世昌生日用英语演唱《生日快乐歌》的桥段就十分明智,但是在现有版本中,第一场刘步蟾对邓世昌夫妇所说“祝你们幸福!”“祝你生日快乐!”都显得太现代,也太白话。
何如真作为邓世昌的妻子,是剧中的重要人物,对邓世昌形象的刻画、塑造有一定作用,但这一人物的出场比较突兀,在毕业操练中,邓世昌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何如真头戴红盖头而来,没有家人陪伴,由刘步蟾等同学操持,来同邓世昌办喜事。尽管刘步蟾与邓世昌亲如手足,但情理上似还不能通过。第二场刘公岛妓院、赌场一场戏,方伯谦等众管带逛妓院,丁汝昌抽大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却也存在分寸把握的问题,也不能把妓院、烟枪在海战失败中的作用过分夸大。其实这何尝不是那个年代许多有钱有权人的一种常态表现呢!还有一些细节有待进一步斟酌,如第一场林泰曾所告知“户部通知丁军门,从今年到甲午年的三年里不准北洋海军购买军舰和枪炮”,上级会对下级发这样的通知?显然这是编剧的“通知”,以构置后面与太后的矛盾之需。第八场邓世昌怒斥东乡平八郎“悠悠中华数千年”一段,五十多句,邓世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邓世昌情感升华到高潮。这样一种表达,已经成为戏曲创作的一种新“程式”,藉此,推动戏剧和人物情感到达高潮,发挥戏曲的演唱表达功能,但如果不能和剧情统一,不能和人物思想情感统一,会有声嘶力竭之感。应该一戏一式,有感而发,有戏而发,在戏剧及冲突中塑造人物,表达感情,推助高潮。
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梅兰芳纪念馆书记、副馆长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