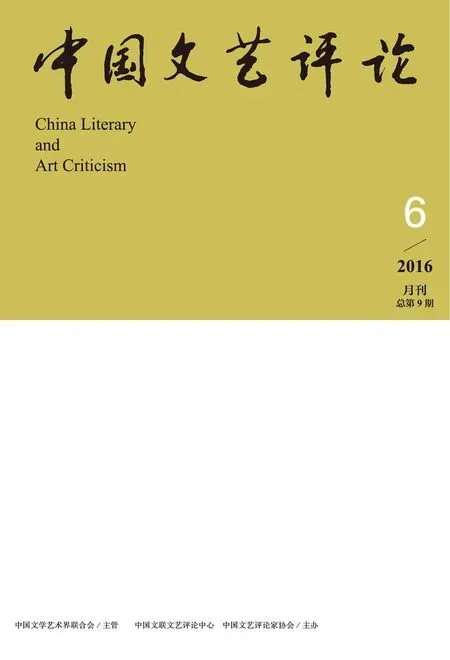讥讽:传统书法评论中的“恶之花”
嵇绍玉
讥讽:传统书法评论中的“恶之花”
嵇绍玉
我国古籍中用“兴观群怨”[1]《论语·阳货》“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赵敏俐、尹小林主编:《国学备览》第一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4页。概括艺术的美学作用与社会作用,其中,“可以怨”既指艺术可以讥讽黑暗的社会,也指社会可以讥讽卑劣的艺术。在书论史上,对书法艺术之讥讽屡见不鲜,有的甚至到相当尖刻的程度。[2]东汉赵壹《非草书》中讥讽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於虮虱,乃不暇焉。”唐李世民《王羲之传论》中讥讽王献之:“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搓挤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还讥讽南朝书家萧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干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宋代书法家米芾,人们对其讥讽甚多。明代项穆《书法雅言》说其字“激厉矜夸,罕悟其失,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端,害则滋甚”。“米邪正相半,总而言之,傍流品也……元章之资,不减褚、李,学力未到,任用天资。观其纤浓诡厉之态,犹排沙见金耳”。“米芾之努肆,亦能纯粹贞良之士,不过啸傲风骚之流尔”。“苏之浓耸棱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资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清代梁巘《论书帖》说米芾之字“落笔过细,钩剔过粗,放轶诡怪,实肇恶派”。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讥讽唐代诸家:“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混,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颜、柳丑恶之风败之欤?”“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撕灭尽矣!”
讥讽,是观赏者的本能之一,如同人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一样。人们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诸如好坏、美丑、有无意思,都会做出能动的反应,到了感情激烈的程度,就会出现嘲笑、讥讽、污辱等形态。书法中的讥讽,是随着书法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有书法肯定就有巧拙、高下、美丑之分。纵观书法批评史,这类讥讽,大多是以譬喻或夸张手法,对书作、书家或书家涉及到的事件进行否定、批评,揭露其可恶、可鄙、可笑。但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这类讥讽在哲学和美学领域,其过程、价值和效果与社会上人们的普遍理解并不一样。
一、赞赏和讥讽是相对的,相互依存
《楚辞·卜居》中有云:“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说明人或事物各有其长处和短处。这从先秦百家到汉王充《论衡》到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都有大量的论述,成为古代朴素的原始美学原则之一。从西方艺术史来看,对美的相对性也有较成熟的论述。古希腊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美是相对的,是对立面的相互冲突和斗争,他有句名言“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是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1]叶秀山、王树人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学术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在此基础上,17世纪英国的美学家哈奇生干脆就把美分为绝对美和相对美。相对美,是拿一个对象与其他相关的对象作比较,只有比较才审视、派生出美,才有优劣出现。我国古代的书论家们对此早就有了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众多书家进行比较鉴别,得出相对的短长优劣,几近贯穿传统书论历史的万里长河。南朝三大书论家袁昂的《古今书评》分析了二十五名书家,比较出各自的特色和风格,并讥讽徐淮南的书法“徒好尚风范,终不免寒乞”;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比较了三十一名书家,讥讽王褒书作“悽断风流,势不称貌,意深工浅,犹未当妙”;庾肩吾的《书品》比较了一百二十八名书家,讥讽卫宣等二十三名书家为“下之下”,皆“五味一色,五色一彩,视其雕文,非特刻鹄,观其下笔,宁止追响”,书中还特意将钟繇与王羲之比较,认为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则天然不及钟但功夫过之。清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魏、晋之书与唐、宋各别。魏晋去汉未远,故其点画丝转自然,古意流露。唐、宋人虽由此出,毕竟气味不同。前则欧、虞、褚、薛,后则米、蔡、苏、黄,何尝不各自成家,亦几于父子不相承袭。故有异有同,有异而实同,有同而实异”。梁巘在《评书帖》总结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法。”[2]潘运告:《中国历代书论选》,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以朝代特色之比较来说明,晋人尚韵乃尚书之气韵或神韵;唐人尚法,表现为书体庄重严谨,法度森严;宋人重意气精神表现,因而笔势纵横,无所羁系。而同是唐人尚法,诸家相比较也各有风格,欧体则瘦劲,颜体则庄厚,柳体则劲秀。同是宋人尚意,苏东坡则趋于遒厚,黄庭坚趋于外拓,米芾趋于雄杰,蔡襄趋于秀润。以上这些论述,无一不是从相对性出发,以不同视角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进行分析,然后概括出不同书家优劣美丑。
更为有意思的是,东西方几乎同代的郑板桥和雨果竟然在美丑“相对论”和“对立统一论”基础上还提出“美丑兼容论”和“美丑转化论”。郑板桥在《丛兰棘刺图》题词中和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都提出同样观点,就是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推而论之,书论中的赞美与讥讽,自古以来则如同孪生兄弟,共一衣胞,或曰男女探戈,仅一步之遥。
二、讥讽取决于评析者的心理判断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与仁者之间看法或评价有差异甚至观点截然相反,都属正常指归。用西方接受美学观点看,叫做“接受者的能动参与”。观赏者的接受活动必然带着强烈的个人理解判断和感情色彩,总是在自身世界的理解中寻找参照物进行比对,既不可能持中性态度,更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态度,完全顾及作品的客观真实性。因而随着观赏家的认知水平、个人修养和时代背景的不同,都有着对艺术观赏的随意性。王献之何等水平,而评者李世民讥讽若是。同是唐薛稷书的“慧普寺”三字,杜甫在《薛稷慧普寺诗》中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说抬头看那优美的垂露体,不歪斜崩塌,也不亏损,三字苍劲有力像蛟龙高耸相缠。而米芾却在《海岳名言》中讥讽薛稷这三个字“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同时讥讽“老杜不知书也”。苏轼其书,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赞许:“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而赵孟頫却在《松雪斋集》中讥讽苏轼“黑熊当道,森然可怖”。项穆也讥讽苏轼其字“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颜真卿书作,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特别推崇“予谓颜鲁公书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而明杨慎在《自墨池琐录卷二》记载:李煜讥讽颜真卿书“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谓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足如田舍郎翁耳”。
正如前文所述,出现这种不同的评判,是由评析者的自身艺术价值观、心理素质和时代背景决定的。以讥讽米芾为例,朱熹和项穆之所以讥讽他,实质是他们想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正统和书统的传统。刘有定在《衍极注》中引朱熹论书说:“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乃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自欹袤放纵,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可以看出,朱熹这段评论明显与米芾的思想不合,米芾性格放纵怪癖,不拘小节,有悖于正统的思想和习俗,这就使得朱熹和项穆抓住其放纵激烈的一面,对其大加挞伐。同一个道理,再来分析米芾对别的书家的讥讽,他在《海岳名言》中言辞偏激,对他人极尽讥讽之能,说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说颜真卿真书入俗品,说欧、虞、颜、柳安排费工,岂能垂世,说徐浩肥俗,全无妍媚等等。他不但对唐代诸多大书家进行不同程度的讥贬,而且在与宋徽宗对话里对同代的诸多书家也深表不满。如此矜自凌人之语,全是由米芾自身的心理素质来操纵。《书画书录解题》指出:米芾讥贬古人太过,不免放言矜肆之习,然此正是米的真实感受和真正面目,毫无客气之处。由于米蒂的书评狂肆放纵,好为高论,有些书学家不仅“不乐闻”,更容易下意识地萌生反感,这就往往会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反过来影响到对米书的评价,有的甚至可能故意以过激诋毁之语来代替公正持平之论。
三、赞赏和讥讽都来源于惊奇
惊奇是审美快感产生的前提。西方美学家曾作过极为精辟的论述。黑格尔认为艺术观照、宗教观照乃至于科学研究都起于惊奇感。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马佐尼在《神曲的辩护》中明确地指出:艺术家和艺术的目的都在于把作品表现得使人充满着惊奇感,惊奇感的产生是在观众相信他们原来不相信会发生事情的时候。作为一种摹仿的艺术,目的全在于产生惊奇感。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爱迪生也将审美的快感和惊奇感联系起来,他认为:“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它的好奇心,使它得到原来不曾有过的一种观念,这就使一个怪物也能显出迷人的魔力,自然和艺术的缺陷也能引起我们的快感。”[1]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7页。
这种美学观映射在书法艺术中,也是深邃而源远的。就书作及其书评来讲,这里面至少包含三层意义:第一,书法作品要给人惊奇感,第二,惊奇之后会产生不同的美学评判,第三,不管什么评判包含讥讽在内的结果都具有美的功能。对第一层来讲,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对其论述较为完备,他尊碑的原因就因为碑给人惊奇,“尽得于目”。他还说赏碑当先“辨其流派,择其精奇”;钟鼎籀字之美,皆因“各尽物形,奇古生动”;元明两朝“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康有为积极倡导书作要给人以惊奇惊美之感。但对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意义,古代书论直接涉及不多,大多认为惊奇仅仅是一种观赏者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或朦胧或模糊或表象,很难一语中的,一清二白,惊奇不能对书作做出实质性的个性解读。此种观点直接导致书论史上产生一个特有现象,就是书论大多讲究形象譬喻,寓多元于直观的、形象化的语言之中,让他人去领悟。米芾曾讥讽萧衍评王羲之语“历观前贤论书,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愈远,无益学者”;认为评语不知所云,华而不实。其实萧衍不过惊奇王羲之书如龙如虎,具生命跃动之力量与气势,而此感觉又难以表述才以喻喻之。萧衍赞许王羲之,米芾讥讽萧衍,两者都对客体有一个惊奇过程。赞许和讥讽不会无缘无故,空穴来风,天设神造,它同属于“惊奇”之后的派生物,本质一致,同出一辙,皆成为美的渊薮。
四、讥讽评判受其他元素的干扰
孟子云:纣之恶,未必如是之甚也。但是“恶居下流”,纣因为恶出了名,不是他作的恶,也会流归于他名下,弄得越来越觉其恶。西方同样持这种美学观点,18世纪末德国作家歌德有一句话最确切地表达纯感官的欣赏与综合式的欣赏:“有三种读者:第一种是无判断欣赏,第二种是欣赏着判断,判断着欣赏,是在重新复制一部带有自己个人感情的艺术品,第三种是无欣赏之判断,而绝大多数评判者属于第二种”。[1][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5-406页。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就是说明观赏者在观赏艺术时,既要忠实于作品,又要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而主观判断直接地会影响着对艺术的评价。
影响书法评判干扰元素中,最突出的当数“人品”介入“书品”。由人论书,免不了“以偏概全”。传统书论中往往是书品直接带入人品,人品直接影响着书品。奸臣蔡京、蔡卞兄弟之书,郑杓在《衍极》中讥讽“其悍诞奸傀见于颜眉,吾知千载之下,使人掩鼻过之也”。说其不但污目,而且还散发出臭气,难闻。赵子昂为元一代大家,但对赵子昂的讥讽历代不绝于耳。傅青主讥讽赵子昂的主要原因在书品之外,其一,出于政治伦理之原因,当时,傅青主作为遗老,对元之书家恨之入骨。其二,赵子昂气质,因其长期生活于山岭之中,颇得山川雄深之气,偏爱妩媚的傅青主自然不加赏识。但去除人品原因,傅青主又以他一双空灵眼睛,对赵书实大加赞赏。他在《字训》中说的:“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非独文章然也”。即使在其《作字示儿孙》诗注中亦称赵书“圆转流丽”。恶赵态却偏以赵态书写,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傅青主实爱赵书品而讥讽其人品。
19世纪法国名著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精神,激励人们与自身的懒惰和社会的不公作斗争。所以,我们对书论中的讥讽从美学角度分析,正如波德莱尔在作品的扉页上写给友人的话那样,“以讥讽来表达赞许,从中挖掘出希望,引出道德的教训来”。[2][法]波德莱尔:《恶之花》编辑前言,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讥讽其实是另一层次的赞许,只是观赏者找到他们最适合表现内心隐秘和真实感情的宣泄方式,来独特地再现他们内心的精神世界,有着比赞许更坚毅的力量,感受着艺术的真谛,点燃着艺术的希望,呼唤着艺术道德的招展。
嵇绍玉:江苏省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理事
(责任编辑: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