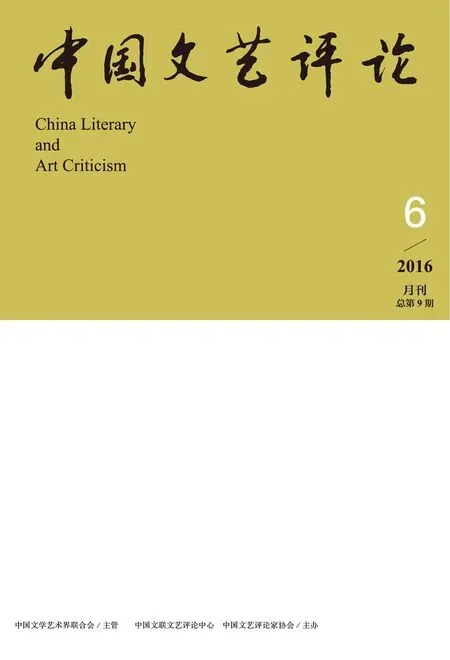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和精神追求
叶朗
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和精神追求
叶朗
今天是张世英先生九十五大寿,又是十卷本《张世英文集》出版,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们现处在一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世英文集》的出版,是张先生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大贡献。在这里,我对张先生的治学和人生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意义谈两点感想。
一、 追求人生的神圣价值
张世英先生的人生和学术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
张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张先生说过,他在西南联大,开始在经济系,后转入社会系,因为听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感到比起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最能触及人的灵魂,同时,他还发现,哲学才最适合他从小就爱沉思默想的性格,因此他就转入哲学系,从此走上一生研究哲学的道路。张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他内心的一种表现,“自己心里好像有泉水要涌出来”。张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熊十力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对做学问的论述。
熊十力先生说过:“为人不易,为学实难。”就是说,做人不容易,做学问也不容易。熊先生的学生牟宗三先生有一个演讲,对熊先生这两句话做了解释和发挥。牟先生说,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学问你都可以做的,这个学问必须进到你的生命的核心里面去,不是自己的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没有真学问出现。牟宗三先生这番话使我想起我们北大的很多前辈学者,他们到了晚年,八十多、九十多岁的高龄,他们的生命力、创造力依旧十分旺盛。如冯友兰先生,他晚年眼睛看不清了,耳朵也听不清了,但他依然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1990年,他95岁临终前才完成最后一卷。用冯友兰自己的话来说,他就像一条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是“欲罢不能”。冯先生为什么这么呕心沥血?因为做学问是他的生命所在。又如朱光潜先生,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连续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三卷,歌德的《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加起来120万字,这时朱先生已经80岁的高龄了。朱先生晚年,又动手翻译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到去世时才译完。朱先生为什么这么呕心沥血?因为做学问是他的生命所在。
张世英先生继承了北大这些前辈学者的传统。张先生最初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有许多这方面的著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先生逐渐转向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在中西会通的基础上,又对哲学基本理论进行研究,出版了《天人之际》《进入澄明之境》《哲学导论》《境界与文化》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张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特别是在哲学基本理论和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想法。在哲学基本理论和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提出新的概念和新的想法,这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困难的。
张先生这些原创性观点是在会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接着讲”。冯先生说,哲学史家是“照着讲”,哲学家是“接着讲”。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不一定“接着讲”,人文学科一定要“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发展,是扬弃,是飞跃。对人文学科来说,“接着讲”才可能有原创性。当然,“接着讲”,还要思想解放,要敢于突破旧说,才能有原创性。思想解放我们天天说,但真正思想解放,敢于突破旧说,并不容易,这需要理论勇气。张先生的著作的原创性,是融会西方哲学的成果,同时表现出极其可贵的理论勇气。
张先生说,他虽然身体疲惫,但他胸中仍然波涛汹涌,万马奔腾。张先生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依然十分旺盛。同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一样,张先生也是“欲罢不能”。这说明做学问是张先生的生命所在,张先生的学问已经进入他生命的核心里面。
张世英先生在《境界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美感的神圣性”这个美学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集中体现了张先生本人的人生追求。2014 年11月,我们举办了一个讨论“美感的神圣性”的美学沙龙,九十多岁高龄的张世英先生、杨振宁先生都在沙龙发表演讲。张先生指出,讨论“美感的神圣性”的意义,就在于赋予人世以神圣性。基督教的美指向上帝,我们的美指向人生。美除了应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具有更深层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是在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中,感受人生的最高的意义和高远的精神追求。杨振宁先生说,研究物理学的人从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堡方程等等这些“造物者的诗篇”中可以获得一种美感,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他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哥特式教堂想要体现的那种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杨先生说的是科学家,艺术家也是这样。艺术家追求美感的神圣性,贝多芬是一个伟大的代表。正像研究贝多芬的学者所说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心灵的彻悟,《欢乐颂》是超越了生命的本体,超越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终极的欢乐。贝多芬的音乐启示我们,在经历了命运的磨难之后,抬起眼睛,朝向天空,歌颂生命,歌颂神灵,放下心灵的负担,了解生命的意义,了解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美感神圣性的思想,指向人生的根本意义问题,向人们揭示了心灵世界不断提升的道路。一个有着高远的精神追求的人,必然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神圣的价值存在。他们追求人生的这种神圣价值并且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分享这种神圣性。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我们从张先生的人生和著作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给我们的人生注入了一种严肃性和神圣性。
二、 一流大学的气象
张世英先生谈到一流大学的气象,主要是两点,一是要有大师,二是要有学派。
张世英先生曾经说,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汤用彤先生、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四个人在台上一站,气象就不一样了。这个气象,就这几位先生来说,是大师的气象,就西南联大这所大学来说,是一流大学的气象。
张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经常说到北大的“大家气象”。
张先生提到,汤用彤先生常说:“笛卡儿明主——客,乃科学之道,但做人做学问,还需要进而达到物我两忘之境,才有大家气象。”张先生说,汤先生不仅做学问有“大家气象”,其为人雍容大度,笑颜常开,也有“大家气象”。张先生又说,北大从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到汤用彤,都有“大家气象”,作为一校之长,确能代表北京大学的学风和文风,北大因他们的名字而生辉,我们今天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大家气象”。
张先生的话启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流的学者,要有真正的大师。当年的蔡元培先生、汤用彤先生、冯友兰先生正是这样的大师,我想,今天张世英先生也是这样的大师。
张先生认为,一流大学还要有学派。张先生说,一流大学的“大家气象”,还体现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派。张先生说:“北大现在最缺乏的是学派的建立。如果北大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学派林立,那才真具有‘大校风采’和‘大家气象’哩!”
一个月前,我去张先生家拜访他,出门的时候,他对我说:“现在应该提出创立学派的问题。”我当即感到,这是张先生当前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无论对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担当的文化责任来说,还是从中华文化复兴的全局来说,都具有战略意义。
任何一场大大小小的学术争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者说,都会分成若干派。但这还不是学派。学派也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一个学科中学派的形成,有几个基本的标志:一要有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体系:二要形成独特的治学风格;三要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四要有一支优秀的学术队伍。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积极影响的有生命力的学派,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派的出现,显示出理论的原创性;学派的出现,有助于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学派的出现,有助于推进学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21世纪是中华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华文化的复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要有体现学术原创性的学派,要有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学术经典、艺术经典、文化经典。19世纪的俄国文化界正因为有一大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所以至今令我们向往。21世纪的中国,也必定会涌现一大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成为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世英文集》的出版,特别值得我们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重视,特别值得庆贺。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责任编辑:韩宵宵)
——开阔的价值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视野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