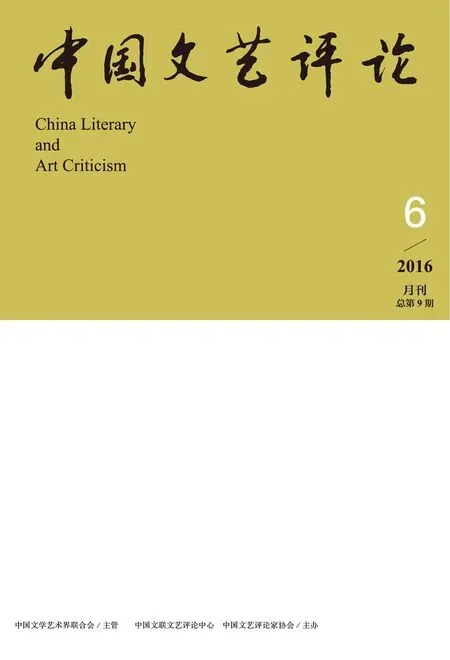在现实主义视野中重审“话剧民族化”
——专访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
陶璐
在现实主义视野中重审“话剧民族化”
——专访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郑榕
陶璐
郑榕简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顾问。自1943年从事戏剧工作以来,先后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如《胆剑篇》中的伍子胥、《武则天》中的裴炎、《明朗的天》中的赵树德、《耶戈尔·布雷乔夫》中的耶戈尔·布雷乔夫,《丹心谱》中的方凌轩等。特别是在北京人艺保留剧目《茶馆》和《雷雨》当中饰演的常四爷和周朴园形象,堪称话剧舞台上人物塑造的经典。在舞台实践不断丰富的同时,郑榕还写了不少表演方面的研究论文。如《〈茶馆〉的艺术感染力》《焦菊隐导演艺术点滴》等。
一、舞台是另一个天地
陶璐(以下简称陶):您从艺的七十多个年头里,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经典人物形象,如《龙须沟》里的赵大爷、《雷雨》中的周朴园、《虎符》中的侯赢、《茶馆》中的常四爷等。您对这些角色的诠释,已成为了话剧表演艺术中的典范,但您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青年时期就读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而您最初进入北京人艺的时候,也是从事舞美制景工作,您能谈谈是如何走上演员之路的吗?
郑榕(以下简称郑):我没上过小学,原来寄居在大伯父家,家里请了一位老师教我们兄妹四个古文,老师中文底子特别好,书画、医学等都懂。我记得当初在我大伯父家的时候,院子很大,有一座大铁门,一般不让孩子走出铁门。只有外出看戏的时候,才有机会坐车去戏院。这就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舞台是另一个天地。除此之外,对于外界的其他事情,我可以说是全然无知。后来我们兄妹几个渐渐长大,寄居在人家家中也不方便,就出来到了北京上中学。那时候的我,又胖又笨,什么都不会。当时学校里面兴演戏,年底同乐会每个班都得演个节目。我们班就排了一个《刘三爷》,并且让我演刘三爷。结果审查的时候被人家说我演的不像个老头儿,又临时改演《请医》,扮演一个病人的太太,没有台词,就在床边坐着不说话。这就是我第一次演戏,也就是从这次开始,我跟戏剧结了缘。
“七七事变”爆发后,大伯父召我们回到天津租界,我在天津租界里上志达中学。学校有个青年会话剧团,由于环境太乱,三番两次想排戏都未成功。后来因故又回到了北京上高中。当时有个北京剧社,我去看了他们演的《日出》,就此迷上了话剧。后来又有了四一剧社,我就去投考,并且被录取了。当时他们在排话剧《北京人》,让我演最后出场的警察,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之后,剧社组织暑期小剧场演出,演出《日出》《原野》《天罗地网》等剧目。有时我们会在剧场前厅等卖票,等到卖够20张,才去后台化妆准备上台演出。1942年,我出演了《日出》里的黑三儿,这是我担任的第一个正式角色,他们觉得我演的还挺好,就准备继续让我出演几个主要角色,但还没来得及上演,我就决定离家去后方。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家境也一落千丈,为了减少家庭负担,我和我的弟弟先后离家,走入社会,开始了个人奋斗的闯荡生活。
1943年,我离家出走到了后方,在西安参加了战干团,这是一个专门收拢沦陷区来的学生青年的组织。在这里我组织了一个剧团,演了几个戏,其中就有于伶的《长夜行》,我自导自演,里面有一句台词:“人生好比黑夜行路,可失不得足啊!”这成为了我的人生座右铭,时时刻刻警惕自己。从战干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党78师去工作,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让我心存的一点希望全部破灭,决计要离开,但却不被放行,于是我决定以后只排戏,不干别的。我在辅导处(一个属于学校性质的部门,专门收拢沦陷区来的学生)组织起了一个剧团排戏。没到一年,遇到改组,辅导处被改成了学校编制,非教职员工被裁减,因此我失了业,开始另谋生计。当时剧社里有位辅仁大学的女老师,和白杨是小学同学,愿意为我写一封信介绍我去重庆见白杨。
1945年,就在日本投降前夕,我拿着遣散费当路费,拿着介绍信到了重庆,见到了白杨。但白杨说重庆演剧的人太多,不容易找到工作。于是没有工作的我只好在街上徘徊,这样过了三天,遇上一个曾和我一起分配在78师的人,他告诉我有一个剧社叫胜利剧社,是私营的,就一个老板,演了很多大戏,借到钱就演出。剧社在一个小楼上,有三间屋,当时正在排一个戏叫《密支那风云》,为了解决温饱,我就参与到了排演中,并因此进入了中国胜利剧社。在剧社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担任剧务的工作,期间也认识了正排演《草莽英雄》的项堃、沈浮等人。我在中国胜利剧社的后期演了几个戏,第一个是陈白尘的《升官图》,我扮演卫生局长,演了没几场被成都警察局封了。之后又演出曹禺的《原野》,由于仇虎没人演,一直让作为剧务的我代排戏。之后也没找着人,就让我正式出演,演完之后大家还挺满意。这之后又出演了《风雪夜归人》和《清宫外史》。
日本投降后,为了凑够路费回北京,我在重庆加入了演剧十二队,由于演剧队有公家经费支持,所以演出次数较多。第一个公演的剧目是《家》,我演冯乐山,之后又演了《上海屋檐下》的林志成,《大雷雨》的库力金,《夜店》的警察,《清宫外史》一、二部等。但由于解放前夕气氛比较紧张,不到三年,演剧队停止了活动,队里的人也都各奔东西。我由于无事可干,在解放前两年到各学校排戏。先去了重庆市女中给他们排演了《娜拉》,后又去清华中学排演了《夜店》《日出》和《海啸》。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四川重庆迎接了解放。解放军把演剧十二队和南京投降时收编的一个杂技团和两个电影放映队组织起来,在电影厂的旧址办了一个学习班。我参与了这次培训,在这里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使我感到兴奋和愉快,我还当导演排演《李自成》。但学习班提前结束,我被分配到重庆市话剧团。话剧团里都是南方的青年,有南京剧专毕业的,也有南京解放后组成的南下工作团的成员。团里让我出演小歌剧《二毛立功记》中的王二毛。由于我不懂音乐,对工人这一角色也不了解,费了好大劲也演不好,还被人数落,于是就有了情绪,想回家。正在这时,我在报纸上看见了关于“遣返还乡”的政策条文,我想这是回北京的唯一机会,于是拿着报纸去找领导,经过多次请求,队上最终批准了我的回乡请求。我回到家那年是1950年。
回家后,我开始找工作。先到了青年艺术剧院,但那儿已满员,他们让我去北京人艺看看。在北京人艺,我遇到了李乃忱,他曾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我在演剧十二队时与他相识。经他介绍,在舞台部门给了我一个名额,于是我就进入了北京人艺,并开始从事舞美制景工作。进入剧院后,我为《王贵与李香香》一剧绘制大海报,并且拿着速写本到处画速写。1950年,剧院决定排演李伯钊等编剧的歌剧《长征》,特地聘请了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焦菊隐来担任导演。
之后,老舍写出了剧本《龙须沟》。剧院演员叶子受院长李伯钊的嘱咐,拿着剧本《龙须沟》找到了焦菊隐。焦菊隐开始有些犹豫,考虑了一夜“这一生要不要再转变一次?”小时候贫苦生活的一幕幕浮现于焦菊隐的脑海。他父亲拖家带口,借住在亲戚家,靠亲戚接济生活。最后,他终于发现了剧本里的“黄金”——活生生的人物!他动了心,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实现毕生志愿的机会。于是就答应排演《龙须沟》。共同的经历(北京劳动人民的生活)将老舍、焦菊隐、于是之凝聚在了《龙须沟》一剧中,创造了话剧舞台上的经典。焦菊隐这一次的加入,让老北京人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转变。
当时老人艺的话剧演员少,群众演员全是歌剧队的。而且焦菊隐更愿意用年轻演员,因为年轻的更能配合他的话剧试验。因此,我也有幸加入了演出队伍。《龙须沟》首演十分成功,轰动一时,它深刻地展现了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被认为是“在新话剧艺术的实践里迈进了一大步,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基石”,最后被推荐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演出了一场。作者老舍先生因此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焦菊隐也在剧院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和老北京人艺话剧队合并,组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曹禺为院长,焦菊隐为副院长。
二、 正确理解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
陶:您曾提到焦菊隐先生是您的引路人,是他的指导让您走上了一条正确的演剧之路,您也是北京人艺里和他合作最多的演员,是他“话剧民族化”探索试验的亲历者。那这一探索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呢?
郑:焦菊隐曾在初创的北平戏曲专科学校任校长三年,期间他拜许多戏曲界的前辈艺人为师,学到很多,受到很大影响,也激发了他对民族戏曲的热爱。之后他离开戏校,留学法国,学习外文,其毕业论文却是谈中国戏曲的。毕业后,焦菊隐回国,在重庆期间,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及丹·钦科(剧院的组织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翻译了许多书和剧本,其中包括丹·钦科的自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等。从中他感到,这是一场戏剧界的大革命,“如何建成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如何在艺术上完全发挥自主权?”这是焦菊隐在国统区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解放前,焦菊隐在北京搞过一个北京艺术馆,成立了一个话剧组,一个京剧组,同时演话剧和京剧,话剧也排戏曲中的古装戏,京剧也学话剧的表演,他希望能将话剧与戏曲融合。后来因为赔了钱,艺术馆没办下去。
解放初期,进步界人士的话剧圈人都崇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其著作《演员的自我修养》成为他们人手一册的经典,但真正能够领会其中要义的人却寥寥无几。焦菊隐进入人艺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大伙在排戏时:否定外部形象,只谈人物思想。一到排练,大伙就开始做桌面工作,分析剧中人物的思想、阶级、背景,认为过去注重话剧表演中的形象创造是形式主义,一律加以批判。这就造成了舞台上出现了“表演情绪”,角色没有性格,没有行动,没有目的,只在一味地情绪化地慷慨激昂地说台词,并且演员说一句话,在脑袋里想半天,全是在表演情绪。焦菊隐认为这恰恰违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过去的技巧必要,但又要培植内心依据。这不是在否定外形,所以焦菊隐进入人艺后就想把这个扭转过来,不搞桌面工作,而是提出要深入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时光看人物的思想是不行的,一定得观察这个人的外部形象及动作。因此排戏时,焦菊隐就会让演员根据角色情况去体验生活两个月,并给每人发两本演员日记,演员将自己体验生活所得的收获感想写在日记上,交给导演,导演看后也将自己的想法写在日记上再返回给演员,平时就通过这样的日记传递与演员沟通,必要时才会找来演员面对面沟通一次。这样的做法就是完全把演员扔进生活中去真切地体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龙须沟》的排演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做法,并且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在《龙须沟》中饰演赵大爷,刚开始我在生活中一直找不到像剧本中赵大爷那样的人——一个思想积极的泥瓦匠。这时焦菊隐就在演员日记中批给我说:首先你得找到泥瓦匠的职业特点。你不要想一下子找到一个跟剧本角色完全一样的人。你得先了解他们这一类人,比如泥瓦匠的生活特点是什么?性格是什么?他们总拿砖,所以你观察他们的手指是并不拢的。泥瓦匠过去都是单干户,虽说整天和泥、水打交道,但十分讲究的是,他们的身上是不能见一个泥点的。要是有一个泥点,就会被人说不会干活,就没人雇佣你了。所以泥瓦匠的打扮比别人都整齐干净。因此后来我演的赵大爷第一次出场时,就是拿着扫帚,先坐到椅子上,把鞋子上的土磕下来,然后用扫帚、簸箕把土收起来。以上这些行动上的细节、人物的职业特点,都是焦菊隐教我观察,教我在生活中去寻找到的。
这其中,于是之获得的成就是最大的。首先,于是之熟悉《龙须沟》中角色人物的生活。因此他在扮演程疯子时,决定要唱单弦儿,这在老舍先生的剧本中并未限定。因为当时唱单弦儿的大多都是由上层没落下来的艺人,过去都是少爷。于是之找了几个唱单弦儿的,给每个人都做了详细的人物笔记,从中体会到这些人物的特点、情感以及遭遇。所以于是之是最早成熟起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叶子大姐比较早体会到人物形象。她找到了剧本中所写的人物——丁四嫂,就是那种大嗓门,男人脾气,被生活压迫着,整天骂骂咧咧,不修边幅的这样一种劳动妇女。我是体悟得比较慢的,所以总挨批,下生活两个月都未得到启发。于是焦菊隐就告诫我说,你这样不行,不能老想着演思想,你必须将这个丢开。初步排演后,我又重新下去体验生活,去补课。那时候早晨9点排戏,我7点钟就去菜市场,在集会上看到劳动人民一样的老头,我就跟在他屁股后面,不管他干什么我都跟着,跟着进茶馆,盯一个小时后再去排戏。在焦菊隐的指导下,最终我找到了“赵大爷”。《龙须沟》彩排那天,我在后台化好妆一看,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赵大爷是这样的。虽然排演过程有很多波折,遇到很多困难,但没想到最后还让我“碰”对了。我演的赵大爷受到了大家的肯定,就这样,我在剧院中由一个不知名的成员成为了一个专业演员,导演焦菊隐引导我走上了一条新的演剧之路——从生活出发,创造人物形象。
陶:听说《龙须沟》排成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是吗?
郑:的确。中央领导都给予了肯定。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看到的大多是“表演情绪”。突然看到焦菊隐用一种新方式——体验生活的方式排出了《龙须沟》,很新鲜,也很好。第一,在题材内容上,《龙须沟》演的是劳动人民,符合解放后文艺表现劳动人民的要求。第二,反映了真实的生活。这是十分难得的,以前演劳动人民,大多都是做样子,而这个戏真正把劳动人民演活了。
陶:那么,焦菊隐先生的话剧民族化试验之路就是从这里发端,然后一步步发展的吗?
郑:话剧民族化试验这条道路其实走的并不顺畅。《龙须沟》的成功,使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遵从“体验生活”这条艺术法则道路上越走越偏,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焦菊隐在排曹禺剧本《明朗的天》时,认为自己对剧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十分了解,就要求演员完全按照他自己熟悉的形象来演,这时候不仅演员烦了,观众也对此不感兴趣了。许多演员本来就对“体验生活”不信服,加上焦菊隐对他们的外形要求严格,所以很多人就对此反感起来。其实人艺自从建院后,有两次大争论:演员角色究竟是从生活出发?还是从自我出发?那会儿大家都尊崇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来演员要从自我出发,于是之反对这个说法,他认为:从自我出发怎么能成人物?演员表演的是人物,所以必须从生活出发。就好比我要演程疯子,我就在生活里找和程疯子相近的人,所以我演的是生活,怎么可能是在演我自己呢?如果演自己,上台后就变不成剧中的人物了。所以说,剧院里一部分人认为演员角色应该从生活出发,即体验生活。而另外一部分认为应该从自我出发。这一争论使得剧院内部思想产生了一些分歧。
当年《龙须沟》的副导演金犁曾说,焦先生要求演员在排演场里“生活起来”,体验生活以后再进排练场。他体会焦先生要求的“生活起来”也就是“行动起来”。另外,焦先生在总结里曾说过一段话:有了思想才产生意志(愿望),有了愿望才产生行动,随着行动而来的是情感和更多的愿望,接着便产生新的行动,新的行动又引起更浓厚的新情感和新愿望。这个发现让我在晚年有新的感触。苏联专家的到来教给我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年提的“形体动作方法”。这最早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徒弟瓦赫坦戈夫提出来的,跟早先的“从自我出发”不一样。瓦赫坦戈夫不主张演员在台上完全进入人物体验,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如何才能掌握人物的内心活动呢?这有一个重要定律,就是“行动=愿望+目的”。演员在台上演戏是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在“我要干什么”的时候得动脑,这时就获得了角色的内心体验,等到了具体的干法上,就是舞台表演,就得注重形式,得演出来,只在脑中想是不行的。实际上就是把表演形式作为舞台演出的重要部分。这个理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完全陷入到角色中,忘掉舞台,忘掉观众”是背道而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也同意了这个观点,并在晚年时提了这个方法。
焦菊隐在排演《龙须沟》时就试验了这个“形体动作方法”。当时,他把表现派大师科格兰的“心象说”介绍给我们。“心象说”主张当演员化为角色在舞台上活动的时候,千万不能失去自己,千万不能失去冷静的控制。演员要清醒、自如地掌握着全部表演。在中国,石挥是实践“心象说”的代表人物。石挥是于是之的舅舅,所以于是之受石挥的影响很深,《龙须沟》的成功让于是之更迷“心象说”这一理论并不断推广,以致有人认为“心象说”就是焦菊隐的学说,是人艺表演学派的代表。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焦菊隐介绍“心象说”给我们,是让我们作为参考,尤其是在创造角色的初期阶段,拿表现派的方法来克服轻视表演形式的毛病。但并不是说舞台上完全按照“心象说”来创造人物。《龙须沟》中的于是之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心象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于是之对劳动人民生活的熟悉,他不是单纯地在模仿,外部形象动作中饱含着他生活体验的感悟。所以说,焦菊隐试验的是“形体动作方法”,成功的也是“形体动作方法”,而非“心象说”。但由于当时不被人接受,这一不成熟的想法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被压在了箱底。
一直到1956年,又请来了另一个苏联戏剧专家库里涅夫来华办表演训练班,库里涅夫曾是瓦赫坦戈夫戏剧学校的校长,他主张的理论就是“形体动作方法”,这样,这一套理论才得以重见天日。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期间,焦菊隐十分认真,天天拿着笔记本上课拼命记,全体演员深受感动。此次的学习让焦菊隐掌握了真正的“形体动作方法”,并弄清楚了一个问题:心理动作和生理动作的区别。“生理动作”指的是一个人的外部特征,比如这个人走路有点瘸,这个人看人喜欢眯缝着眼,这些动作都和人物的内在思想没有关系。而“心理动作”与一个人的思想息息相关,比如这个人喜欢嫉妒别人,这个人心里不满要报复。生理动作有时是下意识的,不受人物意志的支配。舞台上的角色,是不断行动着的,行动则必定有心理动作的存在,因为有了意志、思想、愿望,在抓住这种心理动作的时候,找角色的动作愿望时,演员就进入了内心体验。这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从自我出发”不一样。比如演程疯子,按照斯氏的理论,那就是整个人完全进入程疯子的状态——“我就是程疯子”,忘掉演员自己是谁。而“形体动作方法”不是,如程疯子为什么骂街?为什么要离开龙须沟?后来为什么又要修自来水龙头?为什么又觉得他生活变好了?只有在角色进行到“我要干什么?”时,演员才获得角色的内心活动,进入内心体验。这是很大的一个分别。
焦菊隐正是将“形体动作方法”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提出了“话剧民族化”,提出了中国戏曲的进步性,认为话剧要向戏曲学习。他认为,中国戏曲在形体动作方法的实践上,比斯氏还要彻底。用焦先生的话来说,戏曲给我思想上引了路,帮我认识体会了一些斯氏所阐明的形体动作和内心动作的一致性。符合规定情境的外部动作,可以诱导正确的内心动作,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戏曲比斯氏的要求更为严格。
之前,大家总认为中国的戏曲表演是形式主义的,演员通过练功学会戏曲表演的程式动作,不会功夫演不了戏曲。但焦菊隐说:中国戏曲表演是现实主义的。戏曲艺术中的表演艺术家都能演出角色人物的思想,因为他在人物关键时刻,即“我要干什么”的时候不自觉地进入角色人物的内心体验。好的演员的表演为什么能打动人,秘诀就在此。你看侯喜瑞饰演的曹操,演出了曹操这一角色性格的多变,马连良饰演的诸葛亮,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内心活动。戏曲演员张火丁为什么能够受到大家的肯定和那么多人的喜爱、追捧,最主要的特点也在此。张火丁在演出《白蛇传》时,每一场都带着人物的思想在演,在有了内心体验后,再通过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光想着我这一句的唱腔如何,我下一个水袖动作如何。
这就是焦菊隐对戏曲着迷的原因,也是他在人艺进行话剧民族化试验的内容:将体验与体现糅合在一起,在抓每一个动作愿望的时候进入角色人物的内心体验,动思想,在表演人物态度的时候用外在形式的表演,即体现,比如耍水袖、翻跟头等。与戏曲相比,焦菊隐认为当时的话剧舞台太死气沉沉,根本就没有办法表演,动辄就进入表演情绪。演员在台上拼命“挤”情绪,台下观众却看不懂。比如当时我刚开始演出《龙须沟》时,开幕前半小时我就钻进台上布景搭的小屋里憋情绪,想象着剧中描写的昨日大雨涨沟,脏水灌屋的情况,我饰演的人物一连好几天都没活儿干、没饭吃的感觉……该我上场时,推开门来到台上,没想到把第一句台词都忘了!焦菊隐让我们学习戏曲艺术,学习瓦赫坦戈夫的“形体动作方法”就是要解决这个弊病。这也是焦菊隐的导演理论,但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焦菊隐本人也没有搞的很明确,虽然在艺术实践上一直往这个方向走,但他想达到的目的最终都没有完全实现。
排演《蔡文姬》时,焦菊隐为了表现角色人物的思想,在舞台表现上使用了多种方法,但在人物表现上,除了朱琳演出了角色人物的眼光跟步态外,其他角色都没有达到理想状态,都显得过火,表演形式不自然。观众就会觉得这哪是话剧呀,这不成了京剧了嘛,所以排演《武则天》时又再试验,尝试“无言的动作”“无声的动作”,用小的动作来代替人物语言,语言里面充满了动作,这是焦菊隐后期试验的重点,也是话剧民族化的重点。这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不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在表演时,只能想我要干什么和为什么干,至于怎么干绝不能想,要通过人的下意识来实现,叫“自我抒发”。这跟中国的戏曲艺术是完全相反的,中国戏曲艺术讲究通过试验各种方法和技巧,找到一种最好的方式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意志、内心活动。
排演《茶馆》是焦菊隐话剧民族化试验的一个过渡作品。其花费力气最多的就是在剧目开场时主要人物的登场和开始的群众场面。焦菊隐用的就是京剧表演中的“亮相”,把每个主要人物的出场气氛都做足了,王爷如何上场,太监如何上场,乞丐如何上场等,每个人物的上场都带着鲜明的身份、地位以及人物特征等,让人印象深刻,一开幕就被引进了绘声绘色的大茶馆中。后来《茶馆》被重排,却运用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中的象征手法,这和焦菊隐当初的想法和追求是背道而驰、截然相反的。
三、继承传统、勿忘人民
陶:您看我们现在都在说中国话剧是舶来品,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我们要创造真正属于中国的话剧,形成自己的理论,但您刚才提到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试验并没有完成,既然这套理论在早期的探索是成功的,为什么没有延续和发扬呢?
郑:这个问题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当下话剧艺术的发展中,我们总是在崇拜西方,一提到西方,一提到现代的,认为全是好的、高级的,认为现实主义过时了,西方早就从现实主义走向了现代主义,又走向了后现代主义,我们没有跟上西方的步伐。
1988年冬天,应《文汇报》和上海对外文协的邀请,北京人艺带着剧目《茶馆》《天下第一楼》《推销员之死》等来上海演出,在座谈会上引起了大争论,其矛头指向中国话剧走过的现实主义道路。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西方戏剧流派大量被引入中国的时期,北京人艺的风格、路线也随之改变了。到了90年代,转入到对市民生活、日常生活的关注。2011年,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前往人艺调研时提出了“勿忘人民”四个字。2012年,为了纪念北京人艺60岁“甲子”生日,全院上下倾力创作排演了话剧《甲子园》,剧作以“原创、当代、北京”为主题,以一种精神的坚守呼唤人性的复归。
近几年,北京人艺的风格又在慢慢地往回转,但步伐不够快,“话剧民族化”也始终没有得到正确、全面的认识和弘扬。关键问题是缺乏人才。如今我们国家发展,经济增长,网络普及,许多人盲目崇拜西方,尤其是在艺术上,追求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个性的凸显,认为这才叫艺术,而对于传统文化、现实主义不感冒,对“话剧民族化”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谈到具体的表演问题了。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艺术自由路线,看重的是西方那套理论,或追求影视剧的演出,讲求经济效益。但你要知道,影视剧表演与舞台表演是不同的,影视剧讲求本色演出,人物越自然越好,有的影视名演员演话剧时,观众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这些人连最起码的台词都没有过关。
盲目崇拜西方,说明缺乏自信,总把西方那套理论当作普遍真理来看待、接受,认为西方的是最好的,其实这是错误的。我们是需要借鉴西方,但在向西方借鉴时,不能滥用外来的理念,要在切实考量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整合进我们自身的价值追求。例如现代西方的戏剧潮流,由“再现”向“体现”嬗变,由“写实”向“写意”倾斜,这些和我们自己的戏曲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要善于发现我们自己民族艺术中的宝藏,在传统继承中创新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继续研究试验“话剧民族化”很有必要。当前,我们提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这方面,文艺评论应该起到作用,我们无法硬逼着一个人走某一条艺术道路,但通过评论的推介引导,让话剧艺术积极反映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切身问题,才能得到观众的共鸣和喜爱。我希望能有更多人愿意担起这一重任,将前人留下的宝贵的艺术传统传承下去,发扬开来。
访后跋语:
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我和同事如约来到郑榕先生家中。先生已91岁高龄,但依旧精神健硕,目光有神,讲到动情之处,总会情不自禁地说上几句台词,比画几个动作,宛如一场好戏马上上演。与先生促膝长谈,真是一段温暖的时光。虽只是一次简单的采访,但先生却为此准备了许多材料以备谈到时有据可查,如此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我们敬佩不已。戏剧给予先生无限的多样的生命形态,他也把生命里的热情和好时光全都回馈给了中国话剧的舞台,用实际行动证明着中国话剧曾经的辉煌和未来的希望。老一辈戏剧艺术家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启迪青年人,繁荣发展中国话剧艺术责任在肩、任重道远!
陶璐:《中国文艺评论》编辑
(责任编辑:杨静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