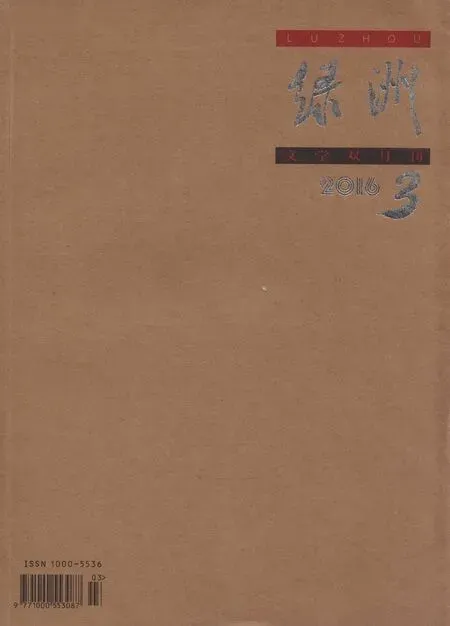采虫草
思 澜
采虫草
思澜
虫草长在哪?我想去看看!高原挂职半年多了,这个愿望终于在2008年5月的那天实现了。
从蔡阳村出发
5月1日上午我顺着大渡河驱车而下,一路山花烂漫,油菜遍野,一下子从凄苦荒寒的康定来到春意盎然的海螺沟,在磨西镇的明珠花园住下。晚上到蔡阳村支部书记罗前华家吃晚饭,商量上雪山采虫草的事。喝酒唱歌谈天,自由自然,融融乐乐,回到明珠花园已是深夜。
因为第二天要上雪山采虫草,心情激动,夜里睡得不踏实,似梦非梦,满脑子都是神奇浪漫的期盼和遐想。不待司机小潘叫早,4点多就醒了。不到5点,天还是漆黑一片,我和小尹、小潘就驱车去蔡阳村老罗家。头脑清爽爽的,纯净而真切。周围的世界还在梦中,沉寂神秘,我们似乎是黑暗世界中行走的幽灵,仿佛能感受到一切生命的律动,而它们却感受不到我们的存在和游动。只有一路挂在雪山顶上圆圆的月亮,不住地跟着我们、望着我们,打破了孤寂的行程。她古雅而又清新、生疏而又熟悉、亲近而又遥远,仿佛是逝去的心爱之物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另一个世界虚幻地展现出来,又似乎是从没见过面的祖辈在那深沉神秘的夜空浮现出慈祥的面容。
到了老罗家,还不到6点,月亮下去了,世界仍旧隐没于灰黑迷蒙之中。老罗一听到动静,很快起来了,连声呼喊他媳妇生火做饭。老罗80多岁的老父亲也起来了,叼着长长的烟袋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吧嗒吧嗒抽个不停,烟火在灰黑的夜色中一闪一闪,忽明忽暗。抽烟的空档,还不时用难懂的四川土话向我们谈论上山采虫草的事。问了一下老罗,大意是说今天天气不太好,可能要下雨,路上要多加小心。不一会村长李猛来了,后面还跟着老罗的堂弟罗前里,他背着一口袋上山准备用的东西。小潘把昨天买的一些东西也从车上拿下来,和老罗他们一起收拾打包。天渐渐亮了,两只小鸟跳到栅栏上清脆地鸣叫,近处的房舍和田野渐渐清晰起来,远处的大山还笼罩在朦胧氤氲的薄雾中,只把一个个像是用水墨洇染出的轮廓呈现到我的眼帘,轻轻浅浅,简简淡淡,形态各异。我漫步出了老罗家的院落,一个人走到田野中,静静地欣赏着这黎明中的画境,仿佛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都融到里面了。这世界成了我无形情感的有形化身,世界因了我存在而灵动起来;我因了这世界的存在而伟大起来。我喜欢夕阳刚刚落山时的景色,喜欢凝视山峦的剪影,现在的景色比她们更多了些灵动和生气,多了些亮丽和清新。
7点天已大亮,只是见不着太阳,淡淡地阴着。我们吃过老罗爱人做的菜泡饭后出发,沿着磨子沟一直往里走。磨子沟早年有一条拉木材用的山区公路,可直达一个叫两叉河的地方,有14.5公里,但因年久不用失修,早废弃了,只有路基和轮廓还在。我们今天采虫草、爬磨子沟雪山要走的大部分缓坡路就在这条道上,剩下的都是爬陡坡。今年,村里在沟里建了一个石板场,把外面的几公里简单地修了一下,勉强可以通车。路面狭窄不平,灌木杂草丛生,路两边伸出的一个个像胳膊一样的枝条,不是在欢迎我这远方的客人,倒像是努力阻拦我的行程。小潘开车异常谨慎,很多地方都是慢慢蹭过去的,我的心也一直提着,生怕出些差错。
车走了约三公里,到了云母沟石板场。老罗说,开车走这一段可以节省我们一个小时的路程,后面的路程按照山里人的速度还要五六个小时,而且很难走。老罗他们把山中过夜所需的东西都放到三个塑料口袋中,每个有四五十斤。他们每人背一个,走起山路来轻松自如。小尹空着手,我只拿一个相机。老罗家海拔1580米,石板场的海拔1700多米,我们要去采虫草的地方海拔在4500米雪线以下,中间的路程20多公里,大约需要爬高2500米到2800米。老罗说要用五六个小时,后来的事实证明,老罗是过高估计了我们的能力和天气状况,整个事情的难度要高于我想象的三四倍,因为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也只是按在家乡低海拔爬几百米的高度来估计这件事的难度。更为艰难的是,我到甘孜后血压升高,一直在吃降压药,而且前些天在患感冒,今天才刚刚见好,体力严重不支。按照常理,不当有此举。对此,身边的人十分担心,小尹说他也是不放心才跟我一起来的。
同行的伙伴们:老罗,李猛,罗前里
从石板场一出发就需要克服困难,这困难主要来自体力。连续十来天的感冒,不停地吃药,已使我的体力十分虚弱。昨天在老罗家吃饭前到田野里散步,走一小段山路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刚开始走的是废弃的林场公路,虽然也是步步上坡,但还算是好走的。刚过丫丫棚,就感觉十分吃力了。我知道这不是爬山时那种正常的疲劳,腿酸气短不说,主要是病后的那种浑身无力,头晕目眩,头重脚轻。眼前的世界不像平时那么清晰真切,我的精神世界也不那么真切,而且二者中间仿佛隔着一层东西。我想这怎么行?一开始就这样,怎么走完20多公里崎岖的山路,爬上4000多米的高山?有此意念作支撑,我的精神世界中体力痛苦不支的呼声和诉求马上被压制下去了。不管怎样,一直往前走,直达目的,这是铁的任务。我心里暗暗地要求自己,全身仿佛立即被调动起一股内在的力量,两腿机械地、不顾一切地跟着老罗他们往前走。老罗他们每人背着50多斤重的行李和炊具,走起路来一点也不吃力,谈笑风生,洒脱自如,还不时停下来接引我和小尹。小尹见我走路吃力,主动把几斤重的相机也接过去了。从一开始,大家就从各个方面照顾我,让我过意不去。我不拿东西不说,就连休息时坐的最好位置,大家都主动让给我。老罗还经常把棕褡子解下来让我坐。这东西用当地一种野生植物叶子编成,背东西时垫在后背,防止磨伤;休息时坐在上面既柔软又干爽,还可以防潮;在山上过夜,铺在身下,还很暖和。老罗他们带的这个东西,一路上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尽管如此,我和小尹还是远远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和节奏。老罗100公斤的体重,1.8米的大个子,据说能喝二斤白酒,饭量也很大,性格豁达豪爽,激情浪漫。这样大的块头,走起山路来一点也不吃力。李猛个子小些,面容谦和,性格随和幽默,见人说话总是笑呵呵的,走路灵便快捷,一路总走在前面。罗前里个子敦厚结实,红红的脸膛上总溢满了汗珠,眼睛里透着质朴憨直,走起路来数他最快,背的东西也数他最沉。他原先还是个猎手,经常打盘羊和野牛。他说前些年他在磨子沟冰川下的一块草地上见到了上百只盘羊。还有一次,他们三个猎手打一只野牛,共打了12枪,那家伙有1000多斤重。去年收枪,老罗和李猛代表上头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最后他是含着泪把双筒猎枪交出去的。他说,交枪比要他命还难受,死的心思都有。一路上他一直在念叨,要是有一支枪,他一定让我们吃上野味。我对小尹感叹道,我们和普通农民之间的距离可以用多种指标来衡量,今天我觉得可以用爬山来衡量。我在城市人中论爬山可算是佼佼者,就是近来不生病,我的速度也不会快很多,只是不会一开始就靠毅力支撑前行而已。这样我和他们的距离就是:背上50斤重的东西由1700米爬上4200多米米再乘上两三倍的速度。这是和老罗他们比,半路遇上打猎和采虫草高手严冲,使我感觉到,我和农民的距离比这还要大。
8点半时,我们遇到了一个70岁的采药老人石宗权。他采的是虫篓,其生物机理和虫草差不多,只是价格便宜,湿的一斤卖7元,一般一天可采10来斤。小尹和他一起抽烟交谈很融洽。我们都走了,他们还在说个不停。
9点40分来到一个山涧瀑布处。此地是山体滑坡地,几块偌大的山石仿佛刚刚从山崖上滚下一样,断裂处的痕迹都是新新的,生生的碎片散落四周,让人感觉仿佛耳边还回荡着震天的轰鸣。老罗说他们上山从来不用带水,到处都是山泉小溪,干净得很,随便喝。说着他便趴在溪边一通牛饮。我也用矿泉水瓶子接了一瓶,喝了一半,只觉浑身清凉异常,人也精神了许多。不料没走多远,肚子便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一个劲地从胃里往外返酸水,开始隐隐作痛。不一会儿就泻了几次,真是雪上加霜。体力越来越不支了,仍旧是靠毅力顽强地支撑着。
10点多到了总棚大坪。这是一块难得的山间平地,有几十亩。坪地北面是一座巍巍耸立着的壮丽山峰,山崖如斧劈刀削一般气势非凡。整个山峰直指苍穹,与云霞相缠绕,如伟岸的大丈夫,磊磊落落,让人联想到峭拔挺立的华山。坪地南面是奔腾咆哮的磨子沟河。在磨子沟这个地质条件十分脆弱的峡谷中,到处都可能发生坍塌和滑坡,这个地方却显得十分结实安全。将来磨子沟要进行旅游开发,此地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11点到了银厂岩洞。相传北边的山沟中有一个岩洞过去产银子,蔡阳村只有一个人知道采银地点,他每年只采一次,从不多采。银厂岩洞下面的河里有一块比一间房子还大的石头,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当地老百姓叫它水滴石穿。也有人说,这块大石头像一扇磨,那个洞就是磨眼,磨子沟就是由此得名。
11点多,一直阴着的天开始下起雨来。老罗他们已经爬上了一个陡坡不见了踪影,我和小尹没带避雨工具,很着急,脚步不自觉地快了起来。刚刚上了几十米的陡坡,就看见老罗笑呵呵地来接我了。他说,一下雨,我看你比什么时候爬得都快,哪来的力气。我说,要是后面有一只雪豹追着,我一定比现在还快。
11点20分到了黄杉大坪,雨越下越大,老罗他们拿出塑料布摊开,五个人都钻到里面去,一边聊天,一边吃饼干。我的胃还是不舒服,不怎么敢吃饼干,也不敢再喝山泉水。大家又说又笑,我却心思沉沉的。因为雨一直这样下下去,上雪山采虫草的计划肯定泡汤了。雨时大时小,沟里沟外白茫茫一片,山峦树木笼罩其中。我的心情也随着雨的大小而忽明忽暗、忽高忽低不断变化起伏着。约过了半个小时,我听见了几声鸟叫,看看沟里腾起了云雾,我高兴了,因为凭经验我知道,这些征兆预示着雨要停了。果然,虽然天未晴,雨却渐渐停了。我们收拾行囊,继续前行。小尹找来一棵树枝给我做拐杖,罗前里用砍刀三下两下帮我把它收拾好。有了它的帮助,走起路来省了不少气力。
12点多到了两叉河,是磨子沟南叉和北叉的交汇处。我们要去的是南叉,磨子沟冰川在那里,也是磨子沟河的干流。北叉叫石龙沟,老罗说离这里几公里的地方,有几块前后相接的大石头,其形状特别像龙。石龙沟因此而得名。我们在两叉河过河朝南走。河水湍急,我们从河中间的大石头上跳跃而过。我手脚无力,不听使唤,根本没有跳跃能力,是在老罗的搀扶下勉强迈过去的。小尹后来说,这时他已看出我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岂不知,我体力早已不支,早已经是靠毅力支撑前行了。
遇上了采虫草高手严冲
过了河开始爬山。12点半,爬上几十米陡坡,在一块横着几根大树干的平地上碰到了蔡阳村村民严冲。严冲坐在一根大木头上,不言不语地抽自己的烟,眼睛漫无目的地朝斜下方的灌木丛中看着,见我们过来,友好地笑笑,算是打了个招呼。他瘦高个,脸黑黑的,鼻子大大的,倒戴着一个旅游帽,从不正视别人,说话也不多。但说出来的话都很坚定,很有把握,给人很自信的样子,一看就是农村那种在生产生活上出类拔萃的能手。他祖辈以打猎为生,到他这一代仍然是打猎高手。前几年国家不允许捕杀野生动物,去年又收了枪,他只好放弃了此种营生。他从小练就的爬山本领,在蔡阳村周围无人能比。老罗说他爬山的速度比他们还要快一倍。他还是当地最有名的采虫草高手,他在山上有自己独到的“药堂子”,别人找不到,这几年每年光采虫草就能挣四五万元。他的老婆也是前些年在山上采虫草时谈的。他今天早晨六点多上山,现在已经采了十几根虫草下山了,每根50元,他今天已稳稳地收入五六百元了。这个时节虫草刚刚长出来,很难找到。我们后来遇到的两对小夫妻在山上住了三天,每人才采到一两根,看看大雪盖住了草坡,只好下山了。
严冲拿出他采的虫草给我们观看、拍照,虫草那黑褐色、肉乎乎的小头,像是一个个小蝌蚪黑尾巴,十分可爱。长在草地上的虫草,只有这个小头偷偷地露在外面,与枯草、干枝和黑色的泥土颜色一样,很难分辨。李猛不小心把一根虫草弄断了一截,四五双眼睛盯着不足一平方尺的地上找了十多分钟也未找到。老罗说,前些年妻子给他准备了八天的口粮,还煮了一大块腊肉,让他上雪山采虫草。他眼睛不太好,到了第三天才采了三根。最后一根竟然是摸到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想笑。当时,他累了,采不到虫草也心灰意冷,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休息,手却不由自主地在周围的草丛中盲目地摸索着,突然一个小小的肉乎乎的东西荡在了他的指间,他马上把手停下了来,细细地感觉着,确证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也不敢用眼睛去打碎那可能的希望。旁边一个人走过来,发现了老罗的异样姿态,便上下打量一番,当那个人顺着老罗的指尖看去是,发现了一颗虫草那黑黑、可爱的头头,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但他也只能期望老罗的手快点移开,于是故意喊老罗起来一起去找虫草。老罗看了那人一眼,从他那焦急不安的眼神中知道自己指间那肉乎乎的东西可能就是虫草,于是老罗的手就坚定地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一寸都不敢离开。老罗知道,只要他的手变换一下位置,那人就会迅速冲上去,大喊一声,“老罗,我发现了一棵虫草!”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那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怯生生地说:“老罗,你的手指间好像是一棵虫草耶!”老罗会意地笑笑说,“我早就感觉它是虫草了!”老罗也是文学天才,讲起这事来生动有趣,惟妙惟肖,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严冲说磨子沟冰川脚下已盖上了二三尺厚的大雪,虫草采不到,盘羊、野牛也看不到,天还会下雨,劝我们不如回去。李猛他们犹豫了,建议就地宿营。我的体力此时已消耗殆尽,但一想到停下来就意味着半途而废,马上坚定了继续向前走的决心。老罗知道我的心意,坚定地支持我,于是我们便艰难地沿着磨子沟河继续向沟里挺进。
雨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我一手举着伞,一手拄着拐杖,艰难地向着心中的那个目标行走,行走,不顾一切地行走成了我行动的唯一目的,汗水和雨水交融在一起,浸透了我的头发,浸透了我的衣服,浸透我的心灵,湿湿的,凉凉的。我们先是在沟西坡的杜鹃林中穿行。杜鹃花东一簇、西一簇地开满林间,白中染红,红中泛白,经这轻柔、细密的小雨一滋润,愈发显得水灵鲜亮,英气逼人。她们就像山里姑娘红扑扑的笑脸,躲在密林深处偷偷地看着我,既像赞许、鼓励我继续前行,又像笑我疲惫无力、狼狈不堪的惨相。在杜鹃花中我发现了磨西台地桃花林中那种爱吃花蕊的小鸟,见我到来,也不惊慌,从容自如地跳到离我稍远的杜鹃花丛中,继续专心致志地采它的花蕊。老罗说,这是当地最小的一种鸟,山里人都叫它蜂鸟,专吃各种花的花蕊。我跟老罗说,它们真是采花高手呀,竟然采到高山的杜鹃中来了。下午上到近4000米的高山上,我又见到了它。
逆着冰川河前行
在杜鹃林中穿行一公里后,我们就行走在冰川所形成的河谷中。老罗说,此地的海拔约在3000米左右。他们小时候冰川一直到两叉河这地方,这几十年气候变暖,冰川已后退到几公里远的沟底。河谷乱石密布,硕大无比,一块块比房子还大的石头随处可见。每一块石头都保留着运动的姿态,整条沟看上去就像奔腾咆哮的石流。真正的溪流就在大石块间跳跃穿行,生动有力,活泼可爱,就像山里的孩子由沟里奔跑而出,能自由准确,恰当自在地找到自己每一个落脚点,急速而有序地奔自己的前程。满沟的石头大部分都呈灰白色,在它们的映衬下,清澈的溪水也成了灰白色。不时有几块红色的石头跃入眼帘,给我灰白的心情增添了亮丽的颜色,让人兴奋起来。有些靠近岸边的大石头上长满了苔藓,开满了细碎的小花,多为红色和白色,还有的身上长出了小杜鹃树,煞是可爱。有的苔藓在石头上形成了奇妙的图案,像是国画大师的写意画,引人无限遐思。我拍了一些特写,准备回去给人作绘画素材。沟的西坡植被不错,长满了杉树、杜鹃。沟的东坡明显保留了冰川运动的痕迹,地质很脆弱,看来会经常发生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整条沟就是一个活动着的地质公园,充分展示着大自然的变迁过程和巨大创造力、破坏力。我在大石块上行走异常艰难。经过四个小时的消耗,本已疲惫的身心,已是难穿鲁缟之弩,行动的力度、准确性、协调性大大下降,每找到一个恰当的落脚处都十分吃力。我每走几十米就必须停下来,全身支在拐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歇息,望着沟底耀眼的冰川和仿佛滚滚而下的石头而发愁。我不知我的目标在哪里,难度到底有多大。问老罗他们,他们总不能给我一个清晰的图景,而且事实总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和想象,我也只能以旧有的知识来想象未来的一切。我每走一二百米就必须坐下来休息,有时索性躺在大石头上一歇就是十多分钟。那时真是不想起来呀!我躺在那里,看着身边这一切非人性的纯粹的自然,想到了汽车,想到了公路,想到了索道,想到安逸舒适的家园。我还想到了我的哲学信条:自由自然。我原来是把自由和自然作为两个并列的价值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现在看来要适当地改变一下了,纯粹的自然是非人性化的自然,那里是没有人的自由的,人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应该是这种自然。人追求的是自由的自然,是人性化的自然,是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超越需要的自然。
头还在晕,肚子还在闹,身体的酸痛已变成了酥软麻木,四肢仿佛不是长在我的身上,一点也不听使唤。一路上身体的痛苦无以复加,精神上的闲情逸致也荡然无存了。小尹替我拿着相机,照片也很少照,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懒得想,机械的行走成了唯一的目的。然而溪边一块温润活泼的石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把它捡起来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嘱咐老罗回来时想着帮我带上。
在离沟底冰川还有两三公里的地方,有几根大木头横过溪流,算是过河桥,我们就在这里过河。木头不稳,一下雨又湿又滑,看到下面湍急的溪流更是心生畏惧。老罗见我对自己的行动已不是很有把握,连忙伸出粗壮的大手,拉着我晃晃悠悠地过了河。李猛、小罗他们早已在前面无影无踪了。老罗是有意放慢脚步来照顾我的。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了,我的体力、精力和毅力已经煎熬了五个小时了。
后面的路是要爬垂直高度八九百米的大山,雨又下大了,我只好再次打伞前行。老罗说去年夏天,成都来拍专题片的那些人刚过两叉河不远就宿营了,你这样大的干部,能徒步走到这已是很了不起了。他并不十分了解,我今天是克服了好几种病痛前行的!
拦在前面的首先是一道乱石坡,有200多米高,100多米宽,约70度的角。这显然也是冰川运动留下的遗迹,坡上乱石密布,从上面流下的溪流就在我们脚下的乱石间潺潺流过。这里根本没有现成的路,我只能跟着老罗的脚步在乱石中穿行。雨越下越大,路也越来越滑,我不得不又打起了伞,小心翼翼地,异常吃力地向上,向着心中的高度奋力攀登着。手脚根本不听使唤,只是机械地保持着前行的动作,我真担心一不小心跌倒,滚到山下去。每爬一步都十分吃力,每走五六步就必须停下来把气喘匀,再继续前行。我经受着平生未有的毅力和体力考验。如果精神上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就肯定走不下去了。
乱石坡,野猪窝,白杜鹃
上了乱石坡,是一片丛林,路也缓了下来。丛林中到处开满了高山杜鹃,洁白秀雅,给我这疲惫烦闷的身心带来了一丝愉悦。老罗说,从这里到山顶还有四五百米。我想,我每走几步就吃掉几米,胜利总会到来的。我们又沿着林中的小溪往上走了几十米,小尹在几棵高大浓密的杜鹃树下发现了一个屋地大的草窝子,蹄印新鲜。老罗说是野猪窝,赶紧躲开,野猪听到我们动静刚走不远,要是发现有人侵入它们的家,会冲回来拼命地攻击人,那我们就惨了。心里正紧张着,忽然沟对岸传来李猛的呼喊,着实吓了一跳。原来他们已经找到了宿营地,准备在那里安家过夜了。老罗说,李猛他们那边有一个岩洞,早些年打猎人和采药人经常在那过夜,我们是不是就在那边住下,明天再继续爬山。我看看雨渐渐大了起来,根本没有停的意思,我的身体也难以再支撑下去,而且李猛他俩已经在那边安营扎寨了,便答应了老罗的请求。我们听见李猛他们似乎很近,想穿过溪流和丛林直接过去,却发现中间隔着一条深深的峡谷,根本没有路通过。老罗又呼唤李猛,问清了道路。我们沿着溪流和杜鹃林一直向上走,那里是峡谷的尽头。我们就这样又向上爬了几十米,穿出丛林,眼前的图景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透过几棵大松树,是一个漂亮的瀑布,清冷的溪水从天而降,柔美而有力,像女人随风飘动的长发,溪水下来后形成了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潭,稍加盘旋逗留后便欢快跳跃着,在两岸盛开的杜鹃的簇拥陪伴下,向峡谷延伸的远方流去。溪流的对岸,瀑布的下面是一大坡冰雪,洁白无瑕,像用洁白的杜鹃花瓣攒成一样。我跟小尹说,受了这么多苦,只要看到这幅图景就不虚此行了。谁知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呢!
下了陡坡,来到瀑布脚下,再小心翼翼地涉过小溪,是延伸到溪流里的冰雪之地。这地方似雪非雪,似冰非冰,比雪硬,比冰软,老罗说他们叫“雪泡”。在这地方走路要异常小心,既容易掉进冰窟窿,又容易滑倒滚下去。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踩着老罗的足迹走。过了一会,老罗我俩已爬上溪流的对岸,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小尹的身影,我有点着急,唯恐发生不测,赶紧叫老罗去找。不一会,老罗领着小尹上来了。原来小尹落在我们后面,追我们心切,想走近路,果然一下子就掉到雪窟中,把脚崴了一下。所幸洞不深,只陷了半个身子,老罗用力把他拉了出来。
过了沟,沿着沟西岸的一个长形平台是一大片开着白花的杜鹃林。树有一人多高,大都开在险要之处,难以靠近,只能远观。此时,雨小了,丝丝如牛毛,又如织娘手中的透明丝线,细致认真地滋润着杜鹃,编织着这超凡脱俗的美丽图景。这杜鹃花有牡丹和芍药那么大,却不像她们那样肥腴慵懒,而是清秀灵动,静雅脱俗。如果说牡丹是衣食无忧的贵妇人,那杜鹃则是待字闺中,幽居闺楼的大家闺秀,或者干脆把她们想象成身居高山,超凡脱俗的仙子更为恰当。看到她们,我想起了前几年在莲花峰看到的黄山白玉兰那一幅洁白、灿烂、高雅的面容。白色的花开在簇拥在一起的墨绿色杜鹃叶子间,错落有致,灵巧有序,仿佛是丹青高手画出的一幅幅构图的写意画。薄薄的雾起来了,一丝一缕地将她们笼罩起来,缠绕起来。就如仙女那皎洁的面容盖上了一层透明的轻纱,在轻纱后面向你表露着灿烂可亲的微笑;又如美人浴后走进白色帐中,那姣好的容貌和摄人魂魄的身姿迷离可现;还如那一轮白白的圆月,被天边飘来的一片淡淡薄薄的白云轻轻罩住一般,白云并没有遮住她月儿的美丽,只是使她不再那么显露无遗,而是增加了几分神秘和朦胧。我虽已是身心疲惫无以复加,但看到这幅动人心魄的图景,我仍不愿离开。走出一段距离,回过头再看,这幅图景又变了:远远看去,那洁白高雅的杜鹃隐约呈现在薄薄的云雾中,恰如晨曦或薄暮中耀眼的星星,一闪一闪地放射着诱人的光芒,又如用那星光般的话语,向你表露着圣洁静雅的深情。
夜宿猎人岩洞
下午3点,我们又向东北方走了几十米,爬上几丈高的陡坡,便来到了的宿营地。李猛和小罗已在这里埋锅造饭了,看着眼前炊烟升起,湿气蒸腾,我又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是一块在一个小山谷中不到十平米的小平地,两块一丈多高的大石块支撑出一个一人多高,上窄下宽,三角形的大山洞。山洞坐东朝西。山洞的背面一直透到山谷里,可以看到山谷一直向上蜿蜒延伸的样子。洞的前面只有一米多的宽度,再往下就是我们刚刚爬过的那个几丈高的陡坡,出了洞,不小心一步就会迈下去。洞的左面是和大石块连在一起的山崖,右边是一个缓坡,再过去就是密密的灌木丛。洞的下面还可以零星地看到冬日未化的冰雪。我猜想,这个洞,夏天一定有溪水从洞中潺潺流过。我们在洞口挡上了一块大塑料布,这样洞更像一个家样了。我想先民们可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那时他们整天面对着这苍茫久远,亘古不变,默默无语的群山,心里在想什么呢?现在我们处身于他们生活过的环境中,真有一种想和他们对话的强烈愿望。猎人呢?猎人在这样淫雨绵绵的晚上,在这与世隔绝的山洞中都想过什么呢?还有那些采药人呢?老罗说,这个洞历来就是打野牛、盘羊的猎人和采药人住的地方。我此时是多么想念他们,多么想让自己的精神和他们的精神联结起来,融合起来呀!我觉得此时我的精神世界中保存着他们的精神记忆,绵延着他们的思绪。仿佛,他们千百年前早已弥散到这周围崖谷、杉树、杜鹃和冰川中的生活和精神,此时由于我的思念正慢慢地向我聚拢过来。
此时我的外衣和头发已完全湿透。外面的雨下得又大了起来。我的精力和体力消耗殆尽,就连站起来欣赏周围景色的力气也没有了。我一头倒在洞口,躺在棕褡子上,静静地望着天空,突然发现洞顶峭壁上伸出来的杜鹃枝叶在灰蒙蒙、空荡荡的天空形成的剪影十分美丽,便躺在那里拍了几张照片。老罗他们忙于收拾东西,准备晚饭,我想好好感受今天经历的一切,静静地坐在洞口,呆呆地凝望着远处的雪山和近处的杜鹃花,却连感受的能力也没有了,脑子里空荡荡的。不一会,我们喝上了开水。4点多,饭也做好了。每人分了一块煮好的腊肉,肉汤里煮了一大锅面条,还放了青菜。饭吃得似乎不是很香,很多,原因在于我似乎累得缺乏吃饭的力气,再加上胃还是不舒服,酸酸的,隐隐作痛。但吃饭的情趣和味道却是别开生面,前所未有的,饭的丰盛程度也出乎我的想象,亏了老罗他们想得周到,连碗筷都一应俱全。老罗还拿了一塑料桶包谷烧酒,给我们这特殊的际遇增添了情趣,给这寒冷的夜增添了温暖。
5点多,洞里跳跃的火光越来越明亮,这表明大山里的夜提前来临了。雨下得大了起来,高山的冷风夹着冰冷的雨滴一阵阵向洞中袭来。天气渐渐冷了,冻得我瑟瑟发抖。洞里的地阴湿湿的,上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石块,我们在上面铺了一块塑料布,垫了一块棕褡子,盖上了一条薄棉被,头冲着北边的洞壁,脚伸向南边的篝火,睡下了。
虽然疲惫不堪,虽然老罗他们把最好的条件让给我,但一开始还是睡不着。一是身下的石头硌得难受,二是天气冷得人发抖,三是伸不开腿,窝着难受,因为脚下就是火。洞里地方小,只能勉强躺下四个人。老罗和李猛没睡觉,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围着火塘热乎乎地聊起了村里的事,我迷迷糊糊的,听不真切。老罗还把他拿的两条秋裤给我一条,套在外面,感觉比原先暖和多了。我每隔十来分钟就要翻个身,调整一下姿势,重新布置一下身下铺的,身上盖的,总想找到一个舒服的感觉,可没过一会又变得不舒服了。就这样,似睡非睡,翻来覆去,不断地折腾着。有时实在难受,就坐起来,烤火聊天。
到了11点,李猛说土豆烤熟了,喊我起来吃,我也是实在躺不住了,就爬了起来。篝火旺,开水沸,雨滴滴,夜沉沉,精神也开始活跃起来。这时,我想到了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和苏轼的《赤壁赋》,还想到了我前几年在湖南八大公山原始森林夜宿小顶坪的难忘经历,想到了比人生,比社会,甚至比自然更久远,更超越的东西。想到了被压缩成一粒尘埃的渺小生命,被切割成瞬间存在的生命,如何与浩渺无边的宇宙,与亘古绵延的宇宙相连接和相提并论呢?这种思索和上面那几篇文章的主题是一致的。此时的情境也把小罗他们激发成一个个存在主义者了。小罗对我说,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苦,爬到这个山洞里来,度过一个这样的夜晚,真是难得呀!我和你们真是有缘呀!我是一个最下层的农民,你们回到北京,我去不了北京,你们也不会再来了,就是来也不会到这个山洞里来了。这可能是我们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面,真是难得呀,太难忘了。我提议唱歌吧,把歌声,把只有在这大山的黑夜中才能发出的生命的歌声、生命的呼唤唱出来吧,唱给那一直对我们默默无语、毫不在乎的永恒和广漠。老罗本来就是一个激情浪漫的人,我这样一说,他马上来了劲,其余的人也都响应着。歌声于是在这高高的山上,黑黑的夜里响起了,伴着跳动的火的光亮,传得很远很长。我相信,那一夜的歌声一定激起了大山里有生命的、无生命的一切存在的注意。他们一定惊诧于这个山洞里这几个生命的存在,一定会对我们的存在产生了一些好奇和敬畏。
凌晨一点多我们都唱累了,也困了。小尹主动要老罗睡觉,他来看火,火是不能灭的。我们烧的都是不发芽的杜鹃,被雨浇得很湿,洞中原有的一些干柴已烧得差不多了,火如果灭了,再生很难,这样漫漫的寒夜是更难熬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唐诗的这个意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虽然风物殊异,味道却有几分相似。
雨还在下,我在为明天前程的担心中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小尹看火不在行,但很努力,几次醒来都见他在努力地用口袋煽火。有时实在不行了,就把李猛叫醒,帮他“救火”。他后来说,此行最大的成就就是“救火”,他是好几次把火从快熄灭的边缘救着的。
4点半老罗起来和他换了班。
清晨6点醒来。听听外面,雨似乎停了,隐隐约约,远处还传来鸟叫声,我的心激动地一跳,天晴了!果然没过半个小时,洞口对面的山峰虽然还包围在云雾中,但我突然发现有几缕阳光射了进来,阳光是金黄色的,这几缕金色的阳光如在凄冷的山谷中投进了一些温暖的火种,把整个群山扰动了,对面山峰那一团团被寒夜冻得凝滞的云雾,开始活跃起来,蒸腾起来。日照金山!我蓦地想到了人们经常说的,游客平时难以碰上的雪域奇观。据说只有在晴天日出或日落,太阳和大地呈十五度角时才会出现这种景色。中央电视台专门在海螺沟等了一周,也未能拍到这个景色。想到这里,我立即拿着相机冲出了山洞,来到一块平坦的高地上,朝磨子沟冰川看去,眼前的景色让我惊异万分:云雾打开了,太阳出来了,我看不到她的面容,却看到了她的光芒,看到了她的光芒照射下的圣洁的冰川!金黄色的磨子沟冰川清晰亮丽、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太激动了,太幸运了,大山太公正了,她给了极度辛劳的我一个最好的回报。然而太阳、大山和云雾太吝啬了,几分钟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金色的雪山便隐没到厚厚的云雾中了。又过了一会儿,待云雾再次打开时,日照金山已变成“日照银山”了。老罗说,他们经常上山,这种景色也是偶尔才能碰上,你到这里能看到这种景色,真是太难得了!太幸运了!
牛场梁子,爬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度
7点半,吃完饭,我们又出发了,目的是再爬上六七百米,到老百姓采虫草的接近4500米的高山上去。横在眼前的首先是一个四五百米高,六七十坡度的山峰。山峰的下面是近百米高,几十米宽的大“雪泡”,上面是一片枯草和刚发芽的嫩草覆盖着乱石的陡坡,有三四百米高。虽然经过了一夜的休息,但体力并未恢复,从3500米向4200多米的高处爬山,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我几乎是每走三五米就要停一停,每走十几米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老罗一直在我周围,细心照料着我,遇到艰险处还伸手拉我一下,坐下休息时,总是把棕褡子从背上解下来叫我坐。李猛和小罗走得比野牛还快,不一会就远远地把我们甩在后面了。这里离雪线几百米,已是长虫草的地方,他俩不时地到南边的悬崖下搜寻。我也按老罗的描绘注意眼前的迹象,除了黑黑的泥土、黄黄的枯草、团团的白雪,什么也没看到。
天晴了,对面山峰上升起了一丝丝、一片片、一团团漂亮的云雾,风吹云动,形态万千,气象万千,不断地给我疲惫的心灵注入欣喜和激动。每每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回过头,或者干脆坐下来欣赏一下这美丽的风光,便唤起一些新的动力。越往上走,磨子沟冰川也越来越清晰了。磨子沟冰川不比别的冰川,纯洁干净,像雪一样。冰川中间露出一块空旷的褐色山崖,像一个踽踽独行的老者,生动可爱。老罗说,当地人叫“雪佛爷”。
9点钟突然听见对面冰川方向传来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原来发生雪崩了。远远望去,一大块冰川坍塌下来,向沟底冲去,势不可挡,壮怀激烈。塌下的地方,映射出淡青色的光芒,森严可怖。旋即,冰川周围蒸腾出团团雪雾,弥漫了整个峡谷,蔚为壮观。
爬山途中,突然听到山顶传来李猛他们的吼叫声,接着看见上面被他们踩下的一块比脸盆还大的石头飞滚而下,好在老罗我们都是在南边走,石头是从北边滚下,呼啸而过,虚惊一场。事后,大家议论想起来都十分后怕。
我们爬的这个陡坡南边是陡峭的海拔5000多米的雪峰和陡崖,人站在下面,感觉高不可越,危不可攀,神气逼人。北边是大片大片还未开花的杜鹃林。这宽几十米浅浅的山谷,原来也一定是被冰川覆盖。老罗说,这里其实是一个大花果山。一到夏天,中间是一片大草坪,百草丰茂,深不见人,两边万木披绿,千芳竞秀。到了秋天,各种各样的野果子挂满枝头,五颜六色,看都看不够,别说吃了!这里有很多草药,特别是贝母很多,贝母鸡喜欢吃贝母,每年夏天都有成群的贝母鸡栖息在这里。贝母鸡长得花白色,比家鸡还大,三五成群,咯咯乱叫,十分可爱。当地人说,吃贝母鸡的肉比吃贝母更能治病。说话间,忽然听到,南面山崖上传来“叽咯咯……叽咯咯……”的叫声,清脆明亮,婉转悠扬。老罗说,这就是贝母鸡,就在高处的崖头上,顺着他的大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隐约看到了矮树下一直缓慢跳跃的贝母鸡的剪影,的确比家鸡修长硕大。
眼看离山顶还有100多米了,小尹已实在走不动了,我叫他原地休息,我和老罗继续前行。最后的50米特别陡,感觉几近垂直,而且覆盖着没膝的厚雪,我咬咬牙,凭着一种不登峰顶绝不罢休的信念,手脚并用,拼命地往上爬。我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我像小尹一样放弃,不登上峰顶,那就会悔憾终生,肯定比当年王荆公游华阳洞还要后悔。哗啦啦,就在旁边几米远的杜鹃树下飞起了一只漂亮的贝母鸡,让我又惊又喜。
腿软绵绵的,脚下踩的也是软绵绵的,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头脑又晕又胀,只有我的意志是清晰坚定的。
在老罗的扶持接引下,我终于爬上了海拔4200多米的峰顶牛场梁子。天又阴了起来,雾气弥漫了四周的景色,只有周围的杜鹃林,林下的白雪和老罗、李猛、小罗我们几个人是清晰的。更清晰的是我的心灵和精神,我清晰真切地感受到我跃上了我的心灵高度,我的精神世界的最高峰。我静静地坐在杜鹃树下的雪地上体验到此时的感觉,雪从来没有这样白,杜鹃的叶子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绿,叶子中间的花蕾也比开放的花朵还可爱,淡黄的底色中点染着红褐色,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们更象征着潜能和希望了。老罗说,再过半个月,这里就是杜鹃的花海,比下面的杜鹃花要漂亮百倍。我对老罗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我已从这一个个硕大的花蕾中凝视出了这一切。
李猛全身躺在一棵伸向悬崖上空的杜鹃上,闲适自得地看着我微笑,好像已经理解我此时的内心感受。小罗不停地用黄色的衣袖擦着红通通的脸上的汗水,用明亮纯朴的眼神看着我,与我无声地交流着。他是一个农民式的存在主义者。我想到昨天夜里与他的对话,猜想他此时此刻一定又在思考什么质朴而深刻的哲学问题。老罗则在杜鹃树下一尺多厚的雪地里,东走走,西看看,嘴里还不停地赞叹着我的爬山毅力。其实在纯真的自然面前,我和这几个农民对生命的感悟,对事情的理解,是如此相近。我感觉我们是那么地平等亲近,大家与那个最伟大的真理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知识、学历、财富、权位此时此刻真的一文不值了。
记住这一刻吧:这地方叫牛场梁子,海拔4200米,上来时是10点,下去时是10:20。为了这一刻,我真的花了20多个小时,在雨中走了20多公里,爬高了2500多米。4200米,这是我有生以来完全靠自己的体力从海拔1700多米爬上的最高的地方。我把自己的人生气度、人生勇气、人生底气一下子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个心灵的高度,这是一个精神的高度,这是一个生命的高度。坐在厚厚的雪地上,看着周围那一树树超凡脱俗、生机待发的杜鹃,想象着开放的情景,端详凝视着头顶触手可及的天空,静静地过滤着我所经历的自然、人生和社会中的诸多事情,人生如初,一切仿佛回到了绝对的纯净和本真,无限的未来正在那里萌动生长。
下山,明珠花园的梦
此时天又下起雨来。老罗说,到老百姓聚集采虫草的地方还要爬被雪覆盖的200多米的山,而且那地方已完全被大雪覆盖了,根本不可能看到虫草,不主张再往上爬。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我已登上了我心灵中的高度,我已找到了我要找的感觉。我决定下山,恋恋不舍朝我们原计划要去的那个最终的目标方向拍了照片,那是一条杜鹃林下的雪野小径。
下山的时候李猛又给我做了一个更好使的杜鹃拐杖。有了它的帮助,速度就快多了。
12点多下到山底,过磨子沟冰川河时李猛和小罗把一根木头抬起来,给我当桥栏杆,老罗则护送我过河。过了河我们就在几块大石块上休息,吃了点东西。我赶紧拿相机补拍了来时没拍的风景。李猛和小罗说还要到另一个采虫草的地方看看。他们总为没采到一根虫草而遗憾。岂不知,我此行爬山之意不在虫草,而在雪山云雾之间也!
过了两叉河,又走了一段,李猛他们追了上来,后面还跟着两对从山上采虫草下来的小两口。他们说,山上下大雪,什么也看不到,三天只采了一二根虫草。他们走起路来,一路小跑,像兔子一样,一眨眼就没影了。快到石板场时雨又下得大了,我打起伞。下一个大坡时跌了一跤,险些从坡上滑下去,把手心擦破了。
4点整来到石板场。小潘在那刚好容下越野车的山坡上居然把车掉过头等我,秘书小武把我的保温杯里放满了开水,打开盖子,还热气腾腾的,用力喝一口,顿时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那一刻我感觉他们是世界上最可爱、最亲近的人!小潘说,这是他当司机二十多年最艰险的一次掉头,稍有闪失就会滚到冰川河里,世界上最难的事在就是“磨子沟掉头”!上了车,我又回到文明的世界,回到了人化的自然之中了。小武要把我的杜鹃拐杖扔掉,被我制止,我要把这一段高山的杜鹃一直带在身边,有她,那隐没在远方和时光中的故事可时时被勾引出来。
小武上车赶紧给海螺沟管理局打电话报平安。他说,昨天山下下了一整天暴雨,大家很担心发生泥石流,每隔二十分钟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5点多把老罗他们送回家后,我到海管局食堂吃了一碗热姜汤面,给又肖锋局长打了个电话。他不放心,昨天本来想找几匹马,亲自要陪我上山的,被我婉言拒绝了。
6点多,回到明珠花园。此时,又软又暖的大床成了我生命的第一需要,倒头摊在上面,一觉就到了第二天九点多。睁开眼睛,困意犹在,又闭上了,似睡非睡,我把这两天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顺着放一遍,倒着再放一遍,反反复复,细细品味,轻轻过滤,一次比一次美好,也一次比一次模糊,或许真的又睡着了,诗化地梦游着昨天的故事。
责任编辑刘永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