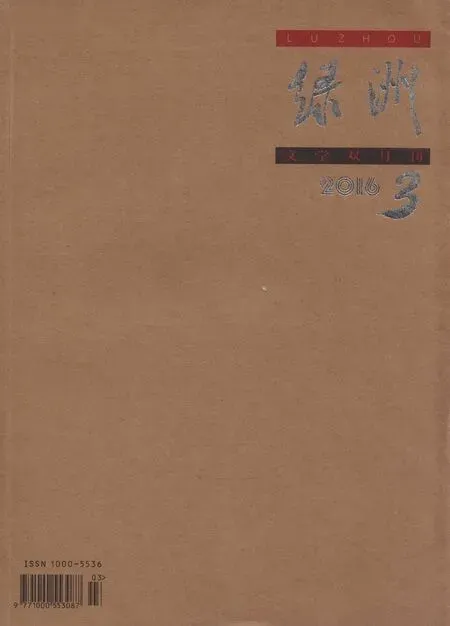假戏假做
冯积岐
假戏假做
冯积岐
他们到达西水市的时候下午四点半了。
他们住进了市内的假日大酒店。这里距离明天开会的地方只有两站路。
走进宾馆的房间,他们各自泡了一杯茶,有滋有味地喝着。
胡来说,出去走走吧。
牟醒说,西水市的角角落落,哪个地方没走过?
胡来说,要不,把兰花叫来?
牟醒说,算了吧,只有半天会议,我没有告诉她要来西水市。
胡来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现在给她打电话也不迟。
牟醒一笑:你想她了,得是?你有她的电话,你给她打。
胡来也笑了:啥人嘛?你的情人,我想她干啥?我是说,女人要常伺弄,你不伺弄她,时间一长,她就成为别人的了。
牟醒一笑:我是有自信的。兰花说过,再过五十年,她还是照样爱我。她给我发誓,只爱我一个。
胡来说:你这么相信爱情?
牟醒说:你不相信爱情?
胡来说: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一种理想,理想就是海市蜃楼,永远不可企及,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爱情不能悬在空中,要落地,落在实处。所以嘛,爱情最终归结于肉体。
牟醒吭地笑了:照你说,爱情就是男人和女人在床上那点活儿?
胡来说,有爱情就必然上床。你和兰花长时间不上床,还能有爱情吗?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她早睡在别人的身底下了。真正的爱情是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结合。缺了上半身或下半身,都不行。
牟醒说,你小看兰花了,她只爱我一个,她对我爱的死心塌地,在海南岛,你是目睹过的。爱情,首先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爱情来自大脑和心脏,不是下半身。没有纯洁的情感,你把她整天看守着也是枉然。
胡来说,好吧,你就陶醉在你的爱情中,我出去走走。
胡来下了楼。
牟醒和胡来一同在省城里的群众艺术馆供职。他们是大学里的同学,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说。牟醒和白兰花相好的事是牟醒主动告诉给胡来的。白兰花在西水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有一年,牟醒去塞北市举办全省群众文化工作培训班。在塞北,牟醒和白兰花相遇相识了。初秋的塞北,凉风习习,风景如画。每天晚饭后,白兰花陪着牟醒去郊外散步,两个人谈文学、谈绘画、谈书法。不论谈到什么话题,白兰花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牟醒对白兰花的第一印象是:才女。在一片小树林,当白兰花主动地偎依住牟醒的身体的时候,牟醒紧紧地抱住了她。当天晚上,两个人就睡在了一起。牟醒结婚十年了,他在妻子那里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庞大的肉体之欢。他爱上了这个小他十三岁的已婚女人白兰花。从此以后,两个人逮住机会就幽会。当两个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白兰花呻吟着说,我、只、爱、你一个。
白兰花的这句话刀刻一般刻在了牟醒的心里:我只爱你一个我只爱你一个我只爱你一个。
有一年,海南岛举办学术研讨会,主办方点名要求秦西省的牟醒和胡来参加。去参会的前两天,牟醒给胡来说,我想带上兰花一起去,行不行?胡来说,有啥不行的,三个人更热闹了。再说,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牟醒一听,激动万分:朋友还是朋友,只有真诚的朋友才能这么相互理解,相互关照,相互支持。
到了海口,住进一家宾馆。当天晚上,牟醒就给兰花说,当着胡来的面,你不能对我太亲热,这样,对胡来有刺激。他是咱们共同的好朋友。兰花说,分寸我会掌握的。他有没有女朋友?咋没有带?牟醒说,他有好几个女朋友,可没有一个好过一年的,几个月就分手了。据我所知,身边暂时没有。兰花说,你们男人都这么花心。消费女人像吐瓜子皮一样。我只爱你一个,和你相好一生一世。不会只好几个月就分手。牟醒说,你的老公呢?兰花说,和老公只是搭伙儿过日子,谁还说爱不爱的话?牟醒说,我也只爱你一个。兰花笑了:那就开始爱吧。牟醒把兰花压在了身底下。当兰花很残忍地喊叫了一声之后,牟醒急忙捂住了她的嘴:胡来就在隔壁,你忍着点。兰花吃吃地笑了:忍不住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死了都值了。
上了饭桌,兰花给牟醒夹一筷子菜,必然要给胡来夹一筷子菜,兰花和牟醒碰一次杯必然和胡来碰一次杯。
到了风景点上,兰花和牟醒合一个影,必然和胡来合一个影——她一只手挽住胡来的有胳膊,头颅紧紧偎依胡来的胸,一副十分亲热的样子,比她和牟醒在一起亲热多了。晚上睡觉前,牟醒和兰花要在胡来的房间里去聊一会儿,直至兰花呵欠不断。牟醒一看,就挑破了:你俩回房间睡吧,不必来安慰我,你俩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兰花说,胡大哥真好。胡来一笑:肯定没有牟醒好。兰花脸红了:才说了你一句好,就说坏话了。胡来说,咋能说是坏话?牟醒好不好,你不知道吗?兰花说,当然知道。
有一天晚上,牟醒感冒了,他吃了一片感康老早上了床。兰花说,不去胡大哥房间了?牟醒说,要去,你一个去,我头痛,老早睡呀。兰花说,你不吃醋?牟醒说,吃啥醋?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还怕他偷了你?兰花俯下身在牟醒的额头上亲了亲:我去坐一会儿就回来。牟醒说,你去和他说说话,他一个人孤独。
牟醒在睡意朦胧中听见兰花说,你出汗了。牟醒说,你也出汗了。兰花说,出点汗好。牟醒说,好,好,都好。兰花不知道牟醒是在说梦话,还是清醒着,牟醒说,你咋才回来?天快亮了吧,你们得是睡了一觉了?兰花说,别说梦话了,睡觉。牟醒说,睡,睡,我只睡你一个。兰花躺在牟醒身边,一会儿就睡着了。
胡来还没有回来。
牟醒从包里拿出来一款新手机。这是他上午才拿到手的——他五年的话费超过了一万五千元,移动公司奖励了他一款手机。他办了一个新号。吃毕中午饭,他和胡来上了高铁,还没有使用过一次新手机。
拿起手机,牟醒不知道该打给谁——这个新手机号,他不想叫更多的人知道。他想了想,还是先和兰花通个话——不,既然昨天没有告诉她,他要来西水市,今天就更不能说了。先匿名给她发个短信,来个假戏假做——算是和她玩一回游戏:
亲爱的,我是你的一个男朋友,可以约会吗?
可以,你在哪里?
牟醒摇了摇头,揉了揉眼睛。手机屏幕上还是那句话:可以。你在哪里?这个白兰花,怎么连姓名也不问就答应了约会?看来,这出假戏必须演下去了:
我在西水市,你在哪里?
我当然在西水市。在什么地方约会?
西府大酒店,怎么样?请你吃晚饭。
几点?
六点整。
可以。报上你的姓名。
见面自然知道。
既然是我的男朋友,怕什么?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叫你知道,我就是你日思夜想的人。
我连姓名都不知道,怎么约会?莫非设局?
你是西水市的女画家,谁还敢骗你?当年,咱们恩恩爱爱,在一起翻云覆雨的情景历历在目。你忘了?
既然有肌肤之亲,还怕我知道你是谁?算什么男人?我不来了。
你在省城有几个情人?就我一个吧,还用我说出姓名吗?
我在省城的情人一大把,你不说出姓名,我知道你是哪一个?
别开玩笑了。你说过,只爱我一个,只有我一个。见面你会很惊喜的。
不见面。
牟醒额头沁出了汗,这出戏做不下去了。他刚合上手机,陷入沉思。手机铃响了。他一看,是白兰花打来的,没有接,过了一会,他又给白兰花发了短信:
我不方便接,请理解。
和谁在一起?女人吗?
和市政府领导在一起,谈工作。
不要演戏了。你的演技太低劣。
兰花,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既然逼我,我就告诉你,我姓胡,明白了吗?
在省城,我有两个胡姓朋友。不知你是哪一位?
大胡。
我知道了,六点见。
如果是戏演,这一出,已经合上了幕布,牟醒想,如果他不去,这个手机号兰花迟早会知道的,他会责备我,说我在试探她。如果去,兰花问他,你来西水市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是不是还有约会——到那时候,他怎么也说不清的。令他更吃惊的是,兰花竟然在省城有两个胡姓朋友。是兰花胡诌的,还是真的?牟醒正在为难之际,胡来回来了。
牟醒把刚才和白兰花互发短信的内容给胡来叙述了一遍,胡来说,兄弟,不是我说你,这就怪你了,你说你是不是想试探兰花?说心里话。
是。
兰花是你的妻子吗?你试探她,有这个必要吗?即使她只爱你一个,世上也不会有永恒的爱。你不在她的身边,你知道她会做出什么来吗?
不知道,但我相信她只爱我一个。
还相信她的那句话?你算得上爱情库里的爱情专家了。你说这戏还演不演?
当然要演,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失去她。
怎么演?
是这样,你拿着我的手机去和她吃一顿饭,就说是你刚才发的短信,叫她看一看。你不正好姓胡吗?
胡来在房间里走动了一圈。胡来说,危难之际,还是朋友靠得住,再不要提什么情人了。能给你当情人的女人同样可以给别人当情人。
不,她只爱我一个,我不怀疑她,不然,这一出就不演了。
好。她只爱你一个。我去替你圆场。
胡来走后,牟醒突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走进餐厅,他对什么饭菜也没胃口,只喝了一碗稀饭,就下了楼。
华灯初上。牟醒毫无目标地在西水市走了一圈,上到十三楼时,已经晚上九点了,他打开房间的门一看,胡来还没有回来。他急忙给胡来拨电话,回答是:没有在服务区。牟醒的心跳加快了,他一急,于什么也不顾,给白兰花打电话,回答是: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可怎么办?牟醒认识西水市群众艺术馆的馆长,他先是问馆长,白兰花还有没有其他手机号,回答是,不知道。他又问馆长,白兰花家住在什么地方?馆长说,群众路,大众花园十五栋十楼六号。牟醒下了楼,拦了一辆的士,直奔群众路的大众花园。他只有一个念头:我去找她。我只爱你一个我只爱你一个我只爱你一个。假如她不在家,你贸然找她,你怎么回答她的爱人?见了面再说。这已经不是演戏,这是生活,是刻骨铭心的生活!牟醒这时候十分清醒。他断然上了十楼,按响了六号房间的门铃。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人。男人用疑惑的目光压住他:你是谁?牟醒说,这是白兰花的家吗?男人说,就是。牟醒说,我是兰花的同事,找兰花有事。男人说,打她手机呀,她不在家。牟醒说,手机关机了。男人说,她五点多打电话说,她去省城里开会,上了高铁。牟醒似乎忘记了他身处何地,他咬着牙说:开狗屁会。哄人的话。白兰花。好一个白兰花!牟醒失态了。他扭头就走。男人啪地一声关上了门。
回到宾馆。牟醒轮番给胡来和白兰花打电话。回答是一样的:不在服务区。关机。牟醒明知电话打不通,却还不停地拨,一直拨到了凌晨一点多。牟醒毫无睡意。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只爱你一个只爱你一个只爱你一个。
牟醒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
牟醒站在窗户跟前,远眺着闪烁的霓虹灯。他双手抓紧了自己的头发,咬着嘴唇,生怕眼眶里的泪水喷涌而出。
牟醒抽了一支烟,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兰花在他眼前头晃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一睇,红润而性感的嘴唇启动了:我只爱你一个只爱你一个只爱你一个。牟醒干巴巴地苦笑了几声,将头埋进被子里,发冷似的抖动着:情人情人情人情人啊!
牟醒背起自己的包,拉上了门,到一楼的前台去退了房间。他坐上了去高铁站的的士。
凌晨四点半,牟醒回到了省城里自己的家。他本来想打开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可是,不知怎么地走到了客厅,放置肩上的包儿时打翻了一只瓷茶杯。妻子被惊醒了。她半裸着到客厅一看,不是窃贼,而是她的丈夫:咋回来了?不开会了?牟醒跌坐在沙发上:我不舒服。妻子坐在他旁边,不舒服就去医院,要紧不要紧?牟醒看了妻子几眼:不要紧。妻子的手触摸他的额头,他倒在妻子的怀抱里放声大哭了。
责任编辑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