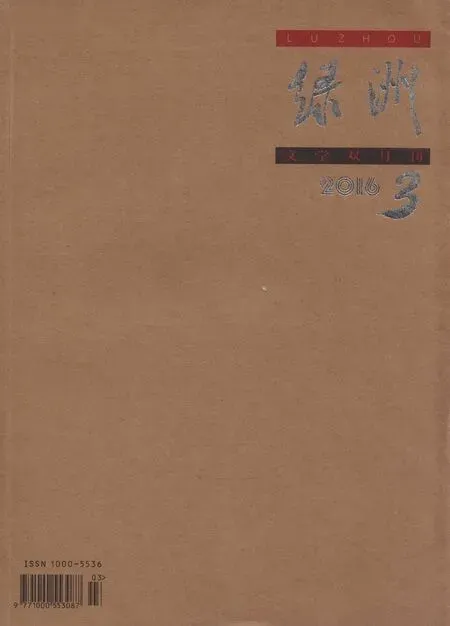一抔乡土
王新军
一抔乡土
王新军
水磨沟
老早的时候,我们西沟一队那片地方,十里八村的人,都叫它水磨沟。
水磨沟,顾名思义,那里有水,是架水磨的好地方。水磨大抵还不止一座,也许两座也不止。但到我记事的时候,的确只有一座水磨了。那时候,水磨沟也已经改叫西沟一队了,也许就是因为水磨太少了吧。
过去,一般人家是架不起水磨的,只有人多地多的大户人家,才有多余的银子,敢往这方面想。架水磨不光是为了自家方便,还是一门相当不错的生意。你想呵,河水那样四季不停地流淌着,石磨吱吱呀呀日夜不休地转着,你磨的是自家的面,人家收的是你白花花的银子嘢。
因此大户人家,但凡不赶骆驼不开货栈的,都要架一座水磨。
疏勒河北下川北镇之后,在约二里的地方折头向西,这一路上,一个湾连着一个滩,河水有一些不大不小的落差。在滩头河里淤一道柴坝,再在滩上开一条新渠,就能引水架磨。十分省事。
水磨吱吱响,响了多少年呀!
水磨对于幼年的我,是个神秘的东西。水没有手,怎么会把石磨推得呼隆隆响?不仅如此,还摇一架大箩,把麦子变成白面。它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河水来自哪里,又流到哪里去了?这些,都是当时的我无法想象的。
那时候磨面,一般都是晚上。白天社员们要上工,时间是公家的,哪里能腾得出来。只有晚上。四五十户人家一座磨,磨面得一户一户挨着来。也有例外的时候——譬如谁家计划不周,还没到时候哩,真就没面下锅了,就会找看磨人说一说,从后面插进来。面箱子净光了,就要断顿哩,不让插,咋办?
这种时候,人们似乎也少有怨言。
插就插吧。
我们家推磨,向来是母亲的事。麦子先在前两天筛净,再用水淘好,装起来捂好。冬天的时候,还要用温水淘。这个工序,我们那里叫淘麦。淘麦不光是为了洗掉麦子上的灰尘,更多的还有润麦的意思。麦子上磨,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太湿磨不出面来,太干了,磨出的面发红。总之要是把不好那个度,一家人就没得好面吃了。这个火候,仿佛永远只有母亲一个人知道。
傍晚下了工,吃过饭(时间紧的时候,往往连饭也先不吃),母亲就吆喝大哥二哥他们,把麦子往磨房里拉。有时候也是提前一天或者半天送过去的,推磨的时候,大多是母亲在操持。
麦子从麻袋里倒出来,堆在地上,再一升子一升子添到磨斗里,看磨人把拴磨的绳套解开,磨就转开了。麦子进入磨眼,从磨盘缝里挤出来的时候,就给磨碎了。再进入箩箱一箩,麸面就此分开。两三麻袋麦子,如是反复五到六遍,天光微微发亮时,看磨人来了,我们的活也结束了。面装进口袋,麸皮装入麻袋,用架子车拉回家去,就好了。
看磨人在磨房角落有一个小房子,冬天的时候,里面有个小泥炉,生了火,旺旺的。炉口倒扣上一个没有底的脸盆,就能烤山药吃。山药就是土豆,也叫洋芋。冬天推磨,母亲总是忘不掉顺手拿上几个山药。一是让我当零嘴吃,一是留给看磨人。山药哪里来的,不知道了。大多时候,吃着吃着,我就在看磨人的小炕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磨还没有推完。我在这期间的任务,就是在装面的时候,帮母亲撑口袋。旁的事,大多搭不上手。
后来水磨便废弃了,因为电磨来了。
电磨也叫钢磨,磨面极快,三四麻袋粮食,个把小时就能搞清楚。我们西沟一队的钢磨房,在饲养场北角的一排杨树下,只占了三间房子的其中一间。包产到户的时候,钢磨房被李家老三承包经营了。李家老三那时候是队里的电工,他会倒腾这些东西。后来听人说,老李家有经营磨房的传统,水磨沟最早的一座水磨,就是他们老李家的。李家嘛,过去水磨沟的大户。
酒坊
每年秋收一结束,我们西沟一队就要开锅烧酒了。
烧酒的那段日子,西沟一队的整个居民点上,都浸透着浓浓的酒香。别的队闻到了,都会狠狠说一声:
“狗日的,一队今年又丰收了。”
队里的酒坊,就在我家门前的知青大院里。知青返城后,房子就空了。两间后来作了队部,其他的都空着。
空着怪可惜的,就改建酒坊了!
开锅烧酒的那些日子,全队就像在过年——
十几条精壮汉子把发好的酒糟从发酵池里起出来,用大脚踩碎,然后放在大锅上蒸。熊熊大火在巨大的锅屁股上舔一阵,亮晶晶的清酒就从一个装在天锅下面的长嘴酒漏子里淌出来,落进下面的一口坛子里。
刚出锅的酒,是热的。
所有走进酒坊的人,都要拿起一只白瓷缸尝一口。尝完了,啧啧嘴,说一声,嗯——好酒。
这酒其实是用玉米芯酿的,没掺多少正经粮食,并不咋的。
但那时候,的确很好。
后来我们西沟一队这酒渐渐有名了,外边人也提了葫芦来打。
几角钱一斤,便宜。
有时候上面来了人,或是开个什么会,也点名要西沟一队的酒。当然,这种时候就见不到钱了,一般都白喝。
我喝酒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闻到酒香,我们就耗子一样往酒坊里钻。端一只白瓷缸在手里,大人们你一口他一口地喝得直咂嘴,那种美气,一眼就能看出来。见一帮娃子们围过来,扁子叔就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咂着嘴,做出十分陶醉的样子对我们说:
“孩儿们,过来,每人赏美酒一杯。”
扁子叔和我们玩儿时,常扮美猴王孙悟空,他这是把我们都当成他的猴崽子们了。
刚出锅的酒,因为热,不怎么辣。见大人们喝得美气,那个贪、那个香,白瓷缸递到我们娃娃手里,每人都是美美一大口。
一口热酒下去,一条火路。不一会劲就上头了。
我们在酒坊院里的麦草堆上躺了整整一个下午,被大人们拉回家去的时候,还一个个头重脚轻的。就那么一口清水,谁料想会那样厉害!后来上了学,会认字了,读到“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这句著名的现代诗,我才一下子把许多事情弄明白。
人生不醉那么一回,哪里知道酒的滋味呀!
分酒坊时,我们家分到了那口烧酒用的大铁锅。
铁锅真大,没地儿放,就一直放在后院里盛杂物。
前些年,假酒喝出人命喝瞎眼睛的事越来越多了,村里人一坐在酒桌上,就想起过去我们西沟一队的玉米小烧来。有一次,二哥想试着把那个酒坊重新开起来,算了一笔账:若实打实地来烧酒,没个啥效益不说,弄不好还要赔钱哩,只好算了。
大仓库
说起来,大仓库是我们西沟一队过去最大的建筑哩。它由四堵墙和六道钢筋焊成的三角梁撑起,东西宽,南北长。里面,是两溜水泥抹面的土仓子,仓子里盛着的,是全队人活命的家当。
那时候队里的保管员,行走腰里挂着一串黄灿灿的铜钥匙,是队里少数几个牛皮哄哄的人之一。
大仓库可真大呵,我们只能走到远处,才能看清楚它的屋顶:两边是斜坡,中间一条高高的人字形脊。房顶上没有铺瓦,只抹了厚厚的麦草泥。大仓库的雄伟,源于它的耸立。说到它的伫立,就不得不说一说它的地基。
大仓库的地基是石头砌的。石头是从北山里一车一车拉来的。拉石头的车,不是汽车,是皮车。有牛皮车,也有马皮车。修大仓库是队里一项大工程,进行了两年,也许是三年。反正一年是绝对修不起来的。这时间,主要用在地基上。
负责砌地基的,是队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地主。那时候,他还戴着“地主”这顶穷人翻身后扣给他的大帽子。地主其实不坏,就是会做买卖,把家业倒腾大了点,比之穷人,多了几亩好地,多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庄院而已。别的什么,都和穷人一样。譬如也吃黑面馍馍,冬天也穿老羊皮褂子,擤完鼻涕了,也要在鞋帮上蹭一蹭手指。在野地里拉屎的时候,也一样把光溜溜的屁股撅得老高,屎硬的时候,也一样要吭——吭——地憋出声音来。
时势弄人呵!地主虽然六十多岁了,虽然老了,在那个年月里,还得干那种搬石头、砌墙基的力气活。
地主知道自己走了霉运,手下干活,就没办法不一丝不苟。无论怎样丑陋的石头,到了他手上,不仅被摆的规规整整,且都能够砌出此起彼伏的花样来。我有一次尿尿时,还掂着小鸡鸡对着那些没有规则的图形展开了一番遐想。我因而不得不由衷地感叹那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地主的高明。
现在想来,一个年迈的老人,日复一日地一层层垒砌着一道长长的石墙,把一块石头与另一块石头之间的缝隙,用水泥砂子的曲线连接起来。这样一个单调的动作,用去了他多少美妙的心思呵!人的心,大约和那些石头一样,颗颗不同,而那些连接它们的水泥砂子曲线,是不是一个老人所要表达的那种心与心沟通的愿望呢?
那一年,要分了。
人们喊出的口号是:集体的东西全分光。
大仓库,自然也就难逃厄运。
起初有人说,大仓库嘛,就不分了,好好的,将来说不定有用。但大部分人还是主张分球掉算了,集体都没有了,留给谁呀?
怕分不匀,开会商量了多种办法,于是分了。
那个地主自己,分了一些什么呢?还是什么也没要?已经记不得了。或许他原本就没有去当时那个乱哄哄的现场。那场面,他在家道败落的时候是见到过的。
在拆除一米多高的墙基时,村人们并没有费多少工夫和力气。大锤一起,石头一会儿就分光了。这倒不是说那石基砌得不够坚固,要知道,人心若是硬起来,石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仓库的旧址,早已成了一片平地。
今年春天我回去的时候,那里被人开垦出来,种上了一片麦子,一片韭菜。麦子和韭菜,都是嫩绿的。
我于是赶紧记下了这一笔,我害怕这座大仓库走出我的记忆。或者说,是害怕它在村庄的记忆中,消失得过于突兀。
九棵柳树
我们西沟一队,最炫目的景观,不外那九棵长在河湾里的柳树。
九棵垂柳很不规矩地长在一里长的河滩上,这里一棵,那里又一棵。从远处看,有两棵柳树似乎显出了相亲相爱的样子。事实上,要用一根长线拴起来,它们还是能够站成一排的。但柳树不是牲口,更不像人那么逆来顺受,它们只跟着河水走。河拐一个弯,它们就在湾子里站住。扎下根,守住脚下一方土。
那些柳树,大多已经老了,有几棵,两三个人合抱都有些困难。据老一点的人讲,这几棵柳树大约已经有一百多个年头了。这能从它们身上粗粝的树皮上看出来。那样的一身皮,看上去本身就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沧桑感。树身的下端,还生了一些碗大的树瘤,乍一看,呀,真是老了。
没有想到,要分田到户的那一年,有人计划要将柳树也一并分掉。这话传出来没有几天,九棵柳树上,便各有了一个红漆写就的编号。
但户多树少,究竟怎么个分法?人们意见不一。
有人建议,先将柳树全部用大锯放倒,再锯成段,按粗细,一户一户分。
分多少,是多少。
这个意见一出口,就遭非议。分屁股大那么一片,拿回去有什么用?
还有人想法更绝,主张将柳树放倒,称斤论两,那样分起来,最是公平。
但这个想法同样遭到了白眼。
于是有人主张不分了,把九棵柳树留给集体。
但这个说法同样遭人非议:现在连集体都没有了,还留给集体东西,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就这样,九棵柳树分了三天,也没有分出个什么结果来。
听说要分柳树了,我们这些娃儿们自然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结果。纷纷相约去柳树上做最后的嬉戏,上上下下,你追我赶,在密匝匝的树桠里捉迷藏,掏两个喜鹊窝什么的,啥都干。这样连续闹了几天,这个最后的告别,似乎没完没了。
一打听,说是大柳树真的要留下来了。但不是留给集体,而是留给西沟一队的后代——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
因为这,我们疯玩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
一些东西,失去的时候才往往被珍惜。如果知道它要长期留下来,又觉得它是那样多余。
大槽子
在疏勒河中游,有那么一片地方,我们曾经叫它大槽子。
印象中,出了村子顺着疏勒河向西走,一直向西走,到了有一片黑树林子的地方,再往北,过了油路——也就是312国道,再过一条大渠,从饮马农场十七队居民点的西面绕过去,向北——就是大槽子。
高处的大片荒草滩被开垦耕种了以后,这一溜子低洼里的草滩湿地被夹在了中间,大槽子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它长得很,也宽得很。草好,是牛羊的天堂。泉眼一个接一个,巨大的泉眼四周,芦苇长得比房子还要高,好家伙,黑压压的,人走过去,就会有野鸭子呀,水喳啦呀什么的扑棱棱从草丛里飞起来,有时是一只,有时是几只,有时候则是一大片,猛然飞起来,黑云一般,把天上的太阳都能挡住。
这里就是父亲带我放过羊的地方。因为它距离我们的村庄实在太远,跟父亲去大槽子,一年当中也不是常有的事情。正因为去的机会不多,所以经常想着去。又因为去那里的时候,父亲常常把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地挂在嘴上,时刻响在我的耳边,拘束得不得了,除了能用眼睛四下里望一望,似乎并不过瘾。比如那些巨大的黑森森的泉眼,被芦苇紧紧包围着。那些泉泉相连而形成的湖沟,里面除了水草,还有野鱼。大槽子里那么多秘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越是这种好地方,父亲越是不许我靠近。那时候,哪怕是做父亲羊群里的一只羊,都要比我自由得多。那时候在大槽子里,能做一只羊在我看来其实也挺好的。那时候我就认为,父亲对我的约束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是放个羊嘛,把自己当成个威风凛凛的大司令似的。放羊,谁不会?羊自己有嘴有腿有眼睛,只要到了有草有水的地方,它们饿了就会吃,渴了就会自己喝,这难不住谁。我这样的心思,完全被父亲看透了。
那一天,父亲很突然地对我说,他想美美地睡一觉。那意思是明摆着的,我马上就把父亲撂过来的话接上了。不接显然是不行的,这就像两个男人过招,人家都放马过来了,你不抵挡就显得太那个了。
所以我说:“那我去放一天羊吧。”
父亲故作惊愕地立直身子,看着我说:“你……不行吧!”
我瞥了一眼被清晨的太阳映得瓦蓝瓦蓝的远空,大声说:“咋不行,不就是放一天羊嘛,又不是扛枪上战场。”
父亲也把目光从我身上收回来,向远处投过去,佯作十分勉强地说:“行呀,那你就试一试吧。”
父亲其实当时已经看出每一次我皱起鼻子后隐藏在身体深处的那种小公牛才有的执拗了。
父亲能把那么一大群羊的心思一只一只揣摩透,把我个十来岁的碎娃子,他是不放在眼睛里的。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执拗,叫父亲有些受不住了。因为我的那种执拗,看上去完全是自以为是的那种,完全是自不量力的那种。父亲当然要拿我一把了,不这样他就不是一个父亲了。当羊群里出现了那种捣蛋羊的时候,父亲轻而易举就能把它收拾得服服帖帖,我嘛,碎娃子一个嘛,父亲根本不放在眼睛里。
父亲指着那一圈羊说:“好,你就试一试吧。”这话一下子就把我的性子激了起来。我用不惯父亲那根差不多被手上的油汗浸透了的放羊棒,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用鞭子。鞭子好,抬手向上一甩,再向下一抽,鞭梢子绕出几个麻花,嘎的一声脆响便能在空中爆炸开来,像过年时节从手里扔出去的粗炮仗,对羊是极具威慑力的。但因为是独自出牧,我还是觉得应该拿上最趁手家伙才放心一些。我把羊毛鞭、牛皮鞭、胶线鞭、麻绳鞭统统拿出来,摆弄了半天,最终还是难以定夺,我只有问从身边走过来的父亲:“哪一种鞭子抽在羊身上最疼?”
父亲在我面前停住,没有马上回答我,他用那两只草黄色的眼珠看着我,不是看着,而是紧紧盯住我的眼睛。那一刻,我蓦地发现父亲的眼睛是那样深,比我先前看到的大槽子里最深的那只无底黑泉还要深。那两枚草黄色的眼仁一动不动,让我在那个夏天的日子里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寒冷。那丝寒冷从脚后跟处升起,直冲脑顶,我的头发梢子都凉飕飕的。父亲就那样看着我,事实上父亲只是看了那么一小会儿,也许几秒钟。但那几秒钟却被我的某种意识在脑海里无限拉长了,我仿佛看见了时间的遥远黑洞,我从父亲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时候父亲突然开口了,他放慢速度,低沉着声音说:“娃子,鞭子抽不疼羊,能抽疼羊的,是人的心——你腔子里那个心有多狠,羊就有多疼。”说完这句话,父亲就撇下我自个走了。
父亲的这句话,一直叫我琢磨到了今天。
后来当我琢磨出一些意味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起父亲手里的那根滑油油的放羊棒来。如果不是用来打羊,父亲手里老是掂那么一根气势汹汹的棍子做什么呢?我甚至以为父亲当时说那话的时候,是害怕他的小儿子如果发起脾气来,会把他的羊打坏。我注意的结果是令我吃惊的,父亲经常握在手里的那根放羊棒,其实是很少在羊身上去找落点的。每一次,当羊群去了它们不该去的地方,我以为那肯定是父亲把棒撂过去打中它们的时候,每一次我都失望了,父亲总是要呔——呔——或者哦——哦——地喊两声,如果羊知趣地回头走过来了,父亲脸上就露出那么一丝娇柔的欣慰。然后拄着那根放羊棒,继续向远处张望。如果羊在听到了他的警告后仍然犹豫不决,或者根本就是蹬鼻子上脸的那种置若罔闻理都不理,父亲就会嗨地一声,一甩膀子,将手里的木棒撂出去。但往往这种时候,棒子落下去的地方,距羊的身体其实很远。羊被哗一下吓回来了,父亲才慢慢走过去,拾了他的放羊棒,在那里站一会儿。这时候,父亲脸上露出的也是那种带了一丝娇柔的欣慰。父亲像一个胜利者一样站在那里,显出非常伟岸的样子。
那一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拥有权力的快乐。那么大一群羊呀,我让它们到哪里它们就得到哪里,我让它们吃草它们就得站下吃草,叫它们什么时候走它们就得马上给我走。那天的羊被我折腾坏了,我像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羊被我玩得团团转。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却被羊美美地玩弄了一把。我的心情完全就是一个小政客冷不防被对手从政坛上一把掀翻的那种样子,我差不多都要绝望了,心情灰到了极点。
那天中午,因为羊被我吆来喝去一直就没怎么正经吃草,我却还为没有走得更远而感到意犹未尽。毕竟是在大槽子嘛,大得呔嘛!
太阳已经偏西了,羊不可能空着肚子或者说只吃个半饱回家。羊固执地来到了一片湿地边,那里有一片丰美的水草,羊肯定是受到它们的诱惑了。但那片地方父亲平常是不愿意让它们靠近的。父亲曾经说,别看那里水草好,其实是一片紫泥溏子,羊到那里去,是要吃亏的。但我记起父亲那句话的时候,已经晚了。羊群像一伙囚犯突然获得了自由一样,看着那片开阔的湿地就情不自禁地冲了过去。
起初,羊只是散开在那片宽阔的湖沟一侧吃草,被羊踩浑的泥水也只没过羊的半个小腿。我知道,这样的深度对于一只夏天的羊无足轻重。但是,有那么一只羊——黑头白鼻梁的老母羊,它吃着吃着,就不自在了。它看了几眼湖沟中间的水草,张开鼻孔嗅了几下,就自以为是地向前迈了过去。它终于衔到一嘴鲜嫩水草的同时,四只蹄子也陷进了脚下的烂泥里,仿佛那水底下有四只神秘的手把它们拽了下去,它挣扎了几下,非但没有走出来,反而越陷越深了。
在它已经感觉无望的时候,它就安静下来开始咀嚼衔在嘴里的嫩草,恐慌和绝望使它一时不知所措了。整个羊群就是这时候从一片惊慌中安静下来的,它们看见那只老母羊正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着水汪汪的嫩草呢,它们却看不到它四只蹄子下面的危险。接着,有一只不甘示弱的羊向前走了几步,还没有来得及伸出嘴巴就陷了下去,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
所有的羊就那样争先恐后地往前冲,它们不顾我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挥鞭阻挠,完全是慷慨奔赴奋不顾身的那种样子。它们有的甚至兴奋地跳了一跳,然后就落在湖沟中间的烂泥里不动了。
这里是大槽子深处,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被陷入稀泥当中的羊群的镇定吓呆了。
……
当太阳落尽我赶着一群被污泥染成黑色的羊回来的时候,父亲在村西边的那座木桥上用一片祥和的目光迎接了我。我早已精疲力竭,被羊群远远地甩在后面。父亲根本不用问,一看那些羊,父亲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一连睡了两天才渐渐恢复了原来的气色。
有了那次经历、或者说有了那半天在烂泥里独自对一群羊的营救,我的身体里好像多了些什么。三天后,父亲在饭桌上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父亲说:“男人嘛,泥水里头好好滚上一回,就啥都知道了。”母亲对父亲这话不以为然,摸了摸我的头,怜爱地说:“你看嘛,把娃整得,脸都瘦下了一圈圈。”父亲说:“儿娃子嘛,不泥里水里滚一滚,咋长大咧?说得。”父亲这么说,母亲似乎也只有赞同了,又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这一次,我把她的手挡开了,我确实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一个男人长大的标志,似乎就是拒绝那个叫做母亲的女人的爱抚。
后来,我又长大了一些的时候,又和同伴们去过几次大槽子,还在那里用农场职工从麦地里拔出来的燕麦草,烧着吃过几次青麦子——青麦穗放火堆里烧黄了,在掌心里一揉,用嘴噗地吹掉麦衣灰,呼地扬到嘴里,一嚼,再嚼,嘿,贼香。吃完了,每个人嘴上都有一个黑圈圈。去泉边洗,如果不认真,有时候洗不掉。
再后来,我们家的羊就全部卖光了,我也再没去过大槽子。
大槽子,这几年听说也因为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泉水干了,草不绿了,鸟也飞走了……这些年,听说那里已经被新的开发者垦成了大条田。只是因为碱大,缺水,一年一年闲撂着。春天,风起时,横扫河西走廊黑洞洞那一片,最先就是从那里刮起来的。
这些天,因为常常想起父亲,所以想起了大槽子,于是动笔记下了这些与大槽子有关的文字。
时过境迁,逝者如斯。
嗟乎!
一筐麦子
秋天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农人们一个个脸上堆满了沉甸甸的笑容。
那些日子的母亲,也和大家一样,脸上洋溢着即将面对丰收的喜悦。用不了两天,村庄周围大片大片的麦子就要开始收割了。
农人们的好心情,总是保持不了多久。就在这天晚上,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
这雨,把全村人的脸都给下阴了。
雨一连下了三天,笼罩在人们心头可怕的情景出现了——地里已经成熟的麦子,开始变灰、变黑,有的麦粒竟然长在麦穗上就急不可待地生出了白嫩嫩的芽儿……
半年的辛苦,一年的收成啊!母亲和村人们一样,心痛得都快吐血了。
天气终于放晴了,家家户户都抢收起麦子来。等麦子碾出来,却找不到一颗来做来年的麦种,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最后,母亲从仓房里端出了下雨前收获的那一筐准备用来当鸡饲料的麦子,准备选它们做明年的种子。
母亲用手拨拉着那筐掺杂着一些草籽的麦子,脸上流露出一层歉疚的神情。母亲自言自语般地对我们说:“早知道大田里的麦子会给雨淋霉了,指望不上,稍微用上些心,这些麦子其实还能多收两筐哩。”
母亲手里的这筐麦子,是种在大田边缘荒地上的。那块荒地去年才开垦出来,春天的时候,母亲和我把种完大田剩下的几把种子撒在了那里,那种不经意间的举动,从心里就没指望能有个什么好的收成。
大田里一忙,母亲和我们也就顾不上那片荒地了,除了浇水的时候跟着大田灌一遍,连杂草也没人去拨。那片麦子竟然就那样长起来了,它们从杂草丛里顽强地伸出头来迎接阳光的照耀,没有一点自暴自弃的样子。因为缺水缺肥,它们把身体里所有的营养都供给了麦穗和籽粒,时刻与疯长的杂草拼着,早早地就成熟了,并且躲过了那场雨,最终被它的主人选作了来年的麦种,成了这一年全村公认的“最好的麦子”。
筛选过后,年迈的母亲抓起一把黄灿灿的麦子笑了,她缺了几颗牙的嘴咧到了一个十分开心的程度。毕竟,我们拥有了一筐饱满的麦子啊!
第二年,因为那筐麦种,我们自留里的粮食获得了丰收。那片小小的荒地,我们再也没有冷落过它。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还是常常有意无意地想起好多年前的那筐麦子,那筐从杂草丛中历尽艰辛走向成熟的麦子。它们在那荒僻的不为人侧目的一隅,时时忍受着野草的诋毁,最终成了那一年村里最好的麦子。这恰似那些出身卑微且时时处处受到冷遇的人,他们当中总有一部分不甘沉沦,始终在艰难和逆境中不屈地前行,最后成为人群当中的“这一筐麦子”。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最好的麦子,就是荒地上长出来的那一筐呢!
烧伤的母羊
宝子是姑妈的儿子,我一直叫他宝子哥。宝子哥不善生计,鳏居多年,于是姑妈为他养了一群羊。说是一群,其实也没有多少只,大约十多只吧,也许二十只,不会再多的,多了宝子哥自己经管不住,姑妈老了,给他搭不上手。
羊圈就搭在屋后面,一套三的土木屋子,立在地上已经三十多年了,有些将要立不稳当的样子,但还是立在那里。只要有人住着,房子仿佛有一股气托着撑着,总是不那么容易倒掉。
羊是个好东西,吆出圈不论河滩地埂,不管什么地方,青草树叶随便什么东西,都能把肚子给填饱。开春产一季羔子,立夏剪一茬羊毛,大钱没多少,小钱经常有。
没油没盐了,卖一领子羊毛。
要备过冬火煤了,截住个羊贩子,卖上只羯羊。
有了这些羊,一两口人的日月,就能糊弄个过来过去。
宝子哥原先在农场的酒厂干过,有喝酒的习惯。后来不干了,也经常喝酒。不光经常喝酒,还经常喝醉。到了这时候,喝酒就成了毛病。
宝子哥,有喝酒的毛病。
好在有些羊呵,卖上几只,宝子哥的酒就能从春天喝到冬天。他喝酒没有什么讲究,啤酒白酒都喝,在家喝,在外放羊的时候也喝,有时候就一条萝卜,有时候有一个馒头也行,大多时候,他干喝——咕,一口,咂咂嘴,咕,又一口。酒把表哥喝成了一个弱不禁风的人。
那年刚刚开春一个天干物燥的日子,粗心大意的宝子哥不知在哪个地方失了手,竟然把后院给引着了。
后院起火了,他却窝在床上呼呼大睡——他又喝多了。邻居们看见了,纷纷赶来救火,其时火已上了羊圈的棚顶,人们冒火打开了圈门,十几只羊却挤在圈的最里边,一步也不肯向门外边跑过来。恐惧让羊挤成一团,面对熊熊大火,它们什么也不相信了,什么主意也没有了。羊圈棚顶的柴草瞬间变成火球,一疙瘩一疙瘩地落下来,羊竟然一点也不知道躲避,空气中立马全成是羊毛燃烧的焦糊味。
羊是宝子哥的命根子,这邻居们是知道的。没有了羊,他们不敢想象他后面的日子。于是有人顶着火冲进羊圈里,把那些身上正着火的羊一只一只捞出来,扔出圈门。
棚倒火熄,羊算是救出来了。虽然烧伤了好几只,但性命无虞,毕竟都救出来了呀。
伤势最重的,是一只母羊,快要产羔的母羊。
当圈棚起火的时候,羊在圈的后旮旯里挤成了一堆,这只母羊就站在最外面。后来听宝子哥说,其实那些被挤在里面的羊,都是母羊下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母羊的儿孙。当棚顶的柴草瞬间变成火球一疙瘩一疙瘩从前面次第落下来的时候,母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它们。
母羊全身的毛几乎被烧光了,一只白羊变成了黑羊。
母羊三天了水米不进,宝子哥无计可施。
第三天深夜,熟睡中的宝子哥被一声鲜嫩的咩——声叫醒了。为了照看烧伤严重的母羊,宝子哥在外屋地上铺了些麦草,把母羊放在了上面。宝子哥拉开电灯来到外屋,看见一只白色的小羊羔跪在躺倒的母羊跟前,小嘴里正叼着那枚烧焦的乳头在用力拱顶。宝子哥后来说,那时候母羊其实已经断气了……它挣扎着活了三天,就是要把羊羔生出来。生出了小羊羔,它也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
后来宝子哥用别的母羊奶喂大了这只小羊羔,它特别特别白,在羊群里是那么与众不同。前年我去宝子哥家的时候,那只小羊已经长大了。宝子哥说,我一直不舍得把它卖掉,就是没酒喝,我也不卖它。说这话的时候,表哥眼里扑闪着泪花。
责任编辑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