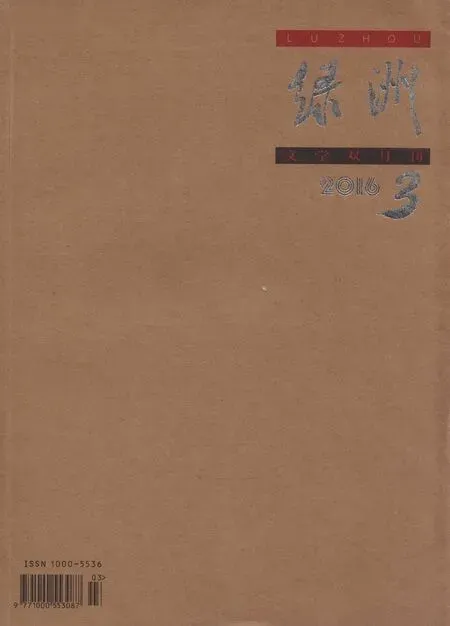那一年的风花雪月
刘 亮
那一年的风花雪月
刘亮
那一年,东西德合并,电视画面的一角,有一个骑在大人肩上的小女孩,不过六七岁的样子,一身白裙,金色的头发、白净的圆脸,眼睛睁得大大地四处张望,显得很好奇,似乎并不清楚眼前为什么会这么热闹,那副可爱模样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年,北京亚运会上,母亲最喜欢的小老乡、被誉为“中国小燕子”的体操名将陈翠婷战胜诸多对手,先后站在了女子团体冠军、女子全能冠军、自由体操冠军的领奖台上。“陈翠婷”这个名字很长一段时间挂在母亲嘴上,而在我心里,我当时更喜欢的则是那个扎着马尾巴、长着一张瓜子脸、身材纤细苗条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樊迪,而她的这些特征也成为若干年后选择女朋友的首要标准。
那一年,七角井有头有脸的风云人物之一、盐厂副厂长孟炜年初被免了职,据说是收了客户五千块钱。才五千!当时大人们都为他不值。
……
那一年,从七角井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而且很多事影响深远,可对我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却不是这些——
亮堂堂的风
那天有风,这本来就是个坏兆头。
但下午放学,我刚从学校走出来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当时我满脑子装的,全是上课时想出来计划以及该如何按照计划实施,好好教训一下孟阳。我得让他长点记心,同时,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可以让老木、大头、二蛋他们三个知道我的厉害,让他们知道,我想当老大可不是全凭嘴上的功夫。
当时的风并不大,连沙子都没扬起来,只卷起几个塑料袋,红的蓝的绿的白的,风筝似的在空中飘来晃去。可这又算什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七角井至少有二百多天都在刮风,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娃,又有哪个不是被风刮大的?虽然我学习不好,可还记得,那个瘦得跟猴一样、成天戴副黑框眼镜的地理老师讲过:这是新疆著名的风口,风从这儿刮起,在二十公里外一个叫十三间房的地方排开阵势,形成闻名全国的“百里风区”,最猛的时候连火车都能刮翻;而狂风卷起的沙尘在南边的库木塔格地区沉积,便成了著名的库木塔格沙漠。更何况,刚刚三月底,正是七角井风最多的时节。
孟阳跟我不在同一个班。我跟他也没什么仇怨,可他实在不该得罪老木,谁不知道老木家跟我家隔得近,从小我们就混在一起,大了以后,他虽然学习比我好,却依然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平时最听我招呼,是我最铁的兄弟。他作业没做是不对,可你孟阳就不能拖上一节课,给老木借一本等他抄完再一起交?干嘛那么认真,跑到老师那告状,害得老木挨骂。这事,老木自己可以无所谓,我可不能不在乎,他丢人,我这个大哥自然也没面子。恰好,我又听说,孟阳只有一个姐姐,我可不怕一个长毛丫头来找我算账。
那一年我十三,大老木将近四个月,正上初二。七角井镇学校初二有两个班,我在二班,也就是所谓的慢班,和我一个班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学习成绩不怎么好或是不怎么守纪律的,连老师都不愿意管;而孟阳在一班,而且他还是一班的数学课代表,不光学习好,人乖巧聪明,小白脸长的也顺眼,是几乎所有老师面前的红人。
当时,我最大的梦想,不是像母亲所期盼的,成绩能从地面一下升到屋顶,直接调到一班。我有自己的梦,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像镇上的王哥一样,成为混子中的老大,不管在哪都受人尊敬,镇上的那些个大人物,镇长、书记、派出所所长……走到哪地皮都颤,走到哪都有人递烟给笑脸,却都拿王哥没招,都得卖他面子。其实,那时我虽然见过王哥认识王哥,但王哥却肯定不认识我,可以说,我们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他更多的是活在七角井跟他有关的传说里,我对他的了解也全都来自传闻,比如说,他曾经一个人打倒过四个比他还结实的小伙子;比如说,为了救一个挨了刀失血过多的兄弟,他一下子就献了600CC血;比如说,为了一个兄弟不被厂里开除,他拎着刀就进了镇长办公室……据说,镇上的混子,不管是东头的西头的,南面的还是北面的,不管是老江湖还是刚出来混的新人,平时谁都不服谁,整天打过来打过去的,却都愿听王哥的招呼,谁和谁之间有了矛盾,再大的事,只要找到王哥,一句话就可以摆平。
在我心目中,王哥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光人长得帅,拳头硬、有一副好身手,还有一帮能够为他赴汤蹈火、两肋插刀的兄弟,走到哪,都有一帮人簇拥着,很是威风。
换句话说,王哥就是我的偶像。
而在知道王哥之前,我一直把哥哥作为自己的偶像。我们家孩子三个,我是老小,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当时上高一学习成绩老是全班前三名的姐姐就不提了,我们俩天生就是对头;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是哥哥,他大我四岁,在镇上的技校上学。哥哥也有一帮子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出去打牌、抽烟、喝酒,有时候还会跟人打架。爸妈都不准哥跟他那些朋友玩,为这骂过他好几次,当面哥都答应得好好的,暗地里却还是经常和他那些朋友聚在一起。根据我的观察,他的那些朋友常来找他,但并不进门,只要在院子外响起一声尖利的口哨,哥哥马上就会找借口出门。
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屈起大拇指和食指,按照哥哥教的方法,放进嘴里使劲地吹,想吹出那种又尖又利仿佛能刺破云霄的声音。在我看来,哥哥长发一甩、然后吹响一声口哨时的样子非常的帅,可轮到我,左手换右手,不管怎么吹,也吹不出一点响动。这让我非常沮丧。
“差不多了吧?咱就在这等着!”出了校门,走出大概一百米,二蛋站住,四下张望了一会开口道。
我回过神,有些不满地看了二蛋一眼,我相信,如果是王哥和他的那些兄弟有什么行动,大家肯定都会听王哥的命令行事,不会有这么多的废话。我们四个人里,难道你二蛋是老大吗?但很快,我就把心底的不悦压了下去,他们三个虽然都和我走得很近,但真正听我话我能指挥得动的,只有老木,而大头和二蛋之所以愿意和我亲近,是因为我能给他们好处。别的不讲,他们都看过我那一箱子小画书,吃了我不少好吃的,我还给他们一人送了一把弹弓枪。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想让他们真正服我,我还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好在,这样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
“好,咱们就在这等他,敢不给咱哥们面子,咱们也别跟他客气!”我强压着心头的紧张,故作镇静地点点头,大人似的说着,和老木、二蛋在马路边的树林带旁站了下来。现在,就等大头的消息了,按照我的计划,刚才我安排他去侦察孟阳的行踪。据老木说,今天正好轮到孟阳值日,他得打扫完教室卫生才能回家,肯定会回得晚一些。
“咱们这样,不好吧?”老木脸涨得通红,嗫嚅地说着,直到现在,他还在犹豫。
这家伙,胆子比老鼠都小。我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壮起胆故意大咧咧地道:“你怕啥?待会你们都不要动手,看我的!”在我的想象中,孟阳的脸此刻就在我的面前,我先是左手虚晃一下,然后出右拳,重重地砸在那张小白脸上。这拳是直奔他鼻子去的,只这一下,就要让他满脸通红,染满鼻血。虽然孟阳还没出现,可我的拳头已经开始发痒,迫不及待想砸到他脸上。
孟阳怎么还不来呢?我的心越来越亢奋,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汹涌奔腾,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已燃烧起来。我相信,只要他一到,我肯定会真的动手,真的。现在可不比从前,远的不讲,哪怕是搁在去年,别说孟阳惹的是老木,就算他直接得罪了我,我也不敢多看他一眼,因为他爸就是年初刚被免职的盐厂副厂长孟炜,正好管着我爸。
“来了!”二蛋忽然开口,打破沉寂。
我抬头,果然,前面,大头正快步向我们跑来。“来了!来了!”他人没到,声音颤悠悠地,已经远远地传了过来。
大头跑近,我们四个人全都猫着腰,钻进了路边的树林带。这也是我计划中的一环,我想,我们必须躲起来,如果让孟阳老远就发现了我们,他肯定会意识到不对,肯定会有所准备或者是提前开溜,那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和我们一起走出校门的老师、学生全都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风不光把我身旁三人的脸吹得发白,也把整条马路吹得空荡荡的。
按大头的说法,孟阳并不是一个人在干活,还有一个人在帮他,而且,帮他的人并不是他姐姐,而是一个男的。由于距离远,大头并没看清那人是谁。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两个人,而我们有四个,照理没什么可担心的,可我的心仍然“噗噗”地跳得厉害。
我似乎听到,七角井镇子后面,山的背后,隐隐约约,响过来一种朦朦胧胧的声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但它经常在我耳边神奇地响起。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走出小镇,翻过山,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找一找,找到那个声音的源头。而且,我还知道,只要这种声音一起,很快便会有大风刮来。
马路上,孟阳和那人这时已经出现在我视线里,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两个人挨得很近,显得很热络。
怎么会是他?
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就像身边那些叶子落尽光秃秃的沙枣树,我呆呆地挺立着,呆呆地看着,全身发冷、似乎泡在冰水中,又仿佛从天堂一下子跌进了地狱,太突然,以致于连呼吸都忘了……
那两人显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径自从我眼前走过去,可他们的声音却锤子似的砸进我耳朵,死沉死沉:
“我这忙,你可一定要帮。以后你万一遇上什么事,有谁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来给你撑腰!”这是孟阳身边那人说的,话语里夹着谄笑,怪怪的,就像米饭里掺了沙子。
“嗯,好吧。”听得出,孟阳应得有些不情愿。
天仍是亮堂堂的。随着突然刮起的一阵疾风,几乎在一瞬间,风的声音已经大了起来,嘈杂了起来,“呼呼”声、“嗖嗖”声、“吱吱”声、“呀呀”声、“哕哕”声、“呜呜”声、“沙沙”声……在我的印象中,风有好些个颜色,黑的、灰的、黄的……可今天这风,却是亮堂堂的,虽然不见踪影,但风从各种物体上掠过发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并在我身体内部形成回响;脚下的大地似乎一下子便变软了,仿佛一头受到了惊吓的动物,身体在不停地战栗,整个七角井这时都开始发抖;空气中到处是春风该有的那种硌牙的土腥味……
“咋办?那是你哥……”盈耳的风声中,不知夹杂着谁的声音,和我的心一样绝望,似乎跌进了深渊。
亮堂堂的天。
亮堂堂的风更劲、更猛了,响在耳边,也响到了我心底。
月光下的沙枣花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想跟哥哥说话,心里老有一种被他出卖被他欺骗的感觉。
如果他问我是原因,我会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他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一想到他在孟阳面前那副低三下四想讨好人的丑陋嘴脸,我就觉得恶心、想吐。可他并不给我机会,在家时,他老是一个人,默默地呆坐着在墙角,就像电视里坐禅入定的得道高僧,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要不然,就是在屋子里不停地转,就像一头被人关进笼子里的狼;再不,就是趴在桌子上使劲地写,搞得跟三好学生一样,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我宁愿相信鸡有三条腿也不相信他是在学习,我抑制不住自己强烈的好奇心,曾经想过偷看,有一次,甚至成功地走到他背后都没让他察觉,可让我失望的是,虽然当时他一只手支着下巴一手握笔,在桌边已经坐了足足半个钟头,面前的信纸却仍是空的,一片雪白,一个字都没憋出来;我还发现,他胆大包天,都敢在家里抽烟了,虽然还避着爸爸妈妈,却不再躲我和姐姐,似乎一点也不怕我们告状,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呛人的烟味,以前他也抽烟,却从不在家抽,身上也没有这么刺鼻的味道;另外,和从前一样,他还是经常出门,但让我奇怪的是,他出门似乎并不是找他的那些朋友,因为每次他出门前,我都会伸长耳朵,细心谛听,可我并没有听到那种熟悉的口哨。
哥哥身上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而且我敢肯定,这秘密和孟阳有关。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按镇上的惯例,每周六晚都有电影,这一天也不例外,中午放学时,写着电影名字的小黑板便在电影院窗户上挂了出来:《百色起义》,一听名字就是打仗的,肯定会很好看。
吃完饭,本来,按原计划,我是要去找老木、大头他们,一起去看电影的。可我发现,哥哥今天吃饭吃得格外的快,不光快,而且吃得很专心,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这哪是我哥?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而且,饭吃完,哥哥并没有急着出门,这更是出乎我的意料。眼看电影就要开始了,他怎么还不走?难道,他不看电影要在家学习?我不信,就算这世上真的有三条腿的鸡我也不信。还有,他的那些朋友为什么没来约他?
他到底要干什么?我很好奇。
正因为如此,我临时更改了计划,出门后并没有直奔电影院,而是藏进了家门口的林带里。
不出我所料,我躲了没多久,哥哥便出了门。
七角井的夜一如既往的宁静、祥和。
银白的月色笼罩下,哥哥走得很急,我轻手轻脚,生怕惊扰或是踩疼了地上的月光似的,心也砰砰狂跳着远远地缀在他身后。
很快,哥哥便走过几排平房,走出了我们所在的盐厂二队居民区,顺着一个道口上了马路,在马路上走了没几分钟又穿过马路拐向另一个道口,道口旁有一个篮球场,哥哥笔直穿过球场,又穿过一条林带,终于站住了。
我跟着他,小心翼翼地钻进林带,但我不敢离他太近,虽然站在同一条林带边,可我们隔了足足十几米,我全身放松,借着林带里树的掩护,轻手轻脚一点点向他那边挪过去。
哥哥身前,大约二十米外正对着他的是一排砖房,只看那排场大气的双扇铁门就知道,这排房子比起我们家的房子明显要高档得多,也新得多,不像我们住的房子是土块院墙,这里就连院墙都是簇新的红砖垒砌起来的。这些房子也是盐厂的,但住的却不是像父母那样的普通工人,而是当官的领导。我不知道“中南海”是什么意思,但镇上人都把这片地方叫“中南海”。
耳边,一声尖利的口哨划破宁静的夜突兀地响起。
我心一惊,那口哨声很熟,是哥哥,他在跟谁联络?
谜底很快就要揭晓,我小心翼翼地从林带里探出头。
没多久,那排砖房靠右第二家的大铁门“吱呀”一声张开口,吐出一条黑影。月光下,那人快步走向哥哥,而哥哥也往前走了几步。
“把这封信给你姐,就说我在这等她。好吧?”我看见,哥哥往那人手里塞了个东西。
“好吧。”那人低低应了一声,像是有些不大乐意。
我看不清那人的脸,但这一个“好吧”却让我的心一激灵,是孟阳!短短的一瞬间,我不光知道了他是谁,而且很快便想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为什么哥哥会讨好孟阳?为什么哥哥会变?为什么哥哥整天趴在那写东西,还抽那么多烟?这下全都有了答案。虽然才上初二,可我们班已经有男生女生谈起了恋爱,真真假假说不清,反正大家都在议论。不用说,我的哥哥也坠入了情网,而孟阳的姐姐孟月就是他的目标。
孟阳回去,等了足足有半个钟头,那道门终于再次张口,吐出一个苗条的身影,她身上,是一袭比月光更白的连衣裙。
“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呢?”哥哥大步迎上去,显得很开心。
“你来干什么?给你说多少次了,我得学习。”苗条身影开口,似乎有些不高兴,声音就像响铃一样脆生生的好听。
“学习学习,你不能老是学习呀?你也得出来走走、活动活动,你看这月光多好,”哥哥笑着,先抬头看了看天,接着把头又瞄向那个苗条身影,侧转身,抬起一只手,指着林带大声说道,“还有这沙枣花,多香啊……”
哥哥看天说月色的时候,我也抬起了头,今晚,挂在树梢的月亮并不比平时圆,但经哥哥一夸,似乎就是比平时要柔要亮,一下便烙在了我脑海中;当哥哥视线又转向林带、林带里的沙枣花时,我也把目光投向了身边——月光下的沙枣花。七角井的林带,大都是一种格局,中间种杨树,两边是沙枣。而这时,我正好站在一棵沙枣树旁边,眼前就有一枝沙枣花。虽然花就在眼前,但起初我并没有留意到它的香味,哥哥话说完,仿佛一扇门被打开,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激荡而出,一会就塞满了我的鼻腔、塞满了我的气管、塞满了我的心肺、塞满我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让人觉得说不出的舒泰。
这香,或许是她带来的,要不然之前怎么会没有呢?我一边想一边定睛细看:银白的月光下,只见一朵朵小小的黄里透白的沙枣花,就像一个个怕见生人脸上含羞的小女孩,藏在枝叶间,隐住身形。有生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打量沙枣花,并把它收进自己的记忆,看上去,它们并不起眼,可从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却覆盖了整个小镇,还有小镇周边,那些铺满黑石子的戈壁滩。
也是这花、这香让我突然想到,七角井也是有春天的,虽然,七角井的春天来得要比内地晚得多、也短暂得多。
这一点,很多年后,当我第一次走出小镇,到南方打工时才发现,而当时更让我惊奇的是,被漫长的寒冬所苦,裹在厚厚的棉袄里的七角井人所期盼的春天,新疆当地少数民族甚至要跳起欢快的“青苗麦西来甫”来热烈庆祝的好日子,在南方人眼里根本就没当回事。也难怪,即使大冬天,南方的山也是青的,水也是绿的,花照样开得蓬蓬勃勃,树上也依然挂满了翠碧的叶子和小鸟的欢唱。他们一年四季过的都是春天,哪能像七角井人一样对春天大惊小怪?就像他们的生活,天天都有鱼有肉,而在七角井,这是过年过节有大喜事才能吃得到的,奇怪的是,那么多好吃的,他们却吃不出一点高兴来。
这让当时已经二十出头的我意外而又失落。也是这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世界有多么的大;而且,虽然同在一个星球,同样是人,可我的家乡七角井以及出生在七角井的我与内地以及内地人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
“行了,沙枣花有啥看的?”苗条身影开口,不耐烦地说着,打断我的思绪。
“有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你?”哥哥声音大了起来,似乎有些急了。
“再别说了,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想这些。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苗条身影叹了口气,继续道:“我爸说了,以后我们的路都得靠自己,而且只有考上大学离开七角井这一条路,如果考不上,那这辈子就都得受人冷眼让人笑话了。”
“这些我知道,可……”哥哥嗫嚅着,话都说不囫囵。
“不行,我得回去看书了。”话说到这,苗条身影一转身,说走就走,没有丝毫犹豫。
“月月,我爱你!”眼见着苗条身影已经到了门口,手已经摸到了门上,哥哥突然开口,大声喊道。他的声音混杂在沙枣花的甜香里,在莹白的月光下久久回旋,有深情、有不甘、有无奈、有失落,但更多的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悲伤,隐隐带着哭腔。
眨眼间,泪水便模糊了我的双眼:
那个苗条身影蓦然回头,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向哥哥跑过来,她的脚步是那样轻盈,就像一头奔向泉水渴急了的小鹿,也像亚运会上正在进行体操比赛的樊迪,白色的连衣裙在空中飘飞,如月光下盛绽的一朵花;而哥哥张开双臂,心有灵犀地迎过去,然后两个人紧紧地拥在一起……画面就此定格。
然而,这却只是我的想象。苗条身影稍一停顿,接着便消失在门里。
月光下,沙枣花香如故……
太阳雨
七角井镇子后面的戈壁,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近处,一览无余的,是荒凉复又荒凉的戈壁,除了星星点点几丛骆驼刺、红柳枝,似乎很难寻到什么生命的迹象。可是,只要你用心,透过气息奄奄的表面,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那,也是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
戈壁上最常见的动物是蜥蜴,苍灰色,拖着一条长尾巴,四条腿十分灵活,加上一双敏锐的眼睛,想捉到它并不容易。每每走到一丛骆驼刺前,虽然你并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可你的脚步已经惊扰了它,只听“窸窸窣窣”几声响,它飞快地钻出来,慌慌张张窜入另一丛骆驼刺。你惊异着走过去,可是,在你走过的几丛骆驼刺中,竟又出乎意料地钻出几只,让你不得不佩服蜥蜴家族的昌盛以及它们隐身术的神奇。
那天是星期天,半上午,本来我们四个打算到戈壁滩上烧洋芋吃,结果,路上大头竟然抓到一只刺猬。他不知从哪听说,把刺猬裹上泥,烤熟了,泥一揭,刺猬的壳就掉了,而且肉味道极好。于是我们就动手,把从家带来喝的水全倒上,和了一大堆泥,裹好刺猬,又找来些枯死的红柳枝,老木甚至回家把点灯用的煤油也提来倒了一些。很快,烈焰腾空,浓烟滚滚。当我们费尽周折,满怀希望地把泥团敲开时,刺猬蠕动了几下,竟爬了起来。气急败坏的我们,一顿乱石,就让它死于非命。
起初我们把精力全放在了刺猬身上,洋芋直接就丢进了火堆,也没像往常一样用土盖住,到最后,刺猬没吃成,洋芋烧得也不成功,8个大洋芋,基本上都成了焦炭,每个能吃的还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吃到嘴里一股糊味,难以下咽。
可就这样,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吃得很香。洋芋吃完,二蛋提议,去学校打乒乓球。
回到镇子,天仍是晴朗朗的天,中间钉着一颗白亮的日头,湛蓝的天穹下稀稀疏疏地缀着些乌白的云团,云团间,不知怎么突然便落下些雨滴子来,雨不密,却有黄豆大小,砸得林带里的叶子、还有树上挂着的各色塑料袋“沙沙”直响,像是喊疼;砸得林带里的麻雀“叽叽喳喳”不停抱怨;砸在马路上,一下就是一个麻钱大的湿印;砸在浮土路上,一滴雨便是一个蚕豆大的坑,还要浮起一小股烟尘。
看着晴朗朗的天,我们几个一下便兴奋了。七角井雨是极少的,有时连着几年也见不着,下得再久也不过十几分钟,往往连地皮都打不湿。更何况,天上还有这么好的太阳,不光是我,他们三个一定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太阳雨。
确实稀罕。
“小雨小雨快下大,地上的娃娃不害怕。”大头最先喊了起来,一边喊一边敞开衬衣,向前冲去,好像这样就能多淋几滴雨,多占些便宜。我们三个嚷着,在后面追。
很快便到了篮球场前,穿过林带,再往前,便是大名鼎鼎的“中南海”了。
我们正向前跑着,喊着,篮球场旁边林带忽然窜出几条人影,都是小伙子,年纪比我们大得多,看上去却比我们还要兴奋,也在雨中疾奔。
但很快我便发现了异常,那4个身影,前面一个白衬衣显然在逃,想躲过后面3个黑T恤的追赶。他两条长腿撒开,步子迈得老大,很快便穿过篮球场,眼看前面便是马路。离那么远,我似乎都能听到他急促的心跳、粗重的喘息。
可是,到了马路边,那个奔跑的身影就跟中了定身法似的,一下子停了下来。
我们四个这时早就停住了脚,一起看热闹。只见,白衬衣前面的马路上,不知从哪又冒出来5个黑T恤,成扇形排开,朝他围过去。
我瞪大了眼睛,虽然离得远,可那5个黑T恤中的一个,看身材、看走路姿势,不用走近我也知道,那是哥哥。这段时间,准确地说,是从他的表白被孟月拒绝以后,他在家变得更加沉默,烟也抽得更狠了,一个多月工夫,右手食指、中指似乎已经染上了爸爸这个老烟枪手指上才有的那种黄。
他很痛苦,这我知道。
等我们几个凑过去的时候,8个黑T恤已经把白衬衣围在了篮球场边上,而白衬衣鼻梁上架着的一副近视镜,端端地正好对着哥哥的脸。
“早就警告过你,再不准缠着孟月,你他妈欠打是不是?不听话。”哥哥身边一个长头发似乎是跟那副眼镜有仇,手指着一块亮亮的玻璃镜片,骂道。而他的话也让我一下子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我没缠着她,是她让我去,给她讲题来着。”白衬衣看着眼前气势汹汹的几个人,低声咕哝着,似乎有些怕,但又不服气。
“你他妈还不承认。告诉你,以后再敢缠着我兄弟的马子,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长头发的手指头直接戳到了镜片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哥哥也开了口,声音不高,却显得很认真。
白衬衣嘴巴张了几下,似乎看出哥哥没有动手的意思,一下子镇定了很多,“我知道你喜欢她。你放心吧,她根本就看不上我。”这句话就像一条鱼一样,从他嘴里游了出来。他的话让我的心一阵轻松。但紧接着,又一条鱼游了出来,“不过,你嘛?她就更看不上了。”
“你个王八蛋!”这下,哥哥身边长头发才收回来的手一下拍在了白衬衣头上,拍篮球一样。
白衬衣身子一晃,往后退了一步,眼睛仍看着哥哥,“就算你把我打一顿,打趴下,她就能喜欢你?”
这大概也正是哥哥所担心的,他脸沉着,没有开口。
“再说了,你把我打一顿,我去派出所一告,你不光要蹲黑房子,还得赔钱,你自己觉得划不划得来?”说到这,白衬衣脸上已经有了笑意。
他的话说得我的心一惊,确实,如果哥哥真的把他打了,他去派出所报了案,那哥哥肯定会被抓走,家里还得给他赔钱。想想,是有些划不来。正想着,下嘴唇一凉一麻,正好被一颗大雨点砸上,我一抿嘴,微微的有些咸有些涩,这还是我第一次尝到雨水的滋味,还是罕见的太阳雨,跟七角井的水质很像,跟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七角井人的命运也很像,这也是那场雨,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白衬衣话音刚落,紧接着是“噢”的一声惨叫,我忙定睛细看,只见哥哥一只拳头才收回来,另一只拳头又已经落到了他脸上。白衬衣想往后退、想躲,可他身后也是人,将他堵着,让他无法闪躲逃开。
一会工夫,白衬衣脸上已经挨了四五拳。
“行了、行了,再不能打了,把人打坏了也是个事。”哥哥身边几个人一起动手,却是拦住了他,长头发两只手捉住他一只手,劝。
“你他妈的。今天来,本来没想收拾你,你他妈还敢吓唬我,打的就是你。”哥哥一只手指着白衬衣,嚷着,还想往前冲,却被身边几个人拦的拦、抱的抱,无法挣脱。
再看哥哥对面的白衬衣,眼镜已经掉了,鼻子上估计也挨了拳,鼻血直淌,手捂都捂不住,将整张脸糊得血红,连地上、白衬衣上也滴了许多血。刚开始他还只是想把血止住,后来才意识到打他的哥哥已经被人拦住,想明白了,一抬腿便跑。
混乱中没人拦他,白衬衣一会儿便消失不见了。
当天中午,哥哥被镇派出所的人带走。了解了事情前因后果的爸爸妈妈下午便带着钱和一大兜吃食出了门。
第二天上午,哥哥重新回到了家。算一算,他在派出所前前后后呆了还不到20个小时。从派出所出来,哥哥还是哥哥,虽然看上去有些疲惫、委顿,但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出多大变化;可事实上,经过那20个小时,他变了,整个人都变了。
哥哥不说,我无法想象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总之,那以后,哥哥虽然还是不爱学习,却老实多了,再不惹事了,跟他那帮朋友也慢慢疏远了。而且,他还再三劝我要好好学习听大人话、最好一辈子不犯事、不进派出所。我得承认,虽然我并没有把哥哥的话全都听进去,但多少还是受了些影响,直到今天,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好人。
两年后,哥哥技校毕业进了镇化工厂,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工人,并于三年后与一个长相很普通的女孩子结了婚,很快又有了孩子。
哥哥的生活平凡得出乎我的想象。
过后我常想,如果没有那一年的那20个小时,我们兄弟的生活很可能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好是坏?我猜不出。
责任编辑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