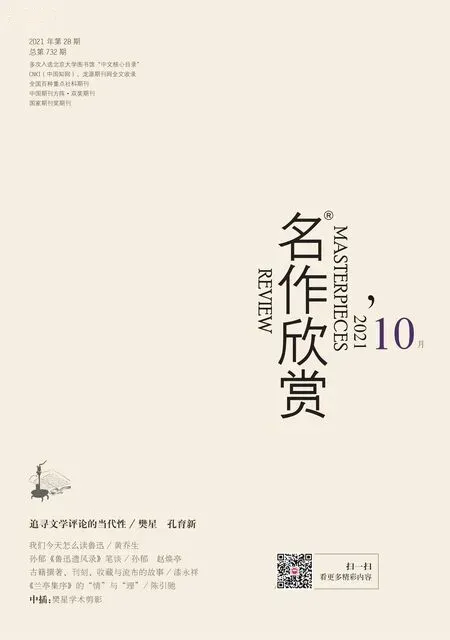题旨正误,意蕴重彰:说《关雎》
北京 李山
重庆 刘书刚
题旨正误,意蕴重彰:说《关雎》
北京 李山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是中学语文各种版本教材的必选篇目。对《诗经》各个层面的解读,两千多年来从未停止。然而正因为它多解,也就为人们的多元理解提供了可能。在语文教学层面,对《诗经》解读到什么程度,同样值得思考和关注。本期推出三篇由高校学者撰写的关于《诗经》不同篇目的解读文章,以期为语文教学提供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开阔的思路。——编者
《关雎》被现代人视为“爱情诗”。本文采用欧阳修“据文求义”法,从诗中“君子”“淑女”称谓及篇章中出现的乐器两方面反驳了这一流行说法,认为诗篇为周代婚姻典礼的乐歌。诗篇主题确定,有助于理解诗篇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
《关雎》 据文求义 婚礼乐歌
自从“诗三百”成为儒家经典即成为《诗经》后,就有了各种解读。汉唐经学有经学的解读,宋明理学有理学的解读,清代朴学有朴学的解读,近代自然又有本着各种观念的多样解读。于是,总有一个问题萦绕笔者心中:今天的人又应怎样解读《诗经》?把“三百篇”这样的经典当成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体系论据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有害无益。就《诗经·关雎》篇而言,从汉代直至今天流行的说法,都有“先入为主”的弊端。也就是说,都无视诗篇自身透露的信息。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今天读《诗经》,应该重新从欧阳修《诗本义》“据文求义”的阅读主张做起。其大要是:解释前先精研《诗经》文本,其他相关的解说,不管其立说者有多大权威地位,也得先过文本本身的文脉义理这一关,合则取,不合则去。在经学重“家法”“师法”的传统势力下,欧阳修能提出这样的解经主张,胆识非凡。然而,今天要“据文求义”,关键倒不在胆识,而在克服因循守旧、炒冷饭不觉难为情的荒怠。
具体做法呢?以个人肤浅经验而言,要“据文求义”。盯着文本是首要的,然而仅此还不够。在考古发达的今天,我们有一个幸运,就是可以读到、看到孔夫子和汉宋大儒见不到的出土文献和相关器物。结合传世文献,深研这些文献和器物,尽力溯源诗篇的时代,尽力深切地感受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氛围、人文情调、文化精神,然后“据文求义”,庶几能对《诗经》篇章的主旨有更为切近的理解。这不是为新而新,实在是只有这样,才能经由《诗经》这样一部民族文化创生时期的经典,把握自己文化的根脉。笔者相信,只有如此,《诗经》的价值才会真正得到彰显;只有如此,《诗经》才会贴近当代读者。
本文以下关于《诗经·周南·关雎》篇题旨及含义的讨论,就是想做点这方面的努力。
“爱情”说是误解
《关雎》位列《诗经》三百篇之首,最需要“据文求义”来纠正历来各种误解。西汉时期的儒生,说《关雎》是“刺康王”,即讽刺西周建立后第三代王周康王的。东汉时期又流行另一种说法:《关雎》是赞美后妃之德的。所谓后妃,就是周文王妻子太姒。两种说法影响持久,却都让人有“丈二和尚”之感:诗篇哪有康王的影子,哪有太姒的痕迹?可是,西汉时期经学家说“刺康王”,是因为他们把《诗经》认作了可据以干预现实、纠正当权者的大经大法;其“康王”说,或许还透露了一点有用消息,即诗篇或为西周早期作品。至于东汉时的经生,把《诗经》的一些篇章尽量往古老里说,是其明显的偏好。《关雎》被他们说成是歌颂周文王之妻太姒德行的篇章,又与他们用经典为万民树立典范、法度的学术取向相合。古人的说法,就先谈到这里,下面说说现代人对《关雎》的误解。
现代误解与古代有什么不同?一言以蔽之:古人的误解在其以“美刺”说此诗;现代的误解,却是由爱情至上的心态弄出的新花样。今人各种注本,当然包括各种教科书,解释此诗几乎众口一词,认定《关雎》“是一首爱情诗”。曾见过一个选本还说此诗是写一位男子“偷偷爱上”一位淑女的。真能抖机灵!不过,这样理解倒也不是找不到依据,他们是从诗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等句子来立论的。一位男子因思念淑女,弄得寝不安枕,翻过来、倒过去地在床上折腾,在一些现代人看来,不是坠入情网、为情所困,又是什么?爱情说以此得立。然而,单看上述句子,的确如此,可是,据此就说诗篇是“爱情”之作,却是十足的断章取义、“现代化”古人。
《关雎》为婚礼乐歌
何以这样说?首先是篇中的人称形态不对。篇中“君子”“淑女”对举,明显是旁观的第三者才有的语态。试想,在一个群体里,就以正值“恋爱季”的大学班级为例吧,一位男同学爱上了班上的某位美女,若他写诗说:“那位美好的女生啊,是正派男生的好配偶。”不是要被当成精神不正常吗?表达爱意的诗,能用这样的人称语态吗?《关雎》篇以“君子”与“淑女”的人称名谓对举,不是表白爱情该有的称谓。《诗经》中也有传达爱慕的篇章,例如《郑风·褰裳》,其“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可好心看上我?看上我,撩裙渡溱水来找我——的句子,就是“子”与“我”并举的。这才叫传达爱情。这是第一点,即诗中人的称举方式不对。
其次,是篇中乐器不对。诗言“琴瑟友之”,《小雅·棠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都是以“琴瑟”喻夫妻和睦。就现有《仪礼》等关于“周礼”记载而言,一般典礼都有“升歌”,即盲目乐工四位升堂演奏,二人唱、二人以琴瑟伴奏。因此,《关雎》言“琴瑟友之”,也应该暗示的是典礼场合。理解诗篇要看全文,单看这一句,容易把古代男女理解得像今天一些男生,操着吉他对女孩唱“我心中不能没有你”之类的情歌。可是,顾及诗的全篇,“琴瑟友之”就绝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因为诗篇还有下文“钟鼓乐之”的限定。句中的“钟鼓”,是不可再视为示爱乐器的。中国有鼓很早,大汶口文化、山西陶寺文化等遗址,都曾出土过用鳄鱼皮蒙制的木鼓;说到钟,就今天发现的西周最早的钟而言,是三件一套,要敲击成乐,还需要一个悬挂乐器的架子。如此,挟瑟之外还得带着一套编钟,拖一副木架,有这样去向女子示爱的吗?
更关键的是,当琴瑟与钟鼓一起出现于诗篇时,暗示的是一场典礼才有的音乐规模。周代举办典礼,如上所说,堂上一般有目盲的乐工歌唱,用琴瑟伴奏,称“升歌”。同时,堂下的庭院还有乐工奏乐相应和。就《仪礼》记载而言,升歌之后,堂下演奏,称“间歌”。升歌、间歌相应相和,才是一场典礼的歌乐之局。《仪礼》所记之礼等级略低,所以没有出现钟鼓,但是,在《左传》《国语》等文献所记载的列国使者聘问活动中,却是有“金奏”即使用铜钟乐器的。这可以参考王国维《释乐次》的研究。《关雎》先言“琴瑟”,再言“钟鼓”,正是暗示出典礼场合的用乐情形,符合周礼的规制。说起来,对现代学者而言,结合周代礼制,对诗篇文义的推求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难题。然而,被“爱情”“诗经是民歌”之类观念塞满了头脑,是无暇或不屑于去做这样的推求的。也就是说,现代学者解释此诗,在“先入为主”的观念挂碍上,并不比古人好多少。
至此可以说,《关雎》根本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爱情诗”,而是婚姻典礼的乐章。诗篇原本是带着自己使用场合的印记的。不过,笔者设想,这样的理解起码要受如下两方面的质疑:
其一,再回到“辗转反侧”那几句。有人或许要问:你说《关雎》不是爱情诗,那上举“辗转反侧”云云,又是什么?答曰:难道结了婚的夫妻就不需要爱情了?夫妻之间的真爱,一般叫恩爱,是限定在婚姻伦理范围内的。诗篇言“辗转反侧”,也是在婚姻范围内的祝福。而且这祝福还有其生活的针对性,那就是好夫妻难得。请看《史记·外戚世家》开头的议论:“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小心貌)……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配偶、父亲)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贵为君主,尊为父亲,也未必有个好婚姻,司马迁此言,不是好夫妻难得的高论吗?唯其难得,才有诗篇的祝福。因此,上述几句与其说是某个爱恋中人的内心独白,不如说是对“好配偶”这一人生幸福的渴望;或者更准确,是诗人对眼前一对“新人”未来鹣鲽情深的祝愿。
其二,也许有人还会质疑:《礼记》等文献不是说“婚礼不用乐”“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吗?答曰:《礼记》等确有这样的说法。可是,“之子于归”的《周南·桃夭》难道不是嫁女之歌吗?“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的《召南·鹊巢》,不是表送亲的“用乐”吗?《礼记》成书于东方的儒生,时间为战国,周南、召南之地在今河南、陕西,时间总在春秋以前;地域相差数百公里,时间相隔几百年。在《诗经》与《礼记》之间,到底哪个可信,相信是不用多言的。一言以蔽之,儒家文献所说“婚礼不用乐”,应该是东方的风俗,据此否认《关雎》篇婚礼乐歌的属性是很成问题的。
《关雎》的文化蕴含
以上所说,是《关雎》的主题和它的用场。虽然说的是一首诗篇的基本事实,可关系重大。因为诗篇涉及婚姻在当时的历史地位,也涉及古代文化的某些基本逻辑。
那么,婚姻在当时的地位如何?对此,《礼记·郊特生》所言“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礼记·哀公问》所言“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的话,最能道及婚姻在西周时期的重要性。不论是“附远厚别”还是“合二姓之好”,都是说婚姻联合异姓异族的重要作用。西周建国之初,其总体人数少,远远不及殷商遗民。而且,据《荀子》等文献记载,西周封建诸侯七十余,这既是周人诸侯邦国迅速占据当时天下的各个要地的举措,也是周人群体大规模的分散和化整为零,同时,也是与天下众多异姓异族的广泛接触。周人若不想只用武力压制天下其他人群,就得想方设法联合异姓异族。周人实际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与异姓之间广泛地缔结婚姻关系,就是一个不可不选的办法了。在当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血亲意识既普遍又根深蒂固,而利用婚姻缔结这样的方式联合不同人群,正所谓顺势而为,其实是对一种古老观念的推陈出新。由此,一种新的广泛联合的宗法制形成了。
婚姻既然在新的家国社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婚姻缔结之际,举行隆重的钟鼓齐鸣的婚姻典礼,不是必然的吗?如此婚礼上有“关关雎鸠”祝愿夫妻和谐的乐歌,不也是很自然的吗?了解西周特殊的历史背景,阅读《关雎》篇章,才可以感受到它的历史沉重,才可以了解到先民在缔造文明社会时所显示的智慧。由此,《诗经》作为一部文化经典,其记录历史的价值才可被真切地感受到。
历史的事件属于过去,而历史造就的文化逻辑却可以延续很久。如上所说,据《仪礼·燕礼》记载,招待列国聘问使者时,歌唱“乡乐”时第一首歌即《关雎》,是其受重视的表现。因而可以说,婚姻关系的缔结很受当时重视。如此,当我们读到《易传》如下的文字时,才不会感觉突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周易·序卦传》)这就是中国关于家庭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天地阴阳合生万物一样,男女结合才是人伦的开端,才是社会生活的起点。于是,再读《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也容易有如下的领悟:有子所说,不过是在说“好家庭出,好的社会成”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很明显,这样的逻辑,与西方《圣经》上帝先造男人再造女人,男女偷吃禁果而世俗社会开始所呈现的文化逻辑大相径庭。笔者以为,《易传》《论语》的观念,是可从西周重视婚姻缔结作用找到它的历史根源的。
当然,领悟这样一种文化逻辑,实有赖于对《关雎》主题的重新认定。很明显,将《关雎》读作“爱情诗”,其背后所涵藏的文化意蕴,是会黯然不彰的。
作 者: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工作,致力于《诗经》研究。有《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建构》等专著。
重庆 刘书刚
《豳风·东山》选择了一个极具情感浓度的时间段落,抒写的是诗人行役结束、踏上归途之后的种种情绪,对于家园的想望构成了《东山》一诗的核心情绪。本文以独特而细腻的体悟方式,将诗中幽微的情愫进行了诗意化的描摹。
《东山》 行役诗 家园想望 诗意描摹
对于朝代的更替而言,以暴易暴几乎无法避免,周王朝确立其统治即与一系列战争有关。此后,周室也与其周边部族如犬戎、淮夷之属,处于不断的摩擦、争斗之中,这使得与战争相关的行役诗,成为《诗经》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豳风·东山》即是一首典型的行役诗,按照《诗序》的说法,它与周公东征伐淮夷、奄国的历史事实有关:“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孟子》中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记载,诗中之东山与孔子所登之山被考证为同一座山。诗中“于今三年”一句,也与周公东征的历史相吻合,所以,《诗序》为此诗提供的写作背景并没有遭到太多的质疑。但《诗序》为诗歌所认定的作者则饱受诟病。依其意见,此诗是大夫为赞美周公之德,代出征将士述其所见所思而作,这显然太过迂曲。所以,崔述《丰镐考信录》中“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的说法就得到了更多的认同:此诗本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