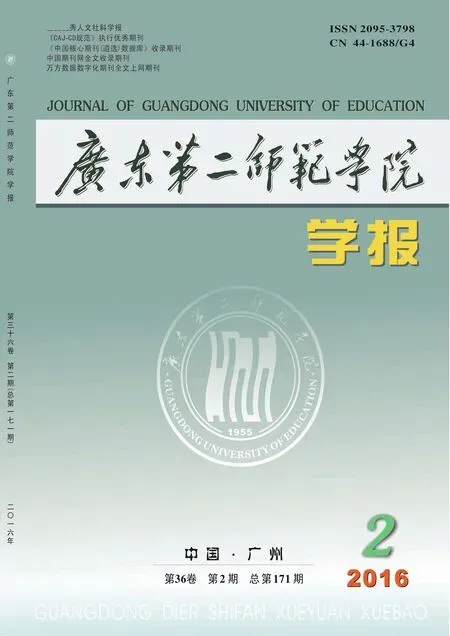乐观主义对大学新生压力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袁立新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3)
乐观主义对大学新生压力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袁立新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3)
摘要:以163名大学新生为被试,使用纵向研究设计考察乐观主义对新生的抑郁变化的影响及对压力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与悲观者相比,乐观者在学期初和学期末两次测量的压力知觉和抑郁都较低,但分层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初始的抑郁水平及压力知觉的影响后,较高的乐观主义可以预测学期末较高的抑郁水平。同时,乐观主义对大学新生学期末的压力知觉与抑郁水平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乐观者更容易受压力的影响而导致抑郁情绪增加,而悲观者的压力知觉与抑郁的关系不显著。
关键词:乐观主义;压力知觉;抑郁;大学新生
一、引言
乐观主义是指个体的一般结果期待倾向[1]。乐观者倾向于积极正面地评价事件的发展,认为未来的结果是积极的;而悲观者倾向于消极负面地评价事件的发展,认为未来的结果是消极的。相对于特定情景与事件的结果期待倾向,乐观主义反映着个体稳定的素质特征,具有跨时间、跨情景的稳定性[2]。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乐观主义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在健康心理学领域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们相信,乐观主义与个体的心理适应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乐观主义者要比悲观主义者有更好的心理适应[3]。过去的研究发现,乐观主义与生活满意度、积极的情绪和自尊等有正相关;相反,悲观主义与抑郁症状、负向的情绪有正相关[2,4,5]。一些研究者使用纵向研究设计考察了乐观主义对个体的抑郁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初始抑郁水平及一些相关变量后,乐观主义对个体未来的抑郁状况仍具有预测作用,乐观主义有利于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3]。有人对56个有关乐观主义与心理适应关系的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表明乐观主义与应对、生理症状和消极情感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抑郁情绪的关系最为密切、稳定,效应量达到-0.46[6]。
一些研究者深入探讨了乐观主义对抑郁的影响机制,发现乐观主义可以通过调节压力的作用而保护个体免受抑郁损害。Chang等人对青少年、大学生、年轻成人以及年老成人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在不同年龄人群里,乐观主义对压力与抑郁关系都有调节作用[7-9]。具体而言,乐观可以缓和与减轻压力对个体抑郁的不良影响,保护心理健康,起到压力缓冲的作用;而悲观可能会使个体更容易受压力的不良影响,使个体的抑郁情绪恶化,成为压力与心理适应的易损因素。
是否在任何情况下乐观都有利于心理的适应而悲观都不利于心理适应呢?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反的证据。Norems、Cantor的研究表明,个体对未来有不好的期待未必就是坏事[10]。他们认为,防御性的悲观主义可以保护个体少受焦虑的影响,从而使用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应对,有效地面对压力的挑战。Tennen、Affleck更提出了乐观易损的假设(vulnerability hypothesis),认为乐观未必总是与较好的身心适应相联系的,当外部环境非常不利时,对未来的乐观可能会不利于个体的适应[11]。Chang、Sanna对大学生的研究[12]也支持了这种假设。该研究发现,乐观主义对持续压力与抑郁的关系有调节作用,虽然乐观者要比悲观者有较低的抑郁,但乐观者要比悲观者更容易受持续压力的影响而导致抑郁。
但过去的研究仍存在下面的不足:首先,有关乐观主义对压力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的研究都采用横向的研究设计,只能考察乐观主义对压力与同时测量到的抑郁的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不能考察乐观主义在个体未来抑郁的变化中是否也具有压力调节的作用。其次,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如当外部环境非常不利或者受持续压力的影响时,乐观可能会不利于个体的适应[11-12]。在面对危机或者是新生活、新环境的时候,乐观主义对个体适应的作用如何呢?过去,研究者们对乐观主义在一些严重病患(如乳腺癌[13]、冠状动脉手术[14])的作用有所研究,但对乐观主义在个体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如升入大学)中意义的研究较少。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从广州某高校中抽取6个班的163名大学专科一年级新生为被试。其中男生53人,女生110人;最小年龄18岁,最大年龄22岁,平均年龄19.46±0.85岁。在测验前征得他们同意参加两次调查(个别不同意的学生没有参加测验),第一次是在学期初(开学第2周),第二次是在学期末(第16周)。
(二)测量工具
第一次对学生测量了乐观主义、抑郁和压力知觉三个变量,第二次只测量抑郁和压力知觉两个变量。也就是说,除了乐观主义只在第一次测量,其他两个变量都测量了两次。
1.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
采用作者修订的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16]来测量学生的乐观主义倾向。该量表是在Scheier与Carver的生活取向测验修订版(LOT-R)的基础上加入Mehrabian的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MOP)的部分题目修订而成。量表含有11个项目,包括五个正向描述项目和七个反向描述项目,采用1~5分计分。计分时把反向题目的分数反转过来,高分代表乐观,低分代表悲观。在本研究中,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1。
2.Beck 抑郁问卷(BDI)
采用Beck抑郁问卷[17]来评估学生的抑郁。BDI由21个“症状—态度类别”组成。每个类别都有4级描述,计0-3分,总分范围是0-63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由于很多学生没有填答第21题(有关性欲情况的问题),所以只计算前面的20个题目。本研究中,BDI在第一次测量的alpha系数为0.79,第二次测量的alpha系数为0.86。
公司技术优势明显,注重研发投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技术领先的系列化产品。2015年至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从970.51万元激增至2515.12万元,增幅达159.15%。2009年以来,上机数控连续多次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且拥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公司的研发能力主要体现在强大的整机设计能力、一流的数控技术开发能力、先进的核心精密部件制造技术和丰富的新品研发经验。
3.压力知觉量表(PSS)
由Cohen等人编制[18],该量表主要测量个体在过去一个月内所经历的主观压力。本研究选择10题版本的PSS,包括6个危机感受描述项目和4个积极感受描述项目。每个项目采用1-5级计分。本研究中,PSS第一次测量的alpha系数为0.79,第二次测量的alpha系数为0.70。
(三)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由研究者指导被试填答问卷。所有被试都是自愿参与的,第一次(T1)是在开学第二周进行,第二次(T2)是在学期的第十六周进行,两次施测约相距15周。两次测量的数据采用SPSS10.0进行管理与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乐观主义、压力知觉与抑郁的关系
两次测量的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平均分、标准差列于表1。由表1可以发现,乐观主义与压力知觉(T1)和抑郁症状(T1)及压力知觉(T2)都有显著的负相关,但与第二次测量的抑郁症状(T2)的相关不显著。两次测量的压力知觉和抑郁之间都有显著的正相关。

表1 乐观主义、压力知觉和抑郁的平均分、标准分和
注:*P<0.05,**P<0.01,下同。
(二)乐观者与悲观者在压力知觉、抑郁的差异
以乐观主义的平均分为分界点,把学生分为乐观者和悲观者(一般情况下是用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极端组的分界点,但本研究的被试相对较少,所以以平均分为分界点),比较两组学生在两次测量中压力知觉及抑郁的差异,结果见表2。

表2 乐观者与悲观者在压力知觉和抑郁的差异
从表2可发现,虽然乐观者第二次测量的压力知觉和抑郁都比第一次测量有所增加,悲观者则相反有所下降,但仍然与预期一致,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测量,乐观者都要比悲观者有更少的压力知觉和抑郁。乐观者在学期初和学期末两次测量的压力知觉和抑郁都有所上升,而悲观者两次测量的压力知觉和抑郁都有所下降。
进一步的配对t检验结果表明,乐观者在两次测量的压力知觉(配对t(71)=-1.505,P>0.05)和抑郁(配对t(75)=-1.078,P>0.05)的差异都不显著;而悲观者在两次测量的压力知觉(配对t(68)=2.591,P<0.05)差异显著,抑郁(配对t(68)=1.844,P>0.05)的差异不显著。
(三)乐观主义对压力知觉(T2)和抑郁(T2)的调节作用检验
参照有关研究的建议[19-20],使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在控制学期初学生的抑郁(T1)影响后,乐观主义对学期末的压力知觉(T2)与抑郁(T2)关系的调节作用。在进行回归分析前,所有变量都转换成标准分。以第二次测量的抑郁(T2)为因变量,第一步加入抑郁(T1),第二步加入压力知觉(T1)和压力知觉(T2),第三步加入乐观主义,第四步加入压力知觉(T2)与乐观主义的标准分生成的交互项“压力知觉(T2)×乐观主义”。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抑郁(T1)的主效应显著,可解释抑郁(T2)25%的变异;在控制抑郁(T1)、压力知觉(T1)和压力知觉(T2)后,乐观主义对抑郁(T2)的主效应接近显著(F(1,129)=3.63,P=0.06),可解释抑郁(T2)2%的变异;压力知觉(T2)与乐观主义的交互效应也显著,可以解释抑郁(T2)2%的变异。说明在控制抑郁(T1)的影响后,乐观主义对压力知觉(T2)与抑郁(T2)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考察乐观主义的调节作用,使用回归分析分别考察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压力知觉(T2)与抑郁(T2)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抑郁(T1)和压力(T1)的情况下,乐观者的压力知觉(T2)对抑郁(T2)有显著影响(b=0.53,Beta=0.56,t=5.10,P<0.001);而悲观者的压力知觉(T2)对抑郁(T2)的影响不显著(b=0.17,Beta=0.20,t=1.75,P>0.05)。这一结果说明乐观反而会使压力知觉与抑郁的关系加剧,而悲观则不会。

表3 乐观主义对压力知觉(T2)与抑郁(T2)的调节作用检验
四、讨论
与前人的研究[2,6,9,21]结果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乐观主义与压力知觉和抑郁症状(当时的及四个月后的)都有显著的负相关,乐观者比悲观者体验到较低的压力和抑郁症状。
一些研究者也使用纵向的研究设计考察了乐观主义对个体抑郁水平变化的影响。 Vickers和Vogeltanz对190名大学生的研究[22]发现,在控制初始的抑郁水平、消极情感、积极情感、日常琐事及日常琐事与积极情感的交互效应后,乐观主义仍然对10周后的抑郁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乐观有利于抑郁水平的降低。Brissette等人对大学新生的一项研究[23]发现,学期初时的乐观主义得分可以显著地预测一个学期后大学新生抑郁水平的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却得到了与上述研究相反的结果。本研究发现,在控制学期初的抑郁水平(T1)和压力知觉(T1、T2)等相关变量的影响后,乐观主义对大学新生学期末的抑郁水平有显著的正向的预测,即乐观会导致更多的抑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不同乐观水平的学生在学期初和学期末体验到的压力的变化有关。本研究对乐观者与悲观者在学期初、学期末两次测量的比较也发现,经历差不多一个学期的大学生活,乐观者的压力知觉水平却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而悲观者的压力知觉水平则有显著的下降。由高中升入大学,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很多大学新生在第一学期里都可能会有适应的困难。乐观者在学期初时,更容易带着较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生活,低估了在未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而在经过约一学期的学习生活之后,他们对现实的困难慢慢会有较客观的评价,发现理想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落差,从而体验到更多的压力,并导致抑郁水平升高。而与乐观者相反,悲观者总是认为未来的道路会充满坎坷,困难重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学生活后发现大学生活并没自己想象中那么困难,压力知觉会有显著的降低,使抑郁水平也有相应的下降。
本研究发现,乐观主义与压力知觉(T2)的交互作用对新生学期末的抑郁也有显著预测,说明乐观主义对大学新生未来的压力知觉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乐观者更容易受压力的影响使未来的抑郁感增强,而悲观者学期末的压力知觉与抑郁的关系不显著。这与Chang和Sanna的研究[12]结果一致,支持了Tennen和Affleck的“乐观易损”假设[11]。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乐观者的抑郁水平受期末的压力水平的影响较大,当压力水平较低时,乐观者的抑郁得分非常低,而在压力水平较高时,乐观者的抑郁水平有较大的上升。因此,在第一学期应当加强对新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应大学生活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新生对在大学阶段所面临挑战的心理准备,避免对适应大学生活的盲目乐观;同时,应加强应对压力的策略指导,帮助乐观者有效应对大学生活中的压力,保持较低的抑郁水平。对悲观者来说,他们对大学生活可能出现的问题更有心理准备,因此不容易受压力的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被试只是广州市一所大学的学生,由于学校层次、类型和管理的差异,学生面对的压力及适应也可能会有不同。今后的研究应扩大样本的层面,从不同学校抽取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研究。其次,本研究的样本较小,只有163名学生,如果按照高于(或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的原则来划分极端组的话,会导致极端组的人数太少。再次,本研究只考察了在新生入学后很短(14周)的适应期里乐观主义的影响,对更长时期的影响如何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五、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Tennen和Affleck的“乐观易损”假设。虽然乐观者在学期初和学期末两次测量的压力知觉和抑郁都比悲观者低,但在控制初始的抑郁水平及压力知觉的影响后,较高的乐观主义可以预测学期末较高的抑郁水平。同时,乐观主义对大学新生学期末的压力知觉与抑郁水平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乐观者更容易受压力的影响使抑郁恶化,而悲观者的压力知觉与抑郁的关系不显著。
参考文献:
[1] SCHEIER M F, CARVER C S. Optimism, coping and health: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lized outcome expectancies[J].Health Psychology, 1985,4:219-247.
[2] SCHEIER M F,CARVER C S, BRIDGES M W. 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neuroticism (and trait anxiety, self-mastery, and selfesteem):A reevaluat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67:1063-1078.
[3] SCHEIER M F, CARVER C S. Effects of optimism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Theoretical overview and empirical update [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992,16:201-228.
[4] CHANG E C, MAYDEU-OLIVARES A, D’ZURIKKA T J. Optimism and pessimism as partially independent constructs: Relations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7,23:433-440.
[5] MARSHALL G N, WORTMAN C B, KUSULAS J W, et al. 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pessimism: Relations t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mood and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62:1067-1074.
[6] ANDERSON G. The benefits of optimism: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6,21:719-725.
[7] CHANG E C, SANNA L J. Experience of life hassle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f one is optimistic or pessimistic[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3,34:867-879.
[8] CHANG E C. Doe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8,25:233-240.
[9] CHANG E C. Optimism-pessimism and stress appraisal: Testing a cognitive interactive model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dults[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2002,26:675-690.
[10] NOREMS J K, CANTOR N. Defensive pessimism: Harnessing anxiety as motiv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51:1208-1217.
[11] TENNEN H, AFFLECK 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ptimistic explanations and dispositional optimism[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7,55 (2):377-392.
[12] CHANG E C, SANNA L J. Optimism, accumulated life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djustment: Is it always adaptive to expect the best?[J].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3,22:97-115.
[13] CARVER C S, POZO C, HARRIS S D, et al. How coping mediates the effect optimism on distress: A study of women with early stage breast cance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65:375-390.
[14] SCHEIER M F, MATTHEWS K A, OWENS J F,et al.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recovery from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57(6): 1024-1040.
[15] 杨新宇,李齐全,胡鹤玖.大学新生适应期心理问题的分析与教育措施[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4(3):63-65.
[16] 袁立新,林娜,江晓娜. 乐观主义-悲观主义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研究[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27(4):55-59.
[1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91-194.
[18] COHEN S,KAMARCK T,MERMELSTEIN R. A global measure of perceived stress[J].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83,24:385-396.
[19]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20] 卢谢峰,韩立敏. 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协变量——概念、统计检验及其比较[J].心理科学,2007,30(4):934-936.
[21] ASPINWALL L G, TAYLOR S E. Modeling cognitive adaptation: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oping on college adjustment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3:989-1003.
[22] VICKERS K S, VOGELTANZ N D.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s a predictor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0,28:259-272.
[23] BRISSETTE I, SCHEIER M F, CARVER C S. The role of optimism in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during a life-transi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82(1):102-111.
(责任编辑肖雪山)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ptimism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of Newly Admitted University Students
YUAN Li-x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P.R.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163 newly admitted university students by using a longitudinal methodolog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optimism to depression, and examine optimism as a moderator of the link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higher optimism could predict the higher level of depression when 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perceived stress had been controll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optimism wa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to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Namely, the optimistic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mpacted on stress and then their depression went worse, while for their pessimistic counterpar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optimism; perceived stress; depression; newly admitted university students
收稿日期:2015-12-13
作者简介:袁立新,男,广东湛江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849;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16)02-00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