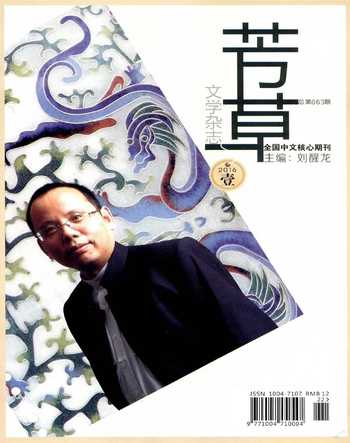卡齐姆叔叔的马儿
法济利·伊斯坎德尔[俄]著 文吉译

卡齐姆叔叔有一匹出色的赛马,唤作洋娃娃。几乎每年的赛会它都能赢回些奖项。它尤其擅长一种只在我们阿布哈兹本地出名的长距离奔跑项目——切拉兹。
切拉兹,就是把马匹赶进湿滑的地里迫使其滑着跑。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能跌倒也不能停步。留下最长划痕的那一匹赢得比赛。这种比赛项目有可能源自于山路崎岖的生活环境,马匹在落脚困难的时候可以滑行的能力显得尤为珍贵。
我无法细细列举它的气质性格,何况在相马方面我完全是门外汉。我从马背上离开,却也没开上小汽车。
洋娃娃的身形体态我还清楚记得。它是一匹不算高大的红棕色马,身体修长尾巴也长,额上有一抹白色。概而言之,从外形上它和一般的阿布哈兹马并无太大区别,但既然它获过那些奖项,加之名声在外,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白天它在萨比特谷地或者在那周围吃草。傍晚时分会自己踱回家,静静立在大门旁,小耳朵不时地竖起。叔叔抓来一撮盐,边用手喂给它吃,边轻声说着些什么。洋娃娃小心翼翼地蹭上他的手掌,鼻孔轻拂几下,镶嵌在眼白中的紫罗兰色马瞳吓人地斜视着,就像遍布血红色经线的小小地球仪。收割玉米的时节,叔叔会把玉米秆收集起来,到了晚上马儿就会嘎吱嘎吱地大嚼新鲜玉米叶子。
玛尼采婶婶,叔叔的老婆,时不时会抱怨叔叔整日只顾照料自己的马。事情并非如此,叔叔是个优秀的男主人。我觉得玛尼采婶婶只是稍微有点吃马儿的醋,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只能照看母牛和山羊而感到懊恼。话说回来,谁又知道女人到底抱怨什么呢。
偶尔,洋娃娃没有从萨比特谷地回来,叔叔知道后,无论多晚都会系上腰带扛着斧头外出寻找。有时会深夜才返家,下半身沁满露水,如果下雨则是浑身湿透。他坐到火旁边取暖,火光映出线条粗犷又利落的优美头颅轮廓,还有静静张开的十指。他安宁地坐着,要紧的任务完成了——洋娃娃找到了。
大热天里,叔叔会牵它去洗澡。站在齐腰深的冰水里,他给它从头到脚冲洗,梳理鬃毛,挑清刺实和每一根草屑。“苍蝇成堆,”他口中嘀嘀咕咕,从它肚子上刮下一撮厚颜无耻不屈不挠非要停在那里的苍蝇。在水里洋娃娃表现得更加平静。只偶尔焦躁几下,不停颤动肌肉赶走飞虫。
我站在河边,欣赏叔叔和他的马儿。每一次弯下腰舀水,他消瘦身体上的肌肉都会蔓延开去,透显出其下的骨骼。有时候蚂蟥会吸到腿上,他边从水里走出来边随意地扯下蚂蟥,然后穿戴整齐。我们非常害怕蚂蟥,因此从来不敢下河游泳。
洗浴之后,有时叔叔会抱我坐上马背,他则牵着缰绳,两人一马上山回家。小径非常陡峭,我总是害怕从湿漉漉的马背上溜下去,双腿用尽全力夹紧马肚子,两手紧攥马鬃。潮湿的路程并不舒适但总是愉快的,我感受着担惊受怕的喜悦和窘迫。窘迫来源于我觉察到马儿对乘客的厌恶,而这厌恶,我惶恐地认为它并不公平。每当缰绳上的劲儿松开时,它都会回头去咬我的脚,但我时刻警惕着不让他得逞。通常我们就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到达家门口,我翻身爬下马背,心情愉悦又兴奋,因为不仅骑了它,且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地面上。
一次,我们还是如此这般走到大门口,咱们的一位邻居(不知为何特别不讨狗喜欢)突然从院子另一头出现,几只狗向他猛冲过去。
“走开!走开!”叔叔大喊道,但一切已经太迟了。“接住!”他把缰绳抛向我。
我觉得,马儿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早在他回过头来之前我就感觉到了。我拼命攥紧缰绳。它开始频频回头,我已明白要遏制住它就像试图拦住倾倒的树木,绝无可能。它起初快步奔跑,而我在它背上上下颠簸,仍然想要抓紧它。但它变换步伐开始飞驰,平稳又不可阻挡地加快速度,就像倒下的树木那般加速。绿色的东西不断闪现,狂风扑面而来,仿佛在这样的速度下老天都变了脸。
如果不是我的堂兄,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他住在离叔叔家不远的小山头上,听见狗吠声便走出来查看。他看到了我,跑到小路上又是喊叫又是挥舞双臂。洋娃娃在他面前几米处笔挺挺地停下,而我则从它头顶飞了出去摔在地上。我跳起来,惊讶地发现温和的天气又回来了。但突如其来的冲击打断了我的思绪,有什么东西把我掀翻在地上。此时我的堂兄已经猛冲过来将缰绳从我手中夺去,并开始安抚洋娃娃。原来在惊恐之中我一直紧紧攥住缰绳,即使落马之后也没松手。
自那之后,叔叔再未让我骑过洋娃娃,我也再没提起。但这并不代表我对它变得冷淡,相反,我爱之更甚。本该如此啊——它这样的骏马,除了自己的主人谁都不认。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叔叔本人它也不轻易与之。想要给它戴上笼头,叔叔得慢慢地靠近,伸出一只手,讲些温柔好听的,摸到之后再轻轻抚摩它的马肩马背,最后才把铁嚼子塞进它嘴里。如此轻手轻脚慢慢悠悠的动作只有养蜂人开箱取蜜才能与之相提并论。通常叔叔靠近它时,洋娃娃都会后退几步,扬起头撇向一边,全身紧张地颤动着,随时准备以猛力一冲来应对任何不谨慎的动作。仿佛每一次它将自己交到主人手上都伴以羞耻和恐惧。
有时,当我们下到萨比特谷地去摘黑果越橘和桂樱的时候,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它。经常是这个样子,你叫它:“洋娃娃!洋娃娃!”而它伫立在那里用惊异的眼神凝视你。如果试图走近,它就会甩开它那长长的红色尾巴逃跑。一离开家它就完全野化了。还经常这样,在胡桃林里,黑莓灌木丛里或者蕨草堆里猛然传来噼啪碎裂的声音和脚蹄声,人惊呆了:完了完了野猪冲过来了。但从灌木丛里冲出来的是洋娃娃,一团火红色的幻象从身旁飞掠而过,只瞬息间马蹄声就在遥远处归于寂静。
“看见洋娃娃了没有?”叔叔见我们从萨比特谷地回来便问道。
“看到了。”我们齐声回答。
“好样的,小伙子们。”他满意地说,仿佛这就是我们在谷地里唯一能做到的事,至于其他,都不值得一问。
家里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叔叔对马儿的深爱,哪怕他自己从未说过只言片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野性难驯,但洋娃娃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叔叔。每天晚上它立在大门口,只要听到他的声音便会立刻转头观望,注视……
有时候叔叔会在白天里抓住洋娃娃,侧身骑上马背——两腿放在同一边。这是他年轻勇猛时学会的一招。这种无声的滑稽戏十分逗乐,而当他一贯刻板的脸上猛然冒出一个微笑时更是尤为好笑。看得出他心情不错,这好心情则来源于他马上要踏上的遥远又有趣的骑行旅程。叔叔把洋娃娃拴在苹果树上,将罐子灌满水,刮了胡子还洗了头。玛尼采婶婶开始抱怨,但他充耳不闻地匆忙披上毡斗篷,抱怨声就像冰雹粒子一样砸在毡斗篷上被崩飞。
他甩开腿跨上马鞍,安坐妥当,一根神气的短鞭握在手中,身形匀称,健壮有力。他在院子里稍作停留,下达了家长在临行前的最高指示,而后灵活地俯下身自己打开了院子大门,御马快步离去。此时此刻,你无法不为他着迷。只有婶婶继续唠叨着,装作不听他讲话也不去看他一眼的样子,但最终还是无法忍住。手中时而拿起筛子,时而又忘了木柴捆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她莫名地忧愁,但所为何事——我们不得而知。
……战争越来越近。山口那边的某处已然有战斗发生,如果仔细倾听的话,能听见极远处的炮群似已疲倦的轰隆声。村子里几乎没有年轻小伙子和男人剩下了。
有一日,村主任宣布要临时动员所有的驴子和马匹向隘口运输弹药物资。起初拉走了所有的驴子,而后确定了牵走马匹的日子,以便大家把马拴回家中准备停当。
前天夜里叔叔把洋娃娃赶进了院子,到了第二天早上没有放出去。同一天,邻村远近闻名的驯马师穆斯塔法来到家中。来者身材矮小,双眉短粗,一双警觉小兽似的眼睛从眉下向外四处打量。
我们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为了对他的来访表示尊敬,家里杀了一只鸡,婶婶还端上来一瓶樱桃酒。
“动员令听说了吗?”他问道。
“当然。”叔叔回答。
“你怎么办?”穆斯塔法一舔嘴唇,努力忍住不在叔叔之前举起酒杯。
“你自己看嘛,”叔叔朝院子撇撇下巴,“还不是得送去。”
“糊涂啊,”驯马师不带停顿紧接着说,“敬你的房子,敬老的小的,敬全家人!”
“谢谢……”
一饮而尽,而后二人不声不响地夹菜。叔叔一如往常的无精打采,满脸索然无味。客人则恰恰相反,逍遥快活。我们这些孩子坐在一边,边偷听边贪婪地望着客人把鸡身上最好的部分消灭殆尽。
“我知道糊涂,但没别的法子……”
“所以我今天来找你——给你个法子……”
“没用,谁都知道我家的洋娃娃……”
“不是我说你啊,但……”
“敬你的家人,去了那的,都能回来!”叔叔朝隘口方向一昂头。
“谢谢你,卡齐姆。命由天定,有这命的——能回来,没有的——又能怎么办呢……”
复饮一轮。客人油腻的下巴又开始忙碌起来。
“你想想,即便马能还回来,也不是原来那匹了。”
“能怎么办呢——动员令,法律。”
“据说他们能驾驭得了我们的马?他们连自己的马都招架不住。”
“能怎么办呢……”
“法律要的是马,又不是洋娃娃……”
“但大家知道……”
“款待款待,大家都会闭嘴的。”
“穆斯塔法,这个你瞧见了吗?”叔叔捏起一块白色的干酪。
“看见了,”穆斯塔法说,浓眉下的小眼稍显不安。
“你知道,我把它吃进肚子里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吗?”
“你想说什么?”
“毕竟我们想吃的是又白又干净的奶酪,否则就胃口全无。这件事上也是如此,穆斯塔法。”
“讲起话来像毛拉一样,但你还是让马去送死。”
“我知道,但这样更好。”他又出乎意料地苦涩地补充道:“我们的小伙子们半截身子都扎进了这该死的烘炉里,何况马儿……最好为他们干一杯。”
“当然,干一杯,但法令怎么说的?那上面说……”
我至今记得,叔叔苦楚的话语是怎样毫无防备地刺痛了我。大概是因为往常他的话总是冷酷无情冷嘲热讽的。正是如此,他极少微笑,而一旦微笑——便是点燃的喜悦,就像黑夜里擦亮的一根火柴。
吃饱喝足,他们洗净油手走到院子里。卡齐姆叔叔,高大、苦闷、忧愁,而一旁的驯马师——矮小、容光焕发,硬邦邦的后脑勺油亮泛红。
叔叔逮住洋娃娃给它套上笼头。穆斯塔法走上前去牵马,然后毫无缘由得,他开始把它向后推。我呆立当场,心以为他是醉了。而后他猛然附身抬起马前脚。洋娃娃响鼻一哧,伸长脖颈便咬,但他随手便推开了洋娃娃,仍旧迫使它抬起了前蹄。他趴在地上,喘着粗气逐一检查四只蹄子,先看前脚,再看后脚。当他走到马背后时,我心想:他要为自己的无耻行径付出代价了。但马儿不知为何没有尥蹶子踢他,甚至在他抓住它的尾巴擦净后蹄以便查验马蹄铁的时候,它也没有蹬他,却只是一直颤抖。
“前掌得重新钉了,”他起身说,“去马鲁哈那条路你知道的……”
叔叔从厨房搬来工具箱。“马儿又不是他的,为什么他还要帮着张罗?”我边瞧着穆斯塔法边想,试图去揣测驯马师复杂的心理。
洋娃娃被牵到苹果树的树荫下,那里拴着穆斯塔法的马。
“你们家的苍蝇是怎么回事——我的马都快被叮死了!”穆斯塔法看了一眼自己的马,是又惊又气。
“家里的羊招来的,”爷爷说道。他过来搭把手。
叔叔轻轻握住洋娃娃嚼子旁的缰绳,稳住它。小个子驯马师站在马肩旁边,抬起一只马蹄,开始从马蹄铁中起出生锈的铁钉。他在箱子里刨了一会,变戏法似的找出一把马掌钉,放到口中抿住。而后,他一次取出一颗,只两三下便敲入毫无抵抗的马蹄中。每敲击一次洋娃娃便退缩一下,波浪似的颤抖传遍全身,像石子掷入水中泛起涟漪。
“洋娃娃啊,”叔叔同马儿说话以便安抚,让它知晓正在进行的工作。不知道为何,穆斯塔法弃用了已经在石头和干草上磨亮的第二只马蹄铁,而代之以叔叔箱子中一只新的,是生了锈的马蹄铁。在他做活时,洋娃娃的尾巴猛扫他了几次。每一次他都抬起头来,因为钉子碍住了嘴只能气愤地含糊几句,仿佛没有料到它如此幼稚的行为。
“现在随便你怎么蹦!”他把锤子扔回箱子,直起身说道。叔叔单手抓起箱子,似乎不愿将它提回屋里,即使从背后也能看出他的状态很糟。洋娃娃和穆斯塔法的马拴在了一起。
取下来的马蹄铁像银子一般流光闪耀,我挡住它,想一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捡起来,但爷爷一把将我推开,自己拾起马蹄铁。他转身便将之钉在大门上——能带来幸运。门上已有另一只马蹄铁,磨损得相当厉害,而这一只即使在背光处也银光闪闪。大概爷爷觉得是时候转转运了。
穆斯塔法要走了。叔叔为他牵住马嚼子旁边的缰绳,驯马师两手稳稳攀住吱吱作响的马鞍,忽然停下来。
“要不,再把鞍子给它重新备一下?”他说道,那样子就像要扯下自己的马鞍再将它装到洋娃娃背上。
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悄无声息地跌进草里溜走,洋娃娃浑身一个震颤。我一直盯着苹果,想一会去捡起来。它滚到篱笆旁边的草丛里停了下来。
“不用了,穆斯塔法。”卡齐姆叔叔思忖片刻,说道。
穆斯塔法跳上马背。
“再见。”他说着,用短鞭驱动自己的马。
“一路顺风。”叔叔直到马儿趋步向前才松开手中的缰绳,,以免显得主人在逐客。
穆斯塔法在道路转弯处隐去不见,叔叔转身进屋,而我还惦记着苹果。走到篱笆旁边用脚去扫开草丛,苹果已然不在那里。我起初还感到奇怪,直到看到了一头猪。它慢慢悠悠地在篱笆的另一侧来回溜达,仔细倾听着苹果树叶的沙沙声。看来,是它把嘴伸过篱笆的间隙偷走了我的苹果。我拿石子扔它想将它赶走,但是徒劳无益。它就站在不远处,与其说是在防范我不如说是在留意苹果,让人觉得十分懊丧。
一整天叔叔都卧在房间里抽烟。消瘦修长,盯着天花板吞云吐雾,辗转反侧。玛尼采婶婶不敢去打扰他,只得一个人完成所有家务。她不时打发我们去看看叔叔在做什么。我们穿过菜园子,扒在小窗上观察叔叔。他什么也没干,只是躺着抽烟,盯着天花板,还是那样伸长了身子翻来覆去。
“他在干什么?”我们回到厨房时婶婶问道。
“没干什么,就是抽烟。”我们回答。
“好吧,让他抽吧。”她说道,飞快地给自己的卷了一根纸烟点了起来,同时打量着门口,免得让爷爷看到。
傍晚时分,来了一位村苏维埃的小伙子。他像那些习惯于闯进别人家院子里的人一样,用棍子轰走看门狗,走进了厨房。所有人都知道他为何而来,而他也知道大家对他的目的心知肚明,但是为了体面,他还是用各种胡言乱语做了开场白。虽然婶婶暗中派人去喊,但叔叔仍『日不肯露面。最终,小伙子做出一副假惺惺的悲痛神情挑明了自己的来意。以同样假惺惺的悲痛神情他拽起洋娃娃的缰绳,并将它从院子里牵走。小伙子将缰绳拉直到极限,仿佛是在努力扩大自己和马之间的距离,沉默地向我们阐明马的事和他无关,要怪就怪法令去。然而,大概因为他做得太过明显,以至于我们这些孩子并不相信。我们觉得在从家到法令那里的途中,他会揪点什么东西下来留给自己。
他前脚刚迈出院子,我们就跑进菜园躲进玉米地里,暗中跟踪他。果不其然,他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大石旁停下,爬上去,猛地跳上马背。洋娃娃火冒三丈,但却无法将他掀翻在地。我们这里的好骑手实在太多了。
“动员令!”他大喊一声,既非吆喝马儿也不是为自己做无罪辩护,随即御马飞驰而去。到村苏维埃还有五公里路程。我们一直站在那里,直到马蹄声听不见了才默默地回到院子里。
几日后,叔叔被征去参与木材木料的贮备工作,而邻居家的母牛在萨比特谷地里被熊猎杀了。它一直嗥叫着,似乎是在寻求帮助,但没有人敢下到谷中。我们聚集在谷地边缘,骇人的嗥叫声压抑着谷中的黑暗和我们心头的恐惧,持续了几个小时之久。这之后叫声开始拉长变弱。奶牛的呼救声仿佛不再企图挣脱逃向上方的人群,而是随着血液向谷底流淌。再然后,叫声变成细微的、比嗥叫更加疹人的呻吟。人们十分固执地聆听这声音,努力从其他夜的声响中将之分辨出来,不愿放过它,仿佛敏锐的听觉可以延缓死亡瞬息的来临。最终一切沉寂下来,而从遥远的隘口那边开始传来战争的沉闷轰隆。又过了几日,牲口从母牛被猎杀的地方经过,都伸长鼻子嗅嗅血迹而后大声嗥叫,仿佛是在为逝去的同伴送别。而后血迹被雨水洗净,动物们都安宁下来。叔叔归来听说此事,在林中设下埋伏并连续蹲守了几日,但熊并未出现。
日子一天天过去。叔叔只字不提马儿,我们也不去让他想起,因为婶婶早就预先警告过了。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供谈资,叔叔变得更加沉默了。经常是院门一响,婶婶抬头望望他的背影,说道:“我们的主人又烦闷了。”
某天早上我第一个起床,因为头一天在树上发现了几枚无花果,隔夜之后应该熟透了。我走到门廊上,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见:大门前立着一匹马。
“洋娃娃!”我惊呆了,大声叫道。
“不可能啊!”婶婶兴奋地回应道,仿佛等待我的高呼已久。
我从门廊上一跃而下向大门口跑去。几分钟后,一家老小都聚集在了大门前。叔叔最后一个出来。他用轻盈的步伐平静地穿过院子,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保持冷静。他在我们面前太过克制,或许他只是觉得现在高兴未免太早。
马儿被放进院子里。它踱了几步,犹豫地停在叔叔面前。他绕着马儿走了一圈,仔细打量着。这时我们才发现,它是如此消瘦和极度疲乏,走动时一窝苍蝇从背上嗡嗡腾起,而后又重新落回背上,好似一群微小的食腐秃鹫。原来是马儿的背上受伤了。
“它遇上了什么人,经历了些什么啊!”爷爷打破众人的沉默,似乎是在为马儿辩护。
“去!”叔叔挥手去驱洋娃娃,它走了几步便停下站住,突然望向叔叔。
“去!”叔叔又一扬手赶它走动,并与它四目对视。
他轻蔑地忽视了马儿背上的伤口,似乎有比伤口更加重要的东西需要注视和倾听。洋娃娃又踱了几步,再次犹豫不决地停下脚步。大家全都沉默不语,马儿仿佛被这沉默吓到了,又望向自己的主人。
“去!”他又是一声呼呵,马儿离开原地挪动几步,绝望地再次停驻。
它不再左顾右盼。苍蝇重新飞回马背扒在伤口上,但是叔叔依旧蔑然无视,仿佛马儿是故意弄伤了背,以便将他的注意力从它身上发生的要紧事件上引开。
“快停下。”爷爷轻轻地说,虽然叔叔什么也没干。
“中了邪,”叔叔疲惫地回答,“垮了……”他转过身走进屋里。
我不明白什么叫中邪,但是能察觉到马儿身上有着可怕的变化。
“难道伤口不会好了吗?”我不愿相信,追着出去干活的爷爷问道。他在苹果树荫中坐下,开始编箩筐。
“关键不在于此,”他说,弯曲变形满是老茧的手指停下动作,双眼凝视着手中的箩筐,思索了一番,补充道:“它的傲气被磨灭了……”
“什么傲气?”我问。
“一目了然,马儿的骄傲。”他心不在焉地答道。
他将篾片横向穿进竖直的不断晃动的木条中,用有力的手指束紧,让箩筐紧实扎密,就像在马肚子上系紧鞍子的束带。
“但是它可以休息啊。”我提醒道,努力琢磨着他话语中的含义。
“于事无补。它身上已经没了神采。”他继续扭转,压弯,拉紧一根根柔韧的新刨平的核桃木条。某种不肯老去的对快乐的渴求被编织进箩筐里。是的,这种渴求一直伴随着他的每一举每一动。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正因为如此,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他才表现得依旧坚不可摧。他具有一个优秀农民和同时是大艺术家的天赋——从工作中寻得愉悦,而不是去等待那常常颗粒无收的虚幻成果。但彼时我仍未醒悟,只是为洋娃娃感到难过。
马儿在院子里养了一个月。我们这帮孩子仍旧相信,等到它养精蓄锐足了就会变回成原来的样子。现在由我们自己带它去洗澡,给它打青草料,为它赶苍蝇,用煤油擦拭伤口。一段时间过后,伤口痊愈了,马儿养的膘肥骏俏。然而它身上的某些东西确实永远地改变了。现在,如果走近把手放在肩背上,它不会再颤抖,而只是静下来仔细聆听。偶尔当它静下来聆听时,会觉得它在试图回忆,却又无论如何无法记起原来的自己。
不久后,爷爷牵着它去了磨坊,因为我们的驴子没能从山口那边回来。后来它被租借给了邻居,叔叔不再骑它,甚至不愿再接近它。洋娃娃依然记得他,听到他的声音便会抬起头来,但叔叔只铁石心肠一般从旁走过,不看一眼。
“你也太无情了!”一天,大家在厨房准备吃午饭时婶婶说道,“哪怕过去看一眼,摸一下……”
“是不是觉得,你比我爱马更甚。”他面无表情地回答,把纸烟凑到火边,吞吐起来。
秋后,洋娃娃被卖到了邻村,换回来五百斤玉米——叔叔家中吃饭的嘴太多,自己种的不够吃。
我们再没见过洋娃娃,但有一次听人提起过。新主人骑它去看赛马,将它拴在马桩上,自己则钻进了人群。冗长的一轮轮赛事中气氛逐渐达到顶点,洋娃娃听到人群的喧哗,马蹄踏地声,闻到躁动的马群的气味,似乎记起了什么。
无论如何,它扯掉了拴绳飞驰入场,一路超越身旁狂奔的骑手们,几乎整圈都跑在最前面,完全忽略身下狂舞的马镫和满场观众的口哨和震耳大笑声。而后,它被其他马匹超过,自己退下场来。
洋娃娃之后,叔叔再未置身于赛马场内。看得出来,岁不饶人,今不同昔。